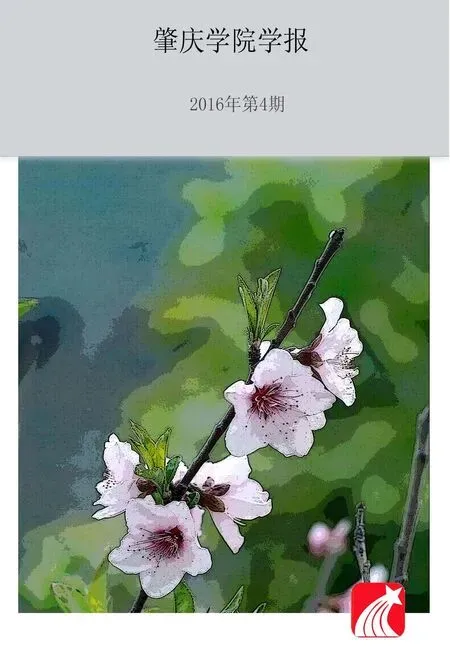幸福感與文學創作的心理驅力
梁沛好
(肇慶學院文學院,廣東肇慶526061)
幸福感與文學創作的心理驅力
梁沛好
(肇慶學院文學院,廣東肇慶526061)
幸福感與文學創作驅力之間,有著緊密的內在關系,構成雙向互動的心理結構。從幸福感的視野看,文學創作動機出于創作主體的各種不幸使然。他們的情感宣泄與升華、需要的渴求與滿足、自我的認知和評判、寫作的目標及其實踐,往往形成一股創作的巨大心理驅力,要在文學這個詩性世界中去尋獲一種幸福感。文學的創作動機不同,作品的層次品位不同,作者從中獲得的幸福體驗也各有層次之別,從而帶給受眾的審美效果也迥然有異。時代呼吁涌現更多抒寫心靈和精神層面的幸福感的高品質作品,去引領大眾的閱讀審美潮流,以提升國民的幸福指數。
幸福感;文學創作;心理驅力
“文學即人學”,其實,“文學也即幸福學”。文學的歸旨是創作主體通過在心理及精神層面上的表達,去探求一條自我及人類的幸福之路。而文學創作本身,也讓作者深刻地體驗到一種幸福感。著名作家張笑天說:“文學,讓我一直幸福著。”[1]當今作家陳應松也談到:“寫作的過程,就是一個不斷幸福的過程。”[2]的確,文學讓世界上古往今來無數藝術家為之一生執著,那就是因為在它里面有著最大的幸福。幸福感與文學創作驅力之間,究竟有著怎樣的內在關系及其心理結構?當今的幸福心理學理論,為這一論題之迷的揭示,提供了科學而重要的理論依據。在幸福感成為一個世界性和時代性的一個熱門話題的文化語境下,從幸福感的視野去探究文學創作的心理驅力及其雙向的關系,更能切合時代和現實去探索當今文學的發展與繁榮。
人的心理結構天生具有一套動力平衡系統,當人體驗到不幸、痛苦時,心理的動力平衡系統中的幸福指數就會傾斜下降。而與此同時,也會產生一種重新恢復平衡的傾向。這之于創作者,就會用寫作這一方式去尋獲積極的情感,從而讓幸福感得以反彈回復。而這個機制運作的內驅力,就構成了文學創作的心理驅力。幸福心理包括情感、需要、認知、行為等四大構成要素[3]1,這幾方面會直接影響和激發作家的創作動機,促使寫作行為的發生;反之,在創作過程中,又坦然地展露出作家對幸福的追尋及其幸福感的體驗變化過程。
一、幸福感與作者的情感宣泄與升華
幸福感首先表現為一種情感。人由于其自然本體的脆弱往往會遭遇各種不幸,所謂人活世上,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這時,人就會自然地產生消極情緒和情感,讓人感到痛苦;但人的本我奉行的是“唯樂原則”。趨樂避苦,尋求幸福是人的天性。人生的真諦就是人能勇敢地面對自己的不幸來尋獲幸福。而文學創作則是一條能很好處理消極情緒,超越不幸,重獲幸福的藝術途徑。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中的文藝升華論認為,藝術家往往把壓抑的“力比多”能量移置到文化領域中的較高目標,讓他們的“力比多”得以宣泄與釋放,這是一種“性”的升華。這之于文學創作,那就是作家通過文學抒寫這條渠道,讓壓抑在心中的不愉快情緒,得以宣泄釋放,減輕痛苦與悲傷,重獲一份解脫、寧靜和喜悅;同時在文學的抒寫中,通過對這些情感進行“冷處理”,改變對事物或事情的認知,也會從而減輕消極情緒,轉而獲得一種積極的情感體驗,重新找到另一種幸福感。
曠世奇書《紅樓夢》是如何誕生的?曹雪芹最為原初的一股強大的創作內驅力,正如他在著作的第一回中所寫道:“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4]7那是經歷了由“錦衣紈袴”“食甘厭肥”的少年淪落為“舉家食粥酒常賒”的潦倒貧困書生的人生巨變的作家,那份心中積壓的深沉悲憤與無奈情感的迸發,是一股廣義上的“力比多”的宣泄與升華的需要。文學的抒寫,讓作者找到了宣泄與升華的藝術途徑,在這個對往事的重構中,重整了他內心深處積淀的厚厚潛意識,逐漸把情感升華至一種精神的境界,從中感受到在精神上對不幸的參悟、解脫與超越,感受到一種對人的自由生命秩序的重構帶來的沉靜以及自我實現帶來的淡淡的喜悅和幸福:“雖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繩床,其晨夕風露,階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懷筆墨者……敷演出一段故事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悅世之目,破人愁悶,不亦宜乎?。”[4]1可以說,正是作家的巨大不幸和磨礪,成就了其驚世之作。
像曹雪芹那樣通過“文藝升華”去尋找幸福感的創作現象是很普遍的。古代有遠逐嶺南、流放天涯的蘇東波在詩詞境界中參悟到“何似在人間”的幸福;當今有走紅的學者型女作家徐坤,在《春天的二十二個夜晚》等長篇巨著中那一份“用寫書來為婚變療傷”的深刻體驗;而俄國的普希金,則在《我曾經愛過你》等詩篇中,感受到望著婚紗背后的另一種淡然的幸福……所以,可以說,寫作最為原初的驅力往往出自作者的“寫作治療”。
而文學創作過程中的高峰體驗,則是作者情感宣泄與升華的最佳心理狀態,這種在深度寫作時完全忘我的超然狀態,本身會體驗到一種寫作快感,獲得極大的愉悅與幸福感。心理學家馬斯洛認為,這是一種自我實現超越性需要滿足時產生的心理體驗。當代新寫實派代表作家池莉在《池莉談短篇小說創作:多種宿醉一樣美麗》一文中時談到:小說創作的過程是一次次“暈在好酒好花里不能自拔”的美麗宿醉[5]。其實這就是創作過程中異常歡快、高度興奮、深深陶醉的高峰體驗。這種體驗,令她在創作的過程中獲得一種感情和精神的升華,感受到一股極大的幸福暖流。當這種高峰體驗到來時,有些作家還會出現“癲狂狀態”,如俄國的果戈里在創作《欽差大臣》時,郭沫若構思《地球啊,我的母親》時,都有過這種體驗以及由此帶來的幸福感。
在當今被稱之為“大眾寫作”的時代,呈現出文學創作的后現代多元化。像曹雪芹、蘇東波他們這樣的傳統作家的傳統創作,關注的是人在心靈和精神層面上的追求,因而作品體現出的是精神性的“升華之作”;也許,在創作中體現出的是一種物質上的舍棄,但在精神層面上卻會收獲到一種高層次的生命價值感,一種充實的人生幸福感。但當今文學中也存在著不少欲望化的“宣泄之作”,特別是一些網絡文學,如,江南的《此間少年》、張韜《理工大風流往事》、衛慧《上海寶貝》、棉棉《糖》等,像這類作品主要表現出生理層面上的感官宣泄;因而,創作中獲得的僅是生理、心理上的快感,是一種較低層次的短暫的幸福感。
可見,幸福感與情感的宣泄與升華構成一種互動關系:創作主體的不幸感受,往往會激發他們情感的宣泄與升華,去平衡和恢復下跌的幸福指數,從而構成文學創作的心理內驅力;反之,在創作上他們會因為對情感的駕御和表達不同而獲得各自不同層次的幸福感。
二、幸福感與作者的需要渴求與滿足
人有各種需要,心理學家弗蘭克概括為:人有生理、心理和精神三大層面的需要。馬斯洛則細分為六個層面: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愛和歸屬需要、自我實現需要、超越性需要。人在生存現實中,卻往往無法滿足各種需要;但文學這個烏托邦世界,則能讓作者間接地滿足現實世界中無法滿足的需要;作為人類精神家園的文學,還具有超越功能,讓作者超越低層的需要,直接獲得高級的精神需要的滿足。而需要的滿足,就使人產生積極肯定的情緒,讓人感到幸福;反之,需要的缺失,就使人產生消極否定的情緒,讓人感到不幸[3]5。具有追求幸福天性的作者,缺失的不幸,往往會激發起他們的創作。
莫言,可謂是一位通過創作去獲取生理、心靈和精神多個層面需要的滿足從而尋求幸福的經典作家。在他的鄉土文學作品中,不遺余力地坦露了他童年時代的饑餓、孤獨寂寞的心靈,以及成年離家后無根漂泊和“無后不孝”的無奈。正是這些在生理、心理及精神多個層面上的巨大缺失和人生的不幸,讓他闖開了一條文學的金光大道,造就了這位諾貝爾獎的大師,讓他獲得創作體驗以及創作成果帶來的莫大幸福。莫言在他的《饑餓和孤獨是我的創作的財富》一文中,真實地表白了他的創作驅力。莫言作為“鄉下的城里人”和“城里的鄉下人”不可調和的雙重身份,讓他的那份故鄉情結顯得復雜而矛盾。他“憎鄉”又“戀鄉”,“歸鄉”又“離鄉”,形成了他在精神靈魂歸宿上的巨大缺失;但這卻激發起他以瀟灑雄勁的文筆締造出瑰麗、神奇的高密東北鄉,寫下了蜚聲海外的《紅高粱家族》。而在莫言內心深處,那種難以釋懷的“無后不孝”的宗族文化帶來的精神性缺失,則引發了他對中國的宗族文化與“一孩化”計劃生育國策這對矛盾之間的深入思考,用《蛙》圓了他的“兒子”夢,贏得了茅盾文學大獎,更贏得了滿滿的幸福感。
而另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的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說過:我只想在文學這個“虛幻的夢中遨游”[6]。因為這個夢能讓相繼痛失親人的他重獲幸福。19世紀的童話大師安徒生也有異工同曲之妙,在生活中飽經苦難,在愛情上飽受痛苦的他,卻在美妙的童話世界締造中得以一一如愿以償。
所以,可以說,善于超越成為古今中外藝術家的某種天性的成分及人格特質。他們把自己人生的遭際與不幸,各個需要層面上的缺失帶來的情緒,化作強大的創作驅力,在文學這種藝術審美和把握中,以豐富和激越的情感,以充滿哲理和睿智的思辨,掙脫各種現實的束縛,讓自我超越世俗和羈絆,回歸到質樸純真的內心世界和自由生命狀態,從而獲得一種超越性需要滿足,領悟到一種身心愉悅的幸福感。
在當今這個轉型期的社會,作家作為一群心靈敏感、思維敏銳的特殊群體,生存其間,自然和大眾一樣,甚至比一般大眾的感受更深刻和細膩。缺失和不幸,往往激起他們的創作欲望,成為創作的一股強大心理驅力,他們試圖通過文學這個“白日夢”來獲得一份虛擬的、間接的或超越性的滿足,重新平衡內心的幸福感。但當今文學中的“世俗化”“欲望化”寫作,如,何頓《我們像葵花》、朱文《我愛美元》、邱華棟《生活之戀》、慕容雪村《原諒我紅塵顛倒》等作品,以大膽直露、肆意渲染的手法,凸顯對權、錢、色的欲望的追逐,而缺乏對世俗的超越,缺乏中國傳統審美文化中的含蓄、喻意、中庸和優美。因而在創作中得到的僅是在生理和心理層面上的快感,一種較低層次的幸福感。只有體現出藝術應有的超越性和詩性的創作,才能令創作主體真正參透人生的際遇,進入一個超然的人生境界,獲得較高層次上的幸福感。
三、幸福感與作者的認知與評判
由于幸福感的產生很大程度上是主觀的,個體對事物的感知、體驗及評判也影響其幸福感。在文學這個伊甸園里追尋幸福的作家們,文學創作動機的激發,還與創作主體對環境、對自身的認知與評判等有關。
著名學者謝有順說:“真實的、有勇氣的寫作起源于對人類此時此地的存在境遇的熱切關懷,并堅持用自己的心靈說出對這個世界的正義判詞。”[7]20世紀90年代一躍為“文壇外高手”的王小波,這位“我思故我在”的獨立特行的思想家,他的創作驅力就是源于對現實生存的人文環境的熱切關懷以及充滿正義感的評判。他最初的寫作是16歲作為知青到云南插隊的時候。“文革”的瘋狂、嚴酷和荒謬,讓這位敏感的少年再也無法成為“沉默的大多數”,于是他用故事和小說來斥訴知識分子遭遇的政治不公和命運的不幸。王小波把他經歷和深刻體驗過的“文革”時代以及當今社會人類生存狀態中的荒謬與苦難,通過睿智的思辨和辛辣的反諷,以黑色幽默的文學樣式再現出來,宣泄也升華了“心頭之憤”,彰顯了這位浪漫騎士、行吟詩人、自由思想家與不幸抗爭的勇氣與生命的尊嚴,使其心靈和精神裂傷,得以診治與康復,令他在詩性世界中,提升了明理、樂觀和瀟灑的積極情感,尋找到一種寫作的幸福感。為此,王小波對寫作樂此不彼,后來,他干脆辭去大學教師這一天底下令人羨慕的職業,做一個自由的撰稿人。
20世紀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的后現代主義作家塞繆爾.貝克特,也在對人類在戰爭中所遭遇的劫難的深刻體驗和理性的審視中,激發起他反傳統的創作,開創了“荒誕派”小說和戲劇先河,寫出了《等待戈多》等著名作品,“以一種新的小說與戲劇的形式,以崇高的藝術表現人類的苦惱”[8]獲得諾貝爾獎;而更為重要的是在這個過程中讓憂郁、痛苦、失望的他尋找到一種解脫與幸福。
也有作家則是在自身的認知及評價方面促使他成就為一代文學大師,如賈平凹的自卑感、史鐵生的殘缺感等,成為他們追逐文學夢的強大內驅力。小時候的賈平凹,天生身體孱弱,備受家人的嫌棄和同學的冷落,形成在同齡人面前的弱勢地位,令他自己都不接納自己,對身體自我、心理自我及社會自我的評價都產生不滿,形成一種無助感、孤獨感和自卑感,給幼小的心靈留下重重的精神及人格創傷。阿德勒認為,自卑感雖然是一種消極的情緒感受,但并非是完全消極的。相反,當一個人感到強烈自卑感時,他往往會力圖發展自己,以成功來克服自卑感。這時,自卑感就成為推動人積極向上的動力,即人格動力[3]104。正是來自這種人格創傷的不幸,賈平凹最原初的寫作動機勃發了:他要以“文學”這個夢想來改變自己的命運和處境。“對我來說,人生的臺階就是文學的臺階;文學的臺階也就是人生的臺階。”[9]他在創作成功的鮮花與掌聲中,改變了對自身的認知及評價,重新尋找到了自我的驕傲與幸福。而史鐵生則在寫作中對“殘缺感”有了豁然開朗的領悟,也在寫作成就感中尋找到人生的價值感和幸福感。
文學,是創作主體對世界及自我的一種認知、審美和表達,是一種藝術地把握世界與人生的方式。《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10]中國傳統文論很早有“心物感應論”的藝術起源論。在燦若星河的文學世界里,其實有許多創作都源于創作主體對自我及世界的認知及評判,他們在創作中化解、釋然各種沖突引起的消極情緒和不幸體驗,在文學的審美中,尋找到詩性棲居以及自我實現的幸福感。
但當今文學中的某些創作,特別是一些“憤青式”的作品,如,韓寒《三重門》、孫睿《草樣年華》等作品,以非理性的信念、偏激的心態去認知和評判當今的社會與教育,在作品中凸現自我與社會及世界的沖突,在創作的宣泄中,雖能獲得一種一吐為快的輕松與解脫,但未能真正通過創作提升自我的認知與評判的能力,獲得積極的情緒體驗;未能在寫作中實現自我內部、自我與社會的和諧統合,因而無法在創作中獲得一種真正的喜悅和幸福感。
四、幸福感與作者的寫作目標及實踐
在浩繁卷帙的文學長河中,每一部作品背后,都可或顯或隱找到作者的寫作目標,以及對人生幸福的追尋軌跡。幸福心理學認為,幸福的產生有賴于人們的行為目標及實踐,個體達成目標的活動方式以及實現目標過程中的成敗將直接影響人的幸福感[3]13。對于整個人類的文學創作史來說,引發作家創作動機的寫作目標是復雜多樣的,因而他們的抒寫方式及其幸福體驗也呈現出多元化。
人們都盛贊傳統作家特別是批判現實主義作家勇于肩負社會使命感。極為經典的一例就是魯迅先生當年的“棄醫從文”。這種“拯救國民”的偉大的寫作目標,成為魯迅文學創作的強大內驅力,讓他找到了在他心目中比行醫更富社會價值的人生意義,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第一代宗師,獲得了自我實現的極大滿足感與精神上的幸福感。
在后現代多元文化共存的當今文壇,也涌現出了一批批魯迅式富有使命感的現實主義作家,如王小波、余華、賈平凹、六六等,他們敢于直面當下社會轉型期的現實問題,既用犀利的筆鋒揭露丑惡,又以睿智的思辨去洞察歷史與現實;既用人文關懷的情懷去關注民生,又以獨特的體察去探索和思考當代人的生存與幸福。他們在抒寫當代人在大時代面前面對欲望,面對苦難如何駕御自我,超越自我的同時;也體驗到創作主體本身駕御自我,超越自我的精神引領,以及創作成功帶來的成就感與幸福感。也應盛贊那些“生態文學作家”,如姜戎、徐剛、于堅、李保薦、葦岸等,他們出于對生態環境現狀的熱切關注和高度的責任感,創作出許多關于“人與自然”命題的警世之作。他們在為大地、山川充滿憂患與關愛的情懷中,獲得寫作上帶來的精神的富足、充實與幸福。此外,還應贊譽出于心靈和精神需要之作,像史鐵生、周國平、徐坤等作家,他們真真正正在心靈的伊甸園里,尋找一種不僅是自我,也是人類共有的心靈圣藥和精神力量,尋獲一份心靈層和精神層的超越性的幸福感。還無可否認現代的一些心理減壓之作,如風趣健康的喜劇小品、輕松寫意的旅游文學等,作者在輕松幽默的創作和演繹中,也會釋放自我,在給大眾的心理和精神減壓中也會獲取一份愉悅和幸福感。
但那些為版稅而作的商業文學,為感官宣泄而作的垃圾文學,為文字游戲而作的無厘頭文學等,雖然創作主體都有自己明確的創作目標,但這些作品與文學應有的社會審美功能和審美規范相互矛盾和沖突。所以,他們在創作中雖然不乏抒寫自我的那份愜意及愉悅,不乏追逐名利帶來的滿足感,但體驗到的只是較淺層的幸福感,而無法獲得精神上的心靈層的恒久幸福感。
綜上所述,從幸福感的視野去觀照文學創作的心理驅力,可對紛繁復雜的文學創作心理作出一個更為深入、明晰的梳理和辨析,不難發現:文學的創作動機多種多樣,但其創作的深層內驅力均是作者的“不幸”使然。一般而言,作者的內心沖突越大,缺失越大,情感就會越強烈,寫作的動機就會越大,寫作的行為越能體驗到更大的幸福感。文學的品位層次參差有異,作家從創作中獲得的幸福體驗也會有層次之別;與此同時帶給大眾的審美效果也迥然不同。馮驥才說:“文化界要承擔的責任就是使人們精神幸福。”[11]在創建幸福中國,筑構“中國夢”的當今時代,人們呼吁有更多震撼心靈,體現精神享受的高品位作品,去引領大眾的閱讀審美潮流,去提升國民的幸福指數,讓文學充分發揮其應有的社會功能和美學價值。
[1]張笑天.文學讓我一直幸福著[N/OL].吉林日報,2011-03-01[2015-12-08].http://jlrbszb.chinajilin.com.cn/htm l/ 2011-03/01/content_702257.htm.
[2]陳應松.陳應松寫作與讀書——最好的生活[DB/OL].(2010-01-18)[2015-12-09].http://news.qq.com/a/201001-18/001779_3.htm.
[3]鄭雪.幸福心理學[M].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04.
[4]曹雪芹,高鶚:紅樓夢[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
[5]池莉.武漢故事(序言)[M].武漢:昆侖出版社,2004.
[6]葉渭渠.川端康成小說選[M].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1985:676.
[7]謝有順.先鋒就是自由[M].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4:113-114.
[8]《等待戈多》作者塞繆爾·貝克特簡介[DB/OL].中學語文教學資源網,(2008-09-26)[2015-12-10].http://www. ruiwen.com/news/40266.htm.
[9]魏鋒.追尋“丘比特”的賈平凹[N/OL].焦作日報,2015-06-11[2015-06-11].http://epaper.jzrb.com/htm l/2015-06/ 11/content_346846.htm.
[10]吉聯抗.《樂記》譯注[M].北京:音樂出版社,1958:1.
[11]馮驥才.創作高質量作品增強老百姓“幸福感”[DB/OL].中國經濟網,2011-03-10[2015-12-10].http://finance. ce.cn/rolling/201103/10/t20110310_16551475.shtm l.
(責任編輯:禤展圖)
Well-Being and the Psychological Driving-Force of LiteraryWriting
LIANG Peihao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and Literature,Zhaoqing University,Zhaoqing Guangdong 526061,China)
ract There isa close internal relation between well-being and driving-force of literary w riting,forming an interactive psychological-structure.In view ofwell-being,themotive of literary w riting comes from all kinds ofmisfortuneofw riters.Their feeling’sventand sublimation,their demand’s longing and content,theirautognosisand appreciation,their ambition’s establishmentand behavior,all the factors form a stream of powerful driving-force,whichmakesw riters seek well-being from romantic literatureworld.Differentmotives,different levels of works,and the w riters'differentwell-being experience cause different aesthetic perceptions of audience. Our times call formore high quality workswhich w ill lead aesthetic trend and improve people'swell-being feelings.
ords well-being;literary w riting;psychologicaldriving-force
I04
A
1009-8445(2016)04-0030-05
2015-11-14
梁沛好(1966-),女,廣東高要人,肇慶學院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