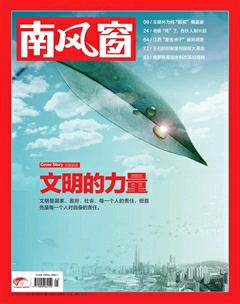“無愧于心”的道德直覺
石勇
我們都說:“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于心”。這個“人”,包括了“我”,但更多地指“他人”。
在《讓直覺和世界的真相相通》(見本刊2015年第26期)這篇文章中,我在破解著名的“電車難題”時說,“豈能盡如我意,但求無愧于心。”在到底是讓失控的電車按既定軌道撞死5人,還是由我們選擇拐向岔道,拿無辜的1人生命去救5人,我們都是極其痛苦的,是無法盡如我意的,但再痛苦也得選。這個時候的判斷標準就是“無愧于心”。
這兩句話,都在說:我們對做一件事最終應該聽從的,不是頭腦的想法,不是他人的意志和壓力,而是我們內心的聲音,是內心深處的直覺。這是一種對最真實的自我負責的態(tài)度。我們得先對得住內心深處的直覺,否則一些想法和行為可能是錯的,也許真會干出蠢事或壞事。
這個直覺,包括了道德上的直覺和理性上的直覺。違背直覺的東西,在我們的內心深處肯定覺得不對勁。而只要感覺不對勁,那肯定有問題。
比如在“電車難題”中,當我們在“5條人命比1條人命更有道德份量”的壓力下,選擇了拐向岔道撞死1人時,我們對自己的辯護是“功利最大化”這類道德哲學上的依據(jù)。它在很多地方沒錯,但用在這兒卻不合適。問一下內心,我們真有道德權利,像上帝一樣可以裁決別人的生死,拿一個無辜者的生命去挽救其他人嗎?我們可以在他們中預設因為人多就享有生命特權,人少就必須為別人犧牲?這就是不對勁的地方,它通不過內心深處的道德直覺和理性直覺。而再澄清一下,我們之所以有拐向岔道這種想法,是因為在“5∶1”的壓力之下,愿意這么去想,在心理上的功能是盡可能減少這種壓力。所以,這個想法只是在頭腦上去說服自己,但并不能說服內心,不可能“無愧于心”。
2015年12月下旬的幾天,北京、上海、南京、廣州、沈陽等城市,都籠罩在霧霾之中,呼吸極為困難。雖然我們已經在霧霾中生活很長時間了,但還是相當難受。好,我們就來設一個思想實驗。
這個思想實驗是這樣:大家都知道霧霾的一個貢獻是汽車尾氣,私家車肯定是有一點“貢獻”的。我們現(xiàn)在排除其他“貢獻”,比如污染的工廠,以及某些政府部門治理的不力,等等。假定為了減少霧霾,除了你之外的所有私家車主,在某一天,突然像約好了一樣不開車出行了(你事先不知道),那么,請問,你是否感覺到自己也有道德義務不開車?
再來一個思想實驗。假設你所在的街區(qū),加你在一起有100個人,沒有清潔工之類,99個人都輪流起來打掃街區(qū)衛(wèi)生,他們和你都沒有丟垃圾在這條街區(qū)上,那么,當輪到你的時候,你是否覺得有道德義務也去打掃?
我相信,無論怎么選,在到底開不開車,到底打不打掃街區(qū)上,我們都能找出一堆理由。有些理由看上去還振振有詞。但問題是:能無愧于心嗎?能通得過道德直覺和理性直覺嗎?
我發(fā)現(xiàn),在霧霾的思想實驗中,如果我是私家車主,我真有不開車的道德義務。大家都已經行動起來為減少霧霾做貢獻了,我無動于衷既占了大家便宜,也表現(xiàn)出了一種對自己責任的麻木。這個時候說“為什么不是治理工廠的污染或某些政府部門負責而是我不開車呢?”只是頭腦、個人的價值觀、欲望等強行為自己找理由而已,內心還是知道哪兒不對勁。
但是,在街區(qū)的思想實驗中,我真沒有也跟著那99個人一起打掃的道德義務。大家去做好事并沒有給我創(chuàng)造一個道德義務,讓我也要如此。不錯,我是感受到了道德壓力,但這是“美德”給的壓力,不是道德義務給的。我不去打掃并沒有什么錯,只是沒那么偉大而已。如果我屈服于這個壓力去打掃,我發(fā)現(xiàn)是被強迫的,違心的,無非是為了解除壓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