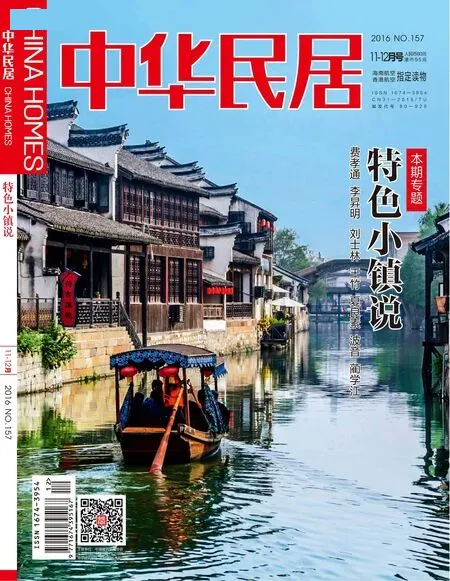小城鎮建設熱的五大原因探討
撰文劉士林
小城鎮建設熱的五大原因探討
撰文劉士林
時下,小城鎮建設成為一大社會熱點。各種有關小城鎮建設的大小會議、論壇也如家常便飯般,隨時隨處召開。諸多專家學者圍繞小城鎮建設也提出了各自獨到的見解和建議。但關于當下小城鎮熱背后的深層次原因,卻鮮有人提及。為此,筆者專門就此問題進行了思索和調查,并進行了總結。依著『方法論』的原理來看,筆者認為,深入剖析其背后的原因,是對小城鎮建設別具重要意義的。

劉士林
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院長、首席專家,光明日報城鄉調查研究中心副主任,國家“十三五”發展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文化部文化產業專家委員會委員,主要從事城市科學、文化戰略、智慧城市和城市文化研究等。
任何一個社會發展熱點背后必有其深層原因。小城鎮在熱浪滾滾的城市化進程中異軍突起,更不會是一種偶然,而是各種力量、利益、需求在相互斗爭和博弈中最終達成的結果。具體可以從以下幾方面來探討。
再現了“城市自然規律”的作用。所謂“風水輪流轉”,在城市化進程中,“大都市”和“小城鎮”這對基本矛盾,也是一種相生相克的關系。美國著名規劃大師劉易斯·芒福德曾把城市的重要功能之一稱為“容器”:一方面,它“構造致密而緊湊,足以用最小的空間容納最多的設施”;但另一方面,任何容器也都是有限的,一旦這個本來就比鄉村高度集中和擁擠的聚落形態吸納了過多的人口和資源,其結果只會是越來越糟,陸續帶來房價昂貴、交通擁堵、就業壓力增大、環境污染加重、社會分化加劇、公共資源短缺(如教育、衛生資源短缺)等諸多“城市病”,使不堪重負的城市面臨著解體的危險。
如近年來鬧得沸沸揚揚的“華為遷出深圳事件”,不是因為別的,而恰是因為深圳本身的過度繁榮。這是一個深刻的悖論:一方面,一個城市要想迅速“揚名立萬”,必然要最大限度地強占、劫掠周邊城市的生存資源和機會,這就是所謂的“人無橫財不富”;另一方面,這個“狼吞虎咽”的過程不僅破壞了大自然的資源鏈條和生態平衡,也超出了其自身的承受力和消化力,結局必然是要把原本就不屬于自己的東西重新“吐”出來,這就是所謂的“福報不夠”。現在的很多大都市,越是成功就越是“百病纏身”,說明最終決定城市興衰的不是“人力”而是“天意”,是某種一般人看不見、捉摸不透的“城市自然規律”。
改革開放30多年來,大城市的發展占盡了天時、地利和人和,小城鎮和農村的利益與需求被忽視。但我們最終發現這制造了一種虛假的“繁華都市泡沫”,所有小城鎮和農村的生態、空間、人口、社會和文化問題,最后都無一例外地“還”給了城市,而貌似強大的大城市也根本不足以承擔。就此而言,小城鎮的復興與大城市的困境完全符合城市發展的自然規律,不僅直接再現了城市的“容器”本質,也尤其深刻地體現了“損有余而補不足”的“天之道”,是宇宙中固有的“城市自然規律”對無序失控的城市化強行調節和平衡的結果。從詩性智慧的角度來講,這是中國城市的“風水”正在發生重大轉向;從理性智慧的角度來講,這是“自然之手”重構中國城市的整體格局、合理配置人口和資源、避免環境和城市走向解體的必要手段。
反映了“中國式城市化”機制的存在。 筆者一直認為,中國不同于歐美和拉美國家,我們已經走出了一條與鄧小平所說的“中國式現代化”相適應的“中國式城市化”之路。與西方國家的城市化主要由市場主導、拉美國家的城市化主要由西方主導不同,中國城市化的一個突出特點是由政府和市場共同主導,以及政治體制和社會制度共同構成推進中國城市發展的核心機制。
此輪小城鎮最大的實惠和紅利,可以說主要是來自政府政策方面:一是2016年4月,國家發改委和國家標準委聯合下發《關于新型城鎮化標準試點的通知》,其中首次提到“特色鎮”建設。這等于在以“62個城市+2省(安徽和江蘇)”為試點范圍的“新型城鎮化標準試點”已實施了兩年多后,終于為小城鎮這個最低的城市層級敞開了大門。二是2016年5月3日,國家發改委發布消息稱,為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和李克強總理關于特色小鎮發展的重要批示,將強化對特色鎮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支持,以資助特色小城鎮提升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功能,并計劃于年內挑選和建設1000個特色小鎮。7月20日,住建部、國家發改委和財政部三部委聯合下發《關于開展特色小鎮培育工作的通知》,進一步明確表示,到2020年,全國要培育1000個左右主打休閑旅游、商貿物流、現代制造、教育科技、傳統文化或美麗宜居等各類主題的特色小鎮。盡管有人會認為這只是政府行為,但其實不然,它恰恰完全符合“由政府和市場共同主導”這一“中國式城市化”的機制。
在此,筆者認為也必須對當下較為流行的“市場主義城市化”論調提出批評,他們以主要由市場主導的西方城市化為標準,將我國日趨嚴重的城市病、昂貴的生產生活成本和不斷降低的幸福感等都歸結為政府主導所致。當他們憤怒地譴責和批判中國城市的環境、交通和公共服務時,一般都忘了一個明顯的事實,那就是這些年中國的城市化實則一直是按照西方的城市理論、方法、技術和標準來規劃和建設的。如果硬要把今天的城市說成“爛攤子”,那么無論如何他們所信奉和躬行的一大堆西方城市理論是難辭其咎的。城市化要協調和均衡發展,最好的辦法是政府和市場各司其職,而不是在二者之中擇其一。
契合了《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的要求。關于中國城市化應該走什么道路,改革開放以來一直有兩種聲音:一種是走小城市發展道路。以夏書章的“超微型城市論”和“費孝通的微小城市論”為理論代表,以1989年國務院制定的“嚴格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等城市,積極發展小城市”(俗稱“三句話方針”)為大政方針。另一種是走大都市發展道路。在理論上以2002年“大上海國際都市圈”研究報告首次提出走“以大城市為主的城市化發展道路”為代表,在實際行動中以2004年全國183個城市提出建設“國際化大都市”為象征。但實踐證明,它們各有偏頗。前者把“大都市”與“小城市”對立起來,看不到都市化已成為決定自然環境和社會結構變化的核心機制與主要力量,基本上屬于一種城市化的“窮過渡”思維。后者作為“單體城市”的最高形態,只關心“自己”而排斥一切“他者”,必然加劇城市之間的“同質競爭”,造成區域內資源、資金和人才的巨大浪費和低效配置。

在經歷了反復的思想交鋒和實踐檢驗,基于良好的城市分工體系和合理的城市層級關系的城市群,最終被確定為我國新型城鎮化的“主體形態”。城市群是關于大都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頂層設計。因此,我們應在《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的語境中去理解和把握兩者關系,防止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尤其切忌把“小城鎮熱”看作是對“大都市熱”的全盤否定。
實際上,直到今天的小城鎮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本就得力于大都市的發展。甚至可以說,如果沒有大都市本身的問題和危機,人們也不會這么關注小城鎮。如果說過去對小城鎮重視不夠,那么目前應該做的是以“補短板”的方式適當提高,并在與大都市的協調發展中規劃設計小城鎮的未來。
我們應在《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的語境中去理解和把握兩者關系,防止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尤其切忌把『小城鎮熱』看作是對『大都市熱』的全盤否定。
符合西方小城鎮的發展經驗。在歐美國家,小城鎮不僅數量多,而且有較強的吸納人口能力,這對疏解人口向大城市集聚發揮了重要的延緩和截流作用。在美國,3萬—10萬人的小城鎮大約占到全國城市總數的九成以上,極大地減輕了大城市的壓力。英國主要通過建立新鎮分散大城市人口,其新鎮人口規模一般控制在6萬人以內,而現有的3000個小城鎮絕大多數人口都不超過10萬人。德國則形成了比較良性的“逆城市化”機制,大中城市的中產階級往往選擇居住在郊外的小城鎮。相關統計表明,其中有一半以上的家庭定居在2萬—10萬人的小城鎮。事實上,歐美國家能形成今天以小城鎮為主體、相對均衡的城鎮體系結構,并不是一兩天完成的,他們曾經也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

歐美國家能形成今天以小城鎮為主體、相對均衡的城鎮體系結構,這絕不是一天完成的,他們曾經也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
以英國的小城鎮發展為例,主要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8世紀中葉到19世紀50年代,這一時期的小城鎮發展較快且分化劇烈。1801年,英國5000人以上的城鎮數量為105座,到1851年這個數量就增加了一倍。在這個階段,臭名昭著的“圈地運動”是主要推手,也徹底葬送了英國鄉村的田園牧歌夢想。第二階段,從19世紀50年代到20世紀30年代,隨著工業化和大城市的快速發展,各種“城市病”集中爆發。受其影響,小城鎮的發展也進入停滯狀態,數量不增反降。第三階段,從20世紀30年代至今,小城鎮發展進入到持續平穩的成熟階段。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推動這一進程發展主要依靠的是政府,而不是市場。為了推動小城鎮的復興,英國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如20世紀30年代實施的農業保護政策,1945年和1947年分別頒布的《工業配置法案》和《城鄉規劃法案》等。這和我國小城鎮所走過的“土地城市化”“村村通公路”“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特大鎮擴權”等路子極其相似。從某種角度來看,這已表明,從最初矛盾對立、城市剝奪鄉村到兩者協調發展,是人類城市化必經的歷史階段。現在只要努力把城市化的后遺癥和小城鎮規劃建設好,就符合歷史的規律和進程,而沒有必要徹底否定前一個時期的城市化。
承擔了“十三五”時期的城市化任務。“十三五”時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其中一個重要的約束性指標是“引導約1億人在中西部地區就近城鎮化”,一個重要的戰略任務是“促進區域與城鄉協調發展”。因為,現實已不允許我們圍繞已開發過度的東部地區和日益不堪重負的大城市做文章。然而需要提醒的是,一些課題組在做長三角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規劃時,仍在執迷于提升上海、鄭州等“中心城市”的“首位度”,事實上,這根本就是行不通的。
參照世界城市化的一般規律,目前全球只有約1/8的城鎮人口居住在28個人口超過1000萬的巨型城市中,而接近一半的城鎮居民仍居住在人口小于50萬的城市里,可以說小城鎮一直是人口聚集的主空間。自然,這也符合實現我國城鄉協調發展的現實需要。一方面,以東部開發密度較低的小城鎮為重點,可以有效緩解東部地區的發展壓力;另一方面,以高水平的規劃設計引領中西部小城鎮科學發展,還可以避免中西部大城市重蹈東部大都市“過度城市化”的覆轍。由此可知,大力培育和發展我國小城鎮,可以為城鄉人口和資源要素流動提供一個安全的蓄水池,對完成“十三五”時期我國城市化的主要目標任務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
“羅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小城鎮也不會在朝夕之間就完美無缺。我們在深感大都市發展矛盾重重、千難萬險的同時,也不要把小城鎮建設設想得十分安靜和協調。在城市化進程中被注入過多新的內涵和關系的小城鎮,注定將是一個各種資源、資金、人群在其中沖突、博弈、斗爭的新戰場,因為這正是其有活力、能發展的前提和基礎。所以,我們對小城鎮建設的艱巨性和復雜性同樣要有信心和耐心,并通過不懈的努力和奮斗把它們建設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