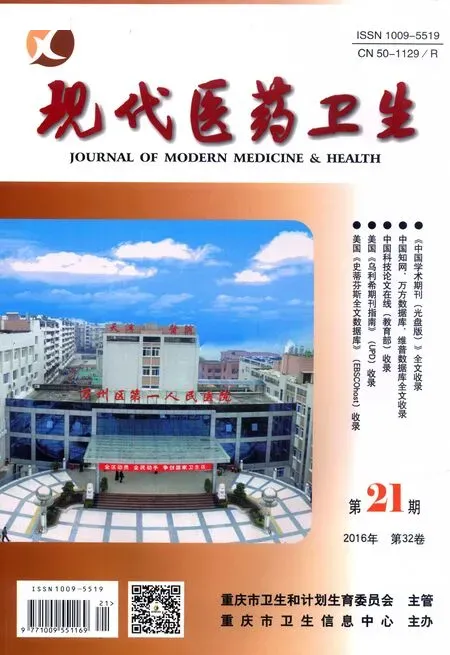腫瘤的精準治療新方法*
王婧,祝強綜述,王燕一△審校
(1.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yī)院海南分院口腔科,海南三亞572013;2.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yī)院外科臨床部,北京100853)
腫瘤的精準治療新方法*
王婧1,祝強2綜述,王燕一1△審校
(1.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yī)院海南分院口腔科,海南三亞572013;2.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yī)院外科臨床部,北京100853)
腫瘤/治療;基因;綜述;精準醫(yī)療
以往傳統(tǒng)的腫瘤治療以“單一的‘破壞性’治療”為主要治療模式,但存在治療方法單一、簡單、粗放等弊端:外科切除的適應證狹窄,創(chuàng)傷大;全身化療和放療存在周期長、費用高及療效不確切等缺點。以個人基因組信息為基礎,結合蛋白質組、代謝組等相關內環(huán)境信息而衍生的精準醫(yī)療,以達到治療效果最大化和不良反應最小化為定制醫(yī)療模式,該模式具有靶向性、高效性、預防性的特點,將開啟醫(yī)療新時代。2015年4月,美國癌癥研究協(xié)會年會(AACR)在美國(費城)召開,此次會議匯集了目前所有癌癥主要領域的最先進研究成果,全球的目光再次聚焦在了“精準醫(yī)療”[1]的概念上。
1 精準醫(yī)療概述
精準醫(yī)療是隨著基因組測序技術的發(fā)展,以及大數(shù)據(jù)科學和生物信息科學的交叉應用,繼而發(fā)展起來的一種新的醫(yī)療模式[1-2]。與傳統(tǒng)醫(yī)療相比,其突出體現(xiàn)了個體化醫(yī)療,具有前瞻性、精準性、預防性、個體性、微創(chuàng)性、綜合性和便利性的特點[3]。精準醫(yī)療基本流程包括基因測序尋找治療靶點、大數(shù)據(jù)生物技術分析分類、精準外科、藥物治療干預和精準康復療效跟蹤調整,不僅達到對疾病及個人的精準治療,更能提高對疾病的高效預防[4]。“人類基因組計劃”取得階段性勝利后,“精準醫(yī)療計劃”在美國已宣布推出,并將其應用于惡性腫瘤的治療。
2 精準醫(yī)療與腫瘤
精準醫(yī)療的興起與蓬勃發(fā)展反映出人類對疾病的恐懼。世界衛(wèi)生組織(WHO)《全球癌癥報告2014》中統(tǒng)計全球癌癥病例在2012年約1 400萬人,并預測2025年癌癥病例約為1 900萬人,2035年將會達到約2 400萬人。2016年年初的2015癌癥報告顯示,僅我國就新增癌癥患者430萬人,死亡280萬人。
20世紀80年代以前,腫瘤治療以“單一的‘破壞性’治療”為主要治療模式,包括了外科手術、放療及全身化療三大手段[5]。不可否認,這些治療方式在當時條件下確實延長了腫瘤患者的生命,并為醫(yī)生廣為采用。但簡單、粗放的腫瘤治療模式頻現(xiàn)弊端:外科切除的適應證狹窄、創(chuàng)傷大;全身化療和放療周期長、費用高、療效不確切。
驅動癌癥的誘因是分子病變,故而不同癌癥有其各自的基因印記、腫瘤標記物及變異類型。目前患者應用抗腫瘤化療藥物的治療有效性低于70%,甚至20%~35%的患者接受的是不恰當?shù)乃幬镏委焄1],這是因為癌癥患者沒有足夠的時間去承受反復試驗和摸索。治療敏感性的需要使得疾病基因信息的精確性尤為重要。如果可以精準地定位和篩選與疾病密切相關的基因,靶向個性化治療就成為可能[6]。除此之外,由于精準的定位,治療中的療效監(jiān)控及愈合評估也變得準確與可信。如果能夠實現(xiàn)個體化的腫瘤治療,將會擺脫近乎盲目的治療方式,不僅大幅提高療效,避免過度醫(yī)療,而且可減輕患者經濟負擔及醫(yī)療資源的浪費。高通量分子檢測技術的出現(xiàn),可以從個體基因組中分析和鑒別出患者疾病的個體差異,從而利用這種個體差異更加合理地指導臨床治療,這已成為醫(yī)學界的廣泛共識[7]。基于大規(guī)模癌基因組學的數(shù)據(jù),體外腫瘤模型已經在建立中[8],一方面提供更直接、準確的平臺用于腫瘤發(fā)生機制的研究和早期診斷、標志物篩選,另一方面,提供有效體外平臺用于抗癌藥物的篩選。可以設想,不久的將來,靶向抗癌藥物的篩選將像目前抗菌藥物藥敏試驗一樣快速、有效、經濟。
精準醫(yī)療將短期目標定為惡性腫瘤的藥物治療,而基因測序技術為腫瘤精準治療提供了必備條件[9]。一是檢測腫瘤易感基因。通過DNA測序技術確認腫瘤致病基因或是否攜帶易感基因,從而應用合適的靶向治療藥物,或者采用其他更加適宜該患者的治療方式。在腫瘤早期階段即實施干預治療,將有可能極大地提高疾病治愈率,顯著延長患者生存時間。二是檢測腫瘤靶向藥物靶點。個體差異在藥物靶點上得以充分體現(xiàn),使用靶向藥物治療前檢測其是否攜帶藥物靶點將會對用藥效果做出更加準確的判斷,做到藥效的最大利用,減少不必要的醫(yī)療費用。
15年前,攜帶Bcl-ABL突變基因的慢性髓性白血病患者5年存活率不到30%,但針對該突變基因的靶向藥物“格列衛(wèi)”的臨床應用,使該類患者5年存活率從30%上升到90%,最初接受“格列衛(wèi)”治療的患者生存期已經超過20年[1]。2010年11月,我國衛(wèi)生部首次發(fā)布了《結直腸癌診療規(guī)范》,該規(guī)范明確規(guī)定:確診為復發(fā)或轉移性結直腸癌時,應進行相關基因狀態(tài)檢測,接受愛必妥(西妥昔單抗)、帕尼單抗[抗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GFR)單抗]治療的復發(fā)或轉移性結直腸癌患者,必須檢測腫瘤組織的KRAS基因狀態(tài)。如果KRAS基因突變,會旁路激活細胞內信號傳導,從而導致愛必妥、帕尼單抗等抗EGFR單抗失效。所以,醫(yī)生應有針對性地區(qū)別給藥。
3 精準醫(yī)療的推進
外科手術方面,數(shù)字化精準外科操作、術中導航、計算機輔助快速成型、三維有限元建模技術等有效完善了立體概念,對于機體復雜的生理結構及重要的血管、臟器可以理想模擬呈現(xiàn),便于術者合理進行手術干預,制訂個性化手術方案。術中聯(lián)合導航檢測、超聲監(jiān)測,可以引導術中定位,有效術中跟蹤,對選擇最佳手術入路、減少損傷、提高病灶定位精度等有重要臨床意義[9-10]。例如骨科常用的術中導航脊柱外科手術等。
藥物治療方面,通過確定突變基因,真正個性化給藥。基于基因組學的治療手段已經成為腫瘤患者的標準治療選擇[11]。針對鱗狀細胞肺癌的大樣本基因圖譜分析發(fā)現(xiàn),TP53基因突變率高達83%,為靶向藥物的研發(fā)提供了重要信息[12]。EGFR、KRAS、EML4-ALK、HER2、BRAF已被證明與肺癌細胞的異常增殖密切相關[13],針對EGFR突變使用的吉非替尼,針對間變性淋巴瘤激酶突變的克唑替尼都已經成熟應用于臨床。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yī)院口腔科早在2009年就進行了針對腫瘤的“精準”嘗試。對1例79歲上腭部肉瘤樣癌伴壞死并頸部轉移的女性患者,首先進行實驗室檢查,結果顯示,ERCC1、TUBB3、RRM1、TYMS、STMN1、TopⅡα高表達。同時,對該例患者進行了基因多態(tài)性分析,并測序分析顯示,EGFR基因第19、20、21外顯子未見突變。該結果提示,目前臨床常用的化療藥物,如鉑類、氟類、吉西他濱、卡倍他濱、長春瑞濱、培美曲塞、抗微管類、依托泊苷類等對其均表現(xiàn)為高耐藥性、藥物敏感度低,化療效果差。所以,將放療作為患者的首先治療方法。患者接受了精準的放射粒子植入術,避免了長時間、大劑量、高消耗用藥,預后良好。除了腫瘤的精準藥物治療,依托我國第一個高場強術中MRI系統(tǒng),解放軍總醫(yī)院口腔科將進一步探討術中MRI導航精準定位頜面部惡性腫瘤手術邊界的可能性。分組對照研究顯示,導航組手術切緣陽性率[10%(2/20)]明顯低于常規(guī)手術組[44%(20/45)],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07),且首次切緣陰性結果與組織病理學結果高度一致。
雖然精準醫(yī)療在推進中成果喜人,但仍有不可忽視的2個問題。第一,成本。精準醫(yī)療的初衷是兼顧診療成本效益的最大化,減少不必要的耗費,但需要依賴于診斷技術的研發(fā),以及需要基于現(xiàn)代醫(yī)學研究信息成果之上的診斷與管理系統(tǒng)[14]。檢測技術的進步使得基因檢測與分析成本在逐年降低,但由于其對于技術與檢測條件的高要求,目前能夠進行疾病基因分析并且真正靶向治療的仍局限于少數(shù)醫(yī)療機構,而基因信息之間的共享也存在局限,精準醫(yī)療大范圍的推廣依然困難重重。第二,異質性。同一類型的腫瘤在不同個體可能有不同的基因突變型,即使檢測到相同的突變基因而靶向用藥,個體反應的差異性也使得精準醫(yī)療的開展任重道遠。
4 精準醫(yī)療長期目標
精準醫(yī)療的長遠目標是健康管理。在治療疾病的同時,要在疾病風險評估、疾病進展把握及最佳治療方案預測等方面不斷加大科研投入,從而擴大精準醫(yī)療在疾病預防和衛(wèi)生保健等諸多領域的作用和益處[15-16]。
根據(jù)該長遠目標,勢必將鼓勵和支持開發(fā)創(chuàng)造性的新方法用來檢測、測量和分析范圍廣泛的生物醫(yī)學信息,包含分子、基因、細胞、臨床、行為、生理和環(huán)境參數(shù)等[17-18]。可以預測,數(shù)以百計的不同類型的免疫細胞普查將會成為常規(guī)檢查項目;血液檢測將可以檢測出癌癥早期出現(xiàn)或復發(fā)的腫瘤細胞或腫瘤DNA[19-20];而基因型測定將會揭示出其特定的基因變異,從而為特定疾病提供個體化保護。
婦科腫瘤易感基因BRCA的攜帶者已被明確有60%~80%的累積風險,預防性雙乳腺和卵巢切除術作為控癌策略,已使接受此手術的女性在過去10年增加了1倍,將患癌概率降低了80%~96%[21]。另有部分攜帶者,選擇采用更加敏感的磁共振成像作為腫瘤早期篩查的工具,用以監(jiān)控與預警。結腸癌與APC基因突變密切相關,多數(shù)患者于40歲前發(fā)病,但20歲前發(fā)病極為罕見。據(jù)此特征,攜帶APC突變基因的個體,接受預防性切除的時間可以推遲至青春期后期或學業(yè)完成時。與甲狀腺癌密切相關的RET基因突變,分為A(最低)~D(最高)4種亞型。D型攜帶者出生1年內進行手術,B、C型攜帶者于5歲前接受甲狀腺全切,A型攜帶者可以推遲至5歲后或降鈣素檢測陽性時實施手術。精準健康管理,極大降低了惡性疾病發(fā)病率,將對攜帶者生活的影響降到最低[21-22]。
精準醫(yī)療提供了一個強大的框架方案,將會加快其在不同領域的應用[14]。2015年2月,我國基于精準醫(yī)療在全球的發(fā)展戰(zhàn)略,成立了中國精準醫(yī)療戰(zhàn)略專家組,由19位相關領域專家組成了國家精準醫(yī)療戰(zhàn)略專家委員會。在2030年前,中國精準醫(yī)療將投入600億元,相信我國在精準醫(yī)療領域必將大有作為。
5 小結
精,指熟練、精細、專一;準,指符合標準、依據(jù),最終目的是“止于至善”。精準醫(yī)療體現(xiàn)了人文醫(yī)療理念,依從循證醫(yī)學原則,符合生命質量和生理功能保存原則。精準醫(yī)療是復雜的系統(tǒng)工程,將組學技術、數(shù)字影像、系統(tǒng)生物、信息科學、大數(shù)據(jù)等現(xiàn)代技術手段與傳統(tǒng)醫(yī)學相融合,其高效、快速、全面地推進需借助生物樣本庫、測序平臺、大數(shù)據(jù)分析、電子病歷的支撐[23],才能實現(xiàn)基于大數(shù)據(jù)、生物學信息的精準診斷,基于基因組學的靶點獲得和精準治療。追求微創(chuàng)化,崇尚“低碳”,實現(xiàn)個體化醫(yī)療,在有限的醫(yī)療投入下實現(xiàn)患者個體和群體獲益最大化。追求精準化、個體化、綜合化的多學科協(xié)作治療[24]是腫瘤治療的未來趨勢所在。
[1]Collins FS,Varmus H.A new initiative on precision medicine[J].N Engl J Med,2015,372(9):793-795.
[2]Lander ES.Cutting the Gordian helix—regulating genomic testing in the? era of precision medicine[J].N Engl J Med,2015,372(13):1185-1186.
[3]王巖.骨科精準醫(yī)療:應用與思考[J].中華醫(yī)學雜志,2015,95(31):2512-2515.
[4]Robinson PN.Deep phenotyping for precision medicine[J].Hum Mutat,2012,33(5):777-780.
[5]Chen C,He M,Zhu Y,et al.Five critical elements to ensure the precision medicine[J].Cancer Metastasis Rev,2015,34(2):313-318.
[6]Abrams J,Conley B,Mooney M,et al.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s Precision Medicine Initiatives for the new National Clinical Trials Network[J]. Am Soc Clin Oncol Educ Book,2014:71-76.
[7]Rubin MA.Health:make precision medicine work for cancer care[J].Nature,2015,520(7547):290-291.
[8]黃亨平,吳明松.內質網(wǎng)應激—腫瘤治療的新靶點[J].現(xiàn)代醫(yī)藥衛(wèi)生,2014,30(17):2600-2603.
[9]韋余達,李爽,劉改改,等.基因組編輯技術在干細胞疾病模型建立和精準醫(yī)療中的應用[J].遺傳,2015,37(10):983-991.
[10]羅小美,陳繼冰,牛立志.靶向免疫治療聯(lián)合放射治療在晚期黑色素瘤中的研究進展[J].中國腫瘤臨床,2015,42(4):255-258.
[11]蔣洪德.精準肝切除術治療肝膽管結石病78例效果分析[J].現(xiàn)代醫(yī)藥衛(wèi)生,2014,30(12):1826-1827.
[12]劉鵬飛,張會來.精準醫(yī)療在非小細胞肺癌中的應用[J].國際生物醫(yī)學工程雜志,2015,38(4):247-255.
[13]蔡尚,田野,徐波.腫瘤分子放射生物學在精準醫(yī)療時代的機遇與挑戰(zhàn)[J].中華放射腫瘤學雜志,2015,24(6):729-733.
[14]Dolsten M,S?gaard M.Precision medicine:an approach to R&D for delivering superior medicines to patients[J].Clin Transl Med,2012,1(1):7.
[15]Porche DJ.Precision medicine initiative[J].Am J Mens Health,2015,9(3):177.
[16]夏峰,韋邦福.精準醫(yī)療的理念及其技術體系[J].醫(yī)學與哲學,2010,31(11B):1-3.
[17]Mirnezami R,Nicholson J,Darzi A.Preparing for precision medicine[J].N Engl J Med,2012,366(6):489-491.
[18]Klauschen F,Andreeff M,Keilholz U,et al.The combinatorial complexity of cancer precision medicine[J].Oncoscience,2014,1(7):504-509.
[19]錢其軍,吳孟超.腫瘤精準細胞免疫治療:夢想照進現(xiàn)實[J].中國腫瘤生物治療雜志,2015,22(2):391-398.
[20]王海濤.去勢抵抗性前列腺癌精準醫(yī)學研究的探索[J].中國腫瘤臨床,2015,42(17):850-855.
[21]Kaufman HL.Precision immunology:the promise of immunotherapy for the treatment of cancer[J].J Clin Oncol,2015,33(12):1315-1317.
[22]鄧愛文,熊日波,曾參軍.精準醫(yī)學在外科領域的應用進展[J].南方醫(yī)科大學學報,2015,35(11):1662-1664.
[23]韓俊毅,陳炳官.精準醫(yī)療背景下基因和基因組學對外科疾病治療決策的影響[J].腹部外科,2015(4):292-293.
[24]Levy-Lahad E,Lahad A,King MC.Precision medicine meets public health:populationscreeningforBRCA1 and BRCA2[J].J Natl Cancer Inst,2014,107(1):420.
10.3969/j.issn.1009-5519.2016.21.016
A
1009-5519(2016)21-3306-03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81101727)。
△,E-mail:wyy301@hotmail.com。
(2016-04-04
2016-0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