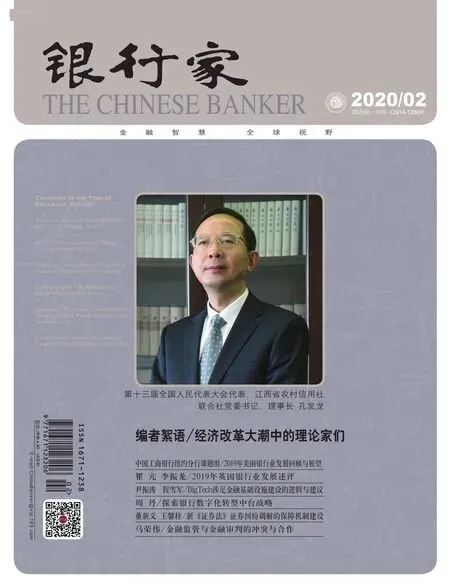杠桿率的宏觀審慎監管效果及其局限
章彰




杠桿率是金融危機后巴塞爾委員會提出的用于補充銀行資本充足率的宏觀審慎監管工具。籠統地說,杠桿率指標至少涵蓋了資產負債表杠桿、經濟杠桿和嵌套式杠桿三部分。銀行所有者權益與資產的比例即為資產負債表杠桿,也有的用資產與所有者權益的比例來表示,稱為杠桿倍數,它可以看作是財務杠桿,反映權益撬動資產的能力。假如銀行沒有表外資產,杠桿率就是指資產負債表杠桿。而經濟杠桿是資產負債表杠桿的延伸,其實是更加廣義的杠桿。對于銀行的一些表外資產(如貸款承諾),資產負債表杠桿不足以反映杠桿風險的全面性,經濟杠桿的概念由此而生。嵌套式杠桿則反映出金融創新的復雜性,指銀行持有金融資產中本身還有杠桿,是在杠桿之中嵌套杠桿,多層次的資產證券化、再次資產證券化或結構性信貸產品往往具有此類特征。全球銀行業3%的杠桿率監管目標底限應該是上述三種杠桿率的綜合反映。
宏觀審慎監管的新視角
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在2007年左右正式實施資本管理高級方法,實施后銀行風險加權資產計算變得非常復雜,而且計算結果難以在銀行之間進行比較,模型風險很大程度反映在風險加權資產中。金融危機后,模型風險廣為詬病。推出杠桿率作為監管指標是風險計量從復雜向簡單的回歸,它能排除模型對風險的影響,更加簡單和直觀地反映銀行承擔風險的大小,降低銀行之間比較風險大小的難度。這一目的從銀行杠桿率的計算口徑體現出來。杠桿率計算采用的風險暴露是四部分加總,包括(1)表內風險暴露;(2)以重置成本計算的衍生品風險暴露和潛在將來風險暴露附加;(3)證券融資交易產生的風險暴露;(4)表外風險暴露。其中(2)和(3)還有一些限定標準。全球銀行業從2018年1月1日開始正式實施杠桿率監管要求,并以3%為標準,杠桿率和資本充足率構成了“后危機時代”宏觀審慎監管的重要指標。
全球銀行業以3%為監管標準說明現階段只有部分銀行同時能夠滿足資本充足率和杠桿率雙重約束的要求,還有相當一部分銀行只能滿足資本充足率要求,杠桿率無法達標。2018年之前杠桿率不達標的銀行,必須要通過調整資產結構來降低自身的杠桿風險。我國銀監會在《商業銀行杠桿率管理辦法(修訂)》中明確要求,境內外上市的商業銀行以及未上市但上一年年末并表總資產超過1萬億人民幣的其他商業銀行需要披露杠桿率信息,從2015年4月1日起正式實施。
雖然我國正式實施杠桿率監管要求的時間尚不滿一年,但通過表1和圖1數據分析可以得出四點基本結論。
14家上市銀行一級資本充足率和杠桿率均能滿足最低監管要求。5家大型銀行的杠桿率均超過6%,其他9家銀行的杠桿率均未超過6%,反映出其他9家銀行比5家大型銀行使用了更高的杠桿,最低杠桿率4%的監管要求對9家銀行的約束作用更大,尤其是杠桿率最低的平安銀行已經接近4.5%。據巴塞爾委員會披露,2014年末大型國際活躍銀行平均杠桿率5%,而較小銀行平均杠桿率5.3%。簡單地類比,我國大型銀行好于國際同業,其他9家銀行與國際同業大致相當。
一級資本充足率和杠桿率對不同規模的銀行影響程度不同。規模越大的受到的影響越小。一級資本凈額、風險加權資產余額、調整后表內外資產余額最大,且一級資本充足率、杠桿率最高的工商銀行,調整后表內外資產余額增幅處于相對較低水平,意味著一級資本充足率和杠桿率的監管要求對其資產擴張影響不明顯。一級資本凈額、風險加權資產余額、調整后表內外資產余額最小,且一級資本充足率倒數第二、杠桿率倒數第三的寧波銀行,調整后表內外資產余額增幅處于相對較高水平。
系統重要性銀行和其他銀行在資產結構上差異不明顯。14家上市銀行在一級資本凈額、資產規模上差異較大,但與風險加權資產的余額相比,計算調整后表內外資產余額增加幅度基本處于40%~50%之間,只有民生銀行增幅不足40%。平安銀行和招商銀行增幅最高,反映出這兩家銀行資產結構與其他銀行存在不同,風險加權資產較低的資產占比高于其他銀行。
14家上市銀行杠桿率變化趨勢尚不明顯。除了中國銀行、農業銀行、交通銀行、浦發銀行和寧波銀行以外,其他9家銀行杠桿率均上升,南京銀行的杠桿率上升幅度最大,浦發銀行和寧波銀行杠桿率下降幅度最大。有國外的研究表明,杠桿率本身也具有親周期性。在經濟擴張期,銀行資產擴張能力強、盈利能力強,銀行杠桿率比經濟平穩期要高。在經濟衰退期,銀行不良貸款增加,盈利能力減弱,銀行杠桿率比經濟平穩期要低。有些國家的監管機構為抵消杠桿率指標的親周期性,考慮在經濟擴張期,設定杠桿率上限,在經濟衰退期,設定杠桿率下限,將杠桿率的監管目標鎖定在一定的區間范圍內。由于我國銀行業實施杠桿率監管要求時間尚短,杠桿率是否具有親周期性還需要持續觀察。
杠桿率與一級資本充足率的關聯關系
杠桿率與一級資本充足率之間存在關聯關系。如下所示:
杠桿率=(一級資本/風險加權資產)×(風險加權資產/表內外風險暴露)
可以將以上杠桿率計算公式轉換為:
杠桿率=一級資本充足率×每單位風險暴露的平均風險權重
如果銀行每單位風險暴露的平均風險權重(以下簡稱“平均風險權重”)能夠保持基本穩定,杠桿率和一級資本充足率之間是正向關系,杠桿倍數和一級資本充足率是反向關系。杠桿率越高,一級資本充足率越高,杠桿倍數越低。杠桿率越低,一級資本充足率越低,杠桿倍數越高。
我國銀監會對2016~2018年系統重要性銀行和其他銀行設定了一級資本充足率的底線目標,同時提出商業銀行并表和未并表的杠桿率均不得低于4%。由此可以推算出14家上市銀行在2016~2018年之間平均風險權重的上限(見表2)。
說明:在《關于實施<資本辦法>過渡期安排相關事項的通知》中明確,系統重要性銀行2016~2018年的一級資本充足率下限分別為8.7%、9.1%、9.5%,其他銀行一級資本充足率下限分別為7.7%、8.1%、8.5%。以上測算將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和建設銀行作為系統重要性銀行,其余的10家銀行作為其他銀行。
根據上述測算結果,2015年三季度末系統重要性銀行中平均風險權重最高的農業銀行和中國銀行在2016~2018年間需要將平均風險權重下降40%,其他銀行中平均風險權重最高的民生銀行需要下降30%,才能滿足最低監管要求。如果未來有其他銀行進入系統重要性銀行的行列,調整平均風險權重的壓力也將顯著增加。當然,如果平均風險權重保持2015年三季度末的水平不變,就需要在未來三年中持續增加一級資本總額,才能滿足監管要求。
我國銀行業杠桿率的監管標準4%高于3%的國際監管標準,我國已被確定為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的一級資本充足率要求也高于國際同業(分別是8.7%和8.5%),但在4%杠桿率和8.7%的一級資本充足率約束下,四家銀行的平均風險權重上限是45.89%,在3%杠桿率和8.5%的一級資本充足率約束下,國際同業的平均風險權重上限是35.29%。鑒于全球銀行業資產結構上的差異,我國的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資產結構調整的難度會大于國際同業。
杠桿率的宏觀審慎監管效果剖析
2008年金融危機后,美國和歐洲的監管機構加強對場外衍生品交易的監管力度,利率掉期、貨幣交叉掉期、信用違約掉期等交易被強制進行中央清算。就衍生品形成的風險暴露而言,杠桿率與資本充足率計算的規則并無本質差異。從信用風險加權資產計算的角度,在滿足一定條件下合格中央交易對手的信用風險權重僅2%,非中央交易對手的信用風險權重差異很大,但都遠高于2%。對于場外衍生品交易量較大的銀行,杠桿率受到的影響不大,資本充足率受到的影響較大。與衍生品交易不同,證券融資交易受到杠桿率的約束更大。按照資本充足率計算規則,回購或逆回購業務以不同類型的債券作為抵押品,根據債券的價格波動水平,設置債券價格的折扣率,合格的抵押品可以扣減風險暴露,與銀行開展回購或逆回購的交易對手方其信用風險權重對計算出的風險加權資產也有顯著影響,折扣率低的抵押品和信用風險低的交易對手使計算出的風險加權資產非常低。按照杠桿率計算規則,風險暴露與抵押品價值之間是否存在缺口是關鍵,無論抵押品性質和交易對手信用風險高低,只要抵押品價值低于風險暴露,就需要把差額加回到杠桿率分母中。例如,A銀行以國債作為抵押品向B銀行融資一億元,約定三個月后購回,扣減抵押品價值后,B銀行的凈風險暴露只有1000萬,如果A銀行信用風險權重為20%,B銀行這筆交易只計算200萬信用風險加權資產。8.5%的一級資本充足率監管要求意味著這筆交易需要17萬的一級資本。這筆交易反映在杠桿率中就有很大不同,B銀行的風險暴露金額除了融出的一億元以外,還需要計算抵押品缺口1000萬元,總共是1.1億元。4%的杠桿率監管要求意味著需要440萬的一級資本,是17萬的近26倍。杠桿率對證券融資業務的宏觀審慎監管效應非常明顯。
杠桿率對我國銀行業資產擴張的約束效應也會逐漸顯現,對表內資產約束大于對表外資產的約束。受到杠桿率約束最明顯的表內資產包括現金及存放央行資產、地方政府債券、同業資產及零售資產等。現金及存放央行資產信用風險權重為零,不會對資本充足率構成任何影響,但卻全額納入杠桿率分母的計算,對杠桿率產生影響。信用風險權重法下,地方政府債券風險權重20%,也需要全額納入杠桿率分母計算。地方政府債券對政府融資平臺貸款的替換降低了銀行的信用風險,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資本充足率,但對杠桿率卻不會有任何影響。銀行和我國其他商業銀行業務往來形成的資產一般是20%或25%的風險權重,個人住房抵押貸款的信用風險權重是50%,其他零售資產信用風險權重為75%,也都需要全額納入杠桿率計算的分母。杠桿率之所以對我國銀行業表外項目的影響不大,計算規則是主要原因。計算杠桿率時,表外項目中可隨時無條件撤銷的貸款承諾按照10%的信用轉換系數計算,比計算資本充足率時此類貸款承諾采用的信用轉換系數高,更加嚴格。但隨時無條件撤銷的貸款承諾主要是信用卡業務產生的承諾,這部分承諾形成的資產在銀行總資產中占比較低,實際上對杠桿率總體水平影響不大;而其他表外項目計算資本充足率和杠桿率采用的信用轉換系數完全相同,沒有體現出差異。此外,我國銀行業涉足衍生品業務和證券融資業務規模遠比國際同業小,杠桿率對這兩類業務的宏觀審慎監管效果并不明顯。
杠桿率的局限性及其改進
結合我國金融市場的情況,可以考慮按照“覆蓋范圍盡可能全面、集團內部不同金融機構之間盡可能比較、監管指標體系盡可能互補”的原則,完善杠桿率監管,構建防范系統性風險的宏觀審慎監管指標體系。
在計算范圍上,逐步將表外理財納入杠桿率計算的分母中。在理財業務的剛性兌付沒有打破的市場環境下,表外理財業務規模的迅速擴張必然增加銀行業的系統性風險。銀行之間的合謀可以進行監管套利,對宏觀審慎監管效果造成沖擊。舉個最簡單的例子,A銀行將理財募集資金以表外理財方式交給B銀行,B銀行同樣將理財募集資金以表外理財方式交給A銀行,A銀行的杠桿率和B銀行的杠桿率都不會反映,這是計算的遺漏項。據不完全統計,現階段大型銀行表外理財的規模遠高于表內理財,還有不斷增長的趨勢。如果宏觀審慎監管要求將表外理財納入銀行并表杠桿率計算之中,大型銀行的杠桿率可能并未如以上計算那么樂觀。
并表層面的杠桿率反映的是并表層面的一級資本和并表層面各類風險暴露的比例關系。出于銀行集團內防范不同法人機構杠桿風險的需要,也為了避免銀行集團內銀行與非銀行金融機構之間、非銀行金融機構之間在風險暴露計量規則上套利,盡可能統一銀行集團內納入并表范圍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如證券公司、保險公司、基金公司、投資公司、信托公司、租賃公司等)計算杠桿率的規則很有必要。證券公司持有凈資本目的在于清算資產時吸收市場價值變化產生的損失,保證證券公司的正常運行,保護投資者,從這個角度看與銀行持有監管資本的目的相同。計算證券公司的杠桿率可以考慮套用銀行杠桿率的方法,用凈資本除以風險暴露。證券公司資產負債表中的資產以交易性資產為主,這類資產承受的市場風險較大,每日市場價格波動會導致證券公司持有的交易性資產價值波動,反映為不同時點上杠桿率分母的變化可能很大。預計證券公司在不同時點上杠桿率的波動也會大于銀行杠桿率的波動。現階段,我國保險公司正在大力推進償二代標準,償二代標準下保險公司的資本分為核心資本和附屬資本,可以考慮將保險公司的核心資本作為杠桿率的分子。銀行集團內不同法人機構資本定義或許不同,作為一項基本原則,銀行集團內無論哪家法人機構開展衍生品業務或證券融資業務,由此形成的風險暴露在杠桿率的分母項上應該保持一致。為此,還需要進一步細化不同金融工具的嵌套式杠桿計算規則,避免復雜金融產品低估杠桿風險。
按照宏觀審慎監管的邏輯,杠桿率應該與資本充足率形成互補,對不同資產結構的銀行都能形成有力的約束。從我國銀行業的實踐來看,兩者的互補關系尚不突出。在引導銀行資產結構轉型方面,杠桿率甚至還蘊含著不審慎的激勵導向。持有較多流動性高資產的銀行和持有較多流動性低資產的銀行安全性不同,但在杠桿率指標上可能完全相同。過于強調杠桿率指標,也可能誘發銀行忽視流動性資產的配置。結合流動性覆蓋率和凈穩定融資比例的監管要求,逐步細化銀行集團內不同法人機構的流動性監管指標,盡可能統一同類資產的流動性風險折算系數,有利于提高宏觀審慎監管效果。
(作者單位:中國銀行風險管理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