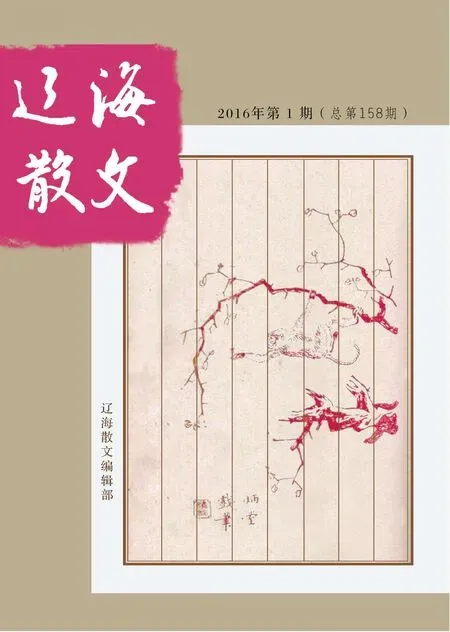傾蓋如故
莫永甫
傾蓋如故
莫永甫

莫永甫
現供職于本溪日報社,主任記者。遼寧省專家庫成員,遼寧省作家協會會員,遼寧省散文學會常務理事、副秘書長,本溪市社會科學學科帶頭人,本溪市政府成果一等獎獲得者,本溪市城市文化課題專家組成員。有專著《歷史 從本溪走過》《重啟歷史之門》《“第三只眼”看衛生》《風云平頂山》問世。
一
一次遠足,一方掛在想象力之外的宗教叢林不經意地停泊在旅途的岸邊,輕輕一瞥,熟悉的親切一下就蕩漾在心間。
想象力,來源于知識的積淀。沒去過黃鶴樓,可崔顥的《黃鶴樓》一詩為你的想象提供了空間。沒見過長江,可蘇軾一首《大江東去》的詞,那“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的描寫讓你對長江有了豐富的想象。
小興安嶺山麓處的歷史遺跡明命寺,矗立于我儲藏的文化空間之外,任我有如何豐富的想象力,都無法想象這座百年名剎具有怎樣的絕塵風姿。疏離如此,又何來輕瞥之下熟悉的親切?
二
呼蘭河源頭的桃山,可看者有四:呼蘭河,懸羊峰,紅松林,平頂山。呼蘭河可追溯蕭紅的文采風流;懸羊峰和紅松林可欣賞森林的自然風光;平頂山可給人登高遠眺、胸懷天下的快感。
呼蘭河源頭的桃山,必看者有一,那就是明命寺。
可看者是具有選擇性,必看者是刪除了選擇的余地,是必須看的景觀。桃山人對景觀的這種定位,不言而喻,是突出了明命寺的重要性。
在桃山的歷史記憶中,明命寺是唯一可觸、可感的歷史豐碑,對桃山的地域歷史文化具有無可替代性的優勢:清朝末年,黑龍江的道觀群中,明命寺的規模冠絕全省,并擁有了一位享譽全國的道教大家,一個小鎮擁有地位如此顯赫的文化名片,誰能不珍而寶之。
三
踏上旅途,沒有平坦,也沒有潔凈,猶如漫漶的歷史,隱隱忽忽,坑坑洼洼。心中一涼,沒有現代化的通途,昨日的歷史也就沒有多大的輝煌。
明命寺坐落的凌云峰,出現在眼前時不過數十米高的丘陵,與“凌云”相去甚遠,丘陵焉能承受名剎之氣勢,心中又一涼。
到得山門,正在興建的明命寺范圍宏大,但施工帶來的紛亂布滿眼前,想起時下流行的“先建廟,后造謠”的順口溜,心中再一涼。我開始質疑明命寺的輝煌歷史。
在我心往下沉之際,桃山林業局的文聯主席褚衍民的一句介紹飄入我的耳朵:“這地方,自興建后的100多年間,都屬于‘龍門派’的道場。”
褚衍民,是桃山文化的熱愛者、主持者和建設者,在桃山林業局領導的支持下,經由他的具體實施,有關桃山文化的書籍一本本問世,有關桃山文化的設施一座座建成,從而成就了桃山小鎮大文化的現象。由他口中說出來的“龍門派”三字馬上讓我對這地方熟悉起來,親切起來。這是什么原因呢?
只因東北道家的龍門派發源于我所在的城市——本溪。
中國的道教一為天師正一教,一為全真教,而以全真教的影響最為廣大。
全真教的祖師王重陽,有7個弟子,在金庸《射雕英雄傳》中,7個弟子個個了得。現實中,7個弟子確實本事非凡,個個都創立了自己的教派,成了開宗立派的一代宗師。《射雕英雄傳》中,7大弟子中的丘處機個性最為鮮明,在全真教的傳承中,丘處機也最為獨到,他創立的龍門派流風所及,涵蓋了關內的大部分地區。后來,因一個杰出弟子的出現,又把龍門派傳播到東北三省,使得東北的名山大川,處處飄揚著龍門派的大旗。
龍門派的這位杰出人物名為郭守真。
在明末清初的板蕩時節,一心向道的郭守真于1630年來到本溪鐵剎山修真問道,歷經30多年的拜師證道和潛修,終成一代大家。借奉天求雨而得以名聲大顯之機,在奉天創立了太清宮,并派遣弟子到各地建筑道觀,光大龍門派。一時間,龍門派得以一枝獨秀地在東北大地橫無際涯地發展,本溪鐵剎山也得以成為東北龍門派的祖庭而獨享尊榮。
眼下,這座毀后重修的寺院竟然是鐵剎山道觀的余緒,心里焉能不生親近之感。
隨之,好奇之心也開始膨脹起來。誰是這座道觀的肇始之人?誰是遵郭守真之命來黑龍江傳播龍門派之道旨的先祖?
詢問之下,褚衍民告訴我,來此修筑道觀的人叫孫永慶。
名剛入耳,心頭就猛地一震。
這名熟悉。
本溪人編著出版的 《增續九鼎鐵剎山志》第250頁載:“孫永慶,住江省鐵驪縣凌云山太圣宮。”“江省”即黑龍江省;“鐵驪縣”即鐵力縣;凌云山太圣宮即眼前的這座廟址。孫永慶收度弟子61人,影響紅極一時。
沿孫永慶上溯,又是出人意料的收獲。
孫永慶是龍門派的第18代弟子,他的業師是龍門派第17代弟子、黑龍江綏化慈云宮主持劉教賢。上溯到第9代的王太興,即為龍門派在黑龍江的開山之祖。
王太興,與本溪的淵源更為深厚。他原本就是東北道教龍門派的開山祖師郭守真的第二弟子,而且是在本溪鐵剎山收度的。后來,遵從郭守真的旨意,遠涉間關山水,來到黑龍江綏化,創建慈云宮,成了黑龍江道教龍門派的開山之祖。
在我認為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與我所在的城市疏離的地方,與我的文化認知不在同一區域的地方,因為道教的龍門派而得以熟悉起來,親切起來。難道文化如同人身之血脈,在體內無處不達?
歷史就是這樣讓人不可思議,文化也是這樣讓人不可思議。
四
眼前的一切,雖是毀損后的重建,但空置的土地仍是輝煌后的蒼茫。
1898年,48歲的孫永慶從綏化的慈云宮來到這里。孫永慶是一個出家比較晚的道士,原來的經歷我們不知道,但敢肯定的是,這人很有悟性,也很有道緣。要不,他不會在50歲的時候創下偌大的道業。當他在慈云宮時,在黑龍江龍門派的開山道庭里,他會想到慈云宮的祖師爺王太興來自本溪鐵剎山嗎?會想到回東北龍門派的祖庭瞻仰瞻仰、拜訪拜訪嗎?
也許有,也許沒有,但敢肯定的是,1898年以后的孫永慶滿腦袋裝著的是如何創建凌云山太圣宮,讓龍門派在這一方土地生根開花,讓道家文化在這里張演得繁花似錦。
他居住茅庵,在荒野之地,獨對日升月潛。
道教發展的歷史,有一條規律,常常是一些杰出人物,善于抓住到來的機會,建起了一個一個的道觀群,一波一波地向四周擴張。
凌云山不會給孫永慶這樣的機會,孫永慶是創造機會創建道觀的,這更顯出了孫永慶的不平凡。一個夏日,孫永慶看見凌云山東北山腰處有廟宇輝煌,如海市蜃樓般美麗,很久才散去。他為這個事很奇怪,幾年來盤旋心中不知其意。又過了幾年,孫永慶兩次在夢中夢見神仙,神仙伸手指著出現海市蜃樓美景的地方告訴他,此山乃福地仙鄉,應在此處修建廟宇。今天看來,孫永慶的奇遇大有杜撰的可能,但他杜撰得很有邏輯,并以此杜撰為自己創造了修廟建寺的機會,有如此智慧的人干什么事都能成功。
孫永慶的話讓眾善信們深以為是,從而開始了22年創建明命寺的征途。其間,孫永慶又獲得了別人捐助的100多畝荒地,又獲得了大財東金純廣財力、人力以及組織管理等多方面的極大幫助,整個的建設因他個人的影響而得以有利、有力地推進。
孫永慶未等到功德圓滿的這天就去世了,但他的徒弟劉園清、何園方等人把明命寺的建設推進得轟轟烈烈,并終在1919年完美竣工。
道家的傳承精神令人訝然,看道教的發展歷史,我會不自覺地和傳統的教育聯系起來。任何艱難、任何困苦,中國的教育家們為了弦歌不絕,一定是艱苦卓絕,教而忘私。抗戰時期的一批中國學人,為文化不絕,徒步數千里,來到云南重組西南聯大。戰爭年代,中國一流的學人們,常常饑不果腹。化學系教授黃子卿曾寫過一首詩記載當年的艱難困苦:
飯甑凝塵腹半虛,維摩病榻擁愁居。
草堂詩好難驅瘧,既典征裘又典書。
名人聞一多必須出售石章維持生計。學校常務委員梅貽琦的夫人與人合作制作糕點售賣維持一家人的溫飽。
正是這些優秀學人的堅守,西南聯大在最困難的歲月中,培養了楊振寧、吳健雄、鄧稼先等等科技巨子。
教育的成功,標志是人才培養。道家發展的成功,標志是師徒傳承。
東北龍門派的始祖郭守真,24歲來到本溪鐵剎山修真悟道,57歲時到奉天祈雨,解了旱情,自此,名聲大震。借此機遇,郭守真派遣徒弟到東北三省建寺筑觀,闡揚道教,龍門派得以風靡白山黑水間。郭守真的度世宏愿,沒有他14大弟子的繼承發揚,龍門派在東北也難有這一派大好形勢。
孫永慶開創的明命寺基業,如果沒有徒弟劉園清等人的繼承和強力推進,只能命歸夭折。
道有道統,教有教業。道之不存,統之焉附?教之不存,業之焉附?
孫永慶手下的61弟子,把明命寺的規模建成了黑龍江省之冠,并住持五大道觀,龍門派的影響冠絕一時。如此風氣和土壤,才培養出了黑龍江省道教大家劉明哲。說起劉明哲,他和沈陽太清宮方丈紀至隱、遼寧省道教協會會長房理家道誼深厚,而紀至隱來自本溪兜率宮,房理家來自本溪鐵剎山,又與本溪大有淵源。
離開本來與我毫無掛葛的明命寺,突然想到一句話:白首如新,傾蓋如故。文化讓我和明命寺有了熟悉之感、認知之感、親近之感。
責任編輯 潘 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