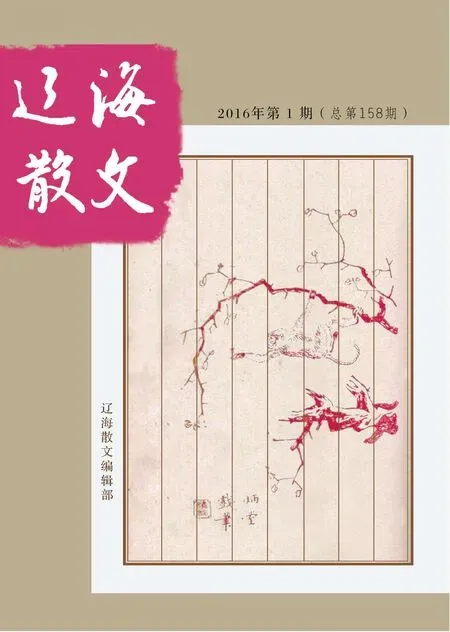父親的對聯,母親的年飯
春容
父親的對聯,母親的年飯
春容

春容
本名王春榮,遼寧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全國女性文學研究會委員,遼寧省婦女研究會副會長,遼寧省作協特邀評論家。出版個人專著、合著等共15部。在《文學評論》《文藝報》等報刊發表學術論文、評論多篇。偶有散文作品發表如 《苦瓜吟》等,出版哲學隨筆 《順其自然》。
早年,農村的年,格外像年。不像現在,城里的年不像年,農村的年也那么淡。年的味道寡淡得沒滋沒味。所以,上了點年紀的人,就像魯迅筆下的“九斤老太”,總是懷舊,總覺得這舊歷年像老太太過年——一年不如一年了。因為“格外像年”的年漸行漸遠,所以,它也就特別值得懷念,套用文壇老祖母冰心那句“童年就是一個深刻的夢”,可以說“格外像年”的年,就是我們一個深刻的童年夢。
早年的年,特別像年,因為那年味都是忙出來的。臘月底,年跟前,大人小孩兒都忙年。首先,年味是小孩子們“作”出來的。其次,年味是母親的手“做”出來的。還有,年味是父親的筆墨“寫”出來的。如此,一作、一做、一寫,那年味怎能不濃呢?而今,年復一年,幾十年過去了,我們只能不無傷感地問:“格外像年”的年哪里去了?原來,新媒體時代的年,都被小青年的“蘋果”遮蔽了,更被擁擠的民工潮打在回家的包裹里了,自然也被那個億萬人追捧的“春晚”替代了。這就難怪如今的年味兒那么寡淡。
孩子們作出的年味,是孩子的天性釀出來的歡樂。小時候,父母總是叨咕,過年,過年,就是“過孩子”。沒有孩子使勁作的年,就不像年。父母的“年經兒”,可把孩子們樂壞了,慣壞了。平日里,辛勞的父母忙于一家人的吃喝拉撒睡,無暇顧及孩子們。過年了,父母才把自己對孩子那大把大把的愛毫無保留地傾注在他們身上——放羊(養)。所以,過年時候的孩子最有天性,那就是可勁地作,理直氣壯地作,合理合法地作。哪怕上房揭瓦,父母也舍不得打,舍不得罵。再說了,過年打罵孩子屬于大忌。過年的時候,家家的男孩子都享有特權——可勁作,作出花兒來,大人們才高興。而男孩子過年最大的樂趣就是放鞭炮。衣服兜里裝滿了“大地紅”、小鋼鞭,手里拿著一支點燃的“巴蘭香”,舍不得一整串一整串放的小鞭,點著了,然后一個個地往外崩。那才叫過年呢,嘎嘎響,嘎嘎樂。記不清哪一年,有個淘氣的男孩子,看到奶奶在熱炕頭上睡得正香,就悄悄地把點著的小鞭放在奶奶手心里。結果把老太太崩得一個猛子從炕上躥到地上。再一看不得了,奶奶的手掌被小鞭崩得黢黑黢黑,雖然沒見血,也夠嚇人的。就算這樣,大人也就嚇唬嚇唬他,沒把他怎么樣。就算這樣,男孩子年年都享受著家族賦予他們的特權,照樣作,照樣淘。不作,不淘,沒年味。女孩子過年沒有男孩子的特權,也沒有男孩子那么淘氣,那么作。但是,女孩子也有女孩子的小心思:希望能有一件自己喜歡的花衣服。父母對女兒的小心愿自然心知肚明,就是再困難也想方設法為閨女置一件新衣服。父親辦年貨的時候,順便把家里準備來年用作種子的花生帶去賣掉,扯上幾尺花布,老閨女的新衣服就有著落了。“新年到,新年到,新年穿件花棉襖”,身穿花衣的女孩過年的時候總是離那些亂放小鞭的淘氣小子們遠遠的,生怕把新衣服崩壞了,弄臟了。年,對于鄉村女孩來說,就是一個“美”的 夢,一件可以在閨蜜面前臭顯擺的花布衫。
舊歷年的年味兒是女人的雙手“做”出來的。漿洗被褥、刷碗洗碟、撣灰掃塵、蒸年糕、炸面魚、擺供品,真是忙得腳打后腦勺。忙年的女人格外像女人,做供品,擺供桌,孝敬先人,這是母親們必須親手做的神圣活計。舊歷年,家家都供奉族譜。據說,族譜是請薩滿開了光的,族譜上面寫著列祖列宗的大號。供著宗譜的那面墻安放著一張印著福壽字樣的紅色桌圍子。這張印著福壽字樣的紅色桌圍子一年只能露一次面,只要母親把那個大紅桌圍子拿出來,孩子們就知道年來了。供桌上面擺滿了供品,各種美味佳肴分裝在八個大碗里,有豬頭肉、整條魚、油炸的馃子,還有白面大饅頭等等。每個供碗上面都有點綴,讓供品更好看,更讓先人滿意。“點綴”主要用粉絲,把粉絲用開水燙一下,或者把它扎上把,過一下油,那粉絲就像女人過年前在理發館燙的頭發一樣,曲里拐彎,煞是好看。然后,再用粉紅色的染料過一下色,碼在供碗上面,這就完美了。為了不讓家里的饞貓偷吃供品,大人們事前就用好吃的大魚大肉喂足了它,讓它吃膩了,供品就安全了。小時候,我們不太理解母親的做法,總是羨慕嫉妒恨那只饞貓。吃足了的饞貓過年的時候,就只管在熱熱的炕頭上打呼嚕,它已經酒足飯飽了。
忙年,母親最拿手的就是做年糕。秋收的時候,母親就把大黃米和黏高粱米精心地收藏起來備用。年前,如果能求來拉碾子的牲畜就用牲畜拉,求不來自然得人來拉。母親有時自己推著沉重的石碾子把黏米碾成黏米面。到了做年糕的時候先用開水把面粉燙一小部分,接著用笸籮搖啊搖,搖成小小的顆粒狀,然后把這些搖勻了的面粉均勻地撒在蒸屜上。撒的時候不能亂撒,一層大黃米面,一層紅高粱米面,一般撒四層就可以了。這還不算完,最上面要撒上秋天收藏的各種顏色的豆粒。紅紅的是小豆,白白的是大蕓豆粒,還有灰白色的花雀蛋豆粒。最后,用大劈柴燒火,蒸上一個小時,年糕的香甜味就冒出來了。香甜的年糕味冒出來了,家中每一個犄角旮旯都充滿著年味。可是,蒸好了的年糕,還不能吃——太燙。大人嚇唬小孩子:別急,先把饞蟲咽回去,要不能燙掉心!蒸好的年糕連蒸屜一起提出來放到廈屋涼涼了,再用大切刀一方方切好,碼在籃子里,掛在廈屋的房梁上,等著慢慢吃。切好的年糕一層一個顏色,紅黃搭配,兩色兩味,很漂亮。吃年糕的時候,桌子上一般都放上一碗糖水,年糕好吃不好消化,蘸著糖水吃,又香又甜,糯糯的,滑滑的,口感好極了。每當我們乖乖坐著吃年糕的時候,母親總是坐在一旁,用手攏著她那忙亂了的頭發,臉上帶著微笑,滿足地看著我們大口地嚼著年糕,嘴邊淌著糖水。若干年過去了,母親已經不在了,可是,其情其景,猶在眼前。對于子女來說,母親就是家,母親就是年。沒有母親的年不是年,沒有年糕的年,自然也沒有了年味兒。
女人們“做”年的時候,男人們就清閑多了,可以躺在熱炕頭上放長條兒。可以心安理得地吃著剛剛炸好的面馃子、炒花生。父親的年,卻沒有那么悠閑。每到年底,他就忙著搜集當年的對聯新詞,準備給鄉親們寫對聯。在我的記憶里,年復一年,我們全村的對聯都是父親的杰作。所以,如果說年是母親做出來的,在父親,年就是他的筆墨寫出來的。父親出身農家,但他有機會讀了三年私塾。母親常說,別看你爹只念了三年書,給個中學生都不換。那時候,我認為父親就是我見過的最有學問的人,私塾館也自然成了我童年的夢。說來很幸運,父親讀私塾的機會是撿來的。我祖父有五個兒子,三個女兒,可謂兒女齊全,多子多壽。五個兒子在祖父的眼里就是五條龍,調理好了,就會家業興旺。祖父精心地為他的五條蛟龍策劃著未來:大伯父協助祖父管家,家族“常務”;二伯父、三伯父種地、打魚,主勞力;老四,學做木匠活,掙現錢;老五,是老兒子,念書,識文斷字。可惜,祖父的如意算盤首先被他的老兒子打破了。老五,死活也不去念書。老叔說,那書上的字就像沒脫殼的蕎麥,像海邊礁石上長著的鴨食,黑壓壓的,見了就眼睛疼。就因為這,排行老四的父親,撿了個上學的機會。父親一邊學徒,做細木匠,一邊讀私塾,結果在這個大家庭里,我父親最合適,又學手藝,又有文化。事實上,做細木匠還真得有文化,二者互補。父親滿徒之后,他的手藝在左近村莊有口皆碑。誰家嫁姑娘娶媳婦打衣柜,都離不開我父親的手藝。他做的立柜,樣子好看,結實耐用,可以傳代。我老家直到現在還在使用父親做的立柜和“春凳”(一種橫放在立柜前面的長條、帶抽屜的凳子)。它像一件古董似的,見證著歲月的流失,記載著父親精湛的手藝。
父親“寫年”,我做“司書”。每到年底,按慣例,鄉親們都會把自家買的大紅紙按照需要裁好,什么大門對兒,房門對兒,廈屋對兒,包括牲口圈、雞窩、鴨架子等等的小條幅,卷好,寫上張三李四王五的戶主名,送到我家。我會按照先來后到給他們排好隊,再由父親給他們一份份寫好。寫好的對聯在炕上鋪開、晾干,再一份份地卷好,等著“用戶”來取。寫對聯沒有報酬,還要搭上筆墨和時間。可是,我們從不計較這些,而且這正是父親大顯身手、樂此不疲的好事。母親總說,寫對聯交人。交人,得干實事,不能光靠嘴出溜人。父親有一本收藏多年的楹聯書,好像是那種薄薄的宣紙,線裝的書,我記不太清楚了。每到過年前,我就驕傲地把它拿出來,把筆墨準備好。準備筆墨,我總認為那可是一門不小的學問。首先得把各種型號的毛筆用水泡好,泡到筆毛軟軟的,光光的,不帶一點舊墨痕跡。然后,磨墨。墨是一種叫“金不換”的長方形的墨塊。硯臺是一種沉甸甸的大方硯臺,能裝小半碗水。手把“金不換”在硯臺上一圈圈來回地磨,磨到什么程度得父親試寫一下之后才知道。父親不說好,我就一直在磨。父親寫對聯的時候,我在炕桌上鋪平對聯紙,用手輕輕地拽著,父親就在上面揮毫潑墨。那時候,我覺得父親是世界上最棒的父親,我是世界上最好的“司書”。一般情況下,父親都會按照舊詞寫,因為多數人家都喜歡舊詞的對聯,顯得更有年味兒。父親愿意寫舊詞,他說,舊詞大都是繁體字,筆畫多,寫起來,豐滿,好看。但是,父親本意是愛寫新詞,他說新詞有新意。父親年前也搜集點新詞,有的人家喜歡新詞,有新鮮感。至于那些小條幅,我也可以順口就念給父親寫,什么“五谷豐登”(貼在谷倉上的)、“六畜興旺”(貼在牲畜欄上的)、“肥豬滿圈”(貼在豬圈上的),以及“出門見財”“抬頭見喜”什么的。父親的字,不是顏體,也不是柳體,他自己說那就是“黑體”,是從私塾先生那里學來的一種自由體。那時候,我根本不懂毛筆字還有“體”之說。只要是父親寫的對聯,就是世上最好看的“體”。過年的時候,家家戶戶都貼上父親寫的對聯,我在小閨蜜面前總是覺得特有面子。有時,還不無虛榮地跟她們說,你家的對聯是我寫的。人家反駁我,你會寫?啊!那不是你爹寫的嗎?是我磨的墨,是我拽的紙。就是!就是!咋的?
陳舊的鄉村,家家戶戶,年復一年,變化是那么緩慢。但是,只有一年又一年的舊歷年,寫著“黑體字”的對聯才會把那舊意蓋了去,為陳舊的村莊裝點出一點點新意。如今,“農耕人家谷滿倉,書香門第春常在”的“黑體字”已經被千篇一律的“印刷體”覆蓋了,成了歷史。那些“格外像年”的年,已經離我們越來越遠了,留下的那一點點遺痕,便成了一種鄉村文化記憶,永遠揮之不去……
責任編輯 江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