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天石,從象牙塔走向聚光燈
肖瑩

楊天石和他的“書滿為患齋”。(本刊記者侯欣穎 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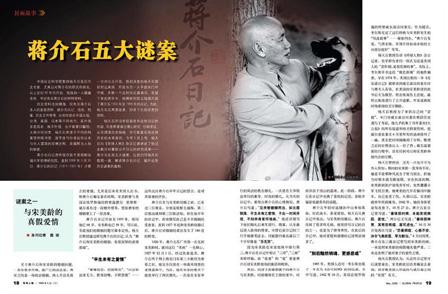
本刊2009年5月(下)總第81期封面欄目文章《蔣介石五大謎案》
歷史資料浩如煙海,僅有關蔣介石本人的直接資料,就分為日記、信函、檔案、歷史文件,等等,分別存放在中國大陸、中國臺灣、美國、日本等不同地方。其中很多是孤本,既不外借,也不能復印翻拍。大部分時間里,楊天石奔波于不同的檔案館和圖書館,逐字逐句抄錄這些從未與世人謀面的珍稀史料,發掘鮮為人知的秘密。
埋身書堆,楊天石翻出幾本仍飄著淡淡油墨香的樣書,向《環球人物》記者總結起自己的2015年:“我出版了一套7卷本的《楊天石評說近代史》,和美國傅高義教授一起主編了一套3卷本的《中日戰爭國際共同研究》,還再版了4本有關中國近代史和蔣介石的書……一共14本,大約600萬字。我這輩子,從來沒有在哪一年出過這么多書!”語氣里,有一種他自己都難以察覺的欣慰。
這間10平方米的辦公室,楊天石笑稱“書滿為患齋”。除了書架間狹長的過道和辦公桌前可丁可卯的空隙,整個屋子被泛黃的書籍資料堆滿,如果來訪的人超過兩個,就難有騰挪之地。從事近代史研究四五十年,楊天石有一多半時間在這局促的空間度過。那些故紙堆的背后是浩瀚的歷史,而他暢游其中,試圖打撈真相。
楊天石和他的一系列著作見證了幾股學界熱潮的發端、興起和回歸理性。剛剛過去的2015年,或許是由于“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這個重大時間節點,他的研究成果井噴式出版。當然,這一切的開端,還得從10年前那個3月的清晨說起。
胡喬木說:“你的路子是對的,要堅持這樣走下去”
10年前,楊天石已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員。
那年3月26日,寄存于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的部分蔣介石日記正式對外開放。楊天石和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張海鵬受邀,提前趕赴美國,準備盡早親見這批資料。25日夜里,年過七旬的他既興奮又緊張,拉著張海鵬做起了“攻略”:“明天看蔣介石日記的人肯定很多,咱們早一點去排隊。”
第二天一早,想象中的擁擠場景并沒有出現。當他們匆匆趕到研究院的檔案館外時,驚訝地發現四周一片空寂。“后來才知道,檔案館當時并沒有廣泛對外公布這個消息。之所以邀請我,是因為知道我一直在做蔣介石方面的研究。”
楊天石對蔣介石的研究,緣起于上世紀80年代。當時,他受命撰寫并主編《中華民國史》中的一卷——《北伐戰爭與北洋軍閥的覆滅》,蔣介石作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成了他繞不過去的研究對象。他到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查閱資料,第一次看到蔣介石的老師、秘書毛思誠藏在墻壁中才保存下來的一大批資料,如蔣介石日記類抄本、仿抄本以及電報、書信、文稿等,立即被吸引住了。
1988年,楊天石根據蔣介石日記及他與汪精衛之間往來函件等大批資料,發表了自己第一篇以蔣介石為研究對象的文章——《中山艦事件之謎》,多角度分析了中山艦事件的成因,指出其中有國民黨右派的陰謀,蔣介石誤信謠言、中了圈套的一面。胡喬木讀后,評價是一篇“有世界水平的文章”,親自接見并鼓勵他:“你的路子是對的,要堅持這樣走下去。”
2002年,楊天石出版了自己在該領域的第一本獨著——《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沒想到,與學界認可并肩抵達的,還有一場激烈的批判——有人化名攻擊他的書是在替“千古罪人”蔣介石翻案,甚至直接上書中央領導,要求對他進行處理。當時的社科院院長陳奎元受命仔細研讀,認為“這本書是扎實的學術著作,是研究不是吹捧”,兩位中央領導同志也做了指示和批語,這場持續了3個月的風波才畫上句號。也是因為這次風波,楊天石研究蔣介石的名聲從國內傳到國外。以至于胡佛檔案館決定開放蔣介石日記時,首先就邀請了楊天石。
檔案館對日記的存放極為嚴密,楊天石看到的只是縮微膠卷影印件。為了防止它們被夾帶出去,檔案館規定不能翻拍、復印,不能用電腦打字、錄入,只能用檔案館提供的紙和筆抄錄。于是,整整兩個半月,楊天石每天趕到檔案館,一頁一頁翻閱、摘抄,連中午都不出館,吃過自帶的便當后,一直工作到閉館。
蔣介石日記現存53年,分4年4批開放,楊天石也4次前往胡佛檔案館,共用10個半月,才將所有日記研讀完畢。他摘錄的三大摞、足足兩尺高的資料,如今整整齊齊擺放在“書滿為患齋”中。
隨著對這批日記的研究不斷深入,楊天石腦海中蔣介石的形象也漸漸豐滿起來。“我還在讀中學的時候,看到陳伯達的《人民公敵蔣介石》這本書,對蔣的印象定格在‘人民公敵這4個字。但現在,他的形象在我腦海中已經變得立體、豐富起來。”
毛澤東曾明確指出,蔣介石在抗戰中“有功勞”
第一個找上門來要為楊天石的研究出書的,是山西人民出版社。彼時,剛剛進入新世紀,蔣介石仍屬于“敏感人物”。楊天石回憶說:“對我的新書,統戰部認為‘有價值,但會引起爭論,建議不要出版。新聞出版總署卻堅持‘既然有價值,就應該出版。”幾經溝通,書稿被刪去一篇文章,其余部分一字不改。這篇文章的取舍,成了這本書的大陸版與香港版的唯一區別。
2008年,《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正式出版。它受到各方關注,首印的5萬冊很快售罄,楊天石本人也由此走出專業領域的象牙塔,開始被大眾知曉。
當年年底,深圳《商報》舉行“2008年度十大好書評選”,來自全國各地的50位專家一致將票投給了《找尋真實的蔣介石》,但有關方面最終將這本書從獲獎名單中拿掉了。隨后,沈陽一家報紙也決定將這本書評為年度十大好書,并請楊天石準備一份獲獎感言,可一個多月過去了,又沒了消息。楊天石忍不住打電話到報社:“你們不會也取消了我的獲獎資格吧?”對方連忙回應:“沒有,沒有,只不過……我們決定不對外宣傳了。”后來,楊天石收到一尊已經斷成兩截的水晶獎杯。如今,它和香港文化部門頒發的“香港書獎”獎杯一起放在“書滿為患齋”的書架上。

2016年1月14日,楊天石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本刊記者 侯欣穎 攝)
出版和獲獎都一波三折,楊天石卻并沒有后悔走上蔣介石研究這條路。“蔣介石活了88年,一生經歷了近代中國的許多大事,把他研究清楚了,給予準確的歷史定位,可以提高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科學水平,彰顯共產黨實事求是的精神與光明磊落的廣闊胸懷,有助于兩岸和平關系的建立和發展,促進國家民族的和諧與統一。”他還特別搬出書來,向《環球人物》記者解釋,“我說蔣介石在大陸時期有兩大功、兩大過是有根據的。僅就抗日這一點來說,1943年,毛澤東在發給彭德懷的電報中明確肯定‘蔣在抗戰中有功勞;1991年,由胡繩主編、經胡喬木審定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一書中明確寫道,蔣介石‘承認第二次國共合作,實行抗日戰爭,是對國家民族立了一個大功。我不過是用自己的研究進一步闡述了這些說法而已。”
事情的轉機出現在2009年。那年年初,中國圖書評論學會聯合全國31家媒體評選“2008年度十大好書”,決定無論如何要將這個獎項頒給《找尋真實的蔣介石》。雖然是遲來的肯定,楊天石還是很高興。這個獎項的意義在于,他的研究第一次得到專業層面和輿論界的正式認可。
楊天石的研究和生活就這樣潛移默化地改變了。他在海內外旅行,常能聽見有越來越多的人、用越來越理性的聲音談論蔣介石,也常能聽見對他的理論探索和研究勇氣的肯定。“曾經的那個頭上長瘡、腳底流膿的‘蔣禿子‘蔣該死(寧波話里蔣介石的發音)的形象,在不少人的心中都發生了變化。”
或許是看到市場反應的熱烈,很快,有人開始緊跟楊天石的腳步,從各個角度出書“解密蔣介石”。有一段時間,市場上有關蔣介石題材的作品多達上百種。“其實資料只有那么多,尤其是新資料。有幾個人真正靜下心來把材料研究透了再動筆?往往是抓到一點點材料就趕緊用最短的時間拋出一本書來,先搶占市場再說。”楊天石對這樣的“學術現實”有點無奈,只是繼續埋頭,按自己的節奏做著研究。
“民國熱”從險學成顯學
從2006年赴美國研讀蔣介石日記,至2015年學術成果井噴式出版,楊天石在這10年中的經歷,與整個社會“民國熱”的發展大體合拍。
通常,民國時期指的是1911年辛亥革命結束清王朝統治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這38年時間。作為距離我們最近的一段“大歷史”,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有關民國的話題常被貼上“敏感”的標簽。即便解讀,也是臉譜化、教條化的,缺乏鮮活的血肉和細節。
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人們思想的逐漸解放、檔案的逐步公開,以及歷史敘事范式的日漸多元,以往單線條解讀民國史的模式受到沖擊。“老百姓越來越希望了解那個距離我們最近的昨天,渴望了解真相、還原歷史。”楊天石說,正是基于這種對民國歷史再認識的需求,才有了“民國熱”。
2005年,一套由葉圣陶編纂、豐子愷繪圖,首次出版于1932年的《開明國語課本》經重印悄然面世。但彼時,“民國”還沒熱起來,它也并未引起太大反響。
2006年,海南出版社以《武夫當國》為題,重新推出民國著名記者陶菊隱的《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5冊、146萬字的龐大體例,生動勾勒了一段上自袁世凱朝鮮發跡、下至張學良東北易幟的風云變幻,將民國時期軍隊間的格殺、軍閥們的密室陰謀活靈活現地重現在世人面前。雖然有不少學者對這種全景式的寫法提出疑義,但書中記載的翔實史料,還是激發了人們的強烈興趣。
2010年9月,陳丹青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提出,民國人的精神、氣節、習性、禮儀都帶有一種特殊的“范兒”。一時間, “民國范兒”成為文化熱詞。不過,一些人對民國的一切人和事不加區分地予以追捧,使得這一熱詞被過度解讀。
一些學者的相關研究很快受到關注:錢理群對魯迅的持續解讀,許紀霖對民國文人的深度剖析,余英時從陳寅恪文集中看出中國情懷,羅志田注意到清末民初文化的裂變與傳承。出版市場也迅速反應過來。《開明國語課本》再次重印出版,很快就脫銷,《西南聯大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南渡北歸》等相關著作,接連創下圖書銷售紀錄。
2011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持編纂、精心打磨了三四十年之久的《中華民國史》終于在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際出版。在楊天石看來,這似乎標志著“民國熱”達到高潮。

陳丹青畫作《國學研究院》。他所提出的“民國范兒”,在近些年成為社會文化熱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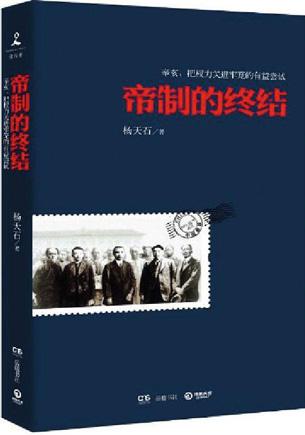
楊天石近作《帝制的終結》封面。
“曾經,大家嚷嚷著‘史學危機。歷史學家寫的書沒人愿意出版,就算好不容易開印,能有3000冊印量就不錯了,還不一定能賣出去。現在不一樣了。因為‘民國熱,大陸學者的作品已經滿足不了讀者的需求,不少出版社只能轉而從臺灣引進歷史著作。我在臺灣的一些學者朋友,幾乎都在大陸出了書,而且銷量都不錯。”楊天石所從事的研究領域,從幾十年前的險學,變成了如今的顯學。
這樣的市場繁榮之下,一些出版商和作者為了攫取短期利益,開始劍走偏鋒。曾經波瀾壯闊的歷史,被簡單消減為所謂的“小故事”“小片段”,干癟而片面,難以撐起宏大的主題。只要感性不要理性,只要娛樂不要深刻,“民國熱”就這樣被過度娛樂化了。最嚴重的是,有的作者和出版社偽造蔣介石日記、偽造宋美齡的歷史,雖經揭發、批評,卻一版再版,堂而皇之地出售而毫無顧忌。
如今,回望這10年間民國圖書出版的高低起伏,楊天石的感情復雜極了。究竟是《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踩準了“民國熱”的節奏,還是自己也成了這股浪潮的中堅力量?這是個一時無解的問題。
擦亮歷史的鏡面
事實上,“民國熱”只是近年來歷史熱的諸多表現形式之一。《環球人物》記者查閱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發現,從2006年至2013年這8年間,歷史、地理圖書的年出版種數從9000余種攀升至近1.7萬種,且漲幅逐年遞增,直至近兩三年才止步趨穩。
學者們對打撈歷史的熱情,被前所未有地激發出來。
復旦大學教授陳尚君長期致力于唐代文獻的搜集整理、考訂補正。2005年,他重輯出版了372萬字的《舊五代史新輯會證》。業內普遍認為,他用11年時間“打撈”出唐、宋之間湮沒、缺失的歷史,為此后的五代史研究提供了最原始完備的五代文獻。
“從十幾萬頁的解密檔案里尋訪歷史,既是我每天的工作,也是我一直以來堅持的信仰。”說這句話的,是中國冷戰史研究“第一人”沈志華。1996年至2002年間,他個人出資140萬元,從俄羅斯和美國搜集俄國解密檔案1.5萬余件。那之后,沈志華不斷從檔案中“發現歷史”。2007年,他與幾位學者聯手出版了《中蘇關系史綱(1917—1991)》,對中蘇關系的許多重大事件做出新的注釋;2009年,他任主編的《美國對華情報解密檔案(1948—1976)》出版,較為全面系統地展示了冷戰時期美國情報機構對中國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狀況的認知、分析、評判和預測;2012年,他在《冷戰五書》中首次披露俄國檔案館關于朝鮮戰爭的解密文件,揭示了朝鮮戰爭爆發的歷史真相;2015年,由他主編的12卷本《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系(1945—1991)》出版,包括不少孤本在內的2600余件中蘇檔案得以面世,為中共黨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外交史、冷戰史的研究提供文獻史料的支撐……
楊天石也將此前參與寫作《中國通史》時的6萬字初稿翻了出來,擴展、豐富、提煉,在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際出版了36萬字的《帝制的終結》一書。究竟什么階級、階層是這場革命的領導者?辛亥革命為何犧牲很少,卻迅速取得勝利?孫中山讓位于袁世凱是由于軟弱性和不徹底性嗎?每一個問號后面,楊天石都用多年辛勤搜集的大量史料,特別是新史料來回答。
辛亥革命及抗日戰爭勝利等一系列紀念日的接連到來,推動著整個社會為打撈歷史行動起來。
2011年,由南京大學教師聯合兄弟院校、研究機構完成的《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全部出版完成。編著過程中,百余名專家、學者為獲取一手史料,先后赴日本、美國、英國、德國、中國臺灣等地,進行了經年累月的搜求與整理。這套共72卷、4200萬字的巨著,是世界上關于南京大屠殺最翔實的史料集。
2014年5月,中國僑聯開始在全球華僑華人中征集二戰時期日本軍國主義罪行史料。最終,共有6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數萬名僑胞、社會熱心人士提供了1萬余張電子圖片、2000余張實物照片、1000余冊書籍、100余分鐘視頻等珍貴史料,涉及日本軍國主義在太平洋戰爭中的各種反人類暴行……
就連境外學者也開始反思中國在世界近代史中的作用和地位。“過去,西方學者回顧二戰歷史,從不提中國。近些年,越來越多來自英國、美國甚至日本的學者開始意識到,中國是這段歷史中無法回避的關鍵。”楊天石給《環球人物》記者舉例,“英國學者拉納·米特就出版了一本書,《中國,被遺忘的盟友》,專門講述了西方人眼中的中華民族抗日戰爭全史,引起國際上的廣泛關注。”
如果說歷史是一面鏡子,那些曾經因為資料的缺失、觀點的偏頗變得模糊的鏡面,正經由這一雙雙“打撈歷史之手”重新恢復锃亮。正如楊天石對《環球人物》記者所說的:“歷史是復雜的,歷史人物也并非簡單的忠奸立辨、黑白分明。歷史學家的使命,就在于科學、正確地去打撈它、敘述它、評價它。”
“民族振興是我們刻骨銘心的向往”

楊天石(中)和資中筠(左二)等中央文史館館員在廣西采風。
當相對專業的史學研究以可讀性極強的方式呈現在讀者面前,原本生活在公眾視線之外的楊天石,煥發出學術生涯的“第二春”。而和他同樣被“學術第二春”激勵著,成為這個時代中堅力量的,還有他的朋友們:著名紅學家周思源、著名古歷史專家李學勤、著名國際問題專家資中筠……
“周思源是我的中學校友,比我低兩級。他做紅學研究、寫歷史小說,2013年還在央視《百家講壇》開講《千古一后》。可以說,這些年一直處于發展的狀態。”楊天石頗為佩服這位“老弟”的豐沛精力。
交往更多的,則是中央文史研究館的一批學者們。文史館是1951年由毛澤東倡議設立的,具有統戰性、榮譽性的文史研究機構,楊天石于1998年9月8日被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镕基聘為文史館館員。
“因為統戰性的定位,文史館最初規定,館員應以非黨員為主,共產黨員數量不能超過館員總數的5%。后來,主辦機關改變思路,想將文史館辦成名人館,把文史學界最著名的學者都請進來。”楊天石回憶說,“李學勤在研究中國古代歷史方面是國內頂尖專家,對甲骨文、鐘鼎文、簡帛學都十分精通,文史館很想將他吸納為館員。一位領導問我,‘李學勤是不是黨員?他當然是!按當時的規定,不能聘任他為文史館館員。最后領導下定決心,改了這條規定。”
資中筠是在這之后加入文史館大家庭的。
2009年,文史館有意聘任資中筠為館員。最初,她很干脆地拒絕了,并坦率說出自己的理由:一旦有了文史館館員的身份,在某種意義上就要代表官方發表看法,如果再就某些問題發表意見就不那么方便了。“這件事被上報到溫家寶總理那兒,溫總理當即表示,‘我們文史館正需要這樣敢講話、敢提出不同意見的人!”
資中筠加入文史館后,楊天石和她的接觸漸漸多了起來,發現她“確實比較敢講話,而且常常講一些別人講不出來的話”。
她環顧“大國崛起”的語境,毫不客氣地對愛國口號下滋長起來的虛驕之氣予以否定,面對“國學熱”的興起,又冷靜地提示要警惕“三從四德”、豪華殯葬等封建糟粕的借尸還魂。她一如既往地圍繞著知識分子與啟蒙問題展開思考,發表了諸多文章,并表達了不少觀點,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僅2011年,這位已逾八旬的學者就憑借《資中筠自選集》等3套著作頻頻現身各大圖書排行榜。
資中筠曾說,自己這一代知識分子,“盡管經歷不盡相同,還原底色卻有相似之處”。“民族振興是我們刻骨銘心的向往。我從未‘居廟堂之高,卻也不算‘處江湖之遠,不論在哪個時代,自己處境如何,對民族前途總是本能地有一份責任感和擔當……”對于她這樣的說法,楊天石也欣然點頭稱是:“我們這一代人,經歷了太多的歷史轉折,所以會比較敏銳地發現一些問題,也比較敢言。”
如今,資中筠聽從朋友的建議,申請了自己的微信公眾號,作為重發有價值舊文、澄清冒名之作的大本營。楊天石對微信的態度卻完全不同:“我也會用,但絕不在微信上發表任何意見。”他說,自己現在只想韜光養晦,把自己想做的研究做完,對過往的研究作一個總結性歸納,然后正式和蔣介石這個研究課題告別。
“至于下一步,很多出版社的朋友希望我能寫一本《蔣介石傳》,但我還沒有下定決心要不要去做這件事情。如果有可能,我想寫一本有關宋明理學的書……”楊天石坐在那里,面向鏡頭,目光深邃。他仿佛透過相機,看到了未來的自己,“我不知道上帝還給我留下多長時間。在我去見上帝之前,有幾件事情若是不做完,我會閉不上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