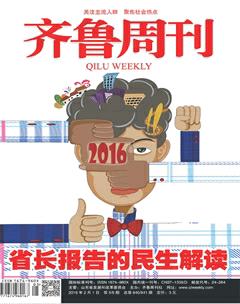一鞭子打醒春天□宋長征
伴隨新年的腳步,春天也來了。立春伊始,萬象更新。宋長征的散文《一鞭子打醒春天》,是其系列散文《鄉村游戲譜》中的一篇,講述立春這一天的特殊節日:鞭春牛,古老而又獨具農耕文明特質。“年味”逐漸籠罩,閱讀郭廣生的《如約那盞燈》,一段溫馨的愛情和警察堅守崗位的不辭辛勞,讓人心生暖意。
鞭春牛:喜慶節日,一年農耕初始,造泥牛置于街,內藏花生糖果。牽牛、趕牛者多為成人,花衣涂面,且趕且唱《鞭牛曲》。我家養牛,黑老犍,胛高背闊,拖曳時光前行。只是捶牛過于殘忍,縛于大樹,將睪丸擊碎。痛哉!鞭打春牛春初始,萬象更新好種田。
——題記
牛是大地的忍者,是力量之神的化身,高高的肩胛,像一座鼓鼓的山包,平展的腰身,能安放沉重而素樸的流年。牛的眼,因布滿春天的底色而清澈,而純凈,而飽含對人世的悲憫。一架沉重的犁杖,除了能犁開深深的泥土,還能犁開一個人往日的記憶。牛有著世間最為隱忍的性格,就像一個生在鄉間的農人,躬耕于野,只為粒粒深情的谷物。牛的要求最為低廉,用血汗換回瑩潤的谷物,卻甘愿咀嚼粗糲的稻草。
父親在老屋里抽煙,劣質的煙草氣息,混合著牛重重的鼻息。土墻上,牛的身影厚重而立體,折射出我們家艱難的生活。那些失去了汁液與養分的麥草,被咀嚼,被強大的牛的胃囊融解,就像我們吞咽一場場苦難的風雨。
日子總會慢慢好起來的,父親說。日子總會慢慢好起來的,村莊里的很多人說。這是一句難以求解的方程,我不知道他們的理由來自哪里。家,就是一個個破舊的院落,人,就是一個個面容憔悴的人。好像只有眼神落在牛的身上時,才驟然閃現希望之光。
立春是二十四節氣的第一個節氣,是天文意義上的春季的開始。立,始建也。春氣始而建立也。從這一天開始,氣溫,日照,降雨,開始趨于上升、增多,有利于春耕,有利于種子發芽生長。
鞭春牛,一個形式大于內容的民間儀式,代表村莊里的人對春天到來的歡欣,也代表春耕大忙即將開始。每個人的眼中都生出一縷綠色的焰火,每個人心里的那塊土地在漸漸復蘇,每個人喜形于色,好像一縷縷春風通過萬千個毛孔滲透進日日與泥土相親的血肉。
我們是把鞭春牛當做一場盛大的游戲看待的,同時,也有一些小小的期盼藏在心底。探花爺領著,頭上戴著高高的紙做的頭飾,身穿藏青色土布棉袍,動作夸張而神采飛揚。所謂的春鞭,是用五色紙糊成,在手中隨著身體有節奏的律動而搖晃。身后是另外一些或戴面具,或者化了濃妝的村人,每人手中都有一把形而上的春鞭,每個人口中都念念有詞,像是一場神秘而莊嚴的儺戲。
“一鞭曰風調雨順,二鞭曰國泰民安,三鞭曰天子萬歲春。”我不知道何時流傳下來的鞭牛曲,一經探花爺的嘴跌宕起伏,聲聲震痛鼓膜,一縷飄到天上,喚來春風春雨,一縷穿過田野,喚醒沉睡一冬的土地。所謂的春牛,就是泥塑的土牛,由幾個壯年勞力抬到村口,牛頭朝向無邊的田野,身后是我們居住多年的村莊。探花爺一聲喊——鞭春牛啰!很多支春鞭揚起,擊碎土牛龐大的身軀,大人搶碎裂的土塊,我們搶牛身子里預先放好的花生糖塊,此謂之“搶春”。
高承在《事物紀原》載:“周公始制立春土牛,蓋出土牛以示農耕早晚。”是說周族是農業民族,統治者又重視農業,周公制鞭牛之禮是完全可能的。《周禮·月令》:“出土牛以送寒氣。”漢代鞭春牛已相當流行。《后漢書·禮儀志》:“立春日,……京師百官皆衣青衣,郡國縣道官下至斗食令吏皆服青幘,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門外以示兆民。”這說明鞭春牛的習俗在很早的農耕時代就已經出現,并作為一種神圣的儀式流傳于大江南北。
我對牛的印象深刻,完全出于我家很多年一直養牛。父親在月光下鍘草,麥草,稻草,玉米稈,在月光下被鍘成一寸寸小段兒,這些來自大地上的草木,最后經由一頭牛重返田野。所以,我從不拒絕一頭牲靈溫順的目光。它們不會像人一樣思想,也不會我們的蠅營狗茍,甚至不知道什么才是自己的權利,只承擔起耕種的義務。它的肩胛是為田野而生,它的力量是為大地而蘊藏。它的眼神呢,是在告訴我們每一個人的來處無非是草木深處的一座座村莊。
一個人生而為人不是來世間攫獲的,是一種與自然萬物同呼吸共命運肉體與精神的雙重體驗。牛所具有的悲憫,應該就是神的指引,牛所具有的草木情懷,就是我們應該遵循的秩序與持守。
紀曉嵐在《閱微草堂》中有《戒殺牛》一章:“里有古氏,業屠牛,所殺不可縷數。后古叟目雙瞽。古嫗臨歿時,肌膚潰烈,痛苦萬狀,自言冥司仿屠牛之法宰割我。呼號月余乃終。侍姬之母沈媼,親睹其事。”是說古家以殺牛為生,后來古老漢雙目失明,妻子臨死的時候患了肌膚潰爛病,說是冥司用殺牛的方法割宰她,慘叫了一個多月才死去。
我相信這是一個流傳已久的民間傳說,以果報的方式告訴人們要善意對待世間的牲靈。信神在而為信仰,有了信仰才有對天地萬物的敬畏,有敬畏才會喚醒一個人的初心。除此之外,人間別無他途。
(宋長征,青年作家,菏澤成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