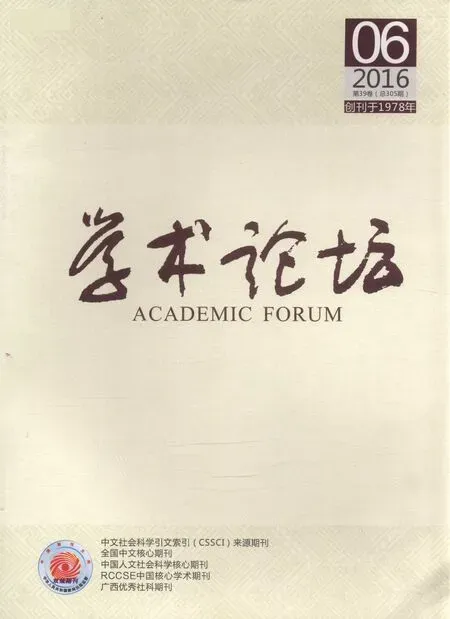半閉海制度對南海低敏感領域合作的啟示
張穎
半閉海制度對南海低敏感領域合作的啟示
張穎
[摘要]《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半閉海制度為半閉海區域的沿岸國家開展海洋合作提供了法律依據,倡導在相關國際組織的參與下從海洋生物資源開發、海洋環境保護和海洋科學考察三個方面開展具體的合作。中國應借鑒半閉海制度的實踐經驗,從漁業資源管理和養護合作著手,進而擴大到海洋環境保護、海洋科研等低敏感領域的合作。這樣做不僅能降低區域內沖突的敏感性,更有助于區域內各國的良性互動,并為未來海底油氣等非生物資源的合作直至南海海域爭端的最終解決尋求契機。
[關鍵詞]海洋法公約;半閉海;南海;低敏感領域合作
由于南海在經濟和政治戰略上的雙重重要性,近年來圍繞南海島嶼主權歸屬和海域管轄劃界的紛爭波譎云詭,因為該問題涉及到各爭端方的實際利益,因此運用國際法來解決南海爭端并非易事。也正因為如此,在探尋南海問題解決的道路上,我國政府一直倡導“擱置爭議、共同開發”[1]。國內外的一些學者也建議南海各方應加強互信,從“低處的果子摘起”[2];“首先實施低層面(低敏感)領域的合作”[3];還有學者進一步提出了低敏感領域合作所涉及的主要方面[4]。這些建議是具有現實性的,尤其在現階段,通過開展低敏感領域的合作來加強互信和聯系,對南海爭端的緩解或為日后能夠最終地解決具有現實意義。那么這些合作應該如何開展?相比于《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以下稱《海洋法公約》)在解決南海主權爭議問題上的諸多缺陷[5][6],在倡導和推進海洋合作的問題上,被譽為“海洋憲章”的《海洋法公約》有沒有相關的制度能夠為南海的低敏感領域合作提供依據和幫助呢?答案是肯定的,《海洋法公約》所規定的半閉海制度①根據海洋法公約第九部分“閉海或半閉海”的規定,對這兩個制度的規定是相同的。由于本文旨在討論南海的區域合作問題,故在行文中僅涉及其中的半閉海制度。,特別是有關生物資源管理和海洋環境保護方面的區域安排與合作制度,能夠為南海的低敏感領域合作提供一些思路和啟示。
一、半閉海制度及其對南海的適用
(一)半閉海制度的由來
半閉海問題是第三次聯合國海洋法會議列入的一項新議題。在1972年3月召開的海底委員會上,由56個亞、非、拉發展中國家提出的“海洋法項目和問題綜合清單”中的第17項為“閉海和半閉海”。這項綜合清單后來被海底委員會核準,從而使閉海和半閉海項目正式列入海洋法會議的議程之中。經過四期協商討論會議,在最后獲得通過的UNCLOS中,其第九部分規定了半閉海制度,共有兩個條款,分別是第122條半閉海的定義、第123條半閉海的合作。需要注意的是,半閉海制度本身所包含的諸多法律問題并未在UNCLOS的規定中得到全部體現,比如半閉海的海洋劃界、航行權利問題等,這一結果既反映了這些問題的敏感性,也說明美國、前蘇聯等海洋大國為維護自身的利益而對UNCLOS的制定所產生的影響。
(二)半閉海制度釋義及其對南海的適用
UNCLOS第122條規定:“為本公約的目的,‘閉海或半閉海’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所環繞并由一個狹窄的出口連接到另一個海或洋,或全部或主要由兩個或兩個以上沿海國的領海和專屬經濟區構成的海灣、海盆或海域。”
UNCLOS沒有分別對閉海或半閉海進行定義,而是通過兩個標準一并對其進行了規定,即:(1)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所環繞并由一個狹窄的出口連接到另一個海或洋的海灣、海盆或海域;(2)全部或主要由兩個或兩個以上沿海國的領海和專屬經濟區構成的海灣、海盆和海域。符合其中的任何一個標準,即可被認為是閉海或半閉海。
關于半閉海的合作,UNCLOS第123條規定:“閉海或半閉海沿岸國在行使和履行本公約所規定的權利和義務時,應互相合作。為此目的,這些國家應盡力直接或通過適當區域組織:(a)協調海洋生物資源的管理、養護、勘探和開發;(b)協調行使和履行其在保護和保全海洋環境方面的權利和義務;(c)協調其科學研究政策,并在適當情形下在該地區進行聯合的科學研究方案;(d)在適當情形下,邀請其他有關國家或國際組織與其合作以推行本條的規定。”本條使用的措辭“應互相合作”和“應盡力”,使得本條所規定的合作更傾向于一種倡議,而不是一種強制性義務。
從上述規定來看,半閉海的定義所包含的范圍非常廣泛,許多海域都在閉海或半閉海的范圍內,如地中海、波羅的海、加勒比海、北海、東海(東中國海)、黃海等,當然也包括南海。
雖然中國官方沒有對南海的地理范圍做出界定,但是從地理上看,南海是位于中國南部的陸緣海,被中國大陸、中國臺灣島、菲律賓群島、大巽他群島及中南半島所環繞,為西太平洋的一部分。南海的地理概況符合上述第122條釋義中的第2種情形,即“全部或主要由兩個或兩個以上沿海國的領海和專屬經濟區構成的海灣、海盆和海域”。此外,通過國內外學者對南海地理概況的描述,不難發現各國政府和國內外的學者對南海屬于半閉海這一認識并無爭議。
二、半閉海——地中海區域的合作實踐
地中海是一個位于歐、亞、非三洲之間的海域,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海之一。它由北面的歐洲大陸、南面的非洲大陸及東面的亞洲大陸包圍,面積251.6平方千米,沿岸共22個國家。位于其西北面的是三個高度發達的工業化國家,東北面是一些工業化發展程度有限的國家,東面和南面則是數量較多的發展中國家。地中海西部通過直布羅陀海峽與大西洋相接,東部通過土耳其海峽(達達尼爾海峽和博斯普魯斯海峽、馬爾馬拉海)和黑海相連。19世紀時開通蘇伊士運河,接通了地中海與紅海。作為世界上最大的陸間海,地中海有著復雜的地質地理環境和極具差異化的沿岸國家,幾乎體現了半閉海區域海洋合作所可能包括的所有問題。
(一)海洋生物資源管理
早在1982年《海洋法公約》通過以前,FAO大會在1949年9月24日就已經通過了《關于建立地中海漁業一般委員會的協議》(General Fisheries Commission for Mediterranean,以下簡稱GFCM協議),負責管理地中海的資源,協議于1952年2月20日生效,并分別于1963、1976、1997年進行了修訂①1997年的修訂通過了兩項修正案,一個是允許FAO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成員成為GFCM的成員,并將地中海漁業總理事會(Council)的名稱改為地中海漁業一般委員會(Commission);另一是關于委員會的自主預算問題,即和FAO的預算“去聯系化”,包括對成員方添加新的義務。修正案已于2004年獲得委員會三分之二的成員方接受后生效。。GFCM協議共17條,主要內容包括委員會及其成員資格②GFCM協議第1條第2款規定了委員會的成員資格,即向FAO的組織會員和合作會員開放,以及雖未非組織會員,但滿足以下條件之一的聯合國、聯合國所屬專門機構或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的會員開放:(1)沿岸國或合作會員國之領土全部或部分位于區域內;(2)沿岸國或合作會員國之漁船在區域內捕撈本條約所規定之魚種;(3)前述兩款之任一國家系區域性經濟一體化組織之成員,及該國已轉移本條約所規范事項范圍內之權限予該經濟一體化組織。,適用范圍③GFCM協議第4條規定了適用范圍:委員會應在序言所述之區域實施第3條條文規定之功能與責任。第3條第1段規定GFCM的目的是“促進發展、養護、合理管理及最佳利用海洋生物資源暨區域內可持續發展養殖。”,功能與責任④GFCM協議第3條第1款的(a)至(h)項規定了八個方面的功能和責任。包括:(1)資源開發利用問題的海洋學、生物學及技術性的側面定位;(2)調查的調整促進;(3)共同調查計劃的做成;(4)調查技術等的標準化;(5)漁業制度的比較研究;(6)促進防止漁民職業名的調查;(7)援助取得材料設備;(8)加盟國及FAO委托事項的審議及勸告活動。,與其他組織的合作,以及協議的保留、生效和爭端解決等。
(二)海洋環境保護
UNEP在地中海海洋環境保護的區域安排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地中海行動計劃(MAP)是UNEP資助地中海沿岸國家處理海洋污染問題的首個區域海計劃(RSP)①1972年瑞典斯德哥爾摩聯合國人類環境大會之后,UNEP于1974年發起區域海計劃(RSP)。區域海計劃旨在通過對海洋和海岸的可持續管理與利用,防止全球海洋及海岸生態環境的急劇退化,使海域相鄰國家共同參與綜合及專項行動以保護其共享的海洋環境。迄今為止,已有140多個國家參加了聯合國環境署支持的13個區域海計劃。另外5個伙伴計劃也成為了區域海計劃的成員。為此,區域海計劃已成為覆蓋全球18個海區的最廣泛的保護海洋和海岸環境的倡議。。
MAP最早由UNEP在1975年初的保護地中海的政府間會議上提出,這次會議不僅通過了MAP,而且為即將通過的區域框架性公約和議定書等法律文件做出了實質性準備②相關的法律文本主要有三個:(1)在FAO的贊助下準備了防止地中海海洋環境污染的公約草案;(2)由政府間海洋咨詢組織(IMCO)準備并起草的防止石油和其他有害物質污染地中海的合作議定書草案;(3)由西班牙代表準備的關于防止船舶和飛機傾倒導致地中海污染的議定書草案。;1976年UNEP再次召開關于地中海保護的全權代表大會,會議通過了《保護地中海免受污染的公約》(《巴塞羅那公約》)和兩個議定書,分別是《預防地中海海區船舶和航空器傾倒廢物而造成污染的議定書》和《在緊急情況下合作控制地中海石油及其他有害物質造成污染的議定書》;其后,又有五個議定書③分別是1980年的《保護地中海免受陸原污染之雅典議定書》、1982年的《關于地中海特別保護區的日內瓦議定書》、1994年的《關于開發大陸架、海床和底土的議定書》、1996年的《預防地中海海區危險廢物越境轉移及其處置造成污染的議定書》和2008年的《海岸帶綜合管理議定書》。獲得通過。這些法律文件為地中海沿岸國家進行海洋環境的保護提供了法律基礎。
(三)地中海區域合作實踐的成功因素分析
1.制度構建模式的創新為區域合作奠定了法律基礎。就目前的半閉海區域合作實踐來看,UNEP在海洋環境保護及合作領域為半閉海區域提供了三種制度性合作模式。一是分立模式,即對不同的海洋合作問題構建各自獨立的法律制度予以解決,例如北海區域;二是綜合模式,即對所有的海洋環境問題一并立法予以規制,如波羅的海區域;三是綜合與分立相結合的模式,即框架公約加議定書的海洋環境保護制度,如地中海區域。在綜合與分立相結合的制度模式下,各方在簽署框架公約后至少要批準一項議定書,且各方承諾隨著條件變化還將盡快批準其他議定書。
2.來自主導國家和國際組織的支持是區域合作的推動力量。地中海區域合作的實現,法國、意大利兩國在早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兩國曾最早提出有關控制地中海油污的協議,法國更是利用自身的經濟、技術和資金優勢,擴大了其在地中海區域的影響,成功主導了20世紀70年代早期的地中海區域環境保護,例如對于海洋環境污染的檢測和治理,法國支付了很大一筆費用,這些資金的作用甚至持續到UNEP開始主導地中海區域海洋環境保護之后的一段時間[7](P68)。
3.組織框架的完善是持續開展區域合作的有力保障。地中海區域的成功之處還在于建立了比較完整的組織框架。不論是上述GFCM協議下的地中海漁業合作,還是UNEP倡導下的地中海海洋環境保護合作,該區域合作的諸多成就和相關國際組織完善的組織框架所發揮的職能和作用密不可分。現有組織框架不僅能夠滿足相關國際組織日常事務性工作的需要,而且在資金支持、法律完善、活動開展等方面都有相應的組織機構履行其職能,在海洋合作事務開展的過程當中,這些組織機構分別發揮著建議、實施、監督、評估等不同的作用。
三、半閉海制度下的合作實踐帶給南海低敏感領域合作的啟示
(一)南海的區域合作現狀
自《海洋法公約》通過以來,雖然南海周邊國家已經簽署了不少有關海洋合作的雙邊協議,如2001年4月中國和印度尼西亞簽署的《漁業合作的諒解備忘錄》及其后的《利用印度尼西亞專屬經濟區部分總可捕量的雙邊安排》;2004年9月中國和菲律賓簽署的《漁業合作諒解備忘錄》,尤其是2002年中國和東盟各國簽署的《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以下簡稱《宣言》),表明各方在南海海域進行合作的基本共識,《宣言》第六條規定:“在全面和永久解決爭議之前,有關各方可探討或開展合作,可包括以下領域:(1)海洋環保;(2)海洋科學研究;(3)海上航行和交通安全;(4)搜尋與救助;(5)打擊跨國犯罪,包括但不限于打擊毒品走私、海盜和海上武裝搶劫以及軍火走私。”但是由于南海的合作多以雙邊協議的方式進行,《宣言》這樣的多邊性政治文件又鮮有具體和義務性的規定。因此,目前南海的區域合作仍處于自發和無序的狀態,呈現出機構復雜、形式交錯的局面。目前,南海的相關區域合作表現在以下方面:
1.海洋生物資源管理。在南海并沒有一個專門的區域漁業管理組織來協調處理漁業資源問題。目前,世界上已經建立了14個區域漁業管理組織,這些組織覆蓋了世界上所有的海域和幾乎所有的重要魚類種群。其中與南海區域相關的漁業管理組織有兩個:一個是亞洲-太平洋漁業委員會(APFIC),該委員會由FAO大會第三屆會議在1947年建議成立,并最終于1948年11月成立。目前有20個成員國,包括中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和越南等部分南海周邊國家。委員會設有FAO亞洲及太平洋區域辦事處,其宗旨是通過發展和管理捕撈及養殖活動以及通過符合成員目標的有關加工和銷售活動,促進水生生物資源的全面、適當應用。但是該組織只是咨詢和建議性的機構,不負責南海生物資源的管理。
另一個是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WCPFC),該委員會根據《中西太平洋高度洄游魚類資源的管理和養護公約》(WCPFC Convention)于2004年12月正式成立。會員包括中國、中國臺北①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是在1995年《聯合國漁業資源協議》通過后建立的,因此,臺灣作為“漁業實體”有資格以中國臺北的名義加入該公約。、菲律賓等南海周邊國家和地區,合作非會員包括泰國、越南等國家。該委員會旨在“依據「一九八二年公約」及「協定」,經由有效的管理以確保中西太平洋高度洄游魚類種群之長期養護與永續利用。”
2.海洋環境保護。UNEP RSP共包含18個海洋區域項目,為全球的海洋環境保護問題提供了全面的方案。其中東亞海洋項目包含了西太平洋區域,南海屬于該項目下的次區域。該項目關注海洋污染的來源和后果等問題,1981年通過了《關于保護和發展東亞海洋區域海洋環境和沿海區域的行動計劃》,最初,有五個國家參與了該行動計劃,分別是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和泰國。到1994年,又有澳大利亞、柬埔寨、中國、韓國和越南五個國家加入。另一個有關東亞區域海洋環境的項目是東亞海環境管理伙伴關系計劃(PEMSEA),1994年由GEF(全球環境基金)建立,聯合國開發計劃署 UNDP負責實施,IMO負責執行。目前,PEMSEA已經由一個全球環境基金的項目逐漸轉變為一個區域性國際組織,旨在通過政府間、機構間、部門間的伙伴關系,促進海洋和海岸帶資源的持續利用和綜合管理,通過海洋環境的改善提高東亞海地區人民的生活質量。目前有11個國家參與,其中包括中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越南等南海周邊國家,臺灣被排除在外。目前該計劃包含了在一系列試點地區開展的海洋合作計劃。
3.中國參與的其他南海區域合作機制。(1)政府間的南海區域合作機制。1994年的東亞海環境管理伙伴關系計劃(PEMSEA),旨在進行沿海岸帶的綜合管理;2001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及全球環境基金(UNEP/GEF)南海項目,旨在保護棲息地、漁業,對地源污染進行管理;1981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東亞海行動計劃,旨在協調各國政府、聯合國及援助機構的行動,促進東亞海洋環境問題的溝通與交流;1979年的政府間海洋學委員會(IOC,屬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西太平洋分委員會,旨在開展海洋科學、海洋觀測、海洋數據和信息交換,促進國際合作和協調規劃研究;1986年的亞洲發展銀行(ADB)設立的環境持續發展項目,中國已獲項目共65個。(2)非政府間的南海區域合作機制。1981年成立的東南亞海洋法律、政策和管理計劃(SEAPOL),是一個由學者、政府官員和個人組成的非政府機制,旨在便利東南亞和亞太地區現有海洋法律政策的信息互換,該計劃現已終止;1990年發起的南海政治沖突管理的研討會,該研討會旨在贊助和支持一系列關于南海政治沖突的交流和對話;1993年的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CSCAP),旨在通過向政府提交政策建議,以推進該地區各國的相互信任。
此外,中國沒有參與的非政府間區域合作機制有兩個:一個是1976年的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另一個是2001年的可持續漁業行動計劃。
(二)南海開展區域合作的困難
1.南海爭端日益加劇,南海各方開展區域合作的政治意愿差異明顯。自2009年以后,南海爭端呈現出復雜化、國際化的發展趨勢,隨著有關周邊國家加緊開發南沙海域資源以及東盟國家內部協調的加強,以及美國、日本、印度等區域外國家對南海爭端的介入,圍繞南海島嶼的主權爭端和南海海域劃界爭端日益加劇[8]。這一現實情況對南海的區域合作帶來了困難和阻礙,例如漁民實際捕魚區域范圍的不確定,漁業糾紛加劇等。
2.政治、經濟、文化多方面的差異導致南海各方對區域合作持有不同意識和態度。南海區域共有九個國家和中國臺灣地區,除了因南海爭議而涉及的六國七方(中國、越南、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文萊、菲律賓和中國臺灣)外,還包括新加坡、泰國、柬埔寨三國。這些國家在政治制度、經濟水平和宗教文化等方面都極具差異。
3.缺乏區域合作的內部主導力量,南海區域合作推動力不足。南海區域合作目前由UNEP、FAO等國際組織作為主要推進者,但是區域組織的推動尚需區域內各方的支持與合作。由于南海各國對海洋事務合作抱有不同的立場和態度,能夠在資金、技術、影響力等各方都起到推動作用的內部主導力量尚未出現,這也是制約南海區域合作發展進程的重要原因。
4.南海區域合作法律機制欠缺,區域合作缺乏約束力和系統性。到目前為止,南海區域合作的法律機制尚未得到廣泛和良好的發展,表現為區域公約的缺位和法律實施機制的欠缺。南海至今尚無囊括所有南海周邊或大多數國家、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政府間海洋事務合作的區域協定,由于缺乏區域公約的統領,南海區域合作法律呈現出碎片化和“軟法”規制的特點,在各個項目、計劃、組織之間缺乏溝通,甚至造成資金、人員的浪費和短缺。
(三)半閉海制度及其實踐對南海低敏感領域合作的啟示
《海洋法公約》確立了海洋利用和管理的基本框架。雖然《海洋法公約》的半閉海制度所涉及的范圍非常有限,不能為半閉海的沿岸國家處理領土爭議或海洋劃界等問題提供幫助,但是半閉海制度本身就說明了半閉海海域的特殊性。一項成功的區域合作離不開合作各方良好的政治意愿、持續的資金保證、合理的法律基礎和高效的機構安排,現有的規定和合作實踐能夠為南海這一半閉海海域的低敏感領域合作提供一些方向和思路。
1.正確評價南海區域合作中的信任問題。從地中海區域的合作實踐來看,該區域的國家間關系錯綜復雜,有很多妨礙合作的因素,諸如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間的領土、宗教和歷史沖突,希臘和土耳其有如世仇,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待海洋環境保護的不同態度等問題比比皆是,但不同的政治制度、經濟實力、宗教信仰甚至歷史積怨卻沒有阻礙該區域海洋環境保護合作的實現。換個角度來看,正因為存在差別和爭議,合作才有必要。故筆者認為,當前因缺乏互信而導致南海區域各方合作意愿較低的客觀現實固然存在,但是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的差異,包括主權問題的爭議并不是阻礙合作的必然因素。關鍵還在于尋找南海各方的共同關切,以共同的利益促進合作的開展和深化。
2.合理借鑒地中海區域合作模式的成功經驗
(1)框架公約加議定書的雙層法律機制對南海區域合作的借鑒意義。在南海區域合作法律機制的模式選擇問題上,中國已有一些學者在關注和研究南海海洋環境保護或漁業區域合作的制度模式[9][10][11],面對南海錯綜復雜的問題和形勢,同樣是區域矛盾重重但最終獲得成功的地中海模式具有積極的借鑒意義,去推動并達成一項在南海低敏感領域的區域合作框架公約,將已有的雙邊和多邊合作整合納入區域合作結構體系中,是建立起南海區域合作法律基礎的合理選擇。
(2)中國和東盟應在區域合作中發揮主導者作用。從地理上看,南海面積約350萬平方公里,中國主張管轄的海域占到2/3,作為南海周邊一個正在和平崛起的大國,中國有責任牽頭推動南海的區域合作,勇于承擔更多的義務;從實踐來看,近年來中國政府越來越多的釋放出牽頭推動南海區域合作的信號。2012年1月中國國家海洋局發布《南海及周邊國際合作框架計劃(2011-2015)》,以及2013 年5月的《中國海洋發展報告(2013)》都表示出中國在推進南海合作,確立海洋事務強國地位上的決心。2013年9月在廣西南寧召開的第十屆中國—東盟博覽會上,中國倡議建立“中國—東盟海洋伙伴關系”,中國已經設立30億元人民幣的中國—東盟海上合作基金,用以推進合作項目。東盟作為區域性國家組織,始終以推進區域合作為己任,在促進經貿合作和區域協調等方面有豐富的經驗。因此,中國和東盟有能力也有責任在南海區域合作中發揮主導者作用,這對于從內部推動南海區域合作進程意義重大。
(3)以漁業合作和海洋環境保護合作為先導,分階段完成區域合作目標。在漁業合作領域,近期目標是制訂和完善區域漁業合作管理基礎方案,即確定漁業合作的基本原則,完善包括漁業資源調查與統計、捕撈限制、漁船與漁具、漁業貿易、漁業增養殖等方面的法律機制,扭轉漁業資源衰退的總體局面,初步形成良好的區域合作氛圍;遠期目標是在條件成熟時設立區域合作管理委員會,負責制定共同的南海漁業政策,從漁獲量到各國配額,以及漁業信息統計、科研合作、檢測調查等環節開展全面綜合管理。
(4)重視區域組織的功能與作用。UNEP和FAO等國際組織對推動和促成區域海洋合作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不僅被近幾十年海洋發展和合作的實踐所證明,也是今后區域海洋合作的趨勢之一。雖然國際組織和專門機構的參與并不能保證區域合作的成功,但是無論從相關區域組織所具有的影響力,還是其在既往區域海洋合作中所擁有的經驗,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所能夠提供的資金支持,都對南海的區域合作有著極大的推動力。因此,應該重視并正確評估相關國際和區域組織所發揮的功能和作用,加深與相關國際組織的合作,積極參與其活動和事務。
3.以南海區域各方的共同關切為基礎,進一步拓展《海洋法公約》框架下的合作深度與廣度
(1)充分利用南海區域合作的現實基礎。一方面,國際法上的合作原則是開展國際合作的理論基礎[12](P93-113)。從1970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國際法原則宣言》,將國際合作原則確立為現代國際法的基本原則之一,到《海洋法公約》有關生物資源的養護、海岸相向或相鄰國家間專屬經濟區、大陸架界限的劃定、半閉海制度和技術的轉讓等相關制度①參見《海洋法公約》第61條、第74條(3)款、第83條(3)款、第123條、第144條的相關規定。都體現出現代國際法和海洋法倡導的合作原則,此外,在一些聯大決議和國際公約中也有關于共享資源的合作義務的規定,在該原則下,各國有義務為達成合作承擔協商談判、信息交換等積極義務,國際合作原則已經滲透在現代國際關系的方方面面,構成開展國際合作的理論基礎。另一方面,南海已有的區域合作實踐是南海開展區域合作的現實基礎。
(2)以南海區域各方的共同關切為基礎有序拓展合作領域。《海洋法公約》規定的半閉海制度將區域合作指向漁業合作、海洋環境保護和海洋科考這三個方面,半閉海制度的意義也正在于鼓勵半閉海區域的沿岸國家積極開展海洋合作。但是《海洋法公約》的制定已經有30余年,對于海洋合作的范圍也應該隨著時代的發展而填補新的內涵。因此,半閉海區域的合作不應僅限于以上三個方面,而是應從各沿岸國的共同關切和共同需求出發,以漁業合作和海洋環境保護合作為重點,逐步開拓并完善在海洋旅游、海洋搜救、海難救助等領域的合作,并在遵守國際法規則的前提下適時開展海上能源的共同開發。可以說,現階段以南海各方的共同關切為基礎,積極開展南海低敏感領域合作,不僅有利于保護南海的資源和環境,更不失為緩解南海爭端、另辟道路尋求解決南海問題的有益嘗試。
[參考文獻]
[1]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關于“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主張[EB/OL].http://www.mfa.gov.cn/chn//gxh/xsb/wjzs/ t8958.htm,2014-01-07.
[2]Robert Beckman,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nd the Maritime Dispu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107:2013.
[3]李金明.論南海問題法律爭議與解決步驟[J].云南大學學報(法學版),2012,(1).
[4]王秀衛.南海低敏感領域合作機制初探[J].河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13,(3).
[5]楊澤偉.《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主要缺陷及其完善[J].法學評論,2012,(5).
[6]楊澤偉.論《海洋法公約》解決南海爭端的非適用性[J].法學雜志,2012,(10).
[7]See Peter M Haas,Saving the Mediterranean: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Cooperation,New York[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0.
[8]李金明.《海洋法公約》與南海領土爭議[J].南洋問題研究,2005,(2).
[9]張湘蘭.南海漁業資源合作開發的國際法思考[J].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3).
[10]陳明寶.南中國海區域漁業資源合作開發機制研究[J].亞太經濟,2012,(2).
[11]隋軍.南海環境保護區域合作的法律機制構建[J].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6).
[12]Tara Davenport.The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Hydrocarbon Resources in Areas of Overlapping Claims [A].Robert Beckman eds.,Beyond Territorial Dispu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Legal Framework for the Joint Development of Hydrocarbon Resources[C].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2013.
[責任編輯:劉烜顯]
[作者簡介]張穎,武漢大學中國邊界與海洋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漢 430072;陜西警官職業學院副教授,陜西 西安 710021
[中圖分類號]D993.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434(2016)06-0068-06
[基金項目]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海上共同開發國際案例與實踐研究”(13JZD039)階段性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