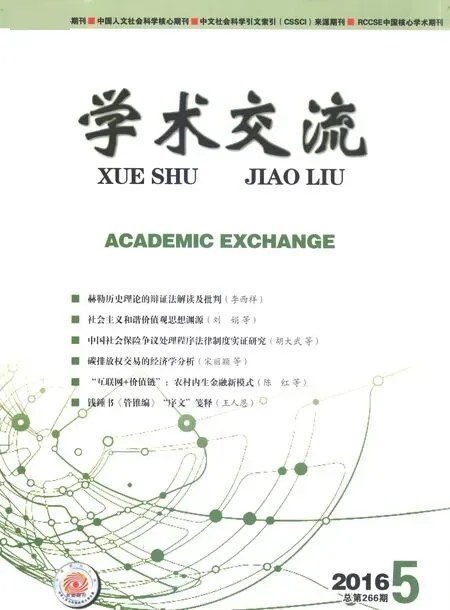論刑事庭前會議的效力
賈志強
(吉林大學 法學院,長春 130012)
?
法學研究
論刑事庭前會議的效力
賈志強
(吉林大學 法學院,長春 130012)
[摘要]在“以審判為中心”的司法改革背景下,庭前會議具有重要的制度價值,而庭前會議的效力問題是實現其制度價值的一個關鍵點。在我國法律規范層面,刑事庭前會議的效力僅僅是“了解情況,聽取意見”,該規定的模糊性直接導致了庭前會議效力的模糊性和爭議性。但在司法實踐層面,在一些案例中法官們在適用庭前會議時并不拘泥于“了解情況,聽取意見”,而是賦予了庭前會議以一定的效力。庭前會議的效力應主要由兩方面構成:一是程序的時效性,即在庭前會議的啟動、內容等方面均有一定的有效時間的限制;二是結論的約束性,即庭前會議上不僅能夠以法官裁判、參與各方達成共識等方式形成結論,而且這種結論對于參與各方和后續庭審具有約束力。在觀念上重視產出與投入的平衡,注重庭前程序的作用,接納程序性裁判,厘清成本與收益、庭前與庭審、程序性與實體性裁判這三組重要關系,有助于我們在庭前會議效力問題上達成共識,并促成庭前會議效力的真正實現。
[關鍵詞]庭前會議;效力;時效性;約束性
一、引言:“以審判為中心”背景下的庭前會議
“以審判為中心”,是我國目前刑事訴訟改革的重大目標。恪守“以庭審為中心”,突出和強化庭審的地位和功能,確保庭審實質化是“以審判為中心”的應有之義。*參見閔春雷:《以審判為中心:內涵解讀及實現路徑》,載于《法律科學》2015年第3期,第39-40頁;汪海燕:《論刑事庭審實質化》,載于《中國社會科學》2015年第2期,第103-104頁。“以庭審為中心”,決不能被理解為“所有事項均應放在庭審中處理”。恰恰相反,庭審程序應當集中地、專門地處理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問題,這就需要庭前程序能夠事先起到一定的過濾和整理功能。在2016年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同志強調,以庭審為重點不是搞程序繁瑣主義,要發揮好庭前會議作用,對控、辯雙方沒有爭議的證據可以在庭上打包出示、從簡調查,從而讓法庭調查和辯論重點圍繞爭議點展開,努力查清疑點,提高效率。[1]可見,在“以審判為中心”的大背景下,作為我國刑事庭前程序的核心環節,庭前會議制度對推動實現上述改革目標具有重大意義,具體體現為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庭前會議制度的完善有利于實現庭審的純粹化。庭審應當純粹化,即庭審的功能應當是解決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問題,而不是解決諸如法官回避、管轄、出庭證人名單等問題或爭議。庭前會議制度為庭審的“減負”提供了空間,控辯雙方之間的一部分問題或爭議能夠提前在庭前階段得到溝通或解決,利于純化庭審功能,確保整個庭審的質量。第二,庭前會議制度的完善有利于保障庭審的集中化。“審判程序應盡可能地一口氣完成,亦即直到辯論終結均不中斷。”[2]185集中審理是法官自由心證連續性和新鮮性的保障,并有利于提高訴訟效率。庭前會議制度不僅可以促使控辯審三方提前為庭審做好準備,而且能為庭審提前掃清一些障礙,從而盡量避免庭審不必要的中斷,利于實現庭審集中。
然而,要實現我國庭前會議之于庭審程序的上述意義,明確庭前會議的效力是一個關鍵點,庭前會議的效力問題直接決定著這項新增制度的預期立法目標能否實現。*事實上,我國目前已然存在庭前會議功能失范的危險,而效力的模糊甚至缺失是導致功能失范的根源之一。參見吉冠浩:《論庭前會議功能失范之成因——從庭前會議決定的效力切入》,載于《當代法學》2016年第1期,第150頁。對于庭前會議的效力,目前我國相關法律規定模糊,在理論界和實務界也存在較大爭議,在司法實踐中更是做法不一、缺乏共識。基于此,本文擬對庭前會議的效力問題進行探討,以期對庭前會議程序實現其應有的制度價值有所幫助。
二、保守與務實:法律和實踐層面上庭前會議效力的不同“面相”
目前,關于庭前會議的效力,我國在立法上并沒有明確規定,相關的最重要表述就是“了解情況,聽取意見”。但該表述所傳達的意思較為模糊、籠統,可謂撲朔迷離,其背后是相關法律規范制定者對庭前會議效力的保守態度,這就為我國庭前會議效力的缺失奠定了基調。然而在一些具體司法案例中,我們卻能夠發現一些司法機關對庭前會議效力的理解并不拘泥于“了解情況,聽取意見”,而是以一種務實的態度賦予其明確的效力,從而使庭前會議能夠發揮其應有的功能。
(一)法律規范層面:僅是“了解情況,聽取意見”
我國《刑事訴訟法》對庭前會議的規定只有第182條第2款這一個條文:“在開庭以前,審判人員可以召集公訴人、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對回避、出庭證人名單、非法證據排除等與審判相關的問題,了解情況,聽取意見。”單從該法條文義上來看,主持庭前會議的審判人員可以在該程序上對上述法條中所列的問題“了解情況,聽取意見”。但庭前會議到底具有什么效力,從上述條文當中得不到明確答案。全國人大法工委的同志在對該條款進行釋義時對非法證據排除問題特別進行了說明:“這里規定的非法證據排除,只是聽取意見,具體如何排除要根據本法第五十四條、第五十六條、第五十八條等的規定依法進行。”[3]可見,全國人大法工委的同志認為在庭前會議上法官對非法證據排除問題不能進行裁判,而只能聽取意見。
我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以下簡稱為《解釋》)第183條、第184條對庭前會議程序作了進一步的解釋。關于庭前會議的效力,《解釋》的文本透露出兩種意思。第一,第184條第1款列舉了作為庭前會議內容的管轄異議、回避、申請調取有利于被告人的證據等8項程序性事項(其中第8項為兜底條款),但并未指明庭前會議對這些程序性問題的效力,也就是說審判人員可以就這些問題向控辯雙方“了解情況,聽取意見”。第二,第184條第2款對證據開示和整理的表述暗含著庭前會議上的這種活動對后續正式庭審程序具有一定的約束力:“審判人員可以詢問控辯雙方對證據材料有無異議,對有異議的證據,應當在庭審時重點調查;無異議的,庭審時舉證、質證可以簡化。”但在某些具有一定指導意義的解釋性工具書中,有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認為:“庭前會議只能了解情況和聽取意見,法院不能在庭前會議中對回避、出庭證人名單、非法證據排除等程序性事項作出裁定、決定。對于庭前會議達成的共識,也不具有法律效力。”[4]190但讓人感到困惑的是,該書認為:“對于雙方在庭前會議中提出的意見和問題,能夠在庭前解決的,應當盡量在庭前解決,以免影響庭審的正常進行……總之,通過庭前會議,盡量使控辯雙方對程序事項的意見分歧解決在庭前。”[4]190上述解釋中透露出一種“糾結”的立場,庭前會議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卻又鼓勵法官在庭前會議上盡量解決程序性意見和爭議,試問,在不具備法律效力的情況下,這些程序性問題能算是被真正地解決么?控辯雙方在庭審時再次提出在庭前會議上已“解決”的問題,法官應如何處理?
(二)司法實踐層面:對“了解情況,聽取意見”的突破
借用薩默斯教授的話來說,實踐中的法(law in practice)超越了紙面上的法(law in book)。[5]司法實踐中存在法院賦予庭前會議以一定效力的情形,對法律規范中的“了解情況,聽取意見”有所突破。在一些案例中,法官肯定了庭前會議的效力,即法官在庭前會議上對一些事項直接作出了裁斷,或者法官對控辯雙方在庭前會議上達成的合意賦予了效力,庭前會議上形成的結論或共識對后續庭審具有約束作用。就目前筆者搜集的案例來看,我國司法實踐中庭前會議的效力至少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在庭前會議上法官對一些程序性申請或事項直接作出答復、裁斷。例如在許某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案中,法院共召開了兩次庭前會議。在第一次庭前會議中,辯護人申請證人出庭作證,同時也對案件的管轄及分案審理提出了異議。控辯雙方針對上述事項分別發表完意見后,法官駁回了辯方的管轄異議申請和分案審理的申請。在第二次庭前會議中,法官就出庭證人名單的問題聽取了控辯雙方意見,控辯雙方均表示不申請證人出庭,同時辯護人還表示沒有新的證據向法庭提交。在該案中,法官對辯方的程序性申請直接作出了裁斷,在出庭證人名單方面也達成了共識,在后續庭審中上述問題未被提及。*參見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3)一中刑初字第5268號刑事判決書。另外,在一些專門針對非法證據排除問題的庭前會議上,法官對“排非”問題進行了調查,并在庭前會議上直接對“排非”爭議作出了裁斷。*法官直接作出“排非”決定的案例可參見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2013)登刑初字第571號刑事判決書、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2013)皖刑終字第00297號刑事裁定書;法官直接作出不排除某些證據決定的案例可參見廣西省金秀瑤族自治縣人民法院(2013)金刑初字第55號刑事判決書、河南省潢川縣人民法院(2014)潢刑初字第46號刑事判決書。
2.庭前會議上進行的證據和爭點整理對庭審具有約束力。在河南省禹州市海某案中,由于該案涉案人數眾多(被告人多達20人)、案情復雜(涉嫌27個罪名),法院利用庭前會議進行了證據和案件爭點的整理,控辯雙方的爭議焦點集中在某一被指控的行為能夠構成敲詐勒索罪和黑社會性質組織的認定上。通過召開庭前會議,法官確定了庭審的重點,法官最終僅用了1天就完成了這場原本需要4天的庭審。可見,本案庭審過程受到了庭前會議上控辯雙方對證據和爭點整理所達成共識的約束。
3.庭前會議筆錄在庭審中被直接作為證據使用。在上海谷某貿易有限公司等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非法經營案中,二審終審法院在論證關于一審判決改變起訴指控罪名的問題時引用了庭前會議記錄中的相關內容,認為一審法院已在庭前就是否改變起訴指控罪名聽取了控辯雙方的意見,控辯雙方就此問題已達成共識。加之辯方也在一審庭審中對上訴單位及上訴人是否構成非法經營罪發表了辯護意見。據此,二審法院認為一審判決改變起訴指控的罪名依法有據。可見,在本案中二審法院認為一審庭前會議記錄具有法律效力。*參見(2013)滬一中刑終字第1529號刑事裁定書。另外,在吳某1隱匿會計憑證、會計賬簿、財務會計報告案,吳某2故意殺人案,許某販賣毒品案等案件中,庭前會議筆錄中的內容被法官作為證據在正式庭審中使用。*三個案例可分別參見河北省巨鹿縣人民法院(2013)巨刑初字第61號刑事判決書、江蘇省揚州市人民法院(2014)揚刑初字第00019號刑事判決書、四川省隆昌縣(2015)隆昌刑初字第16號刑事判決書。
綜上可見,“了解情況,聽取意見”無法真正滿足司法實踐的需求,法律規范層面的撲朔迷離擋不住司法實踐對庭前會議效力的探索。但上述個案中的做法不足以被視為我國司法實踐中的一般做法,還有一些法院因為“了解情況,聽取意見”的模糊和難以捉摸而對庭前會議的效力問題感到困惑。這就需要在理論上對庭前會議的效力作系統而明確的闡釋,化解“了解情況,聽取意見”所帶來的困境。
三、時效性和約束性:庭前會議應具備的兩種效力
沒有效力的庭前會議是一種“不完整的程序”。從訴訟原理上來說,庭前會議屬于一種刑事訴訟行為。刑事訴訟行為“乃法院、當事人或訴訟關系人所為引起刑事訴訟效果之行為”[6]。可以說,訴訟行為的總和,構成了完整的刑事訴訟程序過程。[7]作為一種刑事訴訟行為,庭前會議的行為主體是控辯審三方,該三方主體在庭前會議上的行為應當產生一定的訴訟法效果,對后續的訴訟進程產生影響或者拘束力,否則,庭前會議極易淪為一種“走過場”的程序。即使控辯審三方意欲通過庭前會議處理一些問題,但如果在后續程序中控辯審三方可以隨意擺脫前面庭前會議上行為或結論的約束,召開庭前會議的最初目的無法實現,最終可能導致控辯審三方失去召開或參加庭前會議的動力,庭前會議將難以實現其提高庭審質效的功能和價值。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英國的失敗經歷值得我們警醒。答辯和指導聽證(Plea and Directions Hearing)是英國刑事訴訟中的一種庭前程序,與我國庭前會議程序相類似。在一段時間里,英國司法實踐中出現了一種窘境,庭審法官可以隨時推翻控辯審三方在答辯和指導聽證中就某些問題或事項形成的決定或安排,答辯和指導聽證中的結論對庭審法官沒有約束力。這種情形對控辯雙方產生了極大的負面后果,突出表現在控辯雙方的律師對于親自參加答辯和指導聽證失去了積極性,其結果是出現在答辯和指導聽證上的律師往往不是出庭律師本人,而由其助手或其他律師代為參加。根本原因在于“沒有什么動力能使他們打亂自己的時間表去參加一個不具有重要性的預備程序庭審”,“如果他們不喜歡結果,他們總是可以向審判法官申請另一個裁決。”[8]334上述問題直接導致該程序難以實現其立法目的。總地來說,程序的時效性與結論的約束性應是庭前會議程序效力的兩個主要構成方面。
(一)程序的時效性
首先,庭前會議應在啟動方面具有時效性,即控辯雙方的申請必須在庭前階段提出,或者法院必須在庭前階段依職權直接決定召開。這一點在多數法治國家中都有所體現。以美國為例,在聯邦層面,庭前會議可依控辯雙方其中一方的動議召開。與此同時,某些動議必須在庭前提出,例如申請證據開示的動議、申請排除非法證據的動議等。這類動議的提出都有一個最后的期限,如果控辯雙方并未在法官提前規定的期限內提出上述動議,則控辯雙方將會面臨“失權”的程序性后果,那么用以解決相關問題或事項的庭前會議將不會被允許召開。在我國司法實踐中,有些案件中庭前會議的召開明顯值得商榷。例如在周某涉嫌受賄、挪用公款案中,在一審庭審結束6個月后(甚至被告人已經在法庭上作完了最后陳述),法院又依職權召開了庭前會議以商討重新審理的相關事宜。*參見楊璐:《南昌大學原校長周文斌案一審將開啟第二季:律師稱將全案重審》,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75888,2015年10月10日訪問。且不論這次重新審理合法與否,一審庭審結束后再召開庭前會議,明顯違背了啟動庭前會議的時效性要求。
其次,在庭前會議的內容方面,控辯雙方均應在庭前會議上提出各方的程序性請求,如果控辯雙方在庭前會議上未提出法律所規定的問題或事項,在進入到正式庭審階段后控辯雙方將失去提出相關申請或異議的權利,除非具有某些法定的正當理由。其實在《解釋》中關于辯方“排非”申請的提出就存在著類似時效性的規定。根據《解釋》第97條、第99條、第100條,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申請“排非”具有一定的時間要求,即除非在庭審期間才發現相關線索或者材料的,辯方必須在庭前階段向法院提出“排非”申請。辯方在庭前申請“排非”,法庭認為存在疑問的,應當召開庭前會議。符合上述“但書”情況的在庭審時提出“排非”申請的,法庭可以在辯方“排非”申請后立即進行調查,也可以在法庭調查結束前一并進行。不符合上述“但書”情況的在庭審時才首次提出“排非”申請的,法庭應當在法庭調查結束前一并進行審查。可見,當辯方違反《解釋》第97條所規定的時間要求而在庭審時才提出“排非”申請時,第100條第3款以一種延后審查的方式對上述行為施加一定的制裁。
最后,庭前會議可以缺席召開。為防止訴訟程序被過分拖延,當法院已履行其相關告知義務后,如果相關各方在無正當理由的情況下不在事先規定的日期參加庭前會議,法院可以在某方缺席的情況下組織召開庭前會議。當然,庭前會議的缺席召開要以法院履行了其告知義務為前提,并且法官在確定庭前會議召開時間時也應事先充分照顧到控辯雙方的一些特殊情況,控辯審三方提前對庭前會議的召開時間做好溝通。以我國臺灣地區為例,經法庭合法傳喚或通知后,如有無正當理由而缺席者,法官得僅對到庭之人行準備程序,即進行“缺席之準備程序”。[2]194
(二)會議結論的約束性
庭前會議的結論具有約束性有兩個層面的含義:首先,在庭前會議上應當允許形成一定的結論,即法官可以對某些事項直接作出裁斷,控辯雙方或控辯審三方之間也可以就一些事項達成合意;其次,庭前會議上形成的結論應當對參與各方和后續庭審產生約束力。
關于庭前會議參與者可以就某些事項達成合意這一點,目前在學界和實務界已基本達成共識。主要爭議在于法官能否在庭前會議上對一些程序性事項直接作出決定或裁判。支持者認為庭前會議可以被視為一種程序性裁判程序,法官對程序性事項或爭議作出裁判乃應有之義。*支持者意見可參見陳瑞華:《評〈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對審判程序的改革方案》,載于《法學》2011年第11期,第57頁;高潔:《程序性爭議的庭前聽證程序》,載于《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12年第5期,第110頁。反對者則認為控辯雙方有爭議的事項,庭前會議不作決定,留待庭審時解決。*參見莫湘益:《庭前會議:從法理到實證的考察》,載于《法學研究》2014年第3期,第59頁。其中一種反對理由是:一方面,《刑事訴訟法》規定審判人員在庭前會議中的職責是“了解情況,聽取意見”,并未賦予其裁決權,根據“公權力法無授權不得為”的原理,審判人員不能裁決;另一方面,刑事案件的處理應當以庭審為中心,裁判結果形成于法庭,如賦予庭前會議以裁決權,恐有因裁決不當而影響司法公正之虞。*參見朱孝清:《庭前會議的定位、權限和效力》,載于《檢察日報》2014年8月13日第3版。筆者認為,法官可以對庭前會議上的一些程序性事項作出決定或裁判。除了可以從上述程序性裁判的角度論證外,更為直接的是,可以從我國既有的法律規定中找到一定的支持。
《解釋》第184條第1款列舉了7項可以在庭前會議上探討的程序性問題。先以第3項申請調取有利于被告人的證據為例,《解釋》第49條規定,人民法院接受辯護人調取有利于被告人的證據的申請后,應當向人民檢察院調取,并未規定人民法院必須在何種特定的程序、時間里才能接受辯護人申請并決定向檢察機關調取相關證據。那么綜合《解釋》第49條和第184條第1款第3項來看,法官在庭前會議上完全可以作出接受或者不接受辯方申請調取有利于被告人的證據的決定,這與法律規定并不相悖。同理,將《解釋》第184條第1款第6項和第97條、第99條、第100條,第184條第1款第7項和第186條第2款這幾組法條結合起來看,對于控辯雙方在庭前會議上提出的“排非”申請和不公開審理的申請,法官也可以直接在庭前會議上作出決定。與上述三種程序性申請的情況不同,根據《解釋》第222條第1款、第202條、第203條、第217條,法官對于控辯雙方證人、鑒定人、有專門知識的人出庭的申請以及提供新證據的申請都可以直接作出同意與否的決定,只不過上述條文規定的都是在庭審過程中控辯雙方提出相關申請的情形。既然在庭審時法官可以直接對上述兩種申請作出決定,那么當控辯雙方的申請提前到庭前會議上提出時,法官當然也可以在庭前會議上對這些申請直接作出決定。如果按照上述某學者“公權力法無授權不得為”的邏輯的話,那么在庭前會議上提出的提供新證據和證人、鑒定人、有專門知識的人出庭的申請難道只能等到庭審時才能由法官來作出同意與否的決定?這顯然是對相關法條的機械理解,不符合常理。根據《刑事訴訟法》第20條和《解釋》第15條第3款,回避問題應由院長、檢察長、公安機關負責人或者審委會、檢委會來決定,管轄由基層法院改為中級法院時法官應報請院長決定。關于同級別法院之間管轄變更和上級法院改為下級法院的管轄變更,《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并未規定具體的決定權屬。但在司法實踐中,上述兩種管轄變更均應經過法院相關領導的審批。因此,對于控辯雙方在庭前會議上提出的回避申請和管轄異議,法官則無法直接作出裁判,只能是“了解情況,聽取意見”。綜上可見,從我國目前的法律規定及其內部邏輯來看,除了回避申請、管轄異議外,對于其余5項程序性申請,法官在庭前會議上均可直接作出相應的決定或裁判。
明確了在庭前會議上可以形成一定的結論這第一層含義后,更進一層的是,庭前會議上控辯審三方形成的共識及法官對某些事項作出的決定,對相關各方以及后續正式庭審程序的進行產生約束力。這種約束力體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在庭前會議上已形成決定或共識的事項,除非有正當理由,控辯雙方在庭審上不得再次提出;二是若無正當理由,在后續庭審中,庭前會議上已形成的決定或共識不得被隨意更改。從比較法的角度來看,我國臺灣地區《刑事訴訟法》第273條第2款規定,“若法院依本法之規定認定無證據能力者,產生約束效力,該證據不得于審判期日主張之。”可見,在我國臺灣地區的庭前會議程序中,法官不僅可以對控辯雙方系爭的證據能力問題直接作出認定,并且該認定對于正式庭審具有約束效力。在英國,答辯和指導聽證由于沒有被賦予一定的效力,從而在司法實踐中出現了上文中所描述的難以有效適用的尷尬。為了改變這一局面,英國在后來制定的《刑事程序和偵查法》中賦予了答辯和指導聽證明確的效力。《刑事程序和偵查法》第39條、第43條規定,法官在該程序當中能夠就證據可采性方面的爭議以及其他程序性事項或問題直接作出對后續庭審程序具有約束力的裁判。同時,對于法官在答辯和指導聽證上作出的程序性裁判,當事雙方有權申請法官撤銷或作出不同的判決,但前提是法官認為控辯雙方的這種動議“在看來符合正義的目的”。[8]334在我國司法實踐中,一些地方性的庭前會議實施細則也將會議結論的約束力包含在了其中。例如,根據太原市法、檢、司三家聯合會簽的《關于規范公訴案件庭前會議工作的意見》的規定:一方面,在召開庭前會議時控辯雙方已就相關程序性問題形成合意的,在正式庭審程序當中雙方不得再提出相關異議,除非法官認為提出異議的一方具有正當事由;另一方面,在召開庭前會議時,控辯雙方應當互相開示證據,該證據開示對控辯雙方的后續庭審活動具有約束力,即未在庭前會議上開示的證據不得在后續庭審中出示。*參見馬倩如、馬紅彬:《山西太原:積極探索工作機制辦案模式對接修改后刑訴法》,載于《檢察日報》2012年11月30日第4版。
四、觀念的轉變:實現庭前會議效力的根本保障
綜上,庭前會議的效力決不只是“了解情況,聽取意見”,庭前會議必須被賦予明確的效力。我國立法中一句撲朔迷離的“了解情況,聽取意見”的背后可能體現了立法者對庭前會議效力的一種保守的回避態度。這種語焉不詳直接導致了庭前會議效力的模糊甚至是缺失,進而對于庭前會議的適用率以及提高庭審質效的立法目的產生了負面效果。*司法實踐中庭前會議的低適用率以及對提高庭審效率的有限作用可參見左衛民:《未完成的變革:刑事庭前會議實證研究》,載于《中外法學》2015年第2期,第471、476、477頁。但要真正實現庭前會議的效力,只在規則層面突破“了解情況,聽取意見”的阻礙還是不夠的。從根源上來說,立法者和司法者應當實現觀念上的轉變,厘清庭前會議效力背后的三組基本關系:
第一,應重視產出與投入的平衡。這里涉及的是成本與收益的關系。不被賦予一定效力的庭前會議是一種只有投入沒有產出的程序,這種規則本身就不符合“成本—收益”的效率原理,同時也無法對程序適用者產生正向激勵,最終只能受到相關各方的冷落。
第二,應注重庭前程序的作用。這就要求處理好庭前程序與庭審程序的關系。“庭審中心主義”并不是“庭審壟斷主義”,真正實現“庭審中心主義”的國家其庭前程序反而更加發達,由庭前程序承擔更多的過濾和整理功能,確保庭審定罪量刑的核心功能。在適用庭前會議時應把握好實體問題與程序問題的界限,庭前會議可以承擔部分與實體有關的證據和爭點整理功能,但只能“點到為止”。應杜絕庭前會議的完全實體化,決不能將正式庭審的質證、辯論等環節前移到庭前會議中進行,導致庭審被架空。
第三,應接納程序性裁判這種新的司法裁判模式。這就要求我們平衡好實體性裁判與程序性裁判的關系。應當逐漸樹立起程序性裁判的新理念,改變一直以來的“重實體輕程序”的慣性思想,以拓寬法官行使裁判權的程序空間,而不是“唯庭審是瞻”。“以裁判為中心”是審判中心主義在我國未來的努力方向,[9]在庭前會議中法官也可對相關程序性爭議作出裁判。
唯有實現觀念上的轉變,明晰上述三組關系,才能撥開“了解情況,聽取意見”背后的“迷霧”,最終對庭前會議的效力問題形成共識,實現庭前會議規則的完整性,在“以審判為中心”的司法改革進程中實現庭前會議應有的價值。
[參考文獻]
[1]商西,程姝雯. 孟建柱: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將試點[N]. 南方都市報,2016-01-23(AA04).
[2]林鈺雄. 刑事訴訟法(下冊)[M]. 臺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7.
[3]郎勝.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釋義[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395.
[4]江必新.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理解與適用[M]. 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3.
[5]Summers R. Instrumentalism and American Legal Theory [M]. l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21.
[6]蔡墩銘. 刑事訴訟法概要[M]. 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12: 67.
[7]宋英輝,等. 刑事訴訟原理[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138.
[8][英]約翰·斯普萊克. 英國刑事訴訟程序[M]. 徐美君,楊立濤,譯.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9]閔春雷. 以審判為中心:內涵解讀及實現路徑[J]. 法律科學,2015,(3): 42.
〔責任編輯:馬琳〕
[中圖分類號]D925.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0-8284(2016)05-0107-06
[作者簡介]賈志強(1987-),男,山東濱州人,博士研究生,從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
[基金項目]中國法學會部級課題“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研究”(CLS〔2015〕C07);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刑事訴訟證明模式研究”(11BFX111);吉林大學研究生創新研究計劃項目“刑事庭前會議制度研究”(2014077);國家“2011計劃”司法文明協同創新中心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15-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