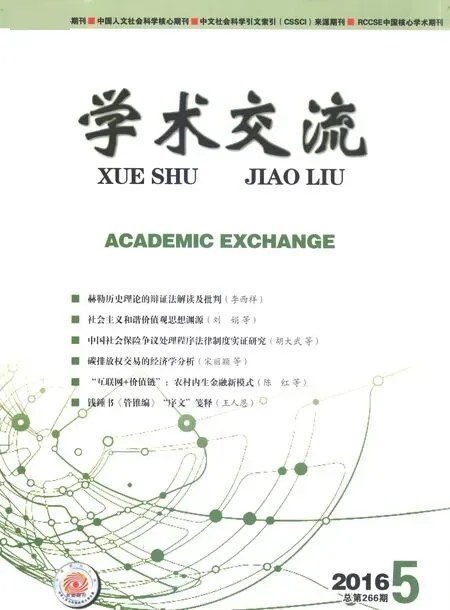普遍規定主義倫理學的實踐意義與難題
賈 佳
(揚州大學 社會發展學院,江蘇 揚州 225009)
?
社會學研究
普遍規定主義倫理學的實踐意義與難題
賈佳
(揚州大學 社會發展學院,江蘇 揚州 225009)
[摘要]R.M.黑爾的普遍規定主義元倫理學理論將道德判斷的規定性與“可普遍化”兩種屬性相結合,看似既保證了道德判斷和道德原則的指導行為的“屬人”特性,又在康德主義的意義上確保了道德判斷的理性和客觀性。以普遍規定主義的元倫理學理論為基礎,將其與實際生活中的事實性情境相結合,黑爾走向了以人際偏好的最大滿足為最高目標的功利主義。黑爾的元倫理學理論標志著元倫理學向規范倫理學的靠攏和對實踐中道德問題的重視,而他的理論的局限則是理性的工具性應用本身的局限。
[關鍵詞]“可普遍化”;規定性;功利主義;基礎主義;元倫理學
R.M.黑爾(R.M.Hare)認為,道德命題同時具有規定性和“可普遍化”兩重屬性。道德命題的規定性特質能夠成為道德分歧中的不變因素,這樣才能在不同文化中進行理性的道德探討。不過僅僅具有規定性的道德命題是不夠的,同樣具有規定性的單稱祈使句就不能被看作是道德命題;道德命題的規定性必須是“可普遍化”的,這樣才能既不陷入相對主義,又能保證倫理學學科的科學性。黑爾構建起的“普遍規定主義”倫理學理論,通過對道德語言的意義與邏輯關系的研究,力圖做到在理論上邏輯嚴絲合縫經得起推敲,在實際生活中能夠解決各種各樣的道德分歧,讓元倫理學的研究有更大的實際意義。
一、 普遍規定主義元倫理學理論的提出
黑爾提出,道德語言,尤其是“應該”這樣的概念在道德語境中在充分的意義上使用時,具有兩重屬性。其一為規定性,表明了道德語言與一般性的規定語言即祈使句具有一定的聯系,也就是說,“應該”語句蘊涵著一個祈使句。祈使句總是與人,尤其是人的行為相關;更重要的是,祈使句所表達的不是某種經驗事實,而是說話者的意愿或要求。與陳述句不同,祈使句不具有“是”層面的真值條件,單稱祈使句類似于情感主義者對道德命題的看法:具有任意性并且是個人意愿的一種表達。道德語言與單稱祈使句在“規定性”意義上的相似性說明道德命題同樣不具有“是”層面的客觀性,而總是與人的意愿、要求與選擇相關。但這并不表明道德命題本身是主觀任意的,而只是表明了道德命題的客觀性在“意義證實”*包括邏輯實證主義的“意義證實”原則和波普爾的“證偽”原則等。標準范圍之外,因為道德不能缺少有意識的人的參與。道德命題代表了人的行為傾向。
道德概念的另外一種屬性是它的“可普遍化”性質。黑爾認為這是道德語言與描述性語言的相同之處,即其描述性意義。在使用道德語言時,如果認為某一行為或人是“好(善)”或“應該”的,就不能認為與其在普遍屬性上完全相同的另一行為或人是“不好(惡)”或“不應該”的,否則就是陷入了邏輯矛盾。道德命題的可普遍化的意義在于:首先,一定程度上可普遍化的性質使道德命題有可能具有真值條件。可普遍化為道德命題提供了一種標準,即“好在何處”的標準,因此當一種“好的標準”被某一社會公認,就有了驗證某一事物或行為是否為“好(善)”的真值條件;只不過與描述性命題不同,這種真值條件不是分析性的存在于概念的意義和邏輯關系之中,而是一種實質性的道德要求。[1]94-110并且,真值條件本身會隨著人們道德觀念的變革而發生變化。其次,可普遍化的性質使“是”與“應該”之間具有了一種“隨附性”[2]的關聯而非任意為之。道德語言的標準即其描述性含義所表達的是一種客觀的事實性標準,對這一標準的認同表明了對某種“事實”的認同。因此,對某一個公認的標準而言,“應該”是建立在“是”的基礎上的而不是與“是”毫無關系。再次,“可普遍化”的性質將道德命題與一般的單稱祈使句區分開來。單稱祈使句并不需要有一種事實性的標準作為基礎,并且即使存在一種事實性的標準(或不如說是“原因”),它也不必要是可普遍化的。而使用了“應該”等價值詞的道德命題卻必須要有一個可普遍化的事實性標準,否則對“應該”的使用就是不恰當的或至少是“加引號”[1]121-126的。將道德語言與一般祈使句區分開來,就是將普遍規定主義的元倫理學與情感主義區分開來,認為道德判斷不是個人意愿和情感的任意表達,而是在客觀標準之下做出的理性選擇,這也是道德判斷具有可普遍化性質的另一個重大意義:即道德判斷本身可以是理性和客觀的。只不過“客觀性”指的不是經驗事實,而是有理性的人將會一直做出的客觀抉擇,即“主觀的普遍性”。*類似于康德意味的“客觀”。
普遍規定主義倫理學理論將道德判斷的可普遍化性和規定性兩種屬性相結合。可普遍化的性質使道德判斷具有一種能夠進行理性推論的邏輯結構而不會任意為之,使道德推理以及在一定程度上解決道德分歧和道德爭論成為可能;而規定性則使道德判斷具有“屬人”的性質,而不存在于“世界的客觀結構”[3]之中。這兩種屬性的結合使道德判斷能夠理性地引導人的自由選擇,從而達到人的自由和理性的結合。道德判斷的規定性說明人具有在不同行為之間進行自由選擇的能力,而道德判斷的可普遍化性質則促使人在使用“應該”等道德語言做出道德判斷指導道德行為時,必須能夠同意道德判斷成為普遍化的“命令”而非任意的個人選擇。這樣一來有理性的人就不但有選擇的自由,而且必須承擔選擇的后果。黑爾在元倫理學層面上解決了人的自由意志和理性的普遍法則束縛之間的矛盾;并且由于道德判斷和道德行為是自由的人的理性選擇,因此每個人都要為自己所采取的行為負責,道德行為不同于外力強制下的“不得不”的行為,也不同于“任意”的行為。從而黑爾認為,普遍規定主義倫理學是對康德實踐哲學在元倫理學層面的闡釋,是對康德實踐理性三大定理“善良意志”、“人是目的”和“意志自律”在邏輯層面分析闡釋的結果;使任何一種實質性的倫理學理論都能夠在抽象的形式上檢驗其合法性。這樣的元倫理學理論能夠全面滿足一種充分的倫理學理論需要滿足的各項要求,既不會像自然主義、直覺主義那樣陷入僵化無法與外界對話的窘境,也不會像情感主義那樣任意為之甚至否認道德判斷本身能夠具有一定的科學性和真值條件[4]127-145,從而能夠在承認道德分歧的同時,通過對道德語言評價性含義在不同文化中使用上的一致性[1]94-110使不同文化之間的對話和交流,化解道德沖突成為可能,而不必陷入相對主義困境。
二、 普遍規定主義元倫理學在規范倫理學中發展
通過對道德概念的語言學研究和邏輯分析,黑爾希望元倫理學能夠為論證規范倫理學的合法性提供一種形式化的邏輯基礎。他以普遍規定主義的元倫理學為論證前提,得出的結論則是功利主義的。“功利主義在《道德語言》中寂靜無聲,在《自由與理性》中還是綿軟無力,到了《道德思維》中卻變得清晰鮮明。”[5]這一理論推進的進程,正是黑爾由普遍規定主義元倫理學到偏好功利主義規范倫理學論證過程的體現。
由前所述,道德命題的“可普遍化”特性要求“對同樣的描述性事實做出同樣的道德判斷”,邏輯上這意味著某種自我帶入:一個合道德的行為就是行為人既在實際的道德情境中規定應該如此行事,并且在假設的與實際情境中的普遍性事實完全相同的道德情境中,行為人將自己置于道德行為接受方的立場上依然規定對方應該如此行事的行為。通過對道德判斷的可普遍化性質推出了第一個結論:
(1)合道德的行為即某一道德情境c中,行為的所有相關方都理性地規定應該如此行事的行為。問題在于,行為的相關方是否能夠都理性地傾向于同一行為。畢竟,之所以需要道德,本身即是因為人們的行為傾向與選擇之間存在各種矛盾沖突。而針對這些不同行為人的不同偏好,黑爾認為,從可普遍化“對普遍的描述性要素相同的事實應該做出同樣的道德判斷”[1]129出發,必須“對不同人的不同偏好同等看待”[6]17。偏好指向的內容是主觀的,但“某個人對某事具有某種強度的偏好”卻是形式化的客觀標準,不涉及任何實質性道德內容,邏輯上完全可以通過比較偏好的強度來達成道德判斷上的一致。因此,通過偏好強度的比較來確定行為的道德與否就成了可普遍化的邏輯要求。至此可以推論出“可普遍化”的第二個結論:
(2)在某一道德情境c下,如果x偏好的強度a為s,y偏好b的強度為t;某一行為A將會滿足x對a的偏好,但無法同時滿足y對b的偏好;那么行為A是否合道德就要看s與t之差。若s大于t,在情境c下行為A的執行就是合道德的(前提是x對a的偏好無法以任何其他不損害y對b的偏好的行為來滿足)。結論(2)是一個簡化了的雙邊道德情境,在多邊比較中,從“可普遍化”中推出第三個結論:
(3)在某一個道德情境c下,如果x1、x2、x3……xn偏好a的強度分別為s1、s2、s3……sn,y1、y2、y3……ym偏好b的強度分別為t1、t2、t3……tm;某一行為A將會滿足x1、x2、x3……xn對a的偏好,但無法滿足y1、y2、y3……ym對b的偏好;那么行為A是否合道德就要看s1+s2+s3+……+sn與t1+t2+t3+……+tm之差。若s1+s2+s3+……+sn大于t1+t2+t3+……+tm,在情境c下行為A的執行就是合道德的(前提是x1、x2、x3……xn對a的偏好無法以任何其他不損害y1、y2、y3……ym對b的偏好的行為來滿足)。
這種對偏好強度的比較得出的結論是功利主義的。不過,與以往的各種功利主義理論不同的是:首先,黑爾的功利主義以自己的非認知主義性質的普遍規定主義元倫理學為基礎,是對道德概念的邏輯與實際道德情境中的描述性事實相結合的結果;其次,“偏好”這一與“人的行為與選擇”相關的計算標準的提出進一步表明了黑爾即使在規范倫理學中依然堅持的非認知主義立場。黑爾將對功利計算的標準定為“偏好的滿足”,由于偏好的指向相關于行為的選擇,而“偏好”本身又具有最大程度的形式化的性質,因此回應了批評者對“功利”如何界定的質疑;對偏好強度的計算以及通過“自己處于他人立場”的假設,也使對“功利”計算的方式盡可能地達到了客觀準確。
三、 普遍規定主義作為道德的基礎
黑爾一直熱切地希望道德哲學能夠具有一種指導實踐的效果,并且能夠使我們的社會和生活變得更“好”。但他的倫理學理論總地來說卻是建立在哲學邏輯這一最抽象、似乎距離實踐最遙遠的理論基礎上的,甚至他一直認為道德哲學就是哲學邏輯的一個分支學科。[4]1黑爾并不認為這會使他的道德理論在指導實踐的意義上造成困擾,相反,他堅信想要有一種能夠在實踐中起到權威作用,給人們的實際生活做出規范性指引的道德哲學理論就必須將其建立在一種中立性的、邏輯或語言學的理論之上。在《道德思維》中,他將其引申為正是這樣一種中立的理論要素為道德哲學提供了基礎(foundation)。
可以將黑爾的觀點理解為:(1)道德哲學(大體上)是屬于邏輯或語言學領域的學科;(2)它具有一種基礎性的作用;(3)它能夠幫助我們清楚地反思我們的道德思考,并且由于(1)能夠幫助我們思考我們所說的道德語言究竟具有什么樣的意義;(4)當我們這么做的時候,我們就發現了(2),即道德哲學的基礎性意義。
問題在于,這種對道德的“基礎”的尋求本身,究竟是一種理性的訴求,還是對理性和邏輯的盲目?黑爾稱自己的道德理論尤其是元倫理學的理論是一種康德式的普遍主義,但康德對“理性”的統治作用卻是持懷疑態度的,所以他才會在批判實踐理性之前對“純粹理性”進行批判。而黑爾對一種合理性基礎的追求是否陷入了一種笛卡爾主義的泥潭中?黑爾認為自己的理論與笛卡爾主義是完全不同的。笛卡爾最終依賴的是對某些實質性真理存在的臆測,只是因為這些理念是“清楚而明晰的”;而黑爾卻是通過一種非認知主義的方式在所有人之間達成了一種共識,而這一共識的基礎不過是這些人對某些語詞用法的一致性同意。
今天,在哲學的各個領域中,基礎主義的觀點正在漸漸失色,對黑爾理論的否定性態度與這一趨勢也不無關系。黑爾對道德思考的基本觀點是我們不能僅僅通過對自己“直覺”的反思得出道德結論(至少不能將其放在第一位),因為這些“直覺”只不過是“我們自己的”,而不具有一種基礎性的性質。黑爾認為道德思考需要的首先是一種語言學上的探求,即他所堅信的第(1)點,但這一語言學探求卻是一種追求基礎,并且擺脫“我們自己的”道德直覺的欲望的結果。對那些不同意尋求語言學作為道德哲學基礎的人,黑爾的理論無法提供一種方法論上的理由使他們拒絕直覺主義,這一理由獨立于黑爾與他們之間的實質性分歧。他們或許自己也相信基礎主義,但是認為這一基礎就是某些道德見解本身;或許他們并不接受基礎主義,而是僅僅關注于這些觀點所暗示和假定的東西。黑爾對這些人所持方法的反駁需要依賴對自己理論所持的信念。
四、 普遍規定主義的邏輯與實踐
黑爾試圖通過對道德概念的邏輯和語言學分析,得出一個理性的普遍規定主義的元倫理學理論,并將之應用于規范倫理學當中,對人們的實際生活中倫理規范的形成進行設定和指導。在這一過程中,元倫理學從一種純粹的理論范疇中走出,削弱了元倫理學與規范倫理學之間的界限。黑爾對以往規范倫理學的態度是批判性的,他認為不通過對道德概念的元倫理學階段的理性分析,僅僅從個人自己所認定的實質性道德原則或事實性原則出發,建立起來的規范倫理學理論是任意、無根基的,并且不同的規范倫理學理論之間很容易發生無法解決的各種沖突,而道德原則沖突的后果對一個社會來說很可能是毀滅性的。當黑爾用一種非認知主義的方式將人們的道德觀念理解成為理性的人的具有可普遍化性質的規定和偏好時,“道德”不是“事實”中的一部分,但每一個理性的人在自己的生活中所面對的確實是各種各樣的事實性要素,這樣,“應該”不等同于“是”,但也無法脫離“是”的束縛自行其是。這種對“是”與“應該”的理解方式使元倫理學有可能與人們的現實生活接軌并對實際生活中出現的道德問題進行指導、化解道德沖突。但是,黑爾在倫理學在規范倫理階段的功利主義路徑與他的普遍規定主義元倫理學本身并不完全相應,而是在解決實際生活中的道德問題時尋求了一種無法用邏輯和理性本身進行解釋的手段:積聚性相加。這種手段的優勢在于使偏好強度具有了可比較性,從而為處理實際生活中的道德沖突等道德問題提供了工具性的方法;而問題則在于其本身對于一種普世的、工具化的理性的要求。
問題似乎更多的在于黑爾通過理性分析得出的“合邏輯”的道德結論究竟做到了什么。當使用一種非認知主義的態度看待道德時,道德與人的觀點、態度密不可分。而如果合道德的行為就意味著理性的人的觀點的一致性,那么黑爾在這里就給能夠實施道德行為、具有道德原則的人設定了一個限制:即只有理性的人才能是有道德的人。那么對黑爾來說,“理性”的人又意味著什么?理性一般意味著審慎,即知道個人的行為和抉擇的做出能夠帶給自己和他人多大程度的偏好的滿足。不過同時,黑爾也意識到了“偏好”本身是否理性的問題,他提出“狂熱者(fanatic)”[7]這個概念就是證明。狂熱者盲目地追求某一特定理念而不計行為所造成的后果,黑爾甚至認為在幾乎不可能發生的假定情境下,有可能某一狂熱者對自己理念的固執超過了該理念的實施對他人所造成的傷害的負面偏好,在這種情況下黑爾認為只能贊同狂熱者的理念,只不過這種情況在實際生活中不會發生,因此不需要重視。不過如此一來,“理性”和“非理性”的界限又在哪里?似乎只能認為理性的人就是能夠將自己的偏好進行普遍化的人。黑爾在這里的做法完全忽視偏好本身的內容而只注意偏好的強度,并認定所有“狂熱”的偏好在實際生活中都終將由于在強度上無法壓過絕大多數人反對如此實施的偏好而失去道德上的正當性。并且,即使存在一時一地的“群體性狂熱”導致一種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傷害,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有可能將這種群體性狂熱加以適當的引導使之導向較為無害的活動當中,就如同用參與和觀賞競技體育運動的狂熱取代對斗獸場中殺戮的狂熱一樣。[6]142問題是,如果這種偏好的轉移影響到了偏好的強度,并且被降低了的偏好的強度遠遠大于由此行為而受到傷害的人的負面偏好的強度時,是否為了偏好的最大滿足而犧牲少數人就成了合理的呢?當黑爾用“反思思考”剝除了我們自己本身持有的道德原則的“偏見”時,所剩下的唯一標準就是他的以不同人的不同偏好為指向的功利標準。于是問題又回到了起點:黑爾的體系化的方法在系統內具有一定的邏輯縝密性和組織完整性,卻由于標準的單一性和排他性而無法在系統外得到佐證。人們可以贊賞黑爾理論的嚴密與完整,卻完全拒斥這一理論本身。
五、 邏輯與事實區分的模糊
將黑爾的功利主義理論與元倫理學的邏輯關系割裂在實際操作層面確實能夠看到一定的簡便性和可操作性,但這樣一來,這種功利主義本身就會失去黑爾所固執的“邏輯基礎”。但這又不禁會使人產生疑問:一種“基礎性”的倫理學理論是否就比“無根基”的規范性道德更加合理與可行?當代哲學家和倫理學家往往拋棄或懸置了以往哲學中的“形而上學”基礎,與此同時,有些學者(如黑爾)選擇了一種更加理性化的邏輯學基礎作為哲學和倫理學真正的根基,更有些后現代的哲學和倫理學家希望能夠直面生活本身,而放棄以往哲學傳統中對“基礎”的追求。在這樣一種潮流中,黑爾的以元倫理學為基礎的規范倫理學理論受到了更多的攻擊。這種攻擊不僅僅出現在對普遍規定主義與功利主義之間邏輯推論關系的斷層上,更多的是來自對元倫理學中的概念之間的邏輯和語言學關系本身的質疑。
問題出現在“可普遍化”上。“可普遍化”究竟是一種邏輯上的必然性要求還是對“應該”語義的一種實質性解讀,很大程度上并沒有定論。從這里也可以看出,對“應該”一詞的語言學解讀本身是否已經摻雜了一些事實性的成分?至少黑爾的解讀路徑本身是有些模糊的。在構建他的普遍規定主義理論時,黑爾宣稱我們不能將道德的基礎建立在道德直覺上,但是卻可以并且只能將邏輯和語言學的基礎建立在語言學的直覺上,通過對日常語言“應該”的邏輯分析,最終得出了通向規范倫理學的結論。在這里,他是用一種語言學的“慣例”代替了一種道德上的“慣例”。但正如很多學者指出的,“應該”在日常語言中的用法是十分復雜的,黑爾所做的工作,是將復雜的“應該”簡單化為一種“可普遍化的規定”,而這個定義本身卻很難說是內在地存在于所有人的“語言直覺”之中的。
緣起于黑爾的元倫理學,通過對道德概念的語言和邏輯學分析,澄清了很多以往在規范倫理學中十分模糊的問題,其中最大的貢獻也許就在于將“休謨問題”[8]重新理解為“是”與“應該”、事實與價值的區分。而這樣一種區分對倫理學本身的發展方向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曾經主要是負面性質的,邏輯實證主義哲學與情感主義倫理學利用這種區分割裂了事實與價值,甚至將道德判斷本身看成是一種無意義的說話者個人情緒和意愿的表達。*如艾耶爾在《語言、真理與邏輯》第六章中,認為價值判斷不過是情感的表達。相對主義的理論對倫理學的發展和人們道德生活的影響幾乎是災難性的。黑爾的普遍規定主義元倫理學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是對情感主義和道德相對主義的應對和反擊。只不過與以往的“自然主義”路徑不同,黑爾的反擊是建立在事實與價值二分的基礎之上的非認知主義的,其最大的特點是將理性主義與非認知主義相結合,在此基礎上將“是”與“應該”的關系進行了重新的認識,用“人”的理性選擇取代了所謂的“道德事實”。只要“人”不喪失其“理性”的“普遍化”“個人偏好”的能力,以普遍規定主義為基礎的道德就可以說永遠是不同社會都“應該”采納的。這樣一來,道德就在社會發展和人的認識的恒常流變中歷久常新,即不局限于一時一地的道德原則又與理性的“人”的行為緊密相關。然而黑爾的理論絕非無懈可擊,后現代倫理的發展為“理性化”的倫理學理論提出了很多尖銳的問題,其中有很多是黑爾無法正面回答的。
究竟有沒有一種能夠在任何社會、任何時代都能適用的倫理學理論?黑爾認為只要理解了道德概念的邏輯構造,就能夠在元倫理學的基礎上構建這樣一種規范倫理理論,因為對理性的人來說,他們的偏好和規定總是與一定的“事實”相聯系,更重要的是這樣一種聯系即“是”與“應該”的聯系并不是一種決定與被決定、蘊涵與被蘊涵的關系,而是一種更為松散的弱“隨附性”關系。道德規范是關于人的,而非人之外的世界。但在這里是否存在著一種對“道德”的強行解讀?當代德性倫理學者往往認為對道德概念的理解、對倫理風俗和道德規范的構建都是與一個社會、一個時代的現狀相互關聯的,乍看起來黑爾的理論似乎也是如此,但仔細研究之下卻可以發現,黑爾對“普遍化”的道德概念的追求使得不同時代、不同社會下的不同道德狀況都成了對理性的人的偏好和規定傾向的不同解讀,而對“應該”本身的立場卻并沒有任何變化。但作為一個空泛的“可普遍化的規定”的傾向的“應該”,是否能夠承載作為道德基礎的重任?更重要的是,以往的人類社會并非如此重視具有“普遍性”的東西,對普遍性的強調更多的是從基督教式的“普世”價值中凸顯出來的,而在今天的多元文化的世界中,對“普世性”的宣傳一方面似乎有助于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對話與合作,另一方面卻又很容易成為某種“主流”“強勢”價值觀推廣自身價值理念,進行政治和文化侵襲的工具。“普遍性”本身的基礎又在哪里?基礎主義在尋求道德根基的同時,又不斷地把對根基的追求推向更深遠的地方,但能否得出一個最終的“基礎”?答案很可能是“不能”,于是道德的根基就從來都沒有牢固過。而另一個問題則在于“普遍化”究竟可以推廣到哪里。宣揚“動物權利”的倫理學家彼得·辛格認為普遍化應該適用于所有“可感物”,只有這樣才能不在廢除“種族歧視”之后,依然宣揚“物種歧視”[9],這對環境倫理學來說是一項十分重要的舉措,但同時又使我們對“普遍化”的定義本身產生了質疑。“普遍化”是否有其界限,界限又在哪里?是人類、有理性的存在、還是一切可感物亦或是整個宇宙的全體?我們又怎么來評判“普遍化”的界限?黑爾的理論嘗試構建起一系列生活的準則,但毫不意外地,它也必然帶來更多的問題。
六、 總結
黑爾的元倫理學理論標志著元倫理學向規范倫理學的靠攏和對實踐中道德問題的重視。他的理論作為一種體系化的理論本身的自洽性和其與體系外對話的困難是黑爾倫理學最大的特點和難題之一。黑爾要求我們在反思思考時放棄直覺性的道德原則,于是他的理論的評判標準就成了該理論自身。這個西方哲學有史以來一直存在的問題并沒有因為黑爾對邏輯和理性的極度重視而得到解除。作為對情感主義和道德相對主義的應對和反擊,黑爾對“是”與“應該”關系的重新理解以及對“應該”的“可普遍化”和“規定性”雙重特征的把握是具有歷史意義的突破,但無論是“可普遍化”還是“規定性”是否真的是“應該”的應有之義還是黑爾為了方便論證而強行設下的定義并歸之于“語言直覺”的常識,卻似乎還需要進一步商榷。普遍規定主義倫理學最重視的是人的理性慎思,由此黑爾和很多功利主義的推崇者一樣,在某種程度上認為正是人性的“自私”促成了道德的出現。在闡述一個自私的道德教育者如何對自己的孩子進行道德教育時[6]191-198,充分體現了黑爾對道德的這一態度。這種對道德的工具性態度成了很多人對其理論的詬病之處;但另一方面,如果順從他的理論的前提與推論的邏輯,卻又很難對其進行具有實質意義的辯駁與質疑。黑爾理論的局限是理性的工具性應用本身的局限。對其理論在特定范圍內部的批判只能是一種細枝末節上的修修補補,而想要超出他的理論,需要質疑的則是理性本身——即它對道德的基礎性作用及其作用方式。但無論如何,正視黑爾的元倫理學,就是對現世道德生活中種種道德現象的重視,這對以往的元倫理學理論來說是完全不同的。黑爾的元倫理學及其導出的規范倫理學,預示了一個更加體系化,更追求理論的邏輯深度卻又現實導向的道德哲學的發展方向。
[參考文獻]
[1]Hare R M. The Language of Morals[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2]Hare R M. Essays in Ethical Theory[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66-81.
[3]Mackie J L. Ethics: Inventing Right and Wrong[M].London: Penguin Books, 1991:15.
[4]Hare R M, Sorting out Ethics[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5]Bernard Mayo. Moral Thinking: Its Level,Method and Point[J]. Philosophical Books,1982,23(3):173.
[6]Hare R M. Moral Thinking[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7]Hare R M. Freedom and Reason[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105.
[8]休謨.人性論[M].關文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509-510.
[9]Peter Singer. Reasoning towards Utilitarianism, Hare and Critics[C].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147-161.
〔責任編輯:巨慧慧〕
[中圖分類號]B82-0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0-8284(2016)05-0153-06
[作者簡介]賈佳(1980-),女,江蘇揚州人,講師,博士,從事當代西方倫理學、元倫理學研究。
[基金項目]教育部基金“西方德性倫理的諸道德哲學形態研究”(12YJC720059)
[收稿日期]2015-0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