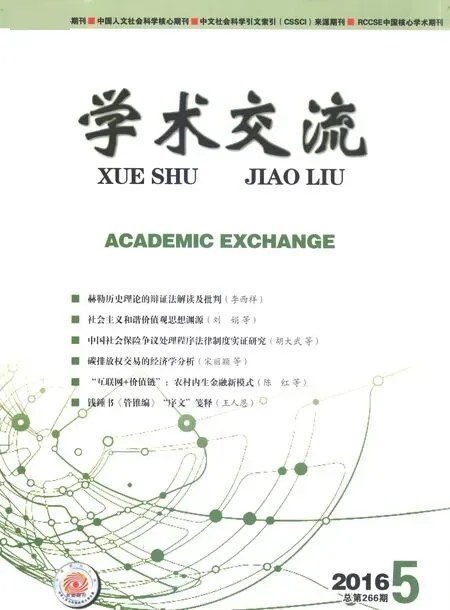錢鍾書《管錐編》“序文”箋釋
王人恩
(集美大學 文學院, 福建 廈門 361021)
?
錢鍾書《管錐編》“序文”箋釋
王人恩
(集美大學 文學院, 福建 廈門 361021)
[摘要]錢鍾書先生的《管錐編》壁立千仞,博大精深。1979年版《管錐編》之序文短小精悍,蘊義豐贍,因以古文寫就,且典故密集,不易釋讀。今對《管錐編》之序文作一箋釋,以廣其傳。
[關鍵詞]錢鍾書;《管錐編》;序言
《管錐編》是國學大師錢鍾書先生的學術代表作,它壁立千仞,博大精深。1979年版《管錐編》之序文短小精悍,含義頗豐,序言云:
瞥觀疏記,識小積多。學焉未能,老之已至!遂料簡其較易理董者,錐指管窺,先成一輯。假吾歲月,尚欲賡揚。又于西方典籍,褚小有懷,綆短試汲,頗嘗評泊考鏡,原以西文屬草,亦思寫定,聊當外篇,敝帚之享,野芹之獻,其資于用也,能如豕苓桔梗乎哉?或庶幾比木屑竹頭爾。命筆之時,數(shù)請益于周君振甫,小叩輒發(fā)大鳴,實歸不負虛往,良朋嘉惠,并志簡端。
一九七二年八月
1979年版之《序》共有兩段文字,第一段寫于“一九七二年八月”——可見此時《管錐編》已基本完成,第二段文字為“一九七八年一月又記”。《〈管錐編增訂〉序》寫于“一九八一年八月”,又有《再版識語》(1982年6月)《弁言》(分別寫于1989年10月、1993年5月)。以上序言皆為中華書局版原有。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版《管錐編》出版于2001年1月,前有楊絳《代序》,其中有“因為他在病中,不能自己寫序”一句,據(jù)此可知,三聯(lián)版無錢先生序文。楊絳《代序》寫于“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下距錢先生逝世的1998年12月19日僅一年。上述諸序,以1979年版《管錐編》之序文最為厚重和重要*本文所引《管錐編》文字除注明者外,均見中華書局1979年8月版《管錐編》、1982年9月版《管錐編增訂》。,而序文以古文寫就,且典故密集,不易釋讀,本文嘗試做一箋釋,以廣其傳。
瞥觀疏記,識小積多
二句以自謙語氣出之,亦含讀書為學之經(jīng)驗。瞥,眼光掠過、不正視。《淮南子·說林訓》:“鱉無耳而目不可以瞥,精于明也。”意謂鱉雖無耳朵,但眼睛卻蒙蔽不了,因為它失去了聽覺,視覺就變得特別靈敏。這里用“瞥觀”是謙詞,意為粗看。清人梁玉繩有一書名起得很謙虛的筆記,即《瞥記》,其文史考釋內容十分豐富,《管錐編》引錄梁玉繩《瞥記》多達十處。疏記:粗記。“疏記”之“疏”,為“粗疏”之“疏”,不為“注疏”之“疏”。《梁書·王筠傳》曰:“余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雖偶見瞥觀,皆即疏記,后重省覽,歡興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或為錢先生“序言”所本。另,“疏記”有“分別登記”之義,《史記·匈奴列傳》:“于是(中行)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眾畜物。”識小:語出《論語·子張》“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識,讀作志,《漢石經(jīng)》作志,《漢書·劉歆傳》引同[1]。《論語》所言為世間之通理。比如入山尋寶,有人撿到的是金子、美玉,有人撿到的是爛銅、石頭;又如做學問,有人看到的是大問題,寫的是鴻篇巨制,有人看到的是小問題,寫些細枝末節(jié)的短章小制。錢先生用“識小”是自謙為“不賢者”。古人以“識小”用于書名者甚多,多寓自謙之意,如明代周賓的《識小編》,是記載掌故瑣事之書。又如清人董豐垣的《識小編》、清人姚瑩的《識小錄》。又如《管錐編》兩次引用過的清初人徐樹丕的《識小錄》。徐樹丕為江蘇長洲人,號“活埋庵道人”,由明入清,隱居不仕,卒于康熙年間,另有《杜詩注》《埋庵集》等。《四庫全書》無《識小錄》,大概因徐為明遺民的緣故。
學焉未能,老之已至
二句乃自謙、感慨之語。學焉未能,語出《論語·先進》:“(子曰)‘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愿學焉。’”其實,此時錢先生已出版了多種文學作品和學術著作,如《寫在人生邊上》出版于1941年,《人·獸·鬼》出版于1945年,《圍城》出版于1947年,《談藝錄》出版于1949年。老之已至,語出《論語·述而》曰:“葉公問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fā)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序言落款時間為“一九七二年八月”,此時錢先生已虛齡六十三,剛從河南五七干校回到北京不久。古代文人未老言老、未衰言衰、未愁言愁、未貧言貧、未醉言醉者屢見不鮮,最經(jīng)典的例證如:屈原作《離騷》時尚在中年,然《離騷》中反復嘆老:“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杜甫《杜位宅守歲》:“四十明朝過,飛騰暮景斜。”白居易《隱幾》:“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歐陽修做滁州太守時虛齡四十,而《醉翁亭記》寫道:“而年又最高, 故自號曰醉翁也。”蘇東坡三十八九歲時任杭州通判,其《正月二十一日病后述古邀往城外尋春》詩云:“老來厭逐紅裙醉,病起空驚白發(fā)新。”清人姚瑩《識小錄》卷六有“文人喜言老”條,羅列甚多,可參*姚瑩《識小錄》卷六 “文人喜言老”條云:“昌黎生于唐代宗三年戊申,順宗永貞元年,守江陵府法曹參軍,時年三十八歲,《上李巽書》云:‘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又云:‘發(fā)禿齒豁,不見知己。’以未四十之年而遽言老,蓋老者,衰病之辭。公貞元十九年《與崔群書》云:‘近者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時年三十六耳,乃齒落發(fā)禿,有老之漸,故輒言老,年歲固不計也。少陵《贈翰林張四學士垍》詩云:‘此生任春草,垂老又飄萍。’在開元、天寶之間,杜公年亦僅三十許,而已云垂老。又《樂游原》詩:‘數(shù)莖白發(fā)那拋得。’《投贈哥舒》詩:‘已見白頭翁。’時天寶中年,公才四十,固已稱翁耶!天寶十三載秋大雨,杜作《秋雨嘆》云:‘老夫不出長蓬蒿。’時公僅四十三,已稱老夫矣。東坡通判杭州時,年三十九,《戲子由》詩云:‘如今衰老都無用。’又熙寧五年《吉祥寺賞牡丹》:‘人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人頭。’時東坡實年三十七耳,豈文人結習好言老耶?抑好用精神者血氣易衰耳?余未三十,兩鬢已星星見白,故知諸公非欺人語也。”見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xù)編第六輯、沈云龍主編《中復堂全集識小錄》第2318-2320頁,文海出版社,1974年影印本。。錢先生此處的“老之已至”之感慨并非傳統(tǒng)文人嗟老嘆貧的狡獪筆法,而系寫實,飽含悲涼之意。
遂料簡其較易理董者,錐指管窺,先成一輯
料簡,語出蔡邕《太尉楊公碑》云:“沙汰虛冗,料簡貞實。”“料簡”與“沙汰”相對為文。簡,簡選,挑選。理董:整理。同義詞連用。“董事會”即“理事會”。用“料簡”一詞,是指在一大堆筆記中挑選了一部分。據(jù)孔慶茂所著錢傳載,錢先生寫《管錐編》時作為參考的讀書筆記整整五大麻袋[2],故用“料簡”一詞極為形象而準確。“料簡”亦作“料揀”,洪適《隸續(xù)》一《漢平輿令薛君碑》:“料揀真實,好此徽聲。”*洪適《隸續(xù)》一《漢平輿令薛君碑》,見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第68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5月版。
錐指管窺:點明書名寓意。語出《莊子·秋水》:“子乃規(guī)規(guī)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 錐指:以錐指地。喻學識淺陋,所知有限。管窺:從管中看天。喻所見者狹小。秦漢典籍中,運用“錐指管窺”者甚多,如《史記·扁鵲列傳》、《韓詩外傳》、劉向《說苑·辨物》等。《韓詩外傳》:“譬如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大,所見者小,所刺者巨,所中者小。”[3]清人胡渭有《禹貢錐指》,今人楊樹達有《漢書窺管》,書名皆取義于《莊子》。
關于書名“管錐編”之寓意,學者們多有探索,海外的夏志清、柳存仁、高陽*《錢鍾書的〈管錐編〉》,見臺灣《聯(lián)合報》1979年7月26日、27日聯(lián)合副刊。和國內的陸文虎、李洪巖均有論證。陸先生透露,有一洋博士不懂《管錐編》的寓意,竟然把“管錐” 直譯為“管子與鉆子”;他指出,錢先生曾表示《管錐編》的英文譯名可叫作“有限的觀察——關于觀念與文學的札記(Limited views: 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陸先生又引韓愈《毛穎傳》、《新五代史·史弘肇傳》之材料,認為“管”、“錐”二字分別是“‘管城子’、‘毛錐子’的省略性叫法”,錢先生的筆名一為“中書君”,這與“管城子”“毛錐子”一樣,都是“筆”的別名,《管錐編》即筆會、筆記、編排的意思[4]。李洪巖先生別有會心,他進一步認為既然“中書君”是錢鍾書的筆名,而中書君即筆,即管城子、毛錐子,即管錐,所以“‘管錐編’三字藏有著者的名字,正是‘錢鍾書集’的意思”[5]。陸、李二先生之說足資借鑒。李先生所謂“正是‘錢鍾書集’的意思”云云甚確(詳下)。竊以為,“管錐編”實含有扌為謙之意。《周易·謙卦》:“無不利扌為謙。”王弼《注》:“指扌為皆謙,不違則也。”亦作謙扌為,錢先生曾在答鐘來因信中用之:“奉書甚感吹噓甚上之意。然足下?lián)种t,遂為老夫生事”[6]。錢先生字默存,是其尊人錢基博老先生所起,語出楊雄《解嘲》:“攫挐者亡,默默者存。”意在“叫他少說話”,其“父親因鐘書愛胡說亂道,為他改字‘默存’”[7]。平生謙扌為至極的錢鍾書以錐指管窺命名其學術代表作實含有謙扌為之意。
先成一輯:若粗略看過,則會忽略“輯”字之意,錢先生之文字字有來歷,此句亦非率爾操觚。今按:輯者,集也。《漢書·王莽傳》:“大眾方輯。”顏《注》:“輯與集字同。”《漢書》注中屢見不鮮。寫于1978年的《管錐編》之《又記》有“初計此輯尚有論《全唐文》等書五種,而多病意倦,不能急就”諸語,可知用“輯”乃一以貫之,“一輯”即指《管錐編》一部書。明乎此,則可知李洪巖先生釋“管錐編”為“錢鍾書集”之說甚確,盡管他未以“輯”字為“集”字進行論證。
《管錐編》之“編”,亦不可粗略看過,一部書或書的一部分都可叫編。張舜徽先生指出:“載籍極博,無逾三門:蓋有著作,有編述,有鈔纂,三者體制不同,而為用亦異。名世間出,智察幽隱,記彼先知,以誘后覺,此之謂著作;前有所因,自為義例,熔鑄眾說,歸一家言,此之謂編述;若夫鈔纂之役,則惟比敘舊事,綜錄異聞,或訂其訛,或匡其失,校之二科,又其次也。”[8]要之,天下書籍可分為三類:第一類,無復依傍、獨立創(chuàng)作的書,這一類即是著作,秦漢以上為多,如“五經(jīng)”。第二類即編述。“述”有繼承發(fā)展之意。此類書的特點是在前人創(chuàng)制的基礎上,用自己新創(chuàng)的義例加以提煉,使其書有集大成的特色,既有新思想新方法,又有新的價值,其代表作是《史記》,漢魏以下為多。《管錐編》即屬此類。第三類即鈔纂。排列已有的資料,組裝抄定成書,其代表作是《太平廣記》,唐以后為多。“編”不同于“篇”,許多報刊寫成“管錐篇”,誤。
假吾歲月, 尚欲賡揚
《爾雅·釋詁》:“賡揚,續(xù)也。”亦作“賡飏”。《說文》謂“賡”為古文“續(xù)”字。此處意謂日后將補續(xù)出版。據(jù)我所見資料,錢先生尚有論《全唐文》《杜少陵詩》《玉溪詩集》《韓昌黎集》《陳簡齋集》《莊子》《禮記》等十種,我們翹首以盼——其中許多爭論不休的問題,錢先生可能早已給出了精辟的答案。“假吾歲月”是古人常用寫法。《論語·述而》:“加我數(shù)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史記·孔子世家》:“假我數(shù)年,若是,我于《易》則彬彬矣。”孔子意謂上蒼讓我多活幾年,到五十歲時去學《易》,則可無大錯。錢先生意謂上蒼讓我多活幾年,可以再補續(xù)出版《管錐編》。章學誠《文史通義》有“假年篇”,旨在強調讀書須有愚公移山精神。錢碧湘先生《天降難得之才 惟恒持者大成》有言:“錢先生從‘干校’返京,知識分子前途未卜,我等蕓蕓眾生仍惶惶不可終日。錢先生則一如既往,處亂局而自定,埋頭潛心于學問。此后他又經(jīng)歷了棄家流亡、重病失語、唐山地震、煤氣中毒等諸多磨難。無論外部環(huán)境多么惡劣,無論自己身體多么病弱,錢先生始終孜孜不倦,持之以恒,終于成就大業(yè),為國家和民族留下皇皇巨著《管錐編》。……錢先生得天賜之才,以九死不悔之心執(zhí)著學問,琢磨以成大器。”[9]無論從題目還是內容看,錢碧湘都是錢先生之解人。
又于西方典籍,褚小有懷,綆短試汲,頗嘗評泊考鏡
西方典籍:指外文書籍,錢先生精通英文、法文、拉丁文、意大利文、德文、西班牙文,美國學者黃國彬譽之為“在七度空間逍遙”[10]。《管錐編》引用外文書籍達一千余種,其中大多數(shù)文字是錢先生自己翻譯的,不少新的西方文藝理論由錢先生最早引進國內。錢先生外文好,故能打通中外,打通古今,所論既有寬度又有深度。
褚小有懷,綆短試汲:語出《莊子·至樂》“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褚:囊,袋。綆:汲水器上的繩索。又《荀子·榮辱》:“綆短不可以汲深井之泉。”可見“綆短”句為當時通語。錢先生意謂:我的口袋雖然小,但還想多裝一點;井繩雖然短,但嘗試去汲取深井里的水。換言之,自己學問雖然很小,但有探索發(fā)明的愿望。語氣至為謙抑。
頗嘗評泊考鏡:“頗嘗”一詞,常人或會不作深究而輕易放過。其實,它也是用典,三國杜恕《體論·用兵》:“恕性疏惰,但飽食而已,家有書傳,頗嘗涉歷。”“頗嘗”含有“曾經(jīng)非常”的意思,如李白《上安州李長史書》:“頗嘗覽千載,觀百家。”韓愈《送進士劉師服東歸》詩:“仆本亦進士,頗嘗究根源。”竊以為,韓愈詩“頗嘗究根源”似為錢先生所本,韓愈言自己曾經(jīng)非常用功于考取進士,錢先生言自己曾經(jīng)非常用功于西方典籍。錢先生文字字有來歷,信矣!評泊:評說、評論,宋人常用語。朱耆壽《瑞鶴仙·壽秦伯和侍郎》:“教公議,細評泊。自和戎以來,謀國多少,蕭曹衛(wèi)霍 。”張炎《摸魚兒·己酉重登陸起潛皆山樓正對惠山》:“乾坤靜里閑居賦,評泊水經(jīng)茶譜。”考鏡:即章學誠《校讎通義》所謂“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縮語,旨在對歷代學術進行考辨,對其源頭進行考察甄別。也可作“鏡考”。《漢書·谷永傳》即用“鏡考”。考:校,比照。
原以西文屬草,亦思寫定,聊當外篇
屬草:猶屬文,寫作。寫定:指經(jīng)自己思考翻譯后寫出定稿。外篇:別于內篇而言,古籍中不少書分為內、外篇,如《莊子》《晏子春秋》《淮南子》《抱樸子》等。大致表達宗旨的列為內篇,有所發(fā)揮的列為外篇。成玄英《莊子·序》:“內以對外立名。內則談于里本,外則語其事跡。”《漢書·藝文志》顏注:“內篇論道,外篇雜說。”錢先生此處用“外篇”也是謙詞。又《管錐編》論“外篇”云:“《與楊遵彥書》:‘或以顛沛為言,或云資裝可懼;固非通論,皆是外篇。’按‘外篇’借用《莊子》、《抱樸子》等子書中名目,意謂題外之文、節(jié)外之枝,即支吾拉扯之托詞借口耳。”[11]此又揭明“外篇”另一義,足以啟人神智。
敝帚之享,野芹之獻,其資于用也,能如豕苓桔梗乎哉
“敝帚之享”語出《東觀漢記·世祖光武皇帝紀》:“帝聞之,下詔讓吳漢副將劉禹曰:‘城降,嬰兒老母,口以萬數(shù),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謂酸鼻。家有敝帚,享之千金。禹宗室子孫,故嘗更職,何忍行此!’”[12]敝帚:破掃帚。享:供奉。自家的破掃帚被認為價值千金。比喻自己的東西,即使不好也倍加珍貴。此乃錢先生自謙語。
野芹之獻:語出《列子·楊朱》。錢先生對《列子》很有研究,《管錐編》里就有專論。《列子·楊朱》:“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莖芹萍子者,對鄉(xiāng)豪稱之。鄉(xiāng)豪取而嘗之,蜇于口,慘于腹,眾哂而怨之,其人大慚。”后遂以“獻芹”或“芹獻”謙言自己贈品菲薄或建議淺陋。此亦是錢先生自謙語。周汝昌先生有一本紅學論集名《獻芹集》,取名亦出《列子》。錢先生素喜駢文,本來用一“敝帚之享”就夠了,但他又用了“野芹之獻”,使得文章不致偏枯而音調和諧。
“其資于用也,能如豕苓桔梗乎哉”應連讀,意為“我的這點東西能起到如豕苓桔梗的作用吧”。“豕苓桔梗”語出《莊子·徐無鬼》:“藥也,其實堇也,桔梗也,雞癕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何可勝言?”《釋文》:“豕零,司馬本作豕囊,云一名豬苓,根似豬卵,可以治渴。”《方言》卷八:“豬南楚謂之豨。”王先謙《莊子集解》:“藥有君臣,此數(shù)者,視時所宜,迭相為君。”郭慶藩《莊子集釋》:“時者,更也。帝者,主也。言堇、桔梗、雞癕、豕零更相為主也。”豨苓即豬苓。雞癕、豕零都是草,雞癕是雞頭草,又叫雞芡實。豕苓、桔梗皆可入藥,乃常見中藥。錢先生將他的著作比為不起眼的草藥,不足貴,雖屬自謙之詞,其中也含自信之意:我的微不足道的小文有時候或有用處。此句拿藥材來比喻,很高明也很巧妙。
或庶幾比木屑竹頭爾
庶幾:差不多;近似。《易·系辭下》:“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木屑竹頭”語出《世說新語·政事》: “陶公(侃)性檢厲,勤于事。作荊州時,敕船官悉錄鋸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后正會,值積雪始晴,聽事前除雪后猶濕,于是悉用木屑覆之,都無所妨。官用竹皆令錄厚頭,積之如山。后桓宣武伐蜀,裝船,悉以作釘。又云,嘗發(fā)所在竹篙,有一官長連根取之,仍當足。乃超兩階用之。”這個故事很有名,木屑可以止滑,竹頭可以做船釘。后用竹頭木屑比喻細微而可供利用的廢置之材。此句又用竹頭木屑做比喻,很貼切也很巧妙。錢先生在給趙景深先生的信中也用過“竹頭木屑”一典:“知大匠不棄散材,有取乎竹頭木屑,感愧感愧!”[13]
命筆之時,數(shù)請益于周君振甫,小叩輒發(fā)大鳴,實歸不負虛往
數(shù),屢次。請益:已受教誨而更有所問。語出《禮記·曲禮》上:“請業(yè)則起,請益則起。”這里意謂數(shù)次向周振甫先生請教,語氣非常謙虛。周振甫(1911-2000),浙江平湖人,無錫國學專修學校肄業(yè)。無錫國專出了許多大人物、大學問家,如錢仲聯(lián)、馮其庸、蔣天樞等。錢基博曾任無錫國專教務主任,周振甫與錢基博有師生之誼;周振甫小錢鍾書一歲,與錢鍾書則有師兄弟之誼。周振甫著作等身,有《周振甫文集》,他1948年即作錢鍾書《談藝錄》的責任編輯。周振甫《詩詞例話》中節(jié)引了錢先生《談藝錄》以及《管錐編》手稿中的一些文字,其“開頭的話”云:“錢先生還把他沒有發(fā)表過的李商隱《錦瑟》詩新解聯(lián)系形象思維的手稿供我采用,在這次補充里還采用了錢先生《管錐編》中論修辭的手稿,謹在這里一并表示感謝”*見周振甫《詩詞例話》第6-7頁,中國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詩詞例話》多處引用了錢鍾書的論著,除《管錐編》外,尚有《談藝錄》《宋詩選注》《通感》等。。《詩詞例話》出版之后,香港人始知道錢先生有《管錐編》這樣的書,可見二人關系之好。據(jù)周振甫言:1975年,錢先生請他吃飯,飯后拿出一疊厚厚的書稿交給他,說要借給他看,這即《管錐編》文稿。作為中華書局的資深編輯和《管錐編》的第一個讀者,周先生讀完后,就起草了《建議接收出版錢鍾書先生的〈管錐編〉》的報告及《〈管錐編〉審讀意見》。1979年,中華書局請周振甫作責任編輯,將《管錐編》作為重點書目出版,并于1993年獲得第一屆國家圖書獎。《管錐編》之細目都由周振甫所編,嘉惠學林,此功甚偉!用簡短的語言將一大段話的核心內容概括出來而又不違原著本義,足見周先生學養(yǎng)之深厚。對于周先生的審讀意見,錢先生給以“小叩輒發(fā)大鳴,實歸不負虛往”的高度評價,周先生謙言道:“我是讀到一些弄不清的地方,就找出原書來看,有了疑問,就把一些意見記下來。我把稿子還給錢先生時,他看到我提的疑問中有的還有一些道理,便一點也不肯放過,引進了自己的大著中。錢先生的《管錐編》很講究文采,所謂‘高文一何綺,小儒安足為’。他把我的意見都是用自己富有文采的筆加以改寫了。《管錐編》出版時,我曾提請他把序中那幾句話改掉,他不肯,就只好這樣了。”[14]《〈管錐編〉審讀意見》十分珍貴,茲引幾條:
周:“請益”、“大鳴”、“實歸”是否有些夸飾?可否酌改?
錢:如蒲牢之鯨鏗,禪人所謂“震耳作三日聾”者,不可改。[15]9
《序》中“小叩輒發(fā)大鳴,實歸不負虛往”是駢文、對句,上句從《禮記·學記》化出:“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后盡其聲。”錢先生意謂周先生對于自己所請教的問題解答得非常詳盡。下句從《莊子·德充符》篇化出:“魯有兀者王駘,從之游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于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游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釋文》:“請益則虛心而往,得理則實負而歸。”此處錢先生意謂向周振甫先生請教都能收獲頗豐。錢先生引二典故贊美、感謝周先生。周先生提請“可否酌改”,錢先生斬釘截鐵地答復“不可改”,并批曰“如蒲牢之鯨鏗,禪人所謂‘震耳作三日聾者’”。考“蒲牢之鯨鏗”典出《文選》班固《東都賦》“于是發(fā)鯨魚,鏗華鐘”之李善注:“(三國)薛綜《西京賦》注曰:海中有大魚曰鯨,海邊又有獸名蒲牢,蒲牢素畏鯨,鯨魚擊,蒲牢輒大鳴。凡鐘欲令聲大者,故作蒲牢于上,所以撞之者為鯨魚。鐘有篆刻之文,故曰華也。”后因以蒲牢為鐘的別名。錢先生意謂:您是大鯨,我是小鐘,我的小書因您而大放光彩。用典精辟而獨特,令人嘆服不已。下句“震耳作三日聾”是禪宗的著名典故,典出《景德傳燈錄》六《懷讓禪師》:“一日,師(百丈)謂眾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日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眼黑。’”極言受震動之烈。這里的“三”不是確數(shù),與“余音繞梁,三日不絕”類似。可參見汪中《釋三九》。又如:
周:楊雄,從木作楊,是有意如此寫,當照排。
錢:遵改。從通用。段玉裁《經(jīng)韻樓集》卷五:《書漢書楊雄傳后》:“其謂雄姓從手者偽說也”。故拙稿作“楊”,但此等處不必立異,遵教甚當。[15]11
關于楊雄之“楊”,從手旁還是木字旁,歷來有爭論。三國時楊修《答臨淄侯箋》云:“修家子云,老不曉事。”楊修言與楊雄是本家,這是“揚雄”之姓本作“楊”的鐵證。《史記》《后漢書》“揚雄”中之姓皆作“楊”。“揚”為唐人學楷書時習慣之訛變,張舜徽先生指出:“唐人書寫,凡木旁字,多急書成才。”[16]錢先生熟稔清代小學家的文獻,他以段玉裁《經(jīng)韻樓集》卷五《書漢書楊雄傳后》為據(jù),在手稿中寫作“楊雄”,然為避免標新立異,故改“楊”為“揚”以從眾。錢先生淵渟岳峙的氣度同樣令人嘆服不已,《管錐編》中多處有“周君振甫曰”,即采納周先生的意見而特別表出。當然,錢先生手稿中也有周先生讀不太懂甚至有誤解者。例如:
周:稱佛典攘竊中土書為夜郎自大,但上文稱“禪典都從子書翻出”,謂“語皆無病”,不知何故?
錢:弟所謂“語尚無病”乃指李翱及宋祁筆記,謂佛書與莊列合,非謂“盜竊”。本文似尚明白。[15]25
周先生未能洞徹手稿之深意,錢先生非常客氣而謙虛地作了解說,用一“似”字,委婉境界全出。又例如:
周:悟性屬魂,記性屬魄,這說似不科學。
錢:古人論文有此說,而治“文論史”者視若無睹,故標之。“科學”與否,非我思存,且其不“科學”亦不待言。[15]51
錢先生有自己的獨立思考,且寓含批評一些學者之意,與周先生思路有異。
良朋嘉惠,并志簡端
“嘉惠”語出《左傳·昭七年》:“嘉惠未至。”賈誼《吊屈原賦》:“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系別人所給自己恩惠的敬稱。簡端:書中。三聯(lián)版“再版識語”言及施其南、張觀教、陸文虎、范旭侖等人“糾謬”“是正”,“弁言”言及“王君依民校讎至百十事”。凡此皆所謂“良朋嘉惠”,《管錐編》中時見“周君振甫曰”、某某君曰字樣。
《管錐編》序文凡164字,內容十分豐富,典故密集,文采斐然,時見駢文對語,自謙語氣貫穿全文,自信之意亦不難感知。明乎此,于了解錢鍾書之為人、《管錐編》之文,不無裨益。
[參考文獻]
[1]高亨.古字通假會典[M].濟南:齊魯書社,1989:404.
[2]孔慶茂.錢鐘書傳[M].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2:194.
[3]許維遹,校釋.韓詩外傳集釋[M].北京:中華書局,1980:346.
[4]陸文虎.《圍城》內外——錢鍾書的文學世界[M].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2:30-32.
[5]李洪巖.智者的心路歷程——錢鍾書生平與學術[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395.
[6]錢鐘書致鐘來因信八封注釋[J].江蘇社會科學,2000,(3).
[7]楊絳.記錢鐘書與《圍城》[M]//將飲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87.
[8]張舜徽.張舜徽集·廣校讎略[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12-13.
[9]錢鍾書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0:248-249.
[10]黃國彬.在七度空間逍遙——錢鍾書談藝[G]//錢鍾書研究(第二輯).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0.
[11]錢鍾書.管錐編(第4冊)[M].北京:中華書局,1979:1476.
[12]吳樹平,校注.東觀漢記校注(第一冊)[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10.
[13]羅厚.錢鍾書書札書鈔(資料)[G]//錢鍾書研究(第三輯).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2.
[14]錢寧.曲高自有知音——訪周振甫先生[M]//沉冰.不一樣的記憶——與錢鍾書在一起.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1999:127-128.
[15]周振甫.《管錐編》審讀意見(附錢鍾書先生批注)[G]//馮芝祥.錢鍾書研究集刊(第三輯).上海: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02.
[16]張舜徽.清人筆記條辨[M].北京:中華書局,1986:411.
〔責任編輯:曹金鐘〕
[中圖分類號]I02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0-8284(2016)05-0189-06
[作者簡介]王人恩(1958-),男,甘肅蘭州人,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中國紅樓夢學會常務理事,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紅學、錢學研究。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guī)劃基金項目《〈管錐編〉破解古代文學學術陳案研究》(14YJA751023)
[收稿日期]2015-12-10
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