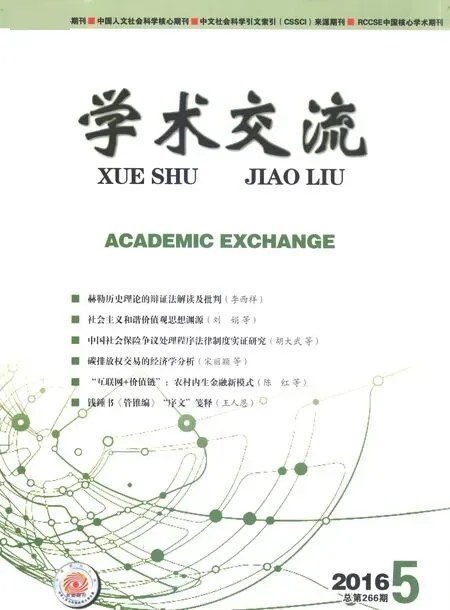民國時期新聞教育思想的多元呈現
李建新
(上海大學 上海電影學院,上海 200444)
?
新聞傳播學研究
民國時期新聞教育思想的多元呈現
李建新
(上海大學 上海電影學院,上海 200444)
[摘要]民國時期的新聞教育是多元呈現的,而且各具特色,存在有大學、社會團體、民間、新聞媒體、報業經營者、政黨、中外合作組織等創辦和運營的新聞教育。從現實存在看,這些新聞教育都是在當時能夠立足于社會、“應一時之需”的新聞教育。在這些不同類型的新聞教育中,萌生了一些較早的中國新聞教育思想和理念,舉其要者有“新聞教育要注意社會環境的需要”“新聞專業的學生要做猴子,不要做綿羊”“新聞教育是綜合性的教育”“入太廟,每事問”“靠感性試水,用理性固基”“敦品勵學”“新聞學如同醫科、法科,應實行5年學制”,等等。這些新聞教育思想大多源于實踐,顧及了現實社會的需要和教學實施過程中的合理操持,務實大于務虛,專注和聚焦于新聞教育本身的成分大。在今天看來,這些思想依然有值得借鑒和效法的內容。
[關鍵詞]民國;新聞教育思想;多元呈現
從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到1949年國民黨退敗臺灣,這是中國近代歷史上比較特殊的一個歷史時期,是中國的新聞教育在經歷了初創與起步期之后逐漸發展的一個時期,也是中國新聞教育多元呈現、類型迭出、流派紛呈、進步明顯的時期。在這一時期,出現了許許多多的新聞教育思想,它們不僅指導了當時的新聞教育的實踐與發展,而且在反復的砥礪中得到了豐富完善,為中國新聞教育發展積累了寶貴的財富。
一、大學新聞教育:新聞教育要注意社會環境的需要
持這一思想的是復旦大學新聞系和以系主任謝六逸等為代表的大學新聞教育單位。謝六逸是復旦大學新聞系首屆系主任。他在1929年9月—1938年8月擔任復旦大學新聞系系主任期間,主張新聞教育要“理論與實踐并重,教學與科研并重”,鼓勵學生鉆研新聞學術研究,出版新聞學書刊。1931年復旦大學新聞系創辦復新通訊社,作為學生實習新聞業務園地;1935年10月還舉辦了首屆世界報紙展覽會。
謝六逸認為:“大學是一國的最高學府,最高學府不能獨立地完成某學術上的研究,殊令人有‘大學無用’之感。”[1]按照謝六逸的設想,大學應該在完善學術研究的設備、盡最大努力滿足社會的環境需要等兩方面進行提高和改進。根據這兩方面的理由,謝六逸主張大學的文學院應該開辦新聞學系或新聞學業專修科。[1]謝六逸還提出了新聞教育要注意社會環境的需要的觀點,認為社會對新聞信息的需求是創辦新聞教育的最根本的出發點和立足點。謝六逸認為,新聞學的知識與技能,是最活用的知識,新聞系的學生對于各種科學必須涉獵,所以他們的常識最為充分。[2]在這個層面,謝六逸不僅概括出了新聞教育的核心宗旨,那就是滿足社會需要,而且還給出了新聞教育的正確路徑——接觸社會,知識與技能同樣重要。
二、中國共產黨早期的理論家:新聞專業的學生要做猴子,不要做綿羊
持這一思想的代表是陳望道。陳望道(1891—1977)是為數不多的早期中國革命家和新聞教育家,他最早翻譯了《共產黨宣言》,其對新聞教育的觀點為共產黨的新聞教育注入了源頭活水。比如他提出的新聞專業的學生要做猴子,不要做綿羊的觀點等。他認為新聞記者應該具有降妖除魔的“孫悟空”的特質,不能像羔羊一樣,不敢抗爭,任人宰割。
從1941年至1950年,陳望道擔任復旦大學新聞系主任達9年之久。他有豐富的辦學經驗和進步的新聞教育思想。 在他主持下,復旦新聞系樹立了民主的優良作風,人才輩出,成為全國各高校中著名的系科之一。作為一名無產階級的新聞教育工作者,陳望道秉持了無產階級新聞教育理念,堅持了無產階級新聞教育的做法,如他堅持新聞教育必須做到理論學習與新聞實踐相結合。1943年3月1日,復旦新聞系恢復復新通訊社(1931年創辦,抗日戰爭爆發后停辦),作為學生實習機構。為了給學生提供更多的實踐機會,1944年4月陳望道先生發起創建新聞館,師生群起響應。為此,他還請書法名家于右任先生題寫了“復旦新聞館,天下記者家”的書作,制成牌匾,放置在新聞系醒目的位置,喚起大家對新聞工作的敬重和熱愛。
最能體現陳望道個人新聞教育思想的是他提出的觀點“新聞專業的學生要做猴子,不要做綿羊”。猴子是聰明、靈巧、智慧、勇敢的化身。猴子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神話中的猴王孫悟空。試想,如果一個新聞系的學生能有孫悟空一般的本領,那他在工作中還有何懼呢?縱有數不盡的妖魔鬼怪沿路阻礙,但猴王最終還是保護師父取回了真經。陳望道希望他的學生也能像猴子一樣,在經過不懈的努力后,能實現心中的目標。從1943年起,復旦新聞系學生每周舉行一次“新聞晚會”。陳望道希望他的學生們能夠像猴子一樣鉆天入地、縱橫四海,在新聞、政治、社會等領域,進行獨具個性色彩的探索。猴子的代表孫悟空最為人們所稱道的是他有一雙火眼金睛,能夠明辨是非,敢于鋤奸滅害,敢于堅持正確的東西,哪怕這樣的觀點一時不為“師傅”所認可。 陳望道把猴子的這個特點與新聞工作的特色結合,以“宣揚真理,改革社會”的方式來教育和要求他的學生。
三、 民間非學歷教育者:新聞教育是綜合性的教育
持這一觀點的代表人物是顧執中。1928年,顧執中在上海創辦了民治新聞專科學校。民治新聞專科學校,是民國時期比較有影響力的一所新聞學校。經過20多年的實踐與摸索,顧執中在其后來的總結中深刻地體會到,新聞教育應該是綜合性的教育。顧執中的新聞教育實踐,其實就是把綜合性教育的理念貫穿始終的過程,經過多年學理的探討和技術上的運用,他不僅建立了報學的理論體系,使報學列為社會科學的一部分,而且對于報業的改進有重大貢獻,世界報業的經營標準因而提高,報界人才的素質也趨于優秀。
顧執中及民治新專堅持在教學中把跟新聞工作有密切關系的知識和技能,像編輯、采訪、管理、印刷和發行等,系統地傳授給新聞系學生。由于新聞對人類社會的重要影響,這些有關新聞工作的知識和技能在實際工作前先行學習,并且要學習得非常之好,是必要的。他認為把從未學習和研究過新聞的人當作新聞記者是一種冒險的行為,因為報社和通訊社在新聞方面所犯的錯誤,有時竟會嚴重得不只發生經濟方面的損失,同時也可能會發生政治方面的對人類和國家極為不利的損害。由于新聞工作的特殊性,顧執中認為新聞記者的情操、態度、方法、思維等,與專業知識及專業知識之外的其他廣博的知識一樣,對新聞記者工作的成敗構成重大的影響。因此,顧執中在教學中堅持新聞教育的綜合性,盡可能多地把相關的知識與做記者的基本要求傳授給學生。
四、“媒介集團”經營者:入太廟,每事問
這一思想的代表人物是成舍我。成舍我以“三個世界”名世。“三個世界”是指成舍我從1924年4月1日至1925年10月1日的一年半時間內先后創辦的《世界晚報》、《世界日報》和《世界畫報》,后稱“三個世界”。三報各具特色,但卻互為犄角,俱損俱榮。因而,成舍我被稱為“中國最早嘗試報團化經營的報人”[3]。從數量和規模看,成舍我當初經營的 “三個世界”完全是一個“媒介集團”,他辦新聞教育,完全是為了“集團”的需要,因此,他對新聞教育的要求更貼近實戰,更注重應用能力的培養和對新聞業態的把控。
1933年2月,成舍我創辦了世界新聞專科學校,這年先開辦附設的初級職業班。首先辦起來的是排字和編輯兩個初級班,由于不收學費,要求入學報名的人非常踴躍。1935年9月,又辦附設的高級職業班;1937年決定開辦本科,7月已登報招生,后因北京淪陷,學校停辦。在第一屆初級職業班招生簡章中,開頭闡述辦校的意義說:“本校目的,在改進中國新聞事業,及訓練手腦并用之新聞人才。”世界新聞專科學校有自己的實習工廠。在該工廠廠房門上有一副對聯,頗引人注目,上聯“莫刮他人脂膏”,下聯“要滴自身血汗”,橫批“手腦并用”。后來“手腦并用”成為校訓。成舍我每次在辦學過程中,對學生們作出的第一個許諾,就是“聘請最好的老師”。在北平新專時期,他所請的老師如張友漁、左笑鴻、薩空了、趙家驊等都是具有豐富學識和辦報經驗的人。在學校工作的其他方面,他也聘請最有工作經驗的人,體現了他的眼光和膽識。[4]
最能代表成舍我新聞教育思想的是他曾經寫給一位學生的題詞“入太廟,每事問”。“太廟”包羅的東西太多,也太有玄機,要真正能學得其中一二,就要“每事問”。五四時期北大提倡并領導新文化運動,蔡元培校長親自發起組織中國第一個新聞學研究團體以及蔡元培、徐寶璜等強調的新聞從業人員必須具備特別之經驗與廣博知識,[5]對青年成舍我產生了巨大影響,其后的新聞事件也使他感受到博識之廣聞對于新聞記者的重要性。因此,他提倡“入太廟,每事問”,要求學生對一切陌生的東西感興趣,要敢于提出問題,提出質疑,要有探賾索隱的治學謹慎,同時,希望從事新聞工作的人,要秉持新聞主義的理想,極力探求新聞事件及其背后隱藏的真理、真相、真情等,要敢于且善于闖一切禁區,縱然是“太廟”禁地也不應擋住記者發現“新聞點”的視角,也不能捂住記者采訪新聞的“新聞嘴”。從今天的視角看,我們可以把“太廟”理解成整個社會。一個合格的“新聞人”,應該是一個完全了解社會的人,能夠對社會的諸多未知進行關注、報道的人,不放過任何社會疑問與疑點的人。“每事問”既是要求,也是法則,更是武器。
1920年4月,成舍我在上海的《時事新報》發表文章說:“總之,輿論家是要往前進的,不可以隨后走的。他是要秉公理的,不可以存黨見的。他是要顧道德的、不可以攻陰私的。他是要據事實的,不可以憑臆想。他是要靠知識的,不可以尚意氣的。”[6]他希望通過這些新聞教育理念的灌輸和堅持能為新聞界培養出“辦報、興學、問政”的合格人才來。他很贊同徐寶璜的觀點,認為辦報是要“立在社會之前、創造正當之輿論”,應“謹慎據實直書”、應代表國民輿論而不是黨派利益等。[7]
五、報人: 靠感性試水,用理性固基
倡導并踐行這一理念的是知名報人趙敏恒。 趙敏恒早年以記者工作名世,后來以新聞教育而出彩。他于1944年出版的《采訪十五年》雖然不是探討新聞教育的專著,但也從中透露出許多新聞教育的信息。這些信息昭示了民國時期報人對新聞教育的看法和要求。
靠感性試水,用理性固基,實際上是顧及了新聞教育的兩個方面,就是實踐與理論。趙敏恒向媒體投稿而被采用,激發了他的新聞熱情,并由此步入新聞殿堂。在他從事新聞實務之后感到新聞工作需要理論的支撐。于是,他在清華學校畢業后,到美國留學,他先在科羅拉多大學文學院就讀,接著又進入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系統地學習了新聞學原理、采訪、編輯、新聞、特寫、社評寫作、鄉村報紙、資料編存、報業管理、廣告、印刷等課程,對新聞專業的基本技能進行了全面訓練,1925年6月,趙敏恒獲得新聞學學士。是年9月,他進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研究院深造。1926年5月,趙敏恒獲得新聞學碩士學位,成為最早出洋攻讀新聞專業并取得碩士學位的中國人。[8]他以自己的親力親為詮釋了他對新聞教育的理解:感性試水,理性固基。其內涵和寓意是,如果要選擇新聞工作,首先要看看自己的直觀感受如何,不能強求,如果一旦選中,則一定要堅定不移、持之以恒,既要在感性上繼續升溫,還要在理論上力求深究,把學科的根基夯結實。1939年1月至1944年,趙敏恒任路透社重慶分社社長,兼任復旦大學新聞系教授,并為重慶的報紙撰寫專欄稿。這期間,他在記者和老師的雙重身份中交替轉換角色,在新聞實務和新聞教育之間探求新聞教育的規律和真諦,總結并踐行了“靠感性試水,用理性固基”這一新聞教育理念。
“我一向對于新聞學校沒有多大好感,而竟對于新聞學系學生如此情誼,實非初料所及。”“在美國密蘇里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系畢業后,雖想在新聞界打出江山,然時時感覺到新聞學校給學生們準備工作的不足和學校教授能力經驗的薄弱。”“回國后看見當時我國新聞學校多半都是野雞學校,某大學新聞系主任,根本沒有作過新聞記者,對于新聞學術毫無研究,拿了新聞系主任招牌,到處招搖,作個人政治活動,令我對于新聞學校的印象,一天比一天壞。”[9]在現實面前,趙敏恒沒有選擇沉默,而是想到了做一個教師,更確切地說是一個新聞教育者的職責和應該擔當的道義。
在《采訪十五年》中有關于新聞教育的一篇文章,題目是《我看新聞教育》,比較核心的內容有:“我離開新聞學校后從事新聞事業的時間愈長久,愈感覺到新聞教育的重要”;“新聞從業人員大致可分兩種:一種純粹職業化,拿它當一種職業養家活口,只求維持飯碗,沒有前進創造精神和意志,另一種則拿它當一種事業,時時想改善,時時求進步”;“新聞學校學生沒有富于經驗的老記者們在旁提攜指導,有無從下手之苦”,等等。他的這種認知,對新聞教育的理解和態度、對想從事新聞職業人生的看法,很具有洞明透徹、引領指導的風范。
六、 政治大學新聞系:敦品勵學
政黨新聞教育也發端于民國這個歷史時期。其中,國民黨創辦的政治大學的新聞教育是一個代表。
1935年9月,國民黨中央常委會決議在中央政校設立新聞系,馬星野負責籌建工作,政治大學新聞系的“目標是培養真誠純潔的青年,成為大公無私,盡忠職守的新聞記者……信仰三民主義,忠愛國家民族,并以促進自由世界人士之團結與了解目標。深信新聞道德重于新聞的采編技術。新聞系之教育使命就是要敦品勵學,發揚以往的光榮傳統,開拓燦爛的未來”。[10]這一時期,政校新聞系的課程設置及師資隊伍的大致情況是:在專業課方面,馬星野講授新聞學概論、新聞事業史、新聞寫作、社論寫作;劉覺民、黃天鵬講授報業組織與經營(報業經營與管理);湯德臣講授采訪與編輯(新聞采訪);錢華講授新聞采訪、新聞編輯;沈頌芳講授新聞編輯;俞頌華講授編輯學;趙敏恒、顧執中講授采訪學;錢滄碩等講授編輯學;王蕓生講授評論;戴公亮講授攝影等。在基礎課方面,有左舜生講授中國近代史;壽勉成講授現代經濟問題;趙蘭坪等講授經濟學;蕭孝嶸講授心理學;孫本文講授社會問題;胡貫一、詹文滸講授哲學;陳石孚講授政治學;戴德華(Edward G. Taylor)及其妻子懷娣(Roberta White)以及周其勛、高植等分別講授新聞英語、英文寫作與英文。其他課程還有文學與寫作、廣告學、會計學等。[11]
南京政府成立后,制定了一些發展新聞事業和教育事業的政策。在教育方面,國民黨制定、頒布的一些政策,相關的法令、法規、綱領等,均有“敦品勵學”思想的體現。
七、 效法西方: 新聞學如同醫科、法科,應實行5年學制
民國時期已經有不少學者從西方學成歸來,并把西方新聞教育的理念、做法等“移植”到中國來。他們的許多觀點,為中國的新聞教育提供了幫助和參考。其中,蔣蔭恩是比較有代表性的一位。
蔣蔭恩曾經在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留學,對密蘇里新聞教育模式相當熟悉,在他回到母校燕京大學任教以后,便有意無意地效法密蘇里的新聞教育。雖然他是《燕京新聞》的發行人,但編輯、校對、出版、發行等各個環節都有學生全程參與。[12]這就為培養學生的綜合能力提供了一個訓練平臺。
新聞學是一個注重應用能力培養的學科,新聞能力與醫生的診病能力、法官的斷案能力、農民的耕種能力等一樣,要在實戰中學習,并靠實戰來檢驗,然后繼續在實戰中提高。在包括蔣蔭恩在內的早年的新聞教育家看來,新聞工作是文人的活計,文人論政在中國有著非常好的傳統,一個記者如果文字功夫不過硬,即便有再好的題材,有再好的內容也無法用新聞作品體現。效法醫科的培養模式,蔣蔭恩提出了將大學的新聞學系改為5年制的觀點,他還進行了相關的論證:新聞教育實行5年制,實際上是增加學生的實戰能力,給他們更多的時間去進行新聞工作的歷練。應該說方向是正確的,但蔣等沒有慮及人文社會科學與醫科的差別以及當時人們的承受能力,所以這樣的倡議并沒有得到多少響應,也沒有開展起來。
從今天的觀點看,可以采取適當壓縮純理論課的做法,把更多的課程安排與實踐掛鉤,或者改變教育環境,如把新聞院系變成一個媒介集團等,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八、總結與討論
中國的新聞教育肇始于民國,也成長、完善、成型于民國時期。雖然民國之后的新聞教育還在發展與提高,但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新聞教育在民國的后期基本形成了幾個不同的類型并在實踐摸索的基礎上趨于完善。但在一個比較長的時間內,“中華民國”或者“民國”不見于歷史的記載之中,民國的新聞教育自然也就在歷史中“消失”了。本文旨在還原這段不應該被忘記的歷史,從教育思想方面探尋新聞教育的發展脈絡與軌跡,以期對歷史負責。因為一部完整的中國新聞教育史需要補全這個歷史的“遺漏”。
應該值得肯定的是:中國新聞教育肇始于民國,拓疆開域,從無到有,這個質的改變是有關注與研究價值的;民國時期的新聞教育是“多元呈現”,正好反映出了民國時期的政治生態、社會生態、教育生態以及人們的思想狀況,新聞教育的思想,似乎也不僅僅是限于新聞教育領域,有影射的作用與功效可資借鑒;國共兩黨的新聞教育都誕生在民國時期,詮釋了新聞業在社會中的地位,體現出了在戰爭與斗爭的環境下它所具有的“槍桿子”的功效特質;中國新聞學研究生教育始于民國,雖然它沒有形成規模也沒有模式出現,但或許它的意義或價值就在于它向新聞教育的那個池塘投進去了一個石子,漣漪隨后泛起;民國新聞教育受西方的影響明顯、密蘇里模式在民國時期大行其道,是源于它代表了那個時代的國際水準與方向;選擇有代表性的新聞教育家進行研究,是因為教師是新聞教育的執行者,也是新聞教育思想的直接體現者與傳播者;民國報人對新聞教育有精準的論述和獨特的看法,說明學界和業界的相互依存、相互配合、相互支撐、相互促進在民國時期的新聞教育界體現得很好。
民國時期新聞教育也有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如完整性、系統性不強,學理與理論建樹欠豐富,個人因素起比較大的作用而體制、組織的力量沒有達到應該的高度。
[參考文獻]
[1]李建新.中國新聞教育史論[M].北京:新華出版社,2003:113.
[2]陳桂蘭.薪繼火傳[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
[3]方漢奇,李矗.中國新聞學之最[M].北京:新華出版社,2005.
[4]方漢奇.成舍我傳略[M]//報海生涯.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192.
[5]成原平.輿論家的態度與修養[M]//報海生涯.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
[6]舍我.輿論家的態度[N].時事新報,1920-04-15.
[7]徐寶璜.新聞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部,1919:92.
[8]夏林根,主編.近代中國名記者[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
[9]趙敏恒.采訪十五年[M].重慶:天地出版社,1944:37-45.
[10]謝然之教授九秩華誕祝壽文集編輯委員會.新聞與教育生涯[M].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0:14-15.
[11]葛思恩.記早期的政治大學新聞系[J].新聞與傳播研究,1989,(1):169.
[12]陳家順.中國近代新聞教育思想本土化的范例——燕京大學新聞教育述評[J].河北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08,(7):44.
〔責任編輯:王巍〕
[中圖分類號]G210;G40-092.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0-8284(2016)05-0195-05
[作者簡介]李建新(1964-),男,山西代縣人,教授,從事新聞學、新媒體業務、新聞傳播教育研究。
[基金項目]2013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研究”(13&ZD154);上海大學新聞傳播學高原學科項目“新媒體時代職業新聞人才培養機理探討及新聞業務法則研究”
[收稿日期]2015-11-24
·新聞史專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