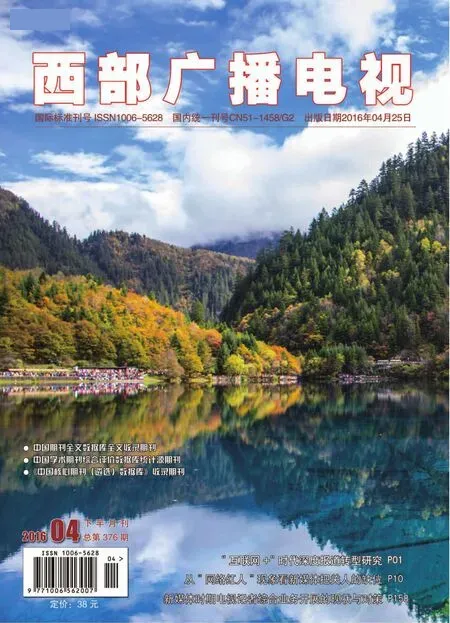從“網絡紅人”現象看新媒體把關人的缺位
張 權 羅 彬
(作者單位:新疆財經大學)
從“網絡紅人”現象看新媒體把關人的缺位
張 權 羅 彬
(作者單位:新疆財經大學)
社會的發展使大眾文化呈現多元化的趨勢,而互聯網又為普通大眾提供了一個更加多元的表達空間。在這種現實與技術的共同作用下,傳統的“把關人”模式受到多種因素的沖擊,如何應對新媒體環境下對信息的“把關”便成為新的問題。本文試圖通過“網絡紅人”現象,分析新媒體環境下受眾選擇信息的狀態,進而得出結論,認為新媒體環境下,“把關”的方式應從對信息的控制轉變為對受眾的引導;同時,也需要媒體、個人、監管機構的共同配合完成對信息的把關。
新媒體;網絡紅人;消費文化;把關人
互聯網技術的革新與進步對社會的各個層面產生著可見或不可見的影響,作為社會“瞭望哨”“潤滑劑”的大眾傳媒更是首當其沖。在傳統的媒介環境下,無論信息生產的專業組織還是組織內部的專業記者,他們既是信息的生產者,也是信息的“把關人”。受眾所接收到的信息在某種程度上都要經過“過濾”與“再加工”,而在西方,媒體更是被稱為與行政、立法、司法并列的“第四權利”。然而,新媒體的出現使傳播“5W”模式中的傳播者、渠道、內容、受眾的線性關系變得更加模糊。例如,在新的傳播工具的幫助下,信息的傳播渠道開始與傳播者融為一體。“網絡紅人”就是在經過互聯網到新媒體的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獨特的社會現象,筆者試圖分析“網絡紅人”現象產生的原因與其帶來的正面與負面的影響,從而對傳播者在新媒體環境下如何引導正確價值取向提出相應對策。
1 新媒體環境下信息把關的現狀
“把關人”理論最早出現在社會學領域,后來由傳播學者懷特將其引入傳播學中。其基本觀點是,大眾傳媒在進行新聞報道不可能是“有文必錄”,而是一個選擇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傳媒組織形成了一道關口,通過這個關口到達受眾那里的只是眾多新聞素材中的一小部分1。新媒體環境下,把關理論的變化體現在傳播機制與傳播內容的變化,前者是傳播者的變化,不僅是數量的變化而且也體現在傳播者層次的變化;后者一方面是新媒體所帶來的海量信息,另一方面是信息的碎片化,下文從這兩個維度分析新媒體把關的現狀。
1.1信息傳播機制弱化把關作用
信息傳播機制是對信息從發布者到接受者的渠道的總體概括。傳播者則居于信息傳播機制的中心環節,新媒體環境下,信息傳播者不再局限于那些受過專業訓練的記者與編輯,而是表現為分層與多元化的特點。首先,政府通過政策等間接方式對信息傳播進行“把關”。例如,國家“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提出不僅要在硬件上建設新一代互聯網接入設備,而且實現萬物互聯,人機交互、天地一體的綜合互聯。其次,根據《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規定》,一般商業網站只擁有轉載權,而不能進行采訪。相關門戶網站在引用傳統媒體新聞時對傳播內容實現“再把關”。最后,截至2015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達到6.88億,全年共新增網民3951萬2。作為在虛擬世界中話語權比重越來越大網民,來自社會不同領域,具有不同的職業背景,通過在虛擬世界中對信息的分享與評論中又進行了把關作業。不同的把關主體,依照各自篩選標準,在信息的處理中難免形成不同的甚至對立的意見,由此原先的把關作用受到弱化。
1.2信息內容碎片化增加把關難度
傳統媒體一般按照“起因-發展-結果”這一基本邏輯對信息加工處理,受眾因此接受到的是一條相對完整的消息。而新媒體的信息接受與處理打破了這種敘事方式,在信息海量性出現的同時,也帶來了信息的“碎片化”。日常生活中,在獲得一則信息后同時又看到與之相關的同類信息,事件的“真相”受制于這些碎片化信息間的互動,最終呈現的“真相”則偏向于價值取向相同的一方的信息。如果按照傳統思路對這些浩如煙海的信息進行把關,其工作量是難以想象的。
2 “網絡紅人”現象對把關作用的消解
“網絡紅人”一般是指以互聯網為傳播媒介進行自我展示,使自己在現實社會中無法實現的強烈表現欲在網絡空間中得以實現,并通過褒貶不一的爭論迅速走紅網絡3。一些具有強烈的表達欲而又不能通過正式的官方渠道經行表達的個人,借助新媒體這一傳播平臺將“審丑”“窺私”等視頻、圖片與網民分享,在主流話語環境下形成強烈反差。這種“抓眼球”“搏出位”的表演在社會、媒體、個人的配合之下可以迅速成為某一時間下的大眾討論的對象,在社會上產生負面影響。
2.1消費文化主導下網民無意識的產物
人們對于物的消費在網絡的影響下更加接近于對符號和符號背后意義的消費,消費的客體依然指向大眾化、娛樂化與商業化。社會快速發展過程中,無形的結構關系將社會大眾局限其中,這種局限所帶來的束縛與壓抑又使人們急需尋找到一種可以釋放壓力的出口,網絡紅人的出現在某種程度上便象征性地成為了表達心理與精神訴求的“出口”。參與感的介入,更是提升了這種互動關系。
俄國思想家巴赫金在他的狂歡化理論中曾指出,狂歡節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全民參與的演出,其理論核心在于實現人的自由平等。
例如,曾在社會上引起關注的“犀利哥”原本是處于社會弱勢的流浪乞討者,然而在某位攝影愛好者的照片中卻成為了“光鮮靚麗”的時尚先鋒,隨著網民的大量關注與電腦合成技術的使用,人們腦海中的“犀利哥”早以遠離了現實中的人物。從關注到不斷參與,網民“狂歡”形成的“網絡紅人”現象不自覺地對把關進行了削弱。
2.2專業主義缺失邊緣議題成為大眾議題
媒體議程設置的本質是某個新聞媒體傳播價值取向的問題4,信息生產者對信息的第一次把關理應是出于對社會負責的態度對信息的篩選。在新媒體的不斷沖擊下,一些具有一定社會或地區影響力的傳統媒體要么出于對廣告投放的追求,要么為了提升自身品牌價值也開始關注“網絡紅人”現象,其不好的價值導向沒有被引導,反而放大了娛樂、庸俗的一面,從“網絡紅人”成為現實社會中追捧的對象。
2016年春節期間,一網名叫“Papi醬”的女子迅速走紅網絡,并成為網民熱議的對象。其走紅固然存在個人努力的成分,清新自然的形象,貼近普通人生活的討論話題。如果忽略媒體的炒作并不公平。例如,新浪微博、愛奇藝等互聯網平臺的重點關注,再加上3月19日由多家投資企業組織公開的2200萬元的廣告競拍活動,都對其走紅起到了一定的推動。
3 把關對策:從信息把關到信息引導
傳統媒體的信息傳播中官方話語常占據主導地位,一些受到關注的人物和事件從敘事角度來看也被塑造成某種固定的模式,宣傳的目的也壓倒了信息傳播的初衷。新媒體的傳播方式已經成為點對點、交互式、滿足接受者內容需求的傳播,新聞從業者需要承擔其對新聞背景社會現象的深度解讀,幫助受眾正本清源從而引導社會輿論5。因而傳統的把關需要尋找到一個新的把關思路,也就是一種對信息絕對“控制”的把關,變為根據不同場景實行引導式把關。
3.1傳受互動提高信息透明度
一個事件從產生再到與預期相悖的結果,在很大程度是由于信息不透明。而新媒體傳播的匿名化加深了信息的不確定性,信息的傳播者也可以是信息的接受者,信息在傳播過程中隨時都可以被賦予新的意義,而進行再傳播。這中間的例子不在少數,而相對典型的就是“芙蓉姐姐”的走紅,網民關注的僅僅是她曬出的大尺度照片,而這些碎片化的信息也就簡化了作為社會人的個體的其他角度。如果媒體可以及時補充相關背景資料,也許就可以還原為一個普通的人從而進行正確的價值引導。
3.2社會動員樹立正確價值導向
社會的價值取向正在從一元向多元過渡,不同的言論與思想在新媒體建構的虛擬空間相互碰撞。“網絡紅人”現象背后的價值觀更多表現為一種急功近利、嘩眾取寵、個人主義至上的特點,雖然不能完全否認其積極意義,但是在浮躁的社會環境下,負面的影響更容易被放大與擴散。2015年新增加的網民群體中,低齡(19歲以下)、學生群體的占比分別為46.1%、46.4%,這部分人群對互聯網的使用目的主要是娛樂、溝通6。互聯網的使用人群正向低齡化發展。一方面,這類人群的世界觀還沒有完全形成,在快餐式的文化影響下容易產生對世界認識的偏差;另一方面,積極的傳統價值觀也需要與社會發展相匹配,避免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悖論。社會、家庭、學校三方應該相互配合,建立從傳播渠道與內容的引導式把關。
3.3建立相應完善傳播規制
“網絡紅人”現象雖然是浮躁空虛的“狂歡”,但是現象的背后也反映了當下傳播資源的分配不均,社會表達權被少數人所占有。信息的獲知權已經基本得到受眾的認可,而意見的表達與媒介的可接近仍然不盡如人意。“網絡紅人”中有人扮丑,有人炫美,他們真實的喜怒哀樂則無人問津。媒體可以搭建正式的表達平臺,為愿意表達個人提供表達的渠道,那么他們也許有其他的選擇,《我是演說家》《出彩中國人》就是其中的代表;同時,廣電管理部門也可以出臺相應政策,保證表達權與接近權的實現。
[1]余霞.網絡紅人:后現代主義文化視野下的“草根偶像”[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49(4).
[2]王魯美.防范"網絡紅人"現象的負面影響[J].今傳媒,2009(8).
[3]范文德.從“信息把關人”到“信息引導人”——媒介融合時代傳統媒體新聞傳播角色的轉換[J].編輯學刊,2013(3).
[4]韓璐.網絡新聞傳播中的“把關人”缺失現象探析[J].今傳媒:學術版,2014(10).
注釋:
1 郭慶光:《傳播學教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2 根據《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統計報告》,2016年1月。
3 彭云峰:《網絡紅人現象的本質與興起原因探析——以“芙蓉姐姐”和“犀利哥”為中心》,載《東莞理工學院學報》2013年第20卷第2期。
4 參見羅彬:《新聞傳播人本責任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54頁。
5 張雨蒹:《新時代媒體人的角色轉換——對“把關人”理論的新思考》,載《新聞世界》2013年第11期。
6 根據《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統計報告》,2016年1月。
本文系2015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新疆維吾爾族日常生活中的儀式傳播與文化認同研究》(項目編號:15xxw003)階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