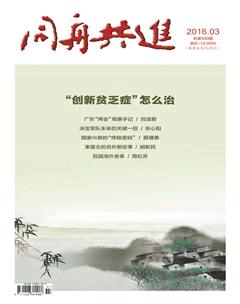國家興衰的“終極密碼”
薛理泰
古今中外,“落后要挨打”是至理名言。讀者從歷史書籍或者紀實電影中可以領悟到,戰敗國的人民豈止是“挨打”而已,簡直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慘不堪言。追源禍始,“落后”是“挨打”的前提。這里講的“落后”,在多半情況下,不是指經濟落后或科技落后,而是指觀念落后或軍力落后。
實力并不能主宰一切
多年來,國內學術界一直強調社會制度的先進性在國際競爭乃至國際斗爭中的重要意義;近年來,似乎又轉為強調以GDP為支撐的綜合國力對國家興衰的重大作用。固然,GDP對于國家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不過,過分強調GDP的作用就違背了歷史事實,也不符合現代國際關系的真諦。著眼于中外歷史重大事件的演變歷程,可以清楚看到,在風云際會的嚴峻考驗中,或在國力發展遇到瓶頸的關鍵時刻,社會制度的先進性或以GDP為支撐的綜合國力,對國家盛衰興亡都難以起到重大的作用。相反,從某個側面看,歷史反而充斥著以弱勝強、以小勝大甚至以野蠻戰勝文明的記載。
應指出,無論是國家興衰還是戰爭勝負,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于戰略思維和決策的正確與否。換言之,決定要素不是表面上的綜合國力,而是領袖的戰略素質和組織能力,以及由領袖制定并為精英群體普遍接受的國家大戰略、國家安全戰略和國家發展戰略。戰略思維和決策水平在整個戰略范疇中占有至高無上的地位,戰略思維是決策藝術的最高境界。當然,若干并非純然是巧合的機會,在一個國家發展的歷史過程中,也起著不容忽視的重要作用,亦即所謂“國運隆否”。
當年,成吉思汗及其子侄輩麾下的蒙古鐵騎橫掃歐亞大陸,所向披靡。行軍途中,大小不等的諸多國家軍隊都被消滅了,眾多民族民眾被蒙古貴族奴役。然而,無論是文明程度還是經濟實力,當時蒙古族遠遜于被其征服的各民族,蒙古族之所以稱雄一時,無非是首領成吉思汗及其左右在政治、軍事上見識過人而已。
從文明進化的觀點衡量,當時的蒙古還是奴隸制社會,而被它擊敗的不少國家都早已是封建制社會,且這些國家的經濟實力也遠遠超過蒙古國。然而,這都無從改變這些封建制大國被奴隸制的蒙古國滅亡的命運,發人深省。
蒙古族向來能射善騎,就小群體而言,在軍事上以強勁的爆發力著稱。這種基本國情、民情,自古已然,并非始自成吉思汗。但在成吉思汗成長之前,蒙古族一貫是個弱小民族,被占領黃河流域的金國百般欺凌,毫無還手之力。在成吉思汗領導下,蒙古才崛起于世界。及其身后,蒙古國勢不久即一落千丈,在漫長的冷兵器時代,雖依然能射善騎,卻一蹶不振,再也沒有強盛起來。由此可見,蒙古族軍事潛力被挖掘、軍事實力快速膨脹,其實是成吉思汗的遠見卓識被蒙古貴族乃至民眾普遍接受以后的必然結果罷了。成吉思汗的真知灼見被付諸創新的實踐活動中,這是蒙古軍隊戰斗力倍增和蒙古政權高效運轉的前提。
中國歷史上,若干異族文明程度遠不及漢族,人口和經濟實力亦遠遜于漢族,卻數次入主中原。如統治中國長達近百年的元朝或數百年的清朝,就是典型的例子。誠然,時隔數百年以后,歷史學家可以歸之于“兄弟民族之間的內部矛盾”。然而,當年的漢族卻視之為亡國之痛。
再以中國近代史上盡人皆知的第一次鴉片戰爭為例。當年中國之所以被英國戰敗,也不能歸因于中國經濟實力不如英國,實際情況恰恰相反。據資料,當時中國綜合經濟實力遠超于英國。在1820年的世界GDP總量中,中國占28.7%的份額,比排名第二至四位的國家的總和26.6%還要多。根據美國人弗蘭克在《白銀資本》一書中的不完全統計,從明朝至清朝前葉,由于中國對外貿易數量驚人,有七千噸至一萬噸白銀由歐亞諸國流入中國,約占當時世界白銀總數的1/3。再加上中國在本土流通的固有的白銀存量,至清代乾隆、嘉慶年間,中國已擁有世界近一半的白銀。由此可見,談到當年中國GDP數額之大、擁有貴金屬之多,英國完全不能望其項背。
再看武器,當年英國遠征軍擁有的無非是載有黑火藥充當內裝火藥的前裝滑膛炮的三桅木帆船而已。中國在沿海布防的軍隊也裝備了這種火炮,屬于同一技術時代的產品。但工業革命后,英國在火炮材質工藝、彈藥質量、機動性、射速、射程、精度等關鍵技術上作了改良,拉開了與中國火炮技術的差距。
1840年6月,英國首批7000人的遠征軍抵達中國,其后又增兵。論裝備火力、機動性以及戰法、調控能力,清軍遠遜于英軍。1842年7月,萬余英軍分兵占領了上海、鎮江,控制了南北漕運,攸關清朝經濟和政治命脈。一個月后,《中英南京條約》簽字。
第一次鴉片戰爭,英國戰勝了中國,原因恐不全是英國人“船堅炮利”而已。康熙之后,中西軍事差距急劇擴大,主要原因是君臣及民間均缺乏危機意識,舉國偃武修文,馬放南山。至于滿朝文武官吏,更是文恬武嬉。士大夫自詡居于康乾盛世之后,猶有余蔭可庇,孰料在戰爭中,一擊即破。況且,中國億萬農民產出的絕大部分物資,都作為城鄉居民生活必需品消耗掉了,豈有余裕用于戰爭?對于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更是毫無裨益。
即如明末引進西洋大炮、開花炮彈,明清雙方在戰爭中頻頻使用,及至康熙朝敉平內亂以后,不但不購置新型號,而且把現有的都擱置不用了。左宗棠西征新疆時,在陜西鳳翔發現了明末開花炮彈存貨,不禁感慨萬千:“利器之入中國三百余年矣,使當時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島族縱橫海上,數十年挾此傲我?”
反觀當年的英國,正邁向“日不落帝國”,國力處于上升過程中,百業振興,精英群體帶著世界視野看待國際事務。相比之下,清朝早過了康乾盛世,舉國發展處在停滯的老邁階段,君臣對于客觀科學的認識尚有隔膜和代溝,遑論以世界視野看待國際事務。
說到底,當年英國的工業生產能力,尤其是人們認識客觀世界的觀念及其社會生活形態,已比中國人超前數個時代。戰爭的結局,不待智者而決。由此觀之,如何剖析“落后要挨打”,尚待商榷。這個說法應該改變為“觀念落后或者軍力落后者就要挨打”。這似乎是一條鐵則,在哪個時代都適用。
國之興衰尤在戰略謀劃
置身于大時代,稟性大開大合的戰略家面對變化莫測的世局,不能僅著眼于常數,還要顧及變數,尤其是關鍵性的變數,以及大時代對這些變數的要求和這些變數對于大時代產生的推動作用。
若論軍事打擊力量之犀利無雙,民主體制之合乎民心,決策機制之科學合理,財經、科技、教育、工農業之雄厚發達,當代應該數美國為最,環球無出其右。上世紀末,美國國力傲視世界,在外交、經濟、金融、科技、軍事諸層面擁有雄厚的資源。設若美國整合各項資源,一體發功,則舉世莫與匹敵。然而,不足十年,美國在外苦于遲遲未結的伊拉克、阿富汗兩場反恐戰爭;國內金融海嘯爆發后,多年來經濟欲振乏力。說美國陷于內外交困,恐怕不是過甚其辭。這期間,在美國,舉凡政治體制、決策機制以及財經、科技、教育、工農業各項支撐基礎,客觀要素并無變化,卻形成了勢移境遷的變動。
究竟是什么因素造成偌大的變動?無他,無非是小布什總統執政時期,美國在大戰略層面上出了差錯,當年華府在發動伊拉克戰爭時在戰略評估上犯下嚴重缺失。無怪乎不久前國務卿克里對此發表評論稱: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是一個嚴重的錯誤”。近年奧巴馬強調“巧實力”,借力使力,隔山打牛,幾個回合下來,終于在亞洲事務中,又逐步由被動轉為主動。
這說明,戰略謀劃是否得當,對于一個國家興衰的重要性,其程度不亞于這個國家的體制、機制及各項支撐基礎。為國家謀劃方略,恰如醫生為病人研究治療方案。醫治沉疴已久的病人,有多條途徑。醫治久病者,保守療法是食療,改善營養,增強病人體質,三個月后可見療效;稍快一些的是藥療,對癥下藥,一個月內可見療效;更快一些的是肌肉注射強身補針,一個療程下來,兩周后可見療效;最快的則是靜脈點滴,一兩天內可見療效。治國猶如醫病。治國方略的基點是高收效、低成本,對策性的建言必須兼顧緊迫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缺一不可。
由此可見,領導人之睿智以及由決策層制定并為精英群體普遍接受的、正確的國家大戰略,確實是決定國家興盛的最基本最具有活力的要素。尤其在瞬息萬變的信息時代,在評估國際格局走勢及周邊情勢走向時,這條規律甚至更為適用。
對于決策層而言,政治體制改革固然重要,可是對戰略謀劃也不能掉以輕心。尤其是在執政當局面對內外困境,治絲益棼,更有牽一發而動全身之隱患時,特別是因應內外嚴峻挑戰之際,更加應該著重于戰略謀劃。戰略謀劃得當,則收事半功倍之效,否則,必有事倍功半之憂。如此而已,豈有他哉。
斯坦福大學異軍突起的啟示
古諺曰:“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這是依據“常法”得出的結論,倘若按照“變法”對待大學教育,結果大相徑庭。斯坦福大學異軍突起,就是以“速成法”提高大學質量的一例。關鍵仍在于最高領導人的創新思維及高效的執行力。
截至上世紀50年代初,斯坦福大學仍是二流甚至三流大學,被人戲稱為“鄉村大學”,遠不能與美國東部那些常春藤大學同日而語。而使斯坦福大學在短期內脫穎而出,躋身美國大學前列的功臣就是特曼教授。
1951年,特曼作為斯坦福大學工程學院院長,以低廉地租將一千英畝校園長期租給工商業界或畢業校友設立公司,再由他們與大學合作,提供各種研究項目和學生實習機會。世界上第一個大學與公司結合的工業園區就此誕生。
隨后,斯坦福工業園區發展成為硅谷,校友們在硅谷創造了數百家知名公司,創造出高科技奇跡;同時還培養了大批時代精英,擁有40多名諾貝爾獎獲得者和上千名美國科學院和工程院院士,成為世界高技術工業園區的楷模。2000年,硅谷一地GDP達到5000多億美元,相當于當年中國GDP總值的半數。可以說,沒有斯坦福,就沒有硅谷。
在斯坦福,是教務長而不是校長執掌校務大權。1955年,斯坦福大學遴選教務長,特曼以高票勝出。特曼的使命是把斯坦福的未來目標鎖定為“美國頂級,世界一流”。要把一所“鄉村大學”辦成一流名校,不啻一項曠日持久的系統工程。
然而,特曼及其同事推動創新思維,打破常規,在短期內達到了這一目的。他們認為,要用“速成法”建成一流名校,必須對癥下藥。一所綜合性名牌大學需要由知名教授群支撐,則全球一流的生源遲早會薈萃于此。校董會為了吸引知名教授,執行雙管齊下的辦法:其一是重金聘請名流大家,輔之以寬松自由的學術環境、一流的設備和實驗室,以及配套的優待人才政策;其二是利用校區空地,蓋建了許多美輪美奐的別墅,供教授闔家擇一居住。
特曼及其同事調查每個專業領域內的知名教授,組織若干個小組,按圖索驥,專程前往,游說教授們來執教。他們提供給教授的工資也因人而異,不過均比原來的工資高出一大截,更答應在其它方面(諸如代聘秘書、配偶就業等)提供優惠條件。即使高工資對有的教授并不具有足夠的吸引力,游說小組還有第二招:提供往返機票及全程招待費用,請教授夫婦一齊到斯坦福大學游覽觀光,不過有一個條件,即教授必須攜帶妻子一起過來才行。教授夫婦來到斯坦福大學以后,對別墅群的印象特別深刻。這批別墅雖不能同億萬富翁的豪宅相提并論,但其規格之高,卻是當年那些教授夫婦可望而不可及的。于是,往往出現了這樣有趣的情況:教授還在猶豫不決,妻子卻決心搬來過舒服日子,這就促使教授作出最終決定。
斯坦福大學為國際知名教授提供的條件確實具有極大的誘惑力:住在美輪美奐的別墅里,享受全美最宜人的冬暖夏涼的氣候,即刻可以領取按照常規需要幾十年以后才能獲得的高工資,何樂不為呢?于是乎,不數年,斯坦福已群集了多位全球頂級的教授、學者,立志向名師叩教的聰穎學子也紛紛聞風而至,從全球各個角落涌向斯坦福。如此,舉凡師資、生源,斯坦福均傲視全美以至全球矣。
古往今來,多少大學都期盼成為世界一流名校,最終夢想成真者卻寥若晨星。斯坦福大學是一個異數。上世紀60年代末,斯坦福躍居美國學術機構前列。及至1980年代,斯坦福已超過了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位居全美大學之首。
領導人的創新思維和戰略謀劃除了對大學影響甚多之外,對跨國大公司也同樣如此。史蒂夫·喬布斯與蘋果公司的故事即是一例,在此不贅述。由此可見,領袖素質好壞及戰略正確與否,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軍隊、學校、公司乃至國家的興衰命運。
美對華戰略謀劃能力的評估
回頭闡述一下美國專家對中國戰略謀劃能力的評估。總體說來,美國戰略家認為中國戰略謀劃能力屬于上乘,否則,中國也不可能在短短30多年中取得持續高速的、舉世罕有的發展成果。
美國戰略家對于中國戰略謀劃能力的正面評估,大體上分為兩層:其一,就政經一體化而言,多年以來,中國決策層巧妙地利用了國內外客觀上存在的正面因素,對于負面因素則采取擱置的辦法,在維持現行體制前提下,取得了持續高速發展的成果。這充分說明中國制定并推行國家發展戰略是成功的。其二,在確保國家安全的層面,盡管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比較險峻,但不論如何,新中國成立后,成功地一再阻遏了大戰降臨的險情。這說明中國制定并推行的國家安全戰略是成功的。
涉及中國的包括軍事戰略及軍力運用的背景,以1962年中印邊境戰爭以及1979年中越邊境戰爭為例,中國軍隊得手后即告撤退,從而既達到了教訓敵手、穩定邊界安全的戰略目的,又避免陷入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綜合國力的持續增長不為之長期牽制。美國戰略家在檢討過去十多年來美國陷于伊拉克、阿富汗戰爭的利害得失時,對于中國高層的上述決策,尤其給予正面評價。
若干學有專長的美國學者指出,中國決策機制的長處是在重大事件突然爆發后,政府可以利用高度集中的有利條件,調動全國各種資源,從而快捷、有力地應付危機。另一方面,美國戰略家認為中國決策機制的短處則是不足以預測、預報危機可能在何時、以什么形式爆發,預防危機爆發的能力成了決策機制中的一塊短板。
考究其中原因,美國戰略家的結論主要有兩條:其一,中國沉浸于和平的環境久矣。憂患意識或危機感不足,無從充分體會“敵存滅禍,敵去召過”的至理名言,對慣性的力量有所忽視;其二,某些決策者清一色由學自然科學的專家或工程師組成。他們擅長于微觀分析及定量分析,若從事經濟建設均是槃槃大才,但在宏觀分析及定性分析方面卻略有不足,因而對大戰略的確立及政略應變性的適時調整欠缺足夠的悟性。
美國總統奧巴馬上任伊始,為適應金融危機后美國國力的相應變化,揭橥“巧實力”的口號,即今后華府在處理國際事務中,不能一味逞強,要改弦更張,需要結合“硬實力”和“軟實力”,巧妙地予以運用。概言之,亦即美國在應付危機手段上,應該“與時俱進”,多從謀略上著手。美國在體現國家意志上,要著眼于運用“軟實力”,并予以最大化,為此,當務之急自然是立足于謀略了。
2010年,始則中日卷入釣魚島紛爭,繼則中國與東盟陷入南海主權的紛擾,終則美韓在朝鮮西海舉行軍演,這一年中國周邊波濤迭起,殺氣陡升,令人困擾。這就是美國為了重返亞洲而運用“巧實力”所致。美國在謀略運用上,看來也在與時俱進。《孫子兵法·謀攻篇》:“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對此,美國似乎開始懂得個中三昧。
中美兩國軍事戰略的區別之一在于:中國軍隊著眼于首先打擊敵軍的薄弱部分,而美軍卻總是選擇敵軍要害的關鍵節點進行襲擊,以圖一劍封喉,產生震撼性的效果。美國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曾強調,美軍須避免陷入大規模的地面戰爭,而應在多數情況下,依靠海、空優勢,組建小型、靈活的地面部隊,打擊敵方的關鍵要害,成為風向標。說明美軍越來越重視遠途突襲的戰略思維。今后美國對付全球恐怖組織,在非對稱軍事行動中,看來也將“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具體說來,亦即打破常規思維,以突襲為手段,直取敵方要害。
至于謀略運用,中國亦非弱者。在古代,中國已有六韜三略,涵蓋軍事、政治以及內政權謀。一部《孫子兵法》,大戰略層次思考之精深,具體運用之出神入化,幾乎生生不絕,化化無窮,至今在中外戰略界膾炙人口。何況,中國近現代史上,更不乏洋為中用、土洋結合的手段,在戰略謀劃上制敵機先的典型事例更是層出不窮。問題在于,時至今日,中國戰略學界究竟有否悟出道理。
美國對中國未來國家地位的戰略定位是,認為中國綜合國力正在迅速增強,對美國全球龍頭老大的地位構成了威脅。這一認識可能已介入其對中國方略的決策過程中了。一言以蔽之,今后美國要以準超級大國對待中國。
若如此,則中國未來尤需警惕不要陷入被動。假如美國尚未把中國視為準超級大國,則沒有整合國際力量對付中國的必要性,中國也不會被過分關注;倘若美國已把中國視為超級大國,兩個超級大國需在地球村和平相處,則美國在對華決策上自然有所忌憚。過去美蘇相處了近半個世紀,彼此打交道時確有一定之規,互相把核心利益視為禁臠,對方不會越雷池一步。一言以蔽之,今后兩國互動關系或許會趨于更加復雜和尖銳。
以往美國對華戰略的制定僅受制于因中美兩國戰略目標差異所形成的利益沖突性矛盾;進入新世紀以后,中美關系迭經風波,一路趔趄,至今仍維持在“斗而不破”的狀態。當前中美關系仍剪不斷、理還亂。雙邊關系的結構性矛盾必然會不時帶來麻煩,雖相當難以調和,卻仍屬可控性質。至于雙方能否突破國際關系史上的陰影,發展一種新型的雙邊關系,則需確立戰略互信,才能真正做到尊重對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由此凸顯了謀略運用的重要性。
此外,世界早已處于核時代,核武器對人類的大規模殺傷能力,至今仍作為有效手段,制約兩國在軍事層面上“見真章”的可能性。在巧妙地運用謀略的情況下,雙方確實存在著處于形格勢禁地步的可能,以致彼此毋須或不能跨入“角力”階段。
李光耀在世時,一次他針對美國在中國影響力不斷擴大的背景下,究竟應該如何看待中國這一問題,直截了當地指出,“你不能阻擋中國的崛起,只有他們自己能這么做。除非你想要向他們宣戰或者是在經濟方面抑制他們的發展。然而,這么做將適得其反。假設中國自身沒有出問題,你們只得接受它會變得更加強大的事實。”今后的美好愿景是,雙方盡可“斗智”,折沖樽俎,卻無須進入“角力”階段;至于“斗氣”,則屬于未入流的手段,大可不必使用。
智庫應重視戰略規劃
當前眾多人士縱論天下事,凡事均歸咎于體制,這并非一種成熟的思維方式,而是有時做了“思想上的懶漢”。開國上將張愛萍在與他兒子張勝兩代軍人的對話中,直言指出:“說什么問題全出在體制?是人!是用人上出了問題!不要一出了問題就全往體制上推,把自己開脫得干干凈凈!”這就畫龍點睛地指出了體制弊端與其是否善于從建言獻策中汲取精華之間的辯證關系。
英國哲學家培根有一句名言——“Dotherightthing”,這遠比“dothingright”重要。就戰略規劃而言,“做對的事”要比“把事情做對”重要得多。對于高層而言,要著眼于規劃如何做對的事,而在基層,則是思量如何去把事情做對。
頂層設計,亦即戰略規劃。戰略規劃正確的話,縱使政治體制不動大手術,也可以沿著正確的方向,大踏步地前進。如果戰略規劃乖誤,則適得其反矣,越是堅決貫徹,惡果越是嚴重。假若此時再在體制上動大手術,勢必土崩魚爛矣。概言之,如果戰略規劃正確得力,即使貫徹執行不力,區別僅在于成績大小。反之,則失之毫厘,謬以千里,流毒所至,無遠弗屆。可見戰略規劃乖誤的后果很嚴重,一定要慎之又慎。
目前中國各行各業都正在興辦智庫。各智庫應格外重視做好戰略規劃,尤其是要在各自研究領域中,在預防、預測、預報上有所建樹。實際上,預防或至少預測危機,對于一個國家應付危機的綜合能力來說,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假如一國政府能做到預測危機,就提供了一種可能性,即能以事半功倍的方式處理危機。如果能夠以綜合治理的方式,采取因應措施,就能達成所謂“防患于未然,消禍于未形”的境界了。反之,假若預測危機的能力不足,則處理危機的成本巨大,勞民傷財,甚至還會留下后遺癥,創巨痛深。所以,預測危機能力的強弱直接關系到政府決策機制的合理高效與否。
一國的決策機制在軍事學上的反映尤為突出。應該指出,無論如何,軍事觀念不能落后,落后的話,挨打是遲早的事。假如決策者缺乏危機意識,戰略家不居安思危,不悉心研究如何打贏一場明天的戰爭,則中國在近代史上被列強欺侮的戰爭,還可能會以不同的方式重演。在信息時代,戰略、戰法快速升級換代,銳利武備日新月異,戰場上的各種作戰要素迅即切換變化,令人目不暇接。這樣的戰爭形態是,快節奏、高強度、全方位以及日益突出的制空權、制交通權的重要性。對信息化戰爭特點的體認,是對軍隊軍官的基本要求。
當前世界各國紛紛實行軍事變革,要旨是確立先進的軍事觀念。而要確立并且貫徹先進的軍事觀念,必須人才先行。過去中央軍委強調指出,“寧可人等裝備,不能裝備等人”。這意味著培養合格的軍事指揮或技術人才應走在研制先進武器裝備的前面。
真正的軍事人才究竟在哪里?應該指出,人才就在各級軍事主官目光所及之處。目前中國軍隊需要的合格人才,并非那些學富五車、才高八斗的飽學之士,而是指確實通曉某一項專業知識且在處理實際事務中又能學以致用的青年才俊。實際上,這樣的人才遍布軍隊上下,目前中國軍隊也已至少在條文上確立了一種機制,能夠在軍營里激勵、拔擢并且容納嶄露頭角的各種人才。今后,這種機制還需催逼各級主官在識人、用人和容人上行動起來。不然,別說從地方吸引人才充實軍旅,就連已經置身軍旅的人才恐怕也留不住。
當前,我國正在雷厲風行地部署并推進軍事改革,這就在客觀上提供了一條捷徑,有助于中國軍隊大力拔擢人才并優化軍隊知識結構。不數年,中國軍隊戰斗力必定噴薄而出。這是可以拭目以待的。
(作者系美國斯坦福大學國際安全與合作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