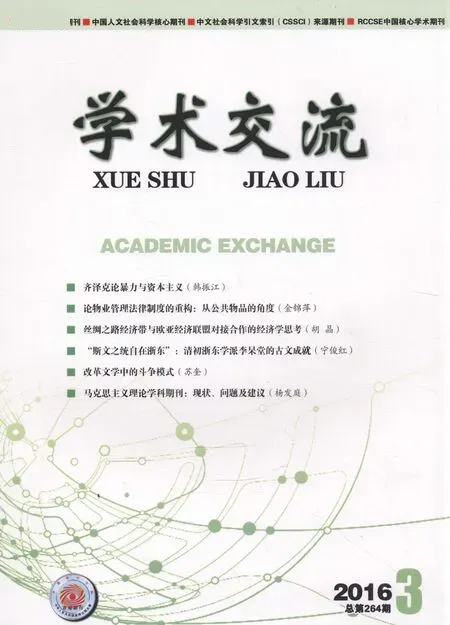文學地理與城市文化異質性——以哈爾濱文學書寫為例
葉 紅
(黑龍江大學 文學院,哈爾濱 150080)
?
文學地理與城市文化異質性
——以哈爾濱文學書寫為例
葉紅
(黑龍江大學 文學院,哈爾濱 150080)
[摘要]哈爾濱作為二十世紀初遠東地區最大的移民城市,帶有一定的殖民性,城市文化異質性特點鮮明。文學地理與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等諸多因素相互關聯,為作品提供了多層次的意義闡釋空間。同時,文學地域性還帶有主觀性和虛構性,作家的文化立場對構建文學地域性有著決定作用。另外,對同一城市相同的地理景觀,因時代不同、作者不同,對城市文化異質性的闡釋也不同。
[關鍵詞]文學地理;城市文化異質性;哈爾濱文學書寫
構成文學作品的兩條基本軸線是時間軸線與空間軸線。文學地理學研究的不是文學中的地理學問題,而是指在同一時間軸上,不同地域空間發生的帶有地域性的文學現象或在同一地域空間內不同時間發生的包含地理諸因素的文學現象。不同學科的研究者在文學地理學中關注的問題也不同。地理學家關注的是文學作品中呈現出的人文地理、政治地理等地理學現象,他們試圖在文學作品中找出有關地理學方面的實證,尤其是地域性強的文學作品能夠為地理學家提供豐富的地理學研究資料;文學研究者并不特別在意文學作品中有關地理的科學性、客觀性和真實性,而是更關注寫作者在作品中如何運用自然地理景觀和人文地理景觀為作品服務,怎樣為文本提供想象的空間依據,寫作者又是如何利用地理景觀闡釋其文化立場,彰顯其審美風格。
在城市題材的文學作品中,寫作者對于城市的自然地理面貌和人文地理景觀的書寫,會根據文體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寫作視角和素材投入。對于游記類的散文,自然地理面貌和人文地理景觀就成為最主要的內容;對小說而言,無論是自然地理面貌還是人文地理景觀皆屬故事的空間環境;對于詩歌而言,自然地理面貌和人文地理景觀既可以是空間背景又可以是抒情對象。但無論何種題材、何種體裁的文學作品,文學地理都不單是地理問題,也不是單純的空間或環境問題,寫作者把地理與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等諸多因素融合在作品中,形成了更為復雜的、多元的意義闡釋空間。
哈爾濱是一座在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方面都很獨特的城市,城市文化異質性特點非常鮮明,是文學地理研究的一個絕好的對象,為眾多作家所書寫和闡釋。本文以哈爾濱市的文學書寫為研究對象,探討文學地理學與城市文化異質性的關系,即文學-地理-城市-文化。
一、 文學地理與城市文化異質性互為表征
“地理景觀的形成反映并強化了某一社會群體的構成——誰被誰包括在內?誰被誰排除在外?”[1]地理景觀既是當地居民生活的一部分,具有觀賞和使用價值,但在某些特殊時期,有些地理景觀也會帶有深深的政治含義。當一個城市的景觀是由殖民者建造,這樣的地理景觀被寫作者寫進作品中,除了記錄生活,往往也被賦予豐富的象征意義。
哈爾濱這座城市是應建設中東鐵路的需要而興建。中東鐵路是清政府和沙皇俄國在遠東地區共同投資興建的最重要的一條鐵路,沙皇俄國旨在通過修建中東鐵路,最終將東北變成其殖民地。中東鐵路在興建過程中,清政府與沙俄簽訂協議,在哈爾濱境內劃分了鐵路附屬區,屬沙俄勢力范圍,把一部分土地劃歸俄屬領地,大部分俄國移民生活在此。隨著十月革命的勝利,一部分俄國貴族也通過這條鐵路移民至哈爾濱,還有部分因不堪忍受俄國和歐洲反猶勢力的猶太人移民于此,在哈爾濱獲得了與俄國移民平等的身份。另外,哈爾濱移民中還有來自波蘭、格魯吉亞、亞美尼亞等20多個國家的移民。薛連舉在其著作《哈爾濱人口變遷》中給出這樣一組數據:十月革命后,俄國僑民的人數于1920年驟然增長到13萬余人,到1922年又增長到15.5萬人,再加上28個國家和民族的僑民,十幾萬人積聚在7.8平方公里的中東鐵路沙俄附屬區內,哈爾濱這座移民城市最多的時候移民人口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以上。[2]哈爾濱很快就成為遠東地區的新興移民城市,移民潮給哈爾濱這座正在興建的城市帶來了外國多元文化及影響。
嚴格來講,哈爾濱不屬于殖民地,但俄屬鐵路附屬區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類似租借地性質。隨著僑民人數的驟增,僑民內部也會按國別、族群形成獨立或半獨立的生活社區,如猶太社區、格魯吉亞社區、烏克蘭社區、突厥—韃靼社區、亞美尼亞社區、波蘭社區等。修建街道,翻蓋房屋,設立教堂,開設酒吧、咖啡店、西餐廳,越來越多的與社區生活密切相關的建筑群興建起來,甚至建造了各自的幼兒園和學校。從居民區建筑群、街道、教堂、商店等地理景觀的建造,到各種宗教的流入與滲透、語言交流,各國各民族的移民按照本民族的傳統習俗慶祝自己的節日,不同國家的移民在服裝、飲食、生習活慣等方方面面都給哈爾濱這座城市帶來深遠影響。僅就宗教影響而言,移民的多國別使哈爾濱的宗教種類繁多復雜,這是中外一般國家少見的。在20世紀30年代,哈爾濱的教堂、寺廟多達128座,其中有東正教、基督教、天主教、猶太教、伊斯蘭教的教堂,也有佛教、道教、天理教和日本神教的寺廟。這些教堂有的還保存完好,有的已經破敗,有的在“文革”中被推翻。盡管如此,現在的哈爾濱仍然有哥特式、拜占庭式、巴洛克式、摩爾式等風格各異的教堂,這些建筑成為哈爾濱現在最具特色的人文地理景觀。
生活建筑群、商業建筑群、教堂等從城市景觀上給哈爾濱帶來了強烈的城市文化異質性的特點。而其他非直觀性的、間接性的文化影響,也滲透在哈爾濱百姓的生活中。獨特的城市文化異質性,自然也會引起觀察力敏銳的寫作者們的關注和重視,將其反映在文學作品和其他藝術作品中。
1920年夏,后來成為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政治家、思想家的瞿秋白被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聘為特約通訊員到莫斯科采訪,他把一路見聞寫成報告文學《餓鄉紀程》。《餓鄉紀程》被稱為中國最早的現代白話文游記。其中,瞿秋白用很長的篇幅記錄了哈爾濱的社會狀況:“哈爾濱簡直是俄國化得生活了”,“哈爾濱久已是俄國人的商埠,中國的俄國的商業顯然分出兩個區域。道里道外市面大不相同。道外是中國人的,道里是俄國人的。……歐戰后俄國商業一天凋零一天,市面差不多移到道外去了。日本乘此機會努力經營,道里的市面幾乎被他占了一半。……哈爾濱道里及秦家崗兩部分,完全是俄國化的,街道都有俄國名字,中國人只叫第幾道街,第幾道街而已。俄國人住在這里,象自己家里一樣……大街兩旁,俄國人有相擁倚坐在路旁凳子上的,有手攙手一面低低私語指手畫腳……中國大街盡頭,一轉彎就是一日本的哈爾濱日本商品陳列所,我們走過時卻不見門口有電燈,已經關門了,然而我記得陳列所里商品很豐富,除農業品平常不足論外,工業品卻應有盡有,形式上看來‘西洋’貨無毫厘差別。”[3]作為一名愛國進步青年,瞿秋白對在哈爾濱道里中國大街(現稱中央大街)的所見所聞,對中國大街上滿是享受燈紅酒綠生活的俄國人以及日本商鋪的開設,充滿了警惕性和批判性,對身在中國猶在外國的感覺非常憤怒,對哈爾濱將淪為俄國和日本殖民地充滿了焦慮和悲憤,對這個被異質文化充斥的城市沒有半點好感。他無心欣賞外國建筑、異域風情,也無心欣賞西方音樂會,而是擔心哈爾濱早晚要淪為日本人的殖民地。
被魯迅譽為中國最杰出的抒情詩人的馮至,于1927—1928年間在哈爾濱短暫工作過。他在詩集《北游及其他》的序里這樣寫道:“來到即分明是中國領土,卻充滿異鄉情調的哈爾濱,它像是在北歐文學里時常讀到的,龐大的,灰色都市。”他的詩篇《哈爾濱》《公園》《咖啡館》《禮拜堂》都是以哈爾濱的景觀建筑為抒情載體,抒發詩人寓居寒冷的北方這個“不東不西”的城市的惆悵。他在一首題為《哈爾濱》的詩中,這樣描寫中央大街:“聽到那怪獸般的汽車,/在長街短道上肆意地馳跑,/瘦馬拉著破爛的車,/高伸著脖子嗷嗷地呼叫,/猶太的銀行、希臘的酒館、/日本的浪人、白俄的妓院,/都聚在這不東不西的地方,/吐露出十二分的心滿意足。”[4]
1935年,中國學術大家季羨林留德途中在哈爾濱短暫停留,后來他在回憶錄《留德十年》中這樣寫道:“這座城市很有趣。樓房高聳,街道寬敞,到處都能看到俄國人……我們出來逛馬路。馬路很多是用小碎石子壓成的,很寬,很長,電燈不是很亮,到處人影紛亂。”[5]給季羨林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位個子矮小的白俄小男孩,駕駛著高頭大馬的西式馬車,甩起長鞭啪啪響。小個子、大車大馬、帥氣的長鞭,給季羨林留下了關于哈爾濱終身難忘的印象。
中國著名散文大家朱自清在致好友葉圣陶的書信(后收入《歐游雜記》)中寫道:“道里(哈爾濱的一個區,筆者注)純粹不是中國味兒。街上滿眼都是俄國人,走著的,坐著的;女人比那兒似乎都要多些。據說道里俄國人也只十幾萬,中國人有三十幾萬。……這里的外國人不像上海的英美人在中國人之上,可是也并不如有些人所想,在中國人之下。……這里的人大都會說俄國話,即使是賣掃帚的。他們又多有些外國規矩,如應諾時的‘哼哼’,及保持市街的清潔之類的。……他們的外國化是生活的趨勢,而不是奢侈的裝飾,是‘全民’的,不是少數‘高等華人’的。一個生客到此,能領略多少異域風味而不感到窒息似的;與洋大人治下的上海,新貴族消夏地青島,北戴河,宛然是兩個世界。……這里的路都是用石頭筑成,在街上走從好方面看,確實比北京舒服多了。”[6]
瞿秋白的報告文學《餓鄉紀程》、馮至的詩《北游及其他》、季羨林的回憶錄《留德十年》、朱自清的《歐游雜記》,都重點描寫了當時哈爾濱最為著名的中國大街(現稱中央大街),作家從不同角度書寫了帶有濃重殖民色彩的城市地理景觀,但表現的不是對歐化的西式建筑的贊美,也不是對那條極具特色的石頭大街的歌詠,而是不約而同地把寫作視角投射到中國城市被殖民化的屈辱上。西方各式建筑景觀、日本商鋪、洋行,成為俄國人、日本人侵占中國領土,搶占中國市場的證據。報告文學、游記、詩,不同文體、不同作家筆下的中央大街,留給讀者的不僅是對昔日中央大街的風景的再現,更是一段不該被遺忘的被殖民的屈辱歷史。雖然它是當時城市生活的重要部分,作家的描寫也很真實,但作者呈現這一地理景觀時,帶著強烈的、反侵略的、民族主義的政治含義。呈現在文學作品中的地理景觀被賦予象征性,可以被看作是某種政治權力的外形化表現。
比較瞿秋白、馮至、季羨林、朱自清對哈爾濱及中央大街的表征,各有側重,有相同也有不同。相同之處是對哈爾濱中央大街地理景觀的描寫,獨特的石頭路面,大街兩旁林立的西式洋樓,街道上消遣娛樂的俄國人,這些在每一個作家筆下是驚人的一致,可見當年都是非常客觀的寫實,但同時也看到明顯的不同。瞿秋白以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特約記者的身份,站在愛國的批判立場上審視已經淪為俄國殖民地的中央大街,并以一位記者的敏銳,觀察到日本已對中國東北地區覬覦已久,趁沙俄勢力削弱,日本侵略者將勢力滲入到哈爾濱,瞿秋白預計不久日本勢力會取代沙俄對哈爾濱控制,時局的確朝著瞿秋白預計的那樣發展。而馮至的詩更多寄寓了一個小知識分子背井離鄉的苦楚,在中國街道看到的卻滿是俄國人,這種場面使詩人馮至感受到身在中國土地卻仿佛置身國外的強烈的疏離感,馮至從心底不喜歡這座寒冷俄化的城市,稱之為“不東不西”。朱自清給葉圣陶講述了自己在哈爾濱的所見所感,他顯然觀察到哈爾濱道里與道外兩個區的明顯不同,道里尤其中央大街,已是俄國人的世界和天堂,這里成為落魄的俄國貴族的失樂園,朱自清比較了同為殖民地的哈爾濱與上海、青島、北戴河的不同,在他看來,這里的俄國人和中國人是平等的,而中國百姓也不自覺地被俄國人的生活習慣、語言等同化。瞿秋白、馮至、季羨林、朱自清等作家筆下的哈爾濱是一個在俄國、日本控制下的屈辱的哈爾濱,作品中描寫的哈爾濱地理景觀的背后透露出的是作家站在民族立場上的反抗,通過城市景觀表征表達愛國主題和反侵略的政治立場。哈爾濱這座城市相較于中國很多城市而言,它的文化異質性形態十分明顯,城市地理景觀也充滿異域色彩,被譽為東方小巴黎,俄國人稱之為“東方莫斯科”,這種比喻透露著殖民者勝利的驕傲,這些帶有殖民者印跡的地理景觀體現出了復雜的政治背景。
二、 在真實與虛擬之間構建城市文化
地理景觀在建造時更重視的是使用價值,觀賞價值居其次。隨著時間的流逝,最初的建造者和使用者已經逝去,但當年建造的地理景觀依然還在,并以多種形式成為被觀賞或旅游的對象,觀賞價值或大于使用價值。如文學作品、電視、電影、報刊、圖片以及新興的自媒體,每一種媒體在消費這些地理景觀時,會從需要的視角表現和解讀。
地域文化對作家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紹興水鄉之于魯迅,湘西之于沈從文,高郵之于汪曾祺,上海、香港之于張愛玲,東北之于蕭紅,大興安嶺之于遲子建,等等,由地域性顯現的獨特的文化特征成為作家獨特性的標志。但從另一個角度而言,文學作品帶有一定的虛構性,文學作品里面的地域性或曰具體的城市景觀、地理風貌等,也不等同于現實地理景觀,同樣可以具有虛構性,是由寫作者通過想象構建而成。作家的文化立場決定其如何構建文學地理,在真實和虛構之間構建城市文化。那么對于在殖民時代建造的地理景觀,離原來的時代越遠,它的殖民性就越被觀賞者忽略,這些景觀的存在意義似乎就在于它的文化異質性帶給觀賞者的新奇感和陌生感。作家在面對時間久遠的帶有殖民性的地理景觀時,也會有自己的文化立場,表現出強烈的寫作興趣,并注入自己的思考。
哈爾濱結束了作為一座移民城市的歷史。在時間上這段歷史成為了這座城市的過往,但在地理空間上仍然留下當年俄國人修建的鐵路、街道、樓房、教堂、花園,其中參雜少許日式建筑。城市空間的基本面貌沒改變,并隨著歲月的發酵,這些地理景觀所呈現的城市文化的異質性特點,為文人提供了更為多元的闡釋空間。哈爾濱城市文化的異質性、多樣性、開放性、包容性等特點,為文學提供了巨大的意義表現空間,使文學具有了無限的可能性。
當代文人仍然把中央大街、教堂、松花江、呼蘭河等具有哈爾濱城市標志性和意義性的地理景觀作為重要的意象寫入文學作品,但現代文學作家筆下的這些地理景觀的象征意義卻已發生了變化。以一組以中央大街為題材的詩歌為例,比較20世紀20—30年代文人與當代詩人筆下的中央大街在創作視角、審視立場等的差別,研究對于同一地理景觀,在不同時代的文人筆下這一意象的內涵和外延發生的變化。
中央大街是哈爾濱的地標性街道,哈爾濱人把它看成是這座城市的靈魂。面包形狀的方塊花崗石鋪成的石頭街面,街道兩側巴洛克風格、折衷主義風格、新藝術運動風格的建筑,有著濃郁的歐陸文化特色。現代作家把它看成是外國冒險家的樂園和破落俄國貴族、被排擠的猶太人的后花園。20世紀初期,一些作家在描寫它時帶有強烈的厭惡感和批判性,而時隔近一個世紀,當代文人又是如何在自己的作品中構建關于中央大街,關于哈爾濱的地理景觀呢?以王愛中的《哈爾濱中央大街》、張曙光的《中央大街》《一個人和他的城市》、楊河山的一組關于中央大街和哈爾濱街道的詩歌為例進行分析。
第一首是收錄于《龍江詩當代文學大系》詩歌卷中,詩人王愛中寫于1991年的《哈爾濱中央大街》。“在這個經緯點/這條石塊拼成的大街/正向著松花江輻射。”[7]410詩歌開篇完全從地理學思維出發,通過經緯度、街道方位,中央大街的顯著景觀特點“石塊拼成的大街”的描寫,實現詩與地理的融合。詩人在后幾節中,用暗喻修辭手法,通過意象的轉換,揭示了這條大街曾經的繁華便是民族屈辱的見證,看似平靜的街面在歲月的更迭中見證了歷史的傷痛。“這是一條平靜的大街嗎?是的/心靈,不再為暴風雪的襲擊而驚愕/這是一條不安靜的大街嗎?/是的/每一道縱橫的石縫里都騷動著透明的生活。”[7]410詩中的核心意象——“中央大街”這一標志性地理景觀,不僅僅是一條有特色、有歷史、美麗的街道,它還見證了這個城市昔日的繁華與屈辱,詩人強烈地表達了中央大街走出歷史陰霾的決心。
第二首詩是中國當代著名詩人張曙光的詩作《中央大街》及《一個人和他的城市》。張曙光是黑龍江籍詩人,在中國有很大的影響力。詩歌中北方地域性非常突出,哈爾濱的很多建筑景觀和雪,都是他詩歌中常用的意象,但這些意象經過詩人的重新構建,已經成為專屬意象。 “石頭砌成的街道,光滑/而堅硬,被歲月和無數的/腳步擦亮。兩旁的槭樹/在四月變得枯萎”[8]108。中央大街在詩人張曙光的筆下,只是一條他每天上班必須經過的街道,與其他街道并無二致。但最后詩人一改平淡的敘述語調,“它們和我們一樣,體驗/并表達著時間的悲哀和歡樂——/這些樹,還有那些石頭”[8]108。詩人在詩中用了兩個意象構成中央大街的靈魂——“石頭”與“槭樹”。近一個世紀過去了,中央大街的石頭和槭樹還在那里,相對于流逝的時光,仿佛石頭和槭樹在空間上獲得了永恒。詩人敘述了一個場景,“當時間的腳步匆匆?它們確實/變得沉寂,我是說那些樹,/沒有鳥兒在枝葉間/為它們歌唱,也沒有畫家/為它們寫生,它們只畫/那些建筑,和付錢的人們”[8]108。在這里詩人已忽視了中央大街殖民歷史的背景故事,而是用中央大街的石頭和槭樹表達時光的流逝,而昔日繁華的西式建筑,成為現在人們觀光消費的去處,在藝術家眼里,也只不過是有特點的建筑而已。
但在《一個人和他的城市》中,“而這條作為歷史見證的街道,用石塊砌成,冰冷而堅實在歲月的變化中依然,保持自身的完整,任憑腳步,車輪,和沉重的歷史/在上面碾過”[9]。“中央大街”“石頭”這些歷史見證物,與時間抗衡,它記憶歷史、承載歷史,它不只是一條街、一塊石頭。
詩人楊河山是一位極具地域寫作意識的詩人,他在隨筆《詩歌與我們生活的城市》中,堅定地表達了“一個城市需要自己的詩歌”的詩歌地理觀念,“哈爾濱需要詩歌,當然,它也產生詩歌。它的不規則的無方向感的街道,體現了這座城市的自由與隨性,而這種自由與隨性的城市品格對于詩歌尤其重要。”*②楊河山:《詩歌與我們生活的城市》,發表于微信公眾平臺“詩歌哈爾濱” ,2015年2月1日。
鑒于這種城市與詩歌關系的理念,楊河山的詩集《殘血如白雛菊》是一部非常有詩歌地理自覺意識的詩集。詩集共分四輯,第一輯的主題便是哈爾濱的建筑,納入了《喜歡》《哈爾濱》《中央大街》《斜紋街》《霽虹橋》等30首詩歌。作者在寫作時自覺繪制出一部詩人自己的哈爾濱詩歌地圖。同時,詩人以《喜歡》《哈爾濱》作為這一輯開篇兩首,表達了詩人的心聲“喜歡哈爾濱”,其他28首詩歌分別以哈爾濱最具地方特色的街道,最具文化異質性的教堂、建筑,美麗的松花江為題,為哈爾濱城市詩歌地理繪制出一張全面、立體、充滿文化異質色彩的移民城市詩歌地圖。“它的建筑(很多人即使長期生活在這里,也不知道是誰修建的),也容易引發詩人的想象,因為它們翠綠的穹頂,紅色或者米黃色的墻,以及上面復雜的紋飾,實在很美,并且有許多故事,雖然有的已變得破敗。”②
《果戈里大街》中描述的這條街道是哈爾濱著名的景觀大街,它的原名叫新商務街、果戈里街,后改為義州街,1958年為紀念毛澤東主席視察哈爾濱時的題詞“奮斗”而改為“奮斗路”。2003年改為果戈里大街,重新修建成俄式風格的景觀大道,是外地游客的必來之處。詩人在詩中抒發了對這條街道的熱愛,因為它伴隨詩人的成長。詩人并沒有關注這條街道的過往。街名的變換更迭其實政治意味很濃厚,最終變回果戈里大街,還是因為打造哈爾濱特色城市的需要,這么具有殖民意味的名字被重新啟用,目的是要強調這座城市的文化異質性特點。
土耳其教堂、圣·伊維爾教堂、復建中的尼克拉教堂、猶太人老會堂,這些帶有殖民標記的建筑現在被一一翻新,成為重要的旅游景觀資源。它們被寫進詩人的筆下似乎在表面上還原了當年哈爾濱的景觀地理原貌,但實際上詩人對這一點表示了充分的懷疑:“我有些恐懼,因為我不能確定/那早已消失的一切是否還會原封不動地復原,/依然原先的樣子,或者僅僅是個贗品。/我不能確定,所有的一切真的能/回到從前?那段經歷,以及令人恐怖的歷史。”[10]17詩人在詩歌中并沒有對當年的外來入侵者表現出恨意,而是把他們看作是背井離鄉值得同情的普通人隔著時空的隧道遙望想象。“一百年前的燈,被人點亮,并且發出/紅色的光芒。那些古老的物件/沉迷與回憶中,被時間之水擦拭得干干凈凈”[10]28,“想起陰郁的上個世紀,而此刻,/遠方正傳出相互射擊的槍炮聲。當音樂響起……/通江街這古老的會堂被照亮/人們忘記了黑暗,雖然夜色籠罩在他們四周/只有這個美妙的歌聲,在城市上空回旋,確實讓人感到如同虛幻。”[10]2詩人坐在有百年歷史的猶太老會堂聽音樂會,一時間產生幻覺,如同穿越時間隧道回到當年的猶太人會堂,仿佛聽見槍炮陣陣,感嘆物是人非。在這里,教堂也好、猶太墓地也罷,這些景觀只能說明城市的歷史,如今人們已賦予新的意義。文學家們在自己的作品中重新構建了一個非常個人化、主觀化的地理景觀世界,但不再關注這些景觀所帶有的政治意義,而是賦予它們更多的人文關懷和歷史虛無主義的闡釋。
這部詩集中第二輯以雪為主題,《一百年后的雪》《殘雪如白雛菊》《雪,或某種祭奠》《雪絨》等20幾首直接以雪為標題的詩歌。“雪”這一意象是東北籍文人唯一不能釋懷的,無論生活在哪里,雪的意象都會頻頻出現在自己的作品中。對于哈爾濱市民來說,雪作為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參與到每一個冰城人的生活中,不見雪的冬天會讓冰城人陷入惶恐。詩人把這一自然地理現象作為詩歌創作的主要選材、主題,甚至靈感,用雪表達這座北國冰城的質感、溫度、浪漫、神秘和與眾不同。
詩歌里的地理景觀是客觀存在的,有一些詩歌地理中的景觀和真實的景觀是一樣的,但詩歌又是主觀性極強的,其地理景觀夾雜著詩人強烈的主觀感受及其對所描述的地區的理解。這樣就形成了這樣一種情形,每首詩中的地理景觀盡管相同,但由于詩人不同,對空間的理解不同,地理景觀在不同的詩人筆下呈現出的文學文化意義不同,甚至對同一地理景觀描述截然相反。詩歌創作的主觀性賦予詩歌地理對景觀呈現出復雜性和多樣性。
[參考文獻]
[1][英]邁克·克朗.文化地理學[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41.
[2]薛連舉.哈爾濱人口變遷 [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8.
[3]瞿秋白.瞿秋白文選[M].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10:76-85.
[4]馮至.北游及其他[M]//劉福春.馮至全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157.
[5]季羨林.留德十年[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17.
[6]朱自清.歐游雜記[M].上海:開明書店,1934.
[7]羅振亞.龍江當代文學大系(詩歌卷)[M].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2010.
[8]張曙光.鬧鬼的房子 [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
[9]張曙光.一個人和他的城市 [J].文學界,2010,(3):52-58.
[10]楊河山.殘雪如白雛菊[M].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5.
〔責任編輯:曹金鐘孫琦〕
Literary Geography and City Cultural Heterogeneity——A case study of Harbin literary writing
Ye Hong
(SchoolofArts,HeilongjiangUniversity,Harbin150080,China)
Abstract:The paper undertakes to choose the sample of literary writing for Harbin and discuss the relation of literary geography and city cultural heterogeneity. Harbin as the largest city of immigrants in the Far East reg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possessed intensive color of colonization, featuring its cultural heterogeneity. Various factors provided multi-level extension of explaining meanings, which mutually connected between cultural geography, politics, culture, history and economy. Meanwhile, writers’ cultural position also decided the building of literary geography, with subjectivity and fiction. In addition, as for the same sites of one city, its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in the city differed due to different times and different writers.
Key words:literary geography; city cultural heterogeneity; literary writing in Harbin
[中圖分類號]I206.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0-8284(2016)03-0200-06
[作者簡介]葉紅(1966-),女,黑龍江黑河人,副教授,博士,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文學思潮與流派、新詩研究。
[收稿日期]2016-0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