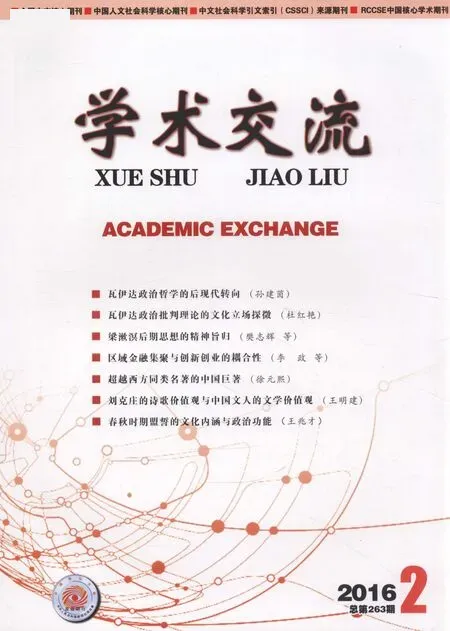評(píng)“食貨學(xué)派”的理論基礎(chǔ)——以陶希圣的“社會(huì)史觀”為探討對(duì)象
白中林
(商務(wù)印書館 學(xué)術(shù)中心,北京 100710)
?
社會(huì)學(xué)研究
評(píng)“食貨學(xué)派”的理論基礎(chǔ)
——以陶希圣的“社會(huì)史觀”為探討對(duì)象
白中林
(商務(wù)印書館 學(xué)術(shù)中心,北京 100710)
[摘要]近年來有豐富的文獻(xiàn)討論“食貨學(xué)派”及其史學(xué)貢獻(xiàn),但對(duì)“食貨學(xué)派”的理論基礎(chǔ)——社會(huì)史觀則語(yǔ)焉不詳。表面上看,高度評(píng)價(jià)“食貨學(xué)派”重視史料與堅(jiān)持社會(huì)史觀是存在矛盾的,但正是在看似矛盾的地方,提供了認(rèn)識(shí)“食貨學(xué)派”的入口。在歷史語(yǔ)境下,考察“食貨學(xué)派”宗師陶希圣發(fā)起社會(huì)史論戰(zhàn)以及創(chuàng)辦《食貨》半月刊的學(xué)術(shù)歷程,澄清其“社會(huì)史觀”的內(nèi)在意涵,重提陶希圣“開創(chuàng)”社會(huì)史研究之于當(dāng)下的意義。
[關(guān)鍵詞]唯物史觀;社會(huì)史觀;食貨學(xué)派;陶希圣
近年隨著民國(guó)學(xué)術(shù)史熱潮,“食貨學(xué)派”*關(guān)于“食貨學(xué)派”的名稱已無爭(zhēng)議,所爭(zhēng)論者只是“食貨學(xué)派”成員范圍,本文傾向折中立場(chǎng),即將以陶希圣主導(dǎo)的與北大中國(guó)經(jīng)濟(jì)史研究室有直接關(guān)系的鞠清遠(yuǎn)、武仙卿等人,稱為“食貨學(xué)派”核心成員;全漢昇、楊聯(lián)陞等受其研究方法影響的稱為“食貨學(xué)派”邊緣成員。相關(guān)論述參見何茲全: 《何茲全文集》,中華書局,2006年,第594-595頁(yè)。這個(gè)輝煌一時(shí)的中國(guó)社會(huì)史學(xué)流派得到了充分重視和挖掘,學(xué)界突破改革開放前的理論教條束縛和意識(shí)形態(tài)的話語(yǔ),從學(xué)術(shù)角度評(píng)價(jià)“食貨學(xué)派”本身的意義。*參見陳峰:《〈食貨〉新探》,《史學(xué)理論研究》,2001年第3期;梁庚堯:《從〈讀書雜志〉到〈食貨〉半月刊》,周梁楷編《結(jié)網(wǎng)二編》,臺(tái)北東大圖書公司,2003年;李洪巖:《陶希圣及其中國(guó)史觀》,張本義主編《白云論壇》第2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向燕南、尹靜:《中國(guó)社會(huì)經(jīng)濟(jì)史研究的拓荒與奠基》,《北京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05年第3期。*參見蘇永明:《“食貨派”的史學(xué)理論與方法》,《史學(xué)史研究》,2010年第1期。盡管有豐富的文獻(xiàn)討論“食貨學(xué)派”及其史學(xué)貢獻(xiàn),但更多是類似于“平反”的研究,如論證“食貨學(xué)派”擺脫歷史公式束縛,重視史料的科學(xué)意義,而對(duì)其理論基礎(chǔ)社會(huì)史觀則語(yǔ)焉不詳。這體現(xiàn)在,要么將社會(huì)史觀視為唯物史觀的一種,要么是轉(zhuǎn)述該派宗師陶希圣原話接近而不是唯物史觀。表面上看,在科學(xué)意義上重視史料與堅(jiān)持社會(huì)史觀是存在矛盾的,但正是在表面上看似矛盾的地方,才提供了重新認(rèn)識(shí)“食貨學(xué)派”的入口。本文訴諸歷史語(yǔ)境,以“食貨學(xué)派”宗師陶希圣發(fā)起社會(huì)史論戰(zhàn)以及創(chuàng)辦《食貨》的學(xué)術(shù)歷程為對(duì)象,澄清“社會(huì)史觀”內(nèi)在意涵,重提陶希圣“開創(chuàng)”社會(huì)史研究之于當(dāng)下的意義。
一、 革命與歷史:作為革命正當(dāng)性理論的唯物史觀
總體而言,對(duì)陶希圣社會(huì)史觀的解讀不外乎兩類:唯物史觀的解讀和非唯物史觀的解讀。這兩類觀點(diǎn)又可以細(xì)分為四種不同的解讀方案:其一關(guān)于唯物史觀的解讀,有社會(huì)史觀即屬于正統(tǒng)唯物史觀和社會(huì)史觀不是“正統(tǒng)”階級(jí)分析式的唯物史觀,而是與馬克思史學(xué)另一重要分支的系統(tǒng)分析的唯物史觀相吻合兩種解讀方向;其二非唯物史觀的解讀,則有社會(huì)史觀乃變相唯心論和帶有唯物論色彩的社會(huì)史觀但非純粹唯物史觀兩種說法。
然而,四種解讀方案都是以唯物史觀為衡量標(biāo)準(zhǔn)的,回顧20世紀(jì)二三十年代之交的中國(guó)社會(huì)思想界,不難理解社會(huì)史論戰(zhàn)與中國(guó)革命的走向聯(lián)系緊密,在這個(gè)論戰(zhàn)背景下,有兩大問題:中國(guó)社會(huì)史分期和中國(guó)社會(huì)性質(zhì)的問題。陶希圣思想的最早研究者德里克,正是從社會(huì)史論戰(zhàn)去理解陶希圣的社會(huì)史觀,并且把社會(huì)史觀放在馬克思主義史學(xué)的整體氛圍中,來論證革命與歷史的關(guān)系。*參見(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與歷史:中國(guó)馬克思主義歷史學(xué)的起源,1919-1937》,翁賀凱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德里克:《陶希圣:變革的社會(huì)限制》,翁賀凱譯,《政治思想史季刊》,2011年第2期。
(一) 作為革命正當(dāng)性理論的唯物史觀
在“革命與歷史”這個(gè)研究主題之下,陶希圣的社會(huì)史觀被視為馬克思主義歷史學(xué)的一個(gè)重要分支的代表,其史學(xué)的意圖同樣指向了對(duì)革命問題的解答,其不同之處,只是在于歷史分期的不同導(dǎo)致的革命方案的不同。但無論這些內(nèi)部的分期如何,作為馬克思主義史學(xué)所表征的唯物史觀毫無疑問成了革命正當(dāng)性的來源。1927年大革命的受挫是社會(huì)史論戰(zhàn)起源的外部因素,陶希圣在發(fā)起社會(huì)史論戰(zhàn)的早期著作中,也特意揭示了這一點(diǎn),即號(hào)召對(duì)國(guó)民革命反思,以便戰(zhàn)勝革命運(yùn)動(dòng)面臨的困難。*參見陶希圣:《中國(guó)社會(huì)之史的分析》,上海新生命書局,1929年;《中國(guó)封建社會(huì)史》,上海南強(qiáng)書局,1929年。各派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xué)家”都想在歷史論戰(zhàn)中找到支持自己觀點(diǎn)的立場(chǎng),以便獲得指導(dǎo)革命行動(dòng)的意識(shí)形態(tài)霸權(quán),使得各派從中國(guó)自身歷史來看待中國(guó)革命的問題時(shí)得出了迥然不同的結(jié)論。
社會(huì)史論戰(zhàn)分為兩次:第一次主要以《新生命》《新思潮》等雜志為陣地;第二次主要以《讀書雜志》為論戰(zhàn)陣地。論戰(zhàn)各方大體可分為三個(gè)派別:新生命派,以陶希圣為代表主張中國(guó)既不是封建社會(huì),也不是資本主義社會(huì),而是一個(gè)階級(jí)結(jié)構(gòu)模糊的社會(huì)(或者以士大夫階級(jí)和農(nóng)民階級(jí)相對(duì)立的社會(huì)構(gòu)造,這里的階級(jí)意指身份),這種特征使得具有封建性質(zhì)的寄生政治勢(shì)力保持權(quán)力,同時(shí)為帝國(guó)主義的利益服務(wù);新思潮派,以郭沫若為代表開始認(rèn)為中國(guó)是個(gè)特殊社會(huì),但是轉(zhuǎn)而贊同斯大林的觀點(diǎn),即認(rèn)為中國(guó)是封建社會(huì),同時(shí)帝國(guó)主義支持著中國(guó)的封建社會(huì)結(jié)構(gòu);動(dòng)力派(或稱托派),認(rèn)為中國(guó)社會(huì)主體是資本主義,帝國(guó)主義支持中國(guó)社會(huì)中資本主義力量的發(fā)展。*參見王宜昌:《中國(guó)社會(huì)史論史》,《讀書雜志》,第2卷2-3期。按德里克的分析,因?yàn)樗袇⑴c這場(chǎng)論戰(zhàn)的各個(gè)派別都把馬克思主義視為有效的分析工具,那么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顯然是他們結(jié)論的合法性保證。
與正統(tǒng)的馬克思主義史觀強(qiáng)調(diào)生產(chǎn)方式和生產(chǎn)關(guān)系對(duì)于歷史發(fā)展的決定作用相比,陶希圣否認(rèn)階級(jí)斗爭(zhēng)在中國(guó)史上的重要性,而強(qiáng)調(diào)外在因素,例如民族、身份群體等對(duì)中國(guó)史發(fā)展的重要意義。他認(rèn)為中國(guó)問題需要通過政治革命,然后落實(shí)民生主義。正統(tǒng)馬派史學(xué)則認(rèn)為是國(guó)內(nèi)外階級(jí)的雙重壓迫導(dǎo)致了社會(huì)的不平等和崩毀,所以要用一場(chǎng)徹底的社會(huì)革命,通向共產(chǎn)主義。不過,無論如何解釋中國(guó)歷史,從革命與歷史在馬克思主義中的關(guān)系看,德里克認(rèn)為仍然可以解釋中國(guó)的馬克思主義者何以將兩者結(jié)合在一起。*參見德里克:《革命與歷史》,第194頁(yè)。這就是唯物史觀作為合法性論證的來源。但是,在何種意義上陶希圣的歷史分析是馬克思主義史學(xué)的一支呢?德里克援引薩明的研究來對(duì)陶希圣的歷史分析予以馬克思主義史學(xué)的定位:馬克思主義內(nèi)部可以容許系統(tǒng)分析和階級(jí)分析,在此陶希圣的歷史分析顯然是屬于系統(tǒng)分析的類型。
只有把陶希圣的分析納入到馬克思主義史學(xué)的分支中,德里克才能在革命與歷史的研究中把馬克思主義史學(xué)作為各派的共同基礎(chǔ),唯物史觀也才能成為合法性論證的保證。*參見德里克:《革命與歷史》,第175頁(yè)。
(二)從系統(tǒng)分析式馬克思主義史學(xué)理解社會(huì)史觀之局限性
就馬克思主義史學(xué)的起源而言,可以說德里克對(duì)列文森的中國(guó)研究進(jìn)行的反駁非常得力,但是如果把陶希圣及其社會(huì)史觀放在這個(gè)總括研究中來理解則可能出現(xiàn)偏差。訴諸德里克的論證材料,就會(huì)發(fā)現(xiàn)他在引述陶希圣的回憶錄佐證自己觀點(diǎn)時(shí),并沒有完整引用。例如德里克對(duì)社會(huì)史觀的說明,只引用其與唯物史觀的契合,但對(duì)陶希圣所講的“接近唯物史觀,卻并不是唯物史觀”棄之一旁。
從陶希圣社會(huì)史觀的思想來源看,1929—1930年他集中閱讀了馬列著作,這與德里克指出的大革命受挫之后,馬克思主義論著的流行相吻合。雖然如此,德里克仍忽視了,陶希圣并不是只閱讀馬克思主義的著作,而是將反馬克思主義著作一起閱讀。由于德里克對(duì)陶希圣馬克思主義史學(xué)家的定位,使得他在論述陶希圣思想演進(jìn)時(shí),把陶希圣思想中與馬克思主義史學(xué)觀點(diǎn)相對(duì)立的東西,列為陶希圣思想的過渡階段,引入馬克思主義史學(xué)之后才得以克服其矛盾之處,仍把馬克思主義史學(xué)列為陶希圣思想的最高演進(jìn)階段。所以,盡管德里克注意到了奧本海默對(duì)陶希圣的影響,以及奧本海默對(duì)馬克思的混淆經(jīng)濟(jì)手段和政治手段的批評(píng),但是通過思想演進(jìn)的排序,他輕易地把奧本海默對(duì)陶希圣的影響打發(fā)掉了,繼續(xù)堅(jiān)持是馬克思主義的商業(yè)資本理論彌補(bǔ)了一個(gè)沒有經(jīng)濟(jì)基礎(chǔ)的統(tǒng)治集團(tuán)理論,并由此影響了陶希圣的馬克思主義觀。*參見德里克:《陶希圣:變革的社會(huì)限制》,第89-90頁(yè)。然而,陶希圣獨(dú)特的馬克思主義觀究竟體現(xiàn)在什么地方?這是德里克疏于解釋的地方。德里克跳過了對(duì)陶希圣馬克思主義史學(xué)立場(chǎng)的質(zhì)疑,只是在最后以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做類型劃分,把陶希圣的歷史分析默認(rèn)為另一種類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xué)。這種論證的力量是很微弱的,跳躍式論證并不能得出陶希圣的歷史分析就是馬克思主義史學(xué)的結(jié)論,由此也不能直接推論陶希圣的社會(huì)史觀就是唯物史觀。
二、另一種誤讀:作為唯物史觀正統(tǒng)的社會(huì)史觀
在時(shí)間序列上,對(duì)陶希圣社會(huì)史觀的定位,首先出現(xiàn)的就是唯物史觀解讀(德里克對(duì)陶希圣社會(huì)史觀的解讀只是學(xué)術(shù)史上的第三種解讀方案,雖然存在某種缺陷,但卻是迄今論證最為豐富和具有理論深度的解讀),這第一個(gè)解讀方案是:社會(huì)史觀即屬于正統(tǒng)唯物史觀。這個(gè)方案的解讀更多是一種評(píng)價(jià)性的說明,即從陶希圣某些時(shí)刻的自我標(biāo)榜或者從陶希圣著作中找到一些類似馬克思主義史學(xué)的分析方式,來說明陶希圣的社會(huì)史觀是歸屬于唯物史觀的立場(chǎng)。例如,親歷社會(huì)史論戰(zhàn)時(shí)期的學(xué)者郭湛波和何茲全先后做出了陶希圣持唯物史觀的論斷。何茲全的具體解釋是,通過訴諸《食貨》半月刊時(shí)代陶希圣的辦刊主張和研究成果予以羅列,尤其是陶希圣關(guān)于唯物史觀的三點(diǎn)聲明:“一食貨學(xué)會(huì)會(huì)員不都是用唯物史觀研究歷史的。二這個(gè)方法又與什么主義不是一件事情。三這個(gè)方法的毛病是在用來容易指破歷史上隱蔽在內(nèi)幕或黑暗里的真實(shí)。因?yàn)樗赋鰟e人不肯又不敢指出的真實(shí),便易受別人的攻擊。”*何茲全:《我所經(jīng)歷的20世紀(jì)中國(guó)社會(huì)史研究》,《史學(xué)理論研究》,2003年第2期,第34頁(yè)。何茲全認(rèn)為這三條聲明恰恰真實(shí)而又有感情的道出陶希圣內(nèi)心深處是執(zhí)著唯物史觀的。
按照這種解讀思路,當(dāng)然還可以從陶希圣著作中找出他的分析與唯物史觀的吻合之處來加強(qiáng)論證。例如,在《中國(guó)社會(huì)和中國(guó)革命》這本書中,隨處出現(xiàn)的對(duì)商品、資本、地租等進(jìn)行的分析,就是直接師承《資本論》。這種分析方式和陶希圣本人的研究說明,在《中國(guó)封建社會(huì)史》和《中國(guó)社會(huì)形式發(fā)達(dá)過程的新估定》等作品中,也頗為常見。
這種僅從外在現(xiàn)象進(jìn)行列舉的解讀,以斷定陶希圣的社會(huì)史觀是否歸屬唯物史觀很容易陷入各執(zhí)一詞的境地。因?yàn)槲覀冞€可以從陶希圣的自我標(biāo)榜和書中找到相反的例證。例如,陶希圣在晚年的《潮流與點(diǎn)滴》《夏蟲語(yǔ)冰錄》中都強(qiáng)調(diào)了與唯物史觀不同的自成一種學(xué)風(fēng)的社會(huì)史觀。*“我雖持唯物觀點(diǎn),仍與唯物史觀不同。我自稱為社會(huì)史觀,而反對(duì)公式主義及教條主義。我主編《食貨半月刊》,講究方法論,同時(shí)注重資料,必須從資料中再產(chǎn)生之方法,才是正確的方法。《食貨半月刊》出版兩年半,自成一種學(xué)風(fēng)。”陶希圣:《夏蟲語(yǔ)冰錄》,臺(tái)北法令月刊社,1980年,第344頁(yè)。對(duì)這個(gè)表面上的矛盾,何茲全的解釋是政治環(huán)境和身份的困境導(dǎo)致了陶希圣前后的搖擺。但是,這個(gè)解釋力是很微弱的,如果說陶希圣去臺(tái)灣后,講話有所顧忌,那么他在創(chuàng)辦《食貨》半月刊時(shí),更多保留的是一種學(xué)術(shù)上的獨(dú)立精神。當(dāng)時(shí),陶希圣對(duì)其史觀的論述反而和晚年回憶相一致:“思想方法接近唯物史觀而不墮入唯物史觀的公式主義圈套。”*轉(zhuǎn)引自陶晉生:《陶希圣論中國(guó)社會(huì)史》,《古今論衡》,1999年第2期,第38頁(yè)。
然而,該解讀方案更為致命的論證缺陷是在陶希圣的歷史分析中發(fā)現(xiàn)的與唯物史觀不兼容的現(xiàn)象。例如,當(dāng)陶希圣的歷史分析不從生產(chǎn)方式著手分析時(shí)、當(dāng)陶希圣強(qiáng)調(diào)士大夫階級(jí)作為觀念生活階級(jí)時(shí)、當(dāng)陶希圣運(yùn)用的階級(jí)概念不是從經(jīng)濟(jì)關(guān)系出發(fā)而指一種身份時(shí),如何處理這些相比經(jīng)典的馬克思主義史學(xué)的唯物史觀而言屬于異端的內(nèi)容?用唯物史觀一言以蔽之,恐怕不是一個(gè)全面的論斷。
三、非此即彼:社會(huì)史觀是唯心史觀嗎
正是由于第一種列舉式的解讀方案存在不同解讀的可能,其解讀的論證基礎(chǔ)并不可靠。所以非唯物史觀類解讀的唯心論方向的解讀方案在第二次社會(huì)史論戰(zhàn)中馬上就出現(xiàn)了,而且其論證的嚴(yán)密性也高于第一種解讀方案。這兩種解讀可以說分別是20世紀(jì)上半葉和下半葉大陸學(xué)界最為流行的界定。在社會(huì)史論戰(zhàn)的氛圍中,由于陶希圣是較早引入唯物史觀的論者,很自然被大家理解為唯物史觀的貫徹者。20世紀(jì)下半葉則風(fēng)云突變,以政治判斷取代學(xué)術(shù)觀點(diǎn),陶被視為馬克思主義的“死敵”。本文試圖排除黨派觀點(diǎn),而從思想自身進(jìn)行考察,所以對(duì)20世紀(jì)下半葉為陶希圣所貼的標(biāo)簽不討論。
在社會(huì)史論戰(zhàn)中,以李季、杜畏之和張橫對(duì)陶希圣的批評(píng)最為直接。李季對(duì)陶希圣的批評(píng)主要圍繞陶希圣的論述內(nèi)容展開,而且是抓表面的矛盾,主要以其對(duì)馬克思經(jīng)典著作熟悉程度來批評(píng)陶希圣對(duì)馬克思學(xué)說的陌生,無對(duì)其歷史觀的辯駁,而后兩者分別針對(duì)陶希圣的歷史研究方法有詳細(xì)辯駁。杜畏之從社會(huì)史觀構(gòu)成的三個(gè)方面出發(fā),去指責(zé)其模糊性和混亂性。*參見杜畏之:《古代中國(guó)研究批判引論》,《讀書雜志》,第2卷2-3期,第6-7頁(yè)。張橫則在分析社會(huì)史觀三個(gè)面向的基礎(chǔ)上,進(jìn)一步合觀之,并結(jié)合陶希圣的具體分析內(nèi)容展開辯駁。張橫在理解陶希圣社會(huì)史三個(gè)面向之后,非常敏銳地總結(jié)出陶希圣社會(huì)史觀指向中國(guó)史時(shí),乃是中國(guó)社會(huì)史一種不斷發(fā)展的過程,這過程不是個(gè)人或觀念的結(jié)果而是生產(chǎn)技術(shù)的產(chǎn)物,它不是偶然的現(xiàn)象而是必要的過程。*參見張橫:《評(píng)陶希圣的歷史方法論》,第3頁(yè)。張橫承認(rèn)從表面上看陶希圣的社會(huì)史觀是屬于唯物史觀的范疇,但是社會(huì)史觀指向的內(nèi)容和結(jié)論卻是完全不同的。
張橫對(duì)陶希圣社會(huì)史觀的批判可以分為一個(gè)總體批判,兩個(gè)主題批判,幾乎涵括了陶希圣社會(huì)史觀的主要指向。一個(gè)總體批判是指陶希圣對(duì)社會(huì)性質(zhì)的分析,偏離了辯證唯物論的基礎(chǔ),即社會(huì)的生產(chǎn)方式和相應(yīng)的生產(chǎn)關(guān)系形態(tài)。而在陶希圣的分析中展現(xiàn)的卻是五花八門的現(xiàn)象和制度。張橫把陶希圣所描述的中國(guó)社會(huì)的復(fù)雜性,視為陶希圣沒有抓到現(xiàn)象的本質(zhì)所致。兩個(gè)主題的批判可以說是總體性批判的展開,張橫以陶希圣社會(huì)史研究中的兩個(gè)支撐性內(nèi)容——商業(yè)資本和士大夫階級(jí)展開了辯駁。商業(yè)資本在陶希圣的中國(guó)社會(huì)史中起著催化劑的作用,尤其是在論述中國(guó)封建制度的崩潰時(shí),陶希圣特別強(qiáng)調(diào)了商業(yè)資本的積極作用。但是,在陶希圣筆下“士大夫階級(jí)”是馴服了商業(yè)資本。士大夫階級(jí)是各階級(jí)的代表,對(duì)各階級(jí)的利益予以兼顧,作為一個(gè)觀念生活階層,在這個(gè)意義上,陶希圣進(jìn)一步把中國(guó)的社會(huì)構(gòu)造分成勞心和勞力的階級(jí),其中勞心階級(jí)是統(tǒng)治者。張橫把陶希圣的這個(gè)論斷斥之為韋貝爾(Marx Weber)*此即德國(guó)社會(huì)學(xué)家韋伯,張橫所引外文名字有一個(gè)字母的錯(cuò)誤即Max,非Marx。式論調(diào)。張橫認(rèn)為唯物論者眼中的階級(jí)社會(huì)結(jié)構(gòu)中存在著不同的階級(jí),階級(jí)又是與社會(huì)生產(chǎn)具有直接關(guān)系,沒有超階級(jí)的分子,社會(huì)的客觀條件使他們始終依附于某一基本階級(jí)。相應(yīng)的陶希圣所指的士大夫階級(jí)不直接從事生產(chǎn)則必然依附與某種基本階級(jí)的利益,所以張橫認(rèn)為陶希圣的士大夫階級(jí)不過是封建地主貴族的代言人。*參見張橫:《評(píng)陶希圣的歷史方法論》,第18-19頁(yè)。對(duì)陶希圣這種史觀上符合唯物論,而分析中偏離唯物論的現(xiàn)象,張橫視之為陶希圣的矛盾性:內(nèi)容與形式的矛盾、敘述與結(jié)構(gòu)的矛盾等。最后陶希圣自然被正統(tǒng)的馬克思主義者視為詭辯主義,唯心論的傀儡。*參見張橫:《評(píng)陶希圣的歷史方法論》,第20頁(yè)。
從正統(tǒng)的馬克思主義史學(xué)眼光來看陶希圣,確實(shí)感到難以理解。雖然陶希圣的歷史分析,某種程度上偏離其史觀的標(biāo)榜,但是在一些方面他對(duì)唯物論的忠誠(chéng)要遠(yuǎn)大于正統(tǒng)的馬克思主義史學(xué)者。例如,陶希圣對(duì)春秋戰(zhàn)國(guó)以降中國(guó)社會(huì)的探索,不停分析其演進(jìn)的形態(tài),而不是視為一個(gè)停滯的階段;并且充分照顧了中國(guó)社會(huì)史的多元性,在社會(huì)總體結(jié)構(gòu)中去討論社會(huì)的演進(jìn),而不僅僅是以階級(jí)斗爭(zhēng)為中心。所以,正統(tǒng)馬克思主義史學(xué)者對(duì)陶希圣的批判并沒有完全成功,因?yàn)樗媾R的不是非此即彼的論證。
四、如何理解“接近唯物史觀卻并不是唯物史觀”:社會(huì)史觀的精神面向
(一)語(yǔ)焉不詳?shù)摹敖咏ㄎ锸酚^卻并不是唯物史觀”
隨著陶希圣主辦的《食貨》在臺(tái)灣復(fù)刊,陶希圣創(chuàng)立的社會(huì)史研究傳統(tǒng)下對(duì)其社會(huì)史觀的定位之說也開始浮現(xiàn),此即社會(huì)史觀“接近唯物史觀,卻并不是唯物史觀”。這第四種解讀方案更多為20世紀(jì)下半葉以來的臺(tái)灣地區(qū)學(xué)界所接受。無論是杜正勝、陶晉生在20世紀(jì)八九十年代寫的文章,還是黃寬重在21世紀(jì)前10年寫的文章,都堅(jiān)持陶希圣的社會(huì)史觀是帶有某些唯物論色彩,但并不等同于唯物史觀。*參見陶晉生:《陶希圣論中國(guó)社會(huì)史》, 《古今論衡》,1999年第2期;杜正勝:《通貫禮與律的社會(huì)史學(xué)》,《歷史月刊》,1988年第7期;黃寬重:《禮律研社會(huì)》,《新史學(xué)》,2007年第18卷第1期。然而,如何解釋“接近唯物史觀,卻并不是唯物史觀”始終懸而未決。而且這種對(duì)社會(huì)史觀的語(yǔ)焉不詳,也難以逃脫第一種列舉式解讀的困境,因?yàn)檫@種解讀做到的只是表面忠誠(chéng),無法解決陶希圣在社會(huì)史論戰(zhàn)中對(duì)唯物史觀認(rèn)肯的沖突。
從上文對(duì)陶希圣社會(huì)史觀的四種解讀思路來看,第一種和第四種解讀方式,其論證邏輯大體是一致的,都是從陶希圣的自我標(biāo)榜或著作中尋找與其論證目的相一致的論據(jù),而對(duì)相互沖突的證據(jù)棄之如敝屣。如此無論其對(duì)陶希圣的社會(huì)史觀如何定位,其論證都是非常乏力的,亦不構(gòu)成后繼努力的積淀。第二種和第三種的解讀方式,則有其豐富的內(nèi)容,無論是肯定陶希圣的社會(huì)史觀是唯物史觀還是否定陶希圣的社會(huì)史觀是唯物史觀,都不是單純的肯定或否定,而是分析為什么如此。不過,可惜的是雖然德里克的努力是在第二種解讀方式之后進(jìn)行的,并且注意到第二種解讀中所指出的陶希圣論述的矛盾之處,但是為了照顧理論的自洽性還是把陶希圣的獨(dú)特性給解釋掉了,硬性把陶希圣的社會(huì)史研究納入馬克思主義史學(xué)的另一個(gè)分析類型;第二種解讀方式,雖然過于立足于正統(tǒng)的馬克思主義史學(xué)立場(chǎng),而把陶希圣展現(xiàn)的中國(guó)社會(huì)史的復(fù)雜性視為矛盾和混亂,但是其對(duì)陶希圣理論的獨(dú)特性的把握卻是十分到位的。那么,我們就要在德里克循名責(zé)實(shí)的努力方向和張橫對(duì)陶希圣社會(huì)史理論獨(dú)特性的理解基礎(chǔ)上,來進(jìn)一步考察何謂“接近唯物史觀,卻并不是唯物史觀”的社會(huì)史觀。
(二)社會(huì)史觀中唯物史觀的影響來源
盡管就陶希圣的社會(huì)史觀來講,僅從表面上的相似論就肯定社會(huì)史觀等同于唯物史觀,可能會(huì)錯(cuò)過陶希圣復(fù)雜的學(xué)術(shù)淵源。但是對(duì)陶希圣社會(huì)史觀的考察仍然要從其自我陳述出發(fā):“我的思想方法,接近唯物史觀,卻并不是唯物史觀。……考茨基的《基督教的基礎(chǔ)》,就是我用心讀過的一本書。然而我的思想方法仍不拘限于此。我用的是社會(huì)的歷史的方法,簡(jiǎn)言之即社會(huì)史觀。如桑巴德的《資本主義史》和奧本海馬的《國(guó)家論》,才真正影響我的思路。”*陶希圣:《潮流與點(diǎn)滴》,中國(guó)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第103-104頁(yè)。陶希圣在自述及其譯本中,通常把Oppenhermer譯為奧本海末爾或奧本海馬,今本通譯為奧本海默,故除引用陶希圣翻譯原文從其譯外,Oppenhermer通譯為奧本海默。同樣,德國(guó)社會(huì)學(xué)家桑巴德現(xiàn)今通譯為桑巴特,本文論述以今譯名定之。該書的研究方法不僅視歷史為一種變化的過程,而且視角更為全面,直接啟發(fā)了陶希圣的社會(huì)史觀。所以,陶希圣通過考茨基連接唯物史觀,當(dāng)然社會(huì)史觀與唯物史觀具有天然的親和性。支撐陶希圣的社會(huì)史研究的一個(gè)關(guān)鍵主題:商業(yè)資本,更是陶希圣直接從《資本論》部分章節(jié)中移譯出來的,商業(yè)資本在其社會(huì)史演變分析中,發(fā)揮了相當(dāng)重要的作用。*參見陶希圣:《中國(guó)社會(huì)形式發(fā)達(dá)過程的新估定》,《讀書雜志》,1932年第2卷第7-8期,第6-7頁(yè)。
雖然陶希圣的社會(huì)史觀與唯物史觀具有非常濃厚的親緣性,但是在陶希圣的社會(huì)史理論中仍然存在唯物史觀難以解釋的現(xiàn)象,即中國(guó)的社會(huì)形態(tài)一直處于變化之中,為什么統(tǒng)治集團(tuán)的上層建筑始終是士大夫階級(jí),一個(gè)沒有經(jīng)濟(jì)基礎(chǔ)的統(tǒng)治集團(tuán)在唯物史觀的解釋框架中始終是存在問題的,而且與社會(huì)史觀的第三個(gè)面向唯物的方法不相符。就陶希圣的社會(huì)史研究而言,還有兩個(gè)疑問:其一為什么在他對(duì)中國(guó)社會(huì)史的觀察中民族要重于階級(jí)?其二為什么“士大夫階級(jí)”中所謂的階級(jí)是一種身份,一種觀念生活集團(tuán)?這兩個(gè)前提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陶希圣隱含的歷史哲學(xué)出發(fā)點(diǎn),或許不需要明確的論證,但是必須有支持性資源。這時(shí)候,陶希圣進(jìn)一步尋找的支持性論證資源就是桑巴特和奧本海默所堅(jiān)持的史觀。
(三)社會(huì)史觀對(duì)精神因素的融合
就桑巴特而言,他的研究目的是要在德國(guó)國(guó)民經(jīng)濟(jì)學(xué)和英國(guó)國(guó)民經(jīng)濟(jì)學(xué)兩個(gè)傳統(tǒng)中進(jìn)行定位,即要破除這兩個(gè)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的藩籬,進(jìn)而達(dá)成一種科學(xué)的、無黨派的立場(chǎng)。桑巴特認(rèn)為他和馬克思的關(guān)系是繼承而非對(duì)抗:“我雖然嚴(yán)格的否認(rèn)他的世界觀,因此也嚴(yán)格否認(rèn)現(xiàn)在總括并評(píng)價(jià)為‘馬克思主義’的一切東西,但我卻無所保留地贊美他是資本主義的理論家和史學(xué)家……凡我的著作中稍微好一點(diǎn)的東西,都是受了馬克思的精神之賜。”*(德)桑巴特:《現(xiàn)代資本主義史》,第3卷序言,李季譯,商務(wù)印書館,1958年,第18-19頁(yè)。但這并不是說,桑巴特就贊同馬克思從學(xué)術(shù)到政治的結(jié)論,他的分析中要阻斷的,可能就是這個(gè)東西,因?yàn)樵诮酉聛硭f:“人們?nèi)绻挥帽扔鳎靡痪湓捴赋霰緯鴮?duì)馬克思著作的關(guān)系,那也許可以說,書中將破除馬克思的魔術(shù)”*桑巴特:《現(xiàn)代資本主義史》第1卷,譯者序。。那么什么是馬克思的魔術(shù)?世界觀,或許是!但無論如何桑巴特的世界觀是與馬克思不同的;精神為萬物之母,這顯然是馬克思所要破除的魔術(shù)!桑巴特堅(jiān)持的正是馬克思根本反對(duì)的東西,即“資本主義是由歐洲精神的深處發(fā)生出來的。產(chǎn)生新國(guó)家、新宗教、新科學(xué)和新技術(shù)的同一精神,又產(chǎn)生新的經(jīng)濟(jì)生活”*桑巴特:《現(xiàn)代資本主義史》第1卷,第25頁(yè)。。可見,盡管桑巴特對(duì)資本主義史的分析是圍繞經(jīng)濟(jì)原則、技術(shù)、組織三者的關(guān)系展開的,但是其核心卻在于經(jīng)濟(jì)主體的經(jīng)濟(jì)意識(shí)所落實(shí)的經(jīng)濟(jì)原則上;這也是陶希圣從桑巴特那里重點(diǎn)吸取的東西。既有經(jīng)濟(jì)史觀、又有辯證法,但是支配者是精神。
而奧本海默的《國(guó)家論》,陶希圣取法之處頗多,不僅有研究方法上的參考,也有國(guó)家圖景的引用。在《國(guó)家論》開篇,奧本海默即明言本書完全討論歷史上的國(guó)家。方法上則是從社會(huì)學(xué)的觀點(diǎn)來考察國(guó)家如何發(fā)生,如何進(jìn)化為現(xiàn)代立憲國(guó)家。*(德)奧本海默:《國(guó)家論》,薩孟武譯,東大圖書公司印行,1977年,第10頁(yè)。為此,奧本海默先駁斥了關(guān)于國(guó)家的其他學(xué)說,然后從國(guó)家的發(fā)生學(xué)的角度考察,國(guó)家之產(chǎn)生乃是種族武力斗爭(zhēng)的產(chǎn)物,并且欲考察從原始侵略國(guó)家如何曲折發(fā)展至自由市民團(tuán)體的。這個(gè)種族的出發(fā)點(diǎn),直接影響了陶希圣在中國(guó)社會(huì)史考察中對(duì)民族斗爭(zhēng)的重視,而不是對(duì)階級(jí)斗爭(zhēng)的重視,盡管陶希圣考察的社會(huì)總體情況,是取法乎考茨基。
在奧本海默的世界史中,對(duì)于同一目的,我們?nèi)绻軌蛎靼渍J(rèn)識(shí)其有兩個(gè)手段(政治的和經(jīng)濟(jì)的),則一切混亂可以避免,因?yàn)槟鞘抢斫鈬?guó)家的發(fā)生、本質(zhì)及目的的關(guān)鍵。現(xiàn)今一切世界史都是國(guó)家史,因此又是理解世界史的關(guān)鍵。全部世界史在沒有進(jìn)入自由市民團(tuán)體之前只有一個(gè)內(nèi)容,就是政治手段和經(jīng)濟(jì)手段的斗爭(zhēng)。從奧本海默的歷史哲學(xué)可以看出,他不排斥辯證法和經(jīng)濟(jì)史觀,但是這些在他那里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根本的東西是意志,是生存欲望。
至此,陶希圣社會(huì)史觀的來源大體上已經(jīng)清楚了,在桑巴特和奧本海默提供的理論框架之下,歷史的方法、社會(huì)的方法、唯物的方法可以兼容,但由此并不能走向馬克思;因?yàn)樵谏0吞啬抢锲鹬渥饔玫氖蔷瘢趭W本海默這里關(guān)鍵的在于意志,這是陶希圣融合的東西,在其中國(guó)社會(huì)史里,載體是士大夫階層。在這個(gè)意義上不能說陶希圣的社會(huì)史觀就是唯物史觀。因?yàn)樘障Jサ纳鐣?huì)史觀帶有某種意志論的色彩,但又不是哪一種因素起決定作用的簡(jiǎn)單劃分。早期陶希圣明確指出觀察中國(guó)社會(huì)應(yīng)取“歷史的觀點(diǎn)(非靜止的)、社會(huì)的觀點(diǎn)(群體之精神)和唯物的觀點(diǎn)(不是心的發(fā)展—天道理氣的流行,而是地理、人種、生產(chǎn)技術(shù)與自然材料造成的)”*陶希圣:《中國(guó)社會(huì)與中國(guó)革命》,上海新生命書局,1929年,第1-2頁(yè)。。但是這種唯物觀點(diǎn)究竟指什么,晚年修訂中可以看出,即生活的觀點(diǎn)或心物合一的觀點(diǎn)。中國(guó)歷史是地理、人種及生產(chǎn)技術(shù)與自然材料所造成,也是觀念的發(fā)展和思想的結(jié)晶。*陶希圣:《中國(guó)社會(huì)與中國(guó)革命》,臺(tái)北食貨出版社,1979年,第1-2頁(yè)。這種觀念論說與社會(huì)觀點(diǎn)中的群體精神相呼應(yīng),這也正是明顯的桑巴特和奧本海默的理論底色。正是陶希圣對(duì)桑巴特和奧本海默史觀的支持性引入,才解決了他社會(huì)史觀所面臨的困境,即一個(gè)不斷變化的社會(huì)形態(tài)為何能夠持續(xù)的為同一觀念階層所支配。但這也說明了張橫對(duì)陶希圣的某些判斷的準(zhǔn)確性,即表面上的帶有濃厚唯物史觀色彩的社會(huì)史觀,而實(shí)際的社會(huì)史分析卻很大程度上偏離了唯物史觀。所以,陶希圣潛在引用的桑巴特和奧本海默的理論資源從幕后走向臺(tái)前,社會(huì)史觀的第三個(gè)面向唯物的觀點(diǎn)改為生活的觀點(diǎn),心物并重也是必然的事情。然而,在陶希圣的社會(huì)史分析中,精神層面和物質(zhì)層面的緊張關(guān)系可以說是時(shí)刻存在的。
五、余論
通過對(duì)以陶希圣為代表的“食貨學(xué)派”的理論基礎(chǔ)進(jìn)行詳細(xì)的分析,不難發(fā)現(xiàn)以社會(huì)史觀為指導(dǎo)的“食貨學(xué)派”其所具有的學(xué)術(shù)意義遠(yuǎn)遠(yuǎn)要超出所謂的“食貨之學(xué)”或現(xiàn)代意義上的社會(huì)經(jīng)濟(jì)史。如果抽離掉社會(huì)史觀去觀察,那么“食貨學(xué)派”所具有的只是專業(yè)的社會(huì)經(jīng)濟(jì)史意義。一旦祛除籠罩在社會(huì)史觀上的迷霧,重返歷史語(yǔ)境,“食貨學(xué)派”的諸多面向?qū)⒁灰怀尸F(xiàn),例如以陶希圣、何茲全為代表的社會(huì)經(jīng)濟(jì)史研究,以陶希圣、沈巨塵為代表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研究,以陶希圣、瞿同祖為代表的法律社會(huì)史研究,整體而言“食貨學(xué)派”的社會(huì)史研究并不是專門史,而是開創(chuàng)了具有新史學(xué)氣象的社會(huì)史范式。
對(duì)此,民國(guó)時(shí)期的學(xué)者還有自覺的認(rèn)識(shí),例如唐德剛認(rèn)為“社會(huì)經(jīng)濟(jì)史”是現(xiàn)代史學(xué)百年來的先鋒。朱謙之則說:“現(xiàn)代是經(jīng)濟(jì)支配一切的時(shí)代, 我們所需要的, 既不是政治史, 也不是法律史, 而卻為敘述社會(huì)現(xiàn)象的發(fā)展, 社會(huì)之歷史的形態(tài), 社會(huì)形態(tài)的變遷之經(jīng)濟(jì)史或社會(huì)史。所以現(xiàn)代史學(xué)之新傾向, 即為社會(huì)史學(xué)、經(jīng)濟(jì)史學(xué)。”*朱謙之《序言》,《西漢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研究》,上海新生命書局, 1936年。隨著學(xué)科建制的完善和社會(huì)問題的政黨化替代解決,社會(huì)史的原初問題意識(shí)逐漸被遺忘,社會(huì)史研究也日益碎片化,并且在歷史學(xué)和社會(huì)學(xué)不同的學(xué)科建制中呈現(xiàn)不同的面貌。在這個(gè)意義上講,我們的社會(huì)史研究比之民國(guó)時(shí)期的“食貨學(xué)派”,顯然缺少了什么,重回“食貨學(xué)派”的社會(huì)史研究起源現(xiàn)場(chǎng),要喚起的正是失去的問題意識(shí),因?yàn)橹袊?guó)的社會(huì)史研究最根本的問題意識(shí)恰恰是回應(yīng)當(dāng)前的中國(guó)社會(huì)之變。
〔責(zé)任編輯:巨慧慧〕
[中圖分類號(hào)]K092
[文獻(xiàn)標(biāo)志碼]A
[文章編號(hào)]1000-8284(2016)02-0157-06
[作者簡(jiǎn)介]白中林(1981-),男,河南商丘人,編輯,博士,從事法律社會(huì)學(xué)研究。
[收稿日期]2015-10-01
·民國(guó)研究專題·
- 學(xué)術(shù)交流的其它文章
- 區(qū)域金融集聚與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的耦合性——基于面板VAR的實(shí)證分析
- 自由與秩序:信息主權(quán)法律規(guī)制的價(jià)值博弈
- “馬克思主義中國(guó)化:理論與實(shí)踐”學(xué)術(shù)研討會(huì)綜述
- 新聞學(xué)術(shù)史研究的又一力作——評(píng)《中國(guó)當(dāng)代新聞學(xué)研究范式的轉(zhuǎn)換》
- 社會(huì)的批判——評(píng)《從富裕到實(shí)踐——哲學(xué)與社會(huì)批判》
- 赫勒對(duì)未完成的歷史哲學(xué)之倫理解讀——評(píng)阿格妮絲·赫勒的《歷史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