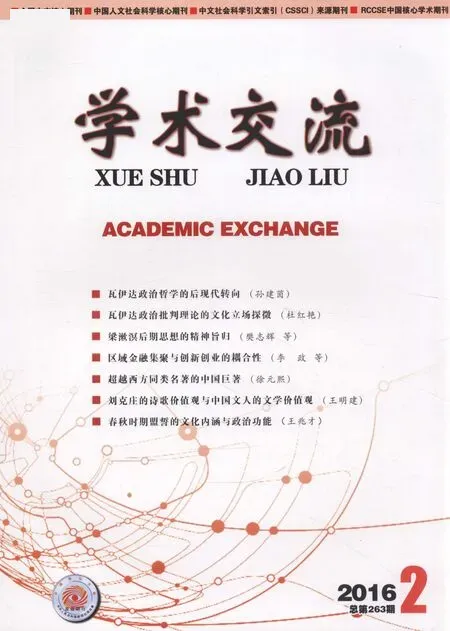單一的真理還是多樣的真理?
[匈]米哈伊·瓦伊達(Mihaly Vajda)
李佳怡 譯
(黑龍江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哈爾濱 150080)
?
單一的真理還是多樣的真理?
[匈]米哈伊·瓦伊達(Mihaly Vajda)
李佳怡譯
(黑龍江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哈爾濱 150080)
[摘要]尋找真理是胡塞爾現象學產生的最基本動機之一。他找到了真理的哲學概念,該哲學概念為他扮演了真理的一般概念的角色,哲學的真理是唯一的真理,任何取得明見性地位的事情就是真理,而且一切真實的事情必須具有主體間明見性。胡塞爾忽略了知識的模仿-反思方面。只有理解了真理是建立在認知過程的整個歷史結構上的,才能找到真理問題的答案,真理的統一概念才能被闡釋。通過考察總體性社會實踐的結構,說明人類認知的各種異質領域之間的差異和聯系、在這個復合體中它們的混合,以及已經實現的歷史進步,才能得到一種完整的答案。
[關鍵詞]真理;胡塞爾;社會實踐;明見性
尋找真理,尋找最終的、不容置疑的真理,即便不是胡塞爾現象學產生的最基本的那個動機,也是其最基本動機之一。
在《邏輯研究》(Logische Untersuchungen)中,真理等同于理想的客觀性。為了獲得真正的知識,需要掌握、擁有客觀的東西,獲得獨立于我們而存在的東西。然而,真理具有知識的特點且它不是一個客體;并且,如果它是知識,那么它也是主觀的、或者至少在某種程度上與主體有關的存在。如果我們想要從真理問題的角度明確說明《邏輯研究》的內部矛盾問題,我們可以說,按照它來理解,一方面,真理就是現實本身,它在各方面都獨立于人,它本身具有客觀性——但另一方面,它也是一個主觀的成就。這是柏拉圖主義和心理主義之間的矛盾。在《理念》(Ideen)中,胡塞爾從主觀主義角度解決了這個矛盾。但由于他從世界中完全隔離和抹去了主體,其成就便是理解真理(和通常的世界),他的確設法解決《邏輯研究》的矛盾,但這樣做的同時又使真理的問題變得完全無法解決,也即難以理解。可以想象,真理是一個客體,一個存在,而不是客觀性和主觀性之間的聯系,同時它也是一種主觀表現:所有客體都和先驗主體相關聯。但如果整個世界,包括真實的和想象的存在,即真理和錯誤,是自我的表現,是主體的構成,那么——如果完全按字面理解——判斷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就取決于我,將自主存在解釋為真實的、真正存在的還是假的、不真實存在的,也取決于我。由于胡塞爾——還沒有看到整個復雜問題的出路——在《理念》中并不承認純粹“自我論”的唯我主義,他也未能給出真理問題的最終答案。如果他能最終解決真理問題,解決方案可能就是放棄他最重要的一切,他的出發點:真理的客觀性。現在,將世界想象為一個主體間的構成,由相處和諧的單子組成,他能公開承認:在《理念》第一卷的框架中,“真理本身”的問題是沒有意義的。
真理,至少在最基本的、“純粹自我學的”現象學領域內(就像幾乎只在我的《通論》中刊出的現象學那樣),不再在通常意義上是真理“自身”了,甚至不是在這樣的意義上;它相關于一種先驗性的“每一人”。[1]238*譯者參:[德]胡塞爾.形式邏輯和先驗邏輯——邏輯理性批評研究[M].李幼蒸,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228.
純粹“自我論”的進一步發展,或者更準確地說,從純粹“自我論”到由社會單子構成的世界現象學理論的推進,對“最終”解決真理問題也是不可或缺的一步。
胡塞爾第三時期的現象學理論提供了一個看似理性的處理真理問題的方式,實際上這種方式與該問題在《邏輯研究》中被提出的方式一致。在《形式邏輯和先驗邏輯》(Formale und transzendentale Logik)和《笛卡爾沉思》(Cartesianische Meditationen)中,真理的概念,和之前一樣,認為真理和真實(Wahrhaftes)存在是一樣的,與不真實、虛假的存在相反。客觀存在與主觀存在相反,而且客觀性作為主觀成就的概念仍然被保留。
真理和邏輯(胡塞爾總是,或者說基本上總是在邏輯的基本規律屬于獨特的真理集合基礎上,同時討論真理和邏輯的問題,因為懷疑它們的有效性就相當于質疑知識的可能性)是先驗的主觀表現,和以任何形式(真實地或觀念上地,潛在或實際地,等等)存在的每一樣東西一樣。在這里,胡塞爾指的是數學,并非沒有道理:
至于數學,邏輯學家們沒有看到哪里實際上存在著完全相似的困難:形成物的觀念客觀性和從主觀側對其構成的活動(計數、結合等等)之間的交互纏結和相伴;因為,對由此產生的困難的物質,源于他們對形式數學基本概念的起源從未進行認真的哲學研究,此基本概念正是主觀構成的形成物。[1]73*譯者參:[德]胡塞爾.形式邏輯和先驗邏輯——邏輯理性批評研究[M].李幼蒸,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70.
因此,由數學充當不證自明的例證和確認,該文章認為,有些事情無疑是客觀的而且是毫無疑問的真理,同時又是一個主觀的表現。沒有人能否認,數學對象是主觀構成活動的結果。(沒有像數字這樣獨立于人存在的本質。)但也沒有人可以否認,數學對象——盡管它們是主觀的——也具有明確的客觀性,而且它們的相互關系構成了毋庸置疑的真理。參考數學并沒有其他目的,只是為了表明,客觀和主觀表現并不互相排斥。作為一篇文章的例證,就其本身而言,當然是正確的,我們當然可以接受這個論證,然而,不要忘記,胡塞爾在最后的分析中將數學作為解決真理問題的一般范例,對此,我們無法接受*為了證實我們拒絕數學預先假定的范式作用,一方面,我們必須詳細討論邏輯和數學之間的聯系,另一方面,必須詳細討論與數學本質相關的問題——在目前的范圍內我們無法進行該討論。但我們大致概述了真理的異質性,也指邏輯和數學,數學和邏輯真理,從這點出發,可以看出,與其他領域的特定類型的真理相比,數學真理不能再作為解決真理問題的典范。。不過,這不應妨礙我們以一種“非偏見”和“非假設”的方式接近胡塞爾研究調查真理問題的結果。
然而,除了完全拒絕胡塞爾的真理概念外,非偏見的方法也無法得出任何其他結論。胡塞爾——在這里,我們必須看到他唯心主義的基本和從未超越的結果——將真理定義為一個存在。“真正現在成為現實的,或者現實存在的,后者是自所與的明證性之對應項。”[1]113*譯者參:[德]胡塞爾.形式邏輯和先驗邏輯——邏輯理性批評研究[M].李幼蒸,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108.在《笛卡爾沉思》(Cartesian Meditations)中,用“個別的明證性還不足以造成持續的存在”*Husserl, Cartesianische Meditationen, p.96.譯者參:[德]埃德蒙德·胡塞爾.笛卡爾沉思與巴黎講演(胡塞爾文集第1卷)[M].張憲,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97.這句話對其進行了補充,“存在本身”或者“真理本身”,對他來說都是一樣的,即,與只為我存在的真理、我認為的真理相比,都是與可無限重復的明見性(evidence)相關的。*參見上條注釋所引書。個體單子的個體主體的約定(constitutum)總是偶然的、不真實的和不正確的,這與單子主體間性的共同體的約定相反,與可以無限重復的明見性相反(在兩種意義上的無限:對同一主體,這種明見性將永遠保持明顯有效,而且它們的有效性可延伸至每一個單子,或屬于同一共同體的每一個單子),它們的相關性是真實和真理本身。我們的問題并不涉及真理是被構成的這一主張;它與“真理和存在”的認同相關。這種認同不僅揭示了胡塞爾的唯心主義,也揭示了所有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社會本體論特征,實際上這也是每一種唯心主義的社會本體論特征,按照馬克思的說法,唯心主義表現為這樣的事實:它一直發展著“能動的方面”,卻不知道“真正現實的、感性的活動本身”。對唯心主義者來說,行動和思想是相同的,或者更準確地說,只有思想被唯心主義承認是真正的人類活動,由此真理作為一個概念的約定,才被認為是與客觀(gegenst?ndlich)約定、客體構成相同的。對唯心主義來說,真理一般不是存在和真理之間的一個關系。真理不能是一種關系,因為如果唯心主義將存在作為非概念、非理想性的東西,那么實際上,存在會變得難以理解、超出人類的力量、與人類和人類行為不相容,實際上,會變得擁有超越人類的力量。在存在和真理的相關性背后,就像在唯心主義的整個概念結構背后,我們發現了對異化世界的概念性否定,這種否定只是作為一個心理過程來實現的。甚至那些認為某種精神的優越性高于世界——高于自然和人類精神——的唯心主義也認同存在和真理。上帝的行為、上帝的世界就是真理本身。唯心主義的這種特征在唯心主義體系至高無上的認識論中得到了證明,事實上就像黑格爾本體論假設邏輯的形式一樣。*盧卡奇的作品《社會存在本體論》有一章是關于黑格爾的,其中作者表明,黑格爾的邏輯是邏輯化的本體論。放棄將存在視作真理就是放棄唯心主義,放棄一種概念——在這種概念下,存在和客觀是一種主觀行為,是異化的主體本身。但是,放棄唯心主義,同時保持異化的前景(這種異化將主觀性等同于個體主義,即便后者采取的是個體主義具體化的形式),就意味著注定讓人類被動、無助,認為人是不相容、可怕、令人費解的力量,是自然的“法則”和——甚至更大的問題——社會的“法則”。如果我們接受上述馬克思有關唯心主義的社會本體論定義的觀點,我們必須意識到,根據唯心主義(無論其具體陳述是什么),真理將永遠等同于良好地、適當地、如此等等地構成的存在。
存在和真理的一致性構成了胡塞爾真理概念的核心,這是無法令人接受的,盡管正是這同一論著使他取得了“真理是人造的”這個我們也接受的認識。
但真理是一種人類約定指的是什么意思呢?這樣說的意思是否就是指,我們斷言真理并不是那些實際存在著的東西,而是對它們的一個主觀上構成的想象?也就是說,這一命題等同于對唯心主義的真理概念的簡單否定嗎?將它稱為否定唯心主義的真理概念,合理嗎?畢竟,這種斷言在唯心主義的基礎上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釋,實際上,這是它第一次出現在哲學史上時的解釋,而且,正如我們所見,它也形成了胡塞爾真理概念的一個決定性因素。把真理解釋為給定客觀性的主觀表象,在另一方面,相當于對真正概念性活動的否認。
真理問題是最基本的哲學問題之一,對這類問題,在馬克思之前,無論是唯物主義還是唯心主義,都無法找到確實令人滿意的答案,甚至找不到一個可以滿足其自身的內部邏輯的答案。唯心主義的最后一句話就是黑格爾的命題“真理具有總體性”。但即便是馬克思式的唯物主義者解決了這一問題,也仍然還有很多問題懸而未決。按照馬克思所說,“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自己思維的此岸性。關于思維——離開實踐的思維——的現實性或非現實性的爭論,是一個純粹經院哲學的問題。”[2]82*譯者參: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5.
不無原因的是,在其歷史發展過程中,馬克思主義本身進行了——雖然沒有公開承認——對最初的馬克思主義準則的修正。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所謂外延概念*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外延概念”,我是指自20世紀30年代起一直占據領導地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概念。(參見:Gy?rgy Mrkus, Discussions and Tendencies in Marxist Philosophy, Kortrs, 1968/7.)毫無疑問,這一概念建立在許多方面之上,尤其是在目前相關方面,主要是恩格斯和列寧的某些論述(分別為《自然辯證法》、《反杜林論》、《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與《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然而,我并沒有批判真實的恩格斯和列寧主義觀念,這種分析將超出本文范圍,我的批評只針對在“外延馬克思主義”中被推崇的真理概念的最基本特征。(按其說法,哲學是一種特殊的科學,對所有領域的現實都有效)的規劃特點將人類認知解讀為一個過程,它通過真理和錯誤的相對關系,匯集到絕對真理的無窮遠點;由此,這種概念表述認為真理是知識與“給定的”世界之間的樞紐,盡管真理只能在人類認知發展的無窮遠點才能夠被獲得。雖然馬克思主義的實踐(praxis)標準也出現在了這一真理理論中,但它完全不同于原來的意義。恩格斯的概念——可以用格言“事實勝于雄辯”來總結并可通過他發現茜素的著名例子清楚地闡明——與上述引用的馬克思的觀點不同。馬克思的觀點是對黑格爾的“事實具有總體性”的唯物主義逆轉。就它建立在反對“總體性”和“絕對”的基礎之上而言,它是唯物主義的逆轉,但就它并非在特定事實和描述它的命題之間的一致性中,而是在人類認知的歷史自辯中尋找對真理問題的解答這一點而言,這種想法與之前無異。
然而,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并用整個《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Theses on Feuerbach)的精神來解讀它,造成了這種現象:談論傳統意義上的真理毫無意義,日常思維的真理甚至科學的真理可以通過它們的實際結果和效用,用實用主義證明其合理性。“外延概念”就是這樣的:它在本質務實理念意義上,將馬克思的實踐(praxis)標準應用于日常思維和科學的真理中,而且為了避免后者的主觀主義相對論后果,它用黑格爾的“總體”概念問題補充了這個實用主義。
問題在哪里呢?讓我們從《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的總體性的視角,重新審視馬克思關于真理的提綱!這里討論的是什么樣的真理呢?讓我們細想一下第一條提綱,在這里馬克思陳述了有關主體和客體的辯證統一的概念!再讓我們細想一下著名的第十一條提綱,在這里馬克思提到“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2]84*譯者參: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7.。如果我們牢記這一點,并意識到馬克思在《提綱》中表達的是他自己的哲學觀點,我們將能夠解釋馬克思的真理概念,或者更確切地說,我們將更清楚地看到在馬克思的心中真理是什么樣的。馬克思談論的是他自己的哲學的真理,而不是一般的真理。對馬克思來說,哲學的真理并非“給定事物的真理”,也不是對已存在事物的反思,而是相對的,即,非閉合的,“總體性”的真理:革命性社會實踐(praxis)的真理,一種實踐(practice)的真理,它除了利用現有的可能性,還為了實現“人的本質”而創造了新的可能性。馬克思在這里談到人的力量和現實性,以及為它們辯護的理由,并不是巧合。馬克思并沒有說,我們能夠借以達到我們目標的所有理論都是實際正確的。馬克思發現了虛假意識的歷史作用,因此他不會持這種觀點。他所提到的理論,是能夠產生人的力量和現實性的理論。
但如果是這樣,我們無法得出任何關于馬克思“一般”真理概念的“直接”結論,這正如,馬克思的跟他對先前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批判有關的“主體和客體辯證統一”的理論不能被解讀為一般性的現實(否則馬克思將成為一名唯心主義者),又如,他要改變世界是針對哲學,而非針對知識、日常,或者科學之類的一般性思維。
馬克思在其《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以及在他的整個哲學觀念中——可以說摧毀了資產階級“形而上學”的整個結構,該結構以抽象個體為出發點。這種摧毀消除了真理的普遍抽象概念和對真理的普遍標準的尋求——它們是早期哲學的特征。我們無法談論“一般性”的真理,因為如果我們這樣做的話,那么日常真理、科學真理、道德真理、哲學真理等的混合將會接踵而來,而真理概念的內部矛盾也會產生,典型如各種資產階級哲學和各種馬克思主義的真理理論。
我們的任務并不是嘗試對馬克思的真理理論,或者更確切地說,對馬克思的“一種”真理理論進行明確的規定,哪怕是概要性的。然而,為了使我們的闡述沒有錯誤,我們想要使用馬克思的例子對其理論中的真理異質性進行解釋。馬克思曾寫道:“經濟學家們向我們解釋了生產怎樣在上述關系(即分工、信用、貨幣等資產階級生產關系——引者注)下進行,但是沒有說明這些關系本身是怎樣產生的,也就是說,沒有說明產生這些關系的歷史運動。”[3]104*譯者參: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39-140.
馬克思的這句話可以解讀為,“經濟學家”只陳述了某些真理的作用,但對其他真理卻保持沉默。但整個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概念表明,這并非馬克思的意圖。對他來說,這并不是除了真理還存在錯誤的一個問題。馬克思接受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作為科學真理。這個真理并不符合特定事實和描述它們的特定前置詞;它是一個科學體系的真理。
李嘉圖從一切經濟關系中得出他的公式,并用來解釋一切現象,甚至如地租、資本積累以及工資和利潤的關系等那些驟然看起來好像是和這個公式抵觸的現象,從而證明他的公式的真實性;這就使他的理論成為科學的體系。[3]49-50*譯者參: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93.
這個科學真理是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真理。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不能說它僅僅是一個相對真理。這是真的,因為它充分描述了整個資本主義經濟機制,不過,是以資產階級的觀點來描述的。
然而,從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角度來看,這個真理原來是一個“錯誤”,盡管事實上它對資產階級經濟進行了充分的描述。政治經濟學屬于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談到“孤立個體”的虛假哲學概念時提到的領域。
在這個自由競爭的社會里,單個的人表現為擺脫了自然聯系等等,而在過去的歷史時代,自然聯系等等使他成為一定的狹隘人群的附屬物。[4]5*譯者參: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
只有到18世紀,在“市民社會”中,社會聯系的各種形式,對個人說來,才表現為只是達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現為外在的必然性。但是,產生這種孤立個人的觀點的時代,正是具有迄今為止最發達的社會關系(從這種觀點看來是一般關系)的時代。人是最名副其實的政治動物,不僅是一種合群的動物,而且是只有在社會中才能獨立的動物。[4]6*譯者參: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
對于政治經濟學而言,上述最發達的(一般性)社會關系的出現只是市場上產生的孤立個體之間的關系,因此,作為一個科學體系,政治經濟學不同于馬克思主義的科學體系。雖然它充分描述了資產階級生產的條件,確實如此,然而,仿佛它們是自然永恒的條件。它描述了資產階級經濟的功能,但認為它是唯一可能的經濟結構,由此甚至其范疇框架使理論接近主題也成為可能,這將不同于馬克思主義建立在自己哲學基礎上的科學范疇。以歷史觀點看,“政治經濟學”不能把握資本主義的境況。
研究組的血鈣濃度恢復正常時間指標(3.24±1.45)天顯著短于參照組(4.54±1.04)天,統計學有差異(t=5.736,P<0.05)。
對生產一般適用的種種規定所以要抽出來,也正是為了不致因為有了統一(主體是人,客體是自然,這總是一樣的,這里已經出現了統一)而忘記本質的差別。那些證明現存社會關系永存與和諧的現代經濟學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記這種差別。……生產不同于分配等等,應當被描寫成局限在與歷史無關的永恒自然規律之內的事情,于是資產階級關系就被乘機當作社會一般的顛撲不破的自然規律偷偷地塞了進來。[4]7-9*譯者參: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5.
馬克思從未否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性和真理性。例如當他批評蒲魯東或各種反動烏托邦時,他甚至以非常明確的方式強調其科學性和真理性:
或者是希望在現代生產資料的條件下保持舊時的正確比例,這就意味著他既是反動者又是空想家;
或者是希望一種沒有無政府狀態的進步,那就必須放棄個人交換來保存生產力。
個人交換或者只適宜于過去幾世紀的小工業和它特有的“正確比例”,或者適宜于大工業以及隨之而來的一切貧困和無政府狀態。[3]68-69*譯者參: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09-110.
這最后一個選擇,即個體交換+大工業+苦難和無政府狀態,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觀點。這是一個真理,然而,卻是絲毫不適合證明我們思想的片面性和力量的一種真理,即科學真理,它在哲學上講是虛假的。之所以虛假,因為存在其他的選擇,要實現“非無政府狀態下的進步”,前提是“我們必須放棄個體交換”。但這個解決方案對開始于抽象、孤立的個體的古典政治經濟學真理而言并不存在,而只是社會關系在個體交換過程中的實現。
我們似乎已經遠離了我們最初的問題,遠離了對真理的現象概念的批判。雖然我們沒有確切證明,但我們的確闡明了問題:構思真理的一般抽象概念是不可能的。有些東西在哲學上可能是虛假的,但在科學上是真實的,正如科學上虛假的東西在我們日常常識中未必是虛假的。最后這一點我們可以通過一個小例子來說明:當太陽出現在地平線上時,如果有人說“太陽升起了”,他并沒有犯錯,盡管大家都知道,這種日常真理在科學上是一個虛假陳述。
這種同樣形而上學的努力使得試圖找到一個真理標準的努力歸于失敗。以一般抽象的方式來詢問“真理是什么”是一個錯誤,就像同樣地以一般抽象的方式尋找真理的標準也是錯誤的一樣,而這在所有的知識領域全都有效。不說“真理”,而是根據不同的認知領域談論不同真理,這并不意味著真理是相對的。不同領域的知識之間不斷地通過歷史相互關聯和相互作用,總會導致它們彼此的“真理”之間持續交融和對抗。
本文的任務并非要解決真理問題。只有理解了真理是建立在認知過程的整個歷史結構上的,才能找到這一答案。只有通過這種方法,“真理的統一概念”(但不是真理的一般抽象概念)才能被詳細地闡述,這個概念盡管存在異質性,卻得以統一,或者不如說,正因為其異質性而得以統一。只有考察總體性社會實踐(praxis)的結構,說明人類認知的各種異質領域之間的差異和相似點和聯系、在這個復合體中它們的混合,以及已經實現的歷史進步,才能提供一種完整的答案。
根據以上所述,我們可以以這種方式描述胡塞爾的嘗試:他努力想找到真知的基礎和標準,這是他整個著述的基礎,最終使他找到了真理的專有的哲學概念,然而,該哲學概念對他而言也扮演了真理的一般抽象概念的角色。真理不只是思想中構成的給定現實的想象,而是一個概念性的“活動”,這一活動能夠而且必須成為造物主的轉換和現實的再創造。因為對胡塞爾來說,它本身是具有精神特征的,它的變換也只是一個純粹的精神過程,發現真理和意識到真理是同樣一件事情,因此在人的本質特征或在其社會歷史過往中,真理并非客觀決定因素。一個共同體所接受的所有的主體間性判斷和所有跡象成就了真理的地位。
對胡塞爾來說,哲學的真理是唯一的真理。他完全忽略了知識的模仿-反思方面,以他的科學真理來看,那種為我們安排和重新建構給定事實的真理,如其所是,并入哲學真理中,因此導致后者也具有片面性。
對胡塞爾而言,普通的無限明見性成為真理的唯一標準并不是偶然。任何取得明見性地位的事情都是真理,而且一切真實的事情必須具有主體間明見性。因此,只要有群體接受它,任何偏見體系都能成為真理。胡塞爾唯心主義的活動原則卻變得相反:“不證自明”的體系變得令人費解,因為它的真理和原則不能通過其明見性被證明。但歷史真相如何能達到無限遠,事實上取決于它從成為明見性而得以產生的那一刻。
然而,一般-統一的胡塞爾真理概念不能掩蓋一個事實,即不同層次的知識有自己不同的真理。
市場上的商人有其市場真理;此真理在其市場關系中難道可能不是對其有用的良好真理和最好真理嗎?因而它可能是這樣一種虛假的真理嗎?只因為受到其他相對性的限制并按照其他目的和觀念進行判斷的科學家在尋求其他的真理,后者可用于處理許多其他事物卻并非市場上所需的事物。人們最終必須終止使自己,特別在哲學和邏輯學內,受到“精確”科學的理想的和規則的掛念和方法的迷惑,似乎精確科學的“自在性”實際上是相關于對象存在和相關于真理的絕對規范的。[1]245*譯者參:[德]胡塞爾.形式邏輯和先驗邏輯——邏輯理性批評研究[M].李幼蒸,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235.
然而,在胡塞爾的唯心主義概念框架內,這種認知,除了接受日常生活的實用真理,也使哲學真理變得實用,因為它斷開了日常意識和(面向總體的)哲學之間的聯系,它把旨在改變社會的哲學真理,從那些頂多僅在純粹的道德意義上為真的烏托邦中分離出來,并且將烏托邦與那些描述既定事實的客觀科學真理進行了對比。
[參考文獻]
[1]Husserl E.Formale und transzendentale Logik[M]//Jahrbuch fur Philosophie und ph?nomenologische Forschung(Band X).Halle:Verlag Max Niemeyer,1929.
[2]Marx.Thesen über Feuerbach(MEGA 1/5, p.534.Theses on F.)[M]//Engels F.Ludwig Feuerbach.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41.
[3]Marx.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M].Moscow: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4]Marx.Einleitung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konomie[M]//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konomie.Berlin:Dietz Verlag,1953.
〔責任編輯:余明全〕
[中圖分類號]B515;B08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0-8284(2016)02-0020-06
[作者簡介]米哈伊·瓦伊達(Mihaly Vajda,1935-),男(猶太族),匈牙利人,教授,博士,東歐新馬克思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本文“Truth or Truths?”寫于布達佩斯,原載Philosophy & Social Criticism,1975,3(1):29-39.本刊經作者同意譯載。摘要、關鍵詞、 均為譯者加。 李佳怡(1990-),女,黑龍江哈爾濱人,博士研究生,從事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
[收稿日期]2016-01-19
中東歐思想文化研究
·瓦伊達政治哲學理論范式專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