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留日法政速成科紀(jì)事
毛亞楠
法政速成科的設(shè)立給了渴求西學(xué)的國(guó)人以便利,加之清庭科舉制度的廢除,留洋更成為傳統(tǒng)士人接續(xù)仕途的終南捷徑,“各省官、私就學(xué)者頂背相望”
1906年11月30日,清朝留日法政速成科的官費(fèi)生、后來(lái)新中國(guó)成立后曾任最高法院院長(zhǎng)的沈鈞儒坐在居所中,鋪開(kāi)信紙,給妻子張象徵寫信,“現(xiàn)存的學(xué)費(fèi)不到60元矣”。寫到這里,沈鈞儒覺(jué)得“可嘆亦可笑”。最窘迫之時(shí),他都到了“短衫褲子破了也不能買”、“出門都不敢坐電車” 的地步。
在日留學(xué)不比在家,處處都得花錢。法政速成科的全年學(xué)費(fèi)是日金四百元,當(dāng)時(shí)的日金比大洋要更值錢,相對(duì)于當(dāng)時(shí)國(guó)人收入而言,這筆留學(xué)費(fèi)用并不是一筆小數(shù)目。沈鈞儒作為官費(fèi)生,雖有每月三十至四十元的留學(xué)費(fèi)支撐,但除了學(xué)習(xí)他還要購(gòu)書、交友、參加各種活動(dòng),這些加起來(lái)支出甚巨,因此經(jīng)常窘迫不堪。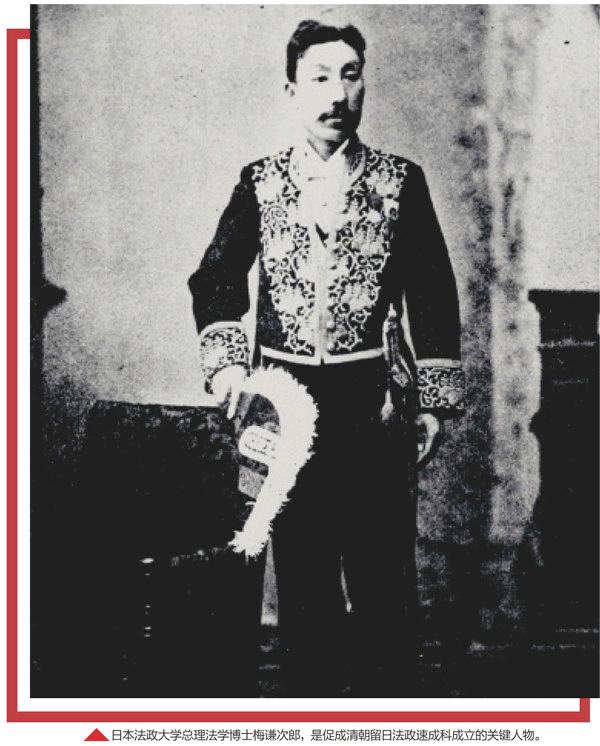
從沈鈞儒身上,大致可窺得晚清赴日留學(xué)的生活日常。然而即便如此,赴日留學(xué)仍是當(dāng)時(shí)的時(shí)代焦點(diǎn),尤其求學(xué)法政,乃是中國(guó)法制近代化的一件大事。而令他們離家去國(guó)、易苦以甘去求學(xué)的原因,是清末變法修律亟求新知和儲(chǔ)備人才的大時(shí)代背景,是甲午戰(zhàn)敗,加之“庚子之役”后國(guó)人的“痛定思痛”。
較之徑赴西洋,清朝政府選擇選派學(xué)生去已經(jīng)汲取西學(xué)的近鄰日本作為留學(xué)之地,于文字、風(fēng)俗、費(fèi)用等更為便宜。而日本方面,在中國(guó)方敗、正崇拜明治維新的成就之際,日本官紳在華的游說(shuō)活動(dòng),也是促成留日浪潮的主要原因之一。他們表面上其美名為親善提攜,實(shí)則包藏野心。當(dāng)時(shí)駐華公使矢野文雄就曾有言,習(xí)法政者將以“日本為楷模,為將來(lái)改革之準(zhǔn)則”。
沈鈞儒當(dāng)時(shí)求學(xué)之地是一個(gè)叫“法政速成科”的地方。1904年,日本東京法政大學(xué)專門針對(duì)清國(guó)留學(xué)生實(shí)施短期速成(一年,后改為一年半)法學(xué)教育,設(shè)立“法政速成科”,以接受清政府派遣的法律、行政、政治領(lǐng)域的留學(xué)生。從1904年5月正式開(kāi)班到1908年7月舉行最后一班畢業(yè)典禮,法政速成科為時(shí)不過(guò)5年,前后受教卻約莫千人,雖為一臨時(shí)體制,卻對(duì)清末政治、法律變革運(yùn)動(dòng)乃至近現(xiàn)代中國(guó)影響甚大。
放眼清末,眾多法政速成科畢業(yè)生歸國(guó),投身于政治、法律變革運(yùn)動(dòng),涌現(xiàn)出一些著名的政治人物和法政人才,他們共同推動(dòng)了傳統(tǒng)法律制度向現(xiàn)代法律制度的轉(zhuǎn)型,對(duì)近代中國(guó)的法律啟蒙起到重要作用。
而百年已過(guò),那些曾在帆影輪聲歲月里負(fù)笈東瀛的法政留學(xué)生是何面貌,他們?cè)诜ㄕ俪煽频纳詈托睦砭秤鲇质侨绾危瑥膹V西師大出版社最近出版的《清國(guó)留學(xué)生法政速成科紀(jì)事》中可見(jiàn)一斑。
“法律界的春天來(lái)臨了”
有關(guān)法政速成科之設(shè)立,史學(xué)界廣泛接納的一條史料,出自清朝、北洋政府大臣曹汝霖所撰《一生之回憶》。曹汝霖在書中寫道:1904年,他即將于日本東京法學(xué)院畢業(yè)回國(guó)。3月里的一天,在宏文學(xué)院學(xué)習(xí)師范的范源濂前來(lái)看他,二人談起回國(guó)后的打算。范源濂鑒于國(guó)內(nèi)目前法政人才匱乏,而日本正規(guī)法政教育又時(shí)長(zhǎng)難待,提議在東京為有志法學(xué)的留學(xué)生特設(shè)法政速成科,“以期快速造就人才”。曹汝霖聽(tīng)后十分贊成,并想到向日本法政大學(xué)校長(zhǎng)梅謙次郎尋求幫助,原因是他向梅謙次郎請(qǐng)教過(guò)幾次,覺(jué)得梅謙次郎有別于那些“不愛(ài)多管閑事”的日本法學(xué)家,“他對(duì)中國(guó)很關(guān)心,人亦爽快明通,不是只埋頭苦干,不問(wèn)外事之人”。
根據(jù)曹汝霖的記載,梅謙次郎后來(lái)接受了曹和范二人的建議,表示“愿意出一點(diǎn)力”,并打算將法政速成科的地址設(shè)在了法政大學(xué),由梅謙次郎親自約請(qǐng)來(lái)授課的教授。
按曹所述,似乎梅謙次郎完全是在曹汝霖和范源濂的提議下才熱心創(chuàng)辦法政速成科。但從時(shí)間上看,這其中似有不合理之處。法政速成科5月初第一班開(kāi)班授課,距離曹和范最初晤談僅短短一個(gè)多月的時(shí)間,眾所周知,開(kāi)設(shè)一所學(xué)校并非簡(jiǎn)易之事,若梅謙次郎對(duì)此事毫無(wú)準(zhǔn)備,實(shí)難想象能在這么短時(shí)間內(nèi)讓一切全部就緒。
事實(shí)上,梅謙次郎之所以全力支持開(kāi)設(shè)法政速成科,與當(dāng)時(shí)日本社會(huì)熱衷于提供“速成”教育也有很大關(guān)系。日本著名中日關(guān)系史專家,原早稻田大學(xué)教育學(xué)部教授實(shí)藤惠秀在其所著《中國(guó)人留學(xué)日本史》中記載:1902年,晚清教育家吳汝綸赴日視察教育,前后居留三個(gè)月。他一方面考察各種文化設(shè)施,一方面參加文部省主辦的有關(guān)學(xué)制的講座,并且訪問(wèn)日本朝野知名人士。日本名士從各種立場(chǎng)發(fā)表多種意見(jiàn),但大多主張中國(guó)當(dāng)時(shí)必須推行速成教育。因中國(guó)當(dāng)時(shí)推行新教育比日本遲了三十年,且日本在明治初年亦推行速成教育。
不僅如此,報(bào)章雜志也跟著鼓吹速成教育。1903年,清末大臣張百熙等奏定《學(xué)務(wù)綱要》,與其說(shuō)獎(jiǎng)勵(lì),不如說(shuō)是命令大家留日研修速成的師范科。當(dāng)時(shí)的日本學(xué)校甚至出現(xiàn)激烈的競(jìng)爭(zhēng)傾向,“如甲校用一年教授完畢,乙校減為八個(gè)月,而丙校更縮成半年。尤有甚者,竟有數(shù)月以至數(shù)日的速成科”。
由此可看,法政速成科是應(yīng)運(yùn)而生的時(shí)代產(chǎn)物。梅謙次郎在詢之于日本小村外務(wù)大臣并獲得后者贊同后,在小村的介紹下,與清出使日本大臣兼留學(xué)生監(jiān)督楊樞進(jìn)行了晤談。楊樞對(duì)此提議“極為贊賞”,并“向長(zhǎng)岡護(hù)美取得前所所擬學(xué)章作為稿本,而與梅謙次郎酌中改定”。1904年4月26日,梅謙次郎向日本文部省正式提出在法政大學(xué)設(shè)置清國(guó)留學(xué)生法政速成科的申請(qǐng),4日后即得日本文部省的認(rèn)可批復(fù)。此后“聘教師,募學(xué)生,旬日而成”,其第一批入學(xué)者共94人。
法政速成科的創(chuàng)設(shè)是當(dāng)時(shí)中日教育界的一件大事,各報(bào)刊紛紛予以報(bào)道。《東方雜志》號(hào)召國(guó)人踴躍入學(xué),《新民叢報(bào)》則斷言“此次政法速成科其將來(lái)之成績(jī),必非師范速成科之所能及”。加之當(dāng)時(shí)諸多學(xué)人對(duì)法律的重視程度,法政速成科之設(shè)立給人以“法律界的春天來(lái)臨了”的感覺(jué)。
課程豐富、生活窘困的日子里
法政速成科的設(shè)立給了渴求西學(xué)的國(guó)人以便利,加之清庭科舉制度的廢除,留洋更成為傳統(tǒng)士人接續(xù)仕途的終南捷徑,“各省官、私就學(xué)者頂背相望”。
按照《法政大學(xué)清國(guó)留學(xué)生宿舍章程》,要成為法政速成科學(xué)員,需為“清國(guó)在官者及候補(bǔ)官員、清國(guó)地方之士紳”,且須“清國(guó)公使之紹介”,經(jīng)考試方可入學(xué)。也就是說(shuō),法政速成科最初設(shè)置的入學(xué)門檻還是較高的。入學(xué)速成科者,需要在本國(guó)已有相當(dāng)學(xué)習(xí)經(jīng)歷,大多具有進(jìn)士資格,甚或?yàn)椤盃钤薄?/p>
根據(jù)速成科規(guī)則,修業(yè)年限第一期定為一年,后來(lái)又延長(zhǎng)為一年半,整個(gè)學(xué)習(xí)分為兩個(gè)學(xué)期,講授的科目有法學(xué)通論、民法、商法、國(guó)法學(xué)、行政法、刑法、國(guó)際公法、國(guó)際私法、裁判所構(gòu)成法、民刑訴訟法、經(jīng)濟(jì)學(xué)、財(cái)政學(xué)、監(jiān)獄學(xué)。
從其所聘師資可見(jiàn)法政大學(xué)對(duì)速成科的高度重視。擔(dān)任講師者,都是各大學(xué)一流法學(xué)家,由梅謙次郎親自出面禮聘。其中,東京帝大教授小野冢喜平次向來(lái)堅(jiān)持在帝大外不講課,卻被梅謙次郎打動(dòng),前來(lái)講授政治學(xué)。日本近代著名監(jiān)獄學(xué)家小河滋次郎則帶領(lǐng)學(xué)生進(jìn)行實(shí)地考察,參觀巢鴨、東京、市谷監(jiān)獄和浦和監(jiān)獄川越懲治所。
速成科的特色是將授課內(nèi)容通譯成中文,主要由曹汝霖和范源濂擔(dān)當(dāng)通譯。如此可省下學(xué)習(xí)日語(yǔ)所需要的三四年的時(shí)間與精力。這為眾多學(xué)生提供了一條便捷快速更新知識(shí)結(jié)構(gòu)以應(yīng)對(duì)劇烈社會(huì)變革的有效途徑。因其“入則能聽(tīng),聽(tīng)則能懂”的優(yōu)勢(shì),法政速成科吸引了更多留學(xué)生慕名而來(lái)。
1906年,受兩江總督端方委派赴日考察教育的吳蔭培曾于法政速成科第四班旁聽(tīng),對(duì)這種教學(xué)方式他有親身體會(huì)。他在日記中稱:“至四班學(xué)堂聽(tīng)法學(xué)博士高野巖三郎講財(cái)政公正厘則免稅特權(quán)一段。有大學(xué)專門部楚北人何姓作翻譯,余援旁聽(tīng)生之例,參坐其間,斷章取義,亦能領(lǐng)會(huì)。”
除此之外,邀請(qǐng)學(xué)界名流開(kāi)設(shè)各種學(xué)術(shù)講座、安排各種考察和實(shí)習(xí),也是法政速成科為中國(guó)留學(xué)生特設(shè)。尤其是為加強(qiáng)中國(guó)留學(xué)生對(duì)所學(xué)認(rèn)知的增進(jìn)而安排的實(shí)地考察和實(shí)習(xí),這在當(dāng)時(shí)日本各校中極為罕見(jiàn)。小河滋次郎的實(shí)地教學(xué)尤其充分,他曾帶領(lǐng)速成科學(xué)生廣泛考察日本各監(jiān)獄,實(shí)地研究各監(jiān)獄牢房、勞役場(chǎng)等處,這些考察活動(dòng)加深了中國(guó)留學(xué)生對(duì)日本近代監(jiān)獄體制的認(rèn)知,對(duì)于其監(jiān)獄學(xué)課程的學(xué)習(xí)大有裨益,清末中國(guó)監(jiān)獄學(xué)的傳入與發(fā)達(dá)也與這段教育有很大關(guān)系。
除學(xué)習(xí)安排的考察外,速成科留學(xué)生自行游歷者也為數(shù)不少。速成科第一班湖南籍學(xué)生廖維勛在日期間對(duì)監(jiān)獄學(xué)極有興趣,曾對(duì)日本監(jiān)獄進(jìn)行了廣泛考察。宋教仁曾與廖維勛談及監(jiān)獄改良,對(duì)廖維勛的監(jiān)獄學(xué)知識(shí)欽佩不已。。回國(guó)后,廖維勛就職于廣東高等巡警學(xué)堂,執(zhí)監(jiān)獄學(xué)課程教鞭,后來(lái)成為清末著名的監(jiān)獄學(xué)大家。
然而,除了豐富多彩的學(xué)習(xí)生活,對(duì)留日學(xué)生而言,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過(guò)得游刃有余是他們最為重要的挑戰(zhàn)。沈鈞儒曾描述其在速成科的留學(xué)生活,“每日工課必忙,七日一休息。或溫習(xí),或出外游玩,亦不可少”。然那時(shí)的留學(xué)生活可不像如今留學(xué)這般寬裕,法政速成科多官費(fèi)留學(xué)生,即使有留學(xué)公費(fèi)支持,可生活仍然常常窘迫不堪。沈鈞儒在1906年致夫人信中提及生活困難,為“妹窘竟不能顧”而慚愧萬(wàn)分——官費(fèi)生的生活都如此,對(duì)自費(fèi)生來(lái)說(shuō)則更加困難。如此條件下,法政速成科的教師和學(xué)生都非常用功,故有連暑假也不休息的學(xué)習(xí)風(fēng)氣。
天道酬勤,法政速成科第一班畢業(yè)的成績(jī),足可用“驕人”來(lái)形容。據(jù)梅謙次郎在畢業(yè)典禮上所言:“初不意試驗(yàn)之成績(jī),竟如此優(yōu)異。此次全科受試驗(yàn)之總數(shù),凡七十三名,其中落第者僅六名……諸子之試驗(yàn),其成績(jī)終如此,實(shí)非豫想所及,是實(shí)有意外之愉快。”
“清國(guó)的雙刃劍”
但事情總有兩面,法政速成科固然積聚了當(dāng)時(shí)中國(guó)眾多精英人才,可隨著留日學(xué)生的大量增加,一些低劣的學(xué)生也得以混跡其中。魯迅在文章《藤野先生》中寫道:上野櫻花爛漫之時(shí),他就曾在花下見(jiàn)過(guò)成群結(jié)隊(duì)的速成班的清國(guó)留學(xué)生,他們逛公園,賞櫻花,將辮子高高盤起宛如“富士山”。魯迅本去中國(guó)留學(xué)生會(huì)館買書,可到了傍晚,卻還要忍受他們滿房煙塵斗亂,學(xué)起舞來(lái)咚響震天。
1905年《東京留學(xué)界紀(jì)實(shí)》所刊《揚(yáng)子江之質(zhì)問(wèn)》,講一位留學(xué)法政速成科的中國(guó)學(xué)生竟不知揚(yáng)子江在何處,此文作者不禁哀嘆,這些學(xué)生年齡基本都在20歲以上,這樣的淺顯常識(shí)都不知道,實(shí)屬不該。而更有甚者,還有一名為李炳吉的直隸候補(bǔ)知府,竟攜一女子同往游學(xué)。
除了法政速成科的人員駁雜之外,法政速成科的教育也存在明顯不足,雖然其時(shí)短效速,能在短期培養(yǎng)人才,但因其在學(xué)時(shí)及教學(xué)內(nèi)容設(shè)置上的先天不足,所培養(yǎng)的亦是粗通近代法政知識(shí)的“半成品”,因此國(guó)內(nèi)外對(duì)其的詬病也一直存在。
但真正加速速成科之消亡的原因,在于清政府的顧慮。中國(guó)社科院法學(xué)研究所副研究員孫家紅將法政速成科稱之為“清國(guó)的雙刃劍”,事實(shí)上,清廷一方面向日本派遣留學(xué)生,一方面又警惕留日生的革命運(yùn)動(dòng),而以胡漢民、汪兆銘、宋教仁為首的法政速成科學(xué)員的革命活動(dòng)逐漸引起注目。
爆發(fā)于1905年末的“留學(xué)生取締規(guī)則”的大規(guī)模抗議運(yùn)動(dòng)是法政速成科第五期學(xué)生中畢業(yè)生占少數(shù)的原因。該規(guī)定是日本文部當(dāng)局應(yīng)清政府之邀而頒布,其條款規(guī)則不僅對(duì)留學(xué)生私生活進(jìn)行干涉,且指向那些從事革命活動(dòng)而被定性為“性行不良”的革命分子,這無(wú)疑是從事革命活動(dòng)的留學(xué)生頭頂一把“懸頂之劍”,日本文部省的做法激起留學(xué)生們的極大憤慨,留學(xué)生們舉行同盟并罷課,要求文部省撤回規(guī)定,在未果之后,一部分留學(xué)生選擇回國(guó)。
1905年12月7日,《東京朝日新聞》刊載評(píng)論指出,八千六百余名留學(xué)生同盟罷課,成為當(dāng)下最大問(wèn)題,是由于清國(guó)人特有之“放縱卑劣”意志所引起。對(duì)此,以《猛回頭》、《警世鐘》、《獅之吼》等聞名于世的同盟會(huì)重要成員、法政速成科第二期學(xué)員之陳天華,將其“絕命書”郵寄清國(guó)留學(xué)生會(huì)館干事長(zhǎng)楊度,12月8日于大森海岸投水自殺,以示抗議。
對(duì)留學(xué)生速成教育的議論紛紛,加上晚清政府為防止留學(xué)生從事革命活動(dòng)而加強(qiáng)了對(duì)留學(xué)生的監(jiān)視和限制。1906年,梅謙次郎在征求清政府的意見(jiàn)后停止了招收速成留學(xué)生的工作。1908年4月,法政速成科第五班學(xué)生畢業(yè),至此,法政速成科正式宣告結(jié)束。
雖然法政速成科的教育存在種種不足,但在1904年至1908年間,法政速成科為中國(guó)培養(yǎng)了大批新式法政人才,大多數(shù)畢業(yè)生回返中國(guó),以全新面貌投入到時(shí)代變革大潮中。
“日式洋快餐”之“消化”
有研究者指出,從清末到民國(guó),活躍在法律界各個(gè)領(lǐng)域的專業(yè)人士,從官員到司法人員到教育研究者,十有八九都是留學(xué)生,而像夏同龢、汪兆銘、陳叔通、程樹(shù)德、居正、沈鈞儒等法政精英回國(guó)后所做的貢獻(xiàn),都足以說(shuō)明這一培養(yǎng)法律人才的速成班還是收獲了“意料之中或意料之外”的各種成果。
然作為《清國(guó)留學(xué)生法政速成科紀(jì)事》的編者之一,北京大學(xué)法學(xué)院教授李貴連對(duì)“法政速成科”對(duì)如今之作用有清醒認(rèn)識(shí),他將其比喻成一個(gè)“日式洋快餐”,既是“快餐”一物,就必定有“消化不良”、“營(yíng)養(yǎng)不均衡”的感受。
但不論對(duì)其“消化”如何,一個(gè)基本的事實(shí)不容否認(rèn),百年前的法政速成科竟能吸引數(shù)千留學(xué)生前往,正式畢業(yè)獲得學(xué)歷者達(dá)千余人,并能于歸國(guó)后,在政治、經(jīng)濟(jì)、法律、外交、社會(huì)、文化等方面表現(xiàn)突出,持續(xù)影響中國(guó)歷史數(shù)十年,這不能不說(shuō)是近代中國(guó)海外留學(xué)史上一大奇事。
“這些法政速成科學(xué)員以有限的新學(xué)知識(shí)未必可以造就一個(gè)民主富強(qiáng)、和諧有序的新國(guó)家,但足以摧毀一個(gè)專制腐敗、風(fēng)雨飄搖的舊體制。”孫家紅說(shu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