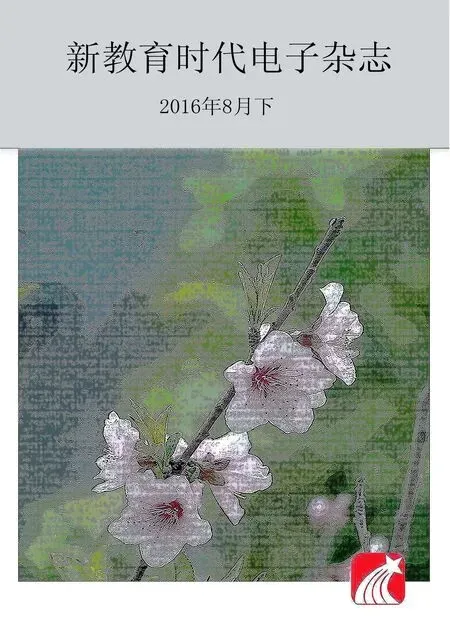得“意”不忘“言”
馬夏牧(南京市玄武高級中學太平門校區 江蘇南京 210016)
得“意”不忘“言”
馬夏牧
(南京市玄武高級中學太平門校區 江蘇南京 210016)
語文老師最基本的任務就是培養學生的語境意識,讓學生學會根據語境尋得文本的原意,得“意”不能忘“言”。用語文的方式教語文,還原語文學科質本潔來還潔去的樸素本質。語文學習在過程之中,沒有過程的語文學習是不具品質,也是沒有實效的。
語境 細節 思維
細看2016年江蘇語文高考卷,給語文老師的感覺就是:考的是“語文”。小到一道選擇題,大到一篇文章閱讀,命題組在每道題的設置上都在提醒我們這些一線老師正視語文教學思維。這種思維,是閱讀教學過程獨有的,而對于其他非語文學科來說,往往可以得“原意”而忘“原文”,只要大腦里有個完整的邏輯框架就萬事大吉。可是如果運用其他學科的教學思維來教語文,僅僅滿足于“原意”或者邏輯框架的獲得,那么我們就會誤入歧途。[1]
正如馬丁·海德格爾所說,“語言是我們每個子民得以存在的精神家園,也是一個民族得以棲居的游牧之地。”廣大語文教師應該高度認識到“原文”在閱讀教學中的重要性,不斷強化“原文”意識,對學生提供正確的引導和適時的指點,讓學生多親近原文,不厭其煩地讀原文,讀出原汁原味原意。
對于語文學科來說,文本的原意不能光靠語文老師的一張嘴和盤托出,也不能單靠語文老師提綱挈領地寫在黑板上,更不能只憑借影視的形式直觀地呈現出來——特級教師黃厚江曾針砭這種現象:“看影視多了,讀課本少了;其他活動多了,語言活動少了……什么PPT,什么鏈接,什么網絡閱讀……似乎大家都有一手。”可是我們不要忘了,語文老師最基本的任務就是培養學生的語境意識,讓學生學會根據語境尋得文本的原意,得“意”不能忘“言”。黃厚江老師一再強調,要用語文的方式教語文,我們要還原語文學科質本潔來還潔去的樸素本質。語文學習在過程之中,沒有過程的語文學習是不具品質,也是沒有實效的。[2]
一、觸摸語境,有所發現
在數學的課堂教學中,數學老師一般不大使用文本,而只需要遵循邏輯鏈條,以自己的“思維蘋果”與學生的“思維蘋果”直接交換。但如果在語文課上,用理科的思維教語文,架空分析,一步到位,學生不能靠語境讀出文本的原意,甚至曲解了原意,一葉障目不見森林,我們何以培養出一個“明白人”,一個“有見識的人”?
一次詩歌教學研討會上,南京市教研員徐曉斌老師就講了一個很多老師會忽略的例子:我們在教學學生鑒賞唐代詩人王維的《送沈子福之江東》時,會很容易把重點落在“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歸”這兩句名句的賞析上,但有沒有仔細玩味過“罟師蕩槳向臨圻”呢?“罟師”就是船夫,那為何不直接說“漁人蕩槳向臨圻”?再聯系詩的首句“楊柳渡頭行客稀”,我們可以想到詩人送別友人時的情境,江邊渡頭已變得行客稀少,可見送客的蘭舟之類早已遠行,只能請江邊打漁的艄公順路捎帶一程,于是這看似平常的字眼里卻可以讓我們深味意境的冷清,詩人的悵惘。只有有了這層鋪墊,詩人才會突發奇想:“我”心中的相思之情,也像這無處不在的春色,一直跟隨著“你”歸去。不必特意寫離愁別苦,別情已經充盈滿篇。
常言道,言為心聲。特別是文學作品中人物的“言”,需要我們仔細品味才能感悟其內心。如《雷雨》中周樸園父子三人相聚一段,各自用語言動作展示著自己的獨特形象。周樸園對魯大海的六次問詢:你叫什么名字?你有什么事吧?那么,那三個代表呢?他們沒有告訴你旁的事情么?你以為你們那些代表們,那些領袖們都可靠么?礦上的工人已經在昨天早上復工,你當代表的反而不知道么?以及周樸園拿出兩個文件等。韓軍老師就在課堂上讓學生多次朗讀,反復品味,交流討論父子三人的語言動作,體味周樸園“從容鎮定、胸有成竹、游刃有余、沉穩老辣”的氣度。
我們要知道,文本,一是以遵循文本的規定性為根本,任何個性化的讀解,都必須遵循文本的規定性,即一千個哈姆雷特還必須是哈姆雷特。有效的文本解讀在確立了解讀核心和原點之后,必當緊扣文本,以文本為基礎,以事實為根據,詳加驗證。一位老師在執教《琵琶行》時,這樣問:為什么淚濕了青衫?為什么白居易有那么多的淚水?一女生說白居易也有同病相憐之感,更能理解琵琶女。老師追問:除同情理解外,淚中還有什么?一生說,孤獨。老師卻沒有給學生闡釋的時間,而是繼續自己的動情演講: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還獨傾。這樣美好的景,卻獨飲,感到孤獨。還有他的所見、所聞,還有他長久的克制,用酒來克制自己。就像序言中的“恬然自安”就是他有意壓制自我的表現。這樣一個男人是注定悲苦的。人生的苦難或者是一種常態,面對苦難不要逃避不要傷痛,要學會等待學會堅強。在苦難面前的等待、堅強,才是我們活著的姿態。五年后,白居易不是被起用了嗎?面對苦難,哪怕等待五年、五十年,甚至一輩子……聽課到此處,明眼人很快就會意識到,這樣處理,《琵琶行》最后的落腳點竟然是面對苦難的態度,破壞了美好的詩境。[3]
同閱一卷書,各自領其奧。我們的閱讀教學應當規避文本解讀的虛化現象,在深層閱讀上下功夫,引導學生深入解讀文本,在閱讀的廣度上感受文本的文化意義,在閱讀的深度上探究作品的精神內涵和藝術特點,讓學生從文本表面進入文本內層。
二、聚焦細節,含英咀華
細節描寫被高爾基稱為“隱藏在文字里的魔術”,沒有細節就沒有藝術,細節決定作品的高度,細節決定作品的深度。細節描寫在文章看似閑筆或贅筆,信手拈來,無關緊要,可有可無;但都是作者精心設置和安排的,不容忽略。我們解讀一篇文章,如果抓住了細節,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氓》的教學過程中,在分析婚戀不同的階段反映女主人公不同的性格情感時,我們會引導學生關注文中一些有意味的細節,如寫淇水、桑葉、斑鳩的句子。臺州中學的一位學生在課堂上卻意外地發現女主人公在不同階段對“氓”的稱呼上——從“子”到“爾”再到“士”,最后干脆稱“其”。臺州的項琪老師馬上就發現這一細節的教學價值,根據稱呼的變化的這一細節帶領同學一起感受人物心理情感變化——從熱戀、新婚、到冷遇,再到最后決裂,不同時期、不同情感,使用的人稱代詞也不同,看似細微的人稱變化中竟然深藏著情感的洪波大浪。
美國作家海明威的代表作《橋邊的老人》是他“冰山理論”的代表作品,閱讀這樣一篇文章就需要好好引領學生尋找文本語言的空白點和斷裂處,探尋語言這片大海平面下的巨大基座,挖掘語言豐富的意蘊。金華中學的江艷玲老師就抓住一個常人都會忽略的細節——老人在回答問題時為什么特意強調“兩只山羊,一只貓,還有四對鴿子”?課堂上學生細細玩味這念念有詞的數量詞,感受到了老人那種博大深沉的情懷以及對生命的尊重和悲憫,老人是一個渺小而又偉大的天使。這就從一個很小的人物視角鞭撻了戰爭尤其是不義的戰爭所帶來的巨大災難和深重的罪惡。
因此,作為語文教師一定要自己先深入研讀文本,有自己獨特的閱讀收獲,再引領學生深入文本。當我們發現其中蘊含的教學資源和教學價值,然后引導學生品味、挖掘其中豐富的內涵,就可以更深入地走進人物的內心世界。
小說《一個人的遭遇》在莫斯科電臺廣播時,令大街上來來往往的行人駐足聆聽,當時寒風撲面,他們聽著聽著便淚眼模糊;在傳到我國后,又不知使多少人留下了心酸的眼淚,而這篇小說的譯者草嬰先生,也是噙著眼淚翻譯的。課堂上的解讀就可以濃縮到一個“淚”字,這里的“淚”不僅是載體,更成了情感的聚焦點,可以此為突破口,讓學生體會。如文中的“淚水浸枕”。正所謂男兒有淚不輕彈,即使像索科洛夫這樣堅強的人也難以撫平心頭的創傷,這說明戰爭給他帶來的創傷是那么的刻骨銘心。他不斷地做夢,夢見妻子和兒子,跟他隔著一道鐵絲網,這鐵絲網是帶刺的,戰爭給他帶來的痛就像這鐵絲網上的刺一樣,深深地扎進了他的心里。那種家破人亡帶來的心靈創傷是什么也無法彌補的,即使重新又有了一個新的兒子也不能。即使無數次地暢想自己與凡尼亞的美夢也無法遏制這個噩夢的出現。
正如一滴映出了太陽光輝的水和一片見證了肅殺清秋的枯葉一樣,文本細節往往能揭示出事物重大的本質特征。所以,在我們分析一篇文章時,只有強化文本細節的捕捉,用心聆聽文本的細節價值,緊扣文本對話,才能真正體悟作者的情思,從而點亮語文課堂。
三、結合文本,提升思維
文本研習要以走進文本為經,以聽說讀寫思為緯,讓學生思維聚焦文本,深入透徹理解文本,從而培養其閱讀能力,提高語文素養。思維不聚焦,就會嚴重影響閱讀教學的有效性。
學生在閱讀中常常會遇到障礙,老師如何指導學生突破,因人而異;但方法巧,用力少,效果好,卻是最佳選擇。符合這一標準的不是老師直接說出答案,而是“相機誘導”,巧妙點撥,做到“四兩撥千斤”。相機,就是在學生處于“憤悱”之境,才給予點撥。如學習《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學生對運用佛貍祠的典故不理解,這時便可投影“耶路撒冷的哭墻”的掌故:“耶路撒冷的哭墻是猶太王國第二圣殿圍墻的一部分,羅馬人在毀城時為了保存自己的勝利證據故意留了下來,而猶太人認為是民族恥辱。以后,千百年來流落異鄉的猶太人一想到這堵墻就悲憤難言。直到今天,每年紀念日,猶太人仍到哭墻前,號啕一片。”通過這一材料的引入,可以讓學生借以理解辛詞中用典的作用。
文本解讀,不是脫離文本的“信馬由韁”。現實中,有的課堂生成過多,轉移了學習重心,如有位教師上《念奴嬌·赤壁懷古》,講到“小喬初嫁了”,就聯想到大喬,從而得出周瑜與孫權特殊的君臣關系,才成就事業。然后又投影杜牧“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的詩句,饒有興致地講述諸葛亮曲解曹植的《銅雀臺賦》,故意激怒周瑜的故事,學生聽得津津有味,但已經忘記了詩詞,而沉浸在三國故事中。脫離了文本,還能叫思維聚焦嗎?就如紀伯倫所言:“我們已經走得太遠,以至于忘記了為什么而出發。”
在學生閱讀過程中,對學生的疑難,老師可以相機引證材料,進行點撥;但這材料一定要精當且必需,否則,會使學生的思維分散,或者轉移到材料上,而忘記了文本中的疑難。常見的弊病是,有時不需要引證材料卻引證,如學習《前方》,在理解第3節時,某位教師投影電視上動物遷徙的畫面,讓學生觀看。將學生的思維從文本拉向了動物世界。這樣喧賓奪主,學生的思維無法聚焦在文本上,而是在大量的多媒體展示中消弭殆盡。
人民教育出版社著名編審溫立三說:“多媒體有時候像一塊‘遮丑'布,掩蓋著教師基本功的不足;赤手空拳能把語文課上得有聲有色的教師,倒能顯出他的真‘功夫'。”身為語文老師,我們的課堂關注點必須定位在學生的表達能力,發現能力和思辨能力的培養和發掘上。讓學生在充分的傾聽、自由的言說、有效的質疑基礎上,憑借自己的知識、情感、智慧、靈性,對外在信息進行選擇、加工和處理,自發地形成對新信息的意義的創造性建構和對原有經驗的改造和重組。走進課堂,我們發現,在探究文學作品中人物思想和形象時,很多時候學生雖然能表達自己的觀點,但浮于表面,少有切中肯綮、深入實質的分析。特級教師李仁甫在執教《漁父》時,讓學生用幾個關鍵詞概括描述屈原的思想,并提出了自己的指導性意見:“我們在回答問題時,要力求用簡潔的語言,盡量不用文中的原始語言,尤其是不要用形象性的語言,因為這些詞只有在語境當中才能凸顯意思。”這種順應學生個體的特點和需求去啟發、鼓勵并加以方法上的引導,方能充分釋放和提升學生的求知欲和思辨力。在引導學生欣賞《滄浪歌》時,李老師通過言語內容是否可以互相調換、重新組合的嘗試,將學生的思考引向了深入,使學生突破了思維的障礙,從而深刻理解了屈原與漁父之間“取義”與“守真”的價值取向的區別。
張志公說:“教一篇文章,必須讓學生透徹理解全篇思想內容……帶領學生好好地讀這篇文章,一字、一詞、一句、一段地都讀懂,把文章的安排組織都搞清楚,讓文章本身去教育學生。”通過對文本的精讀研讀,玩味品咂,披文入境,披文入情,從而提高閱讀素養和審美境界。所以教師的第一要務就是要千方百計使學生的思維專注于文本,觸摸文字,分析語境,品咂語言,真正做到“一字未宜忽,語語悟其神”。
[1]李仁甫. 課堂的風景與語文的邊界[M]: 江蘇鳳凰教育出版社, 2014
[2]浦培根.動態生成課堂:從設計、生成到評價[J].語文教學通訊,2016,(1)
[3]朱昌元.“生成”的藝術[J].語文教學通訊,2016,(1)
[4] 陸亦斌.生成課堂的關注點[J].語文教學通訊,20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