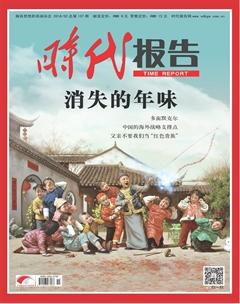魯迅的“暗功夫”
孫郁


編者:2016年是魯迅逝世80周年。毛澤東說,魯迅是“中國的第一等圣人”,而德國漢學家顧彬曾說“中國當代文學大部分是垃圾”,可他對魯迅獨具青眼,譽魯迅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
魯迅的成就,與他是個雜家有關。劉思源先生說那是“暗功夫”,是知人之論。而這功夫之一,乃美術鑒賞與研究。其內在的因素給魯迅文字的支撐力,是不可小視的。
一
我們有時候閱讀魯迅的文本,有種快意的感覺,那大概是美學所講的神思吧。他對美的感受,是跨在文字與色彩間的。這個習慣在幼年就養成了。他對插圖、碑帖、雕塑都有興趣。在那些古舊的世界間找到精神的飛翔之所。圖像的美與文字的美各得妙意,美的意蘊在此流溢著。早期的魯迅對藝術有整體的看法,對文學與美術是一起討論的。這個看似混沌的審美意象,給他帶來的好處,在后來愈發明顯了。
有趣的是他對美術的興趣是跨越中外的。他對現代美術品的注意,始于日本。西洋繪畫與日本浮世繪對其的引力可以想見。也恰是與西洋繪畫的對比才知道故土的藝術的問題,優劣也歷歷在目矣。西洋與東洋的美術,讓其反省故國的美術史的邏輯。而重塑美術圖景的沖動,在他那里是從未消失的。
審美是復雜的心理活動,古人的經驗給他的參照,無意間被應用到小說與詩文里了,其中楚文化的夢幻感對其頗有吸引力。郭沫若《魯迅與莊子》談到了其中的承接點,那多是文字上的考察。其在繪畫的領域,亦有心得。魯迅對南陽漢畫像之感受,多有神筆。大量收藏中,妙品甚眾。楚風浩大,“其來無跡,其往無涯”,林野間“汪洋辟闔,儀態萬方”(《漢文學史綱要》)藝術貴于大氣,于天地間見人心,在心懷中有日月。以詩與哲、詩與畫入文,其境界就非一般儒生可比。
古人的思維里,混沌里藏著寓言。光線、音律諸因子散落著情思,詩文和繪畫都保留了此一特點。魯迅意識到了這些,其審美的律動就借助了其間的因素。或可以說,他喚起了這些因素,成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在受到了現代科學的沐浴后,審美的路向有了變化。一是有確切性的思維,那里邏輯性強,是沒有模棱兩可的一面的。二是神識的思維,憑著直覺進入對象世界,幽微的存在紛至沓來,心靈廣袤而遼遠。這二者交織在一起,便有了奇異的偉力。兩者不同的思維,在魯迅那里是統一的。也因此,他喚起了冬眠的古老詩意,把舊的藝術形式激活了。
19世紀以后的美術,與哲學、文學共舞,出現了許多大人物。此后畫家與作家間互往的故事多多,不勝枚舉。作家諳熟美術者很多,勞倫斯、夏目漱石等都是。勞倫斯論畫,能入肯綮;夏目漱石本身就有丹青之技,是詩畫俱佳的人物。看魯迅日記,他與陳師曾、司徒喬、陶元慶的交往,在畫壇留下的足跡,都值得一思,和法國知識界那些大人物相比,毫不遜色。那里的故事,讓我們這些后人總能夠神往而羨佩。
像林風眠、劉海粟、吳冠中這樣的畫家,是很看重魯迅的。他們在魯迅那里,得到了美術那里沒有的美感。文字中的美感,恰有畫家欲求而不得的內蘊,意象通向更為遼遠的世界。古代畫家從詩文里獲得的靈感何其之多,白話作家給丹青妙手的啟示則十分有限,唯魯迅有微末的幽思,讓畫家如進圣潔之所,可悟之境多多矣。他把文字與繪畫的優長演繹成文字,故有傳神的筆意與靈思。那是畫家與詩人都想求得的神思。魯迅盡攬于懷中,可謂大境界也。
魯迅參與美術的活動,很少寫到文字里,譯介的美術品無數,卻沒寫幾篇美術研究的文章,而只言片語中卻有高論飄然而至,都是不可多得的箴言。其實那些言詞都非天語,乃厚積薄發之心音。對美術的真心喜愛,又無功利之心,便有敬意涌動。他的生命,浸泡在此間,周身都是美麗的光環。也唯其如此,在丑惡的事物面前,毫不畏縮,以圣潔對齷齪,便有凜然之氣在。其美也柔柔,其思也邁邁。神乎其姿,妙乎其意矣。
二
大凡了解魯迅著作的人,都能從其作品中感受到陽剛的力量。說他是中國真正的男子漢,不是夸大的比喻。他的作品有一種力之美,在昏睡的夜里忽然注入強烈的光澤,擊退了絲絲寒意。他厭惡奴態的語言,有一種沖破陰暗的浩氣。在散文隨筆里,那些批判性的言論,都撼動著俗世的圍墻,一道道偽道學的防線就被擊退了。
這個特點在他留日時期的文字里就可見到了。那一時期所接觸的近代哲學與藝術,給他沖擊大的是摩羅詩人的恢宏、勁健之氣,一洗雜塵,閱之如履晴空,四面是燦爛的光澤,就有了一種對強力意志的渴望。那是通過對尼采、克爾凱廓爾的閱讀而得來的神思。《摩羅詩力說》在審美的向路上有一種沖蕩之氣,給人以不小的震撼力。摩羅詩人有如此的偉力,乃心胸開闊、心性放達之故。中國古代曾有類似的狂士與斗士,后來漸漸消失了。魯迅原先以為只有西方有此剛健之士,后來整理遠古的遺產,才知道那些古已有之,只是與洋人的背景不同罷了。他后來寫小說和散文,保持了對力量感的堅守。比如《故事新編》《野草》,不乏氣勢恢弘之所,常有奇語出之。像《野草·復仇》寫出慘烈的力,在灰暗中升騰著不屈的骨氣:
然而他們倆對立著,在廣漠的曠野上,裸著全身,捏著利刃,然而也不擁抱,也不殺戮,而且也不見有擁抱或殺戮之意。
他們倆這樣地至于永久,圓活的身體,已將干枯,然而毫不見有擁抱或殺戮之意。
……
于是只剩下廣漠的曠野,而他們倆在其間裸著全身,捏著利刃,干枯地立著;以死人似的眼光,賞鑒這路人們的干枯,無血的大戮,而永遠沉浸于生命的飛揚的極致的大歡喜中。
他對漢唐氣魄的把握,亦有別人不及之處。比如談及漢代畫像,認為其蒼潤淋漓,是大有風骨的。他喜歡漢代造像,所搜集的《東官蒼龍星座》《象人斗虎》《象人戲獸》《白虎鋪獸銜球》,都很大氣,遒勁、奔放的旋律讓人心動。
漢代文化,還沒有泛道德的影子,思想還有空隙,民間并未都被污染。他后來鐘情于漢畫像的搜集,是有很大的期待的,我們說那是一種復興的夢,也未嘗不可。他所欣賞的司馬遷、枚乘都有偉岸的一面,天馬行空的飄逸,向著神思之處聚攏,燦燦然如午日之光,普照蒼穹。這些都暗自內化在他的世界里,文字銅鐘般回旋在山野之間,歷史與今天的對話空間是異常廣闊的。
他不止一次談到漢唐氣魄的問題,并說日本的浮世繪模仿了漢代造像,那里也有對祖先文明追憶的快慰。他所搜集的漢魏碑帖,大多是蒼勁的,氣韻絕無柔弱之態。他曾親自摹寫過羅振玉編輯的《秦漢瓦當》,感興趣的恰是那天然曉暢的流線、神靈飛動的舞姿。這些后來都暗射到他的趣味里,行文無意間天風散落,爽然如秋意之繚繞。文字有大荒原里的曠遠,亦多暮色里的恢宏,和那些拘泥在小情調里的酸腐文人比,真的是巍巍乎壯哉了。
三
在他沉默的時候,我們也能夠聽到他憂郁的聲音。不能不承認,對底層人的悲憫之情,以及自我的焦慮,給他的文字帶來了一種沉靜、痛楚的韻味。你能夠在許多地方讀出他孤獨的心境流露以及淡淡的悲傷。這是天性里的聲音呢,還是后天修煉使然?我們常常被其敘述感染了。在《故鄉》《狂人日記》《孤獨者》那里,絕望和反抗的東西俱在,讀者會因之而心神俱動。《孤獨者》寫魏連殳死后“我”的感受:
敲釘的聲音一響,哭聲也同時迸出來。這哭聲使我不能聽完,只好退到院子里;順腳一走,不覺出了大門了。潮濕的路極其分明,仰看太空,濃云已經散去,掛著一輪圓月,散出冷靜的光輝。
我快步走著,仿佛要從一種沉重的東西中沖出,但是不能夠。耳朵中有什么掙扎著,久之,久之,終于掙扎出來了,隱約像是長嗥,像一匹受傷的狼,當深夜在曠野中嗥叫,慘傷里夾雜著憤怒和悲哀。
《孤獨者》以憂郁始,也由憂郁終。一點明火的燭照都沒有了。同樣憂郁的是《傷逝》,幾乎沒有暖色,一切都是灰暗的。那種憂郁里有對生命的嘆惋,及其微末的期冀,能夠在此感受到強烈的痛感,還有揮之不去的煩惱,都非關乎己身的獨語,有的是撫摸同類的憂戚。這時候在其敘述里能夠諦聽到耶穌般的柔情。天太寒冷了,在那悸動里傳來的嘆息,仿佛一縷光線穿透了我們的心。
許多自語般的文字里,都有他難以排遣的焦慮。用他自己的話說,內心太黑暗了。古人憂傷的詞語也傳染了他,杜甫、陸游的文字都在此間能夠看到一二。在他所譯的加爾洵、安德烈夫、阿爾志跋綏夫的文章,都有揮之不去的哀愁。后來他在自己的寫作里,也不自覺地染有這類感傷的調子,在他眼里,這也是內心不能去掉的存在。
但他不都是沉浸在憂郁里,內心是厭惡這種憂郁的。當意識到這種憂郁有病態因素的時候,便以自嘲的語氣消解之。他常常從憂郁中走出,以對抗的姿態面對舊我。這時候就出離幽怨了,有了動感的輻射。這讓人想起普希金的詩句,在惆悵的旋律里,奔騰的愛意和飛渡苦楚的激情,就把那些暗影驅走了。
他在介紹尼采、托洛茨基的文章時,感動于那種在絕望后的決然。不滿于自己的狹窄化的時候,精神的角斗就出現了,不斷和自己內心的暗影抗爭,擺脫鬼氣和萎靡之氣,就有了異樣的回旋的張力。許多研究者都看到了此點,一些專著對此都有深入地思考。的確,憂郁背后的那個存在對他十分重要,那是與其他感傷作家不同的存在。《過客》借著主人翁的口說道:
那不行!我只得走。回到那里去,就沒一處沒有名目,沒一處沒有地主,沒一處沒有驅逐和牢籠,沒一處沒有皮面的笑容,沒一處沒有眶外的眼淚。我憎惡他們,我不回轉去!
一方面是糾結不已的惆悵,另一方面又是從其間出走的沖動。沉浸在死滅的寂寞不久就被搏擊的快慰代替了。那是一種新生的可能么?抑或別的什么?一切都那么真實,又那么帶有召喚的力量。憂郁產生于無奈和孤苦的環境,人都難以擺脫它的襲來。作者對此毫不保留,就那么真情地裸露著自己苦楚的心。可是一面又時時從這種絕望的地方位移,走向遠離它的地方。
晚年介紹珂勒惠支版畫的時候,那些含著淚的畫面,不能不說也都是一種呼應。他解釋這些作品時,內心對畫家是認可的。但珂勒惠支對他最重要的是憂郁背后的沖動,于毀滅間不失的靈動之氣。因為唯有大愛者,方可以見不幸而垂淚,臨深淵而凜然。想起他內心黑白分明的個性,人們怎么能不感動呢?
四
曾經說過古文很多壞話的魯迅,其實很有古風。他身上舊文人的氣韻,催生了諸多奇文。要不是與西洋文明相遇,魯迅可能是另一個樣子。他身上的古雅的意味,從未消失,在與尼采、契訶夫相逢后,精神變得渾厚了,但那種古樸的因子,卻頑強地保留下來。他那么喜愛晦澀的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自己面對中國問題時,卻退回到吳敬梓、蒲松齡的道路了。在小說中,他借鑒了古小說的理念,以白描的手法隱含深意,大有快意。那些對風情的描摹,猶如古畫一樣靜穆有趣。他所譯的作品,艱澀、幽玄者頗多,而自己動手寫作時,則沒有西化的痕跡,完全中國化了。
有時他的筆端含有漢代的高遠之氣和六朝的蒼冷,有時則見明清以來江南水鄉的詩境。《阿Q正傳》《孔乙己》都是白描,但舊街市與店鋪間的人情世故,傳神地表現出來。那是寧靜的畫面,中國古老的鄉鎮凝固在一種死滅中,而當我們的作者沉浸其間的時候,偶能見到古奧里的一縷新風。那些爽意的吹拂,蕩去了霧氣,顯示了道路的深。一個謠俗里的詩意就這樣蠕活了。
《朝花夕拾》里多次出現鄉村賽會的美,紹興古劇里悠揚的情思。鄉風里飄動著淳樸的青草的氣息,那里無疑有著一種眷戀。《故事新編》里流動的是高遠的精神遺響,莊子、老子、孔子時代的悖謬之歌,款款而來。中國古代的情思在其筆端是有的,從靜穆里發現奔流的喧嚷也是有的。因為沉靜,故可以抵擋流行色的誘惑,也因為古樸,文章與詩境就有了悠遠的余韻。
魯迅的古風還體現在小品里,開現代書話另一條路。他不太愿意像周作人那樣沉浸在舊書的描摹上,害怕的是染上象牙塔氣,可是有時候也偶爾涉足于此,不過不是賞玩其趣,而是和古代的幽魂糾纏,乃另一心境的閃現。借談古人,實則寫今世恩怨,還是與現實對話的。
如果放棄對現實的對話,只在象牙塔里看人看世,他一定會寫出比周作人更古雅的作品。他偶爾涉足古書和藝術品題跋,已有不凡之筆。比如《書的還魂和改造》《隨便翻翻》的天然麗質,《買〈小學大全〉記》的老到,等等。文字是白話的,背后卻有古典的韻致,給漢語言發展帶來了諸多啟發。他文章的散淡古樸之美,對后來的小品文作家頗多影響。黃裳、唐弢、文載道、舒蕪都受此風所誘,即便是白話八股文四溢的時候,也沒有去其古意,堅守舊文人的品格。在文體上,魯迅的豐富性是周作人、林語堂諸人均不及的。
如果說這種古風是一種美的話,它與明清的文人是不一樣的,和民國的學人也是有別的。同樣是運用古文,魯迅已經把它過濾過了,在外文的語境里洗刷過,也受到了民間話語的沐浴吧。于是那些文字獲得了一種新意,如此明亮,如此豐饒,又如此不飾雕飾。古樸是一種境界,新文學的作家解此意者,真的寥寥無幾。
魯迅是一個帶著奇妙的美意進入漢語世界的人。他遠采漢唐之韻,近得民間之夢,旁及域外之魂,以寫實而通幽玄,因戰斗而獲柔情,于喧嚷中有靜謐,在無望中得自由。因為有了魯迅,中國的審美地圖被改寫了。此后,我們才擁有了能與世界真正對話的真人,有了可以炫耀的新文藝的傳統。我私自以為,一卷魯迅著作在手,乃天地間最大之快活。與之為伴,方能隨其吟之舞之,入詩意之境。在無趣、無智奚落著大眾智商的時代,有了這樣的詩意,我們的世界還不至于荒涼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