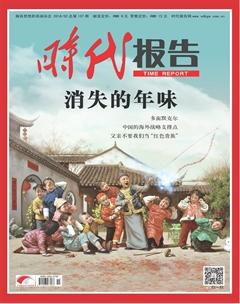和李克強握手照上了雜志封面
范慶鋒
頒獎結束以后,會議組織者通知我們,時任團中央第一書記李克強要接見大家,地點是團中央會議室。
我們到達團中央時,離原定見面還有一段時間,會議組織者讓隨行的中國青年報記者李建泉給大家在團中央大門口合了影,然后就根據會議組織者的引領到了團中央會議室。
約定接見的時間到了,只見李克強同志由團中央宣傳部的同志陪同走了進來。坐在靠門口的應該有劉健、張延平和趙彬。我和貴州的盧程坐在會議桌的中間位置。不知道為什么,李克強和前面幾個人握手時,中國青年報攝影記者李建泉的相機一直按不下快門,只是到了我面前,和我握手時聽到快門“咔嚓”了一聲。此后,再也沒有聽到李建泉手持相機的快門有響聲。就這樣,李克強和我握手的照片就成了唯一,后來刊登在了《青年報刊界》的封面上。
若干年后,河南文藝出版社的一位負責同志見我時對我說,“我有一本刊登李克強和你握手照片的雜志,我是從那本雜志上知道你被評為首屆全國青年報刊十佳記者的。”他說,“我一直珍藏著”。
當時印象中我也保存過一本。但后來辦公室幾經搬動,一時沒有找到,期間,我也動過向河南文藝出版社那位朋友索要那本雜志的念頭,但仔細想想,君子不奪人所愛,也就作罷。可能是老天作美,在后來一次搬動辦公室時,我意外地找到了那本雜志,趕緊把握手照讓報社照排室的同志掃描下來,在出版我的新聞專著《做有思想的媒體》時作為珍貴資料放了進去。為此,出版《做有思想的媒體》一書的出版社的負責同志還提出過涉及國家領導人的要作為重大選題上報的問題。
李克強同志接見我們大家后不久,就來到河南就任省長,報社總編輯也曾提議說,是不是去拜訪一下李克強同志。我仔細想想,我是做記者的,不能因為和李克強同志有過一面之交就去打擾他,也就作罷。而且,直到李克強同志在河南先省長后省委書記,再到遼寧任省委書記和到中央擔任領導職務,也沒有動過去找他的念頭。
李克強同志接見之后,按照原定日程,我們一行十幾人要到陜西西安去采訪。在采訪過程中還發生了不少有趣的事情。
上海《青年報》的王建敏的經歷和我有點相像。所不同的是,他是因為在工廠寫新聞報道出色而被選調到了報社,而我則是從農村基層因為熱愛新聞報道而進了新聞單位。說來也巧,當時安排我們兩個每天都住在一個房間。晚上閑聊時,王建敏先說河南人這不好那不好,我一時來氣,就說,你們上海人有什么好的,坐公共汽車,還要看看站牌上標的價格,如果從所在站坐車要一毛二分錢,而下一站只要一毛錢的話,上海人寧肯走路到下一站坐車,也不想多花那二分錢。當時,全國收入水平都不是太高,我說的是真事,上海人就是非常精于算計。我還揶挪揄地說,你們上海人買個香菜,什么時候都不是論角,每次都是幾分幾分的買,小氣死了。這一說不當緊,一下激怒了王建敏,他從床上跳起來,幾乎要和我動粗。
第二天,一向非常和睦的我倆誰也不跟誰說話。同行的《中國青年報》等北京的幾個同志說,你們兩個關系那么好,今天是怎么了?我如實把頭天晚上發生的事情說了一遍,他們也跟著起哄起來。
說真的,在此后的歲月中,除了趙彬給我寄過寧夏的特產枸杞外,相互之間聯系最多的還是王建敏和我。有一次他從上海到鄭州參加一個全國性的會議,通過大會秘書處找到了我的聯系辦法。我們通了電話。遺憾地是那天我在外地出差,而第二天他則要離開鄭州,沒有得以在鄭州見上一面。
又過了幾年,偶然從網絡上發現王建敏已經調到了上海人民廣播電臺,我在他博客后面給他留言,我們因此又聯系起來。他給我寄來了他的第三部著作——《分享走過的路》。這時恰逢我的新聞專著《做有思想的媒體》即將交付印刷廠印刷出版,我想,屆時我也應該回贈一本書給他。
當年評選十佳青年報刊記者時,每個獲獎者都有各自的特點,對此,當時的全國青年報刊協會副秘書長武志蓮老師說得非常到位。我們不妨在20年過后再來回味一下武志蓮老師的點評。
武志蓮老師說,在本單位他們都是業務骨干,他們用筆勤奮耕耘,每個人都有百萬字以上的作品,而且不斷有好新聞、好作品問世。他們熱情謳歌改革開放的時代,弘揚開拓進取精神,維護青年的合法權益,根植改革開放時代的共青團工作;他們嫉惡如仇,鞭撻丑惡現象;他們不斷追求業務上的獨創和創新,力爭能不斷超越自己。
武志蓮老師評價說,體育記者馬年華,21歲進入中青報,獲獎多達20多次,被人稱為“獲獎專業戶”。女記者趙彬,作風踏實,能吃苦,去寧夏貧困山區一呆就是半月20天。她曾因揭露逼死人的罪犯,面對尖刀坦然自若。她挺身而出為四名青年伸張正義,最終戰勝邪惡。她作為一名地方青年報的普通記者,兩次榮獲全國新聞獎。《黃金時代》女記者溫眉眉長于理性思考,她喜歡躺在草坪上與打工妹喝著汽水談天說地。她的采訪對象,最后都成了她的好朋友。因此,她筆下的女性個個絲絲入扣,有深度……如此等等,當我在修改這一章節,找到當年那本雜志,重讀武志蓮老師的點評時,當年那些事、那些人都栩栩如生地走到了我的面前。我難忘同他們短短的相聚,更想知道,20年后,他們都在哪里,都在什么崗位上工作,他們是不是有了更多的建樹。我祝福他們,也期望有一天能與他們重新相聚。
20年過去了,在寫作此書之前,武志蓮老師造訪我新調任的雜志社時,我曾對武志蓮老師說,20年前我對你的承諾至今還沒有兌現,但是我一直牢記在心。
那個承諾就是在首屆十佳記者頒獎會后不久,有一次遇見武志蓮老師,武志蓮老師說,想再搞一屆十佳記者評選,屆時看能不能運作一部分資金,讓當選者每人都得到一定的獎勵。我當時曾不假思索地對武志蓮老師說,這個由我來辦。
但愿這個愿望能得以實現。(本文選自作者《白紙黑字——一個新聞記者和眾多高官的恩恩怨怨》一書第十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