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時代法律如何保護新聞作品
金海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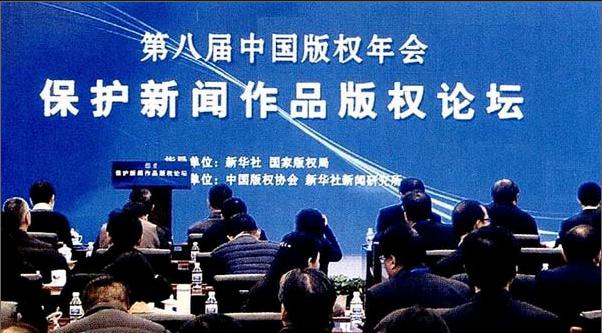
內容提要 在互聯網時代,特別是在移動互聯時代,每一個人部是新聞的使用者,但也可能是新聞的傳播者、生產者。所以在這個時代,人人都可能涉及到新聞和新聞作品的法律問題。
關鍵詞 版權保護 著作權 新聞作品 時事新聞
一、在著作權法上并沒有“新聞作品”的概念。
著作權法上的作品概念與生活中或者其他學科領域中的作品概念可能有所不同。從一張在網絡上廣為流傳的照片說起。
照片中是一只猴子對著鏡頭的臉部特寫。2015年9月,就因為這張照片而在美國加州引發了一場訴訟,各方當事人對這張照片是否構成作品,如果是作品誰是權利人而發生爭議。
實際上,這張照片是一只名叫Naruto的猴子的自拍照。事情是這樣的,英國一位野生動物攝影師David Slater到印尼蘇拉威西島上拍攝當地的野生猴子,他把相機架好之后剛走開,一群猴子好奇地湊過來,其中這只就對著相機鏡頭做出各種表情,拍出了一系列照片。
攝影師將這段故事上傳網絡,照片迅速走紅,還被收入維基百科。但問題來了,誰擁有這張照片的著作權?
美國的一個動物保護組織PETA認為,照片的著作權應該歸拍照的這只猴子,所以代表猴子提起訴訟。而攝影師認為自己為此花了很多錢,購買裝備,遠涉重洋到南亞的雨林里來尋找、拍攝動物,所以應當享有照片的著作權。還有一方是維基百科,它認為這張照片不應該有著作權,而是屬于公共領域。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案例,可以繼續觀察法院將如何處理。而形成爭議的原因之一是,法律上對于新聞作品是沒有定義的。在著作權法上只有“作品”的概念,而沒有“新聞作品”的概念。從法律的角度看,只能按照著作權法上作品的定義來確定爭議對象是否構成作品。
我國《著作權法》和《著作權法實施條例》對于作品有一個定義:“本法所稱作品,是指文學、藝術和科學領域內具有獨創性并能以某種有形形式復制的智力成果。”這一定義相對抽象,但其中有一點很明確,即作品必須是一種具有獨創性的智力成果。
關于如何確定獨創性的問題,有過一段很漫長的過程。美國最高法院1991年的Feist案判決,以及中國法院1994年在廣西煤礦工人報案的判決,對于像電話號碼簿、節目預告表這樣的事實數據匯編形式,闡明了著作權所保護的作品必須具備的條件:作品不僅是由作者付出勞動或者辛勤的投入獨立完成的,還需要具備“最低程度的創造性”。這個創造性的標準,就體現在作者對事實或者思想進行表達時的取舍、選擇與編排。
著作權法對作品的分類是按照表達的不同方式為標的,并不是按照表達的內容,例如是按新聞類、文學類還是藝術類來劃分的。著作權法規定的作品種類有:文字作品,口述作品,音樂、戲劇、曲藝、舞蹈、雜技藝術作品,美術、建筑作品,攝影作品,電影作品和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等等。所以,一個新聞作品從法律上講,可能是文字作品(文字報道與評論),可能是口述作品(電臺報道與評論)、攝影作品,也可能是視聽作品(電視報道與評論)。
新聞類作品涉及著作權保護爭議的,就需要放在這些特定的種類中加以認定,而不能籠統地稱之為“新聞作品”。
二、如何理解“時事新聞”不受著作權保護?
新聞作品一旦被認定為作品,當然就受到著作權保護,為什么還會有那么大爭議?
原因在于《著作權法》第5條的規定:“本法不適用于:……時事新聞”。時事新聞在法律上也有定義,它特別強調的是指通過媒體報道的單純事實消息。
《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5條規定:“時事新聞,是指通過報紙、期刊、廣播電臺、電視臺等媒體報道的單純事實消息”。這個用語和規定跟《保護文學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的規定一致,因為我國已經加入該公約,負有遵守國際公約的義務。
《伯爾尼公約》第2條第8款規定:“本公約所提供的保護不得適用于日常新聞或純屬報道消息性質的各種事實”(The protection of this Convention shall not apply fo news of the day or to miscellaneous facts having the character of mere items of press inforrnation)。它強調每日新聞或者各種消息、事實沒有著作權,“因為這類素材并不具備可以被確認為作品的要件”。但從另一方面看,“采訪記者和其他記者用于報道和評論的文字如果包含充分的智力創作成分,足以看做是文學和藝術作品,則是受到保護的。”
盡管在實踐中對于新聞作品與時事新聞有所爭議,但《著作權法》在此后的歷次修改中均未涉及這一條款。目前由國務院法制辦公布的《(著作權法)修訂草案送審稿》第9條第1款規定:“著作權保護延及表達,不延及思想、過程、原理、數學概念、操作方法等。”該條第2款規定:“本法不適用于:……(二)通過報紙、期刊、廣播電臺、電視臺、網絡等媒體報道的單純事實消息。”可見,它是把《著作權法實施條例》對于時事新聞的定義上升為法律,從而把“時事新聞”這個概念消解了,替換成更加明確的“單純事實消息”。換言之,不受著作權保護并不是對新聞的報道,而是純粹的消息與事實。如果這個修改草案能夠獲得通過,那么這方面的規定就可以更加明確。
這個修改草案的第1款實際上也是源于國際條約的規定。世界貿易組織《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TRIPS協定)第9條第1款規定:“著作權的保護僅延伸至表達,而不延伸至思想、程序、操作方法或數學概念本身。”《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條約》(WCT)第2條也有同樣的規定。我國也已經加入這兩個條約。而這些規定所體現的正是著作權法上著名的一條原理:“思想表達二分法”,即著作權保護只涉及表達,而不保護表達背后的思想、事實等等。
所以,新聞作品受著作權保護,不受保護的時事新聞是指“單純事實消息”。新聞和事實盡管不受著作權保護,但也不是可以隨意盜用。“對于寄生行為可以采取其他防范方法,例如,對從競爭對手那里竊取而不是向通訊社訂購新聞的報社,可以根據反不正當競爭法提起訴訟”。
在司法實踐中,法院在處理涉及新聞報道類著作權糾紛案件時是如何認定作品與時事新聞的呢?
我們來看北京海淀法院審理的“金報電子音像出版中心訴北方國聯信息技術公司著作權糾紛案”。案件的雙方當事人分別是“人民網”的所有者與“中華廣告網”的經營者,涉案對象是兩篇新聞報道。
第一篇報道主要介紹被采訪工廠采取的環保措施,包括工廠基本情況、具體措施、記者見聞、體會評論等;第二篇報道是對第36屆世界期刊大會活動的介紹,包括議題、出席人員、大會發言人照片和發言全文。
法院認為:“時事新聞,是指通過報紙、期刊、廣播電臺、電視臺等媒體報道的單純事實消息。‘單純事實消息是指對時間、地點、人物、起因、經過、結果等客觀事實的單純敘述,不包括作者的主觀感受、思想情感或修辭、評論。此種消息構成要素簡單,表達形式單一,且為滿足公眾知情權需要盡快傳播,因而不受著作權法保護。”法院認定第一篇報道構威著作權法上的作品,受到著作權保護,第二篇報道則是時事新聞,不構成著作權意義上的作品,因而不受著作權保護。
法院對于法律的適用需要經過解釋,因為法律條文是由相對抽象的概念和規則組成,在司法過程中,法官的作用就體現為如何準確地理解法律條文,進而適用到具體案件。
在上述案件中,法官對于“時事新聞”和“單純事實消息”這些概念就作了進一步闡釋,以便對照個案的具體事實予以適用。最高法院目前正在推行指導性案例制度,如果能夠將類似典型案例加以整理,形成關于新聞報道類作品與時事新聞認定的司法裁判規則和指導性案例,從而在實踐中引導各地法院適用,將非常有意義。
三、互聯網時代新聞作品保護的新形式
互聯網確實給生活帶來非常大的變化,包括所謂的“版權大戰”,也就是在傳統媒體、內容提供者和互聯網服務提供者、移動客戶端等等之間發生了許多著作權糾紛案件。
以2007年《新京報》起訴浙江在線一案為例,《新京報》指控后者未經授權轉載其作品侵犯著作權。這是網絡轉載傳統媒體新聞作品而發生的典型糾紛。原告向被告所在地杭州法院起訴時,被要求每一篇涉案文章立一個案,就是7706篇文章需要分成7干多個案件。這一處理決定引發大量不解和疑惑,認為既有浪費司法資源之嫌,也大大增加了當事人的維權成本。實踐中,互聯網上的轉載量往往非常之大,很難按這個要求來處理。
《著作權法》第33條第2款規定了報刊轉載的“法定許可”制度,即“作品刊登后,除著作權人聲明不得轉載、摘編的外,其他報刊可以轉載或者作為文摘、資料刊登,但應當按照規定向著作權人支付報酬。”這里有兩點需要注意:其一,本條規定有一個“但書”,即如果著作權人事先聲明不得轉載的,他人未經許可就不得轉載;其二,本條規定僅指報刊轉載,并不涉及網絡轉載,未經許可而進行網絡轉載的,仍可能構成侵犯信息網絡傳播權。
著作權法規定了對新聞作品的“合理使用”,因此,即“使用”是有條件的。《著作權法》第22條規定在l2種情形中可以進行“合理使用”,即“可以不經著作權人許可,不向其支付報酬”而使用作品。其中與新聞和媒體相關的情形是:“(三)為報道時事新聞,在報紙、期刊、廣播電臺、電視臺等媒體中不可避免地再現或者引用已經發表的作品;(四)報紙、期刊、廣播電臺、電視臺等媒體刊登或者播放其他報紙、期刊、廣播電臺、電視臺等媒體已經發表的關于政治、經濟、宗教問題的時事性文章,但作者聲明不許刊登、播放的除外;(五)報紙、期刊、廣播電臺、電視臺等媒體刊登或者播放在公眾集會上發表的講話,但作者聲明不許刊登、播放的除外。”
由此可見,首先,媒體刊登或者播放的是其他媒體已經發表的“關于政治、經濟、宗教問題的時事性文章”或者“公眾集會上發表的講話”,而不是所有的新聞作品。其次,作者可以事先聲明,未經許可其他媒體不得刊登、播放。
《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是依據著作權法制定的行政法規。在該條例的第2條規定:“除法律、行政法規另有規定的外,任何組織或者個人將他人的作品、表演、錄音錄像制品通過信息網絡向公眾提供,應當取得權利人許可,并支付報酬。”
同時,該條約也規定了網絡環境下的“合理使用”的情形:“通過信息網絡提供他人作品,屬于下列情形的,可以不經著作權人許可,不向其支付報酬:……(二)為報道時事新聞,在向公眾提供的作品中不可避免地再現或者引用已經發表的作品;……(七)向公眾提供在信息網絡上已經發表的關于政治、經濟問題的時事性文章;(八)向公眾提供在公眾集會上發表的講話。”
這些規定實際上是因應互聯網發展的新形勢,將合理使用的規則適用到網絡環境中。因此,網絡環境并非法外之地,網絡經營者使用新聞作品的,仍須遵守《著作權法》和《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的規定。
當然,在互聯網時代,法律對于網絡經營者,特別是網絡服務提供者也提供了一些特別的免責或限制責任的規定。《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為網絡服務提供者(ISP)規定了“避風港規則”,提供信息存儲空間或者提供搜索、鏈接服務的網絡服務提供者,如果按照“通知+刪除”的要求履行義務的,可以免責。《侵權責任法》也有類似規定:“網絡服務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時采取必要措施的,對損害的擴大部分與該網絡用戶承擔連帶責任。”】最高人民法院在相關司法解釋中也規定:“網絡服務提供者能夠證明其僅提供自動接入、自動傳輸、信息存儲空間、搜索、鏈接、文件分享技術等網絡服務,主張其不構成共同侵權行為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在實踐中,網絡經營者所提供的究竟是內容還是服務,也不乏爭議。特別是在一種新的技術或者商業模式剛剛開始時,更容易產生爭議。
例如,“今日頭條”使用其他媒體新聞報道的方式,到底是提供的鏈接服務還是屬于直接提供內容?從“央廣網”報道與“今日頭條”網頁的對比中,可以看到,兩邊的新聞報道在內容上完全一致,但“央廣網”原始網頁和“今日頭條”移動端網頁的不同之處在于,后者把前者網頁中的廣告全部消除了。盡管后者在網頁鏈接上顯示的地址是“央廣網”,所以看上去像是提供的一個鏈接,但是并沒有完整呈現原始網頁,就使原始網頁失去廣告機會,本來可能獲得的收益就無法實現。這種做法導致《廣州日報》社、搜狐、湖北日報傳媒集團等先后起訴北京字節跳動科技有限公司(“今日頭條”的經營者),形成一系列案件。當然,在國家版權管理部門和司法機關對相關案件的處理當中,“今日頭條”也與大量新聞作品或新聞報道提供者、經營者達成了許可協議。
在移動互聯時代,新聞內容的使用確實已經發生非常大的變化。不僅需要考慮保護的問題,實際上還有如何使用的問題,即如何以高效、低成本的方式讓新聞內容、新聞報道獲得傳送。同時,新聞作品的傳播與使用也是一個與市場和利益相關的行為。在這個過程中如何兼顧各方利益,可能是一個更為深層的問題。
在新技術、新媒體和新市場的條件下,新聞作品的保護與使用涉及諸多方面的改革與創新,諸如新聞作品的權利與歸屬、新聞作品的價值和實現模式、新聞作品的許可授權方式、新聞作品對公眾與社會的影響等。而明確的規則和有效的司法或執法措施是新聞與媒體進行改革與創新的重要基礎和法律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