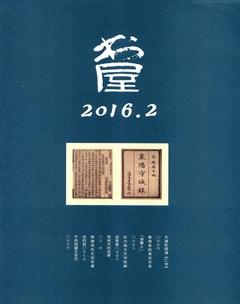天道輪回讀《仁學》
鄭佳明
今天我們紀念譚嗣同是為了向他學習,向他學習什么呢?實際上譚嗣同參加維新時間并不長,整個戊戌維新也才一百多天,之前他在湖南搞新政,時間也很短。他的一生大放光華、照耀后人的有兩件事:一個是他的慷慨就義,再加上他的詩,“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極大地放大了戊戌維新運動的影響和意義,喚醒時人,激勵后人。中國人畢竟都是惜命的,他主動放棄自己的生命來呼喚麻木的國人,驚世駭俗。他悲天憫人的情懷、劍膽琴心的大美,打動了億萬人。還有一個人——汪精衛也寫過這樣的詩,“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汪精衛沒做到,譚嗣同做到了。
他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寫《仁學》,梁啟超對《仁學》的評價很高,他說我們寫不出,我們也不敢寫。梁啟超說譚嗣同是這個時期學術和思想界的一顆彗星,他就是在中國思想啟蒙沒有開始之前的最黑暗的時候,天上劃過的一道流星,所以后來無數人都追隨他,到今天我們都得紀念他,而且會永遠的紀念下去。
一
我今天發言的題目是《天道輪回讀〈仁學〉》。為什么說天道輪回?《仁學》寫于1896年,到現在是兩個甲子,老話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兩個六十年應該是滄桑巨變。站在今天這個時代讀《仁學》,我在想,跟那個時代相比,我們的思想變了嗎,變了多少?法國歷史學家費南爾·布羅代爾十分重視歷史周期研究的意義,毛澤東、黃炎培也有著名的歷史周期問答,在歷史的節點上,這種思考是需要的。
取這個題目還有一個原因,與另一個瀏陽人胡耀邦有關。耀邦去世前的冬天曾經與朱尚同先生(時任湖南教委黨組書記)在湖南共同背誦《哀江南賦》,探討其中“天道周星,物極不返”的內涵。
《百年潮》記載了朱尚同的回憶:“耀邦問,你讀過《哀江南賦》沒有?我說,庾子山作的,我還背得出。耀邦同志高興了,說你起個頭。我背誦道:‘粵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陵瓦解……’耀邦同志也接著背誦,一直到‘天道周星,物極不返’。耀邦突然問,這兩句你怎么理解?我一下怔住了。耀邦說,一般以為,庾信是說侯景火燒臺城后,梁朝已矣,不可復興。而就自然和人事規律來說,物極總是必返的,說‘物極不返’,是庾信在梁亡后的悲憤之辭,是反意而用之。”
那是1988年11月27日的事情.當天晚上朱尚同步行幾條街爬六樓到了我家,激動地告訴我白天他與耀邦在九所聊天的情況。耀邦那天很放開,講了很多重要的思想,我們都很激動,很觸動。后來,德平同志陪李昭大姐從江西“共青城”到湖南來,長沙市委派我去湖南到江西的邊境迎接(我時任長沙市委常委、宣傳部長),當晚我在蓉園向德平報告了此事。朱尚同的回憶后來發在《百年潮》2000年第一期上。那天的談話,如果起個標題的話,我看可以叫《天道周星,物極不返》,那是所見的耀邦去世前一次較長的談話,他充滿了對黨和國家的歷史和前途的真知灼見,充滿了焦慮心情和憂患意識。
今天德平同志講,耀邦曾多次讀《仁學》。斗轉星移,耀邦關切的那些問題與《仁學》中闡述的那些問題一直在歷史中回響。我一直想再讀《仁學》,正好借著這個叫我發言的機會,又把它讀了幾遍。《仁學》的思想豐富,觀點龐雜,文字有點兒跳躍,可能是他思緒靈感萬千,筆跟不上,腦子來得太快。《仁學》是譚嗣同多年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厚積薄發,內涵深刻蘊藉久遠。讀《仁學》是在讀一股憂患家國的思想潮流,一段悲愴時代的歷史脈搏,一些跳躍奔騰的思想火花,一個新鮮熱情的生命。文中的思想火炬,映照著我們今天對歷史與現實的關切。一百多年來,中國人在“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路上急行軍,歷史上很多好思想都沒有來得及細想,更沒有時間回味。因為我們走得太快太遠,所以忘記了出發點。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歷史的節點上,應該回望自己的過去,回顧自己出發的原點,當初我們要到哪里去,我們還在這條路上嗎?歷史巨大的鐘擺,一定的時候會擺回來,尋找它本身的位置。我們年輕時候曾經批判伯恩斯坦“運動就是一切,目的是沒有的”,從布羅代爾的長歷史觀來看,我們應該一以貫之去追求當初的目標,至少是階段性目標。我們“沖決羅網”了嗎,實現了“仁”嗎?我說天道輪回讀《仁學》,就是從一個較長的歷史周期來追問以《仁學》為代表的戊戌維新時期改良思想的價值。
二
譚嗣同《仁學》的最偉大之處,是它打開千年“禮教”枷鎖,恢復了孔孟“仁愛”的真義,并賦予“仁”與時俱進的時代意義。康有為以“仁”為思想武器,發動了維新運動。譚嗣同與他相同,又不相同,兩人都在講“仁”,但是對待“仁”的另一面,也就是在對待“禮”的問題上,也就是對舊的禮教和秩序的問題上,譚嗣同超越了康有為。《仁學》對“仁”的闡述達到了中國思想界前所未有的高度。
什么是“仁”?孔子說,“仁者愛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孔子的仁愛精神,就是博愛、忠恕、尊重和平等,來自上三代中華先民的美好價值。孟子把這種價值用到政治上,提出“仁政”思想。最初的孔孟之道充滿了人文主義溫情和人道主義精神。但是孔子又講,“克己復禮為仁”。“仁”就有了另外一個注解“禮”。什么是“禮”呢?“禮”是“周禮”,是那個時代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規范、秩序,就是通過一定的禮儀形式維護“親親尊尊”的宗法關系和等級秩序,維護一種特定的不平等。“仁”是核心價值觀,講愛,講平等,“禮”是行為規范,講等級和親疏,講不平等,既矛盾又統一,兩千多年來二者的矛盾運動推動了儒家文化的發生、發展和衰弱。
孔子在強調“親親、尊尊”時候,仁愛被打了折扣,戴了枷鎖。開始還講,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愛妻順,雙方都有責任和義務。后來漢武帝董仲舒“廢黜百家獨尊儒術”,講“三綱五常”,“仁”變小了,“禮”變大了,專制等級強化,嚴重的不平等了。“仁”被打了第二道折扣,加了第二道枷鎖。到了宋明理學,“三綱五常”加了“存天理、滅人欲”,以佛、道規范人心,仁愛思想被打了第三個折扣,加了第三道枷鎖,“仁”完全成了道德責任和政治秩序。清王朝是少數民族政權,兩百六十多年統治者一直生活在政權合法性和穩定性的焦慮之中,綱常名教加上嚴厲的閉關自守和思想鉗制,以道德教化、科舉仕途、文學藝術推行綱常名教,愛情、親情、人欲、人性被森嚴的禮教扼殺,中國人失去了獨立的人格、自由的思考、人性歡樂、創新的能力,整體素質下降,民族精神沉淪,這是近代中國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兩千年下來道統、法統延續下來,人道、人性喪失殆盡,儒家思想被徹底閹割了。近代思想家中,譚嗣同最先指出了問題的要害,對“禮”、對“名教”、對“三綱五常”發起了猛烈的批判。他寫道:“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仁學·十四》)“三綱之懾人,足以破其膽,而殺其靈魂。”(《仁學·三十七》)
對于中國儒家文化的核心價值觀,譚嗣同的《仁學》有兩大貢獻:一是他站在仁愛的立場上,堅持這個中國古老珍貴的核心價值,同時把“仁”和“禮”(包括三綱五常)剝離開來,打碎歷史加在“仁”上的道道枷鎖,恢復了孔、孟仁愛思想的初衷,恢復了中華民族價值哲學的本初內涵,讓中國傳統文化找到了與時代的結合點,解決了中國核心價值的古、今問題。二是《仁學》融儒、墨、道、佛、耶之學以及西學于一爐,以“以太”為“仁”的基礎,論證“通”為“仁”之第一義,沖決一切黑暗否塞和網羅,并最終實現“仁—通—平等—大同”之理想世界。譚嗣同給“仁”賦予了新的生命,這個“仁”既古老又新鮮,既傳統又現代,貫通中西方甚至佛教價值觀念,闡發了仁愛思想的普世意義,解決了中國核心價值的中、外問題。
大家普遍注意到,譚嗣同對禮教的嚴厲批判具有極大的思想啟蒙意義,對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思想解放具有深遠的影響。而他同時對儒家文化的堅守和對“仁愛”思想的古為今用,并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甚至有人批評他講“仁”跟康有為一樣是“托古改制”。新文化運動在批判“吃人”的禮教的同時,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全面否定孔、孟之道和傳統文化,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潑掉了,這種狀況持續了半個多世紀,愈演愈烈,直到“文革”打倒“封資修”、“評法批儒”、“批林批孔”,把“仁”和儒家文化徹底丟掉,讓中國陷于歷史虛無主義和文化虛無主義之中,這是中國文化的悲哀、中華民族的悲劇和今天社會道德潰敗的歷史文化根源。
譚嗣同的仁學既是對苦難中的中華民族生存意識與生存意志之召喚的自覺應答,又是高瞻遠矚放眼全球的“世界主義”(梁啟超語)。“譚嗣同回答了當時時代提出的問題,指明了時代前進的方向,就這兩點上說他不愧為人類歷史中的一個大運動的最高理論家,也不愧為中國歷史中一個代表時代精神的大哲學家”(馮友蘭語)。
《仁學》的思想洞穿歷史長河,解決了中國與世界、歷史與現實溝通與和解的大問題,蘊含著偉大的天下精神、人道主義精神和以人為本精神,這可能是很多學者和政治家稱頌這本書的原因。
三
譚嗣同用中國古老的哲學概念“道器”、“體用”,來闡述中國本位文化與西方文化的關系,價值觀與政治制度、體制的關系,為變法提供思想武器,他的這些探索沒有后來那么強的功利色彩,具有長期的哲學價值。
面對西方列強的威脅,晚清中國人急著找出路,經世思潮、洋務思潮、維新思潮、共和思潮,一浪高過一浪,其中維新思潮出現在歷史的十字路口。在一些舊政權統治較軟弱的國家,例如英國、日本和俄國走通了改良主義道路,以較小代價實現了歷史轉型,中國錯過了這樣的機會。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過于強大,封建文化過于深厚,長期對外封閉對內禁錮,固有的滿、漢矛盾,清政府既腐敗無能又專橫頑固等等。頑固派堅守夷、夏之防,死抱著“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傳統。從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到張之洞的《勸學篇》,洋務派花了很大力氣才戰勝頑固派,讓“中體西用”的思想成了氣候。甲午戰爭的失敗,讓“中體西用”的歷史局限暴露無遺。維新思想家要改革封建專制這個“體”,觸動了專制政權的根本,他們失敗了,可是他們的思想到了今天仍有現實意義。
本來“道”和“器”是古老哲學概念,具有中國哲學特有的模糊性,人們一直認為,“道”是原則、理念、是形而上的,屬于精神范疇;“器”是工具、器物,形而下的,屬于物質范疇。明、清以來,以道為體,以器為用,重道輕器,重義輕利,坐而論道,空談心性,驕妄虛空,不務經濟的傳統士風,已經積習深厚,到了足以亡國之地步。
明朝的遺民王船山看到了這一點,他有一段名言:“天下唯器而己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謂道之器也。”(王夫之《周易外傳》)他認為“道依于器”,顛覆了自古以來“天不變道亦不變”的思維定勢。譚嗣同很喜歡這段話,曾多次引用。但是時過境遷,譚嗣同面對的是洋務派的“中體西用”。如果說道、器之辯還是講哲學的話,體、用之爭純粹是講政治了。張之洞的《勸學篇》是講“中體西用”的經典,主張在維護君主專制制度的前提下接受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技藝,并以這種新技藝“補”專制舊制之“闕”,“起”清廷統治之“疾”。張之洞的公式是:“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勸學篇·會通》)
《勸學篇》在朝野影響很大,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嚴復等都從理論上予以了批判。譚嗣同在論述道、器關系的基礎上批駁“中體西用”思想。一是把“道器”與“體用”結合在一起講,推陳出新,用他的道器觀闡述他的體用觀。他說:“道,用也,器,體也,體立而行,器存而道不亡……器既變,道安得獨不變?”器是本體、是根據,道是作用、是表現;二是講道、器同一。他強調“道器不二,道隨器遷”。他認為道、器同源互動,體、用同源互動。否定割裂道器、體用的觀點;三是講變法就是變器,他說:“變法者,器既變矣。”“酌取西法,以補吾中國古法之亡。”甚至于“盡變西法”,變法是變“體”;四是物質在先,精神在后,他說“以太為體”,“仁”為用。他說:“夫仁,以太之用,而天地萬物由之以生, 由之以通。”總的來看,他認為精神的東西依賴于物質的東西,物質的東西在變,精神也要變。他的哲學傾向于唯物唯實,求新求變,他的哲學超越了那個時代,閃耀著中國近代思想的啟蒙之光。
一百多年的歷史證明,道隨器變、體用同源、變法變器等思想觀點比中體西用、全盤西化、西體中用都更科學和進步,里面蘊含著與時俱進、從問題出發的認識論,比較接近實事求是的思想。譚嗣同跟晚清考據學者不同,跟清議官僚不同,沿著解決中國問題的思路,有什么問題解決什么問題的思路,把晚清民族危機中產生的經世思潮、洋務思潮推向了維新思潮的新高度,為維新思潮的和后來的民主共和思潮做了哲學的準備。他雖然有很急躁和激烈的情緒,但他在方法上堅持了秉中而執兩的態度,在矛盾沖突十分尖銳、經濟社會急劇裂變的條件下,這種中庸之道、中正方法實在是最好的選擇,勝過了“矯枉必須過正”的態度。作為那個時候那么年輕的他,真是難能可貴。
值得我們今天思考的是,譚嗣同當年的思考成果同樣被歷史忽視了。回首望去,我們很快跨過了譚嗣同們的改良主義思想,錯過了歷史的十字路口,走上不斷激進化的道路,后來左的和右的思潮各執一端,難以形成共識,消耗了資源,阻礙了進步,以致我們今天仍停留在實際上的“師夷長技以制夷”、“中體西用”的思維定勢中。從“五四”激烈的反傳統,到“文革”破四舊、批林批孔,直到今天的“左右”之爭,在道與器、體與用的思考上,中國思想界并沒有完全達到當年譚嗣同的認識水平。
道和器、體和用本來是方法問題,但是近代中國人總是和價值、制度一起講,實際上爭的是價值和制度,所以總也講不清楚。一個民族的價值觀對這個民族國家的政治制度有重大影響,可以說有什么價值觀就有什么制度,這就是中國人講的“天不變道亦不變”。譚嗣同指出在歷史變革的時候,制度的變化是第一性的,制度的變化可以改變價值觀念。譚嗣同兩個甲子前已經認識到的問題、較好地解決了的問題,我們為什么糾纏不休?根本的原因是價值觀和制度中的封建專制基因仍然在頑強地表現自己。洋務、維新、共和,雖然我們越來越激進,封建主義的專制、宗法、等級和愚民思想并沒有因為封建帝制的退出而退出,仁愛、自由、民主和平等的思想也沒有因為民主革命的勝利而勝利。后來,封建專制思想披上革命的外衣,以左的面貌橫行于“文革”時代,時隱時現于改革開放時期,在最近幾年的腐敗現象中借尸還魂。
四
《仁學》體現出一個思維特點,就是傳承和變革的關系把握得比較好,這也是一直困擾中國的一個大問題。
譚嗣同激烈地批判傳統,他說:“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但他從繼承傳統的角度批判傳統,他說,“仁之亂也,亂于其名”,他呼號沖決名教網羅,為的是發揚真正的仁愛、平等精神,他對中國的傳統的批判是一種“揚棄”而不是全盤否定。那個時代的進步的訴求就是變法改革,就是有序變革,而不是徹底的推翻重來。《仁學》給人的印象是龐雜、多樣,孰知這正是我們當今所缺乏的多元、包容、妥協和中庸。譚嗣同無意之中處理好了后人難以處理的一尊與多元的關系,我們今天看到的《仁學》,視角那樣廣闊,文化那樣豐富,涵蓋那樣久遠,內涵那樣深刻。譚嗣同在處理中學與其他學術關系、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情韻與義理、知與行的關系上,都在“不成熟”中勇敢探索,給人以啟迪。這是改革者的思維,這是改良主義的特征,是那個時代人的特權。說到這里我真想說一句,要向改良主義學習。
這幾年,我看習近平講話里有一個很重要的觀點,就是講傳承,把傳承和變革結合起來。他講前后兩個三十年是有聯系的,要一體的來看,中國共產黨九十多年的歷史要一體來看,共產黨與以前的歷史也要聯系起來看。他最后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古代、近代、現代一體的文化脈絡中走出來的,這里面就有傳承和變革的關系。
有人說譚嗣同是中國激進主義的先驅,我不這樣看。如果說激進主義是我們民族的悲哀,過錯不在他,而在于統治者,歷史一再證明,專制主義是激進主義的根源。清王朝嚴厲地鎮壓了戊戌維新,譚嗣同血濺菜市口,唐才常自立軍起義失敗,變法演變成革命,中國走向一個更大時空的輪回。激進主義從方法論上講,就是割裂歷史傳承關系,脫離當時的環境去看歷史,用激進主義歷史觀衡量歷史。不講漸進,不講妥協,不講包容,唯我獨尊、唯我獨革。從《仁學》到上一個甲子是1956年,那是中國的一個歷史節點。我們現在又是一個甲子,又處在一個歷史的節點,何去何從?我曾經以為“文革”那樣的災難浩劫不會重演了,這兩年“文革”言論、思想甚至理論死灰復燃,有些學者、理論家也在鼓吹極左的一套,我很納悶,改革開放、依法治國都是在與極左思潮的激烈斗爭中前進的,如果讓極左的一套成了氣候,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國豈不是空談?我深感憂慮。
回眸兩個甲子,有兩方面的教訓,一方面我們要吸取譚嗣同這種傳承與變革的思想,一種歷史主義、現實主義的思考;另一個方面從執政者來講,也要正視并認真解決改革者提出的問題,哪怕是尖銳的問題,哪怕是尖銳的不同的見解,真知灼見最初都是以不同意見的形式出現的。這樣,才能為改革騰出更大的空間,留出更長的時間,減少新的折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