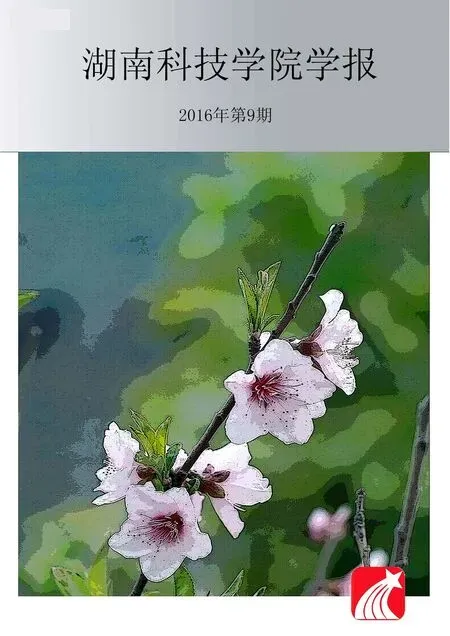略論岑仲勉突厥史研究的學術貢獻
舒 薇
?
略論岑仲勉突厥史研究的學術貢獻
舒薇
(上海大學 文學院 歷史系,上海 200444)
岑仲勉是我國著名的隋唐史專家,同時也是研究突厥史的大家,《突厥集史》、《西突厥史料補闕及考證》是他研究突厥史的兩部代表性著作。論文主要從岑仲勉對沙畹《西突厥史料》一書的補闕和訂正,對相關的史實的考訂,對突厥碑文的整理,整體研究和系統考訂等四個方面論述其突厥史研究的學術貢獻。
岑仲勉;突厥史;《突厥集史》;《西突厥史料補闕及考證》
岑仲勉(1886-1961),原名銘恕,又名汝懋,字仲勉, 廣東順德人。早歲在海關、鐵道、鹽運等機關任職,40歲左右始專心于治史,1937年在陳垣推薦下入中研院史語所任研究員,人生經歷與滿腹學問俱奇,被稱為大器晚成的史學家。其于史學考證,有《兩周文史論叢》、《墨子城守各篇簡注》、《隋書求是》、《通鑒隋唐紀比事質疑》、《唐史余瀋》,散篇則多收入《岑仲勉史學論文集》;于金石銘刻,有《郎官石柱題名新考訂》、《金石論叢》;于邊疆史地,有專著《突厥集史》、《西突厥史料補闕及考證》、《漢書西域傳地里校釋》、《佛游天竺記考釋》、《黃河變遷史》,論文匯輯為《中外史地考證》;于詩文別集,有《唐人行第錄》、《讀全唐詩札記》、《讀全唐文札記》;晚年據講義編定通貫性的《隋唐史》。在史學方法上,探究史源,校其異同,辨其正誤,補其缺略。學術界對岑仲勉的研究多集中在其唐史領域,本文將重點介紹其突厥史研究的學術貢獻。
突厥作為我國古代活躍在北方草原上的一個強大的游牧民族,其興衰與中原密不可分,對中國和中亞乃至世界的歷史都曾經發生過巨大的影響。整個突厥汗國時期,突厥本民族并沒有產生本民族的歷史著作,對突厥史的研究,主要借助于漢民族史書的記載,如:《隋書》、《周書》、《北史》、《新唐書》、《舊唐書》中的《突厥史》,以及《資治通鑒》、《文獻通考》、《唐會要》、《通志》、《通典》等書籍中的相關記載,包括一些文人僧人的游記雜文等等。
沙畹一書對于突厥史的研究實有重要意義,時至今日仍備受好評,但不可否認其書在史料、體例等諸多方面均存在著不足。首先漢文史料選擇狹窄,以《冊府元龜》和兩唐書為主要史料;二是缺少“史料編年”,使得全書最后的西突厥史與前文似乎脫節;同時考證方面不盡詳盡。岑仲勉為補沙畹一書的闕漏,以《西突厥史料》為基礎,進行了考證和完善,寫成《西突厥史料補闕及考證》。
由中華書局1958年出版的岑仲勉的《西突厥史料補闕及考證》、《突厥集史》二書,是中國學者整理突厥史料的代表性著作,兩書耗時二十余年,在突厥史研究領域做出了開拓性的貢獻。本文擬對岑氏研究突厥史的具體貢獻略作分析。
一補闕和訂正沙氏一書
較之沙書,岑氏的進步,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編撰史料編年。沙畹一書由于缺少“史料編年”,使得全書最后的西突厥史與前文似乎脫節,而岑氏所做的工作,將史料編年詳細敘述,使得歷史脈絡和全貌更好的把握。岑仲勉注重經世之學,在史源考證方面,“創根問底”,考辨源頭,“竭澤而漁”,遍搜相關史料,判別異同,判斷史料等次,將史料進行對比歸納,找出史料背后的“真實”。
岑氏《西突厥史料補闕及考證》一書自序中說:“至本篇所補,專在編年。除去隋書、通典(太平寰宇記略同)及兩唐書內西突厥專傅,與夫沙氏書元龜部分之正文,不復移錄外,凡史部石刻有涉西突厥之時間性材料,均一一采擷,編附適當或相近之年份。如取輿前數者臺觀,漢籍中之西突厥遺聞,相信已得什九已上。補闕部分遇有疑難時,均就所見附加考證。惟較為復雜之問題,則另作專篇討論。”
在史料編年摘錄的基礎上,在《突厥集史》中,他重新梳理了歷史的脈絡,按時間順序為我們展開歷史的全貌,遇有異議的史實,岑仲勉分條摘錄,且附有論文來論證。《突厥集史》上冊編年按照時間順序展現了突厥興亡的全過程,卷一編年起西魏大統八年,訖北周大象二年;卷二編年起隨開皇元年,訖仁壽四年;卷三編年起隨大業元年,訖大業十三年;卷四編年起唐武德元年,訖武德九年;卷五編年起唐貞觀元年,訖貞觀十二年;卷六編年起唐貞觀十三年,訖貞觀二十三年;卷七編年起唐永征元年,訖弘道元年;卷八編年起唐嗣圣元年,訖長安四年;卷九編年起唐神龍元年,訖開元十年;卷十編年起唐開元十一年,訖天寶十四載。史料編年補闕以及突厥史編年,對于我們整體把握突厥的歷史有很大的幫助,通識突厥史方便了進一步研究的可能。
在編年之外,岑仲勉對相關的史料按照主題分類,將史料匯集在相關主題之下。沙畹一書漢文史料選擇狹窄,以《冊府元龜》和兩唐書為主要史料。當然作為外國學者,對中國古籍史料的情況不甚熟悉是可以理解的,但即使是這三本史料,沙畹亦未窮盡。而岑仲勉將正史、文集、典籍、碑志、石刻各類史料中與突厥相關的內容都幾乎窮盡摘錄,分門別類進行整理,其用功之勤,實在為后來學人佩服。史料的分類大大方便了存疑史實的辨偽,岑仲勉兩書后附的論文中所考證的問題,多來自前文史料整理時所發現的異議。
對沙畹的一些錯誤觀點,予以考證和反駁,譬如西突厥究竟在何時分立的問題上的論述。岑仲勉首先介紹了“西突厥”、“北突厥”、“東突厥”三名,皆我國史家為求語意明了而創立,并非之自號如此。“處西方這既稱西突厥,于是處東方者唐人或稱北突厥”,“突厥居我之北,曰北突厥者,顯就我國與彼之地理關系而立言。若西之自然對象應為東,故唐以后作家又立東突厥之別名。”[2]107隨后,既然西突厥本由東突厥產生,那么兩者間的政權分割始于何時。
新課程改革下的高中物理教學不再是教師一個人完成的教學活動,在課堂中更多是突出了學生的主體地位.在物理實驗課程中,學生是實驗的實際操作主體,在實驗過程中,學生能都獨立思考實驗步驟和實驗過程,從而得出實驗結果,可以通過反復的實驗驗證自己的猜測,培養自身獨立思考物理的能力.學生在自身實際操作過程中還可以發現問題,對于自己操作過程中的不足之處能夠及時的發現和彌補,不僅能夠有效地掌握相關的知識,更能夠不斷的提升自身的實際操作能力.
關于突厥分裂的史料眾多,沙畹認為是由于沙缽略和木桿不和,因而分立為東西突厥。沙氏此說來源于《冊府元龜》,岑仲勉追溯史源,發現《元龜》錯誤引自《舊唐書》,《舊唐書》以“木桿與沙缽略有隙”,因而分出了東西突厥,以木桿可汗為突厥之始。但是,更多的史料證明,木桿可汗在位時間為553-572年,而沙缽略在位期間為581-587年,兩個可汗不在同一個時代,因此更談不上“有隙”的問題,此說當然不能成立。岑仲勉根據《隋書》和《新唐書》相關記載,考證得到東西突厥分裂源自大邏便(木桿子)和沙缽略不和。
《新唐書》為后出之書,能根據更多材料,對上述諸說有所匡正。據《新唐書·突厥傳》記:“西突厥其先納都陸之孫吐務,號大葉護,長子曰土門伊利可汗,次子曰室點密,曰瑟帝米。瑟帝米之子曰達頭可汗,亦曰步伽可汗,始與東突厥分烏孫故地有之。”即到達頭時就有了西突厥。沙畹認為:“當士門、室點密之時,突厥實已分為二支”,“東西突厥之分,固始于六世紀中葉,(即土門、室點密時——引者),然政治之分立,得謂其實完成于582年(即達頭可汗時——引者)也”,即沙畹認為東西突厥分裂于582年。但岑仲勉稱“余則未敢茍同”,指出當時突厥其仍在西征黯戛斯、突騎施和索格底亞,自然不會分裂“西突厥之完全分立,應以大業六、七年(611-612)射匱繼位之時為準”。所以岑仲勉根據《通典》得出結論,認為東西突厥分立于611年或612年。
二考訂相關史實
沙畹一書在考證方面不盡詳盡,而這一部分正是岑仲勉治史用力最勤之處,成就斐然。《補闕》一書中對西突厥治下的西域相關地區,岑仲勉對西域各國和羈縻府州進行了考證,如:西突厥以何時分立,從西史及突厥語推出室點密汗之尊號,西突厥世系考,證明東突厥處羅侯汗死于西征波斯及昭武即葉護之異文,唐代十六國羈縻府州數,西域十六國都督府州治地通考,曲氏高昌補說,庭州至碎葉里考,弓月之今地及其語考,處月處密所在部地考,嚈噠國都考,羯師與賒彌今地詳考,黎軒、大秦與拂壈之語義及范圍,曲氏高昌王外國語銜號之分析等。
岑氏《突厥集史》下冊則為突厥本傳、突厥部族傳記以及漢文、突厥文之碑銘的校注以及相關人物的傳記和碑志的考證。并附譯文和論文多篇,足供研究突厥史者參考。在論述突厥本土生活的時,岑仲勉細致考訂了周人和突厥民族文化、習俗的相類之處,分為封建、“族”之意義、事火、十二屬、指天社誓、數名之萬、尚九、殉葬、贅面、收繼婚、半子、尊號、色尚藍、鐵之名稱、地域觀念、方向尚東等眾多相同或相類似的方面,為我們展示了真實的突厥生活的風貌,揭示中華民族和突厥的密切關系。
在一些史實的論證上,岑仲勉不迷信權威,將史籍中有錯誤和出入的記載,通過詳細的比對和考證,嚴密論證,得出自己的觀點,還原歷史的真實。如,《通鑒》開元八年下記暾欲谷掠涼州契苾部而去,結語謂“毗迦由是大振,盡有默啜之眾”,馬長壽以為“此結語恐不適當”,甘涼二州回紇等部不堪王君奐的壓迫,北奔突厥,“直至開元十五年始可云苾伽‘盡有默啜之眾’”云云。按開元十五年北奔的部落似只是抗拒的一部,所以元和時代境內還有契苾部流浪;唐末甘州回鶻之立國,也就以開元前住落此一帶之部落為骨干(參看《東方雜志》四一卷一七號拙著誤傳的中國古王城),河西的鐵勒并未掃數退回漠北。何況此種部落在太宗、高宗時已住落我國,還在默啜之前,非默啜當日所能統治,根本上不能說是“默啜之眾”呢!
再有《周書》突厥傳記他缽可汗說:“但使我在南兩個兒孝順,何憂無物耶!”《隋書》突厥傳改作“我在南兩個兒常孝順,何患貧也!”《通鑒》一七一采用了隋傅的句語,胡三省注:“在南兩兒謂爾伏、步離二人,所部分西北,皆南近中國。錢大昕通鑒注辨正二駁之,已引見周傳校注。岑仲勉指出馬長壽獨謂胡注“此說似較允當”,是不可不加以討論的。隨后詳細分條來論述自己的觀點:(一)北族對侄、甥輿子輩之間,亦有區別。(如兇闕特勒碑云“朕昆弟、姊妹之諸子及朕諸幼王子。”)據隋傅,爾伏統東面,步離居西方(胡注:“所部分西北”是錯的,應言“分東西”),皆他缽之侄,今說“兩個兒”,究有不合。(二)他缽轄制全國,分藩之貢獻,是部族制度本分事,不應作“但使……”“常……”之不定語氣。(三)分統東西則茌方位為兩翼,今日“在南”,于位置上說不過去。(四)最要是周傅所用之“物”字,隋唐時代對外之賞遺,常曰“賜物”若干,“物”均指絲織品而言。此外如隋文帝詔:“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沙缽略表;“此國所有羊馬,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繒彩,都是此物”(以上二事均見《隋書》);創業起居注一:“義士等咸自出物,請悉買之(馬也),”李大亮疏:“每見一人初降,賜物五匹。”(《舊唐書》六二。化龍池本《太平寰宇記》“物”作“絹”。)貞觀廿一年六月詔;“知見在沒落人數,輿都督相計,將物往贖”(《全唐文》),用法無不如此。至于“畜牧部落的首領,主要是以馬回贈”(同前引《考古學報》四三頁),可見“何憂無物”的話萬萬不適用于爾伏二人。(五)在記述他缽的話之前,周傳說:“朝廷既輿和親,歲給繒絮錦彩十萬段……齊入懼其寇掠,亦傾府藏以結之,他缽彌復驕傲。”隋傅亦云:“周、齊爭結姻好,傾府藏以事之,佗缽益驕。”其輿他缽的話互為聯結,文甚顯然。馬氏書亦嘗注重周、齊兩方之饋送,估計每年至少有絲繒二十萬段。倘依胡注立解,頗嫌自不呼應。(六)原夫胡氏立說,或因“兒”字難解,亦許反抗外人之蔑視,然而無可疑也。游牧部族之習慣,勢優者對勢劣者常以父輩自居,故唐太宗說延陀父事我,默啜請為武后子,毗伽認玄宗為父,毗伽死,伊然繼位位,玄宗敕書依舊稱為兒可汗。他缽視周、齊如兩兒,無非當日爭事突厥所致。
通過前面六條的論證,岑仲勉得出結論:“綜此觀之,胡注不可信據也明矣。這一段辯論并不是咬文嚼字的考證,而是反侵略的重要問題。唯其突厥初時憑藉優勢,對北朝東西兩方,采取漁人態度以實行侵略,才迫使我國不能不急圖自衛,而印起隋文帝施行反間、唐太宗擒伏頡利等一串連事實,并非隋、唐敵視突厥帝國之形成,加以破壞。倘照胡氏解釋,則蒙蓋了突厥當日對華之野心,抹煞史實,是非不明,使沙畹責備隋、唐之讕言,得以朦混世人耳目矣。”[3]
三對突厥碑文進行整理
岑仲勉對突厥碑文進行整理,包括突厥文墩欲谷紀功碑、突厥文闕特勤碑、突厥文毗伽可汗碑三種,都是逐面逐條的注釋改譯。征訂了如梅祿、匐、頡跌利施可汗、曲漫山、婆葛、失畢等語的對譯。岑仲勉廣泛應用對音方法考訂邊睡外域古地名,對音方法雖不十分可靠,但先生的考訂極少穿鑿附會,其原因在于先生通英文、法文、日文,又能藉助于工具書求出突厥語、吐火羅語中的語源和語意。[4]岑仲勉借助此法,用突厥石碑與唐代舊譯對比,依據外文釋讀,逐字逐句翻譯,再次基礎上借助大量史料進行考證,從而整理出這三種碑文,為突厥史的研究打開了新的局面。
試舉岑仲勉翻譯的突厥文闕特勤碑為例。731年(開元十九年)三月,征戰一生的偉大的突厥英雄、突厥毗伽可汗的胞弟左賢王闕特勤去世,年僅47歲。唐朝派金吾將軍張去逸等送唐玄宗璽詔前往吊奠,并為他立祠廟,刻石為像。732年(開元二十年),毗伽可汗立《故闕特勤碑》,碑文由突厥文和漢文書寫,其漢文碑銘由唐玄宗“御制御書”。碑分大小2塊,為大理石制,至今仍矗立在蒙古國鄂爾渾河流域和碩柴達木。闕特勤碑對研究古代突厥史具有不可替代的極其重要的價值,同時也是中國與突厥友好關系的見證。史書記載,開元十五年(727年)秋,吐蕃寫信給突厥毗伽可汗,約他一起侵擾唐邊境,毗伽可汗不但予以拒絕,并且將吐蕃的來信送交唐朝,唐玄宗很贊許毗伽可汗的友善,在長安紫宸殿設宴款待來送信的突厥大臣梅錄啜,又允許在朔方軍西受降城設立互市,每年以布帛數十萬匹與后突厥交換軍馬,以壯大騎兵隊伍,并改良馬種,從此中原的馬匹更加強壯。
闕特勤碑陰側三面為突厥文,碑文是以毗伽可汗的口氣寫的,表現了毗伽可汗與其弟突厥左賢王闕特勤的深厚感情,文中寫道:“如闕特勤弗在,汝等悉成戰場上的白骨矣。今朕弟闕特勤已死,朕極悲惋。朕眼雖能視,已同盲目,雖能思想,已如無意識。”“闕”是人名,“特勤”是突厥貴族子弟的封號。闕特勤碑漢文和突厥文內容有所差異,漢文碑文重點強調唐朝與突厥的友好關系,突厥文碑文則以緬懷闕特勤一生的功績為主,對中原漢人有很多不實的描述,多用訓誡、勸告的口吻提醒突厥人對漢人要保持警惕。碑文的翻譯對我們理解當時的史實和突厥與中原的往來具有重要意義,岑仲勉先生做出了杰出的貢獻。
四整體研究與系統考訂
中原和突厥長期存在著聯系,所以擁有大量的突厥漢文資料,但由于突厥族存在的時間跨度長且地域跨度廣,導致史料分散且錯訛極多,這些都增加了突厥史研究的難度。而岑仲勉能夠超越前人,勤勉治學,將東西突厥聯系起來,進行整體研究,對突厥史漢文資料做系統的考證、整理,為后人研究突厥史鋪平了道路。
岑仲勉先生在《突厥集史》一書中總結到:“《突厥集史》稿大致寫定于十年以前,因行將付排,再作一回總校,間有零零碎碎的見解,插補不便,故掇拾而成此編后之記。我之研究突厥史,西突厥史既略試問津,如不兼明東突厥的情況,則得其偏而缺其全,尋其流而昧其原,未免陷于一知半解。”[5]3此是為準確而全面的把握突厥的歷史全貌而做,沙畹所做的《西突厥史料》只是注重西突厥的歷史,而忽略了西突厥本來就是從東突厥中分裂而來,所以研究西突厥史必須先通東突厥史,這樣才可以避免在研究中犯偏概全的錯誤。
《突厥集史》一書,研究對象是將整個突厥汗國都納入研究范圍,包括東突厥、西突厥和后突厥。該書廣泛輯集散見于大量漢文古籍中的有關突厥的史料,匯集了正史、文集、典籍、碑志各類史料中與突厥相關的內容,包括正史中的突厥本傳、與突厥關系比較密切的其他諸部落的傳記、突厥人的碑志、列傳等等。此外,還收載了古突厥碑銘的漢譯文,以及外國學者的論著選譯。岑仲勉對突厥史的系統研究對于我們整體把握突厥的歷史有很大的幫助,方便了進一步研究的可能,為后來的學者指明了方向。
[1]劉斌.《西突厥史料》與《新唐書》“西域史料”的關系[J].滄桑,2013,(2):45-47.
[2]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補闕及考證[M].北京:中華書局,1958.
[3]岑仲勉.突厥集史·編后再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8.
[4]邢玉林.潛精治史著作等身的大家岑仲勉[J].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2,(4).
[5]岑仲勉.突厥集史·再版后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8.
K27
A
1673-2219(2016)09-0042-04
2016-06-24
舒薇(1992-),女,湖北黃岡人,上海大學文學院歷史系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隋唐史。
(責任編校:張京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