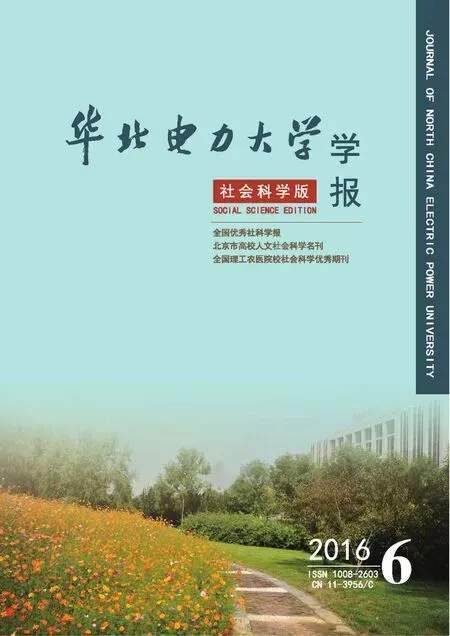試論信息法益的擴張與刑法回應
王肅之
(武漢大學 法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2)
?
● 法學前沿
試論信息法益的擴張與刑法回應
王肅之
(武漢大學 法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2)
隨著信息犯罪的發展,其法益的擴張需要被關注和認可。無論是信息秩序還是信息財產都需要從法益的角度重新被認可。需要立足于理論探討,從刑法的角度對信息法益作出恰當的回應。
信息法益;信息秩序;信息財產
一、法益與信息法益
(一)法益在犯罪理論中的地位
“法益”一詞是舶來品,是我國刑法學者從德日刑法中借鑒來的概念,一般在刑法目的或功能角度被探討,認為法益是刑法的保護客體。但是法益在犯罪理論中是否應該有地位、應該有什么樣的地位,國內學者卻存在較大分歧。主要有以下三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我國刑法理論無需納入法益概念。根據通說,犯罪客體是我國刑法所保護的、為犯罪行為所侵害的社會關系。[1]據此,行為構成犯罪,根本原因就在于侵犯了特定的社會關系,并且所侵犯的社會關系越重要,那么犯罪行為對社會的危害性就更大。在此基礎上,依據犯罪行為所侵犯社會關系范圍,可以將犯罪客體劃分為如下三個層次:一般客體、同類客體和直接客體。根據上述觀點,特定社會關系作為犯罪的客體要件,體現了犯罪的本質,無需再納入法益的概念。
第二種觀點認為,我國刑法理論應該納入法益概念,但是刑法構成要件當中不應納入法益概念。張明楷教授認為,根據我國刑法的規定,刑法的任務與目的是保護法益。所以侵犯法益是違法性的實質。[2]也就是說,張明楷教授的違法構成要件、責任要件兩階層的犯罪論體系中,法益是作為違法構成要件的實質內容而不是獨立的構成要件。周光權教授雖然在犯罪論體系上采取的是犯罪客觀要件、犯罪主觀要件、犯罪排除要件三階層模式,但是同樣也沒有將法益納入犯罪構成要件。[3]
第三種觀點認為,我國犯罪構成要件體系應該納入法益概念,置換社會關系概念作為犯罪客體。該說認為,犯罪客體是刑法所保護的被犯罪活動所侵害的社會利益。[4]或者認為,我國現行刑事立法實踐表明,許多犯罪不宜將其客體歸結為“社會關系”,但是完全可以將其歸結為“法益”。[5]
筆者同意上述第三種觀點。理由如下:第一種觀點是我國刑法的經典理論,該觀點可以看做把法益的政治屬性從其自然屬性中剝離出來作為刑法所保護的客體。其看到了刑法的政治內核,并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發揮著重要作用。但是隨著刑法從政治刑法走向市民刑法,刑法理論也需要作出必要的調整,抽象的社會關系有時難以完全對刑法的保護客體提供精準的指引,所以我國刑法理論有必要對法益概念進行合理的接納。第二種觀點沿襲自德日的經典理論,有其理論上的淵源。德日刑法理論,一般不將法益直接作為犯罪成立要件,而是作為犯罪所侵犯的、刑法所保護的客體。在刑法理論上,法益更多承擔的是解釋與批判的機能。[6]但是這種脫離了構成要件的法益概念在一定情況下會使法益概念的虛化。如我國臺灣*我國臺灣刑法理論主要沿襲自德國,在犯罪論體系上采取的是三階層體系,法益并非犯罪成立要件,而是較為抽象的理論概念。學者許恒達就指出,法益是一個外在堅實而內在空虛的概念,由于其定義內涵極不明確,具體操作上很難說得出法益/非法益的界限何在。[7]第三種觀點,較好地融合了前兩種觀點的長處:一方面,用法益置換“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成為犯罪客體,可以使犯罪客體“走下神壇”,使之能夠作為具體的可判定要件,有利于在罪刑法定與社會發展之間找到合適的判定界限;另一方面,將法益概念納入我國現有體系,而不是盲目地對我國的犯罪構成體系完全重構,可以在完成刑法自我調整的過程中減少過多的理論代價。
(二)信息法益的現實地位
簡單來說,信息犯罪所侵犯的法益就是信息法益。筆者認為,信息犯罪包括但不限于以信息為對象的犯罪(如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的犯罪)、以信息為工具的犯罪(如利用信息實施的有關犯罪),也包括與信息相關的其他犯罪。隨著信息犯罪的愈演愈烈,人們逐漸認可信息犯罪的法益有必要從刑法的角度作出單獨的考慮。但是如何從刑法角度作出考慮,還有待于進一步分析。簡單來說,可以有兩種理解:一種理解可以認為信息法益具有從屬性,即就法益而言,自然人、法人、國家無疑是法益的主體,這是自啟蒙運動以來法律應秉承的原則與精神,就信息法益而言,其實也可以理解為國家法益、社會法益和個人法益三部分,要根據信息的內容確定法益的類型。另一種理解可以認為信息法益具有獨立性,是與國家法益、社會法益和個人法益并列的獨立法益。這種理解是參照了有學者對于生態法益的理解。在同樣作為風險社會所衍生的法益,就生態法益的體系定位,有學者認為應與國家法益、社會法益、個人法益并列[8]。筆者認為,生態法益也罷,信息法益也好,都是對于法益的一種縱向概括——對于涉及生態或著信息的國家、社會、個人法益的總稱,而不是一種橫向的劃分。既然信息法益并不是新的法益劃分形態,那么信息法益的主體也就和其他法益類型的主體不存在實質區別,也主要包括自然人、法人、國家。
這樣一種理解似乎能夠得到普遍的認同,這是因為,相比于認為信息法益是一種獨立法益,認可其是一種附屬法益更妥當。但是當這一問題在另外的情況下討論時,就有了不同的結論。很多學者認為,對于信息財產問題、信息社會秩序問題,不應認可其對于傳統法益內容的擴展。如有學者認為,從理論上講“網絡秩序”*在信息社會的現階段,信息秩序通常表現為網絡秩序。是一種特殊秩序,即便擾亂一般也不具有對現實社會的實際危害。[9]筆者認為,信息法益種類上的從屬性與形式上的獨立性是并存的。正因為信息法益包括國家法益、社會法益、個人法益,所以對于其中新出現的信息法益形式也應當給予獨立的地位,如信息財產、信息秩序等。
二、信息法益的理論分析
(一)信息財產
筆者認為,應該承認信息財產,但是也不應對其作擴大化的理解,應分情況予以討論:
第一,信息虛擬財產該如何認識?類似問題進入學界視野源于網絡游戲中的天價“裝備”等財產,在此也以其為例進行討論。第一種觀點認為我們認為對虛擬財產進行刑法保護是一個必然的趨勢。[10]網絡游戲裝備和游戲幣等虛擬財產從性質上也應屬于刑法所保護的財物范疇。[11]上述觀點可以理解為一種積極的觀點。根據這一觀點,由于信息網絡的發展,信息網絡中的虛擬財產可以與現實的價值實現某種對接,所以應當對其財產性予以承認。第二種觀點認為,對于虛擬財產的意義應當予以否認。事實上網絡游戲的運營商雖然聲稱對于一切虛擬財產享有所有權,但事實上卻無法實現對虛擬財產的所有權。[12]其實,所謂的虛擬財產并不歸屬于游戲玩家,其實際的權利主體乃是運營商。雖然玩家可以進行形式上的“交易”,但是并沒有產生現實的社會意義,本身不是法律行為。第三種觀點認為,應秉持一種折中的觀點。其不贊同將任何游戲物品均上升為法律保護對象意義上的財物。[13]也就是說,游戲本是一個“過程”,意義并不在于虛擬物品的取得。何況“虛擬財產”僅是對于玩家有價值,并沒有一般社會意義上的價值。對于不玩網絡游戲的人來說,幾千元的裝備可能一分錢不值。當然也應該辯證地予以看待,畢竟該類物品對于特定人群是有價值的,所以應該采取一種限定肯定的態度。至少目前將一般虛擬物納入財產范疇予以保護的條件尚不成熟。[14]筆者認為,第三種觀點較為妥當,限定保護的原則應該被肯定。刑法是保障法,具有最后性,對于虛擬財產,雖然有必要從法律角度對其加以保護,但是目前從民法的角度對其該如何保護尚未完全確定,不宜通過刑法來全面對其進行保護。但是如果標的較大、社會影響較大,則有必要考慮刑法是否應該介入。
第二,對于信息、數據應否承認其財產價值?根據現有立法的態度,對于信息、數據不應直接被刑法保護,主要根據數據、信息的內容來決定是否對其進行保護、該如何保護。但也有學者認為,信息具有利益屬性,是信息受到法律保護的基礎。[12]或認為,對于大數據的財產化保護將不會存在爭議,具有無法回避、無法逆轉的現實必然性和必要性。[13]筆者認為,雖然信息、數據的價值性毋庸置疑,但是這種價值尚且不宜直接認定為財產價值。一方面,信息、數據的財產性不宜衡量,處于一種極大的不確定之中,無法對其做出準確的量定。另一方面,在民法等法律都未對信息、數據作出規制之前,刑法不宜過早地介入,否則可能會有悖于刑法的謙抑性。
(二)信息秩序
信息社會也不是無序空間,也需要有一定的秩序。但是對于這種秩序,是應該承認其具有獨立的意義,還是應該否認其是社會秩序的一種?目前學界尚未形成統一的意見。一種意見是,信息秩序具有獨立的價值,應該被肯定和承認。信息社會已經在現實社會之外架設了一種額外的空間,信息社會,特別是信息網絡中的社會秩序,應該被認可是社會秩序的一部分。甚至于有學者指出,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的社會秩序,信息社會中的犯罪行為還有可能破壞市場秩序。如有學者認為,有償“刪帖”行為不僅嚴重破壞網絡秩序,而且嚴重擾亂了市場秩序。[17]另一種意見是,信息社會不過是現實社會的投影,應將其看作現實社會的信息表達。信息社會并不是現實社會形態,其中的所謂“秩序”并不是刑法意義上的社會秩序。這種對社會秩序的影響是間接的。[18]
筆者認為,信息社會已經成為一種社會形態。信息網絡中的行為已經不僅僅局限于“0”或“1”的數字表達,而是具有現實的意義。信息社會本身也產生了一定的為人們應遵守的秩序,并且這種秩序具有社會意義。所以,應該認可信息秩序是社會秩序的一種,在此基礎上對其進行深入的研究,才有可能通過刑法促進良性信息秩序的形成。
三、刑法對于信息法益的回應探討
(一)對于信息財產的回應
目前侵犯信息財產的案件并不多見,但實際上被查處的只是很少一部分。目前對于該類犯罪,往往是按照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條中的思路予以處理。如臨海市發生一起特大案件,由多人組成的網絡犯罪團伙,通過木馬程序獲取游戲玩家賬號后,對其中的裝備進行售賣,獲取利益,涉案金額逾五百萬。*參見臨海市公安局網站《臺州日報:臨海警方破獲一特大網絡盜竊案》,http://www.tzga.gov.cn/linhai/News/Details.aspx?id=555555564460,2015年8月20日訪問。這一案件,警方卻是考察從性質上是否屬于“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換言之也就是分析其是否構成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條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但是上述思路存在不妥:上述盜取虛擬財產的行為,并未對于計算機系統造成實際的損害,既沒有導致系統的癱瘓,也沒有導致數據的滅失。他們只是讓數據轉換——從一個玩家到另一個玩家手里,那么對于計算機信息系統的破壞何在?
筆者認為,之所以會出現上述偏差,是因為對于信息財產沒有做出正確的判斷。如果認可信息財產屬于應受刑法保護的財產,那么完全可以換一個思路,從盜竊罪的角度考量這種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根據官方的解釋,構成盜竊罪罪以下三點必不可少:第一,需要有非法占有目的。第二,盜竊行為需要具有秘密性。第三,在數額、次數、方式等方面符合刑法的要求。*參見參見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釋義(第5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77頁。從理論上說,如果認可虛擬財產的財產性,盜竊虛擬物品的行為自然屬于盜竊行為,應該受到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的調整。但是這里有一個問題,構成盜竊罪,除非在次數上或者方式上符合法定要求,否則就需要根據數額予以判定。但是對信息財產的侵犯在方式上不符合入戶盜竊、攜帶兇器盜竊、扒竊,所以更多地需要對于數額進行判斷。然而信息財產的價值出于很大的不確定之中,如何進行判定確實是一個難題。筆者認為,需要尋找相對確定、客觀的價值標準。以游戲虛擬財產為例,該類財產價值的判斷不可按照玩家交易的價格判定,而應該按照運營商發行的價格予以判定。這是因為,玩家之間的價值具有很大的隨意性,不具有代表性。而運營商的價格是針對所有玩家的,具有相對的客觀性,而且不會過分波動。在確定價值標準之后,就可以判定是否達到“數額較大”的標準進而判定是否構成犯罪。
另外,從長遠來看,有必要通過立法對于信息財產的法律性予以肯定。不過筆者倒不建議直接在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中作出規定。這和我國刑法立法狀況有關。我國刑法第二百六十五條也是有關盜竊罪的規定,是關于盜竊罪的提示性規定。在第二百六十五條中有“盜接他人通信線路、復制他人電信碼號”按照盜竊罪處罰的規定,所以在該條中與上述項并列規定將盜竊信息財產按照盜竊罪處罰較為妥當,能夠在實現立法目的與節約立法資源之間取得平衡。
(二)對于信息秩序的回應
目前對于這一問題,實務部門已經有所關注。這要從網絡誹謗行為說起。網絡誹謗的危害影響傳播速度極快,而其危害的消除卻又是緩慢和困難的。[19]為了回應網絡誹謗犯罪,司法解釋就誹謗罪和尋釁滋事罪中有關社會秩序的問題作了解釋,將信息秩序看作社會秩序*兩高于2013年聯合頒布《關于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其中的第三條和第五條:第三條規定,利用信息網絡誹謗他人符合七種情形之一的,屬于“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第五條規定,利用信息網絡辱罵、恐嚇他人,情節惡劣,破壞社會秩序的,以尋釁滋事罪定罪處罰。。
有學者指出,《網絡誹謗解釋》在刑法理論和司法實踐中的真正貢獻,在于可能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具體探索——對于“公共場所”和“公共秩序”的探索性解釋。[20]筆者認為,這一觀點有道理,畢竟該司法解釋在對于信息秩序解釋的問題上作出了一定的嘗試,有進步之處。不過筆者認為,該司法解釋的也并非沒有值得商榷之處。其中第三條的規定筆者是認可的,通過信息網絡實施的誹謗行為完全可能“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但是第五條的規定則有待商榷。這涉及到對于信息秩序的范圍理解問題。該司法解釋將信息秩序視為社會秩序,但事實上,二者并不能完全等同。一方面信息秩序可能會出現一般社會秩序的良好、混亂等基本狀況,有其一致之處。但是另一方面,信息秩序不可能出現“打砸搶”等惡性事件。正因為如此,學者們才會在信息秩序究竟是不是社會秩序的問題上爭論不休,而又各有理由。這和信息社會與現實社會的區別有關。信息社會中人們的存在方式是一種缺場的存在方式——無需身體的現實、直接接觸,通過信息網絡就可以實施一定行為,這種缺場性也注定了一些行為和事件在信息社會是不存在的。對應的,信息秩序也可以理解為一種不完全的社會秩序。所以,第三條中諸如“群體性事件的”、“公共秩序混亂”等情況是完全可以在信息社會發生的。然而第二百九十三條尋釁滋事罪中的社會秩序卻要求具有在場性(與缺場性相對),比如“他人”、“場所”的表述所以才會有諸多學者認為這樣的解釋不妥。
所以,筆者認為與其解釋為第二百九十三條尋釁滋事罪,不如解釋為第二百八十八條擾亂無線電通信管理秩序罪或者第六章的其他犯罪更為合適。相應的,對于其他信息犯罪涉及信息秩序的,也要在立法和解釋中注意,在將信息秩序解釋為社會秩序時,注意在場性與缺場性的區別,作出恰當與合理的解釋,使刑法能夠有效地、恰當地維護信息秩序。
[1] 高銘暄,馬克昌.刑法學[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52.
[2] 張明楷.刑法學[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111.
[3]周光權.刑法總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67-71.
[4] 曲新久.刑法學[M]. 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8:59.
[5] 魏東.論作為犯罪客體的法益及其理論問題[J]. 政治與法律,2003(4).
[6](德)克勞斯·羅克信.刑法的任務不是法益保護嗎?[J].樊文,譯.刑事法評論2006(2).
[7] 許恒達.刑法法益概念的茁生與流變[J].月旦法學雜志,2011(10).
[8]簡基松.論生態法益在刑法法益中的獨立地位[J].中國刑事法雜志,2006(5).
[9] 李曉明.刑法:“虛擬世界”與“現實社會”的博弈與抉擇——從兩高“網絡誹謗”司法解釋說開去[J]. 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15(2).
[10] 劉守芬,申柳華.網絡犯罪新問題刑事法規制與適用研究[J].中國刑事法雜志,2007(3).
[11] 于志剛,于沖.網絡犯罪的裁判經驗與學理思辨[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3:333.
[12] 黃太云.知識產權與網絡犯罪立法完善需認真研究的幾個問題[J].中國刑事法雜志,2007(3).
[13] 黎其武.盜竊游戲物品與網絡犯罪[J].河北法學,2005(4).
[14] 戴長林.網絡犯罪司法實務研究及相關司法解釋理解與適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4:34.
[15] 皮勇,黃琰.試論信息法益的刑法保護[J]. 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1).
[16] 于志剛. “大數據”時代計算機數據的財產化與刑法保護[J].青海社會科學,2013(3).
[17] 劉靜坤.網絡敲詐勒索、非法經營案件法律適用問題探討[J].法律適用,2013(11).
[18] 孫萬懷,盧恒飛. 刑法應當理性應對網絡謠言——對網絡造謠司法解釋的實證評估[J]. 法學,2013(11).
[19] 趙遠.網絡誹謗的刑事責任問題研究[J].中國刑事法雜志,2010(8).
[20] 于志剛.現代刑法學的使命——全國刑法學術年會文集:2014年度[C].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14:1079.
(責任編輯:李瀟雨)
On the Expansion of Information Interests and the Response in Criminal Law
WANG Su-zhi
(School of Law,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crime, the expansion of interests need to be noticed and recognized. Both information order and information property need to be recogni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interests. It is necessary to discuss how criminal law can make an appropriate response basing on the theory discussions.
information interests; information order; information property
2016-10-26
王肅之,男,武漢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
D920.4
A
1008-2603(2016)06-003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