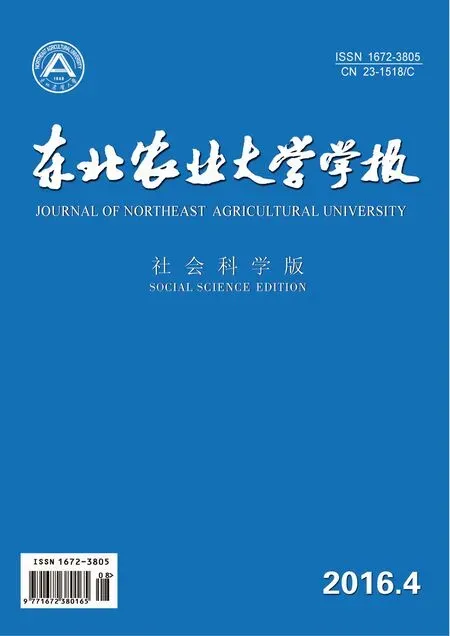從空間角度解讀《舍巴日》中的性別敘事
譚 婷 汪立珍
(中央民族大學,北京 100081)
從空間角度解讀《舍巴日》中的性別敘事
譚婷汪立珍
(中央民族大學,北京100081)
根據福柯等人的觀點,空間不僅僅是一個地理基點,更是一個包含復雜權力秩序的集合體。《舍巴日》作為土家族作家孫健忠創作轉型的代表作,揭示了土家族在發展進程中出現的深刻變化。小說中時間被淡化,突出空間特征,包括地理空間、神圣空間和文化權力空間等,呈現出湘西土家族富有活力的地域文化身份。小說中的不同空間在對話時反復呈現出傳統性別秩序,地理空間的性別化體現出女性的“他者”地位,神圣空間的消解與重置體現出女性感性與男性理性的對立,文化權力空間內的兩性關系則體現出男性的主導力量。從性別敘事角度考查兩性關系在小說不同空間內的反復疊現,有助于了解敘事中作家對土家族內部傳統性別秩序的態度,以及土家族在面對現代化沖擊時兩性關系的變與不變。
空間;性別敘事;《舍巴日》
20世紀中葉,“空間轉向”成為學術界研究的新態勢。列斐伏爾認為“我們已經由空間中事物的生產轉向空間本身的生產。[1]”他認為這是生產力發展、知識直接介入物質生產的結果。列斐伏爾提出空間具有社會性,不僅包含生物—生理關系,還牽涉到生產關系,他將空間分成自然空間、神圣空間、歷史空間、矛盾性空間、差異性空間等。福柯認為,空間并不是靜止的、死亡的,相反,它是活躍的、具有思辨性的。在他看來,空間之間不是單純二元對立的,我們不是生活在虛空中,“是生活在一組關系中,這些關系描繪了不同的基地。[2]”,也就是說,空間是多種關系的集合。索亞不斷發展“第三空間”理論,他提出,第一空間是物質空間,第二空間是構想的精神空間,第三空間強調“統治、服從和反抗的關系,它具有潛意識的神秘性和有限的可知性,它徹底開放并且充滿了想象。[3]”所以,第三空間既是真實空間又是想象空間,它將第一和第二空間中的二元對立關系解構后再重構。本文在綜合幾位學者關于空間認識的基礎上認為,空間不僅是地理存在的基點,還是社會關系的集合體。空間是權力秩序的體現,具有多重性、異質性、富有生命力等特征。“空間轉向”為文學作品的創作與研究提供了另一種思索,在許多作品中,“空間已成為現代小說敘事中的一種重要元素。[4]”作家們不僅將空間作為故事發生場所,還用空間表現時間、壓縮時間,甚至用空間謀篇布局或推進故事發展,空間角度對了解作家作品中的權力關系極為重要。
《舍巴日》是土家族作家孫健忠于1985年發表的一篇中篇小說,“舍巴日”在土家語中是“擺手舞”的意思。小說主要講述了一個來自原始部落的女人掐普在現代社會里的種種不適,農村老惹在面對商品經濟發展時的不斷抵抗,年輕人不滿父輩的固執,在城市文明的誘惑下不斷“出走”的故事。孫健忠以前瞻性的思考深刻描繪了土家族在現代文明進程中與外界文化之間的碰撞與沖突,揭示了土家族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深刻變化,傳遞了他對民族發展的焦慮與希冀。
小說《舍巴日》具有明顯的空間化特征,不僅展示了民族發展過程中的地理空間,還將土家族人的文化、歷史融入小說中,呈現出湘西土家族富有活力的地域文化身份。孫健忠通過《舍巴日》探索身處地域和文化“雜居”地帶的湘西土家族人的歷史命運,不斷挖掘不同“層級”文明碰撞下土家族人的心路歷程。小說中的時間被淡化,突出了空間的發展、變化,使得空間承載了更多的信息與內容。《舍巴日》中的空間化書寫涉及地理空間、神圣空間、文化權力空間等,四種不同地理空間的人在對話時出現的悖謬與荒唐在小說中體現得淋漓盡致。作者將地域空間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并置呈現,性別敘事在這種多重視域的空間化寫作中貫穿始終,作家將地理位置性別化,讓女性角色承擔“返魅”的意味,使得傳統性別秩序在不同空間中反復呈現。從小說的空間化角度探索貫穿文本的性別敘事,有助于了解敘事中作家對民族內部傳統性別秩序的態度,以及土家族在面對現代化沖擊時兩性關系的變與不變。
一、地理空間
小說里的人物與現實存在的人一樣,必須在具體存在的地理環境中相互交往。因此,生存空間具體表現為個體存在的地理空間,地理空間的物理屬性表現為小說中的空間場景。地理空間是人物活動的現實場所,也是文本敘事中開展的基點。《舍巴日》中的地理空間是十必恰殼—里也—馬蹄街—港口,孫健忠將不同形態的土家族文明并行擱置,既沒有單純否定現代理性社會中另一個原始的“我”的存在,也沒有單純肯定勢不可擋的現代文明。“十必恰殼”是原始巴人居住的地方,十必是小野獸,恰殼是大森林,那里的人們說著古老的巴語,跳著“撒憂爾嗬”和“舍巴日”舉行古老的儀式,恪守古老的傳統,他們“歡樂多于痛苦”。“里也”是“可耕種的土地”,即農村。在這里,土家族人靠以土地為生,大瓦房在村子里錯落有致,一派寧靜、自足的景象。以獨眼老惹為代表的里也人是轉變狩獵采集方式后的生產力代表。馬蹄街是農產品聚集地,商品經濟發展水平較農村高。但馬蹄街上有些人心術不正,買賣中出現欺詐行為。港口即大城市,是孫健忠筆下土家族人要面對的必然發展趨勢。老惹的兒子寶光、寶明去大城市打拼,在金錢的誘惑下逐漸“異化”,將自己看作不斷生產的機器,逐漸忘卻土家族人的歷史與傳統。作家通過人物在這四個地理空間的轉換,不斷審視土家族歷史發展過程,指出一種明顯的文化悖論。
十必恰殼—里也—馬蹄街—港口轉換成小說中的主人公,即:掐普—老惹、寶亮—巖耳—寶明、寶光,實質上即:女—男—女—男。可以看出,地理空間實際上被性別化了,而地理空間的性別化又反過來指涉了女性的“他者”地位。地理空間與主人公的性格十分貼切。大森林是茂密的、神秘的、多產的、感性的,正如女性性格中的柔軟及擁有神秘的生殖力量。農耕土地是堅硬的,正如老惹性格固執一樣。馬蹄街界于城市與農村之間,雖已發展但水平還不太高,如巖耳一樣雖已商品化、為人精明,但她依然無法擺脫舊習俗的桎梏。寶光和寶明的雄心勃勃象征著城市的發展,并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了“異化”。兩名女性分別代表十必恰殼和馬蹄街這兩個空間,一個是原始、愚昧的地方,另一個是商品經濟開始發展的地方,而男性則代表里也和港口城市這兩個地方,里也擁有人賴以存活的土地,而城市則象征著為人向往的更高級的生活,男性總體上象征更好的生活、更先進的生產力,而女性則更多代表原始的、未開化的力量,其實是指代了女性的“他者地位”。
此外,地理空間的流動與選擇體現出女性的“第二性”特征。掐普和寶光、寶明都是從一個地理空間到另一個地理空間,地理空間的錯置不僅使他們的身體流浪,文化的“錯位”感更使得他們的心靈經受了流浪。掐普從原始部落來到農耕社會并觸摸到商品經濟,她的流浪富有強烈的隱喻意味,象征著傳統文化的流浪。掐普來到農耕社會后,發現這里的巴人已經失掉了很多自己的歷史與傳統,不跳舍巴日,不敬白虎神,“不得了,白虎是老祖宗,我們子孫怎么能趕他、射殺他?掐普開始發現里也人的不善了。[5]”她的丈夫不親近她,她也不用像在大森林里一樣守著部落的火堆,只是不斷地耕作、耕作,最后她發出了感嘆,“啊,親愛的十必掐殼,多么叫人懷念,掐普好悔啊,她為什么要離開自己的部落,跑到里也這個痛苦的地方來呢?[5]”這是掐普對以前生活的懷念,也是作者發出的感嘆,民族的傳統和歷史多么令人懷念!掐普,這一十必恰殼的代表,在經歷了排斥、融合的過程后最終因無法適應現代社會,又找不回自己的家園,真正成為了流浪者。寶光和寶明在大城市的流浪導致了其“異化”,他們回到家鄉后,一句話也不說便倒床睡了七天七夜,“唉,我累,我累,累……[5]”“我怕,怕,怕……那火車叫得好嚇人啊!還有汽車,滿街來來去去的汽車……[5]”“‘真不知道,當初我們為什么要跑到這個鬼地方來?’‘你后悔了?’‘我想回去,我們家鄉多清靜啊,多安逸啊!’…[5]”寶光和寶明在夢中說的話真實反映了他們的處境:在大城市里像機器一樣工作、生活。然而他們醒來后聽說自己睡了七天七夜,便慌張地背起行李要再次出門,他們把金錢看得比土家族人最重要的節日——趕年更重要。“阿媽,如今世界上的事,我和你老人家難說清楚。外邊是不清靜,我和寶明是去吃苦、受罪。可是我們會慢慢慣勢的,會喜歡過外邊那種生活的。阿媽,這是‘時代’……[5]”這是土家族人面對現代工業文明時的向往與焦慮,他們縱然在大城市中艱難打拼,也要義無反顧地擁抱它,這是不可抑制的現代化潮流的巨大誘惑力。掐普、寶光兩兄弟的不同選擇顯示出理性男性與感性女性之間的差異,掐普拋棄自己在文明社會打下的基礎,“后退”回去尋找自己的原始部落,這是女性更念舊、更感性的體現,原始部落在這里像母親一樣可以給予掐普溫暖。寶光和寶明在遭受心靈的磨難與流浪后,理性地選擇繼續“出走”,去習慣大城市的生活與節奏,城市像父親一樣給與他們力量。他們奔赴象征男性的城市,又成為城市象征中堅硬的一部分。
《舍巴日》中的地理空間是有性別的,男性如老惹的三個兒子奮力沖向馬蹄街、港口城市,男性的拼搏、理性象征著城市與發展,掐普的蒙昧、神秘象征著森林與落后,巖耳的小精明正如商品經濟剛起步的馬蹄街。男性在發展過程中占據著重要的、富有活力的部分,他們代表的空間是堅硬的、理性的,女性要么趨于原始、尚未開化,要么理性程度不如男性,她們代表的空間是神秘的、柔弱的,作家利用性別化的地理空間,敘述了土家族女性在歷史發展過程中作為“他者”的位置。
二、神圣空間
神圣空間是指“某些空間由于它的特殊性而被賦予了‘圣’的特性。[6]”,“在世俗空間中有時也能體驗到能夠喚起空間的宗教體驗所特有的非均質的神圣價值。[6]”《舍巴日》中多處描寫掐普跳舍巴日、敬白虎神、敘述洪水神話的場景,她雖已脫離十必恰殼這個原初語境,但每當這些場面出現時,這些空間對她有著神圣意味,構成了她在里也的神圣空間。小說在神圣空間內也不斷推動傳統性別秩序的呈現,在不斷“祛魅”的現代社會,掐普身上的“魅”一部分被認可一部分被排斥。
查乞在土家語里是錦雞的意思,她兒時便從十必恰殼來到里也,早已習慣里也人的生活。當獨眼老惹想給寶亮定門親事時,他“急忙去找那位一胎生出五男二女、又會捉鬼弄神的查乞,求她給老三寶亮找個合適的女人。[5]”可以推測,查乞在里也的生活里有部分是與“神鬼”有關的。或者,她從十必恰殼來的這一身份使得她身上帶有某種神秘意味。當掐普想要尋找祖先白虎神的幫助時,“她去找同是從十必掐殼部落來的查乞。一升米,兩顆雞蛋,錢紙和香,使查乞變成神的信使。她騎著走馬,嘀嘀嗒嗒回到遙遠的武離鐘落山,又把老祖宗廩君白虎神請來。[5]”這種古老的巫術有著神秘的力量,查乞的身體作為白虎神與人們溝通的媒介,逢請必應。掐普是查乞從原始部落帶到里也來的,她身上也充分體現了“魅”的特點。當查乞叫她挑選一個人作為她的丈夫時,“她不敢挑,只在心里默默數著,數到十五(這是個吉祥的數字)的時候,隨手抽出一張。就是這個了。這不是她的意思,是天的意思,是白虎神的意思。[5]”她的命運像古老的部落一樣遵從保護神的意愿,將命運的決定權交給白虎神。當掐普踏入現代社會后,她依然遵從古老的信仰,曾前后兩次尋求過白虎神的幫助。一次是當她不明白丈夫為什么對她不理不睬時,白虎神在查乞身上附身后告訴了她原因,她請求白虎神將巖耳吃掉。還有一次是當寶亮被關進監獄后,她請求白虎神將自己的丈夫帶回來。在掐普的眼中,丈夫的無愛是因為其魂魄被其他女人“勾走了”,于是她跑去貓記飯鋪找巖耳要求比試投劍、采野果、打野豬、跳舍巴日,要求她歸還寶亮的“魂”。像掐普這樣想依靠神靈殺死情敵、到情敵面前“索魂”等做法在現代文明中是不可理喻的,體現出其原始、蒙昧的特點。白虎神從頭到尾都沒有幫助掐普任何事,她用自戕的極端手段換得了寶亮的同情,寶亮實際上主導了她的命運、愛情與婚姻。在掐普的神圣空間里,白虎神的力量受到了質疑,她的命運也不由神來決定,而是由她現實中的丈夫來決定。
掐普是原始文明的象征。謝友祥認為,土家語稱呼祖父為“阿譜”、“爬譜”等,與“掐普”音近,所以掐普還有比“花兒”更深的含義——老祖宗[7]。他的分析有一定道理,掐普不僅來自原始森林,她還將民族的歷史帶了回來,她像老祖宗一樣了解民族的過去。舍巴日最初用于祭祀等儀式場合,古老的儀式歌成為原始文明的標志,傳播舍巴日的掐普也就成了原始文明的載體。不僅如此,掐普還告訴里也人人死是一件值得快樂的事情,應跳“撒憂爾嗬”,她將阻擋白虎進門的弓箭拔掉,提醒人們白虎神是巴人的祖先,應該歡迎等等。掐普是“魅”的代表,她代表民族的過去,她身上體現出在現代社會不受歡迎的“原始”“野蠻”與“落后”,然而也正是這個來自原始部落的野人帶回了民族傳統,恢復了某些已被“祛魅”社會遺忘的民族文化。
《舍巴日》中的洪水神話作為隱喻貫穿小說的整個謀篇布局,隱喻了土家族的發展。“滔天的洪水退了,世間上沒有人了,只剩下葫蘆船上的兩兄妹,阿哥叫布所,阿妹叫雍尼。[5]”在孫健忠看來,現代化就像一場洪水,是對土家族文化的一次重大考驗,但土家族文化的根脈會像洪水神話中的布所和雍尼一樣存活下來并繼續繁衍生息。洪水神話與文中多處內容相互照應,小說最后部分有一場大雨下了三天,雞、豬等都患了瘟病,掐普說:“阿爸老祖宗,只怕要漲齊天大水了,老祖宗,世間上就會沒得人了,救救我男人吧,只剩下葫蘆船上的兩兄妹了。[5]”掐普內心深深地恐懼著洪水,她甚至認為應該殺一個人去敬白虎神。里也社會里法律規定連牛都不準隨意殺,更何況用人祭祀這種野蠻的儀式?掐普總是與現代文明格格不入。
小說中的巖耳與木瓜丈夫是表姐弟,她受娘家脅迫嫁給表弟,就像洪水神話中的“兄妹婚”一樣。洪水神話中的“兄妹婚”有著神圣意味,是民族繁衍生息的力量,但孫健忠有意打破這個空間,將“兄妹婚”看作是愚昧的、阻礙民族發展的。這場大雨就像一場儀式,古老的神話提供前車之鑒:洪水會沖走必然要被沖走的人,即不利于社會發展的人,比如木瓜表弟和野人掐普;洪水最終留下了寶亮與巖耳,一個美麗、精明,一個踏實、肯干,他們的結合承載了民族的希望與繁衍生息的力量。
小說在“返魅”與“祛魅”的敘事中往來穿梭,查乞和掐普都是“魅”的代表,巖耳雖想徹底“祛魅”,卻無法擺脫傳統思想的束縛。寶亮不斷對掐普進行“祛魅”改造,他掌控了掐普的感情,他也成為掐普神性空間運行的中心。寶亮出獄后與巖耳終成眷屬,既是打破了“兄妹婚”的神性空間,又寄托了作家對新神話的期待,期待他們的結合能帶來新的力量。
三、文化權力空間
福柯認為,“空間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礎。空間是任何權力運作的基礎?[8]”“空間乃權力、知識等話語,轉化成實際權力關系的關鍵。[9]”即:空間不是靜止的、死亡的,是一種權力表征的方式,在一個空間內,不同的人被賦予不同話語,產生不同權力。文化權力空間在小說中的呈現寓于人物關系中,人物的刻畫與人物關系體現出不同話語的較量。《舍巴日》在文化權力空間內通過兩性之間的位置、兩性關系等方面指涉了女性的“他者”身份。
從女性特征來看,掐普與巖耳代表了女性的兩個極端。掐普是從大森林里走出來的,身上擁有與理性文明不同的特征,她不洗臉、不洗澡、不梳頭,一身騷臭,是野人模樣。她不懂文明的法則,把跑出去的家豬打死后扛回來,渾身有使不完的力氣,她身上原始、蒙昧的特征不討男性喜歡。而巖耳則積聚了為男性激賞的所有條件,她為人精明、風情萬種,“加上她完全照一個城里女人最新派的打扮,噠噠響的高跟靴,屁股包得緊緊的褲子,米黃色毛線開胸衣,在手腕上和手指上閃閃發亮的手表和金戒指,渾身散發出的捉摸不定的異香,使她顯得無比華麗和高貴。[5]”巖耳是一個迷人的精靈,是貓記飯鋪里的“搖錢樹”,是顛倒眾多男人心魄的女人,她是“現代物質文明的樣品”。無論是野蠻的掐普還是柔情似水的巖耳,她們都被“物化”,被標簽化、被反復觀看。掐普的“原始人”裝扮、生活習慣被人嘲笑、戲弄,巖耳的美則被物化成城市的復制品,高跟靴、包緊的屁股、毛線開胸衣、手表和金戒指、異香,城市文明的包裝更加突出她的女性特征,巖耳成為城市物質的消費者,而她也成為男性的消費對象,滿足男性的欲望與窺視。西蒙娜·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概括出:“女人既是夏娃又是圣母瑪利亞。[10]”無論將女性看作天使或者惡魔,其實質都是將女性作為不平等主體對待。巖耳既是“迷人的精靈”,又是害寶亮進監獄的間接推手,她美,但也有“毒”,男人必須當心。當掐普第一次聞到巖耳身上的香味時,她認為正是這香氣勾走了寶亮的“魂”,于是她回里也后摘了很多野花戴在身上,希望這樣的香味能吸引男人。在這里,巖耳已被當作包括掐普在內的許多女性的“樣板”,她們觀察她,模仿她。男性設下的刻板印象將女性同化為帶有香氣的、溫柔的、有鮮明女性特質的。所以當掐普長久地糾纏著寶亮,跳舍巴日想討得他的喜歡時,寶亮并沒有從她身上找尋到任何“女人”的愉悅感,不惜用暴力拒絕她的要求。“她要,她要……她受不了哪,就會死哪!讓那個該死的巖耳,把寶亮的魂魄退回來……老祖宗,老祖宗……[5]”掐普體內不斷萌動的生命力催發了“我要,我要”的乞求,向男性乞求。不僅在男性的眼中,掐普不受人喜歡,甚至在女性的觀念里,像掐普這樣的野人算不上“真正”的女人。“真正”的女人應該像巖耳一樣有嬌嫩的臉龐和豐腴的身體,可以撫慰男子的身體和心靈。寶亮的身體和心都屬于巖耳,而掐普一樣都沒有,與其說掐普敗給了巖耳,不如說她敗給了先進的“文明”。
掐普與巖耳的特征被孫健忠刻畫得淋漓盡致,而她們與男性的關系更體現出男性的主導地位。掐普原先所在的部落里,分工極為明確,“男人進山打獵,下河捕魚,女人或出去摘野果子,或留下帶孩子,烤獸肉和守火堆。[5]”這說明男性在掐普所在的部落里已經占據經濟主導地位。掐普來到里也后,認獨眼老惹為阿爸,跟他學做陽春,老惹總是一種包容的、指導的姿態管理掐普的生活、勞作,因為他認為掐普是需要被管教的“野人”,潛意識里將她放在比現代人低的位置上。巖耳雖美麗、精明,但也沒能逃過“姑家女,伸手取,舅家要,隔河叫”的傳統習俗,被貓家當“續骨種”接過來成為一個傻子的媳婦,平日里要忍受像西尼嘎這樣的男性客人的調戲,“讓這個風騷女人給自己端飯送菜,高興時調笑幾句,把眼睛勾著她那最誘人的部位看,甚至乘人多擁擠時,故意貼近那個柔軟的身體,伸手隨便在什么地方捏一把,以不多幾個錢,買來一種享受,實在不算吃虧。[5]”而一有風吹草動就被貓老板收回所有的鑰匙,失去經濟大權。巖耳沒有主導自己命運的權利,她需要不斷犧牲自己的身體為貓家打理好飯鋪,即使是明知道遇見了想占她便宜的人,“故意扭扭迷人的腰肢和屁股,回頭給西尼嘎一個極其嫵媚的笑臉,仿佛給他一種暗示,一種鼓舞,一種幻想。[5]”將一個來自原始部落的女人與一個商品經濟發展中的女人聯系起來的是一個來自農村的男人。寶亮迫于老惹自殺的壓力而將掐普娶進門,但他卻不愛她,他愛的是精明美麗的老板娘巖耳。小說中有兩段分別關于寶亮與巖耳、掐普親熱過程的描寫:
“她快活得發著抖,又去熱烈地吻他,不停地長久地吻,將一個舌頭伸進他的嘴里。她還狼一樣用牙齒咬他,用舌頭舔他……一張嬌嫩的臉盤與一張粗糙的臉盤相互摩挲,如牛挨癢。后來他們倒下了,在草地上胡亂翻滾半天,終于聯結成一體,直到彼此將對方捏得粉碎。[5]”
“這晚上,是掐普一生中最快樂的一個晚上。她發了瘋似的,大聲哼著,呻吟著,哭著,喊叫著。寶亮用手捂她的嘴。她又像母狼一樣,殘忍地撕咬寶亮,露著尖利的牙齒,伸出長滿小刺的舌頭,還伸出一對鋒利的前爪……若不是寶亮奮力反抗,說不定已被她撕個粉碎。吃進肚子里了。她還唱起歌來,大聲大聲唱,像狼的嚎哭。[5]”
仔細對比這兩段描寫,掐普更具有“原始”的特點,她像只野獸或動物一樣,而巖耳的“嬌嫩”則讓寶亮非常享受。同樣是用舌頭、“像狼一樣”舔寶亮,然而寶亮所傾注的情感完全不一樣。他對巖耳是出于真心喜歡,而對掐普則是同情。用性來滿足一個女人的需求,讓女人臣服,寶亮似乎已經占據一個更高的位置,在這個位置上,無論是原始女性,還是現代女性,她們身體的欲望都需要他來滿足。“她并不是因為認識到自己的劣等性才把自己交給男人,而是因為她把自己這樣交給男人,她才接受了她是劣等的這個觀念,才建立了關于這種劣等性的真理[10]。”就是這樣兩個女人,在寶亮進監獄的時候,巖耳“厚起臉皮來闖鄉政府”為寶亮伸冤,當她被擋回來后,她倒在床上直流眼淚。巖耳是極度傷心的,既為牢里的寶亮哭,也為自己悲慘的命運而哭。掐普并不知道寶亮去了哪里,她滿山遍野地去找尋寶亮,把屋里屋外的地方都找遍了,她甚至用手去扒開每一座墳墓,看看里面有沒有她的丈夫,她野蠻卻情真意切!巖耳與掐普這兩個女人都如此堅定地愛著寶亮。最有趣的是結局設定,真相澄清后寶亮回到里也,掐普和巖耳和睦得如同親姐妹。掐普與巖耳在寶亮進監獄后開始和解,等寶亮回來后,掐普選擇了悄悄離開回到自己的世界,成全寶亮與巖耳的愛情。在這段三角關系里,掐普與巖耳從競爭對手變成了姐妹,而這個農村男人完全成了中心。
《舍巴日》中的女性沒有主宰自己命運的能力,兩性關系呈現出拯救與改造的態勢。因為男性的需求,查乞將掐普從原始部落里帶出來,獨眼老惹不斷改變她勞作的方式,教她如何適應農耕生活——比采集漁獵更穩定的生活方式。而掐普的男人——寶亮,則傳輸給掐普現代人關于婚姻的觀念:婚姻要基于愛才能幸福。寶亮按照現代女性的模樣改造掐普,送她香粉、新膠鞋和起花滌確良襯衣,叮囑她“拖鞋落雨天穿。衣服等夜邊洗過澡就穿。[5]”寶亮用男人的眼光改造著這個從原始森林來的女人,一步步改變她對自我的認知,并將自己逐漸同化成“商品化”的女人。巖耳表面上雖是風光的飯鋪老板娘,但她是迫于舅家壓力嫁給了一個傻子,她一輩子都被限制在這個小小的空間里,沒有愛,沒有性,只有唯利是圖的舅舅、只會呵呵的傻子和一幫占她便宜的男人。當她遇到寶亮時,她像遇到救命稻草一樣死死抓住,但她的命運依然跟這個男人的命運緊密相連,寶亮進監獄,貓老板便沒收她的鑰匙,使她失去權力;當寶亮出獄后,她便同時獲得了自由,恢復飯鋪老板娘的身份。寶亮實際上拯救了巖耳的愛情與生活。
《舍巴日》里的男性與女性處于“看”與“被看”的位置,男性在兩性關系中體現出其主導位置,他們掌控著女性的命運,這種不對等關系突出了男性的力量與中心位置,并將女性置于“他者”的位置上。
四、結語
《舍巴日》中的地理空間是有性別的,從十必恰殼—里也—馬蹄街—港口,小說中的男性占據城市與土地,女性占據森林與小鎮,而女性傾向于原始、愚昧、感性、軟弱,男性則傾向于現代、文明、理性、精明強干,所以男性和女性代表的地理空間帶有不同特點。在神圣空間里是“魅”與“祛魅”的博弈,查乞和掐普這兩個從十必恰殼來的女人在文明社會里充當“魅”的角色,寶亮成為掐普神圣空間的中心,為了他,掐普多次請求祖先白虎神的幫助。以寶亮為代表的男人則是現代社會中“祛魅”的象征,他按照現代人的生活方式不斷改造掐普,不斷祛除她身上的“野性”。小說中的女性與男性處于不對等的位置,女性特征被極端化,要么野性如掐普,要么可愛如巖耳,她們與男性之間的關系是被改造、被拯救的關系。通過考查《舍巴日》中性別敘事在不同空間中的呈現,可看出小說中不同空間的疊合呈現出傳統性別秩序,體現男性的主導力量,女性仍處于“他者”位置。
[1]亨利·列斐伏爾.空間社會產物與使用價值[M].王志弘,譯//包亞明.現代性與空間的生產.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2]米歇爾·福柯.不同空間的正文和上下文[M].陳志梧,譯//包亞明.后現代性與地理學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3]愛德華·W·索亞.第三空間:去往洛杉磯和其他想象地方的旅程[M].陸揚,譯.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4]龍迪勇.論現代小說的空間敘事[J].江西社會科學,2003(10).
[5]孫健忠.猖鬼[M].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2.
[6]龍迪勇.空間敘事研究[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4.
[7]謝友祥.土家族文化尋根中的未來關懷——重讀孫健忠的《舍巴日》[J].民族文學研究,2001(3).
[8]米歇爾·福柯.空間、知識、權力—福柯訪談錄[M].陳志梧,譯//包亞明.后現代性與地理學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
[9]戈溫德林·萊特,保羅·雷比諾.權力的空間化[M].陳志梧,譯//包亞明.后現代性與地理學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
[10]西蒙娜·波伏娃.第二性[M].桑竹影,南珊,譯.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6.
I247
A
1672-3805(2016)04-0066-06
2016-04-24
譚婷(1992-),女,中央民族大學少數民族語言文學系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
———評《土家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