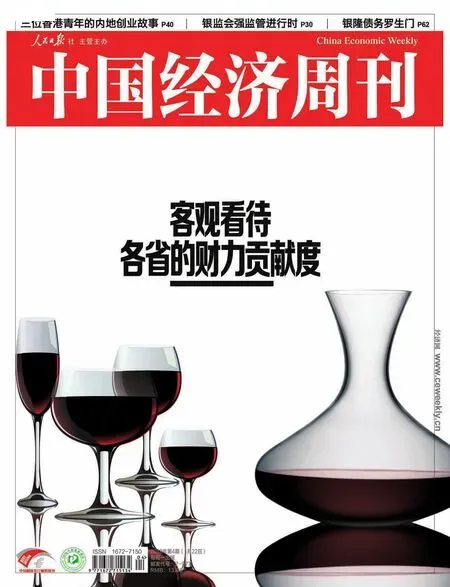加快“大金融”監管整合步伐
葛豐
近日有媒體報道,按照中編辦的安排,國務院辦公廳已將其經濟局六處設立為金融事務局,該機構將主要負責“一行三會”行政事務方面的協調。
此舉可以被看作中國加快金融監管整合步伐又一標志。在此之前,與之類似的金融監管框架性改革還包括央行新推出“宏觀審慎評估體系”等等。而這些近期加速呈現的“大金融”監管思路嬗變,正合去年底發布的“十三五”規劃建議稿所提出的“實現金融風險監管全覆蓋”戰略方向。對此大監管戰略,業內人士形象地稱之為“超級監管”。
人為構建的金融監管框架需要不斷去適應金融市場發展趨向。因此,中國的金融監管基本框架從統一到分業再到統一,絕不是簡單的重回起點,而是在更高水平的金融格局中主動求變的全新征程,其合理性乃至必要性在于:
首先,綜合監管符合金融機構混業經營發展趨向。這主要體現在混業經營相比分業,能夠更為有效地整合市場、產品、技術、信息、資金等資源,有利于金融機構形成規模效益與損益互補機制。因此,伴隨近年來金融市場化進程加速,國內金融機構業務品類不斷外延,經營范圍不僅觸及銀行、保險、證券、基金、信托等各分支領域,而且很多看似單一的創新業務,實則也已很難被嚴格歸類到任何一種傳統金融門類中去;而面對這種情況,只有審慎的、全覆蓋的綜合監管,才能同時滿足金融發展與金融穩定雙重需求。
其次,綜合監管是應對“新常態”復雜多變經濟形勢的重要抓手。這主要體現在當下金融調控面臨的任務相互關聯、相互牽制,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等多重任務只有在各種調控手段相互兼容、高度協同的前提下,才能并行不悖向前推進。譬如舉個最簡單的例子,相比較易把控的社會融資總量,融資結構配比對于穩增長、調結構、防風險等任務,可能更是一個具有帕累托改進效應的關鍵變量,而這個變量究竟如何設置目標,以及如何達到目標,顯然只有在“一行三會”等所有監管機構充分共享信息、密切統一行動的情況下,才能有效逼近最優解。
第三,綜合監管是中國金融開放進程中亟需補強的制度基礎。這主要體現在因為種種原因共同作用,當今全球金融體系動蕩加劇,因此,在中國金融開放進程已不可逆轉的大背景下,中國有必要依托綜合監管等制度建設,及早謀劃如何應對越來越顯著的外部風險侵襲。譬如對于套利資本流入流出,與之相關的除了央行主要負責的匯率、利率以及資本項目管制等環節,分別在“三會”監管下的金融機構與金融市場的表現同樣舉足輕重。
當然,綜合監管并非只有一種模式。事實上,即使是在發達國家,監管模式也各不相同且持續處于動態改進過程中(但總的方向是統一性加強)。因此,對于身為新興經濟體的中國而言,當下真正可行的選項,是在堅持發揮分業監管所長的基礎上,對落后于形勢的部分,有針對性地加快金融監管整合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