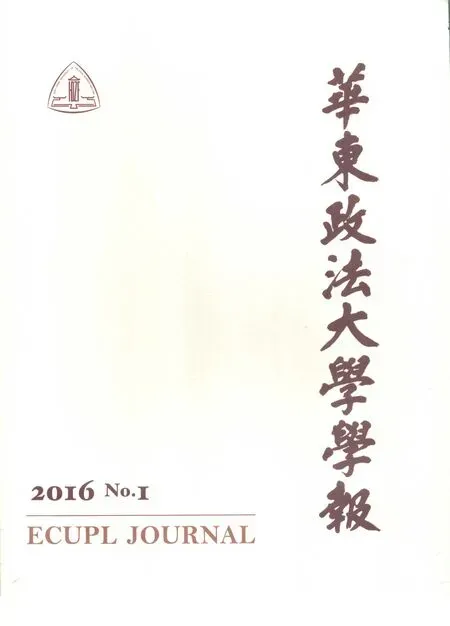國家所有和國家所有權
——以烏木所有權歸屬為中心
朱 虎
?
國家所有和國家所有權
——以烏木所有權歸屬為中心
朱虎*
目次
一、烏木歸屬國家所有的可能依據及反駁理由
二、國家所有權的法秩序闡釋
三、烏木情形中的國家所有權
四、相關私法規范的解釋
五、結論
憲法中的國家所有和私法中的國家所有權具有法秩序的一致性,后者是前者所具有的國家內容實現義務功能的展開方式之一,同時要受到前者的約束,兩者共享了規制這個規范目的。并非所有財產都應采取國家所有方式實現規制目的,選擇何種規制方式應考量多個因素并按照比例原則進行審查。在烏木情形中,對烏木挖掘的負外部性的消除不應將烏木歸屬于國家所有的規制方式實現,相關的私法規范應據此予以解釋,甚至進行合憲性的目的性限縮,烏木不能由國家直接享有或取得所有權。
國家所有國家所有權規制埋藏物烏木
《憲法》中所規定的國家所有相關條款,之前一直沒有在教義學上得到充分的重視和精細的教義學闡釋,其與私法中所規定的國家所有權之間也處于“剪不斷,理還亂”的關系之中。但是,這兩年所發生的烏木歸屬、狗頭金歸屬、風能歸屬等事件,卻“吹皺了一池春水”,導致了對憲法中的國家所有條款、私法中的國家所有權條款以及它們之間關系的思考和討論。本文即選擇以烏木所有權的歸屬作為中心,討論憲法中的國家所有和私法中的國家所有權。
一、烏木歸屬國家所有的可能依據及反駁理由
有觀點認為烏木歸屬國家所有,主張烏木屬于特定的客體,而現行規范或者規定這些客體屬于國家所有,或者規定可由國家依據特定的地位而取得所有權。這些觀點或者認為烏木屬于文物、古生物化石、礦產資源、野生植物資源或者其他自然資源,因此依據明確的法律規定直接屬于國家所有;或者認為烏木屬于天然孳息或埋藏物,因此由國家取得所有權;或者認為烏木屬于無主物,依據《民事訴訟法》“認定財產無主案件”的特別程序規定,經公告后無人認領的,歸國家所有,〔1〕“彭州天價烏木案”,即吳高亮、吳高惠訴四川省彭州市通濟鎮人民政府行政糾紛案件中,原告之一吳高亮即認為,烏木屬于野生動植物資源,但依據《物權法》第49條的規定,法律沒有規定的動植物資源,就不屬于國家所有;同時,烏木屬于孳息,應由用益物權人取得。而被告主張原告并非烏木的發現者,也并非從原告的承包地里挖出,同時烏木屬于埋藏物,依據《民法通則》第79條第1款屬于國家所有。而一審法院和二審法院都確認烏木并非由原告吳高惠發現,也并非在原告吳高惠的承包地內發掘,因此,吳高惠與被訴具體行政行為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關系;同時認為,本案不存在平等主體之間的民事爭議問題,被訴行政行為也非行政裁決行為,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1條規定,不符合行政附帶民事訴訟的受理和審理條件,因此,吳高亮要求法院在審理行政案件的同時對烏木所有權爭議一并進行審理的理由不成立。筆者依次剖析如下。
(一)文物、古生物化石、礦產資源、野生植物資源或其他自然資源
結合《物權法》第51條和《文物保護法》第5條第1款、第4款第1項和第6條的規定,中國境內出土的一切可移動文物,除確定屬于集體所有和私人所有的之外,皆屬國家所有。該法第1條宣示立法目的為“繼承……歷史文化遺產”,結合《文物保護法》第2條所列舉的文物類型、《文物認定管理暫行辦法》第1條第2款以及日常語義,〔2〕《文物認定管理暫行辦法》第1條第2款規定:“本辦法所稱文物認定,是指文物行政部門將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文化資源確認為文物的行政行為。”《辭海》將文物界定為“遺存在社會上或埋藏在地下的人類文化遺物”,參見《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版,第2383頁,“文物”詞條。可知文物應屬文化遺物,顯然在文義上不包括烏木在內。
依據《古生物化石保護條例》第3條第1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管轄的其他海域遺存的古生物化石屬于國家所有。該條例第2條第2款明確規定“本條例所稱古生物化石,是指地質歷史時期形成并賦存于地層中的動物和植物的實體化石及其遺跡化石”,烏木可能并非地質歷史時期形成,也并非化石,故并非該條例所稱的古生物化石。
依據《憲法》第9條第1款、《物權法》第46條、《礦產資源法》第3條第1款和《礦產資源法實施細則》第3條的規定,礦藏或礦產資源屬于國家所有。《礦產資源法實施細則》第2條則規定:“礦產資源是指由地質作用形成的,具有利用價值的,呈固態、液態、氣態的自然資源。礦產資源的礦種和分類見本細則所附《礦產資源分類細目》。新發現的礦種由國務院地質礦產主管部門報國務院批準后公布。”烏木并未被列入《礦產資源分類細目》,也并未由地質礦產主管部門公布為新礦種,因此,至少在目前,烏木不屬于礦產資源。
依據《物權法》第49條規定,法律規定屬國家所有的野生動植物資源,屬國家所有。同時,《野生植物保護條例》第2條第2款明確規定:“本條例所保護的野生植物,是指原生地天然生長的珍貴植物和原生地天然生長并具有重要經濟、科學研究、文化價值的瀕危、稀有植物。”烏木并非具有生命特征的植物,因此并非屬于國家所有的野生植物。
因此,至少從文義和現行規定上而言,烏木無法依據上述規范被認為屬于國家所有。但是,有疑問的是,烏木能否有可能通過法律的新規定被認為屬于文物、古生物化石、野生植物資源,或者被公布為新礦種,或者能否應當進行類推適用上述規范,從而屬于國家所有,仍需要進一步考慮。
同時,《憲法》第9條第1款規定:“礦藏、水流、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等自然資源,都屬于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規定屬于集體所有的森林和山嶺、草原、荒地、灘涂除外。”《物權法》第48條規定:“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等自然資源,屬于國家所有,但法律規定屬于集體所有的除外。”由此,烏木是否能夠被認為屬于“等”所包含的其他自然資源,從而屬于國家所有,仍值得思考。
(二)天然孳息
《物權法》第116條第1款規定:“天然孳息,由所有權人取得;既有所有權人又有用益物權人的,由用益物權人取得。當事人另有約定的,按照約定。”如果烏木是在國家所有的河道或土地中,且該河道或土地上無用益物權,則有觀點主張,烏木屬于土地的“天然孳息”,從而由國家取得所有權。〔3〕梁慧星教授即持有此種觀點,參見徐霄桐、李麗:《民法專家激辯天價烏木歸國家還是發現者》,載《中國青年報》2012年7月7日第3版。龍衛球教授也主張烏木屬于天然孳息,但其認為,如果烏木確實發掘于村民承包地之中,那么應由用益物權人取得所有權,參見龍衛球:《烏木權屬紛爭折射中國法理變遷》,載《河南法制報》2012年8月3日第14版;據此,似乎如果烏木是發掘于國有土地上,那么應由國家作為土地所有權人而取得烏木的所有權。但本文認為,此時根本不能夠適用《物權法》第116條第1款。通常認為,原物的天然孳息是指原物的出產物或者按照該原物的用法所取得的其他收獲物。就土地而言,土地的出產物,指所有在土地上生長出來的東西,而土地的其他收獲物,指依據土地的用法產生的收獲物,比如石頭、沙子和其他的土地部分。〔4〕[德]拉倫茨:《德國民法通論》(上),王曉曄等譯,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05、406頁。但烏木并非土地上生長出來的出產物,也非依據土地的用法而產生的其他收獲物,故并非天然孳息。〔5〕有學者根據立法觀點認為該款的目的是對勞動的保護,故孳息似乎應限制于勞動所得的出產物,而烏木并非勞動所得,因此并非孳息,參見王永霞:《彭州烏木事件的法解釋學思考》,載《政法論叢》2013年第4期。反駁此種觀點的正確觀點則認為,孳息歸屬并不應采取“勞動保護說”,而是應當采取“延續取得說”,具體請參見金可可:《論烏木之所有權歸屬》,載《東方法學》2015年第3期。同時,天然孳息在與原物分離前必須是原物的成分,物的成分在分離后可能屬于天然孳息,也可能并非天然孳息,《物權法》第116條應能直接適用于天然孳息,并按照其規范目的,也能類推適用于分離后不屬于天然孳息的其他成分。〔6〕《德國民法典》第953條即規定了所有權人能夠取得分離后的物的出產物和其他成分。關于中國法,有觀點正確地主張,《物權法》第116條第1款應采取同樣的解釋方案,參見金可可:《論烏木之所有權歸屬》,載《東方法學》2015年第3期。而依據通常的交易觀念,土地包含了土壤、巖石、水文、大氣和植被等要素,烏木不屬于上述任何一種要素,故并非土地的成分。因此,烏木并非土地的天然孳息,也并非土地的成分,故無論是適用還是類推適用《物權法》第116條,國家作為土地所有權人都無法據此取得烏木的所有權。
(三)埋藏物
如果烏木在分離前并非物的成分,那么其是否屬于埋藏物?如果烏木屬于埋藏物,按照《民法通則》第79條第1款的規定,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隱藏物,〔7〕按照用語,似乎“埋藏物”指的是埋藏于不動產中的物,而“隱藏物”指的是隱藏于動產中的物,但由于法律后果相同,因此下文中統稱為“埋藏物”。歸國家所有,此時烏木應由國家取得所有權,國家應給予上繳單位或個人以表揚或物質獎勵。同時,依據《物權法》第114條的規定,發現埋藏物或隱藏物的,一般參照拾得遺失物的有關規定,而《物權法》第113條又規定,遺失物自發布招領公告之日起6個月內無人認領的,歸國家所有。
對于烏木是否屬于埋藏物,存在諸多反對觀點。第一種反對觀點認為,埋藏物的構成包括人為有意的埋藏,烏木不符合該要件。〔8〕王利明:《物權法研究》(上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472頁;王涌:《慎用國家所有權》,載《新世紀》2012年第6期;根據媒體報道,尹田教授和柳經緯教授也持有此種觀點,參見雍興中:《身價暴漲,地下烏木變國有》,載《南方周末》2012年5月31日;徐霄桐、李麗:《民法專家激辯天價烏木歸國家還是發現者》,載《中國青年報》2012年7月7日第3版。“彭州天價烏木案”中,原告也持有相同的觀點,來源:http://finance.chinanews.com/cj/2012/12-06/4386494_2.shtml,2015年6月14日訪問。但是,埋藏物規則的目的是確定一種不可能清晰的物權狀態,由該制度目的決定,埋藏物是否被有意隱藏無關緊要。〔9〕BGHZ 103, 101 , 109= NJW 1988, 1204, 1207; Staudinger/Gursky, 2011, § 984, Rn. 12; 王澤鑒:《民法物權》,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頁;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301頁。第二種反對觀點認為,《民法通則》第79條第1款中的“所有人不明”文義上隱含了埋藏物曾經有所有權人,埋藏物的所有權仍然存在,并非無主物,只是現在所有權人不明,〔10〕王永霞:《彭州烏木事件的法解釋學思考》,載《政法論叢》2013年第4期;金可可:《論烏木之所有權歸屬》,載《東方法學》2015年第3期。同樣的觀點,參見MünchKomm/Oechsler, 2013, §958, Rn. 3.; 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301頁。德國法甚至進一步要求,所有權人不明的情形必須是因為長期埋藏而導致,除此之外的原因導致所有權人不能被查明,應適用遺失物規則,Vgl. Westermann/Gursky/Eickmann,Sachenrecht, Aufl. 7, C. F. Müller Verlag, 1998, S. 484.; Staudinger/Gursky, 2011,§984, Rn. 4.。而烏木上不曾存在所有權,因此并非埋藏物。但是,即使在德國法中,絕對的通說認為,化石等不曾存在所有權的物,基于確定物權狀態的制度目的和相關主體相同的利益狀態,仍然適用或類推適用埋藏物規則。〔11〕BVerwG NJW 1997, 1171, 1172; Westermann/Gursky/Eickmann,Sachenrecht, S. 485.; Staudinger/Gursky, 2011,§984, Rn. 3a. ; MünchKomm/Oechsler, 2013, §984, Rn. 3. ; [德]鮑爾、施蒂爾納:《德國物權法》(下),申衛星、王洪亮譯,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519頁。因此,埋藏物的構成并非必然包含埋藏物曾經有所有權人這個要件,借此無法否定烏木并非埋藏物,自然也不能否定《民法通則》第79條第1款的適用。〔12〕參見王建平:《烏木所有權的歸屬規則與物權立法的制度缺失》,載《當代法學》2013年第1期。
(四)無主物
該觀點認為烏木無主,但在實體法中欠缺依據,故應依據《民事訴訟法》中“認定財產無主案件”的特別程序規定,尤其是該法第192條規定,人民法院發出財產認領公告滿一年無人認領的,判決認定財產無主,收歸國家或者集體所有,因此烏木最終應歸國家所有。但是,反對觀點認為,依據《民事訴訟法》第192條所做出的判決包括“認定財產無主”和“收歸國家或者集體所有”兩項內容,并非認定財產無主就必然收歸國家或者集體所有。在認定財產無主之后,仍應依據實體法規則明確該無主財產的所有權由何人取得,因此關鍵仍在于實體法規則,《民事訴訟法》的規定不能作為無主財產歸屬的實體法依據。〔13〕參見金可可:《論烏木之所有權歸屬》,載《東方法學》2015年第3期。
(五)總的評論
關于烏木歸屬,存在著以上不同觀點。試想,如果《民法通則》第79條第1款未規定埋藏物由國家單獨取得所有權,那么無論規定由發現人單獨享有所有權,還是規定由發現人與其他主體共同享有所有權,可能都不會導致如此大的爭論;如果放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同樣也不會產生這么大的爭論。但是,真正的教義學解釋絕非是通過規范偽裝個人的立場,而是從規范立場出發挖掘出法秩序中所存在的價值判斷,因此,只有結合中國社會新發展中價值觀念的變遷,形成對國家所有權進行法秩序的整體梳理之后,才有可能回答烏木是否應由國家享有或取得所有權這個問題,同樣也才有可能對現有的規范做出合乎整體法秩序的教義學解釋。
二、國家所有權的法秩序闡釋
關于國家所有權的闡釋,需從憲法中的國家所有和憲法秩序中的私法國家所有權兩方面進行探討。
(一)憲法中的國家所有
1.規范內容和功能
《憲法》第6條第1款規定了公有制,第9條和第10條分別規定了自然資源和部分土地的國家所有,第12條規定了公共財產,這些條文構成了《憲法》上有關國家所有的規范群。國家所有包括如下規范內容。
第一,合理利用。《憲法》中“國家保障自然資源的合理利用,保護珍貴的動物和植物”(第9條第2款前句)、〔14〕有學者認為,“保護珍貴的動物和植物”在客體上把“珍貴的動物和植物”與一般自然資源區別開來,表明對這種特殊資源要著重“保護”而非通常意義上的利用,體現了先進的環保理念,參見鞏固:《自然資源國家所有權公權說再論》,載《法學研究》2015年第2期。但無論如何,從廣義上而言,這種保護也可被納入到“利用”的內涵之中。“一切使用土地的組織和個人必須合理地利用土地”(第10條第5款)這些表述,是憲法中國家所有這一規范內容的具體體現。結合《憲法》第26條第1款的國家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的規定,其更是確立了國家所有的此種規范內容。具體而言,合理利用包括了如下內容:(1)利用主體,即誰可以利用;(2)利用對象,即利用什么;(3)利用內容,即如何利用。
由這一規范內容引申出公民合理和共同使用國家所有之財產的基本權利,該基本權利并不違反國家所有中“合理利用”的規范內容,反而是該規范內容的應有之義。同時,結合國家所有的有關“合理利用”的憲法上述相關規范以及《憲法》第33條第3款所規定的公民所享有之人權中所蘊含的行為自由,公民涉及生計的對國家所有之財產的合理和共同使用權可能還涉及《憲法》第42條第1款所規定的勞動權,由此,公民合理和共同使用國家所有之財產的權利充實了憲法中國家所有的規范內容。〔15〕在德國法中,對水資源、街道的共同使用權(die ungest?rte Teilnahme amGemeingebrauch)被認為屬于《德國基本法》第2條第1款所規定之一般行為自由的保護范圍,是基本權利的積極分享/給付權(Teilhabe- und Leistungsansprüche)的表現之一,Vgl. Maunz/Dürig, Grundgesetz-Kommentar, 2014, Art. 2, Rn. 59.。同時,該權利當然也受到《憲法》第51條所規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權利的時候,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之限制。此時,該基本權利被包含于憲法國家所有的內容之中,并對后者予以具體化,同時又受到了國家所有所包含的“合理利用”這一規范內容和《憲法》第51條的限制。因此,從憲法中的國家所有可以引申出公民合理共同使用國家所有之財產的權利。
第二,收益全民共享。《憲法》中“……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第6條第1款前句)、“……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第9條第1款)是這一規范內容的體現,這表明了國家所有財產的收益并非由政府或政府的某一部門所享有,而是由全民所享有。〔16〕參見王旭:《論自然資源國家所有權的憲法規制功能》,載《中國法學》2013年第6期。
第三,任何人不得侵占和破壞。這是對前兩項規范內容的反面性規定,《憲法》中 “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壞自然資源”(第9條第2款后句)、“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占……土地”(第10條第3款)、“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第12條第1款)、“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壞國家的……財產”(第12條第2款后句)這些表述,都表現了憲法中國家所有的這一規范內容。
其次,憲法中國家所有的規范功能表現在以下兩點。第一,國家的內容實現義務功能。國家必須制定一般性法律保護或防止憲法中國家所有的上述規范內容遭到侵害,并且要通過一般性法律的制定實現憲法中國家所有的規范內容。第二,國家所有是否具有防御功能?防御功能往往涉及基本權利對抗國家權力的功能,即如果立法、行政和司法判決侵害了公民基本權利,則可對此提出合憲性質疑。《憲法》第13條所規定的公民所享有的私有財產權享有此種防御功能,前述公民的合理共同利用國家所有之財產的權利也當然享有此種防御功能,如果立法限制這些基本權利,則這些權利作為基本權利可引起對立法內容本身的審查。但是,國家所有與公民的基本權利不同,關于國家所有的上述規范內容的具體實現有賴立法的形成,因此,當國家所有受到一般性法律“限制”時,該限制實際上是通過立法形成國家所有的具體內容,對此并不能提出合憲性質疑。《憲法》第12條規定了“公共財產”,而第13條第2款規定了“私有財產權”,這表明了公共財產和私有財產的不同屬性,體現了私有財產權作為基本權利,享有防御功能,而國家所有作為“公共財產”的形式之一,并非基本權利,不享有防御功能。〔17〕同樣觀點,參見李忠夏:《“國家所有”的憲法規范分析》,載《交大法學》2015年第2期。
2.國家所有的規范目的
按照《憲法》第6條第1款的規定,國家所有的規范目的是通過生產資料的國家所有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如果對這種政治目的進行憲法解讀,可以認為,憲法中國家所有的規范目的是通過國家所有來反對剝削、實現人權的平等保障,即國家所有本質上是作為一種規制手段而存在。〔18〕參見王旭:《論自然資源國家所有權的憲法規制功能》,載《中國法學》2013年第6期;鞏固:《自然資源國家所有權公權說》,載《法學研究》2013年第4期。即使認為國家所有應當從這種理想化的政治理念中解脫出來,仍要承認國家所有之上“公共任務”的存在。〔19〕參見李忠夏:《“國家所有”的憲法規范分析》,載《交大法學》2015年第2期。因此,無論如何,這里存在一個基本的共識,即憲法中國家所有的規范目的在于規制,國家借助其所有能夠在國家所有的財產領域中積極主動地進行規制,實現對國家所有之財產的保護和合理利用。
在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經典論述中,財產權的正當性被置換成私人所有的正當性,私人所有與個體自由緊密聯系在一起,法治國和消極政府也具有同樣的基礎。但是,絕對的私人所有在一些領域會產生極強的外部性,例如環境的污染及因為私利而導致的非理性的使用,導致公共目的與經濟盈利目的之間的沖突矛盾。因此,為了解決這些問題,社會法治國和規制國家理論由此產生,這使得私人所有權和公共所有權的傳統二分法變得模糊朦朧了,“在現實場景中,公共的和私有的制度經常是相互齒合和相互依存的,而不是存在于相互隔離的世界里”,〔20〕[美]奧斯特羅姆:《公共事務的治理之道》,余遜達等譯,上海三聯書店2000年版,第43頁。由此產生了規制的必要性。〔21〕對此具體的論述,參見[美]克里斯特曼:《財產的神話:走向平等主義的所有權理論》,張紹宗譯,張曉明校,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尤其是第九章;也請參見王旭:《論自然資源國家所有權的憲法規制功能》,載《中國法學》2013年第6期。
此時,規制是為了避免市場的失靈,國家有權進行管理、規劃和保護,其有利于促使國家公共任務的實現,而絕非利益的剝奪;從反面講,國家甚至有義務和責任進行規制。基于此,可能會采取多種規制方式,按照規制強度的大小,大致可以區分為對私人所有權的限制(包括對私人所有權的一般內容限制、管制性征收、征收)和直接設立國家所有。國家所有并非在所有情況下都優于私人所有,也并非在所有情況下都劣于私人所有。當論及“公共土地的悲劇”的時候,更為準確的理解是無人所有(無論是私人所有還是國家所有)的財產確實如此。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所采取的方式或者是設立私人所有,或者是由國家進行規制,“公共土地的悲劇”并非必然推導出私人所有的正當性。〔22〕See Hardi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162 Science 1247, 1248 (1968).事實上,并不存在在任何條件下、任何情形中都正當的所有制架構,更為重要的是,在具體的情況下,判斷何種架構總成本更低且總收益更高。〔23〕具體論述,請參見[美]科爾:《污染與財產權》,嚴厚福、王社坤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七章。無論如何,憲法中的國家所有中必然蘊含著規制目的,甚至可以認為國家所有本身就是規制的一種工具和手段。
(二)憲法秩序中的私法國家所有權
1.私法中國家所有權的規范內容
即使國家所有權與私人所有權存在諸多不同,國家所有權也是私法所有權的一種,應適用《物權法》第39條對所有權的一般規定,具有形式上的統一性,〔24〕參見王涌:《自然資源國家所有權三層結構說》,載《法學研究》2013年第4期。故國家所有權也具有占有、使用、收益、處分以及相應的排除權能,這些權能由于憲法中國家所有的規范目的、內容的限制,具有特殊的規范含義。
第一,占有以及相應的排除權能。《物權法》第56條規定:“國家所有的財產受法律保護,禁止任何單位和個人侵占、哄搶、私分、截留、破壞。”這里規定了包括國家機關在內的任何人不得侵占和破壞由國家享有所有權的財產,也實現了憲法中國家所有的任何人不得侵占和破壞的規范內容。因此,如果任何單位或個人實施了私法中的妨害或侵害行為,理論上而言,也可依據《物權法》第34條、第35條、第36條和第37條對國家所有權予以保護。〔25〕反對觀點參見稅兵:《自然資源國家所有權雙階構造說》,載《法學研究》2013年第4期;鞏固:《自然資源國家所有權公權說》,載《法學研究》2013年第4期。其均認為對國家所有權的保護主要是通過公法手段進行,但并未說明為何不能通過私法手段予以保護。
第二,私法上的合理利用。為實現憲法中國家所有之合理利用的規范內容,《物權法》規定了土地上可設立用益物權,并且“嚴格限制以劃撥方式設立建設用地使用權。采取劃撥方式的,應當遵守法律、行政法規關于土地用途的規定”(《物權法》第137條第3款);同時,“國家所有或者國家所有由集體使用……的自然資源,單位、個人依法可以占有、使用和收益”(《物權法》第118條),且“國家實行自然資源有償使用制度,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物權法》第119條),并規定了海域使用權(第122條)、探礦權、采礦權、取水權(第123條)等受法律保護;為實現憲法中國家“保護珍貴的動物和植物”的規范內容,《物權法》第49條對此規定了國家所有權。不僅如此,《物權法》第120條前句還規定了用益物權人行使權利時“應遵守法律有關保護和合理開發利用資源的規定”,這也同樣有利于實現憲法中國家所有之合理利用的規范內容。
第三,收益共享。這無疑也是為了實現憲法中國家所有之收益共享的規范內容,例如,《物權法》第45條第1款規定了“屬于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第56條規定了“國家所有的財產受法律保護,禁止任何單位和個人……私分”。〔26〕有學者認為,在私法中,“全民”具有抽象性,無法成為權利主體,而“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因此國家所有權并非私法所有權,參見鞏固:《自然資源國家所有權公權說》,載《法學研究》2013年第4期。但《物權法》直接規定了國家所有權,似乎已經將國家所有權作為私法所有權的一種,從教義學角度觀察,應在此前提下思考“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的規范含義,既有的思考參見馬俊駒:《國家所有權的基本理論和立法結構探討》,載《中國法學》2011年第4期;本文認為其規范含義在于突出國家所有權所內含的公共屬性和內容形成的民主程序,強調“公有私用”情形中的收益共享和“公有公用”情形中的不能設立排他性私權,而非強調“全民”是國家所有權的主體。
同時,基于憲法中國家所有的合理利用的規范內容所引申出的公民合理和共同使用國家所有之財產的基本權利,私法中國家所有權的內容也受到一定限制。首先,未設定用益物權的國家所有權,應負有容忍公民合理共同使用國家所有之財產的義務,〔27〕金可可:《論烏木之所有權歸屬》,載《東方法學》2015年第3期。此時,公民的合理共同使用行為不構成私法上的妨害或侵害,不可對之請求排除或侵權賠償;其次,經由合理共同使用行為會取得私法所有權。〔28〕德國法中,公共所有的水資源仍然包含了共同使用的權利,由此會產生特殊的私法權利,Vgl. MünchKomm/Oechsler, 2013, §958, Rn. 4.。例如,在國家所有之水資源中進行娛樂性游釣的行為,應予容忍,并且游釣者能夠取得所釣之魚的所有權。
《物權法》中的這些規范一方面向上連接著憲法,為實現憲法中國家所有的規范功能,規定了私法中的國家所有權;另一方面向下對特別法進行了授權,“物權法”充當了“批發商”和“外包商”的角色,有關土地、海域、礦產等的特別法應實現私法中國家所有權的規范內容,也擔當起私權利分配和保護的功能,而并非僅僅是單純的管制,從而最終實現法秩序的統一。〔29〕稅兵教授將之稱為“確權性規范”和“授權性規范”,參見稅兵:《自然資源國家所有權雙階構造說》,載《法學研究》2013年第4期。
2.規制目的與私法中國家所有權
為了實現憲法規范和私法規范在法秩序中的一致性,《物權法》第五章明確規定了國家所有權、集體所有權和私人所有權,此時憲法中的國家所有和私法中的國家所有權應具有相同的規范目的,即借此進行規制。私法中國家所有權的此種規范目的對國家所有權的具體私法規范自然會產生諸多影響。
首先,國家所有權屬于私法所有權,因此自然享有私法所有權的諸多形式特征,但由于憲法中國家所有權和私人所有權的規范目的不同,因此在私法中,國家所有權和私人所有權之間仍存在規范上的不同,例如國家所有權的客體在很多情況下并非特定的物,并且國家所有的自然資源無需登記(《物權法》第9條第2款),與私人所有權的客體一般具有特定性(《物權法》第2條第3款)且要進行公示(《物權法》第6條)不同。〔30〕國家所有權和私人所有權的私法規范的不同,請參見鞏固:《自然資源國家所有權公權說》,載《法學研究》2013年第4期。
這種規范上的不同來源于國家所有權和私人所有權的規范目的不同。私人所有權是一種經濟自由和交易取向的所有權,物權客體特定和公示公信原則都是為了降低交易成本,從而在交易中實現個人自由。但國家所有權則側重公共屬性,其目的在于規制,由此無需那些圍繞經濟自由取向之私人所有權而予以構建的物權法原則,而是更注重以國家所有權為基礎實現規制,協調規制與市場化、公共目的與盈利目的。〔31〕許多學者主張在私法中,用“公物”的概念予以替代“國家所有權”或“公共財產”概念,同時主張基于公物的使用目的,限制私法規范的適用,參見張谷:《公共財產和公物》,載《中德私法研究》(第7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0頁;徐滌宇:《所有權的類型及其立法結構》,載《中外法學》2006年第1期。該觀點與本文觀點的目的相同,僅僅是手段的差異而已,而從現行規范出發,本文仍然堅持國家所有權的概念。該規制目的決定了國家所有權中國家所享有的權利和義務的具體內涵。〔32〕例如,梁慧星教授認為如果法律規定的野生動物歸國家所有,那么野生動物致損,國家似乎就要承擔責任,參見梁慧星:《不宜規定“野生動物屬于國家所有”》,載《山東大學法律評論》(第4輯),山東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但是,依據本文觀點,此種情形中國家所有權的保護野生動物的規制目的也決定了國家的義務射程,規范目的決定了國家作為所有權人所享有的權利,也決定了國家作為所有權人所負有的義務,由此,防止野生動物致損與該規制目的無關,故并非國家作為所有權人所應負有的義務,自然無需作為所有權人而承擔侵權責任。
《物權法》第45條第1款規定:“法律規定屬于國家所有的財產,屬于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此,《物權法》確定了私法中國家所有權的客體必須是法律規定屬于國家所有的財產。就現行立法而言,國家所有權具有不同的規范方式:其一,排他的國家所有權,不能設立其他私主體的所有權,例如礦藏、水流、海域(《礦產資源法》第3條、《水法》第3條、《海域使用管理法》第3條和《物權法》第46條)、無居民海島(《海島保護法》第4條)、無線電頻譜資源(《物權法》第50條)、國防資產(《物權法》第52條第1款);其二,除法律規定屬于集體所有的之外都屬于國家所有,包括土地以及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等自然資源(《憲法》第9條第1款、第10條第1款和第2款,《物權法》第47和第48條);其三,凡法律規定為國家所有的屬于國家所有,除此之外允許其他私主體的所有權存在,包括野生動植物資源(《野生動物保護法》第2條和第3條、《物權法》第49條)、文物(《物權法》第51條)、基礎設施(《物權法》第52條第2款)。在前兩種情形中,無需以其他法律之規定作為依據,可以直接認定成立私法中的國家所有權;而在最后一種情形中,進一步要求以“法律規定”為前提,也即這些財產本身并非必然屬于國家所有,必須以其他法律之規定作為依據,才能成立私法中的國家所有權。〔33〕參見金可可:《論烏木之所有權歸屬》,載《東方法學》2015年第3期。
如果將所有這些財產與《憲法》中規定為國家所有的財產進行對比,可以發現,前者要廣泛得多。僅就自然資源而言,私法將國家所有的客體擴張至野生動植物資源、海域、無居民海島及無線電頻譜資源之上,因此,《憲法》第9條第1款中的“等”意味著一種未盡列舉。但是,國家所有之財產的范圍為何,哪些財產能夠被私法規定為國家所有?這個問題必須結合國家所有內涵的規制目的予以回答。
第一,財產與公共利益的關聯程度。財產越具有整體利益性和長遠利益性,則將之規定為國家所有而進行規制的總收益越高。第二,財產開發利用的負外部性。財產開發利用的負外部性程度越大,將之作為國家所有進行規制的總收益越高。例如,風能和太陽能等清潔能源利用的負外部性較小,因此,將之作為國家所有進行規制的總收益較小。第三,規制的執行成本。如果將某項財產作為國家所有進行規制所導致的執行成本過高,則不宜采取國家所有的方式進行規制,例如,風能和太陽能歸屬國家所有并借此進行規制,則執行成本就會過高。
由于上述考量因素所具有的結論上的不確定性,可能還要輔之以論證規則,即主張不以私人所有權為起點而是以國家所有為起點的規制方式者要承擔論證責任。如此,方能避免全權國家對私人所有權的過分侵蝕。同時,如果根據上述考量因素認為將某項財產作為國家所有進行規制的必要性極大,甚至可以排除在其上設立私人所有權的可能性,或排除其他私主體取得私法所有權。例如,國防設備并非無主物,不能由先占人取得所有權,這是基于特殊目的排除其無主性。〔34〕BGH NJW 1953, 271.如果反之,則可能會容許私人所有權設立或取得。
三、烏木情形中的國家所有權
烏木之上是否應存在私法中的國家所有權,關鍵是結合上述考量因素予以判斷。烏木本身的開發利用具有一定的負外部性,對其過分開挖可能會導致對土地資源和環境的破壞,但如果將消除這種負外部性作為目的,而將烏木作為國家所有并借此進行規制作為手段,這會涉及比例原則的具體應用。
首先,妥當性,即手段是否有助于達到目的。如果將烏木作為國家所有,此時發現人無法取得私法所有權,這無疑可以對避免濫挖起到一定作用,有助于消除負外部性。
其次,必要性,即在同樣有助于達到目的的多種手段之間進行比較。可以消除此種情形中的負外部性的其他方式之一,就是烏木并非歸屬于國家所有,發現烏木者能夠取得單獨或共同的私法所有權,但濫挖破壞土地資源和環境者可能會承擔刑事、行政和民事責任,其中民事責任包括了侵權損害賠償以及停止侵害、排除妨礙和消除危險,這同樣能夠起到消除負外部性的效果。〔35〕有觀點認為,未遵守環境保護和自然資源保護者不能通過先占取得所有權,規范基礎為《物權法》第30條所規定的“合法”要件,并以《德國民法典》第958條第2款所規定的先占要件之一是無先占之禁止作為證明,參見金可可:《論烏木之所有權歸屬》,載《東方法學》2015年第3期。但是,在德國法中,先占的禁止規定指的是禁止先占本身的規定,而非在先占中禁止特定的違法行為的規定(Vgl. Staudinger/Gursky, 2011, § 984, Rn. 9.;Müller, Sachenrecht, Aufl. 4, Carl Heymanns Verlag, 1997, Rn. 2742m.),因此環境保護和自然資源保護規定是否必然和有必要構成禁止先占的規定,是一個法律解釋的問題,仍然需要更多論證。但將烏木規定為國家所有,對發現烏木者的利益侵害較大。兩相比較,烏木并非歸屬于國家所有的方式可能帶來的損害更小。
再次,法益相稱性,也即手段本身的成本和收益應當均衡。將烏木規定為國家所有借此進行規制的收益是存在的,可是烏木雖然經濟價值較高,但其與公共利益之間的關聯程度較低,一般不具有較高的科研價值,不具有整體利益性和長遠利益性,〔36〕參見曾娜:《埋藏物的權屬紛爭與憲法解答》,載《昆明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4期:“在‘天價烏木案’中,通濟鎮政府提出烏木具有很高的科研價值,含有豐富的古生態信息,通過對烏木的研究,可以了解烏木形成當時的自然環境、氣候條件等,將烏木歸為國有,可以保護這一珍稀的不可再生資源。但據專家的意見,烏木對地質學研究的意義不大,而且,用于研究只需一小段即可;另外,從植物學的角度看,形成烏木的樹種現在并沒有滅絕,烏木所具有的主要還是經濟價值。”因此手段本身的總收益較小。與此對應,如果將烏木規定為國家單獨所有,則發現者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慮,可能會采取多種方式進行隱藏,例如臨時掩蓋等待合適機會開挖,或者與國家之間發生持續的歸屬爭議和沖突,例如提起訴訟和暴力對抗等,由此導致不會產生收益的成本。〔37〕具體的分析,參見熊丙萬:《財產法的經濟分析》,載馮玉軍主編:《法律經濟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五章。相應的,將烏木規定為國家所有借此進行規制的執行成本也同樣會較高,這里包括了查明烏木被發現的成本、查明發現者的成本、將之收歸國家所有的行政和司法成本以及排除他人挖掘烏木的相關成本。在這種情形下,將烏木規定為國家所有這種手段帶來的總收益較小,但總成本較高。
可能會有觀點認為,烏木歸屬國家所有,還存在一定的分配正義考慮,將烏木歸國家所有,并且國家給予上繳單位或個人以表揚或物質獎勵,此時國家有可能通過新增收入增進公共福利,實現財富的社會共享,更能體現分配正義。此種分配正義的考慮也可以納入前述的法益相稱性步驟,將此作為烏木歸屬國家所有所可能產生的收益之一。但是,雖然分配正義的目的本身是值得尊重的,可目的的正當性無法當然證成手段的正當性,這里仍然有比例原則適用的可能性。必須承認,將烏木歸屬于國家所有這種手段有助于實現目的,但是,同樣實現該目的可能存在其他手段,例如,由發現者取得烏木的所有權,但對該主體征收所得稅。此時,手段之一是將烏木歸屬于國家所有,但給予發現者以物質獎勵,而手段之二是將烏木歸屬于發現者所有,但應繳納所得稅。姑且不論是否有制度防止代表國家行使所有權的地方政府去侵占或揮霍偶然增加的財政收入,如果發現者經由這兩種手段所取得的個人利益大致相同,則對發現者采取破壞資源和環境行為的激勵似乎并無多大區別,而在分配正義的實現方面也并無太大區別。但由于前述將烏木歸屬于國家所有并借此進行規制可能不符合比例原則,因此較之手段之二,手段之一所造成的損害更大。
綜上,在烏木的情形中,將烏木歸屬于國家所有并借此進行規制這種手段可能不符合比例原則,因此,烏木不應被規定為國家所有,在憲法秩序中,將烏木歸屬于國家所有會導致合憲性的疑慮。
四、相關私法規范的解釋
經由對國家所有權進行法秩序的整體梳理,以及在烏木情形中國家所有權問題的具體分析,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烏木不應由國家享有所有權。在此價值判斷之下,第一,烏木不應被公布為新礦種適用關于《礦產資源法》的規定而歸屬國家所有,并且因為欠缺類推基礎,故不能類推適用現行規定而歸屬于國家所有。第二,烏木不能被認為屬于“其他自然資源”,不能根據《憲法》第9條第1款或《物權法》第48條而被認為歸屬于國家所有。因此,不能依據現有規范直接確定烏木歸屬于國家所有。
如果烏木不能被直接確定為歸屬于國家所有,那么國家是否可以依據其他法律事實取得對烏木的所有權,這涉及更為棘手的《民法通則》第79條第1款。如果嚴格按照其文義進行思考,則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無論是否曾經存在所有權,都應歸國家所有。但如果采取此種解釋方案,則在具體情形中,與根據憲法秩序所得出的結論存在違背之處,因此可能會導致合憲性的疑慮。在烏木的情形中,就是如此,根據憲法秩序,烏木不應由國家享有或取得所有權,而如果對《民法通則》第79條第1款采取上述解釋方案,則烏木應由國家所有,此時《民法通則》第79條第1款似乎違反了憲法秩序。因此,需要對該款規定進行合憲性的解釋。
按照拉倫茨教授的觀點,“假使立法者追求的影響作用超越憲法容許的范圍……可以將法律限縮解釋至‘合憲’的范圍”。〔38〕[德]拉倫茨:《法學方法論》,陳愛娥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217頁。據此,如果《民法通則》第79條第1款的適用結果超越了憲法秩序所容許的范圍,應對此進行限縮。可能的解釋方案是,該款的構成要件除了存在埋藏物或隱藏物以及所有人不明即所有人不可能查明或存在〔39〕Vgl. Staudinger/Gursky,2011, § 984, Rn. 2.; [德]鮑爾、施蒂爾納:《德國物權法》(下),申衛星、王洪亮譯,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519頁。這兩個要件外,還應增加一個要件,即該埋藏物原則上歸國家所有,例外規定能夠存在其他私法所有權,但此時具體的所有人不可能查明或存在。在此,尤指在中國境內出土的可移動文物。按照《文物保護法》第5條第4款第1項,在中國境內出土的可移動文物原則上歸國家所有,“國家另有規定的除外”,構成例外的該法第6條規定能夠存在其他私法所有權,但如果具體的所有權人不可能查明或存在時,應依據《民法通則》第79條第1款歸國家所有。
與之相關的規范是《物權法》第114條,較之《民法通則》第79條第1款,該條中的埋藏物似乎是廣義上的,不包含“所有人不明”這個條件,此時具有多種可能。第一,埋藏物僅能歸屬于國家所有,不能存在其他私法所有權時,不適用第114條前句規定的“參照拾得遺失物的有關規定”,也不適用《民法通則》第79條第1款,因為該款“所有人不明”這個要件不具備,而應適用后句規定的“文物保護法等法律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此時國家直接享有所有權,例如被埋藏的古生物化石和國防動產設備。第二,埋藏物原則上歸國家所有,例外規定能夠存在其他私法所有權,但此時具體的所有人不可能查明或存在,此時應適用《民法通則》第79條第1款,該埋藏物歸國家所有。第三,埋藏物并非歸國家所有,且能夠查明所有權人時,或者原則上歸國家所有,但例外規定能夠存在除國家所有權之外的其他私法所有權,且能夠查明所有權人時,此時在法律效果上要“參照拾得遺失物的有關規定”,并且后句規定的“文物保護法等法律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也有適用余地(即中國境內出土的可移動文物原則上歸國家所有,但《文物保護法》第6條同時規定,確定屬于集體所有或私人所有的可移動文物的所有權受法律保護),此時有關部門應發布招領公告,所有權人認領,且能夠證明其所有,則歸屬所有權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93條);如無人認領,則歸屬國家所有,〔40〕順便指出,《物權法》第113條規定無人認領的遺失物歸國家所有,按照本文的邏輯,該規定仍然具有諸多疑慮。對此的討論和疑問,請參見王利明:《物權法研究》(上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465-466頁;孫憲忠:《中國物權法總論》,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56頁。此時不適用《民法通則》第79條第1款,因為不具備“所有人不明”這個要件。第四,該埋藏物并非歸國家所有,且所有權人不可能查明或者存在時,不適用《民法通則》第79條第1款。
按照此種解釋方案,《民法通則》第79條第1款的適用范圍被極大限縮,當然此時所涉及的并非只是解釋,而是一種依據憲法所作出的目的論限縮,是一種合憲的法律續造,是“在合憲性要求容許的范圍內,盡量維持規范的存續。”〔41〕[德]拉倫茨:《法學方法論》,陳愛娥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217頁。據此,在土地中發現烏木,由于烏木并非被法律明確規定為國家所有,且所有權人不可能存在,因此不適用《民法通則》第79條第1款而由國家取得所有權。
同時,如前文所述,烏木并非土地的天然孳息或土地的成分,因此,無論是適用還是類推適用《物權法》第116條,國家作為土地所有權人都無法據此而取得烏木的所有權,《物權法》第39條所規定的所有權人的“收益”權能不包含對烏木的取得。
五、結論
本文的結論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憲法中的國家所有和私法中的國家所有權具有法秩序的一致性,后者是前者所具有的國家內容實現義務功能的展開方式之一,同時要受到前者的約束,兩者共享了規制這個規范目的,該規范目的對私法中的國家所有權規則具有多方面的影響。
第二,并非所有財產都應采取借助國家所有實現規制目的的方式,選擇何種規制方式應考量多個因素并按照比例原則進行審查,國家所有權的規制目的必須通過對國家所有權本身的限制而實現。據此,對烏木挖掘的負外部性的消除不應通過借助于將烏木歸屬于國家所有而進行的規制方式實現,在憲法秩序中,將烏木歸屬國家所有會導致合憲性的疑慮。
第三,相關的私法規范必須據此予以解釋,尤其是《民法通則》第79條第1款應進行合憲性的目的性限縮。烏木不能由國家直接享有或取得所有權。
可以看出,在烏木的歸屬上,本文的結論是消極意義上的,即不能由國家直接享有或取得所有權。本文并未在積極意義上回答烏木究竟如何歸屬的問題。在烏木不能歸屬于國家所有的前提之下,此時現行法律存在法律漏洞,那么應該如何填補該法律漏洞?烏木是歸先占人單獨所有;或者由土地所有權人或用益物權人單獨所有,無論是因為他享有排他的先占權抑或其他;或者由發現人與土地所有權人或用益物權人各取一半;或者由發現人單獨所有但應給予土地所有權人或用益物權人報酬,抑或反之?在占有人和發現人不一致的情形下歸誰所有?所有這些問題涉及更多的考量,而超出了本文的主題。在烏木情形中,依據憲法可以否定國家所有權,但憲法規范卻無法決定烏木的最終歸屬,因此,在憲法秩序中,憲法對私法的消極控制作用并無疑問,但憲法對私法的積極決定作用卻是非常讓人疑慮甚至被認定為是不可能的。無論是對于國家所有權本身,還是憲法和私法的關系,本文僅僅是一個初步和具體的嘗試,但這些問題無疑值得進一步的深入思考。也許,僅僅是也許,中國法學者對于國家所有和國家所有權的討論以及由此引申出來的討論,是中國法學真正中國化和成熟的契機或標志,對于中國法學者而言,這既是挑戰,也是機遇。
(責任編輯:吳一鳴)
*朱虎,中國人民大學民商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本文系“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項目號15XNI002)的階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