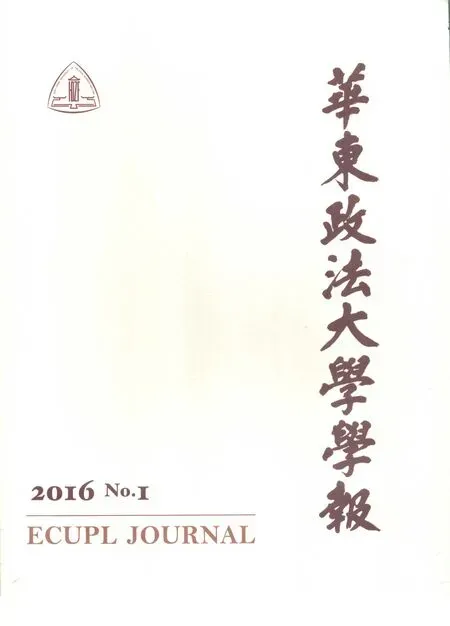“近親屬證人免于強制出庭”之合憲性限縮
張 翔
?
“近親屬證人免于強制出庭”之合憲性限縮
張翔*
目次
一、問題的提出
二、《憲法》第125條規定的“獲得辯護權”是否為基本權利?
三、對質權作為辯護權的內容:刑訴法對憲法的具體化
四、婚姻家庭保護作為憲法確立的“客觀價值”
五、憲法法益沖突與刑訴法學者的解決方案
六、合憲性解釋與個案中基本權利沖突的“實踐調和”
七、結語
新《刑事訴訟法》第188條第1款“強制證人出庭”條款及其但書(“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條款,涉及兩項基本權利——《憲法》第125條規定的“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和第49條規定的“婚姻、家庭受國家的保護”——的沖突,實踐中該條款的適用也存在爭議。該條款體現了刑訴法對憲法的具體化,但在兩項基本權利的保障上都存在不足,有待法律解釋之完善。基于法律的合憲性解釋以及在個案中的法益衡量,在婚姻家庭法益已非常淡漠的具體情境下,可以對該但書條款進行“目的性限縮”,從而得強制近親屬證人出庭質證。不同學科的法學者應該在憲法與部門法之間“交互影響”的認識下,為了法秩序的整體融貫,相向而行。
辯護權對質權婚姻家庭保護合憲性解釋目的性限縮實踐調和
一、問題的提出
2012年修正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新刑訴法)第188條第1款規定:“經人民法院通知,證人沒有正當理由不出庭作證的,人民法院可以強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一般認為,這款規定包含兩個層次的內容:(1)人民法院可以強制證人到庭;(2)不得強制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出庭作證。〔1〕參見陳光中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修改條文釋義與點評》,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270-272頁;朗勝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釋義(最新修訂版)》,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409頁。從憲法學角度看,這兩個層次亦對應兩項憲法保護的法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刑事訴訟法》修正案中新增這一條款,可以被看做國家立法機關在落實“憲法委托”。該款的前半句規定證人可被強制出庭,是為履行《憲法》第125條中“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的規定所科以立法機關的立法義務,而后半句的但書條款則是在履行《憲法》第49條第1款“婚姻、家庭、母親和兒童受國家的保護”所科以立法者的立法義務。
這一條款是對我國刑事訴訟證據制度的完善,貫徹了“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憲法精神(“尊重和保障人權”也見于新刑訴法第2條),其進步意義不容否認。但是,其中兩種憲法法益之間的緊張關系也顯而易見,而相關爭議也已出現在實踐中。例如,在“薄熙來案”中,被告人薄熙來之妻薄谷開來作為證人向法庭提交了作證錄像。在庭審中,被告薄熙來多次要求薄谷開來出庭,法庭認為薄谷開來應當到庭作證,并向薄谷開來說明了其應當履行的出庭作證義務,但她明確拒絕出庭。根據新刑訴法第188條之規定,法庭并未強制薄谷開來出庭。這一細節或許只是薄案審判中的小插曲,但卻蘊含著人權保障的大問題。對此問題,龍宗智教授認為“法庭在處理證人出庭問題上并未出現程序瑕疵”,但同時“這一規定對被告人是不公正的,這一點被立法所忽略了”,“損害了被告的基本訴訟權利”,“違背了訴訟法與證據法的基本法理”。龍宗智教授給出了兩個解決方案:第一,應當明確規定親屬的免證權;第二,在被告要求之下,應當給其在庭審前對質詢問的機會。這兩個方案,都指向對《刑事訴訟法》的再修改。
然而,筆者秉持“法教義學是法學的學科根本”的觀念,認為在法律的文義解釋出現問題時,首先應考慮的是通過法律解釋方法修補其缺陷,而徑行主張修法則有損成文法權威。此外,出于《憲法》的根本法、最高法地位,以及法律應貫徹憲法精神的現代法治原理,法律人在解釋適用法律時,有義務秉持憲法意志作成解釋,使得下位法的適用能夠落實憲法價值。這就是所謂“法律的合憲性解釋”。在新刑訴法第188條第1款中,存在兩個憲法層次法益的保護問題,因此,對這一條款的解釋,必須以合憲性作為重要的考慮因素。
基于以上的認識,本文嘗試對新刑訴法第188條做合憲性的限定解釋,以解決“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在作為針對被告人的不利證人時,是否得被強制出庭的法律爭議。本文的分析,將從第188條第1款所涉及的“辯護權”和“婚姻家庭保護”兩項憲法法益的地位與內容入手,確定解釋該條款的憲法規范背景,最終以合憲性解釋、個案衡量、目的性限縮等方法,針對具體個案給出解決方案。最后,還將一般性地探討憲法與部門法的相互影響,以及憲法與部門法的學術如何相向而行,以實現法學的學科融貫。
二、《憲法》第125條規定的“獲得辯護權”是否為基本權利?
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是,規定在《憲法》第三章“國家機構”部分的“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是否與《憲法》第二章規定的“公民的基本權利”具有相同的性質或者位階,從而可以與第49條規定的“婚姻、家庭受國家的保護”置于同等的地位而進行衡量。對此問題,學理上并非沒有爭論。有趣的是,我國的刑事訴訟法學者,大都不假思索地認為辯護權是基本權利,并經常會引出美國《憲法》第6修正案、德國《基本法》第103條、日本《憲法》第34條等作為論據。然而,我們畢竟不能以外國的憲法文本作為討論本國問題的基礎,而應將論證建基于我國的憲法規范。因此,評價刑訴法學者的觀點,必須解決這樣一個問題:“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規定在我國《憲法》第三章“國家機構”部分的第七節“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并非如日本等國憲法是明確規定在基本權利章中,那么,非列于基本權利章中的辯護權,是否是基本權利?
根據此文本因素,周偉教授認為:“由于‘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并不是《憲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中的內容,因此,還算不上是公民的基本權利”,“從辯護權條款在憲法中的位置看,‘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的規定……是作為司法機關運行中應當遵循的一項原則來對待的。可見立憲者并不認為辯護權是公民基本權利和義務中的有機組成部分,而是一種刑事司法準則。因此依照現行《憲法》,辯護權充其量只屬于從‘審判公開’等司法原則中推導出來的權利”。“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只是刑事司法原則,不是基本權利條款的論證,無疑是相當有力的。如果法學的討論,不受本國法律文本之約束,而任由價值判斷甚至比較法論證泛濫,不僅無助于本國法律問題的解決,還會有損于實定法下的法秩序建構。但與此種法學立場存在緊張關系的是,周偉教授在進一步的論證中,主張通過修憲來確認辯護權,認為應當“將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從‘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那一章節刪除,寫入‘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一章中,將其明確為公民的基本權利”。〔2〕周偉:《憲法依據的缺失:偵查階段辯護權缺位的思考》,載《政治與法律》2003年第6期。
這里的問題在于,周偉教授的論證一方面是對缺乏憲法規范關照的批評,另一方面又同時主張修改憲法的規范文本以達成某種價值目標。這種主張存在價值判斷與實定法的安定性之間的緊張。
筆者曾概括過中國憲法學研究的兩種思維模式:“修憲思維”和“釋憲思維”,前者是批判性的,所關注的是憲法文本的缺陷與不足,并以提出修憲建議為主要的表現形式,而后者大體上承認或者接受憲法文本的正當性,希望通過對憲法文本的闡釋,建立為實踐服務的憲法規范體系。〔3〕參見張翔:《憲法學為什么要以憲法文本為中心》,載《浙江學刊》2006年第3期。筆者傾向于后一種模式,也即法教義學的模式,希望首先通過解釋來處理憲法文本存在的問題,而避免徑行修改憲法而動搖憲法秩序的穩定性,損害法律的安定性價值。基于此種認識,雖然筆者完全認同“辯護權應該是基本權利”的價值主張,但希望通過憲法解釋的路徑來導出“我國《憲法》第125條規定亦屬于基本權利規范”的法學判斷。
對此問題,已有學者作了非常有力的論證。尹曉紅博士發現,我國的幾本權威憲法學教科書都未將獲得辯護權列入基本權利目錄,但她認為“‘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既是一項司法原則,同時也是被告人的一項基本權利”。〔4〕尹曉紅:《獲得辯護權是被追訴人的基本權利——對〈憲法〉第125條“獲得辯護”規定的法解釋》,載《法學》2012年第3期。對此,尹曉紅博士提示了兩個重要的論證基點:第一,與我國相同,許多國家的憲法都未將辯護權規定在基本權利章中,而是在司法制度部分規定;第二,我國《憲法》第33條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作為第3款,加強了對公民基本權利的保護,提出了在刑事司法中加強人權保護的要求。這兩點,指向體系解釋和目的解釋,筆者嘗試就此兩點做一些補充的論證。
一方面,從目的解釋的角度出發,筆者認為,“人權條款”毫無疑問是一種新的價值注入,為基本權利的憲法解釋提供了新的評價關聯。在“人權條款”入憲之前,我們對于基本權利的理解具有法律實證主義的封閉性。以純粹法律實證主義立場,認為只有列舉在《憲法》第二章中的才是基本權利,并無根本性問題。我國既有的憲法教材未將獲得辯護權列入基本權利清單,或許正是此種立場的慣性使然。但是,“人權”具有天然的開放性,人權作為人之為人所應該享有的權利,具有道德權利的性質。這意味著,按照倫理與價值觀念被認為是人權的權利,就應該受到憲法的保障。在憲法中納入具有自然法性質的“人權”,可以被看做是對實定法與自然法的調和,在相當程度上意味著基本權利體系的開放。據此,憲法未列舉的生命權、健康權、遷徙自由等權利,基于嚴格的憲法解釋與論證,都有可能被作為基本權利而得到憲法層面的保護。〔5〕各國依據其憲法文本之不同,對于如何納入憲法未明確列舉的權利,各有不同的操作。關于美國納入隱私權的憲法解釋,參見屠振宇:《未列舉權利研究——美國憲法的實踐和經驗》,中國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關于德國如何將“一般行為自由”解釋為“兜底基本權利”而容納未列舉權利,參見張翔:“艾爾弗斯判決”,載張翔主編《德國憲法案例選釋(第一輯)?基本權利總論》,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同時,列于《憲法》其他章節中的條款,也應該在人權條款的價值輻射下,做合于基本權利的解釋。
另一方面,從體系解釋的角度看,對于基本權利的理解,也不能僅限于憲法的基本權利章。憲法是一個整體,不可做割裂的觀察。對于基本權利的法學思考,應該具有“整體性”和“綜合性”,“在整個憲法秩序中考量基本權利的本質和功能”。〔6〕Peter H?berle, Die Wesengehaltgarantie des Artikel 19 Abs. 2 Grundgesetz, 1962, S.180ff.應當“將基本權利與憲法其他部分的意義關聯放在一個統一的理論中去研究”。〔7〕Luhmann, Grundrecht als Institution, 1965, S.11.
實際上,憲法中“基本權利規范”與“國家機構規范”之間是相互滲透的(我國《憲法》的“總綱”部分也包含了多種性質的憲法規范),在國家機構章中可以找到基本權利規范,同樣在基本權利章中也可以找到國家機構規范。〔8〕參見朱應平:《憲法中非權利條款人權保障功能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95頁。例如,《憲法》第37條第2款中的“非經人民檢察院批準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并由公安機關執行”以及第40條“由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的規定,就具有規定國家機關的權限及其行使程序的性質,也可看做組織規范。前述尹曉紅博士的主張“獲得辯護權是司法原則也是基本權利”,正是此種體系解釋的結果。
從比較法上看,基本權利并非都列于憲法的基本權利章的情形,在各國憲法中非常常見。(尹曉紅博士也基于各國憲法文本的統計指出,多國憲法都將獲得辯護權規定在司法權部分〔9〕尹曉紅:《獲得辯護權是被追訴人的基本權利——對〈憲法〉第125條“獲得辯護”規定的法解釋》,載《法學》2012年第3期。)以德國為例,德國《基本法》的第一章是“基本權利”,包括第1條至第19條,但通說認為,第二章“聯邦和州”中的第20條第4款的“抵抗權”,第33條“擔任公職權”和第三章“聯邦議院”中的第38條“選舉權”,第九章“司法”中的第101條“獲得法官審判權”,第103條“訴訟中的聽證權”和第104條中的“剝奪人身自由的法律程序”,是“等同于基本權利的權利”(grundrechtsgeleiche Rechte)。〔10〕Pieroth/Schlink, Grundrechte. Staatsrecht Ⅱ, 25. Aufl, 2009,S.19f. 當然,德國憲法學的這一通說還有另一個規范依據。《基本法》第93條規定的聯邦憲法法院管轄的案件中,包括了第4a項:“認為公共權力機關侵犯個人基本權利或侵犯本《基本法》第20條第4款、第33條、第38條、第101條、第103條和第104條規定的權利時,任何人所提起的憲法訴愿,”這一條款被認為賦予了這些權利以基本權利的地位。可以看到,在各國都毫無例外地被視為基本權利的選舉權,在德國《基本法》中并非規定在基本權利章,而是位于規定選舉制度的章節,而此種體系安排,只是為了法律條文表述的便利和避免重復。因此,基于體系解釋的方法,考慮到憲法自身的整全性,就不能僅僅將列于基本權利章的權利作為基本權利,而同時應從其他章中確立基本權利。
基于以上分析,筆者認為,我國憲法學可確立“列于基本權利章內的基本權利”和“等同于基本權利的權利”一組概念。〔11〕參見張翔:《基本權利的體系思維》,載《清華法學》2012年第4期。“等同于基本權利的權利”這一概念,可以用來涵蓋位于憲法總綱中的財產權(第13條)〔12〕對于2004年《憲法》修改之后的第13條“公民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是否是基本權利條款,不無爭議。王廣輝教授就曾設問,考慮到財產權規定在總綱部分,“憲法關于財產的規定,到底是財產權利還是財產制度”,認為“憲法確認的是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并存的經濟制度,公民對財產的私有在最基本的性質上不是基本權利的問題,而是作為所有制中的一種表現形式即私人所有制的問題”。王廣輝:《中國憲法中的財產權》,載《江漢大學學報》2008年第2期。但筆者認為,基于正文中關于憲法目的解釋和體系解釋的理由,第13條作為財產權條款應無問題。當然,不能因此忽視其作為所有制的內涵。、經濟活動自由(第16條和第17條)、獲得辯護權(第125條)等權利條款(也可用來涵蓋我國學者關注較多的“憲法未列舉權利”)。具體就我國《憲法》第125條的獲得辯護權來說,雖然是規定在司法制度部分,但是,考慮到指控個人對抗國家公權力的犯罪是個人與國家關系中重要的部分,仍然應該基于前述的目的解釋和體系解釋,賦予其憲法基本權利的地位。至少也應該認為,獲得辯護權是與其他基本權利價值位階相同的權利。
三、對質權作為辯護權的內容:刑訴法對憲法的具體化
憲法上的基本權利規范,用語大多簡略抽象,因而基本權利被認為經常是“有待立法形成”(ausgestaltungsbed ürftig)的。也就是說,憲法基本權利的具體內涵,首先需要立法者在建構相關法律制度時加以認識和形塑。同樣,憲法學上對辯護權條款的解釋,也首先要了解刑訴法學者的認識和理論建構。
根據筆者的觀察,我國刑訴法學者很早就將辯護權的內涵實質化解讀為“獲得有效辯護權”,而在此認識下,與證人出庭直接相關的被告人的“對質權”也被認為是我國刑訴法應當確立的權利。陳衛東教授很早就提出,基于國際標準,辯護權是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所享有的最低限度的權利之一,其是“法律賦予被告人針對指控進行辯解,以維護自己合法權益的一種訴訟權利,這是被告人所享有的訴訟權利的核心”,關于辯護權的內容,他強調包括“享有獲得有效辯護的權利”。〔13〕陳衛東、郝銀鐘:《被告人訴訟權利與程序救濟論綱——基于國際標準的分析》,載《中外法學》1999年第3期。那么,何為“獲得有效辯護”呢?基于國際標準,包括:“調查案件的權利”、“享有充足時間與便利條件以準備辯護的權利”、“詢問證人時控辯雙方力量平衡的權利”、“免費獲得口筆譯的權利”,〔14〕丁鵬等編譯:《歐洲四國有效刑事辯護研究——人權的視角》,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79-85、154-162、231-242頁。其中“詢問證人時控辯雙方力量平衡的權利”就包含了“若證人不愿意出庭作證,控方或辯方可以向法院申請發傳票傳喚證人出庭”〔15〕丁鵬等編譯:《歐洲四國有效刑事辯護研究——人權的視角》,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82頁。的內容。據此,基于“獲得有效辯護”的要求,我國刑訴法學者深入探討了被告人的“對質權”的功能。龍宗智教授認為,“讓事實陳述有矛盾的雙方或多方當面質詢,有利于發現錯誤、揭穿謊言,有利于查明情況、發現真實,這是對質及對質制度的基本意義和價值。”〔16〕龍宗智:《論刑事對質制度及其改革完善》,載《法學》2008年第5期。易延友教授認為:“(對質權的)功能主要在于防止無辜者遭受錯誤追究,保證審判程序的公正和加強裁判的正當性。”〔17〕易延友:《證人出庭與刑事被告人對質權的保障》,載《中國社會科學》2010年第2期。不難看出,對質權是保障被告人獲得有效辯護的應有之義。而作為被告人對質權的對立義務面,就包含了證人的出庭義務,特別是證言對被告人不利的證人的出庭義務。“從對質權的角度觀之,對于不利于被告人的證人,被告人有權要求其出庭作證”,〔18〕熊秋紅:《刑事證人作證制度之反思——以對質權為中心的分析》,載《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09年第3期。“(對質權)主要指向對象是不利證人”。〔19〕郭天武:《論我國刑事被告人的對質權》,載《政治與法律》2010年第7期。
筆者并非刑訴法學者,上述的脈絡梳理或許有欠全面和精準。但總體上可以認為,刑訴法學者的論述中,存在“辯護權——獲得有效辯護權——對質權——不利證人出庭”的邏輯推演,而且也體現了從比較法視角到本土化的思考過程。〔20〕參見陳興良:《為辯護權而辯護——刑事法治視野中的辯護權》,載《法學》2004年第1期。而我國刑事訴訟法最終規定證人出庭,正是在這種認識背景下實現的。新刑事訴訟法第187條第1款規定:“公訴人、當事人或者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對證人證言有異議,且該證人證言對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人民法院認為證人有必要出庭作證的,證人應當出庭作證。”這一規定雖然只是賦予了當事人或者辯護人、訴訟代理人以證人出庭的請求權,而將決定權賦予法院,但總體上仍然體現了“有效辯護”的要求,可以說向著完整的對質權前進了一大步。
從憲法與部門法的關系看,立法機關擁有“具體化憲法”的優先權,立法機關基于對憲法的理解而設計相關制度,是立法機關在落實“憲法委托”,在履行基本權利作為客觀價值秩序所科以國家的客觀法義務。在此意義上,新刑訴法納入第187條及第188條,正是立法者具體化憲法的體現,是對“辯護權”這一憲法基本權利所提供的“制度性保障”或者“程序保障”。同時,刑訴法學者對于《憲法》第125條辯護權的解釋,也可以被接受為憲法學上的解釋方案,〔21〕尹曉紅博士在另一篇論文中也指出獲得有效辯護是辯護權的核心,參見尹曉紅:《獲得律師的有效辯護是獲得辯護權的核心——對憲法第 125 條獲得辯護條款的法解釋》,載《河北法學》2013年第5期。此外,對于《憲法》第125條“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的憲法解釋的完善,還需要考慮其他問題。比如,“被告人”的范圍可否在“人權條款”籠罩下被擴大解釋為所有“被指控人”,從而解決刑事偵查階段的辯護人介入問題,等等。由此也可溝通憲法教義學與刑訴法教義學。(關于憲法與部門法關系的另一層面,“對法律的合憲性控制”,筆者將在下文說明)。
四、婚姻家庭保護作為憲法確立的“客觀價值”
(一)《憲法》第49條作為新刑訴法第188條例外條款的立法依據
如果說新刑訴法第187條和第188條前半句是在對質權層面對作為基本權利的辯護權的具體化,那么第188條的例外條款,就是《憲法》第49條“婚姻、家庭受國家的保護”在刑訴法中的具體化。新刑訴法188條例外條款的內容是“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全國人大常委會王兆國副委員長在關于《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的說明中,明確了這一但書的立法目的:“同時,考慮到強制配偶、父母、子女在法庭上對被告人進行指證,不利于家庭關系的維系,規定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關于這一條款的諸多釋義著作也都認為,強制這些特殊身份的人出庭作證,“不利于家庭關系的維系和社會和諧的建構”〔22〕朗勝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釋義(最新修訂版)》,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409頁。、“有悖于我國傳統的倫理道德要求和人性的基本價值取向”。〔23〕陳光中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修改條文釋義與點評》,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271頁。從這些解釋中,不難看出其與《憲法》第49條婚姻家庭保護之間的關聯性。
這一例外條款的價值源頭,可以回溯到我國“親親相隱”的文化傳統,〔24〕范忠信:《中西法律傳統中的“親親相隱”》,載《中國社會科學》1997年第3期。有論者直接將這一例外條款視為“親親相隱制度的理性回歸”。〔25〕余福明:《論親親相隱制度的理性回歸——以強制證人出庭的例外情形為視角》,載《人民司法?應用》2013年第9期。但若論該條款在實證法體系中的直接依據,則當然是《憲法》第49條。對此,已有學者指出。張龑博士提出了“家價值”的概念,認為我國《憲法》第49條“對家價值給出了基礎而翔實的規定”,并認為“親屬拒證在刑訴中的重新發現……隱含著對家價值的承認”。〔26〕張龑:《論我國法律體系中的家與個體自由原則》,載《中外法學》2013年第4期。張龑博士將這一但書解讀為“親屬拒證”稍欠準確(該條款只是免除了近親屬出庭的義務,并沒有免除作證義務),但他的確指出了這一條款在憲法規范上的基礎。
(二)“婚姻家庭保護”的客觀價值秩序功能
對于《憲法》第49條規定的“婚姻家庭受國家保護”,我國憲法學界也已有學者進行了教義學建構。王鍇博士借用德國的“制度性保障”理論分析了《憲法》第49條的規范內涵。〔27〕參見王鍇:《婚姻、家庭的憲法保障——以我國憲法第49條為中心》,載《法學評論》2013年第2期。卡爾?施米特在其1928年出版的《憲法學說》中提出,應將基本權利與“制度性保障”(institutionelle Garantie)進行區分,認為某些在憲法之前就已經存在的制度,是由憲法所確認的,因此應該受到特別的保護而不能允許立法機關通過法律而予以廢棄。〔28〕Carl Schmitt, Verfassungslehre, neunte Ausflage, Berlin, 2003, S.170ff.被施米特認定為“制度性保障”,從而不能由立法機關廢棄的制度包括:(1)接受法官審判的制度;(2)婚姻家庭制度;(3)星期天的休息制度;(4)民法上的財產權制度;(5)公務員制度;(6)鄉鎮的自治制度。德國戰后制定的聯邦德國《基本法》在第6條第1款規定“婚姻和家庭受國家特別保護”,而在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的基本權利“客觀價值秩序理論”〔29〕參見張翔:《基本權利的雙重性質》,載《法學研究》2005年第3期。之下,婚姻、家庭的“制度性保障”理論也得到了更新。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認為,“基本權利首先是公民對抗國家的防御權;但基本法中的基本權利規定同時也體現為一種客觀的價值秩序(objektive Wertordnung),而其作為憲法上的基本決定而對所有法領域發生效力。”〔30〕BVerfGE 7, 198(198).按照這一理論,基本權利作為客觀價值秩序構成立法機關建構各種制度的原則,也構成行政權和司法權在執行和解釋法律時的指導原則,基本權利構成整個社會共同體的價值基礎,國家應該為基本權利的實現提供實質性的前提條件。〔31〕Robert Alexz, Gundrechts als subjektive Recht und als Objektive normen, Der Staat 29/1990.S.49.然而,此種抽象的要求畢竟是難以操作的,因此,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也在諸多層面上嘗試對這一“客觀價值秩序”進行具體化。實際上,在最終確立“客觀價值秩序理論”的“呂特判決”之前,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就已經開始了對《基本法》第6條規定的婚姻家庭保護的規范建構,最為重要的案件之一是1957年“夫妻共同課稅案”。按照德國1952年的《個人所得稅法》,夫妻應該合并申報所得稅。有夫妻對此提出異議,因為按照新的合并納稅的規定,他們夫妻二人要繳納的個人所得稅,超過了他們分別納稅的總額。也就是說,合并納稅要交得更多。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審查認為,這種稅收政策構成了“對婚姻的懲罰”,違背了“婚姻家庭保護”作為客觀價值秩序科以立法者的保護義務,基于此,憲法法院宣布1952年《個人所得稅法》因為抵觸《基本法》第6條第1款而違憲,并要求個人所得稅的制度建構必須考慮婚姻家庭的制度性保障。〔32〕BVerfGE 6, 55.德國憲法學的通說認為,《基本法》第6條第1款將婚姻與家庭列入國家秩序的特別保護,使其成為了涉及婚姻家庭的全部公法與私法制度的一個原則性規范。一方面,國家不得侵犯婚姻與家庭;另一方面,國家還負有積極的任務,去以適當的措施支持和幫助家庭。〔33〕參見[德]康拉德?黑塞:《聯邦德國憲法綱要》,李輝譯,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359頁。這意味著在各部門法的制度建構涉及婚姻家庭問題時,立法者負有義務去保護婚姻家庭利益。
(三)新刑訴法第188條例外條款在婚姻家庭保護上的進步與不足
我國新刑訴法第188條第1款的例外條款,應該也被看做立法者受婚姻家庭作為“客觀價值秩序”的約束而做制度建構的表現。〔34〕關于客觀價值秩序理論何以可以借鑒而作為處理中國憲法下的基本權利問題,筆者有初步的論證,參見張翔:《基本權利的雙重性質》,載《法學研究》2005年第3期。然而,在證人作證的制度建構上,立法者是否充分盡到了保護婚姻家庭之義務,卻不無疑問。
針對新刑訴法第188條第1款的例外條款的解釋,一般只是認為免除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的出庭義務,而非作證義務。新刑訴法第60條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這一條款一般性地科以了所有知道案件情況的人以作證義務。因此對于第188條第1款的例外條款,通常認為:“規定的是免于強制出庭,不是拒證權”,〔35〕朗勝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釋義(最新修訂版)》,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409頁。對此刑訴法學者多有批評。這些批評所體現的,正是《憲法》第49條“婚姻、家庭受國家保護”的價值理念。萬毅教授在《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出臺后曾上書全國人大法工委,建議將第188條中的“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這一但書規定,移至第59條第1款,即“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除外”,由此構建起真正意義上的近親屬拒絕作證權。在新刑訴法頒布之后,萬毅教授又批評認為:“立法者在立法思想上顧慮重重,既想革新傳統的‘大義滅親’式作證條款、推動我國刑事訴訟制度的文明化進程,又想維護打擊犯罪的實效性,權衡折中之下,遂出現了這種既免予近親屬在庭審階段強制出庭作證,又要求其在偵查階段接受調查、詢問這樣不倫不類的立法。”〔36〕萬毅:《新刑訴法證人出庭制度的若干法解釋問題》,載《甘肅政法學院學報》2013年第6期。這一批評不可謂不尖銳。此外,柯葛壯研究員在肯定這一條款“維護家庭關系的穩定和睦”、“具有人文精神”之外,認為這一條款范圍過窄,認為應當將(外)祖父母、(外)孫子女、岳父母、公婆、親兄弟姐妹、熱戀中的未婚夫妻等都納入免于出庭作證的范圍。〔37〕其他的批評,還包括認為該條規定的親屬范圍過窄,參見柯葛壯:《我國〈刑事訴訟法〉修正三論》,載《政治與法律》2012年第1期。這些觀點,應該說都是基于婚姻家庭保護的價值。在此意義上,新刑訴法第188條第1款的例外條款,在“婚姻家庭保護”這一憲法價值的貫徹上,是有進步的,但在很多學者看來,亦尚有不足。
五、憲法法益沖突與刑訴法學者的解決方案
至此,新刑訴法第188條中存在的憲法疑慮已經清晰了。第一,這一條款在落實“辯護權”和“婚姻家庭保護”兩項憲法法益上都有不足:一方面僅僅規定配偶、父母、子女“免于強制出庭”而非“免于強制作證”乃至“免于作證”,無法為婚姻家庭法益提供充足、徹底的保障;另一方面,在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提供證言的情況下,又不令其出庭接受質證,又有損于被告人的對質權(作為基本權利的“辯護權”的內容)。第二,在這一條款中兩相對立的“獲得辯護權”和“婚姻家庭保護”法益,因為方向相反,也基本沒有同時獲得充分實現之可能性。在具體案件中,往往顧此則失彼,實為兩難。
對此困難,李奮飛博士近期從刑訴法教義學的視角,提出了解決方案。他認為,應當從目的解釋的角度,將新刑訴法第188條第1款解釋為“免于強制作證的權利”而非“作證卻免于強制出庭的權利”,“具體而言就是,如果親屬證人在審前未向控方作證,那么法庭不得強制其到庭作證。如果其已在審前作證,且應當出庭作證,經人民法院通知沒有正當理由不出庭作證的,法院固然不能強制其出庭,但其審前書面證言也不應再作為定案的根據”。〔38〕李奮飛:《“作證卻免于強制出庭”抑或“免于強制作證”?——〈刑事訴訟法〉第188條第1款的法教義學分析》,載《中外法學》2015年第2期。李奮飛博士的解釋方案,應該說相當充分地考慮了“獲得辯護權”和“婚姻家庭保護”兩項憲法法益(雖然其行文中幾乎未提及憲法),也考慮了“查明案件的事實真相”等刑訴法的立法目的。同時,李奮飛博士還相當謹慎地避免解釋導致明顯的“體系違反”,他將新刑訴法第188條第1款僅僅解釋為“免于強制作證的權利”,而沒有更進一步解釋為“免于作證的權利”,因為后者會直接抵觸新刑訴法第60條“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的明確文義。可以推論,李奮飛博士的意思是:將188條第1款解釋為“免于強制作證的權利”后,配偶、父母、子女仍然是有作證義務的,其自愿提供證人證言仍然是履行作證義務的方式。毫無疑問,李奮飛博士的解釋方案相當精致,也有很強的說服力。但是筆者對此解決方案卻有以下幾點質疑。
(一)對“例外條款”做擴大解釋?
法解釋有一個基本規則:對于例外條款、但書條款,應作狹義解釋,而且避免類推適用。刑訴法第188條第1款的“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顯然是一個但書條款、例外條款。李奮飛博士將其含義,從字面的“作證卻免于強制出庭”擴大解釋為“免于強制作證”,有違反解釋規則之虞。例外之所以是例外,乃是因為立法者希望一般規則被盡可能廣泛適用。如果例外被寬泛解釋,則一般規則就被釜底抽薪,立法者本欲達到的一般性目的就會被最終摧毀。所以,對于例外條款的擴張解釋,會造成南轅北轍、背道而馳的效果。拉倫茨指出,如果要對“例外規定”做擴大解釋乃至類推適用,必須獲得立法理由的支持,而于此“參與立法程序者的規范想法可以提供一些咨詢”。但如果從立法理由上看,“其確僅針對此類事例,則不得將其他事例引入其中”。〔39〕[德]卡爾?拉倫茨:《法學方法論》,陳愛娥譯,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257頁。
考諸新刑訴法的立法資料,即使是李奮飛博士也無法認為有資料能支持他的擴大解釋,因為“參與立法程序者”(全國人大法工委刑法室、法工委副主任朗勝等)的解釋并不支持將188條第1款解釋為“免于強制作證的權利”。〔40〕參見李奮飛博士于《“作證卻免于強制出庭”抑或“免于強制作證”?——〈刑事訴訟法〉第188條第1款的法教義學分析》一文中對全國人大法工委刑法室所編《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條文說明、立法理由及相關規定》和法工委副主任朗勝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釋義》的引述。李奮飛博士的擴大解釋,依據的是“刑事訴訟法的整體目的”,強調“個別目的與整體目的的循環互動”。但總體上,他的解釋有欠個別目的的論證,而是以整體目的來擴張個別條款(并且是例外條款)的含義,存在可質疑之處。〔41〕基于例外條款應狹義解釋的規則,前述柯葛壯研究員認為應當將(外)祖父母、(外)孫子女、岳父母、公婆、親兄弟姐妹、熱戀中的未婚夫妻等都納入免于出庭作證范圍的主張在法解釋上也是無法成立的。當然,不妨礙其作為一種“立法論”主張。
(二)基于目的解釋而超越文義?
李奮飛博士所做的是“第188條第1款的目的解釋”,認為“親屬證人免于強制作證才能實現立法目的”。〔42〕李奮飛:《“作證卻免于強制出庭”抑或“免于強制作證”?——〈刑事訴訟法〉第188條第1款的法教義學分析》,載《中外法學》2015年第2期。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目的解釋,也要遵循法解釋的邊界。我們知道,解釋之所以為“解釋”,乃在于其受文本含義的約束。具體而言,就是法律解釋應以文義的可能范圍,或者“文義射程”為邊界。“法律解釋不得超越文義范圍”這一解釋規則,乃是民主原則、法治國原則、法的安定性等諸多原則之推導,限于主題,這里不展開說明。拉倫次引述Meier-Hayoz的論述“字義具有雙重任務:它是法官探尋意義的出發點,同時也是劃定其解釋活動的界限”并指出,“字義可能范圍外的說明,已經不再是闡明,而是改變其意義。這不是說,法官始終都不能逾越字義范圍;然而,其只有在特定要件下始被容許,而且已屬于‘公開的法續造的領域’”〔43〕[德]卡爾?拉倫茨:《法學方法論》,陳愛娥譯,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227頁。。也就是說,如果認為目的應優先于明確的字義,那么所謂的“解釋”已經不再是解釋了,而是漏洞補充、類推適用等法的續造活動。讓我們再次引用第188條第1款:“經人民法院通知,證人沒有正當理由不出庭作證的,人民法院可以強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應該說,其文義是清楚明白的。此外,這一條款的體系位置也有助理解這一條的文義。如前所述,萬毅教授在新刑訴法起草過程中曾建議將這一例外條款作為“證人作證義務”的例外條款,但新刑訴法卻仍將這一條款作為“證人強制出庭”條款的例外條款,這充分說明將其解釋為“免于強制作證”是超越文義的。以目的解釋超越文義,亦為解釋規則所不允許。〔44〕值得注意的是,新刑訴法第187條第3款規定了鑒定人應當出庭而不出庭,鑒定意見不得作為定案依據。這一規定可否被理解為刑訴法已經一般性地確立了“傳聞證據排除規則”,從而可以類推適用于證人證言呢?筆者認為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在于,根據刑訴法明白的條文,針對鑒定意見和證人證言,在不出庭是否導致無效問題上,立法者顯然已經做了分殊的處理,文義清楚,不能超越。(當然,這里依然存在合目的性限縮的可能性,下文將會討論)。
(三)“親屬證人拒不出庭則證言無效”的判斷是否過于倉促?
按照前述李奮飛博士的論述,將新刑訴法第188條第1款解釋為“免于強制作證的權利”并不導致新刑訴法第60條規定的包括親屬在內的所有人都負有的“作證義務”的免除,親屬自愿作證也是在履行作證義務。這一論述是在小心避免第188條第1款的解釋方案抵觸第60條之規定,避免體系違反。但是,如果認為“親屬證人拒不出庭則證言無效”,卻會發現這實際上免除了親屬的作證義務。這意味著,親屬如果在審前已經自愿作證了,但如果他(她)改變主意不想作證了,只要其拒絕出庭,其前面所做證言就歸于無效。這種法效果,已經使得新刑訴法第60條的一般性作證義務條款歸于無效。與此,李奮飛博士所言“法院固然不能強制其出庭”的判斷似乎過于倉促了。
(四)是否忽視了立法者的規范意圖
法律解釋,存在解釋目標的“主觀論”與“客觀論”兩種不同取向。主觀論將解釋的目標確定為探究歷史上立法者的心理意愿。這種觀點被批評為過于僵化,因為時移世易,仍以歷史上立法者的心理意愿為解釋準則,難免有刻舟求劍、膠柱鼓瑟之弊。從而客觀論,也就是以確定法律“客觀上”表現出來的意義為目標,被認為更為正確。然而,并不能因此而認為歷史上立法者的規范意圖毫無意義。當一部法律剛剛制定的時候,就輕易超越立法者的規范設定,而以解釋者的價值判斷為所謂解釋的依據,無疑是欠妥當的,不利于法秩序的穩定。就新刑訴法第188條第1款而言,盡管存在爭議,甚至被萬毅教授批評為“不倫不類”,但其規整意圖明確指向“僅僅免除親屬出庭之義務”而非“免除親屬作證之義務”應該說是非常明確的。在現代的民主法治國家,立法者在創制規范上具有優先的地位,雖然這并不排除法律解釋者參與創制規范的可能性,但完全忽略立法者的意圖也是難以接受的。
筆者整體上認同李奮飛博士更好協調婚姻家庭保護和對質權兩項法益的目標,〔45〕此外,對于李奮飛博士“刑訴法教義學之倡導”,本人非常認同。個人以為,這在刑訴法學科的方法論自覺上,具有開拓性的意義。但在具體方案上存在不同看法。下面,筆者將嘗試提出自己的解決方案。
六、合憲性解釋與個案中基本權利沖突的“實踐調和”
(一)刑訴法的合憲性解釋
李奮飛博士稱其解釋是基于刑訴法的“整體目的”,這是非常正確的解釋方向。但尚需做更為開放的思考,也就是考慮“整體法秩序”。這里涉及刑訴法與憲法關系的第二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前述的“刑訴法對憲法的具體化”):“法律的合憲性解釋”。〔46〕關于中國語境下的合憲性解釋,參見張翔:《兩種憲法案件:從合憲性解釋看憲法對司法的可能影響》,載《中國法學》2008年第3期。關于近年來我國對于合憲性解釋的研究綜述,參見黃卉:《合憲性解釋及其理論檢討》,載《中國法學》2014年第1期。如前所述,新刑訴法第188條第1款,涉及落實兩項憲法法益:“獲得辯護權”和“婚姻家庭保護”,但在兩個方向上都嫌不足。于此,單純依靠刑訴法解釋已經無法完全解決問題,而須做憲法層次的考慮。“為了說明這兩個規范在哪些適用范圍有所沖突,以及為了重建法律的和諧,有人嘗試通過解釋讓低位階規范的文義不再與高位階規范有所沖突。也就是說,人們將低位階規范的適用范圍限縮在高位階規范可適用的情形。這種方式,在實踐上最為重要者,就是我們對于單純法律所為的“合憲解釋”(verfassungskonforme Auslegung)”。〔47〕[德]英格博格?普珀:《法律思維小學堂》,蔡圣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58頁。李奮飛博士的解釋,也包括前述張龑博士的論述,實際上是將價值因素引入法律解釋。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從價值取向的角度來觀察法律,便必須取向于憲法”。〔48〕黃茂榮:《法學方法與現代民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86頁。部門法解釋所需要的價值補充,應該首先從憲法中尋找,而不能輕易超越實證法秩序而訴諸倫理觀、政治哲學或者比較法。在現代法治之中,憲法具有整個法秩序的價值基礎的性質。法律解釋,正如其他在憲法價值籠罩下的法律活動一樣,都應該以憲法作為修正法秩序的缺漏、補充漏洞的規范來源。“來自合憲法秩序的意義整體,對法律可以發揮補正功能的規范;發現它,并將之實現于裁判中,這正是司法的任務”。〔49〕[德]卡爾?拉倫茨:《法學方法論》,陳愛娥譯,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279頁。對于新刑訴法第188條第1款的解釋而言,既然其涉及憲法上的基本權利,就應當避免僅作刑訴法層次的解釋,而應將憲法規范作為“控制性”乃至“補充性”因素而納入思考。
合憲性解釋,是對法律的合憲性解釋。作為解釋,其仍然不能超越法律的可能文義的邊界,也不能因為考慮憲法價值層面,而對法律的目的置之不理。但是,在合憲性解釋之外,還有“合憲性法律續造”的層面。“假使立法者追求的影響作用超越憲法容許的范圍,可以將法律限縮解釋至‘合憲的’范圍。于此,立法者所選擇的準則,在以憲法能維持的程度內,也被維持。此處涉及的不再是解釋,毋寧是一種目的論的限縮。一種合憲的法的續造。”〔50〕[德]卡爾?拉倫茨:《法學方法論》,陳愛娥譯,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243頁。換言之,如果立法者所制定的規范,超越了憲法所能允許的邊界,則可以依據憲法對法律做限縮的解釋。這種限縮,是以法律外的目的考量(作為上位法的憲法)為基礎的,因而是一種目的性限縮。在此意義上,已經不再是在文義范圍內的“解釋”,而是超越文義的“法的續造”。“合憲性法律續造”提示我們,對于部門法的理解,存在一種可以超越文義的法的續造,其依據,是居于上位法、最高法地位的,作為整個法秩序價值基礎的憲法。其方式,是對法律的“目的性限縮”。這意味著,在一般情形下,應當尊重立法者對憲法的具體化,但如果立法者逾越憲法所設定的邊界而謀求某種抵觸憲法的立法效果時,就可以對該當法律規范進行限縮的解釋。并且,即使這種目的性限縮是有違文義的,也可允許,因為這在整體上是取向于憲法秩序的。
(二)個案衡量、“實踐調和”與目的性限縮
就本文所處理的問題而言,對新刑訴法第188條第1款進行“合憲的”塑造的前提,是要明確憲法規范的含義。這里必須面對非常困難的“基本權利沖突”。如前所述,第188條第1款中存在“獲得辯護權”和“婚姻家庭保護”兩個基本權利位階的法益之間的沖突。如何協調?憲法所保護的基本權利,其重要性無須多言,而相互之間并無當然的高低先后之順位關系。例如,言論自由與人格尊嚴,二者在誹謗案件的認定中恒常沖突,但絕無一般性地給出孰優孰劣判斷的可能性。某些情形下,人格尊嚴優先,而在另外的情形下,則是言論自由優先。當兩項基本權利沖突時,“手心手背都是肉”、“世間安得兩全法”,舍此取彼還是舍彼取此,實費思量。憲法學理論在經過艱難探索后,最終明確了“個案衡量”、“實踐調和”的解決思路。〔51〕關于如何處理基本權利沖突的學理發展,參見張翔:《基本權利沖突的規范結構與解決模式》,載《法商研究》2006年4期。
對于相互沖突的法益,通常的認識會認為權衡的結果只能是犧牲一方,而保護另一方。但是,現代的憲法學理論卻要求不能對此匆忙草率地進行抽象的“價值權衡”,而是要讓兩種法益都能發揮最佳的功效。“在不確定的情況下選擇能夠使基本權利規范發揮最大法律效力的解釋”。〔52〕BVerfGE 32,54 (71);BVerfGE 6, 55 (72).德國憲法法院在處理藝術作品的傳播自由與為保護青少年而禁止猥褻物品自由銷售的規范沖突的案件時,提出了在個案中進行“實踐調和”(praktische Konkordanz)的原則。實踐調和原則的基本內涵是:盡管立法者擁有具體化憲法上的“形成自由”和做出評價的權力,但卻不能將某種憲法法益置于絕對的優先位置,并使其毫無例外地、自始至終地相對于別的法益享有絕對的保障。相反,面對相互沖突的法益,立法者應通過充分對比沖突法益在具體情境中的各自權重,而使所有的法益價值都能獲得最妥善的衡平。〔53〕另請參見[德]康拉德?黑塞:《聯邦德國憲法綱要》,李輝譯,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49-51頁。而且,這種“實踐調和”,不僅僅是對立法者的要求,也是對司法過程中解釋適用法律的要求,而司法者在個案中調和基本權利沖突,運用的正是“個案中之法益衡量”的方法。〔54〕參見[德]卡爾?拉倫茨:《法學方法論》,陳愛娥譯,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312頁。
就本文所處理的問題而言,立法者在制定刑訴法相關條款,處理“對質權”與“婚姻家庭保護”兩種法益的沖突時,既沒有賦予“婚姻家庭保護”以絕對的優先性而規定絕對的親屬免證權,〔55〕此外,立法者尚有有效打擊犯罪的考慮,從而“立法方面頗有顧慮”。參見龍宗智:《薄熙來案審判中的若干證據法問題》,載《法學》2013年第10期。也沒有完全倒向“對質權”而規定包括近親屬在內的所有證人都可被強制出庭,應該說思慮尚屬充分。萬毅教授批評“立法者在立法思想上顧慮重重”、“既想革新,又想維護”,但也說立法者在“權衡折中”。其實,對各種價值目標衡量協調,正是立法的常態。即使立法水平大幅度提高,要求立法者對所有案件中的具體情形都預先做出衡量,也屬苛責。筆者認為,針對這一規范,更為重要而可行的是:在個案中針對具體情形,考量兩相沖突的法益的各自權重,比較衡量,以做出最后的權衡判斷。
(三)針對薄案的具體衡量
遵循此“在個案中做實踐調和”的思路,本文不欲提出第188條第1款的一般性解釋方案,而是希望在個案中處理。以本文一開始談及的“薄熙來案”為例,以下具體細節值得考慮:第一,薄谷開來在審前已經提供證人證言,并有作證錄像呈堂,這表明其已不甚在意其婚姻利益,甚至可以認為是放棄了婚姻利益;第二,薄熙來多次反駁薄谷開來證詞,要求薄谷開來出庭,也可理解為其為了質問證人以獲得有效辯護,也已經放棄了婚姻利益的保護;第三,在二人的婚姻關系中,存在違反《婚姻法》第4條“夫妻應當互相忠實”的事實;第四,薄谷開來之證人證言對于認定薄熙來構成貪污受賄犯罪至關重要,其不僅是關鍵證人,更是關鍵的不利證人。
基于以上具體因素,似可如此評價:在夫妻一方指證另一方犯罪,而對方反指其撒謊并要求其出庭質證的條件下,夫妻恩義已絕,需要保護之婚姻家庭法益已非常淡薄。相對而言,薄熙來面臨重罪指控,對其作出極端不利證言的最關鍵的證人之一卻拒絕出庭,從而無法對其證人證言進行質證,導致薄熙來“獲得有效辯護”的法益處于極端危險之中。此時,雖然依據新刑訴法第188條第1款的解釋,法院不強制薄谷開來出庭形式上合法,但卻存在損害重大法益之危險。“如果具體個案清楚地可以被包攝到法條文之下,但目的性衡量的結果卻是反對將該法條適用于此案件,這個法律的適用范圍就可能通過所謂的‘目的性限縮來限制’,使其不再涵蓋這個案件”。〔56〕[德]英格博格?普珀:《法律思維小學堂》,蔡圣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60頁。基于本案中婚姻家庭法益已經至為微弱,乃至于無,而獲得有效辯護以對抗重罪指控的法益非常重大而突出,因此,筆者認為:可以在此案中對“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條款作出“合憲法”的“目的性限縮”,不使其涵蓋此案,也就是,法院可以強制薄谷開來出庭。〔57〕有學者提出,可以用“庭前對質詢問”的方式來解決對質權和婚姻家庭法益的沖突。參見龍宗智:《薄熙來案審判中的若干證據法問題》,載《法學》2013年第10期。但筆者以為,庭前對質詢問并非現有刑訴法已規定的制度,在法解釋中難以包容,只能作為立法建議。同時,“庭前對質”仍然表現出“夫妻對峙”、“反目成仇”的景象,與出庭質證并無根本區別。
七、結語
關于憲法與部門法的關系,筆者還想做一些補充的說明。在處理憲法與部門法關系上,我們似乎應該避免“部門法學者的漠視”與“憲法學者的傲慢”。根據筆者的觀察,一些部門法學者似乎有漠視憲法的基本決定的傾向,在立法第1條寫入“根據憲法,制定本法”后,憲法問題就幾乎不再被提起。而憲法學者又有一種基于憲法作為最高法的傲慢,動輒指稱某某法律違憲,而無視部門法的規范與法理的嚴整體系。那么,憲法與部門法究竟應是一種怎樣的關系?
在前文中,筆者已經描述了憲法與部門法關系的兩個層面:“法律對憲法的具體化”和“法律的合憲性解釋”。首先是“法律對憲法的具體化”。憲法措辭簡潔、意涵抽象,立法者負有將憲法的規范意旨進一步形成的義務,也就是具體化憲法的義務。前述的“辯護權——獲得有效辯護權——對質權——不利證人出庭”的脈絡,也就是從《憲法》第125條“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到刑訴法相關條文的規范生長過程,就是這種具體化的范例。其次是“法律的合憲性解釋”,也就是要求對法律的具體解釋和適用,必須時刻關照憲法價值的落實,將憲法作為法律解釋的“補充性”和“控制性”因素,使得法律的具體操作合于憲法的整體秩序。最后,還有憲法與部門法關系的第三個層面,也就是“法律的合憲性審查”的層面。這個層面最為學術界關注,而在我國尚無有效制度支撐。相關論說甚多,此處不贅。
對于憲法與部門法之關系,憲法學上著名的“交互影響說”是對二者關系要點的最精煉概括。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在呂特判決中,針對“一般性法律可以限制言論自由”的規范,提出了“交互影響”的論證(交互效果、相互影響)(Wechselwirkung),認為,法律固然可以對基本權利做出限制,但在自由民主的體制下,法律卻要依據基本權利的價值來解釋。不能僅僅認為基本權利受到了法律的單方限制,而要同時認識到,基本權利在自由民主國家是憲法所追求的客觀價值所在,對于法律的解釋必須本于此項認識而進行,這意味著法律本身也受著基本權利的限制。〔58〕參見張紅:“呂特案”,載張翔主編:《德國憲法案例選釋(第一輯)?基本權利總論》,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27-28頁。一方面憲法要依賴部門法去落實和實踐,要看到立法者構建部門法秩序的過程也是憲法具體化的過程,要尊重立法者對于憲法的理解和規范展開。同時,對于法律的解釋又必須以憲法精神籠罩和控制。對于法學的學術而言,這意味著,憲法學者必須重視立法機關依據憲法而對憲法的發展,〔59〕關于我國立法機關通過立法發展憲法的實證研究,參見林彥:《通過立法發展憲法——兼論憲法發展程序間的制度競爭》,載《清華法學》2013年第2期。不要輕率否定立法者對社會規整的設想,并有選擇地將立法者對憲法的理解吸收和接受為對憲法規范的解釋,以及充分理解部門法學的學理。同時,部門法學者在解釋法律時,出于維護憲法價值,實現憲法之下法秩序的和諧之目標,應該對法律做合憲性的解釋乃至合憲性的續造。憲法學與部門法學不可相互漠視,也不可以傲慢地以為“本學科可以自足”。這里,援引兩位青年憲法學者的精彩論證(他們所處理的共同問題,是刑法里的“涉戶犯罪”與憲法中“住宅自由”的規范整合),來說明憲法學者在此問題上的自覺。
杜強強博士主張“憲法規范與刑法規范之詮釋循環”、“憲法和部門法的相互動態調適”,他認為:“一國法律秩序本是一個動態的規范體系,對法律的解釋需要考慮到憲法的規定,而對憲法的解釋豈能無視普通法律的規定?法律解釋者負有義務將憲法與下位階法律規范互為動態調整而維持法律體系的和諧。”〔60〕杜強強:《論憲法規范與刑法規范之詮釋循環——以入戶搶劫與住宅自由概念為例》,載《法學家》2015年第2期。
杜強強博士還描述了由部門法入手探討憲法規范的內涵的“以憲就法”與通過合憲性解釋而使憲法價值理念注入部門法的“以法就憲”之間的往返流連,并且批評了實踐中不允許法院援引憲法,而導致法官繞過實定法體系而訴諸虛無縹緲的“法感”的荒謬。
白斌博士近年來一直致力于溝通憲法與刑法,他有這樣的論述:“作為憲法規范的具體化,刑法規范承擔著實踐憲法中基本權利之核心價值的重任。故而,刑法教義學就特定刑法規范開展解釋時,不應局限于從刑法文本與規范框架中尋找依據,也應重視從憲法教義學的高度,著眼于從憲法規范與基本權利價值的層面為刑法解釋尋找理論資源,而不宜對后者完全視而不見,甚或做出有違立憲主義精神的判斷。此條基準無論對于刑事立法,抑或刑事司法裁判活動,都是適用的。”〔61〕白斌:《憲法價值視域中的涉戶犯罪》,載《法學研究》2013年第6期。他主張在涉及憲法問題的部門法適用中,要有“思慮周全、反復衡量的苦心”。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政”;“要使每一項立法都符合憲法精神”。并特別強調“堅持立改廢釋并舉”,強調法律解釋在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的重要作用。對于法律學者而言,這也意味著,要有對憲法與部門關聯性的自覺意識,要理解憲法與部門法之間的“交互影響”,要互相尊重和理解對方學科的知識,通過運用具體化憲法和合憲性解釋的法律技藝,向著憲法教義學與部門法教義學的體系整合,相互融通,相向而行。
(責任編輯:李秀清)
*張翔,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本文受“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青年教師學術創新團隊建設計劃”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