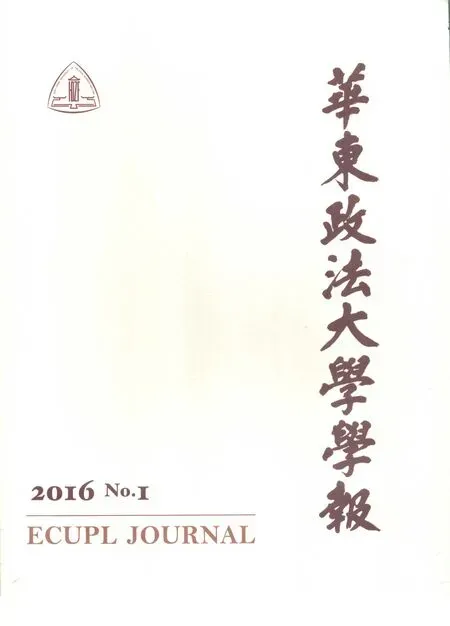論中國現代法學學術之開端
劉 猛
?
論中國現代法學學術之開端
劉 猛*
目 次
一、法學的基礎:法律教育
二、現代法學的要件:研究機關與研究學人
三、結論
現代法學在中國的誕生,是建立在清末民初四五十年的法科教育基礎上的。但是,法律教育并不等于法學研究,清末一系列的學堂和民初的法政專門學校,都是以實務為傾向,著力于培養政治人才和司法官吏,無法也不可能擔負起寄養現代法學學術的重任。處身20世紀的世界學術格局中,中國現代法學的誕生須立于兩個基礎之上,一是要有現代的大學或者學術研究機關,一是要有中國的受過西方法學學術訓練的學者以法學為業研治學術。1917年的北大改革,為法學的誕生提供了一個研究的環境;20世紀20年代一批留學生的回國任教,為法學的誕生提供了智識基礎。也就是在這段時期,現代法學在中國才落地生根。
中國現代法學 法律教育 法政專門學校 北大改革 朝陽大學
在晚清七十年的變局中,中國開啟了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從軍事、技術的西藝到制度方面的西政,次第變更開來。經過國際公法的引入及清末新政修訂法律繼受西法,法律知識也開始了從傳統律學到現代的法學的轉換。
一、法學的基礎:法律教育
傳統中國的學問,是以經、史、子、集為標準分類,并以登科取仕的制度方式加以鞏固和傳承的。隨著傳教士的東來,帶來了天文、數學等西式學問,開闊了國人的眼界。最初,治國者雖然認為它們好玩兒,但并不把這些技巧與國家治理聯系到一塊。等到列強把大清帝國打得落花流水,國人開始正視西方,開始向西方學習,學習西方的“科學”。“科學”者,分科治學;相應的按照西式的分類,法政為其中一科。學習“科學”學問的一個載體便是學堂。
(一)晚清的同文館及法律類學堂
關于中國近代法律教育的論著,已有很多,論者大多都不約而同地把其源頭追溯至京師同文館。〔1〕關于法律教育的著述頗豐,主要有湯能松等:《探索的軌跡——中國法學教育發展史略》,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李貴連:《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法學》(上)、(下),載李貴連主編:《二十世紀的中國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亦載李貴連:《近代中國法制與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李貴連:《中國近現代法學的百年歷程(1840~1949年)》,載蘇力、賀衛方主編:《20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法學卷》,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王健:《中國近代的法律教育》,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程燎原:《清末法政人的世界》,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李貴連等編:《百年法學——北京大學法學院院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何勤華:《中國法學史》(第三卷),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等。1867年12月,設立初衷為培養翻譯人才的京師同文館,在創立后的第五個年頭,聘請英文教習丁韙良開設國際法方面的課程。這跟丁氏翻譯惠頓的《萬國公法》有關,也與一起外交事件有關。1864年普丹戰爭期間,普魯士軍艦在渤海灣拿捕一艘丹麥船,清廷按照惠頓著作中領海規則,提出抗議,船只得以獲得釋放。這讓秉持實用主義的清政府意識到西方游戲規則的用處,為國際法的本土學習敞開了大門。〔2〕參見王健:《中國近代的法律教育》,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138頁。丁韙良在回美國進修一年之后回到中國正式上任,教授萬國公法。其后同文館開設國際公法的課程,并組織翻譯了一大批西方的最新國際公法方面的著作。然而,范圍僅限于國際公法方面,未曾突破到民法、刑法等領域。〔3〕參見王健:《中國近代的法律教育》,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44-145頁。個中原因,無非同文館隸屬于政府,朝中人士的著眼點還是在于能立竿見影的救亡圖存工具,并沒有學問的概念和長遠的規劃。其實嚴格說來,教授“萬國公法”是為了培養外交人才,“萬國公法”只是外交人才必須掌握的一門科目,不能算作法律教育,就像當下財經院系開設“經濟法”,但不能把它們算作法律教育是一個道理;且按照那時的學科體系,“國際公法”能否算作法學尚屬未定之事,它在很大程度上被劃入政治學的范疇。所以,以“萬國公法”的教授作為近代法律教育的開端也不是沒有質疑的余地。1897年開設的湖南時務學堂,還有其他各地的學堂,也有開設萬國公法課程者。其主事者為梁啟超,他的出身和活動重點決定了此學堂不可能側重法律,其目的在于培養政治人才而非法律人才,法律學課程不過是這個培養規劃中不可或缺的一項罷了。〔4〕關于湖南時務學堂,參見李貴連:《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法學(下)》,載李貴連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8-40頁;王健:《中國近代的法律教育》,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170頁。
甲午一役,中國戰敗,清廷不得不變法改革。光緒二十八年四月初六(1902年5月12日),諭曰:“現在通商交涉,事益繁多。著派沈家本、伍廷芳將一切現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參酌各國法律,悉心考訂,妥為擬議。務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隨后設立了修訂法律館。光緒三十一年三月二十日(1905年4月24日)兩人奏請設置法律學堂,以培養專門的法律人才。法律學堂于1906年開學,除了有兩門中國法(指大清律例等傳統律學)的課程為中國教員講授外,其他大部分的課程都由來館修律的日本法律顧問擔任。〔5〕王健:《中國近代的法律教育》,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94頁。除此之外,學部在1907年2月2日設立了京師法政學堂,初“以造就完全法政通才為宗旨”,繼改為“養成專門法政學識,足資應用”,對應用的重視程度加強。京師法律學堂和京師法政學堂的培養目標不同,“再京師及各省法政學堂所設別科,其學科程度畢業年限,均與京師法律學堂大略相同。惟法律學堂專攻法律,畢業者宜專任之于司法官。法政別科兼習法律政治,畢業者可用之于行政司法兩途,其性質微有不同”。〔6〕《學部奏法政學堂別科酌獎出身片》,載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編纂:《大清宣統新法令》(第二十冊),上海商務印書館宣統二年印行,第18頁。關于京師法律學堂與京師法政學堂一個較詳細的比對,參見孫慧敏:《從東京、北京到上海:日系法學教育與中國律師的養成(1902-1914)》,載《法制史研究》(臺北)2002年第3期,第180-181頁。所以嚴格算來,中國現代正規且系統的法律教育應自京師法律學堂開始算起。在地方上,開辦較早的有1905年開設的直隸法政學堂,以培養佐理地方政治人才為目標,強調“以期適于實用”,其各科講授者也是聘請日本人擔任。〔7〕參見王健:《中國近代的法律教育》,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199-204頁。其后1910年,為了滿足司法人才的需求,清廷要求各省法政學堂次第擴充,“特別要盡快培養審判和檢察人員,以應付各地審判廳的急需”,并準予設立私立法政學堂。在政府力量的推動下,各省的法政學堂如雨后春筍般出現,主要是聘請日本人或者留日學生講授課程。這些留日學生還編定了大量的法科講義,實際上都是“日本法學家的著作、講義的編譯性作品”,先在日本編譯印刷,然后運回國內發售。〔8〕王健:《中國近代的法律教育》,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206-207頁。關于法政學堂的名單,參見該書第211-216頁。
清末之際,政治的氛圍是救亡圖存,所以這些法政學堂都是為了應人才需要而創設,并無長遠的規劃,帶有極大的功利色彩。“除了京師法律學堂以外,中國政府之所以開辦法學教育,并不是因為對法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價值有所認識,而只是因為分設法律科與政治科,是一種具有現代性的教育體制,所以清末中國的法政學堂,大都是以培養行政官與外交官為主要目標。而那些在‘法政學’觀念籠罩下的法校學生,雖然接受的是法學教育,但還是將找尋救亡之道、累積入仕資格當做主要的求學目標”。〔9〕孫慧敏:《從東京、北京到上海:日系法學教育與中國律師的養成(1902-1914)》,載《法制史研究》(臺北)2002年第3期,第195、196頁。主事京師法律學堂的沈家本、伍廷芳,中西合璧,深具世界眼光和長久打算,其計劃創設的學堂自然別開一面,非其他學堂所能望其項背,但這畢竟是特例。
1905年科舉制廢除后,原來的入仕做官一途徹底斷絕,官方和民間都在尋找一種解決辦法,以保持人才的接續和社會矛盾的消解,留學一項被納入其中。留學生考試授官逐漸成為一項正式的制度,〔10〕參見王健:《中國近代的法律教育》,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119頁。也可參見程燎原:《清末法政人的世界》,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156頁。在留學所學學科中,無論是從難易程度考量還是與政途所需的應用性考量,法政科都是首選。特別是留日學生的示范效應,使得這種趨勢越來越嚴重,影響了清末民初幾十年的法科學習氛圍。另一個替代方案便是大興學堂。〔11〕關于興辦學堂填補科舉制的功用和科舉廢除后造成的士與大夫的分離,參見羅志田:《清季科舉制改革的社會影響》,載《中國社會科學》1998年第4期。科舉終止后,“各省次第將舊有書院改設存古學堂,以解決士子讀書和出路問題”。〔12〕王健:《中國近代的法律教育》,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01頁。其他學堂亦大興,其中尤以法政學堂最為興旺。而民間“乃以政法為官之利器,法校為官所產生,腥膻趨附,熏蕕并進。借學漁利者,方利用之以詐取人財”。〔13〕《競明〈法政學校今昔觀〉》,載朱有瓛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三輯上冊),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658頁。因為在新近傳入的西式學科中,法政科和仕途最為接近,實際上在清末民初背景下法政人才儼然成了傳統“士大夫”的現代翻版。但是統而論之,這些學堂,無一不是以造就實用政治人才為目的,以彌補科舉制廢除帶來的人才斷缺為目的,不存在學問研究的概念;也就是說,那時雖然學制框架轉換了,但是政治制度和政治氛圍依舊,傳統的登科入仕理念還是深植在每個學堂習法政科的人心中。
(二)大學里的法科
民初培養法政人才的機關,概分兩類:一類是綜合大學里的法科,一是專門法政學校。清末民初出現了大學,這些大學很多設有法科,但是面臨的困難似乎大多一致,那就是教員的缺乏、授課內容完全照搬西方某一國家的法律或法條。這一方面與聘請的教員所屬國家有關,也緣于中國尚未有自身的現代法典和單行法律這些載體。另外,其時大學中法科的誘惑力好似遠小于法政專門學校,相比較來說,法政專門學校更易接觸到法界名流并聽其講課,又因集眾效應更容易進入法界工作,所以大學中的法科不占主導地位。其時設有法科的大學,概有北京大學、北洋大學、山西大學堂(北京大學將在下文論述)。北洋大學作為近代中國第一所大學,其“法律科也是中國近代的第一個法律教育機構”。〔14〕王健:《中國近代的法律教育》,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57-158頁。其從1895年開辦之初就在章程中列有法律學門,“并在其下設若干法律課目”,在1899年產生第一批畢業生二十幾人。〔15〕王健:《中國近代的法律教育》,第154-155頁。雖然其中有王寵惠這樣之后名揚國際法學界的學者,但是中西沖突下發蒙階段的法律教育,在當時尚沒有辦法脫離單純的翻譯、介紹水平。1907年的時候,法律科僅有兩名教師,美國人林文德教外國法,中國人劉國珍教中國法律。〔16〕王健:《中國近代的法律教育》,第155頁。隨后也多聘外籍教員,均以外語講授,帶有濃厚的“美國化”色彩。大約在1914年,北洋“有外籍教員五十三人,除物理、土木工程系各有一英籍教員,法律系有一奧籍教員外,其余均為美國人。……法科的美國教員沒有了解中國社會的能力,他們除給學生講些固定的課本外,就把學生硬塞到許多美國案例里;法科學生肚子里裝滿了美國案例,但要當律師、做法官,還得自修中國法律,因此不少北洋法科的畢業生都轉入了外交界”。〔17〕北洋大學史料小組:《北洋大學事略》,載《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一輯),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頁。據《國立北洋大學三十七年班畢業紀念刊》記載,從1905年到1911年,法科法律學門畢業生僅9名。〔18〕李貴連:《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法學(下)》,載李貴連主編:《二十世紀的中國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2頁。后來經北大校長蔡元培建議,北洋法科并入北大,1918年停辦,結束了其短暫的法科辦學歷程。
山西大學堂在最初籌辦時,與英國駐滬總教士李提摩太達成協議,將山西賠償教案的五十萬兩白銀用于籌辦中西學堂,后改為西齋并入山西大學堂,創辦之初便籌劃有法律學門,為西齋五門中的一門,內分政治、財政、交涉、公法等學。〔19〕《光緒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山西巡撫岑春煊奏請將中西大學堂歸并山西大學堂作為西學專齋折(附合同繕具清單)》,載朱有瓛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一輯下冊),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819頁。到了解榮輅任監督時,在西齋添設一門法律學門,偏重歐美法律。〔20〕《〈山西大學紀略〉記教學上的重要設施》,載朱有瓛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二輯上冊),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008頁。在1906年的職教員表中,西齋教員英國人畢善功教授法律,并拿中西兩齋教員中最高的薪水。〔21〕《1906年職教員表》,載朱有瓛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二輯上冊),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000-1002頁。外國人講授,中國人翻譯,學生筆記,下課后互相對證。由于師資落后、教學方法落后以及課程貧乏,學生所得知識十分有限。〔22〕李貴連:《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法學(下)》,載李貴連主編:《二十世紀的中國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頁。
無論是北洋大學還是山西大學堂的法科教育,都少有可圈可點之處,皆需借助外國人的力量進行講授;雖在中國教育史上留下濃重一筆,只因是其時少有的大學,其對法律教育的貢獻實則乏善可陳。
(三)法科專門學校:以“北朝陽南東吳”為例
民初之際,清末的法律學堂紛紛改名法政學校,如前述的京師法律學堂和京師法政學堂便與財政學堂三所一起,合并為國立北京法政專門學校;也有很多是新設立的。而公立的法政專門學校,“乃據歷來視學報告,其中辦事尚稱合法者,固亦有之。而如吉林公立法政專門學校校風不良,教員學生諸多曠課;福建公立法政專門學校,濫收學生,程度諸未適合,管理教授,亦多懈弛;廣東公立法政專門學校所招學生,程度參差不齊,中有英文算學尚抄寫不清者;湖南公立法政專門學校,教員既多缺席,管理尤欠精神;其余類此者,亦復不少”。〔23〕《1914年9月18日教育部咨行各省聲明本部對于法政教育方針》,載朱有瓛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三輯上冊),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616頁。私立法政學校更是有名無實,“無論合格學生不易招集,即相當教員亦所難求。考其內容,大率有專門之名,而無專門之實。創辦者視為營業之市場,就學者藉作獵官之途徑,弊端百出,殊堪殷憂”。〔24〕《1913年11月22日教育部通咨各省私立法政專門學校酌量停辦或改為講習科》,載朱有瓛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三輯上冊),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615頁。特別是南京的法政學校,管理寬縱,教授松懈,“此類私立法政,能少收一學生,則少誤一青年,而國家社會將來可少受一分禍害也”。〔25〕《〈教育周報〉記南京法政學校》,載朱有瓛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三輯上冊),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651頁。政府因此飭令浙江私立赤城法政專門學校因招生人數突增、無端添列科目、倒填入學日期而停辦。政府還停辦了江蘇省私立南京大學等十三所學校。〔26〕《1913年教育部派員察視私立法政之結果》,載朱有瓛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三輯上冊),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647、648頁。其中比較好的國立北京法政專門學校,是少有的幾所國立法政專門學校之一,約1916年之際,“最近邵校長任內,專任教員多至六人。周校長接辦已減為四人。至饒前校長時,專任職或聘二、三人不等,余皆以兼任職充之。校長接事時,專任教授者仍有兩員。至本年暑假后,魏易、陳介兩員辭職,則僅添聘一人,而兼任教員,乃至有五十一員之多。據此實況,頗與初愿相違,惟事實所呈,亦竟不得不爾。本校為專門學校,以養成專門適用之才為務,以故如司法、如財政、如銀行、關稅等科學,歷年以來,皆聘選法院、財部、銀行等機關學有專長、經驗宏富之員分別講授。此項教員雖系兼任,亦既多歷年所,于所任之講科,類能以實務上之體驗,為專精之啟發。較之專任教員但能講授學理者,于學生方面之利益,所獲轉多”。〔27〕《國立北京法政專門學校五~六年度狀況報告》,載朱有瓛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三輯上冊),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626、627頁。學校方面,更傾向于任用兼職的、從事實務工作的人為教員,歷年皆是如此,國立學校尚且如此,其他各地的法政專門學校的實用傾向,管窺可見一斑。此外還有如上海民國法律學校,其目標不在培養司法官或行政官,而是要使國民具有“完全法治之常識”。〔28〕孫慧敏:《從東京、北京到上海:日系法學教育與中國律師的養成(1902-1914)》,載《法制史研究》(臺北)2002年第三期,第186頁。
這些法政專門學校,以朝陽大學和東吳法學院在后世歷史上名氣最大,當然這基于多方面原因。朝陽大學是1912年由汪有齡等人創辦的私立法科大學,次年8月開始招生,不長的時間內便獲得教育部和法部的表彰。〔29〕參見王郁驄:《校史志略(一)》,載薛君度、熊先覺、徐葵主編:《法學搖籃朝陽大學》,東方出版社2001年增訂版,第8頁。其以注重司法實踐著稱,其畢業生多去做司法官,〔30〕參見王健:《中國近代的法律教育》,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255頁。這樣一所法科學校以培養法律職業人材為目標,而非培養法律研究人員。相對于其他私立法政學校,其課堂紀律較好,學校亦利用各種關系幫助學生謀取職位,以維護學校的聲譽并繼續招生于長遠。經過多年的沉潛,朝陽大學的畢業生開始在社會上嶄露頭角,至1930年代中葉,開始在法政等機關占據中層地位。〔31〕參見楊昂:《學風、世變與民國法學:朝陽大學研究(1912~1946)》,中國人民大學2005年博士學位論文,第61-62頁。在這種集眾效應之下,“無朝不成院”的格局逐步形成。正如陶希圣在《朝陽大學二三事》中回憶的:
中國法學與司法界,朝陽大學出身的人才是第一流,亦可以說是主流。法律教育史上,朝陽大學應居第一位。希圣是北京大學法律學系出身的一個人,何以這樣推重朝陽大學及其校友。我推重朝陽大學,并不是貶低北京大學。因為北京大學法科與法律學系出身的人士不一定進司法界,朝陽大學的校友卻大抵受任法官。中國司法史上,法官之第一流,不止于朝陽大學,北京法政專門學校、上海法政專門學校、還有東吳法學院,皆出了第一流法官。但若說朝陽大學出身的人士為司法界的主流,我想朝陽大學的校友是當仁不讓的。〔32〕黃懷周:《〈法律評論〉紀念朝陽大學創立70周年和〈法律評論〉創刊60周年專刊簡介》,載薛君度、熊先覺、徐葵主編:《法學搖籃朝陽大學》,東方出版社2001年增訂版,第60頁。
朝陽大學還有值得稱贊的,那便是《法律評論》周刊和講義。《法律評論》(The Law Weekly Review)創刊于1923年7月,主要有論說、判例商榷、法界消息、外國法制新聞、裁判小說、參考資料、大理院解釋、大理院判決及裁決全文、重要法令及公文等欄目,每期30頁左右。《法律評論》“意在商榷法制,批評判例,凡足資司法改良者,靡不具載。”其旨趣“要在保司法之尊嚴,圖法制之改善,而溺職違法者,且將予以針砭,期于法治能舉其實,司法獨立,而后國家乃有法治之可言”。〔33〕張耀曾:《題辭》、林長民:《題辭》,載《法律評論》周刊創刊號,1923年7月1日,第1、4頁。其目標在于“1、研究法律問題以推進司法改革。2、評論法院裁判以探究法律真諦。3、公布各省法院新聞,使民眾知曉各地司法是如何運作的。4、刊發介紹各國的法律和司法。5、當司法受干預時,幫助法院維護真理和正義。6、當司法人員有公職不法或違反法律時,幫助民眾申冤。7、評論關涉上海及他處會審公廨和領事裁判權的事務,以引起外國人的注意”。〔34〕Kiang Young,“The Law Weekly Review Foreword”,載《法律評論》周刊創刊號,1923年7月1日,背面第1頁。可見,《法律評論》創辦的意圖,并非在打造一份學術期刊,而是意在研究、改進司法實踐。從創刊號中張耀曾、梁啟超、章宗祥、林長民的“題辭”和江庸的“發刊詞”中也可以明顯看出,他們幾位論述時代背景及創刊心愿,所談的都是法官和司法問題,沒有法學研究的內容。即使它間或刊載一些較有學術性的文章,可是在正本期刊中所占分量極小,不能算它的主要部分,它與《國立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季刊》那種動輒一篇文章十幾二十頁的學術期刊,在性質上是不一樣的;即便是北京法政專門學校的《法政學報》,在學術性上也要比它強出很多。
朝陽講義的名氣很大,據學子回憶:“學校自辦有印刷部,教師講義在授課一日前交稿,至授課之日一定發出講義,授課時口授者及黑板補充者,學生隨堂筆錄,由各班優秀學生隨著整理出朝陽大學一套法學講義,于法學各科稱得起是完美無缺,一時各大學多取為研究法學或應考法官與一般文官重要參考資料。”〔35〕黃懷周:《〈法律評論〉紀念朝陽大學創立70周年和〈法律評論〉創刊60周年專刊簡介》,載薛君度、熊先覺、徐葵主編:《法學搖籃朝陽大學》,東方出版社2001年增訂版,第55頁。陶希圣在《朝陽大學二三事》中說:“民國19年(1930年)之前,朝陽大學出版的法學講義,包括民刑實體法與訴訟法,一部叢書,事實上全國各省區法政學校大抵采用為法學教本……北京大學法科或法學院一直未將法學講義出版問世。朝陽大學出版可以發行全國的一套講義便遍行全國各省區法政學校,為課程和參考的典籍。北大法科既不爭先,朝大也就當仁不讓了。”〔36〕黃懷周:《〈法律評論〉紀念朝陽大學創立70周年和〈法律評論〉創刊60周年專刊簡介》,載薛君度、熊先覺、徐葵主編:《法學搖籃朝陽大學》,東方出版社2001年增訂版,第60頁。北大何以不印制講義呢?因為在蔡元培改革前的北大,“以教員印發講義,而在講堂上照講義演述一遍,便算盡責,并且這種講義,年年如此,永不修增。學生領了講義,就算得了學問,不要筆述,也不要看參考書,不要做實驗的工夫。”參見蔡元培:《十五年來我國大學教育之進步》,載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五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12頁。這導致了學生的不用功,“只是用現成的講義,按部就班地去教學生。學生得了講義,心滿意足,安有進步?”參見蔡元培:《〈法政學報〉周年紀念會演說詞》,載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四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27頁。以至于“學生于講堂上領受講義,及當學期、學年考試時要求題目范圍特別預備外,對于學術,并沒有何等興會。”參見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經驗》,載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八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10頁。因此,蔡元培在就職演說中就說要“改良講義”,“諸君既研究高深學問,自與中學、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員講授,尤賴一己潛修。以后所印講義,只列綱要,細微末節,以及靜旨奧義,或講師口授,或自行參考,以期學有心得,能裨實用。”參見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載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三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頁。關于此措施的具體實施情況,可參見楊瑞:《通往學術之路:蔡元培與北大法科的學術化進程(1916-1927)》,四川大學2006年碩士學位論文,第43-46頁。它風行一時的直接原因卻是:
何以民國17至19年(1928至1930年)以前,法學講義總是北大與朝大領先?這問題的答案是當年北京是國之首都,而民刑事法令與法院審判依據的法理,皆是清末改制的法律案傳承下來的。清朝設立修訂法律館,修訂民刑律及民刑訴訟法,大抵聘日本法學家協助起草。如刑律即是岡田朝太郎,民律即是松岡義正,商法即是志田鉀太郎等主編。辛亥革命,民國肇建。暫行新刑律是以岡田博士主編的刑律草案為底本。民律草案未得公布實施,民事審判以修訂法律館訂定的《現行刑律民事有效部分》為依據而參考松岡博士的民律草案,名之曰《法理》。”“于是北大及朝大的法學課程,刑法及民法為其主課,刑法教授張孝移先生原是協助岡田朝太郎起草刑律的刑法學者。民法教授余棨昌先生就是大理院的民事庭長,后來升任大理院長。各級法院民事審判固然依據《現行刑律民事有效部分》,實際上仍以大理院民事判例為準則。棨昌先生講授民法,自當居于權威地位。張孝移先生講授刑法,不發講義。學生們記下筆記。在北大法律學系里,林佛性同學的刑法筆記后來編輯成書。林先生亦以助教講授刑法,并升為教授。由此可見,朝陽大學的法學講義,自有其權威。其通行全國各省區法政學校,為課本或主要參考,甚至輾轉傳抄,是事理所當然與必至的了。〔37〕黃懷周:《〈法律評論〉紀念朝陽大學創立70周年和〈法律評論〉創刊60周年專刊簡介》,載薛君度、熊先覺、徐葵主編:《法學搖籃朝陽大學》,東方出版社2001年增訂版,第60、61頁。
可以看出,朝陽大學講義風聞一時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力于撰寫講義的教授是實務部門的領軍人物。揆諸歷史,以今之視昔,這種講義教科書中有多少學術含量,值得思量!
應該說,有兩個因素限制了朝陽大學的法學研究,一是其任教者多以留學日本的學生為主,留日學生帶有很大的速成成分。朝陽大學從成立時主導其事的汪有齡到后來的董事長居正,還有很多任教的老師,都是留日學生,帶有濃厚的“東洋化”色彩。〔38〕參見王健:《中國近代的法律教育》,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49-251頁。留日學生無論是留學的心態意向還是所選學校,都有很大的實務傾向。“在學術上,留學歐美的學者大量學成歸國,在政府與歐美關系日漸加強的時代背景下,他們在政學兩界逐步取代了留日學者的地位,這一潮流的更迭體現在法學界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朝陽大學在法學界的地位開始走向衰弱”。〔39〕楊昂:《學風、世變與民國法學:朝陽大學研究(1912~1946)》,中國人民大學2005年博士學位論文,第72頁。二是師資方面雖然其時在朝陽任教的教授大多為名流,但“朝陽大學無論是在抗日戰爭中的四川還是在北京,都是巧妙地利用北平(京)高校集中的優勢,聘請兼職教授,或婉商的辦法,聘請著名教授講課,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的法科教授和燕京大學的一些教授,均是朝陽大學的教授。即使設有專職,也是極少數”。〔40〕韓培基:《回憶朝陽大學的辦學精神和教學特色》,載薛君度、熊先覺、徐葵主編:《法學搖籃朝陽大學》,東方出版社2001年增訂版,第69頁。其教員多為兼職教授,這些人往往以授課為主,對于學校的義務也僅止于此。
通觀朝陽大學的教師、期刊和講義,以及主政者的辦刊辦學理念,可以看出朝陽是一所以實務為導向的法科學校,而“無朝不成院”的氛圍形成之后,已成的優勢只會漸次的加重這種傾向。正如有人回憶的:“我校與法理一項,固屬研究無疑,而法典條文之嫻熟,闡明之準確,尤為他校望塵莫及。使執同學于途,詰以某事實,及其應適用何種法文,率皆前后貫通,應對如流,故我校以法律之實用見稱,良有以也。”〔41〕趙金亭:《離別感言》,載《朝大校刊》(校慶特刊)1935年6月10日;轉引自楊昂:《學風、世變與民國法學:朝陽大學研究(1912~1946)》,中國人民大學2005年博士學位論文,第100頁。寥寥幾句,道出了朝陽的實用風格。在這種實務導向的教學風格之下,朝陽大學很難談得上有法學研究。
東吳大學法學院是東吳大學的政治學教師、也是一位律師蘭金(Charles Rankin)1915年“心血來潮”在上海創辦的,他認為這是“為新生的共和國作出出色貢獻的絕好時機”。〔42〕[美]康雅信:《培養中國的近代法律家:東吳大學法學院》,王健譯、賀衛方校,載賀衛方編:《中國法律教育之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52頁。蘭金的計劃得到了曾任美國駐華法院法官羅炳吉(Charles S. Lobingier)的熱情響應。羅氏是比較法和羅馬法專家,到中國后,他就“關注建立法學院的可能性”,并認為“應當首先將外國法律制度教授給中國年輕人,讓他們將來從中選取素材建立他們新的法律體系”,他為其新探索設計了一種內容廣泛的比較法課程,并提議將“The Comparative Law School of China”作為法學院的名稱。在1919年的一份課程表上看,“法學院的目標就是要使學生充分掌握世界主要法律體系的基本原理,以培養可以為中國法學的創新和進步做出貢獻的學生為宗旨”。〔43〕[美]康雅信:《中國比較法學院》,張嵐譯、賀衛方校,載高道蘊、高鴻鈞、賀衛方編:《美國學者論中國法律傳統》,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586頁。這一時代中國沒有自己的法典,民族國家建構的問題擺在面前,學習西方相關國家的法律也就成了應急之策,于是,東吳法學院提出的對策就是講授比較法。但是,無論法學院如何宣稱,事實上它早期的課程中幾乎沒有任何真正的比較法學習。正如一位20年代的畢業生所說,“很明顯學院被認為是一所比較法學學院并不為別的,只是因為它同時教授中國法和英美法。事實上我們只是學習不同的法律本身,而從未更進一步(指進行認真的比較法學習)”。〔44〕[美]康雅信:《中國比較法學院》,張嵐譯、賀衛方校,第587、589、591頁。
由此可以看出,甫經成立的東吳法學院主要是進行英美法的學習,在交通中西方面尚未成長成熟。據康雅信教授的研究,1927年至1939年這段時間,東吳法學院“才建立了它真正意義上的比較法教學”,“在所有方面實現了真正的比較法教學,包括開設的課程、教學方法,以及通過其研究生課程和刊物進行的學術研究”。〔45〕[美]康雅信:《中國比較法學院》,張嵐譯、賀衛方校,第593-594、616頁。
20世紀最初十年期間,由于清政府的推動和現實利益考量,法政學校遍地開花。到1916年時,法政學校與學生的數目都遠高于同期其他科類的學生數目。據民國初年的調查,許多私立法政學校“完全是營業性質,教員資格不夠,常時缺席,敷衍教學,學生程度很差,來去無常,學額任意填報。”無論是清廷直接開辦的還是地方開辦的,無論是綜合大學里的法科還是法政專門學校,在1920年之前,要么因須聘外國人講授而缺少中國的研究者,要么因為實務導向法政學科始終不脫工具窠臼,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充斥現代理念的學術研究機關,其根本不具有現代法學生長所需的土壤,都不可能孕育出現代意義上的法學。它們不過是在強國御侮的形式下奉行實用主義的工具性托付,這種工具性托付一是由于外敵侵犯,期望反抗列強;二是由于內部的帝制,期望改變無能的政治,在最短期內改變積貧積弱的狀況。如此,哪里會有什么長遠的打算在內,哪里會有法學可言!〔46〕關于清末到北洋時期一個法學發展的概括,參見王泰升:《四個世代形塑而成的戰后臺灣法學》,載臺灣法學會臺灣法學史編輯委員會編:《戰后臺灣法學史》(上冊),元照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貳部分。
二、現代法學的要件:研究機關與研究學人
以上梳理了近代中國20世紀20年代之前的法律教育狀況。當下研治中國法學史的學者,往往會不經意地把法律的講授算作法學發展的一個步驟,并把中國現代法學的開端追溯至同文館“萬國公法”的講授,實則并非如此。雖然法律教育對于現代法學的誕生居功不小,是中國近代法學萌芽和誕生的基礎之一,〔47〕何勤華:《中國近代法律教育與中國近代法學》,載《法學》2003年第12期。但是法律教育并不等于法學研究。法律教育可以是一種職業教育,現代法律是舶來品,只要有能講授法律的人,無論是外國人還是留學歸來知曉大概卻并無精深研究之人,大體都能開班授徒;但是這些教員并無研究法學的意識和能力,他們不過是在傳授一種技能罷了。現代法學作為一種學問,必然不會產生于培養外交、行政人才的清末法律學堂中,也不會產生于職業性的法律學校中,它只能誕生在一個現代的大學或研究機關里;〔48〕胡適在《非留學篇》中曾說,“蓋國內大學,乃一國教育學問之中心,無大學,則一國之學問無所折衷、無所歸宿、無所附麗、無所繼長增高。”關于大學對中國現代學術發展中的重要性,參見左玉河:《中國近代學術體制之創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6-230頁。且“中國現代法學”的出現,不可能依靠外籍教員的力量,只能倚靠中國學者自己的研究。所以從學術史的意義上來說,中國的現代學術,必須奠基于兩個條件之上:(1)現代學術研究機關的存在;(2)中國致力于學術并以此為志業的研究學人的存在。法學亦是如此。
(一)研究機關
北京大學是中國現代史上第一所真正意義的大學,這已屬定論。1898年京師大學堂正式開學,在其預備科和附設的帶有官員速成培訓性質的仕學館、進士館中,便有大量的法律課程;由京師大學堂監督的譯學館,也開設有法律類課程。〔49〕參見李貴連等編:《百年法學——北京大學法學院院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33頁。1909年3月,京師大學堂法政科大學在馬神廟京師大學堂舊址開學,法律學門第一屆12名學生。〔50〕李貴連等編:《百年法學——北京大學法學院院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頁。《北京大學校史》中說“1910年3月30日,分科大學舉行開學典禮”。參見蕭超然等編著:《北京大學校史(1898-1949)》(增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頁。北大檔案館工作人員李向群在“京師大學堂分科大學舊址歷史”中所述,“大學堂分科大學開學典禮于1910年3月31日在馬神廟公主府舊址舉行”,文載《北京大學校報》第1116期,2007年3月20日第4版。似“1910年3月31日”最為可信。課程中有《法律原理學》《大清律例要義》《中國歷代刑律考》《中國古今歷代法制考》《東西各國法制比較》《各國憲法》《各國民法及民事訴訟法》《各國刑法及刑事訴訟法》《各國商法》《交涉法》《泰西各國法》等,并具體規定了各科目的講習辦法及教材的編訂,形成了較為系統的知識傳授。〔51〕李貴連等編:《百年法學——北京大學法學院院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42、43頁。后法政科改為法科,下設法律學門、政治學門和經濟學門。不論哪個階段的法律教育,仍然以培養行政人才和外交人才為目標,其實務傾向加上這種發蒙階段的初練,仍然談不上學術研究層次的法學。民國六年(1917)之前,要么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要么是販賣西學西風壓倒東風,但是都沒有注意到研究。〔52〕參見蔡元培:《北京大學成立第二十五年紀念會開會詞》,載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四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33、834頁。
1917年蔡元培先生就任北京大學校長,在就職演說中特別提及法科:“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敗,以求學于此者,皆有做官發財思想。故畢業預科者,多入法科,……蓋以法科為干祿之終南捷徑也。因做官心熱,對于教員,則不問其學問之淺深,惟問其官階之大小。官階大者,特別歡迎,蓋為將來畢業有人提攜也。現在我國精于政法者,多入政界,專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請教員,不得不聘請兼職之人,亦屬不得已之舉。”蔡元培認為“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53〕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載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三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頁。要求學生抱定“為求學而來”的宗旨,“入法科者,非為做官”。在掌校后,進行了一系列大刀闊斧的改革,廣納人才兼容并包,實行教授治校,提倡研究設立研究所增加參考書,設立各種學會砥礪學生的品性和人格,一匡時弊,風氣為之一變,才使得北大成為了一個現代的大學、現代的學術研究機關。〔54〕關于蔡元培的改革綜述,參見陶英惠:《蔡元培與北京大學(1917-1923)》,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6年第5期,第275頁以下。
之前的法政教育,“大抵都是用一種官僚教育、職業教育。他們的旨趣,就是要學生不請假、把講義背得熟、分數考得好,畢業后可以謀生便罷了”。〔55〕蔡元培:《〈法政學報〉周年紀念會演說詞》,載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四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27頁。那時候的北大也是如此,“各科以法科為較完備,學生人數亦最多”,〔56〕蔡元培:《大學改制之事實及理由》,載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三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57頁。但是風氣最差,大多數人“仍抱科舉時代思想,以大學為取得官吏資格之機關。故對于教員之專任者,不甚歡迎。其稍稍認真者,且反對之。獨于行政、司法界官吏之兼任者,雖時時請假,年年發舊講義,而學生特別歡迎之,以為有此師生關系,可為畢業后奧援也”。〔57〕蔡元培:《傳略(上)》,載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三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70頁。實際上這是清末京師大學堂“老爺”式學生傳統的延續,這種科舉時代的門生觀念和升官發財的陋習,并未因共和制的政治改變而洗盡,還傳染文科理科甚重。〔58〕參見蔡元培:《讀周春岳君〈大學改制之商榷〉》,載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三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91頁。
蔡元培的初衷,是保留“學”的科目,把北大辦成文、理科的大學,其他的“術”科如法科、商科調出北大,成立專門學校,但是因遭反對未能成立。其后,在他的辦學理念統籌下,北大評議會通過《研究所通則》《研究所辦法草案》,規定設立了法科須設研究所,包括法律學、政治學和經濟學三個研究所,其中法律學門的研究方法是各國法律比較學說異同評、名著研究、譯名審定等。〔59〕李貴連等編:《百年法學——北京大學法學院院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55頁。1917年12月,王建祖致蔡元培的信中說,法科各研究所“可告成立”,開設的科目中有“比較法律”,擔任之教員是王寵惠。后來“王君寵惠擔任之比較法律,前月即已開始研究,每星期由研究員分班前往就學”。〔60〕高平叔:《蔡元培年譜長編》(中冊),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5、66頁。王寵惠為耶魯大學法學博士,后又游歷歐洲諸國,是真正具有比較法視野的大家。后來蔡元培回憶:
北大舊日的法科本最離奇,因本國尚無成文之公私法,乃講外國法,分為三組:一曰德日法,習德文、日文的聽講;二曰英國法,習英文的聽講;三曰法國法,習法文的聽講。我深不以為然,主張授比較法。而那時教員中,能授比較法的,只有王亮疇、羅鈞任二君。二君均服務司法部,只能任講師,不能任教授,所以通盤改革,甚為不易。直到王雪艇、周鯁生諸君來任教授后,始組成正式的法科,而學生亦漸去獵官的陋習,引起求學的興會。〔61〕王世儒編撰:《蔡元培先生年譜》(上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83頁。
蔡先生的這段回憶,常常被人引用,但是沒有人把它當做一段很重要的學術史資料。實際上正是這段話,框定了現代法學在中國誕生的大體時間。正是蔡元培一系列的改革,才使北大成為一個現代的大學、現代的學術研究機關。受西方特別是德國教育理念熏染的蔡元培,把北大提高到一種學術研究的高度,開始脫離傳統上登科取仕工具的趣味,對于研究者、學習者來說大學不再單單是一種工具,而更高一層的,還是一種目的,作為一種學術研究的載體。〔62〕關于蔡元培所受德國大學觀影響的研究,參見陳洪捷:《德國古典大學觀及其對中國的影響》,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132頁;金耀基:《蔡元培先生象征的學術世界》,載氏著:《大學之理念》,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增訂版。那么其時的北大為學術研究提供了什么樣的背景呢?概而言之,可以說是以研究為主導的學術獨立自由氛圍、學人間交流的環境。前者是蔡元培通過大力改革、聘請新人專任學者、設立研究所實現的;后者則立基于廢止原來的文、理、法三科和學長,改設為五組十七學系和系主任,法律學與經濟學、政治學、史學為第五組。這樣是為了能夠科際溝通,以打破各自的界限。〔63〕陶英惠:《蔡元培與北京大學(1917-1923)》,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6年第5期,第294、295頁。也可參見楊瑞:《通往學術之路:蔡元培與北大法科的學術化進程(1916-1927)》,四川大學2006年碩士學位論文。
近世早已不是上古時代那種學科貧乏的年代,社會分工越來越細使得學者們逐漸無力靠個體的力量來從事學術研究,特別是20世紀這種風氣越來越盛,這種集合成一個研究社群的好處在以往的學術研究中早已得到證明,研究機構成員運用的是一套話語系統,他們之間定期、不定期的交流會激蕩思想的火花,“思想與思想的接觸往往明顯地刺激了觀察與創造性。沒有相互接觸,觀念和經驗將仍然保留為嚴格地屬于個人;可是,通過互動的媒介,觀念和經驗就可以變成創新和發現的要素”。〔64〕[美]羅伯特?金?默頓:《十七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與社會》,范岱年等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271頁。
作為當時改革最成熟成果的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就顯示出了這一學者、學科間溝通的成功,“這一制度化的學術研究機構,通過所內各式各樣的集會以及期刊的發行,為學者提供了會面及紙上交流的機會,顯然是促進學術成長的一個關鍵的、極為重要的因素”。〔65〕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前言4頁。關于學術期刊在近代學術建制中的作用,參見左玉河:《中國近代學術體制之創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七章。蔡元培北大改革的效果很快明晰的顯現出來,其影響是全國性的,呂思勉在談出版問題時曾說:“在他主持北京大學以前,全國的出版界,幾乎沒有什么說得上研究兩個字的。不是膚淺的政論,就是學校教本,或者很淺邊的參考用書。當這時代,稍談高深學術,或提倡專門研究,就會被笑為不合時宜……還記得在民國八九年之間,北京大學的幾種雜志一出,若干種的書籍一經印行,而全國的風氣,為之幡然一變。從此以后,研究學術的人,才漸有開口的余地。專門的高深的研究,才不為眾所譏評,而反為其所稱道。后生小子,也知道專講膚淺的記誦,混飯吃的技術,不足以語于學術,而慨然有志于上進也。”〔66〕呂思勉:《蔡孑民論》,載《宇宙風》1940年第24期;轉引自左玉河:《中國近代學術體制之創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53頁。正是在這種理念的指導和涵養之下,法律學系延攬了一大批有學識的專任師資,包括王世杰、周鯁生、燕樹棠等,他們不是官吏,不是律師,而是受過正經西方學術訓練的職業學人。他們以教書研究為職業,也以教書研究為志業。
這批人開展學術研究,之間的討論交流和合作十分頻繁;還在北大指導學生進行翻譯,間接地進行學理研究。他們創辦了《國立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季刊》,發表北大同仁的社會科學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他們還有其他社會科學的教授如黃右昌、顧孟馀、陶孟和、高一涵、皮宗石等形成了一個“研究問題、輸入學理”的學術社群或共同體。這一切,都是這個地理上與北大文、理科并行的第三院,給現代法學在中國的誕生提供了土壤。
(二)研究學人
現代學術在中國的生根發芽,不能靠聘請的洋教習,也不能靠出國買一張文憑回國混跡政學兩界的半通不通者,更不能靠以教學為中轉站卻懷揣升官發財之夢時刻準備進入政界的人;它必須靠的是本國的、以學術為志業的學者。鑒于現代法學是一種西方的舶來品,所以這種法學學者是由留學產生的,他們在國外扎扎實實接受現代學術訓練,回國后把教書研究作為職業、志業,期望媒介中西調和法理,形成中國文明的法學。〔67〕留學生在中國現代法學發展中的作用,參見何勤華:《法科留學生與中國近代法學》,載《法學論壇》2004年第6期;對于留學生在“學院化法學”建置過程中的作用,參見裴艷:《留學生與中國法學》,南開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三章。一個區域性的研究,參見袁哲:《法學留學生與近代上海(清末—1937)》,復旦大學2011年博士學位論文。
清末的強國御侮之道,分為兩途,一是國內的自強,以洋務運動為樣本的購買新式武器和聘請洋人幫忙的方式,另一方面是派遣留學生出國學習,期待他們學成回國對國家有所助益。老大中國從傳統社會走上現代化之路,有賴留學生這一群體的愛國激情和智識努力。〔68〕關于留學生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貢獻,參見舒新城:《近代中國留學史》,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138-140頁。留學運動始于向西方學習的20世紀下半葉,有論者把清末這場浩浩蕩蕩的法科留學運動分為兩個階段,即1874年到1895年的初始無意識的零敲碎打階段,1895年到1911年的有計劃有安排的蓬勃發展階段。前一階段是無計劃的派遣,后面一階段中央提倡、地方響應,滾滾成洪流之勢。〔69〕裴艷:《留學生與中國法學》,南開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70頁。就現存資料來看,首先出洋留學修習法科的人是伍廷芳,時為1874年。其后有自費的個人或小規模的政府派遣,目標國家主要集中于歐洲的英法。〔70〕參見裴艷:《留學生與中國法學》,南開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70-73頁。甲午之后,國內留學之風從之前的趨向英美轉向趨向東鄰,原因是多方面的。除距國較近、路近省費、語言近于中文這些技術方面的原因,日本通過明治維新迅速躋身強國之列,這一系列為國人刮目的舉動所產生的范例效應,可能是最主要的因素。東渡日本習法政的人數增長并未換來成正比例的后果,歸國之后,這些留日學生絕大多投身政治,并未帶動中國法學的發展。〔71〕其實,那時日本也是一個剛步入現代化的國家,其學術原創性少。胡適當時說:“中國人在日本留過學的,先后何止十萬人,但大多數是為得文憑去的,就是那最好的少數人,至多也不過想借徑日本去求到西洋的文化。”(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3》,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46頁)雖然胡適說這話帶著歐美留學生輕視留日學生的心理,但也是有很大的道理。這在一定程度上還是與中國的傳統觀念相關,法政學僅為一“術”,不足以言學問,且傳統上讀書便是為了取仕做官。沒有一個理念上的轉變和制度上的支撐,單憑個人之力無法移山。所以回國后他們要么把大學當做晉升的中轉站,要么當做賺外快的兼職。時掌北大的胡仁源校長總結教員如流水來去不已的原因,其中一條便是“社會心理大都趨重于官吏一途,為教員者多僅以此為進身之階梯,故鮮能久于其任”。〔72〕蕭超然等:《北京大學校史(1898—1949)》,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36頁。
習法政學科之人大多是抱著回國實用的目的,上者懷報效祖國拯救政治之愿,下者無非看作升官發財之階梯。這種整體心態帶來的一個結果便是去日本留學者入大學者頗少,入速成科者尤多。入大學本身較難,另外他們對于自身所要學習的也頗有一些清醒,知曉無須進入研究的地步。加上時局混亂,結果是種種亂象橫生,社會評價度也很低,蔡元培回憶說:“那時候到日本學法政的很多,有大部分是入私立學校或入速成科,并不認真求學,甚有絕不到學校,也不讀書,在日本過了多少時候,就買一張文憑回國了。”〔73〕蔡元培:《〈法政學報〉周年紀念會演說詞》,載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四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25頁。之所以出現這種狀況,大半因為日本國立名校能夠接納留學生人數較少,大多數留學者入私立學校或速成科,總體質量當然差勁。〔74〕參見舒新城:《近代中國留學史》,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六章。光緒三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1908年1月3日)《學部奏日本官立高等學堂收容中國學生名額及各省按年分認經費章程折》中說:“然比年以來,臣等詳查在日本游學人數雖已逾萬,而習速成者居百分之六十,習普通者居百分之三十,中途退學輾轉無成者居百分之五六,入高等及高等專門者居百分之三四,入大學者僅百分之一而已。”〔75〕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編纂、曾爾恕等點校:《大清新法令(1901-1911)點校本》(第七卷),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386頁,當然,清末民初的留日學生,回國后許多人對國家貢獻多有,并非個個不成氣候。〔76〕參見程燎原:《清末法政人的世界》,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2、63頁。留日學生對于中國的近代政治、法制現代化和法律教育做出了很大的貢獻,〔77〕關于留日學生在政治及教育中的貢獻,可參見尚小明:《留日學生與清末新政》,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關于留學生在法制現代化中所起的作用,參見郝鐵川:《中國近代法學留學生與法制近代化》,載《法學研究》1997年第6期。但是對于中國法學貢獻甚微。
隨后,清政府對留日習速成科采取了限制政策,之后特別是民國建立以后留學歐美的人漸次增多起來。民國初年,去向歐美留學的人員增多起來,庚款、稽勛局等委派輸出大量人才。歸國后的留歐美學生和留日學生也儼然兩個集團,前者大多看不起后者,認為他們是從“二道販子”那里學到的知識。蔡樞衡感覺到留日習法者作風的共同特色是“注釋或解釋條文中心主義”,“德、法的法學著作常比日本的法學著作質高品優”;〔78〕蔡樞衡:《中國法學及法學教育》,載許章潤主編:《清華法學》(第四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9、10頁。無論是以其時經歷此過程者的描述,還是百年之后再回顧,持之平允地說,歐美留學生確實整體上比留日學生水準要高。〔79〕與留日學生相比,“歐美的法科生明顯學養深厚,他們大多進入正規的法律學院肄習,學有所成。”一個證明性的例子是,1906年,學部舉行第一屆回國游學畢業生考試,考取最優等的四名法科生都是歐美生。裴艷:《留學生與中國法學》,南開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78頁。即使在社會層面,按工資的標準,留日學生也是淪為二等,參見袁哲:《法學留學生與近代上海(清末—1937)》,復旦大學2011年博士學位論文。這恐怕還是與留學意向有關,留日者大多數為了學習法政常識取得功名以回國投身政治;而留學歐美者則是處身于西方的現代大學中,受西式大學理念的熏陶漸染,回國前概已形成“以學術為業”的理念,回國后自然傾向于進入大學做研究一途。蔡元培改革北大,并裁減官員型教員和兼任教員,增加專任教員的數量,〔80〕楊瑞:《通往學術之路:蔡元培與北大法科的學術化進程(1916-1927)》,四川大學2006年碩士學位論文。亦為這些想把學術作為一種職業的留學生提供了職位。但是,我們不能說留日歸來的法科教授沒有為中國法學的誕生做出過貢獻,只是他們的貢獻要等到蔡元培的北大改革、等到留學歐美的人回來導致風氣為之一變之后,他們才被納入到中國現代法學誕生與發展的合流中,積小流以成江海,共同作用漸次成型。
清末民初是中西沖突下建構民族國家的時代、文化交融的時代,也是西化很風行的時代,在這幾十年的時間里,有大批留學德、法、美、英、日的青年人回國,帶回西式的理念和信仰,帶回現代學術的種子,他們影響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這些留學生回國后成為中國現代法學的中流砥柱。他們對于中國現代法學的誕生與成長,意義重大。“他們在中國各法律院校任教,傳播法律知識,翻譯法學著作、教材、論文,創辦法學刊物等方面均發揮著主力軍的作用”。〔81〕何勤華:《中國法學史》(第三卷),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121頁。到了20世紀40年代,據教育部統計,全國大學教授與副教授,法科有339人,其中留學海外的300人,占88.5%;參見該書121頁。由于在西方時受到熏染,認識到大學教授承載著人類文明和民族文化傳承之重任,雖是一種職業卻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翰林,不以做官為目標。加之國內新式學校的出現,為他們提供了既能糊口又能張揚夢想的場所。改制后的北大作為擁有法學研究機關的最高學府,為這些法科留學生提供了研究的環境,提供了一展身手的空間,在吸納了一批留學生為教授后,開啟了中國現代法學的發展征程。〔82〕許章潤教授把近世中國的法學家分為五代,其中清末民初的沈家本、伍廷芳、梁啟超、王寵惠等諸公為第一代,王世杰、錢端升、吳經熊、程樹德等人為第二代;第一代法學家亦中亦西,且多涉身政治;1920年代初期第二代“接受了現代西式法律教育的法律從業者逐漸上場,面對新問題,秉持新理念,嘗試新范式,整個法學面貌為之一變,真正純粹法學意義上的中國學術傳統,濫觴于此,為第二代。”許章潤:《書生事業 無限江山——關于近世中國五代法學家及其志業的一個學術史研究》,載許章潤主編:《清華法學》(第四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42頁。至20世紀20年代左右,經歷清末民初近四五十年的史前準備,實現由“法學在中國”到“中國的法學”之轉換,既因征程勞力,也是水到渠成。如果按照費正清劍橋學派“挑戰—回應”模式分析中國近代史的話,那么中國是在西方列強的逼迫下不得不反抗,不得不下水,去參與國家間競技的世界游戲。這毀了中國,使得傳統凋零不已;也成就了中國,使其在涅盤中獲得重生。暫且不置價值性評估,我們可以看到,法學作為一門舶來的科學,不同于“博稽中外”、“參酌各國法律”的立法活動,也不同于“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同文館、法政學堂講授,還不同于民國時期以習“術”為目的的專門法律學院的照本宣科。它是現代意義上的法律學,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律學或律學解釋學,而是用現代科學方法研究法律產生運行的一門學問,它至少、應該要達到一種研究的水平。改革后北京大學為現代法學提供了一個機構的預備,留學歸來、具有扎實學問的學者為現代法學提供了智識基礎。如果說法學在中國落地生根的話,至少是這兩者齊備之后的事。確切地說,是王寵惠在北大法律研究所指導研究、甚至“王雪艇、周鯁生諸君來任教授后,始組成正式的法科”之后的事,那時才可作為現代法學的開端之時。研究者多把中國現代法學溯至同文館或京師大學堂甫成立之際,“這種事后追認先驅的事例,仿佛野孩子認父母,暴發戶造家譜,或封建皇朝的大官僚誥贈三代祖宗”,〔83〕錢鐘書:《中國詩與中國畫》,載氏著:《七綴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3頁。實在是對學術史“考鏡源流”無甚裨益。因此,按照上述兩項必要條件,即研究學者和學術機關,1917年改革后的北大,其法科研究才算中國現代法學的開端,1920年代左右現代法學在中國方始誕生,這之前的法律學研究都不能算作現代意義上的法學學術。〔84〕王泰升教授在《四個世代形塑而成的戰后臺灣法學》中說:“許多在歐美或在中國接受西式法政教育者,例如,張君勱、王世杰、錢端升、吳經熊、楊鴻烈等,于1910年代后期、1920年代,已漸次在當時中國的法政論壇上嶄露頭角,并使得中國法學面貌為之一變,故具有純粹學術意義的中國的新式/西式法學,可謂系濫觴于此。”(載臺灣法學會臺灣法學史編輯委員會編:《戰后臺灣法學史》(上冊),元照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16頁。)此論斷與本文在結論上是一致的,但缺乏詳明的論證。
三、結論
研治中國法學史,對于中國現代法學的誕生須給予一個大體明晰的時間界定。對于法學乃至任何學術而言,法律教育自有其重要性但也并非必不可少,它只是積幾十年之功給法學的誕生和發展提供了一個氛圍和推動力。現代法學的誕生,不得不注意的兩點,應該是研究學人和研究機關。恰如日本法史學家滋賀秀三氏認為:“某種科學要在學術界確立地位,為世人所承認,必須在大學里正規地系統地講課。”〔85〕[日]滋賀秀三:《日本對中國法制史研究的歷史和現狀》,呂文忠譯,載《法律史論叢》(第3輯),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296頁;轉引自陳新宇:《外在機緣與內在理路——當代日本的中國法制史研究》,載《政法論叢》2013年第3期。可見大學在現代學問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現代學科必須以大學為依托。中國現代法學,需要以學術為業的中國學人,篳路藍縷孜孜不倦,白手起家而漸有所成;中國現代法學,需要有一個提供給學人的研究環境,這個環境在20世紀的世界格局中只能是以研究而非技能傳授為格調的現代大學或研究機關,〔86〕中國現代的學術研究機關,除卻理學、工學的,文科類的大多存在于綜合研究機關內,主要的有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平研院沒有法學的研究,中研院的法學研究開展是在20世紀20年代末期,參見劉猛:《法律科學的中國命運,1912~1949——以中央研究院為中心的考察》,載許章潤、翟志勇主編:《歷史法學》(第六卷),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這個自主的機關通過學術氛圍給個體的學人間提供了一個交流和合作的機會。縱然,法學并非簡單的由這兩個因素構成,還有作為載體的著述、雜志、教育等進行宣傳和代際傳授,但其中起決定作用的則為研究機關和研究學人,其他因素不過為法學的發展錦上添花而已。以此標準,中國現代法學經過幾十年的醞釀,在1920年代左右的北京大學誕生,并延續下來。〔87〕劉夢溪先生認為,中國現代學術發端的時間,應為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標志是承認學術具有獨立之價值,并在研究中開始吸收西方現代的觀念和方法。(劉夢溪:《學術獨立與中國現代學術傳統》,收見氏著:《傳統的誤讀》,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8頁。)很明顯,法學要晚于現代文史之學學術的產生時間。此與時人論述,大體契合。1919年陳啟修評論說:清末維新,泰西法律思想,始漸輸入,迄今二三十年,法校林立,法案山集,號稱明律之士,遍地皆是。然入其肆,則除翻譯書外,國人自著之名作無有也。叩其人,則法學專家無有也。欲從各種法律草案,窺中國法學之程度,則草案皆屬翻譯,不足為憑。欲從實際法律家考之,則法官及律師,大抵為新官僚及高等流氓,不足與談。故居今日,欲審中國法學之程度,幾有末由之憂。〔88〕陳啟修:《護法及弄法之法理學的意義》,載《北京大學月刊》(第一卷第二號),1919年2月,第22、23頁。
縱觀近代法學發展史,我們不禁要問,何以在近代史上早就有幾十年的法科教育,法學卻產生如此之晚?其實,法科學校集眾效應,在短期內就能取得成功,非無由也。就拿朝陽學院來說,往往借助有實力的官員的力量,比如讓任司法院院長的居正來做董事長就是極顯明的例子。民國時期,現代中國初開,專業分工不甚明朗,學人游蕩于政學之間的情況極為普遍,官員退職后擠入大學也在在多有,這種情形在法律、政治學系則尤為普遍,因為法律、政治者,和實踐密切相關。對此,曾有人諷刺說:“這幾個私立大學,除教會辦的以外,沒有像樣的。也有名教授,也有好學生,幾個學校又都自吹是辛亥革命后老革命黨人辦起來的,叫做什么‘中國’、‘民國’、‘朝陽’、‘平民’、‘華北’、‘郁文’等等,名字好聽得很,可是事實究竟怎么樣?事實勝于雄辯。東城的朝陽大學法律系出了幾個法官、律師,就有點名氣。其實誰都知道,那不是靠上課,是靠關系,是靠名流校長不單掛名。”〔89〕金克木:《難忘的影子》,載《金克木集》(第一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版,第756頁。他在文末“評曰”:《難忘的影子》寫的是大學生,都是過去的人和事。現在人,尤其是青年,恐怕有點不大相信是真的了,所以叫做小說很合適。這幾十年的一統天下,容易使人忘了過去,中國的過去和世界的過去。參見《金克木集》(第一卷),第854頁。但是在那時,這種官吏兼任教員的行為頗獲學生的贊許,于是學校也便為了后續招生迎合學生,使這種狀況成為常態。“惟官僚、政客未必有學問,則以自身從政經驗而充任法政科大學教職,往往成為在野官員的首選。而法政大學,為藉官員名聲以揚本校盛譽,憑政客關系,為本校學生拓寬求職面,也不免假借官僚聲名與關系網絡”。〔90〕楊昂:《學風、世變與民國法學:朝陽大學研究(1912~1946)》,中國人民大學2005年博士學位論文,第36頁。法學在傳入中國之初,不過扮演了傳統律學的功能性角色而已,這種長久形成的氛圍沒有新風氣的沖擊是不會改變的。其實,聘請有能力的實務官員進行講授,對于職業教育來說本無可厚非。法學在眾多的學科門類中,并非基礎科學,英美法系所說的法學是一項技能,并把其放在職業性的律師學院中教授并非沒有道理。對于一般學生來說,修習法律的目的在于學會一項技能,他們對于理論的研究既沒有興趣也沒有能力去關注。只有到這種研究具有實地用途時,他們才產生興趣,而這種高深的研究往往只有遇到“疑難案件”時才可能派上用場,但是實務中能有多少疑難案件呢。因此,法學終究是少數人的事兒。寓身于20世紀上半葉國家建構進程中的法律學,現實需要遠大于學術研究需要,而法學之不彰、法律(立法)超越法學研究,可能就沒有什么好奇怪的了!
(責任編輯:肖崇俊)
* 劉猛,清華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本文初稿承陳新宇老師閱后給予建議,謹致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