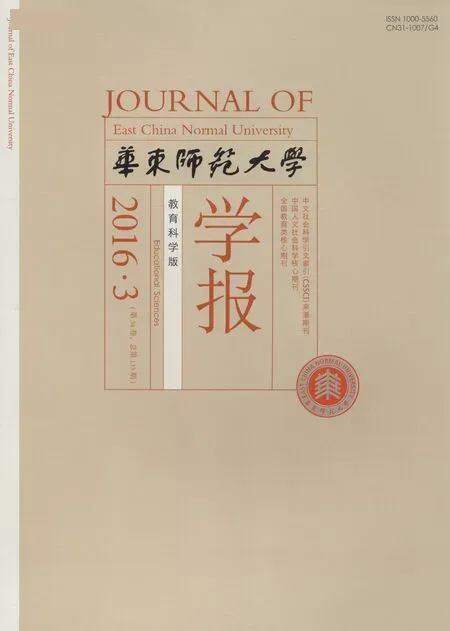英國世界一流大學發展漫談
張 紅 霞
(南京大學教育研究院,南京 210093)
英國世界一流大學發展漫談
張 紅 霞
(南京大學教育研究院,南京 210093)
世界一流大學的根在英國。各色排行榜中穩居前十的最古老的大學非牛津劍橋莫屬;穩居前十的大學的人均占有量也是英國首屈一指;人均諾貝爾獎獲得者人數英國第一;大學排名位置明顯超過世界經濟體排名位置的更是英國。對這些現象進行探討或許對眼下我國世界一流大學建設有所啟迪。
第一,與其說一流大學是先進文化的搖籃,倒不如說是先進文化的自然結晶,這在一流大學形成的早期更加明顯。牛津劍橋孕育于中世紀的神學院,脫胎于翻天覆地的文藝復興,成長于如火如荼的工業革命。從文化上講,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最大的社會功能在于讓普通百姓相信,上帝不再救贖懶漢,上帝的救贖甚至可以量化:一個人創造出的財富的多少,就是上帝對其認可、嘉獎的多少。上帝稱頌那些通過發明創造帶給人類安逸的聰明才智。于是乎,新教的信念和工業化的需求發生契合,進而帶來商品繁榮和市場規則,也帶來了思想的解放和認識、改造自然界的行動。發現“波義耳定律”的著名物理學家、化學家波義耳說,“關于上帝的杰作的‘知識’是同我們贊賞它們的程度成正比的”。而且,“除了信仰的行動,還應該用理性的行動去贊頌和承認上帝,我們通常所具有的關于上帝的威力和智慧的那個一般的、混亂的、懶散的觀念,跟關于那些屬性獨特的、理性的和動人的[科學]概念之間一定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后者是通過對各種[上帝的]創造物的仔細考察而形成的。”(默頓,2002,第145頁)
而且,文藝復興帶來的這些翻天覆地的變化更是植根于兩千年前的古希臘文明之中。實驗科學前驅羅杰·培根,將理性引進神學的第一人托馬斯·阿奎那,他們的成就無不與他們在中世紀的黑暗中對亞里士多德遺產的不懈發掘有關。開創經典物理學體系的牛頓名著《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1687)在寫作方式上遵循了古希臘的公理化模式:從定義、公理出發,導出命題;而其公理(牛頓三定律)是建立在經驗主義的實驗基礎上的,其命題是通過嚴密的數學推理而獲得的。牛頓名著使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兩大哲學流派在科學上得到完美的融合,這不僅奠定了之后幾百年近代科學的基本架構,還在寫作方法上構筑了后世自然科學乃至社會科學的論文結構框架。至此不難聯想到,我國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普及為何如此艱難!因為無論從經驗主義還是從理性主義角度講,儒家“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為學之道都與之背道而馳。我有一位學生曾經振振有詞地說:“為什么不能‘抄襲’?孔子和朱熹不就是這樣的嗎?”
產生牛頓體系的孵化器并不是大學,而是倫敦小酒吧,是一群敢為人先的近代科學先驅定期舉行的沙龍,波義耳稱其為“無形學院”。這個無形學院便是成立于1660年的英國皇家學會的雛形。而且,先有英國皇家學會,而后有牛津劍橋現代自然科學學科的逐步設立。最初的無形學院中的成員并不是以某個“學科”為單位的,而是志同道合的“紳士”。所謂“學科”,英文叫“discipline”,其本意就是紀律、約束的意思。或許是由于同一類探究對象具有某些共同特點,因而對其進行探究的人必須遵循共同的特定的規則才能有效交流,于是形成了“學科”。而我們一百年前移植西方“學科”的時候,只是移植了探究的結論,卻難以移植這種敢為人先、自由平等的文化和遵守共同約束的習慣。我國大學中的學科是分等級的,同一學科里的人往往不是具有共同的探究興趣,而是具有相似的生存手段。名為發展學科,實為爭奪資源。因此,酒吧中沒有學術交流,只有觥籌交錯。在那里,培根的“知識就是力量”變成了“關系就是力量”。
不過,如果真如林毅夫所說,未來經濟學新理論的誕生地一定在最大經濟體國家,科學技術學科也應該大致如此,那么我國世界一流大學的誕生就為時不遠了。中國當今社會經濟發展確實出現了不少獨特現象,如“中國模式”震驚世界。但慚愧的是最早提出“中國模式”概念的卻是外國人。信息化、全球化或許使得新理論的提出者已經不需要本土生長了?
第二,堅守以探究真理為目標的基礎研究是英國一流大學的傳統與特色。基礎學科是應用學科的源頭活水。科學發展史已經充分表明,基礎研究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會引發技術革命、生產力發展和社會觀念的深刻變革。劍橋人哈維發現血液循環,湯姆遜發現電子,沃森和克里克發現DNA結構,給人類生活帶來了無限的福音。
自17世紀近代科學創立以來,自然科學學科發展以不斷分化為主要特征,每一次分化都代表著人類對自然界認識的深化。17世紀后期牛津大學的算術分化為算術和代數;幾何學分為三角法和幾何學;地理學分為地理學、植物學和動物學;力學分為力學、物理學和化學;辯證法分為邏輯學和倫理學(Bowen,1975)。隨著科學知識的激增,學科分類本身受到哲學家、科學家的關注。當時正式提出過學科分類方案的英國人主要有功利主義倫理學創始人、哲學家、經濟學家和社會改革家邊沁,社會進化論創始人、提出“科學知識最有價值”論斷的斯賓塞,科學家、統計學家、哲學家和倫理學家皮爾生。而我國學界對知識分類則少有研究。
即便在實用主義、功利主義盛行的20世紀,英國大學始終堅守基礎研究。牛津大學前校長盧卡斯說過,牛津的校訓由拉丁文寫成:“上帝帶給我光明”,其意思其實就是追求“真理”。羅素的話可以幫助理解這里上帝與真理的關系:上帝是當科學對一些事物暫時不具有解釋力情況下的科學的替代物。20世紀90年代,當英國高等教育體系從二元制向一元制轉變,鼓勵大學發展應用性學科的時候,以劍橋大學為首的學者們對國家是否應該繼續資助基礎研究的問題產生了激烈爭論。為此,時任皇家學會會長的Aaron Klug給予了肯定的回答。負責相關工作的政府內閣大臣Lang說道:“至關重要的是政府要繼續支持基礎的純理論科學,純理論科學研究支持我們在技術應用與認識世界方面取得驚人的進展。”(賴紅冰,1996)由此我們可以理解,為什么英國是人均諾貝爾獎得主最多的國家。
基礎學科是一個民族在自己獨特的文化發展過程中自然形成的一類知識體系,不同的文化類型產生不同的知識論或認識論,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基礎學科體系,因此它具有鮮明的文化屬性。東京大學教授中島隆博認為:“中國自古以來就熱衷于學問的分類。按照經、史、子、集進行四部分類就是其代表,……但是,這并不是僅僅為了對圖書進行分類。它來自于這樣一種世界觀:我們該怎樣把握這個世界,用何種原理進行區分,又在何種形式下進行理解。學問的分類,規定了其文化的根本姿態。”(小林康夫,2005,第30-31頁)由此可見推論,發展基礎學科比發展應用學科,對于中國文化傳統中成長起來的大學而言,難度更大。
第三,通過高等教育系統的有序分化而不是整體轉型,應時而動、開拓創新。自19世紀末社會經濟發展中心移向美國后,英國的科學技術世界第一的地位已經喪失,這主要源于忽視了能夠激發新問題和帶來新資源的應用科學領域。例如1897年劍橋人湯姆遜發現了電子,但標志著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計算機、自動化等相關應用學科卻在美國開花結果。
為了改變這種狀況,20世紀中期以來英國啟動了三次重大改革。一是60年代創建了三十多所多科技術學院,構成與傳統大學定位迥異、相互補充的職業性、應用型、大眾化的教育部門,形成所謂高等教育“二元制”結構。盡管之后澳大利亞、德國、加拿大等也效仿此種“增量改革”模式,但英國的二元結構特征更加明顯,大學與非大學之間等級分明(姚榮,2015)。二是80年代政府大幅度裁減對大學的資助,一大批傳統的、低效益的學科與院系被縮減或合并,其目的在于將大學與多科技術學院一樣推向市場。三是90年代初英國政府頒布《高等教育:一個新框架》和《繼續教育和高等教育法》,將多科技術學院納入統一的大學體系中,建立起公平競爭的市場規則,將大學進一步推向市場,于是產生了一批像沃里克大學那樣的為伯頓·克拉克所稱頌的“創業型大學”(克拉克,2008)。
不過,英國的做法并不是簡單地從“二元制”退回“一元制”。牛津和劍橋的轉型是在確保基礎研究這個“根”的條件下,在“枝葉”上向外拓展。這一點與沃里克大學的全面轉型非常不同。比如,劍橋大學1999年與美國馬薩諸塞的劍橋(MIT)合作,共建“劍橋-麻省理工學院研究院”(CMI)。該研究院依靠兩校卓越的人才、技術和社會資源,開展高水平的研究、學習和商業活動。CMI所帶來的不僅是科研成果和商業利潤,更是在英國高等教育體系中樹立起創新創業的榜樣,并以此推動國家競爭力的增長(王燕等,2002)。所以英國政府撥專款支持CMI。
埃茲科維茨(2005)曾經將創業型大學分為“美國模式”和“英國模式”兩種,美國主要以研究型大學為先驅,英國主要以教學型大學為先驅。其實英國采取的是類似于美國在贈地學院時期的模式——增量改革模式。美國加州在20世紀60年代高等教育總體規劃中采取的更接近英國今天的模式:只有“加州大學系統”內的十所大學可以培養博士生、從事基礎研究,其他大學面向應用與教學。由此可見,歸根結底的改革之道在于,應根據本國具體情況,以最高效率在基礎研究與應用技術之間取得平衡。英國人吉本斯(2011)提出的“知識生產方式轉型”理論是對英國當代大學變革局部現象的描述,但不是整個系統的描述。因為不是所有大學和所有學科都發生同樣或相似程度的轉型。牛津與劍橋就不同。美國諸多常青藤名校并沒有效仿MIT或斯坦福的硅谷模式。實際上吉本斯這個概念所論及的是以理工科大學為主的知識生產主體的多元化和管理過程的復雜性這一科學社會學問題,并沒有涉及知識生產本身的認識論邏輯。其實即便是模式I的“學科邏輯”也是與社會經濟分不開的,只是更需要科學家們的抽象思維能力。正如吉本斯認可的那樣:模式I與模式II是演進的關系,I是II的基礎,I為II的“供給側”。因此,對英國整個高等教育體系的描述用“分化”比用“轉型”一詞更合適。
不過,模式I階段在中國還沒有真正完成。由于我們的基礎是空虛的,增量便是冒進的。我們不少大學和學科還處于經院哲學“前模式I階段”,還沒有出現像阿奎那那樣的大師,找到舊學與新學的契合點,在信仰層面構筑與科學一致的學術文化和大眾文化。但嗷嗷待哺的職業教育等不及了,它們便成為“缺乏供給側的模式II”。不過中國的職業教育可能會成為“反哺”大學的先驅——又一個“中國模式”。但反哺不能迅速解決世界一流大學的學科邏輯先天不足問題,它需要一個成長的而不是移植的過程。
至此可以理解一百多年前哈佛大學校長埃利奧特的感慨:一流大學建設需要兩百年。五年前耶魯大學校長萊文說,亞洲最好的大學東京大學也需要一百年才有可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學。中國也有古訓:“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考慮到后發優勢等因素,我國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學究竟需要多少年?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阿特巴赫認為,世界一流大學的競爭會越來越激烈,對于大多數國家而言,通常只有一兩所能夠達到世界一流(Altbach, 2004)。克拉克·科爾在其《21世紀的高等教育——不能回避歷史》一書中預言,全球化將使得大學在一個國家內部的差異小于國家之間的差異。因此,關于中國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問題,切不可急功近利。而且,世界一流大學必須瞄準國際共同規范,切不可自說自話。歸根結底,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資源貧乏、傳統文化深厚的大國,目前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關鍵在于構建一個可持續的自我調節的分類發展政策環境,并且在社會文化上也能夠建立起與之相配套的相互協調的多元文化生態環境。后者比前者更具挑戰性、更需時日。
埃茨科威茲,H.(2005).三螺旋——大學·產業·政府三元一體的創新戰略(周春彥,譯).北京:東方出版社.
克拉克,B.(2008).大學的持續變革——創業型大學新案例和新概念(王承緒,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吉本斯,M.等.(2011).知識生產的新模式:當代社會科學與研究的動力學(陳洪捷,沈文欽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賴紅冰.(1996).關于基礎研究政策問題的國際論述與爭辯.世界科技研究與發展,(12),77-79.
默頓,L. K.(2000).十七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與社會(范岱年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王燕,孔寒冰,王沛民.(2002).世界一流大學的現代學術職能——英國劍橋大學案例.清華大學教育研究,(1),28-48.
小林康夫.(2005).教養學導讀(趙仲明,譯). 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姚榮.(2015).制度性利益的重構:高等教育機構“漂移”、趨同與多元的動力機制——基于英國高等教育機構變革的經驗.教育發展研究,(21),18-24.
Altbach,P.G.2004.The coasts and benefits of world-class universities.Academe, 90(1), 20-23.
Bowen, J. 1975.AHistoryofWesternEducation. London: Methuen & 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