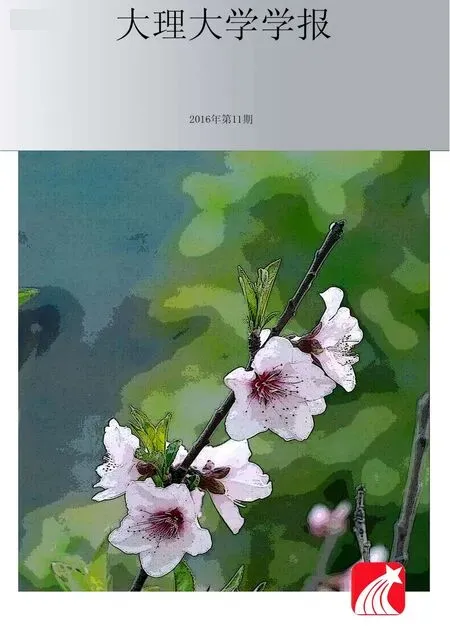馬毓林與《鴻泥雜志》
馬銀行
(麗江師范高等專科學校,云南麗江 674100)
馬毓林與《鴻泥雜志》
馬銀行
(麗江師范高等專科學校,云南麗江 674100)
馬毓林于道光年間從京師至滇,沿途見聞筆之于書,名為《鴻泥雜志》。其書主要涉及山川湖泊、氣候、動植物、交通關隘、商業手工業、官場士人、楹聯詩歌、宗教信仰、風土人情等。在人文地理學、歷史學、文學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價值,體現了作者關懷民生、關注現實、知行合一的人文思想。盡管該書尚存一些不足,但瑕不掩瑜,不但豐富了清代麗江歷史研究的史料,還在地方文化、民族、宗教信仰、旅游資源開發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馬毓林;鴻泥雜志;云南
隨著清雍正年間實施大規模改土歸流,清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以適應生產關系變化的需要,使農業、手工業、商業等得到長足發展,云南進入經濟快速發展時期。內地士人至云南游歷、做官者日益增多,在教育發展、文化傳播、風俗變革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同時也留下大量著述,如《彩云百詠》《滇云歷年傳》《滇小記》《滇海虞衡志》《滇黔游記》《滇南新語》《滇游續筆》《滇南志略》《滇中瑣記》《怒俅邊隘詳情》等,這些著述對清代滇云諸地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宗教、民族、地理、文學、人物等記載詳瞻。《鴻泥雜志》就是這個時代不可多得的一部筆記體著述,作者馬毓林前往麗江府任知府時,從京師至昆明、大理,將沿途所見所聞涉及麗郡風土人情的記載和一些讀書筆記、心得摘要記錄整理,該書大致付梓于清道光年間。
一、馬毓林其人其事
馬毓林(1768-1830),字西園,號雪漁氏,山東省武定府商河縣(今濟南市商河縣)人。年幼聰慧,矢志讀書。19歲中童試第一,30歲中戊午科(公元1798年)舉人,40歲中戊辰科(公元1808年)進士,朝考中選殿試二甲。以主事分刑部,觀政數年后提中廳,差竣實樸,歷主事、中總辦、員外郎等職。嘉慶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時任湖南鄉試副考官,甲申(公元1824年)冬外放云南,乙酉(公元1826年)任麗江府知府。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五月五日,總督阮元、巡撫伊里布上書朝廷,求補任云南府知府,“因云南府為省會首郡,管轄十一州府,為通省知府領袖,政務殷繁,時有緊要案件,必須精明干練之員,方可勝任,藩臬兩司于通省知府內詳加揀選”〔1〕。道光七年馬毓林離職麗江,任云南府知府。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冬以病辭職,“大吏強為慰留。”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欲升迤南道道員,馬毓林力請辭官歸鄉。第二年病逝山東省商河縣,葬于武定府陽信縣。所著有《湖南典試錄》《萬里吟》《鴻泥雜志》存于家。
(一)年幼聰穎,志在讀書
由于受家庭熏陶,馬毓林年幼時父母教導有方。馬毓林之父,“世擅清門,代傳素業,家風淳厚,垂弓冶之良模,庭訓方嚴,啟詩書之令”〔2〕415。其母高氏,“克樹芳型,尤多慈教,著承筐之雅范”〔2〕415。而繼母李氏,“殫育子之劬勞,恩同毛里,篤因心之慈愛,道在均平”〔2〕415。在父母精心教育下,加之章玉輅任商河縣知縣時,致力于發展教育,“事務持大體,尤加意學校,月試極盡獎勸,雖公務叢集不廢,一時科名登進皆所拔萃士”〔3〕。馬毓林年十九時應童子試,成績第一,縣令章玉輅尤為器重,學使劉文恪復核,認為馬毓林在童試中第一當之無愧,“以公冠首,阮宗師科試,以優等食餼”(光緒馬氏族譜)。顯露出馬毓林年幼時的聰慧。
(二)出身書香門第,父輩言傳身教
馬氏宗族在山東商河縣影響深遠,考取功名者甚多,據民國《商河縣志》記載:“清名進士馬翊宸城北馬莊,馬毓林城北馬家菴,至今書香不絕,雖非同宗而各有譜牒,散處各莊者至十余處,亦邑之望族也”〔2〕260。馬毓林出身書香世家,其父馬江、其伯馬淮對其影響深遠,父親以詩文見長,而叔叔則以刑名著稱。
馬江,字桂嶺,乾隆乙酉科舉人,官登州府教授〔2〕267。“生平崇尚實學,作文沉郁頓挫,綽有風骨,詩出入唐宋,不為前人羈縛,書法冠絕一時”〔2〕339。著有《春帆集》《閩嶠集》《觀海集》《余間偶筆蕉軒集》《蒙養拙菴古文》《秋浦韻鈔》《還鄉集》傳世〔2〕339。這對馬毓林日后在文學上的成就產生深遠的影響。
馬淮,字柏源,乾隆庚辰科舉人,官福建惠安縣知縣〔2〕267。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至福建羅源縣為官,“剖斷積案,獄無遁情”〔2〕321。時有林、黃二姓爭葛藤山界,經年不休,馬淮為之斷案,“爾山名不祥,改和息山,為爾斬斷葛藤,永無訟患”〔2〕321。武生鄭某與弟爭奪遺產,官司打十余年而無法斷案,馬淮“責之以大義,喻之以至情,感泣而罷”〔2〕321。乾隆辛卯(公元1771年)官惠安,惠安素稱難治,馬淮“奸剔弊,四境安堵,民歌善政”〔2〕321。因政績顯著,奏朝廷加通判銜。馬淮在惠安時“有稻秀雙歧,永春有鐵樹開花之瑞”〔2〕321,不久因病卒于任上。由于自己為百姓排憂解難、化解鄉里恩怨,百姓懷其德,“海疆人莫不感德”〔2〕321。馬淮的政治經歷對馬毓林后來從政影響深遠。
(三)勤政愛民,頗有政聲
馬毓林為官清廉,勤政為民,頗有政聲。嘉慶戊寅(公元1818年)任湖南鄉試副考官,“典試湖南得人極盛”〔4〕。得舉人李萼等49人、副榜唐晉等9人〔5〕,皆知名士,“階見時龍顏大喜”(光緒馬氏族譜)。道光乙酉任麗江府知府,“政簡刑清”。馬毓林曾撰寫《麗江視事見年歲豐稔漢夷安恬喜賦見志》一文,是對道光早期麗江太平社會的詳實描述,也是關懷麗民的真實寫照。“鼓角聲隨弦誦音,西陲武備氣嚴森。經生豈識籌邊策,壯士頻懷報國心。慷慨有情思倚劍,升平無事欲彈琴。須知鎮靜方為福,忠信常書座右箴。土語侏儷未易知,欣看蒼赤氣恬熙。年豐比戶皆篘酒,俗樸沿街盡貿絲。麥餅乳茶留客坐,蘆笙銅鼓賽神祠。笑余忝作蠻夷長,無詐無虞兩不疑”〔6〕。上闋展現出一幅塞外風光,將士守邊之景;而下闋描寫麗江人民生活恬靜、物產富足的升平之世。馬毓林任麗江府知府時正值賓川饑荒,馬毓林倡捐養廉銀賑災,“賓川屬境歉,公捐廉賑濟,輿誦遍遐邇。”由于馬毓林的積極行動,幫助賓川度過災荒危機,百姓感其德,傳誦一時。
(四)從政清廉,司法公正
馬毓林在刑部任職時,對案件潛心研讀,審理細致入微,“秋審處于巨案疑獄,悉心研鞠,每日夕下,直秉燭閱。案牘初至署,大司馬光悌性最嚴于□官,毫無假借,公遇疑案,即侃侃與必得情況后已,轉后上官,所事倚重治獄,多所卒”(光緒馬氏族譜)。因斷案能力強,獲得同仁的認可,“仁恕居心精勤,蒞事獄多平反,同曹咸推為能”〔4〕。總督阮元知曉馬毓林有較強的政治管理和決獄能力,力請調任云南府知府。道光七年任云南府知府〔7〕。由于云南府為省會,事多繁雜,馬毓林“以靜不涉張皇,而自無廢事”(光緒馬氏族譜)。此時昆明出現張大鵬等倡亂惑眾之事,總督阮元欲以極刑處置領導者及參與者,按察司和布政使竭力勸說,卻無法扭轉局勢。馬毓林勸“以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光緒馬氏族譜)。總督阮元以馬毓林刑名諳練,遂允其請命。馬毓林“立橐搨,奏天廷,甚合上意”(光緒馬氏族譜)。云南府同知啓榮嘗贊曰:“不冤不濫,無縱無枉。不少存幸功之心,能大開三面之網,非公寬仁,烏足以語此”(光緒馬氏族譜)。道光《商河縣志》也有相關記載:“政務殷繁,履任半年積案一空,有張大鵬等大案,毓林日夜研鞠悉得實情,立釋無辜,不枉一人,獄無冤。抑滇人頌之”〔4〕。馬毓林事跡不但在滇云各地聲名遠播,在鄉里也頗有影響。
二、《鴻泥雜志》所記載之內容
馬毓林于甲申年出守滇南,“渡黃河、涉湘漢、過洞庭,由灘河抵鎮沅而南,日日山行。”至乙酉六月始抵滇省,旋補麗郡。馬毓林任麗江知府時利用閑暇之余,考察山川形勝、訪問鄉老友人,曾說:“其山川、人物更有前人所弗及考核者,幸其地僻事簡,公余之暇,取道途所經及聞諸友人者,抄錄成軼。”命名《鴻泥雜志》,于道光丙戌年間流布。清人錢泳論述“鴻泥”之意,“足跡所到,略志鴻泥,以備遺忘,不可謂之閱歷也”〔8〕467。此論與馬毓林著述意義相同。
《鴻泥雜志》,全書共四卷,原文約3.6萬字。前兩卷記載作者從中原地區至滇云沿途所見所聞,后兩卷記載云南軼事和簡述云南歷史,其中對吳三桂在滇事跡記載尤詳。在序中作者表明撰寫之意,“天地之大,品匯之繁,怪怪奇奇,何所不有。如必以親身涉歷之區,所見所聞,筆之于書,以為良朋聚談之助,則游覽所弗及、耳目所不周者,終屬茫然。是何殊于以蠡測海,以管窺天,徒貽笑于大雅乎!”由于我國疆域廣袤,地理差異顯著,民族分布廣泛,其歷史人物事跡、詩詞歌賦、民間諺語歌謠,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因此“使不登諸編簡則過而輙忘,幾與入寶山而空回者無異”。
該書所記載內容豐富,涉及到當時社會的方方面面,是對道光初年云南社會生活的真實寫照。從《鴻泥雜志》分類來看,主要記載山川湖泊、各地氣候、動植物分布、沿途交通、城防關隘、區域農業、手工業狀況、官場士人、楹聯詩歌、民風民俗、宗教信仰等,其中對清代道光年間麗江乃至滇西北社會生活記述尤詳。
(一)對云南山川湖泊之記載
馬毓林在書中對其游覽滇云諸地,所到之處山川多有記載,如昆明太華山、碧雞山、金馬山,大理點蒼山、賓川雞足山、炎涼嶺、鶴慶觀音山、麗江象山、黃山、芝山、文筆山和雪山。其中對玉龍雪山冰川景觀描述頗詳,“雪山,一名玉龍山,在麗郡北二十里,高可萬仞,峰巒削秀,積雪經年不消,望之一片晶瑩,如瓊樓玉宇,近山側則寒風刺骨,未有能躋其巔者。麗郡兒童率于六月內取山雪和以蔗糖,在市售賣,如京師之賣冰水者”。馬毓林曾因公由劍川至麗郡,途經鐵甲山,目睹了鐵甲山森林茂盛的景象,“山上土多石少,樹木叢雜,徑中堆木葉厚尺許。樹根從地中突起,蟠曲滿道,地上樹支木片縱橫無數,亦有大木沉埋地中,上面猶隱隱露出,行人即踏此而過”。馬毓林描述了鐵甲山植被完好,與今天鐵甲山植被稀疏形成鮮明的對比。
(二)對云南各地氣候差異之描述
在書中馬毓林簡要概括云南各地氣候特征,“滇南天氣無大寒大暑,時當盛夏亦須內服綿背心,冬月則小毛衣服即可御寒……大抵滇省天氣除元江、普洱、鎮沅有瘴癘之處,暑熱為多,其余微熱、微寒。雖有不齊,非甚懸絕。”并以切身行動,感知云南的氣候差異,“余于乙酉六月抵滇,正值中伏,早起赴憲轅,涼氣爽肌,頗似北方中秋節后。彼時人言麗郡有雪山,為滇省最寒之地。及十月至麗,山上樹木不凋者,署中蜀薺花尚開放,早晚微涼,如北方九月下旬”。
(三)對云南動植物之記載
由于云貴高原山脈縱橫交錯,形成若干不同的地理單元,區域地理環境差異明顯,為生物多樣性提供了環境。書中記載了馬毓林所見所聞動物中陸生動物20余種、水生動物10余種、農作物10余類。而每一大類農作物又分為若干品種,其中蔬菜30余種、菌類10余種、果類近30種、藥材20余種、花屬22類。
(四)對沿途交通之記述
馬毓林從京師至滇云,途徑黃河、湘漢、洞庭,由灘河乘船至鎮遠,再由鎮遠走山路至滇,對沿途奇聞異事記載頗多,再現了清代中葉云貴交通文化。在陸路方面,對文德關、相見坡、禹梁杠、云頂關等處多有描述,認為這與蜀道相似,“皆鳥道懸空,肩與須雇纖夫牽挽以行,真不亞于蠶叢之蜀道矣”。在水路方面,對自常德至鎮遠水路險灘記載詳細,其灘共有三百余,而其中最險惡者,如“清浪灘、黃獅滾洞、滿天星、高麗洞等,不可枚舉。”對行船艱難也有記載,“每船皆用纖夫十余名,牽挽而上,水程之難,無逾于此”。
(五)對城防關隘之記述
為了加強對地方的管理與控制,清代滇云諸地充分利用險要的地理地形設關立哨。從貴州至云南沿途關卡林立,馬毓林總結了所經貴州沿途關卡,“黔中山多陡峻,鎮遠以西則文德關、相見坡、禹梁杠、云頂關;貴陽以西則黃果樹、鳳凰關、石龍關、打鐵關、拉邦坡、老鷹巖、南車坡等處,皆鳥道懸空,肩與須雇纖夫牽挽以行,真不亞于蠶叢之蜀道矣”。也對昆明至麗江沿途所經關哨作簡要描述,“自滇省至麗郡共十八站,有九關十八哨之險,如碧雞、老鴉等關,尚不甚險隘,帷響水、回蹬、宣化、邱塘各關崇高峻陡,其余如獅子口、排樓哨、六里箐、定西嶺等處,亦皆崚嶒崎嶇,較之黔中山路更為難行”。
(六)對云南手工業發展狀況之記載
清代云南手工業有自己的特色。如通海緞,“滇省所出之通海緞,俗呼為滇緞,省內各街道俱有機房數處”。麗郡地處偏遠,伴隨著服飾的改革,布匹需求量加大,促進了本地紡織業的興起,“婦女多以貿易營生,不解紡織。丙戌春,自川中來數人教人紡織,并能造機杼之具,婦人從學者甚多,學織之布粗惡未能勻細”。
紹興酒在云南頗受歡迎,然而由于運輸成本較高,云南開始紹興酒本土化生產,“滇省所用紹興酒佳者甚多,惟價太昂,每中罈值銀四兩。近來土人有假造者,初飲亦可,惟不能耐久,久則色味俱變矣。”麗江、鶴慶、楚雄等地釀酒業較為發達,“麗江賣燒酒者甚多,其地并無高粱,但以麥曲和稻米為之,味香而薄。亦有黃酒,甜如蔗糖水,飲多亦足致醉。至鶴慶燒酒,不知如何釀法,其氣味較麗郡為佳。楚雄定遠縣出力石酒,味不甚香冽,而氣力較大,似與來自山西之大曲酒各有所長”。
(七)對云南物資流通之記述
清代中葉商業發達,商品流通加速,商人足跡遍布各地,盡管云南地處邊陲,但也成為商品流通與交流的重要地區之一。云南境內流通的商品種類繁多,主要涉及到棉花、食鹽、皮革、洋呢、絲綢、火腿、酒類甚至魚蝦等類。洋呢“出自廣東,商賈販至云南,以此物并無關稅,故價值較他省為輕。每上高洋呢,天青色者,不過每尺一兩。其藍色及各雜色,則每尺只六七錢”。川黔絲綢因成色、尺寸不同,造成了價格差異較大,“其由貴州絲織成者,俱系雜色,每疋足袍料一件,價不過三兩。其由四川絲織成者,藍色居多,尺寸亦極寬長,每疋價銀總需六兩。又有貴州紬,自貴州販來者,每疋長四五十尺,價值亦不昂貴”。
(八)對云貴官場人物之記略
馬毓林在滇期間,接觸各級官員頗多。道光年間云貴官場上有一段佳話:道光丁亥、戊子間(1827-1828)王楚堂、翟錦觀官宦云南。王楚堂〔9〕,字云榭,為云南方伯;翟錦觀〔9〕,字云荘,為云南廉訪,其字中都含“云”,而云南因“漢武朝彩云見南中,云南之名始此。”祁、何金治理貴州,而祁〔10〕400,字竹軒,道光六年任貴州按察使;何金〔10〕400,字竹居,道光九年任貴州布政使,其字中都含“竹”,而貴州“桂竹后稱貴竹”。由于以上四位官員官績顯著,深受官民愛戴,佟景文等作《竹云歌》頌之。嵩浦于道光六年任貴州巡撫時熟知四位官員政績,手書一聯贊之云:“貴竹稱雙竹,云南見二云。”這是幅雙關聯,既符合滇黔別稱的歷史淵源,也與四位官員官績政績相吻合。
(九)對云貴楹聯詩歌之記錄
馬毓林在《鴻泥雜志》中記載所見所聞楹聯有11幅聯。按其內容來說,大致可分為茶棚廟宇、樓閣亭臺、官衙貢院等類。許多楹聯罕見于其他文獻,為了解清代中葉云貴交通線上的世俗民風、山川風物、文人墨跡等提供了重要的文獻資料。馬毓林途經關索嶺時,瞻仰關索廟,記一楹聯,“山不在高,平辟南荒,丞相天威猶在望;子能繼父,力扶炎鼎,關侯廟貌迥如新。”鄂西林相國撰寫云南貢院楹聯一幅,“文明當極盛時,億萬年聲教,不須潤色盡屬太平;賞識在風塵外,廿三郡人才,一經品題便成佳士。”
馬毓林記載的詩人達28位,詩歌達46首。其中唐元明時期的詩人13人,如唐代元稹、白居易等,元代段功夫人,明代建文帝等;清代詩人15人,如錢棨、史漁村、張補裳、杜藕莊、周雁沙、葉小庚等。馬毓林所記載清代詩人、詩歌在其他志書中難以見到,這為研究清代滇云詩人群體、詩歌創作提供了線索。
(十)對宗教信仰區之描述
云貴地區民族眾多,分布定居,宗教有別。馬毓林途經各地留意觀察地方民間信仰。在至滇途中,過飛云洞,看到“蘭若一區,殿宇崇閎,外殿祀關帝”。而洞內石壁上則立觀音大士像,“法相莊嚴,著大紅洋呢斗篷,旁侍善財龍女,神致如生”。馬毓林對關索嶺關索廟地理位置、建筑布局、殿宇分布等記載尤為細致,可見關索在西南地區人們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地位。而麗郡居民對宗教信仰十分虔誠,“麗郡家家好佛,每逢望行香時,見男婦持香燭赴菴,觀者絡繹不絕。其婦女貿易赴市,亦必攜帶金剛、觀音諸經,于交易之余,坐地持誦”。由于麗江臨近西藏,藏傳佛教對其影響深遠,“土通判木睿第四子生有異相,五六歲時能通釋典,及八九歲時,西藏喇嘛來迎,云其師圓寂時有遺言,降生此地。此子與喇嘛相見如舊識,遂偕至郡北解脫禪林,談禪累日,與喇嘛偕赴西藏不復返,當時人皆稱為活佛”。
(十一)對滇云諸地風土人情之記載
滇云諸地因民族眾多,風俗差異顯著,形成具有獨特的區域民族風情。大理三月街起始于唐,至今不衰,成為大理重要的物資交流節日,“每歲三月十三日,大理開市于演武場,集商賈聚四方之貨,交易凡服飾、飲食、器用、書籍以及金玉、珍寶,無不具備。至十七日移城內,二十日散市,俗呼為月街子會”。馬毓林在麗郡日久,對麗江民風民俗知之甚詳,描述細致,主要涉及到龍神祠三月演戲、麗婦服飾、婦女在社會經濟中的地位等。馬毓林及其前任知府王厚慶對麗郡服飾進行改革,“麗郡婦女習染夷俗,身披羊皮,頭戴尖帽,高尺許,背負竹篼赴市貿易。余同年王幼海蒞是郡時,曾出示嚴禁,從此戴尖帽者改為觀音兜,而羊皮則絕不能去。蓋其地天氣較寒,布疋昂貴,惟羊皮價賤,是以大家宦族嫁女、娶婦亦必制羊皮二塊,鑲以寶石、珠玉,以為華飾。其貿易負重者則以粗惡羊皮為之”。
三、《鴻泥雜志》人文思想
《鴻泥雜志》是馬毓林所見所聞、所讀體會之作,書中充滿了作者關懷民生、關注現實的情懷,體現出作者實事求是的編撰思想,反映出作者知行合一的理念。
(一)關懷民生,關注現實
盡管馬毓林出身書香門第,仕途順暢,但能深入民間、了解社會現實,關注普通百姓生活。馬毓林在麗郡時特別留意下層社會生活,深入百姓中間,幫其排憂解難。麗江龍神祠每年三月間演戲,“郡城婦女無貴賤貧富皆往游盛,飾相炫耀”,而貧困者“典田賣谷租賃服飾”,對此陋風馬毓林曉諭禁止。清代中葉,麗江的嫁娶已發生變化,夫家備齊嫁妝成為娶親的必要條件,馬毓林對此提出勸告,不正風氣有所減緩,“嫁妝麗郡女子未嫁者,名曰:‘阿古姬’。赤足蓬頭,有力能負重,往往有三十余歲未嫁者,問其故,則以夫家不能備金鐲、金簪等物,即不許迎娶。”馬毓林對此痛心疾首,決定革除弊風,“余出示曉喻,此風稍息。”
馬毓林途經貴陽時,留意普通百姓的衣食住行,“貴陽東西民婦赤足者多,裹足者亦有之。恒以織草履,編草帽為業,亦有紡綿花者。”由于貴州山多田少,布匹生產極為有限,然而飯食不甚昂貴,“飯一盂值錢三文,謀食尚易,惟衣服甚難。每見大路旁男婦布衣藍縷,皆千補百衲,若懸鶉無一完好者。”這表明當時貴州的食物供應尚可,而服飾卻極為短缺。
(二)記述親聞,下筆公允
《鴻泥雜志》記載內容一者為作者親見親聞,保證了所載內容的真實性。關索及關索廟爭議頗多,然而由于歷史久遠,史料匱乏,難以考證,鑒于關索信仰在滇云諸地傳播廣泛,早已深入人心,馬毓林認為“以關帝威靈,千古供仰,由父及子,隆其廟祀,亦足動人忠義。至武侯手植之松,志以石碣,與召伯甘棠無異,俱不必辨其真偽也。”提出較為公允的評價方法,值得后人借鑒。
《鴻泥雜志》記載內容二者為依據史料抄錄而成。對于史書記載模糊不清者,馬毓林以實事求是的態度考辨其真偽。如乾隆《云南通志》記載麗江花馬石,“緣城西北三百五十里有花馬山,崖石如馬,其色斑爛。昔么些據此,名其國為花馬國,后人附會之,遂謂麗郡產此石”。馬毓林在麗江一年有余,“求之不得,間有人以石求售,稱為花馬石,其實與尋常石無異,并無馬形亦無花紋,”進而認為“足見其誤”。
(三)知行合一,親身涉歷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二則不可偏廢”〔8〕604。在以通過窮經皓首、科舉考試而取得功名的社會里,實為一種先進的思想理念。馬毓林雖然也是通過科舉走上仕途,然而對“行萬里路”樂此不倦。面對著復雜的自然與社會,馬毓林提出了自己的認識觀念,認為“天地之大,品匯之繁,怪怪奇奇,何所不有”。對于自然與社會的認識堅持“必以親身涉歷之區,所見所聞,筆之于書。”進而提出“則游覽所弗及、耳目所不周者,終屬茫然。是何殊于以蠡測海,以管窺天,徒貽笑于大雅乎。”同時對當時社會上流行的閉門苦讀、知行脫節的行為提出批評,“然而九州遍歷,世有幾人,書生不出戶庭,眼光如豆,一旦筮仕分符,凡山川風土、古今人物以及謠諺詩歌。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使不登諸編簡則過而輙忘,幾與入寶山而空回者無異。”馬毓林至麗郡后,把沿途見聞、麗郡風土人情及讀書筆記等撰寫成書,“幸其地僻事簡,公余之暇,輙取道途所經及聞諸友人者,抄錄成帙,非敢借此以問世也。”盡管馬毓林認為撰寫此書“以為良朋聚談之助”“以此編代吾口焉”。然而卻留下了彌足珍貴的史料。
四、《鴻泥雜志》的價值
《鴻泥雜志》前兩卷多為馬毓林見聞記載,中間穿插因地點或歷史事實而引申的歷史故事;后兩卷為讀書筆記,簡要記述云南的歷史。其中對吳三桂在滇之事記載頗為詳細。基此該書的價值主要體現在人文地理學、史學、文學等三個方面。
(一)人文地理學價值
《鴻泥雜志》刊出至今已有200余年,然而《鴻泥雜志》又是當時見聞記載,內容涉及到社會各個層面,不亞于一本百科全書式地方志書,具有濃厚的人文地理氣息,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對農業經濟地理的記載
農業經濟發展受到自然條件和社會經濟條件的強烈影響,在地域上表現千差萬別。馬毓林對滇黔各地農作物分布作了簡要描述,“滇南五谷惟稻、麥、豆、荍四種,各郡皆有。”也記載了貴州水稻種植分布狀況,并對比了區域間的作物種植差異,“黔省東西一帶稻田最多,至安順府稻田更盛……安順以西稻田漸少,入滇界平地較多,惟荍麥、燕麥、包谷等類,稻田亦有之,然較之黔省則大相懸殊矣。”由于滇黔各地糧食價格平平,人們生活較易,“稻米白潔,每觔不過制錢十文。其菜蔬雞鴨魚肉俱不昂貴,是以滇南謀食為最易也。”充分體現了作者對民生的關注。
2.對礦產資源開發的描述
反映出清代云南礦產資源開發的狀況。在礦產資源方面主要記載麗江文筆峰銅屑、東川紫銅、武定綠礦石、大理石、永昌圍碁子、猛緬的水晶、墨玉、翡翠、玉、寶石、琥珀等;也記載了云南食鹽產地及生產狀況。如云南食鹽生產,“滇省食鹽皆由井水煎辦,其法不一。商人設立鹽廠,廠內掘二井,一咸水一淡水,稱為用淡養咸,候咸水養成取出,用鐵鍋煎成鹽塊,如釜大,色黑白不一”。
3.對手工業及商品流通的記述
反映出清代云南手工業發展水平及物資交流的狀況。《鴻泥雜志》記載云南手工業主要涉及到紡織業、皮革業、釀酒業等。洋呢成為大宗進口商品,并在全國廣泛流通。云南本土絲綢業也有一定的發展,“滇省所出之通海緞,俗呼為滇緞,省內各街道俱有機房數處”。貴州、四川紡織品也在云南流通,價格又不甚貴,“其由貴州絲織成者,俱系雜色,每疋足袍料一件,價不過三兩。其由四川絲織成者,藍色居多,尺寸亦極寬長,每疋價銀總需六兩”。羊皮、猞猁、水獺、飛鼠等主要產于麗江,其中羊皮作為服飾在麗江較為普遍,而猞猁、水獺、飛鼠等因價格低廉,使用者眾。云南本地酒業發達,各地都有釀造者,如麗江燒酒、黃酒,鶴慶燒酒,楚雄力石酒等。作為外來酒品紹興酒在滇云各地也頗受歡迎,因利驅使,促使紹興酒本地化生產。
4.對宗教信仰的記載
不同區域、不同種類的宗教形成不同特征的宗教文化景觀。馬毓林觀察、記錄了沿途所見之宗教分布。云貴交通要道之名勝,多成為佛、道宗教廟宇之地,正是這些以宗教內容為核心的文化景觀構成了宗教發展與依托的場所。貴州巖溶地貌較為發達,溶洞眾多,在游勝之處,各路神仙多有崇祀,如飛云洞,洞外祀關帝,洞內祀觀音。因小關索嶺地理位置特殊,在此修建“蜀漢將相祠”,成為云貴關索信仰的重要標志,不僅當地百姓對其頂禮膜拜而且往來官宦、士子、商旅等對其崇拜有加。麗江是藏傳佛教在滇云諸地傳播的區域,也是藏傳佛教東進的終點,藏傳佛教在百姓中產生廣泛的影響。馬毓林詳細記載麗江土通判木睿第四子成為活佛之事,可以說是麗江地區藏傳佛教信仰的重要體現。
5.對社會風俗區的描述
社會風俗是一區域風俗展現的綜合體。滇云諸地因經濟發展不平衡、文化差異較大,社會風俗各異。聚會是人們交往、溝通的重要形式,昆明士大夫多借寺廟、會館等集會,圓通寺、真慶觀是士大夫宴客的重要地點。麗江芝山福國寺是佛教圣地,也是勝覽之處,“寺內皆喇嘛僧,往游者率借僧寮為飲讌地”。因麗江民族傳統、地理環境與其他郡縣有所差異,麗江婦女的生產地位、服飾、習俗等方面差別較大,形成自己獨特的風俗習慣。
(二)《鴻泥雜志》的史學價值
1.客觀地記述并評價了歷史
《鴻泥雜志》是一部具有鮮明特色的游記與讀書筆記的綜合體,前兩卷所撰寫的內容以游記為主,后兩卷所編撰的史事以讀書筆記為主。記錄了從傳說故事開始一直到道光年間,可以說是一部簡略的云南地方通史。其中歷史事件涉及到金馬山故事、南詔碑緣由、古妙香國、南詔建國、竹王、蒙舍大理國更迭、明玉珍寇云南、梁王段功恩怨、阿事跡、驃國歷史、建文軼事、楊升庵戍滇、吳三桂在滇事跡等。對于該書的編撰,作者有選擇性地、較為系統地記述云南歷史與人物,并對事件和人物評價較為客觀,如對李定國的評價為倔強、勇猛與忠誠,評價沐天波的忠順與無奈,因事件不同,對吳三桂的評價褒貶不一。
2.豐富了地方文獻資料
《鴻泥雜志》前兩卷是馬毓林對道光早期云南社會概況的描述,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道光時期云南的社會現實。而這些記載罕見于其他史志,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云南地方史料。
3.為考校其他史料提供依據
大觀樓長聯傳頌海內、影響深遠,然而在長聯的傳抄中,出現別字現象,在沒有一手資料的基礎上,真假難辨。馬毓林所記載大觀樓長聯是作者實地游覽,為第一手資料,內容較為真實,這為考校梁紹壬《兩般秋雨盒隨筆》中的大觀樓長聯、梁章鉅《楹聯叢話》中的大觀樓長聯及楊瓊《滇中瑣記》中的大觀樓長聯提供了依據。
4.還原歷史真相
馬毓林于道光乙酉(公元1825年)秋暢游大觀樓,對清代中期的大觀樓布局、景致記載較為真實,為后人研究大觀樓提供了一手資料。石玉順、李紹飛編著《大觀樓:名樓名聯名詩賞析中國名樓》對大觀樓楹聯歷史論述頗詳,如“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云南提督馬如龍重建大觀樓,他從宋湘的詩作中(這時宋湘已辭世四十年矣)摘出‘千秋懷抱三杯酒;萬里云山一水樓’兩句作為對聯刻以面世。而且,這副對聯原來也并不是楹聯,而是大觀樓樓后的一副古刻聯。下聯居然署‘丙寅(同治五年)春馬如龍’。這種做法,不免有掠美之嫌”〔11〕。此論述認為“‘千秋懷抱三杯酒;萬里云山一水樓’不是楹聯,而是大觀樓樓后的一副古刻聯”與馬毓林描述存在差異。《鴻泥雜志》中記載宋湘大觀樓楹聯比《郭嵩燾日記》記載早30余年〔12〕。
5.撰寫方式獨特
馬毓林在編撰《鴻泥雜志》時,秉承薄古厚今的撰寫方式,對清代以前的歷史記載簡略,而對南明入滇、沙定洲叛亂、吳三桂叛逆等記載較為詳實。同時秉承因現實而追溯歷史,因歷史而回歸現實的理念。在記載金馬山時,對金馬山的傳說故事進行回顧,而在記載陳圓圓在滇事跡時,回歸現實,這在一定程度上使歷史事件記述顯得更為飽滿。
(三)《鴻泥雜志》的文學價值
1.乾嘉時期云南的詩人群體與詩歌創作
清代云南文學出現繁榮時期,一時詩人涌現、詩歌創作輝煌、詩集著述豐富。《鴻泥雜志》涉及到的詩人、詩歌眾多。從詩歌所反映的內容來看,可分為歷史事件、個人遭遇、寫景抒情、關注民生等。如李小云的《普淜旅館題壁》表現了作者詩才雋妙;杜藕莊的《祿豐道中于役有感》反映作者以開闊、豁達的心胸對待仕途的不暢;張補裳為麗井大使時所著《山居漫興》《山居間詠》《詠負鹽婦》《雪中再過鹽路山感賦》等,反映了民生疾苦。以上三位詩人是乾嘉時期云南詩壇三杰,檀萃尤為推崇,“李刺史書吉,字敬銘,號小云。乾隆四十五年舉人,知宜良,升云州知州,與杜藕莊鈞、張補裳霦同官滇南,時稱詩中三杰。檀默齋萃尤推重之,并列三家于滇南詩話”〔13〕。
2.道光時期云貴交通線上的楹聯文化
《鴻泥雜志》書中共記載11幅楹聯,其內容涉及茶棚、交通、廟宇、樓閣、貢院、衙門等。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時清代中葉滇黔交通線上社會生活、世俗民風、歷史景致等。如浩然閣楹聯,“風月勝游同立定,腳跟登上果;神仙清福俱放開,眼界到中央”。該聯簡潔地勾勒了蒼山、洱海山水一色的風光,展現一幅山光水色圖,令人神往,此聯體現情與景、神與形、意與象之間最高程度的形象統一。王厚慶所撰寫的麗江府長聯,成為麗江境內第一長聯,與大觀樓長聯相仿,意境并不遜色,涉及內容豐富,則為今天人們了解清代嘉慶年間麗江歷史狀況的重要文獻資料。
五、《鴻泥雜志》之局限
由于《鴻泥雜志》是作者見聞記載及當地歷史事件選擇性的編撰,主要目的是“以為良朋聚談之助……以此編代吾口焉”。因此在此書編撰過程中尚存在以下局限。
(一)對史實考證不精
作者認為圓通寺由吳三桂所建,“昆明縣治西偏有大叢林,曰‘圓通寺’,吳三桂所建。”據康熙《云南府志》記載:“在城中螺峰山,建自蒙氏元延祐間,重修,梵宇幽□,石蹬旋折,危欄翠壁,丹巖回視,龍江環抱,北郭其前,則萬家煙火揜映,蒼波浩渺中時,一蹬臨疑其非人間世也”〔14〕。可見其誤。沅江一帶,因氣候炎熱,瓜果菜蔬上市時間早于省城,“省城正月內即有賣茄子、黃瓜、蒜苔者,皆來自沅江。”而馬毓林認為“為瘴氣所熏蒸,食之多致病”,有失偏頗。
(二)在編撰、出版中出現漏字、缺字現象
如在記載蒙肚花時出現別字,“蒙肚花出景東山中,生樹皮土,如蘚。”參照乾隆《云南通志》卷三十《異跡·蒙肚花》校勘,乾隆《云南通志》記載:“出景東山中,生樹皮上,如蘚。”
六、結語
《鴻泥雜志》付梓以來,與當時云南諸類志書游記相比顯得較為普通,加之作者在滇時間有限,辭官不久后過世,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該書的流傳,云南史料匯編等書都鮮有提及,可見此書的傳播極為有限。但是由于該書涉獵內容甚廣,在當前學術繁榮、研究廣泛的背景下,該書在地方文化、地方民族、宗教信仰、滇云詩歌、云貴楹聯研究和旅游資源開發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參考文獻]
〔1〕國立故宮博物院清代宮中奏折及軍機處檔折件,第055471編號.
〔2〕石毓嵩.民國商河縣志〔M〕∕鳳凰出版社.中國地方志集成:山東府縣志輯.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
〔3〕龔延煌.道光商河縣志:卷五〔M〕.刻本.1836(清道光十六年).
〔4〕龔延煌.道光商河縣志:卷七〔M〕.刻本.1836(清道光十六年).
〔5〕卞寶第,李翰章,曾國荃,等.光緒湖南通志:卷一百四十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2837.
〔6〕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一百二十〔M〕.聞石,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0:5143.
〔7〕岑毓英,陳燦.光緒云南通志:卷一百十八〔M〕.刻本.1894(清光緒二十年).
〔8〕錢泳.履園叢話〔M〕.北京:中華書局,1979.
〔9〕王崧,阮元.道光云南通志稿:卷一百十八〔M〕.刊本.1835(清道光十五年).
〔10〕任可澄,楊恩元.民國貴州通志〔M〕∕巴蜀書社.中國地方志集成:貴州編.成都:巴蜀書社,2006.
〔11〕石玉順,李紹飛.大觀樓:名樓名聯名詩賞析中國名樓〔M〕.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5:24.
〔12〕龔聯壽.中華對聯大典〔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8:231.
〔13〕單學傅.海虞詩話:卷八〔M〕.清末刻本.
〔14〕李楷.康熙云南府志:卷十八〔M〕∕鳳凰出版社.中國地方志集成:云南府縣志輯.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378.
Ma Yulin and Hongni Magazine
Ma Yinhang
(Lijiang Teachers College,Lijiang,Yunnan 674100,China)
Ma Yulin created Hongni Magazine with the experiences of the journey from Beijing to Yunnan in Daoguang period.The book is mainly about mountains,lakes,climate,plants,animals,gates,commercial industry,manufacturing industry,officers,couplets, poems,religious beliefs,customs,etc.With the importance in human geography,history and literature,it reflected authors'concern on people's livelihood,reality,and the unity of humanistic thought.Although some deficiencies existed in the book,in spite of theses flaws,this book enriched the research materials of Lijiang history research with value in local culture,nationality,religion,tourism resources development.
Ma Yulin;Hongni Magazine;Yunnan
K280.74
A
2096-2266(2016)11-0064-09
10.3969∕j.issn.2096-2266.2016.11.013
(責任編輯 張玉皎)
云南省教育廳科研基金一般項目(2014Y522);云南省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2015年度古籍整理研究項目“《鴻泥雜志》整理研究”;麗江師范高等專科學校麗江文化科研團隊(麗師政發[2014]71號)
2016-09-02
2016-10-17
馬銀行,講師,主要從事地方文化、歷史地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