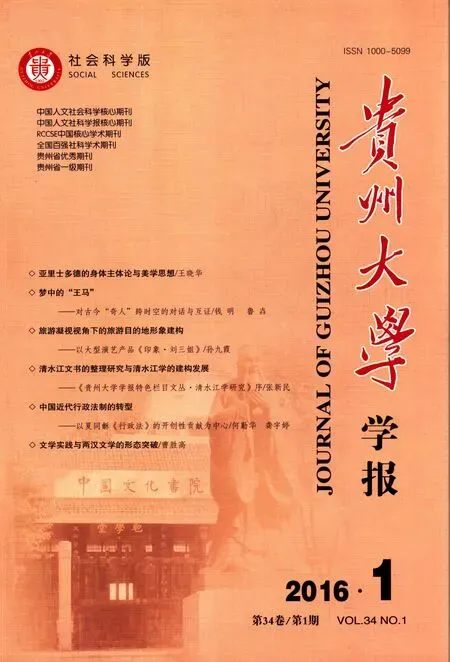“慎獨而致吾之良知”——中年黃綰對王陽明良知學的一種闡釋
張宏敏 李青云
(1.浙江省社會科學院 國際陽明學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 310007;
2.南開大學 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河北 天津 300071)
?
“慎獨而致吾之良知”
——中年黃綰對王陽明良知學的一種闡釋
張宏敏1李青云2
(1.浙江省社會科學院 國際陽明學研究中心,浙江杭州310007;
2.南開大學 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河北天津300071)
摘要:黃綰系浙中王門的一位重要學者,嘉靖七年至嘉靖十二年間任南京禮部右侍郎之職。嘉靖七年王陽明病逝之后,服膺陽明心學的黃綰,通過提攜后學的方式極力宣講良知學,維護陽明心學的“致良知”之教,從而使得良知本體所蘊含的“獨知”“慎獨”的功夫路數得到充分地揭橥與闡發。“慎獨而致吾之良知”,則是中年黃綰對陽明良知學題中之義的一種闡釋。
關鍵詞:王陽明;黃綰;良知;慎獨;獨知;
黃綰(1480—1554),字宗賢,號石龍,學者稱久庵先生,浙江臺州人。作為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的黃綰,青年時期師從理學名家謝鐸而“克苦”用功于程朱理學。中年時期與王陽明、湛若水等心學大家結盟共學,曾一度服膺于陽明“致良知”之學,并創辦“石龍書院”致力于在浙南一代傳播弘揚陽明學。陽明歿后,多次上疏為陽明爭取“名分”,撰有《陽明先生行狀》,輯刊過陽明存世文獻,還嫁女于王陽明哲嗣王正億并撫養之長大成人。晚年因出使安南未成而“落職閑住”于黃巖老家,隱居翠屏山,以讀書、著書、講學終老,并能并自覺地開展對宋明諸儒學術思想的批判,從而提出具有復古傾向的有自家特色的“艮止執中”之學,堪稱中晚明時期“王門”內部自覺批評性修正心學之“先驅”。①筆者在2008至2014年7年間,傾盡全力,展開了對海內外關于黃綰存世著作文獻的查訪、裒輯,最終編校整理完成了40余萬字的《黃綰集》,2014年12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作為《陽明后學文獻叢書》系列出版。
黃綰在正德五年(1510)冬與王陽明在京師結交共學之時,只是基于“圣人之學”的共同志業;在嘉靖元年秋(1522)由臺州奔赴紹興師從王陽明,則是因為王陽明作為“豪杰之士”已經正式揭其為學宗旨——“致良知”之教而服膺之①王陽明學說的根本宗旨——“致良知”的解讀,參見當代陽明學研究著名專家吳光教授的“從‘致良知’到‘行良知’”:論黃宗羲對王陽明“良知”說的轉型與貢獻見《國際陽明學研究》第一卷,第124-138頁及《王陽明的思想學說及其當代意義》(文匯報·思想人文,2013年6月24日)。。嘉靖元年至七年間(1522—1528),黃綰通過與王陽明面晤交往、書信論學的形式,砥礪學問,此時的黃綰已能把握陽明心學的三大核心命題——“良知”“親民”“知行合一”。嘉靖七年王陽明病逝,嘉靖七年至十二年間(1528—1533),任南京禮部右侍郎之職的黃綰,主要通過提攜后學、勸勖上進的形式,在南都極力維護師門“致良知”之教,從而使得良知本體蘊含的“獨知”“慎獨”的功夫路數,得到充分地揭橥與闡發。
本文論述的核心話題是:“慎獨而致吾之良知”,系中年黃綰對陽明良知學題中之義的一種闡釋。
一、“獨知”“慎獨”范疇的文獻學考察
在王陽明的“致良知”之教中,有“獨知”“慎獨”的范疇。本文在論述中年黃綰在闡發業師王陽明的“良知獨知”論之前,有必要對“獨知”和“慎獨”這一對范疇進行文獻學意義上的爬梳。
一般以為,“獨知”的學理依據,即是《大學》《中庸》“慎獨”之“獨”和《孟子》“良知”、《大學》“致知”之“知”,二字結合,即曰“獨知”。如所周知,孟子的“良知”說出現于《孟子·盡心上》:“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1]518在孟子這里,“知”是一種能力認知抑或判斷能力,“良知”則是人人天生具備的一種向善的先驗道德力,無需經過后天教化引導,自然生成,宋儒程頤就認為:“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于天,不系于人。”[2]
《大學》中“致知”,出自于“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文。一般以為,“致知”之“知”與“理”相當,它不僅包括對于自然、社會的客觀規律(天理)的認識與掌握,還在于恢復一個人先天具有的向善的道德本性的道德踐履。如是而論,《大學》“致知”之“知”即趨同于《孟子》“良知”之“知”。朱熹在《大學章句》中“竊取程子之意”而加以解讀,并對“格物致知”進行了發揮,即眾所周知的名句——“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1]10
“慎獨”一詞出現于《禮記》之《大學》《中庸》。《大學》在“釋誠意”之時,兩次提到“君子必慎其獨也”云云:“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閑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3]801-820一般以為,“獨”即生命個體“獨處之地”,朱熹《大學章句集注》就以為:“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修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于己,不可徒茍且以殉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獨知之者,故必謹之于此以審其幾焉。”[1]11“慎獨”即“謹慎于獨處”,一個人在獨處之時須小心謹慎,因為“慎獨”是達至“誠意”之境的不二法門。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通常把“慎獨”理解為“在獨處無人注意時,自己的行為也要謹慎不茍”[4],或“在獨處時能謹慎不茍”[5]。詳而論之:“慎獨”是指個人在獨自居處的時候,也能自覺地嚴于律己、謹慎地對待自己的所思所行,“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時時刻刻注意自我防止、防備有悖道德的欲念和行為發生,以求切實做到表里如一、言行一致。與學界通行的解讀不同,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梁濤教授在其代表作《郭店竹簡與思孟學派》第五章第三節“郭店竹簡與‘君子慎獨’”行文中[6],根據《郭店竹簡·五行》篇“能為一,然后能為君子,君子慎其獨也”的出土文獻材料,通過細致的分析、全面的考察,提出“慎獨”的本意應是“誠其意”,以往人們(包括朱熹)對“慎獨”的理解有不準確、不到位的地方。那么,我們不妨將“慎獨”定義為:“慎獨指內心的專注、專一狀態,尤指在一人獨處、無人監督時,仍能堅持不茍。”[7]
與《大學》一樣,《中庸》“首章”就有“君子慎其獨也”的命題:“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3]691在《大學》這里,“慎獨”特指修養“誠意”的工夫;而在《中庸》中,“誠”則成為“道”之本體,“誠者,天之道”,而君子成就“誠”之本體的修養工夫也應用功于“慎獨”。為了強調“慎獨”之時,君子修德的具體工夫,《中庸》末章又援引《詩經》之文以呼應之:“《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于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1]55-56這里,《中庸》作者先引《正月》之詩以論證君子修養德性,重在“慎獨”,又引《抑》之詩以說明君子的“慎獨”工夫即使在外人不易察覺之處也不應該疏忽荒廢,總之,“君子之誡謹恐懼,無時不然”[1]56。
為了解農村農戶對小額信貸的使用情況,2018年7—8月,隨機走訪了溝張村67戶村民。從農戶的文化程度、家庭年收入、家庭收入來源、信貸金額、貸款期限、民間(私人)借貸等方面獲取數據。通過對相關數據的梳理歸納,探尋農戶在“小額信貸”運行中存在的問題,針對問題客觀分析原因,并就未來“小額信貸”進一步完善提出相應的對策。
二、王陽明的“良知獨知”論
在完成對“慎獨”“獨知”等古典儒學范疇的檢討之后,下面我們再來對王陽明良知學語境之下的“獨知”觀念進行探析。王陽明《傳習錄》第120條、317條*此處對《傳習錄》條目編碼之稱,據陳榮捷2009年版《王陽明傳習錄詳注集評》。中有兩處“獨知”提法,檢索其出處,不難發現,其與《大學》《中庸》的“慎獨”說存在關聯。先看第一處即《傳習錄》第120條王陽明與高第黃正之之間的師徒問答:
正之問:“‘戒懼是己所不知時工夫,慎獨是己所獨知時工夫。’此說如何?”
先生曰:“只是一個工夫,無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人若不知于此獨知之地用力,只在人所共知處用功,便是作偽,便是見君子而后厭然。此獨知處便是誠的萌芽,此處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一是百是,一錯百錯,正是王霸、義利、誠偽、善惡界頭。于此一立立定,便是端本澄源,便是立誠。古人許多誠身的工夫,精神命脈全體只在此處。真是莫見莫顯,無時無處,無終無始,只是此個功夫。”[8]84-85
毋庸置疑,王陽明、黃正之師徒之間對話的文本依據就是《中庸》“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句。王陽明反對在力行“慎獨”工夫時,區分“己所不知時”與“己所獨知時”,以為兩者的工夫的“只是一個”,即無論“有事”“無事”,慎獨工夫皆不可放棄,否則“便是作偽”,唯有如此,才可成就“誠”的精神境界。正是因為“獨知處便是誠的萌芽”,所以王陽明在《傳習錄》第317條討論“誠意”與“致知”的關聯時,特別強調了“獨知處”正是“吾心良知處”:
先生曰:“……誠意之本,又在于致知也。所謂人雖不知,而己所獨知者,此正是吾心良知處。然知得善,卻不依這個良知便做去,知得不善,卻不依這個良知便不去做,則這個良知便遮蔽了,是不能致知也。吾心良知既不能擴充到底,則善雖知好,不能著實好了;惡雖知惡,不能著實惡了,如何得意誠?故致知者,意誠之本也。”[8]220
明季大儒劉宗周在《陽明傳信錄》中摘錄王陽明此段語錄之“所謂人雖不知而己所獨知者,此正是吾心良知處”后,給出了“良知只是獨知時”的簡短評論[9],并以為這是王陽明的一大創見。然而有陽明學者(以王龍溪為代表)對“獨知”的解讀更加突出其“玄妙”的一面,有“近禪”的傾向,劉宗周對此反駁,并為王陽明是論正名:“先生(王陽明)之言曰:‘良知只是獨知時。’本非玄妙,后人(王龍溪)強作玄妙觀,故近禪,殊非先生本旨。”[10]15
其實,王陽明在《答人問良知二首》詩歌之中已對“良知獨知”論作出了“一番充滿詩意的抒發”(吳震語):“良知即是獨知時,此知之外更無知。誰人不有良知在,知得良知卻是誰?知得良知卻是誰?自家痛癢自家知。若將痛癢從人問,痛癢何須更問為?”[11]827《詠良知四首示諸生》也有“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基。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持缽效貧兒”的詩句[11]826。總之,王陽明對《大學》《中庸》的“慎獨”及朱熹《集注》的“獨知”進行了發揮,在堅持“良知”本體的基礎之上,融攝“慎獨”“致知”而發展、演繹“獨知”之論。當然,在王陽明這里,“獨知”仍就工夫論的意義而有,乃是達至“誠”之境的一種方法、路徑。
王畿在《答洪覺山》書信中提出了自己對王陽明“良知即是獨知”的認識,即主張以“獨知”為本體、以“慎獨”為工夫:“良知即是獨知,獨知即是天理。獨知之體,本是無聲無臭,本是無所知識,本是無所拈帶揀擇,本是徹上徹下。獨知便是本體,慎獨便是功夫。……此便是未發先天之學,非有二也。”[13]262這里,王畿從“未發先天之學”即“先天之體”的角度闡釋“獨知”,毋庸置疑,這是一種先驗論的觀點;但是王龍溪把“獨知”(“一念獨知處”)視為“天理”之本體,就顯得未免太絕對了:“獨知者,非念動而后知也,乃是先天靈竅,不因念有,不隨念遷,不與萬物作對。慎之云者,非是強制之謂,只是兢業保護此靈竅,還他本來清凈而已。”[13]264其《水西會約題詞》又云:“今日良知之說,人孰不聞,然能實致其知者有幾?此中無玄妙可說,無奇特可尚,須將種種向外精神打并歸一,從一念獨知處樸實理會,自省自訟,時時見得有過可改,徹底掃蕩,以收廓清之效,方是入微工夫。”[13]29《新安福田山房六邑會籍》:“吾人今日之學,亦無庸于他求者,其用力不出于性情耳目、倫物感應之跡,其所慎之幾不出于一念獨知之微。是故一念戒懼,則中和得而性情理矣;一念攝持,則聰明悉而耳目官矣;一念明察,則仁義行而倫物審矣。慎于獨知,所謂致知也;用力于感應之跡,所謂格物也。” 在此,王畿多次強調了成就圣賢之學當于“一念獨知之微”處用功,這也是劉宗周批評的王畿“禪學化傾向”的癥結之所在。
當代陽明學研究學者吳震教授在《傳習錄》(精讀)一書中,以為王陽明“良知獨知”“這個觀點突出了良知是一種內在的道德能力,這就極大地提升了良知的自主性地位。然而,在強調良知獨知的同時,如何防止良知獨知理論成為個人逞一己之私的借口,卻是陽明良知學所面臨的重大理論問題”[14]。筆者對此表示贊同。吳震接著又提到:“及至明代末年,有不少學者在反省和批判心學之際,就觀察到心學末流有一種嚴重流弊,即往往以個人一己之‘情識’視同良知,究其根源,就是良知自知而他人莫知的觀念在作祟。然而應該指出的是,這些批評基本上是來自良知心學之外的批評。”這里,“來自良知心學之外的批評”的觀點則是可以商榷的,因為本文主人公即生活在明代中期的浙中王門學者黃綰,已經“觀察到心學末流有一種嚴重流弊,即往往以個人一己之‘情識’視同良知”,并在晚年時期積極開展了對陽明心學流弊的批判,并與王龍溪就此展開了多次論辯(筆者另有專文詳論,茲不展開)。
三、黃綰對王陽明“良知獨知”說的“受用”
當代新儒家大師牟宗三認為王陽明的“良知”觀念具有主觀性、客觀性、絕對性。“知是知非”是良知的主觀性,“良知即天理”是良知的客觀性,良知是“乾坤萬有基”是良知的絕對性。”[15]沿用牟氏的觀點“接著說”,陽明良知“獨知”義即要闡發良知的主觀能動性。承上所述,黃綰在任職南京禮部右侍郎期間(嘉靖七年至嘉靖十二年),對業師陽明先生的良知之學(“致良知”之教)進行了“無條件”的“受用”與宣講,并且提出了自己對“慎獨”“獨知”的認知。本文以為黃綰的“慎獨”“獨知”不是“照著(王陽明的“獨知”)講”而是“接著(王陽明的“良知”)講”。茲有例證如下:
黃巖后學王敦夫習舉業于南京國子監,學成歸鄉之時,造訪鄉賢黃綰,“求學問之實”;黃綰有《贈王生敦夫歸山中》文,便以王陽明“致良知”說為學術基點,以“心”“性”“情”論為基礎,重新闡釋《大學》《中庸》的“慎獨”學說,提出了從“良知”→“獨知”的心學求證模式,并且得出“‘惟精惟一’實萬世圣學之源”的結論:“上帝降衷于人,皆有恒性,性之清靜而至真者曰情。斯情也,即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仁、義、禮、智之實,乃堯舜與愚夫愚婦之所同。亙天地、歷萬變而不可磨滅者,惟此而已。故命之曰良知。方其知也,他人所不知,惟己所獨知。古之君子凡有言也、凡有行也,必于此而致思,故見于彝倫日用,一惟天則之依,弗使毫發私意之間,故曰‘惟精惟一’實萬世圣學之源。”[16]黃綰此處對“良知獨知”的解讀,基本沿襲了乃師王陽明的觀點。
黃綰在《贈鄒謙之序》文中論述了王陽明作為“豪杰之士”,所創“良知學”延續孔孟之道、宋儒之學的“道統”意義:“陽明先生究洙泗言仁之教、鄒孟性善之說,以闡良知之旨,謂致知為誠意之本、格物為致知之實,知乃良知、即吾獨知之知,物非外物、即吾性分之物,慎于獨知、盡于物則,則為物格、知至而意誠,著知行不可以兩離、明體用而當歸于一源以曉學者。”[17]據此亦知,此時的黃綰有接續陽明良知學“道統”的心跡。
基于陽明“致良知”之教的“道統”意義,中年黃綰作為陽明良知學傳人,遂不遺余力地以之教化后學。比如“雖未嘗受業陽明之門而能深為陽明之學”的吳興后進邵文化,至南都游學,“自信于良知之學”,時常與黃綰就陽明“良知之旨”進行切磋;在歸鄉之時,黃綰有《贈邵文化》文。此文中,黃綰首先對陽明良知說的學術地位予以認可,有“圣人之道自孟子殆而失傳幾二千載,至宋程伯子始啟其端,迨我陽明先生乃闡良知之旨。學者方如醉夢得醒,而昧者猶以為疑”云云。而中年黃綰已經通過對“圣人之道”的克苦修證,藉此印證出陽明先生的“致良知”即孟子所謂“擴充四端”、孔子所謂“克己復禮”,簡言之,皆“慎獨”也。進而言之,曾子傳《大學》、子思作《中庸》,皆以“慎獨”為要;所以陽明“致良知”之教得以“圓滿成就”的關鍵就在“慎獨”工夫的推進:“惟從事于慎獨,則良知明而至誠立,不待外求而經世之道、位育之功在此矣。昔云‘漢儒不識誠’,非其不識,惟不由慎獨致工,則誠無所在,此其所以不識也。由此觀之,慎獨之學不明于世久矣。囂囂而不已者,豈無故哉!”[18]這里,黃綰已經把王陽明的“良知”等同于“慎獨”。其實在王陽明的良知學體系之中,“致良知”還等同于“慎獨”,比如王陽明在解答高足鄒守益疑惑之時有論:“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獨,即所謂良知也;慎獨者,所以致其良知也;謹慎恐懼,所以慎其獨也。”[12]1382-1383這里,從“本體—功夫論”意義上講,我們可以把王陽明的“致良知”與“慎獨”之間劃等號。
江右王門后學何廷仁曾攜永豐后學朱效才、朱效忠二生游學之南都,時任職南都禮部的黃綰接待了何廷仁一行,并與之論學;此時,黃綰便王陽明良知學教導朱氏二生:“今夫良知在人,弊于氣習,亦何異此?故圣人為教,必使人于獨知之際,因其本心之明,察其私欲之萌,既切復磋,既琢復磨,惟日孜孜,以極‘精一’之工,則私欲凈盡、天理純完,所以立天下之大本而經綸天下之大經,豈有他哉!”[18]5不難發現,對于宋儒的“理欲之辨”,黃綰不加回避,提出了“凈盡人欲,純完天理”即“去私意、純天理”,于“獨知”之中把握“良知”的修養路徑。此外,黃綰還與浙中王門另一學者葉良佩就“陽明先生之所謂良知者”與之論學,有贈文《良知說》[18]5-6。在黃綰看來,“人人自足,圣愚皆同”的良知有兩大特征:“良知人人自足”“良知固無不知”。若要體證良知,必須向內即“獨知之中”用功,經過一番慎獨的修養工夫,即由“慎獨而致吾之良知”。而《中庸》所言“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的工夫指向亦即是人人自足的良知。藉此,黃綰批評了兩種錯誤的為學路徑:一是“舍其良知、徒事聞見以為知”,此謂“支離而非學”;一是“知求良知,溺志忘情、任其私意以為知”此謂“虛妄而非學”。
黃綰在《勸子侄為學文》中,以圣人之學勸勉子侄后輩,重申了“慎獨以致良知”的命題:“夫所謂學者無他,致吾良知、慎其獨而已。茍知于此而篤志焉,則凡氣習沉痼之私皆可決去,毫發無以自容。天地間只有此學、此理、此道而已。明此則為明善,至此則為至善。”[18]6-7黃綰還在《贈應仁卿序》中著重闡述了行“慎獨”工夫以“致良知”的道理:“人之生也,惟性為貴。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不以堯舜而增,不以眾人而損,化于俗而后私意汨之。私意之在今日,雖賢智不免,慎獨所以辯私、克己,乃以作圣。慎之于獨知之中,克之于方萌之際,夙興夜寐,念茲在茲,造次顛沛,無時而離,由仁義行,良知不息,此謂格至之工、天德之學所以拔乎流俗而異于伯術、鄉原者也。”[19]12-13藉此,黃綰又反對了視“情欲意念”為“良知”的觀點:“夫所謂良知者,乃天命本然之良心,四端固有之至善,不涉私邪,不墮意見,循之則圣,悖之則狂。若以任情自恣之心揣量模擬之,似皆曰良知,是又與于不仁之甚者也。”[19]13應該指出,黃綰之所以屢屢反對以“情欲意念”“溺志忘情、任其私意”為“良知”的提法,主要是針對泰州學派的主張。時有學者以“作圣之功”請教黃綰,黃綰乃以“圣學只以忠信為主,但于庸言庸行之間,驗之良知。如何方是忠信?如何不是忠信?于此茍分曉,則作圣之功在是矣”作答[17]2,意在強調“良知”之功在日常生活之中進行,并非憑借玄空冥想所能成就。
與此同時,時有學者對陽明心學之“良知”“知行合一”說予以質疑。此時,作為中年黃綰最為陽明良知學的忠實信徒,予以辯駁,即追溯圣學之源,從儒家經典《孟子》《尚書》之中爬梳出“良知”“知、行”的原始義,從而對時人的的質疑予以回應。這集中體現在《裘汝中贈言》文中[20]12-13。嘉靖十二年(1533)夏間,黃綰好友王廷相離開南都北上任職,黃綰有《紀言贈浚川子》,提出“今日經國、知人、濟變之道,只在于至誠”的論點,而其予以論證的依據則是于“獨知”之地尋求作為“獨知”之理的“良知”:“至誠之本只在獨知之地,獨知之理是謂良知,是所謂萬物皆備于我。于此慎察而精思之,不使一毫習染之私得間之,則為‘精一’之傳、致知之學。”[20]15應該指出,與黃綰、王陽明同時代的著名學者王廷相對陸王心學采取了一種排斥的態度,但是時任職南都的黃綰還是希望摯友王廷相能夠接受乃師陽明先生的“致良知”之教。
而在嘉靖十二三年間(1533—1534),隨著對陽明良知學“獨知”“慎獨”義理解的加深,再加上對“四書五經”等儒家元典的不斷用功;從中年轉向晚年(55、56歲)的黃綰*嘉靖十二年七月,黃綰由南京禮部右侍郎升任京師禮部左侍郎(詳見拙著《黃綰生平學術編年》2013年版,第250頁)。至京師任職之后,黃綰不再像當年在南都禮部任職之時(嘉靖八年至嘉靖十二年),維護乃師陽明先生的“致良知”,其學思理路則由“心學”轉向了“經學”,黃綰晚年經學名作《四書五經原古》即是明證。該書創作主旨可參閱《國際陽明學研究》第三卷,第295-301頁拙文《黃綰經學、政論著作合考》。有意識地擺脫對王陽明心學的依賴,進而主張以《尚書》中“‘精一’之傳”作為“圣賢之學”之根源。比如,黃綰在嘉靖十三年(1534)初所成《寄羅峰(九首之九)》有云:“大人之道,只在正己。正己之要,只在慎獨。獨者,獨知也。獨知之地,四端所在,萬理攸具。孟子所謂‘萬物皆備于我’是也。于此致思則曰‘惟精’,于此歸縮則曰‘惟一惟精’。‘惟一’乃堯舜學問之傳也。曰‘志道’、曰‘據德’、曰‘依仁’,乃孔門學問之事也。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此指點精一用工之方也。夫非思則不精,非精則不一,非一則此心之動,紛紜無已,其可建皇極而立天下之大本乎?于此有立,大人之道盡矣。”[21]12“‘惟一’乃堯舜學問之傳”云云,也說明黃綰在嘉靖十三年左右可能受到“他者”(主要是王廷相)*據筆者考證,嘉靖十三年左右,黃綰曾請王廷相為其在浙南黃巖紫霄山創辦的石龍書院作“學辯”即《石龍書院學辯》,其中評論陸王心學、程朱理學為:“有為虛靜以養心者,終日端坐,塊然枯守其形而立,曰:‘學之寧靜致遠在此矣。’有為泛講以求知者,研究載籍,日從事乎清虛之談,曰:‘學之物格知至在此矣。’” (王廷相著,王孝魚點校:《王廷相集》)在王廷相的思想(道學)體系之中, “仲尼之教”系衡量萬世的絕對標準與唯一依據,孔門之學代表了圣人之(道)學的正統。無論程朱理學抑或陸王心學攙和了佛禪之學的“基因”,故而偏離了“孔門之學”,皆是“異端邪說”。陸王心學家作為“虛靜以養心者”追求“終日端坐”、“塊然枯守其形而立”,此種功夫修養路徑無異于佛教的“禪定”;程朱理學家。影響而打算另辟“道統”,以賡續“圣人之學”。
值得注意的是,嘉靖十三年,原本在京師任職的陽明高足王畿離去南下,至南京任職方主事。臨別之際,同志之士(京師陽明門人)請時任禮部左侍郎的黃綰贈言,黃綰有《贈王汝中序》[22]17-19,有論者以為此“序”文表明黃綰“已經開始對龍溪的思想表示異議”[23]。實則《贈王汝中序》文,也標志著黃綰在完全掌握、“消化”了陽明先生“良知—獨知”說精髓的基礎之上,開始對以王畿為代表的陽明后學的佛教化(逃禪)傾向“宣戰”;且以“儒佛之辨”為契入點,以對宋明諸儒進行“批判”,進而挑戰程朱理學的“道統”地位,藉此主張返歸儒家經典(六經、四子)尋找“圣學”之宗旨,進而重構儒家經學(經典)信仰系統的價值意義。
參考文獻:
[1]〔宋〕朱熹.四書集注[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2]〔宋〕程顥,程頤.二程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1:20.
[3]楊天宇.禮記譯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4]商務印書館編輯部.辭源[M].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624.
[5]夏征農.辭海[M].縮印本.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 1201.
[6]梁濤.郭店竹簡與思孟學派[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2008:292-300.
[7]梁濤.郭店竹簡與“君子慎獨”[N].光明日報,2000-09-12.
[8]陳榮捷.王陽明傳習錄詳注集評[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
[9]吳光.劉宗周全集(第5冊)[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87.
[10]吳光.黃宗羲全集(第7冊)[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15.
[11]吳光,錢明.王陽明全集[M].新編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12]董平.鄒守益集[M].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
[13]吳震.王畿集[M].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
[14]吳震.傳習錄精讀[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117.
[15]牟宗三.從陸象山到劉蕺山[M].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4:217-220.
[16]黃綰.石龍集(卷8)[M].臺灣國家圖書館,藏明嘉靖年間刻本:15-16.
[17]黃綰.石龍集(卷20)[M].臺灣國家圖書館,藏明嘉靖年間刻本:14-15,2.
[18]黃綰.石龍集(卷9)[M].臺灣國家圖書館,藏明嘉靖年間刻本:4-7.
[19]黃綰.石龍集(卷12)[M].臺灣國家圖書館,藏明嘉靖年間刻本:12-13
[20]黃綰.石龍集(卷10)[M].臺灣國家圖書館,藏明嘉靖年間刻本:12-13,15.
[21]黃綰.石龍集(卷19)[M].臺灣國家圖書館,藏明嘉靖年間刻本:12.
[22]黃綰.石龍集(卷13)[M].臺灣國家圖書館,藏明嘉靖年間刻本:17-19.
[23]彭國翔.良知學的展開:王龍溪與中晚明的陽明學[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書店,2005:529.
(責任編輯周感芬)
中圖分類號:B248.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5099(2016)01-0033-07
作者簡介:張宏敏(1982—),男,河北邢臺人,哲學博士,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國際陽明學研究中心秘書長。研究方向:王陽明與陽明學派。李青云(1982—),女,河北邢臺人,博士研究生,講師。研究方向:中國政治思想史。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陽明后學文獻整理與研究”(15ZDB009)。
收稿日期:2015-11-18
國際DOI編碼:10.15958/j.cnki.gdxbshb.2016.0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