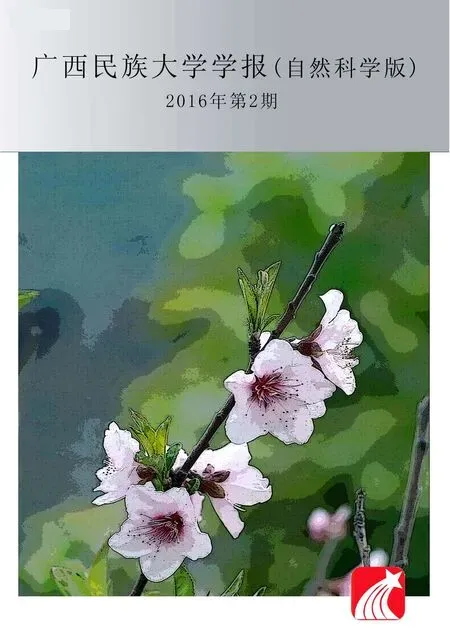老驥伏櫪 志在編史
——周嘉華教授訪談錄*
萬輔彬/問,周嘉華/答
?
老驥伏櫪志在編史
——周嘉華教授訪談錄*
萬輔彬/問,周嘉華/答
編者按:周嘉華先生原籍浙江,隨家人在廣西長大,并畢業于廣西大學.幾乎每年都來廣西看望家人,也順便多次來廣西民族大學講學.是化學史和釀酒史家,曾任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科研處長和中國科技史學會秘書長,獨著、合著40余種專著,發表論文50余篇.他也是個很有故事的人,本刊早就想做他的訪談,他很謙虛,堅持“往后排”,終于在今年接受訪談.這篇訪談是“一杯釀了很久的美酒”,歡迎大家“品嘗”.
萬輔彬(萬):周先生,聽說你退休至今,依然很忙,成果累累.做到了老有所為,過得很愉快.
周嘉華(周):是的,從2002年退休以來,課題不斷,總是有點事可做.剛退休時,忙于還“欠債”.一是我所承擔的,2000年被列入“中國科學院知識創新工程項目”的《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史研究叢書》中的《永利與黃海》一書的編寫.這本書是由化工部大連化工研究設計院編審陳歆文和我兩人編寫.陳先生是長期從事中國近現代化工史研究的專家,是著名的侯德榜研究專家.這本書由山東教育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之后,我又繼續完成我所承擔的,被中國科學院正式立項為“九五”重點項目“中國傳統技術研究”的兩個子項目:《中國傳統工藝全集》(簡稱《全集》)和《中國古代工程技術史大系》(簡稱《大系》).在《全集》中,我和輕工部高級工程師包啟安合作完成《釀造》卷的編寫.包啟安先生長期從事發酵技術,特別是調味品的科研和生產管理,是我國這領域的著名專家.該書已于2007年由河南大象出版社出版.在《大系》中,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后德俊和我共同合著《中國古代日用化學工程技術史》.后先生寫漆器、玻璃,我寫鹽、糖、酒、醋,該書于2011年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從2006年開始,我又參加了由文化部主持的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第一、二批國家名錄評審工作.借此機緣,我加強了對自已熟悉的領域內非物質文化遺產——傳統手工藝的調研工作,跑了許多地方和企業,考察了眾多知名項目的歷史與現狀,收集并整理了相關資料,幫助完成了十幾項申請項目的資料整理和審定的工作.有了這些新的資料,加上原先的研究基礎,我和我所的李勁松、關曉武及北師大的朱霞共同承擔了《中國傳統工藝全集·農副畜礦產品加工》一書的編寫.這本書經過近6年的努力,已于2016年3月由河南大象出版社出版.2011年,化工界幾位同仁和我一起建議:在籌建中國化工博物館的同時,應該編寫一套《中國化工通史》作為建館的基礎建設.這一建議得到中國化工集團公司的重視和支持,并給予編寫工作創造了條件.經過大家3年的努力,終于在2014年交出了第一批成果,由我主筆的《中國化工通史·古代卷》及參與寫作的《中國化工通史·行業卷》就是這批成果之一,并由化學工業出版社于2014年8月出版.計劃中還要編輯《人物卷》《企業卷》《區域卷》《數據卷》等尚待努力.近三年,又應出版社之約先后完成了《中國傳統釀造:酒醋醬》(國家十二五規劃重點圖書),已由貴州民族出版社于2014年7月出版、已完稿的《大眾化學化工史》,已由山東科技出版社于2015年8月出版.應“自然國學叢書編委會”之約完稿的《酒鑄史鉤》,已由深圳海天出版社于2015年7月出版.已修定完稿的《文物與化學》(第二版),也將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總之,這12年內完成了專著9種,論文及其他合作文章十多篇.
萬:許多人退休了,就放下手頭的工作,過著逍遙自在的休閑生活,并認為這種無負擔的生活很愜意.你卻不一樣,有什么不同想法?
周:在我們研究所,像我這樣“退而不休”的研究人員很多,例如華覺明、戴念祖,郭書春,陳久金、宋正海、董光壁、楊文衡等,席澤宗一直忙到81歲,當然,他是院士,不退休,2008年突發腦溢血過世,是忙死的.華覺明今年也82年了,現在比我還忙.這大概是與職業有關.對于過好退休后的晚年生活,每個人都會根據自已的生活環境、身體條件、個人志趣做好自已的安排.不可能再像上班時,有社會的分工、個人的職責及組織的督促.因此,只能是因人而異,各取其樂.我是個書呆子,不太愛動,每天都喜歡看點書報,現在則每天都要扒在電腦前看上幾小時,從書中尋樂.除了了解天下事,使自已不脫離社會外,還可以增知識長見識,使自已不落伍,大腦得到不斷地運動,可能就不容得老年癡呆.這種生活不虛度時光,就顯得有質量了.做點自已喜愛的力所能及的研究,是一舉多得的好事.每當完成一項研究,取得一點成果,自已也會喜不自禁,提高了生活的樂趣.更何況,還有一個職業特點的緣由,即從事科技史研究是需要長期、大量的資料積累,掌握了資料才可言此論它,才有發言權.掌握資料愈多,研究愈深入,對一個問題的認識就愈充分,討論中才能做到有眼有板,言之鑿鑿.再加上我們過去收集和積累的許多資料需要斟酌或更正,要么還需要補充發掘,以求取得更深更準確的認識;要么還需要進一步消化理解,獲得更科學的認識,總之,過去的許多課題研究需要,也有可能繼續深入研究;過去研究的成果也需要深化或擴展.正是基于這種認識,我在退休之后,在休閑養生的前提下,隨心所欲,力所能及地做點課題研究,成為生活中一項快活的點綴.
萬:你剛才講有關退休生活的思考和安排,包括了對自已退休前的科研工作的總結和補充.請您進一步發點感慨、談談退休后積極養生的認知?
周:好的,退休之后,生活上不愁吃不愁穿,沒有壓力.閑暇之際,總會對自已過去的往事進行回顧與思考.在這種反思中,往往會發現一些生活的真諦.例如,我這輩子從事的事業究競如何?有什么價值?活得值不值?這可能是許多老人都會思考的一個問題.我是1964年廣西大學化學系畢業,當時我們都是堅定地表示:絕對服從組織分配.因此,對自已將從事的事業是沒有預見的.系里宣布我被分配到《新建設》雜志社(實際上是搞錯了,當我到北京《新建設》雜志報到時,才告訴我,我應該去中國科學院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室報到.當時這兩個單位同屬于哲學社會科學部)時,我還不知道我將干什么.來到北京,到了位于深宅大院--九爺府(即孚王府,清朝咸豐之弟孚王的宅院)里的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室報到后,才發現這是一個僅有數十人的小小研究單位,并知道自已要研究歷史了.學理科的,研究歷史是乎有點轉行,但看到同來的14位同事都是理工科,心里稍安.我們這批人可能是建室(所)以來最大一次擴容.三位研究生,他們是華覺明(清華大學1959年畢業,導師是中國歷史博物館的王振鐸先生)、陳美東(武漢測繪學院畢業,導師是北京大學葉企孫先生,)、許傳松(南京大學畢業,導師是北京大學侯任之先生),大學生:陳久金、劉金沂(南京大學)、戴念祖、林文照(廈門大學)、劉子央(河南大學)、宋正海(北京大學)、張秉倫(安徽大學)、何堂坤及我(廣西大學).楊文衡、陳瑞平(中山大學)是先勞動鍛煉,65年才來室報到.1965年底又從《新建設》雜志編輯部轉來同是64年大學畢業的郭書春(山東大學)、金秋鵬(廈門大學)、鄭錫煌(中山大學).這17條漢子的加入,似乎使當時的研究室添加了活力,充滿了生機.事實上也是如此.這17個人除了有3人(許傳松、張秉倫、劉子央)因解決夫妻兩地分居而調離外,個個都通過自已的努力成為研究所的骨干和各研究領域的中堅.
萬:應該說當時的這批年輕人后來成為中國科技史界的精英.
周:實踐證明研究科學技術的歷史是需要學理工科的,他們與學文史哲的各有所長,在研究科技史中常常是互補的.學理工科的,要自覺地加強歷史學、哲學等人文學科知識的補強;而學文科的,則需要補學數理自然科學,相對來說他們的難度就較大.
萬:科技史是交叉學科,需要文理融通.從某種意義上說,真正做好科技史研究也是很不容易的.
周:是的,正因為如此,我們這批年輕人來到學部后不久,學部副主任劉導生(當時學部主任是潘梓年)給我們做了一次報告,他要求我們這些新來者,準備好好坐下來,做八年的基本功訓練,把研究的基礎打好,形象地描繪做頭尖(善于鉆研)屁股大(基礎扎實)的研究人材.可惜的是,正當我們摩拳擦掌、全力以赴地進入角色后不久,在階級斗爭緊抓不懈的號角下,1964年9月我們全室除老弱病殘外,全體人員整隊前往安徽壽縣參加農村的四清運動 (楊文衡、陳瑞平、郭書春、金秋鵬、鄭錫煌還沒來室) .1965年4月,四清工作一結束,我們10位年輕人加上外國文學所的四位同志以及主動要求留下來的薄樹人,還有領導我們的團支書,一共16人留在壽縣九龍公社繼續參加勞動鍛煉.1965年11月底,我們回所不久,因于光遠(當時囯家科委副主任,中宣部科學處處長兼哲學所自然辯證法研究室主任)要編寫《世界工業史》等科普巨作,戴念祖和我被借調到哲學所,在于光遠手下打雜.這當然是難得的學習機會,但好景不長.工作還沒入境,毛主席又指示:“下鄉滾泥巴”,于是學部再安排我們到北京門頭溝搞四情,剛集訓完還沒進村搞四清,一聲令下,我們又立即撤回學部,原來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學部的文化大革命在北京乃至全國都是聞名的,對于我們既是劫難,又是磨煉,說起來就話長了,這里就不講了.1970年過完春節不久,根據中央的一號命令,我們又在工軍宣隊的領導(押解)下,整隊前往位于河南息縣的“五七干校”勞動.在干校的生活,楊絳(錢鐘書的夫人)所寫的《干校六記》所描述的干校生活已做了形象的描述.(但是書中的介紹比起我們實際經歷的那要遜色多了).直到1972年夏天,根據總理指示,學部的大批人馬才從干校返京.回京后仍然是運動不斷.總之,在這長達8年多的歲月里,我們是不允許搞業務的.有些同志偷偷地看點業務書也被視為地下活動.
萬: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科研人員被折騰的沒辦法坐下來好好研究.
周:從1975年開始,借助于毛主席論及科技史的最新指示.北京大學化學系一些老師和我所合作編寫《世界化學史》(其實合作編寫的計劃早在50年代末已訂,只是一直運動來運動去而沒有實施).那時,北大的一些老師也可以借此躲開運動,象張青蓮、黃子卿、馮新德等老教授都積極參加了編寫工作,對于我們年輕人是個難得的學習機會.經大家共同努力,該書于1980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這項工作對于我來說,是第一項科研任務.
萬:這真是一次難得的學習和鍛煉.
周: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的1978年,經李昌和胡喬木商定,我們所從社會科學院劃歸中國科學院,業務工作回歸常態.為了彌補喪失的寶貴時光,大家都發奮地工作.在工作中,才逐漸認識到科學史是怎樣的學科,才對這門學科有了依戀.
科學技術史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科學,它描述的是科學和技術從產生到發展的史實,是自然科學和應用科學的歷史.它是歷史學領域中發展較晚,具有特殊性質的一個分支,是一門位于自然科學、技術科學、與社會科學交叉接壤的邊緣學科.從知識體系來考察,科學技術史研究首先要把人類在與自然界適應、斗爭、協調、改造的長期活動中,科學的創新、技術的發明及其積累和漸進的脈絡搞清楚,以期正確地認識科學技術在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認識科學技術在人類自然觀和世界觀的形成中重要作用.若將科學技術看作生產要素,那么科學技術史就可以在更為廣闊的背景中去探索科學技術發展的規律.從本質上來講,科學和技術也是一種文化現象.人類正是借助于科學和技術才具有駕馭自然的能力,才能在適應自然、協調自然、改造自然的斗爭中創造了“人工化的自然”.正是基于這種認識,科學技術史成為人類文明史的主線,成為科學教育的基礎內容之一.看看現實的社會就很容易發現,科學技術的狀況和水平總是這樣或那樣地制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發展.正因為有了這樣的認識,才對這門學科由生疏到熟悉,從冷漠到熱愛,覺得她在人類文明史的建樹中是不可或缺的.
萬:現在國務院學位辦,已把科學技術史列為與歷史學平行的一級學科,正說明了人們對這一新興學科有了新認識和更加重視.近20年,在全國范圍內,科學技術史的研究機構和研究教學人員也有明顯地增長,對這可喜的現象,你有何感想?
周:當今,科學技術史研究隊伍增加了許多新人,大多受過專業的碩士、博士學位訓練,基礎應該比我們當年入行時強多了.現在研究的領域也從內史擴展到外史,科學技術的社會學、人類學等許多新方向也在拓展,研究的課題選擇的范圍更大了.整個學科發展呈現一片朝輝.面對這種新態勢,我特別高興.在與新來者的接觸中,我發現一個問題:一些人急于寫論文,出專著.論文是要寫的,但是切忌浮躁.因為科學技術史的研究不僅需要大量的史料考證和調查研究,還需要扎實的知識鋪墊.我們所的老前輩嚴敦杰先生(王渝生的博士導師)就給我們樹立了一個榜樣,他發表的論文可謂不多,但是每篇論文都是經過大量的文獻考證,下筆十分慎密.論文都是高質量.我在1987年接任所的業務處(即科研處)的工作后,我就極力主張,凡到所大學生或留所研究生,第一年都爭取安排到圖書館或業務處工作,這樣便于熟悉圖書文獻的尋找和使用,可以了解所里的研究項目和許多老同志的研究特點.我的建議現在看來,確實有點偏頗,因為通過其他崗位也同樣能達到培養的目的.但是不立即進入課題組,至少可以靜下心來,扎扎實實地做點基礎建設.在中國科技史界,像夏湘蓉、王毓瑚、李仲鈞等大專家都曾有在高校圖書館工作的經歷.
萬:當前科技界、教育界浮躁風盛行.
周:原因是多方面的.在科學技術史研究中出現浮躁現象,一是急于求成,二是任務壓的.
萬:人們戲稱壓力山大.每年要完成項目、成果(論文、專著)指標,并且與職稱、待遇掛鉤.
周:目前的考評制度極不完善,有許多缺陷,促使這種浮躁之風泛濫.有個別人拿到一篇(本)外文相關論文或著述,翻譯一下,稍加改動,就成自已的研究成果.這不僅涉嫌剽竊,而且人云亦云,人錯你錯,立論閘述也易出現問題.我記得許良英先生(1979年至1982年我們都在近現代史研究室一個辦公室)曾要求其學生,多看資料,寫一個外國著名科學家的傳記應至少看5本以上的相關傳記資料(外文)和必要的第一手原始資料.從中學習、分析和比較鑒別,形成較為準確的認識,才動手編寫.往往對一件事情或一段歷史,由于視角不同,認知基礎不同及治史的方法不同,會有不同的結論或不同的表述,這就需要你作出判斷和取舍,通過自已的消化,形成自已的觀點.
萬:其實,中國古代史或近現代史的科學技術史研究也是這樣.投機取巧是不會成功的.
周:我認為,科學研究中是沒有捷徑可走的.偷懶是要不得的,最終吃虧的還是自已.在科研中要有創新,就必須付出自的辛勤勞動,我的體會是寫出一篇有質量、有新見的論文是很需用功的,是不容易的.只有勤奮和堅持不懈地努力,并運用正確的方法才能不斷取得成功和攀登科學的高峰.
萬:我記得您在我們廣西民族大學講學時曾對研究生說過:“要善于學習”,并說這四個字是您最深的體會之一.
周:是的.“善于學習”很重要.同在讀書,不同的人所收的效果收益卻不一樣.這因為讀書也有個方法技巧的問題.我體會,讀書不僅要讀得下去,還需用腦去思考,用心去領會,真正把作者的本意說教搞清楚,還要通過比較鑒別對他的觀點的長短有所醒悟.也就是說學習是有方法的.這種科學的學習方法,只要你善于觀察,許多成材之士都有自已的一套.因此我認為,除了向古人、先賢學習外,還要善于向老師、同事、友人學習.古人云:“三人行必有我師”.這條哲理我很贊賞.我們大學畢業分配到所,由于當時的歷史環境,從事業務和課題研究,大多都是沒有專門的老師指導,而是邊干邊學,在干中學.我的基礎本來就不如同時進所的,這就促使我要更加努力,虛心學習.在共同的工作中,很快就發現,周圍的每個人都有所長,都有值得我學習的地方.在學習中,不僅增長智慧,培養才干.而且對師友的尊敬,也增強友誼,汲取人緣.凡是和我合作完成某一課題的同事,我都視為師長,從他身上不僅學到自已欠缺的知識,還注意其思想方法上的長處,展闊自已的視野.
萬:您善于與人相處,特別是與人合作研究,這是不少科學研究工作者處理不好的大問題.現在的科研環境中,尤需強調團隊精神.這里不僅涉及人際關系問題,也反映一個人的科研道德問題.請您再細談您的體會.
周:20世紀以來的科學發展的史實表明,重大的科研項目的成功都需要團隊合作,單槍匹馬是難有作為的.每個人都生活在社會的大家庭中,故做人的要務首先是學會與人相處.我記得,在19世紀德國著名的教育家洪堡,在對當時的教育改革中就十分強調,教育的功能除了傳授科學知識和生產技能外,另一重要功能就是要使受教育者學會與人相處,并和諧地溶入社會.當今中國的應試教育,過分地強調了書本知識的傳授,并以考試分數識人.從而忽視了施教育人,(即培養做人的基本道德),這樣就極易偏向了培養極端利已主義的錯軌上去.人與人相處的出發點是“善”,與人為善.“人之初,性本善”就是強調這個道德的初衷即出發點.有人主張,當今的大學教育應當在求“真”即科學真理的同時,加強傳統的求“善”之大學之道,兩者結合,不可偏廢,才能培養出德智兼修的人材.我很同意這一看法.“善”在人際交往中,突出的是“誠信”二字.誠信的前提就是要尊重對方.尊重對方的勞動,尊重對方的人格,以誠相待,友善相處,切忌妄自尊大,唯我獨尊.
萬:您的良師益友可謂多矣.
周:在我50年的科研生涯中,正是眾多良師益友的無私的幫助和指引,才有我的今天和眾多成果.北京大學的趙匡華老師可以說是我尊敬的老師和摯友,自從1975年在編寫《世界化學史》中相識以來,幾度合作,一直給予我極多指教.趙老師出身于北大的名師之家,從小就受到傳統文化的熏陶,對中國古代的文化不僅喜愛有嘉,而且情有獨鐘.他又是學化學的,從事分析化學研究和教學.在化學史的研究中大展身手,實際上是水到渠成.他不僅自已學研碩果累累,而且樂于助人,幫助并培養了眾多學生和同行,他是名符其實的學科帶頭人.我就是受益者之一.我在許多課題的研究都得到他的指教.例如,2006年因為評審非物質文化遺產國家名錄,從不喝茶的我考察起制茶手工藝.在交談中,趙老師就指出,我們是學化學的,研究制茶工藝就從幾種茶(綠茶、黃茶、青茶、紅茶、黑茶及白茶)在加工過程(主要是發酵)中的化學成分變化入手.趙老師的建議實際上指明了研究的切入點和方法,使我研究制茶開辟了自已的途徑.包啟安是中國輕工——食品行業中有較深造詣的技術專家,我與他合作編寫《中國傳統工藝全集·釀造》中,我就從他那里學到不少關于釀造工藝,特別是制醋做醬工藝的具體技術知識.方心芳、程光勝,都是微生物學家,對中國微生物學,特別是發酵微生物工業有著深遂的研究.我與他們的接觸不是很多,但從不多交談中,他們的許多科學論述和精辟見解都給我以啟迪和教育.潘吉星,華覺明、陳美東、戴念祖都是我交往較多的同事.他們的淵博學識和治學經驗,特別是孜孜不倦的治學精神,一直是我學習的榜樣.總之,虛心學習、善于學習,善于向周圍的同行同事學習,豐富自已的學識,增強自已的能力,特別是學會與人共事.我認為這應是我們科研人員治學方法最應重視的修養.
萬:周先生,你曾負責過研究所的科研組織工作和學會的社會工作,您的修養是否與這些工作的歷練有關?
周:是的.我一直認為:幫助別人,實際上也在幫助自己.做點社會工作,為大家服務,不僅鍛煉了自已,還可以通過社會工作結交了許多朋友和師長,從中可以學到許多.通過交往建立了友誼,可以互幫互學地開展自己的研究工作.我從事管理工作主要有兩塊,一是所里的業務處(1987年4月到1995年8月),二是學會工作(1987年9月至1995年9月).我從1980年就參加了由倉孝和和李佩珊主持的建立中國科技史學會的籌備工作.在友誼賓館的籌備會上,他們確定了代表清華、北大、中國科大及醫學、農學、物理、化學、生物各學界著名科技史專家為籌備委員,先后開了4次籌備會議,確立了學會章程,代表產生方法,組織架構及會議地點、會議日程、會議程序等.當然具體的跑腿工作就由我們年輕人來做.就是通過這些跑腿工作,我認識了許多科技史專家.順水推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我很自然地擔負起會議的會務工作.我記得在會議召開的第一個晚上,我陪同倉孝和和嚴敦杰先生到會議住地(位于王府井的總參四招),挨個房間探望赴會的代表.從此以后,學會工作就常找我..第二次代表大會1983年在西安召開,我又成為會務組的負責人之一.在1987年的第三次代表大會上,我被推舉為主持學會日常工作的副秘書長.1990年的代表大會,我當選為秘書長.直到1995年我才卸任,由王渝生接任.長期的學會工作雖然占據我不少時間,似乎影響了我對科研工作的投入.實際上,學會工作還是給我的科研工作帶來好處.例如,學會活動使我更好地了解整個科技史研究的動態和在科技史界結下了廣泛的人脈.給我影響最深的是化學、化工史專業委員會(和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化學化工專業委員會合并召開)的學術活動從1981年起幾乎年年舉辦.、活動有聲有色,不僅進行了學術交流,還合作完成了幾個大科題,《化學哲學基礎》、《化學思想史》、《化學社會學》、《化學方法論》、《中國化學史》等著作出版都是合作研究的成果.
此外,在學會工作期間,我結識了許多老前輩和著名科學家,與他們的接觸中,他們的平易近人,淵博學識,強烈的事業心和對后輩的關懷、扶持給我極大教育.例如袁翰青院士,他曾是北大三大民主教授之一,九三學社的重要成員,歷屆的全國政協常委,也是中國化學史的著名先驅學者,20世紀50年代就在北師大開設了中國化學史講座.我進所所讀的教本就是他的《中國化學史論文集》和張子高的《中國化學史稿》.袁翰青家就在朝內大街我所(九爺府)旁邊,所以有事找他較方便.袁老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5年又患半身不遂.但是,他身殘志不綏,80高齡仍筆耕不輟.每次造訪他家,他總是熱情接待,對我們后學者給予孜孜不倦的指導.有一次,我正與他討論中國古代的豆腐發明,嚴濟慈到訪,我馬上站起來要走,袁老卻說,再說幾句,并客氣地說,歡迎再來.此后,有關的學術活動,只要我去相邀,他都盡力參加,甚至連我的學生戴吾三的碩士論文答辯,請他主持,他都親臨盡力.又例盧嘉錫院士,1988年他從科學院院長的位置退下來后,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在我們的請求下,他兼任了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第四屆理事長(1990-1995).我作為學會秘書長可以與他有較多的接觸.我記得在1990年召開的中國科學技術史國際學術研討會,由于經費結據,我們只能在所里召開,連食堂都沒有,硬件條件極差,安排代表住宿在附近招待所,吃飯在斜對面一研究單位的食堂.開幕式盧老來了,作了精彩的講話,會上舉行了授予英國劍橋大學李約瑟研究所所長何丙郁為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名譽教授,授予何丙郁、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程貞一教授、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徐美齡教授、日本明治大學佐藤健一先生為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名譽會員的儀式.隨后又一起走到南小街的咸亨飯店(一個小飯店)吃了聚會歺.他沒有一點架子,沒有挑剔,一路上和代表熱切交談.還贊許這次會議體現了艱苦樸素,勤儉辦事的作風.他的到來倒是因安保問題,驚動了從市公安局、東城分局到派出所的警察.(盧老當時屬于國家領導人,這類活動應由舉辦單位向公安部門通告).2000年3月10日,盧老請胡亞東(中科院化學所原所長)、郭保章(首都師大化學系教授)和我到他家聊天.他告訴我,已翻閱過我所編寫的《世界化學史》,并詢問了幾個問題,隨后興致勃勃地談了他從美國留學歸來和到廈門大學執教的經歷及和他的老師鮑林的友誼.總之,這些前輩以自身作則為我們樹立了一個學者應有的道德規范和思想境界.
萬:周先生,五十年的科研生涯,你著述頗豐.你能否談談對這些成果的自我評價.
周:五十年的發奮勤練,總算給后人留下一點用鉛字印刷的著述.據初步統計,大概有40多本專著或合著,50多篇文章.這些著作大多是合著,這因為一是這些課題主要是所里承接的或規劃中的大課題,都必須是團隊合作.二是我這個人好相處,正如上面所說的愿意通過合作學到更多的東西.三是我這個比較講信用,別人也愿意找你合作.在合作互幫互學中,很多人成為我的師長或摯友.這些文章中,有些都是應邀而作或是用作會議的敲門磚,談不上是嚴格意義上的論文.從這些著述中,若按時間順序來看,就可以發現筆者對一些問題的認識的深化過程,也就是明瞭我的學術成長的軌跡.例如,當我經歷了5年多的努力,在1983年完成了在《20世紀科學技術簡史》我承擔的任務.過了10年,我重讀該書,越看越覺得不是味,我怎么會寫得那么糟!于是在1999年該書第二版時,“化學發展的新時代”那章我改動較大,幾乎是重寫了.又過了2年,因為編寫《諾貝爾科學獎百年鑒》的兩本書,全面考察了百年諾貝爾化學獎的相關內容.又發現我對20世紀的化學發展認識得還不夠清晰,對許多問題的研究有點淺薄,對諾貝爾化學獎許多獲獎項目的內涵、意義及在化學發展中的影響、地位缺乏有深度的分析.到了2009年,我在《世界化學史》一書的第二版時,就盡可能地將一些新認識補充進去.在去年底編寫《大眾化學化工史》時,由于內容已較熟悉,思路也清晰,寫起來就較快,20多萬字的內容,僅用2個多月即完稿.
萬:周先生,大家都知道你對中國古代釀造史,特別是酒史,很有研究,能否就酒史研究作點介紹?
周:對中國傳統釀酒技藝的研究,起始于1980年.1977年至1979年,我主要研究的項目集中在中國古代陶瓷史和中國黑火藥的發明與發展兩個項目.后來發現,陶瓷史的研究中,我手中沒有出土的陶瓷樣品,又無現代的古陶瓷檢測手段,研究起來就象腳下無基石,只能依仗別人的成果或幫助,工作起來既花經費,又不討好,實難有所作為.火藥史的研究,趙匡華、潘吉星、郭正誼、鐘少異等已做了大量研究,我對做擴展的研究缺乏手段.于是我借轉入世界近現代史研究后契機,放棄了這兩個選題,重新選擇酒史作為我在古代化學史領域研究的新方向.
1979年10月在昌平酒廠參加了由輕工部釀酒處主持召開的有關酒史的研討會后,1980年初冬,清華大學楊根、白廣美(他們都是張子高的弟子)和我在貴州輕工科研所丁勻成的陪同下,專門參觀了貴州茅臺酒廠和遵義董酒廠.這算我酒史研究的起步.從此以后,只要出差方便,我都會順路參觀考察一些名酒廠.粗略回憶,全國除了西藏、青海、甘肅、寧夏及臺灣外,各省的許多名酒廠都留下了我的足跡.到酒廠參觀,主要是學習和收集酒史資料.初學者只要有虛心求教的態度,酒廠的師傅們還是樂意接待的.在這個學習過程中,我非常感謝原輕工部釀酒處的辛海庭、徐洪順兩位先生,他們都是酒界知名的專家,不僅為我參觀酒廠提供介紹信(當時輕工部的介紹信,酒廠是很重視的),而且徐洪順還陪同我參加上海和紹興舉辦的黃酒節,合作完成《黃酒釀造》一書的編寫.由此,我相識了許多酒廠朋友,為以后開展酒文化活動帶來方便.1987年參與籌建酒文化研究會及以后8年的相關學術活動,使我跟酒界的朋友有更多的接觸,學習機會多了,學到的東西也多了.
萬:您如何抓住這些學習機會.
周:我的學習是從兩方面入手,一是到酒廠的生產第一線,收集并考察傳統釀酒工藝的技巧和精髓;二是查閱并整理古代相關文獻,以豐富酒史知識.跑了許多酒廠遂發現,盡管生產酒的科學原理和核心的工藝路線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各地的生態環境和具體的工藝細節的差異,生產的酒在口感上還是有差別的.“大同小異”中的“小異”決定了酒的質量(包括香型、酒度).往往一些“小異”的技巧恰好是造就某種酒的特色和關鍵.因為中國傳統釀酒技藝的特色是利用酒曲發酵,即釀酒的過程依仗著微生物菌系的幫助,許多工序操作都是圍繞著讓有益于釀酒發酵的菌系更好地繁殖做功.而發酵過程的生態環境和某些影響溫度、濕度及介質的操作都會直接改變菌系的構成和其做功能力,最終影響成品酒的精細組合,即決定了酒的質量和品位.釀酒實質上是最早的微生物工程技術,因此,從微生物學的視覺來考察釀酒過程,可以說是用現代的生物技術來剖析傳統釀酒的機理.我就是站在這個平臺上來比較、考察許多名酒的生產工藝,從而有了自己的獨到認識.對相關古代文獻的疏理和考究是從事科技史研究的基本功.這方面的工作決不能小視,同一個史實,往往可能有多個版本,加上古代的著者或刻印書刊的工匠,對于許多工藝技術大多不是親歷者,出現差錯是難免的.而且有一些名詞在不同時期的含義或對象是不同的.例如在古代,白酒曾是指經過濾的一種清酒.唐宋詩詞中出現的“燒酒”是指經加熱后飲用的溫酒,含義都與現在不同.總之,我研究酒史就是綜合了歷史、化學化工史、現代生物技術等知識來把研究推向深入.
萬:這些經驗之談很值得后學玩味.
周: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沒有匆忙地寫有關酒史的文章.可能是工作太忙,一有所里科研項目的管理,二有學會(我當時任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秘書長)的煩瑣工作,三要參與所里的重大課題研究,一直沒有時間坐下來仔細地研究整理手中的酒史資料.1988年寫的“蘇軾筆下的幾種酒及其釀造技術”僅是為第一屆酒文化學術會議而趕寫的文章.現在再看這篇文章,實在是太簡陋了,蘇軾的文集都來不及細讀.直到1994年,因為那時關于蒸餾酒的起源眾說非紜,無所適從.我受臺灣學者劉廣定文章“元代以前中國蒸餾酒的問題”的啟發,對有關文獻中資料進行了一番梳理考證,否定了很多因版本而造成的誤解或對文字的理解而出現的差錯.這篇“中國蒸餾酒源起的史料辨析”可以算是我關于酒史研究的第一篇論文.1998年和趙匡華合著的《中國科學技術史·化學卷》中,我借機對我手中的酒史資料進行初步的小結.到2007年在和包啟安合著的《中國傳統工藝全集·釀造卷》中再一次考研了中國的傳統釀造技藝.直到2014年出版的《中國傳統釀造:酒醋醬》才對部分研究做了一個總括.
萬:您認為,您在酒史研究中,主要解決了哪幾個問題?
周:一是分清了自然界存在的天然酒和人工運用谷物或其他含糖物材發酵而成酒的區別,同時指出,釀酒技術的發明是人們模仿自然界發酵現象的結果.二是厘清了曲糵的發明及商周期間“三酒四飲五齊”的內涵.三是從釀酒技藝的視角把曹操的《九醞春酒方》和賈思勰的《齊民要術》中制曲釀酒說清楚了.四是對蘇軾的《酒經》和朱肱的《北山酒經》所敘述的釀酒技藝及其在中國釀酒史上的地位做了研究闡述.五是對中國蒸餾酒興起于元朝的歷史背景和技術鋪墊作了全面的論述.六是對在明清時期白酒(蒸餾酒)的演進做了初步的整理.七是剖析了許多名酒生產技藝的特點.八是比較中外釀酒技藝的異同,指出中國獨樹一幟的釀酒技藝在世界釀造史上的地位和在微生物工程技術和現代生物技術的貢獻.
萬:您30多年的釀酒史研究,“越釀越香”,在中國釀酒史研究上獨樹一幟.
周:希望有后人繼續努力,把人們關注的酒文化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萬:今天我們的暢談,好比暢飲了醇香的美酒,謝謝您!
[責任編輯黃祖賓]
[責任校對黃招揚]
2015-11-11.
周嘉華(1942-),男,浙江瑞安人,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萬輔彬(1942-),男,安徽繁昌人,廣西民族大學教授,原學報(自然科學版)主編,中國科技史學會理事.
K826.1文獻標識碼: A
1673-8462(2016)02-00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