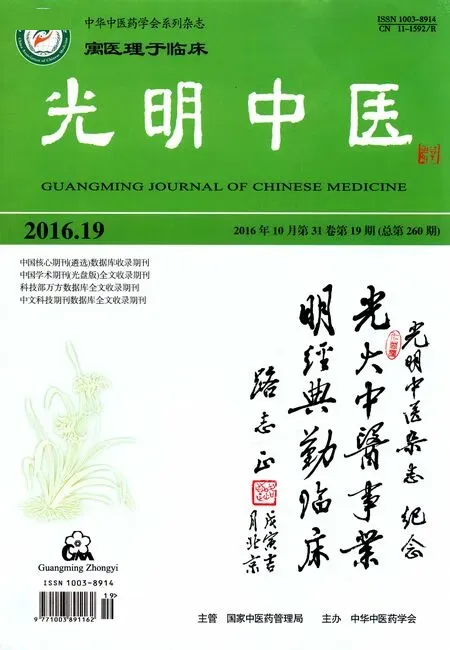慢性心衰中醫(yī)證候演變研究進展
王夢之 姚成增 賈美君 阮小芬 徐 燕
?
【研究進展】
慢性心衰中醫(yī)證候演變研究進展
王夢之1姚成增2△賈美君2阮小芬2徐 燕2
慢性心衰作為各種心臟病的主要并發(fā)癥及終末期表現已被全世界重視,中醫(yī)藥治療慢性心衰已經取得一定療效,尤其是在控制癥狀、改善心功能、降低病死率等方面,療效顯著。但目前,中醫(yī)對慢性心衰證候規(guī)律的認識多源于個人經驗判斷及簡單的病例總結,尚缺乏全面認識。故今后應進一步加強中醫(yī)對慢性心衰治療標準化、客觀化、規(guī)范化的研究,才能充分發(fā)揮中醫(yī)優(yōu)勢以推動中醫(yī)藥治療慢性心衰現代化的進程。現主要從病因病機、證型、證素分布規(guī)律、心功能分級、客觀指標4個方面對慢性心衰中醫(yī)證候研究現狀作一綜述。
慢性心衰;證候;辨證分型;綜述
慢性心力衰竭(chronic heart failure,CHF)是多種心臟病及其他臟器疾病病情發(fā)展到終末階段時心臟功能代償失調的綜合征,目前已成為心血管病領域的重要公共衛(wèi)生問題,被稱為“21世紀最后的大戰(zhàn)場”。近年來,高血壓的治療率和控制率顯著提高,腦卒中顯著減少,冠心病的死亡率也有明顯下降,但隨著人口的老齡化的逐漸加重,CHF的發(fā)病率呈逐年上升趨勢[1]。
目前治療心衰主要以強心、利尿、擴血管等西醫(yī)方法為主,利尿劑、血管緊張素轉換酶抑制劑(angiotensin convering enzyme inhibitors,ACEI)、醛固酮受體拮抗劑能夠明顯改善癥狀,然而長期使用則可能會導致腎功能損害,尿酸升高、藥物不耐受等諸多不良作用。近年來發(fā)展起來的非藥物治療,如心臟再同步化治療(cardiac resynchronization therapy,CRT)等,由于技術、費用、適應癥等的限制也未能為大多數CHF患者帶來獲益。中醫(yī)藥治療具有辨證施治和整體調治,更具個體化,在改善慢性心衰癥狀方面有明顯優(yōu)勢,也越來越被廣大臨床醫(yī)生和患者所接受。由于不同學者對心力衰竭的辨證認識多源于個人經驗和較為簡單的病例總結,從而導致了臨床CHF的辨證方法不統(tǒng)一、證候分型不一致等問題,極大影響了中醫(yī)藥防治CHF臨床研究的規(guī)范化,所以,總結CHF的中醫(yī)證候演變規(guī)律刻不容緩。現將近年來慢性心衰中醫(yī)證候研究做綜述如下。
1 通過病因病機總結慢性心衰證候的辨證分型
《中醫(yī)內科學》書中并未現心衰這一病名,但就其臨床表現來看,可以歸屬于“胸痹”“心悸”“喘證”“水腫”“肺脹”等范疇。根據慢性心衰相關臨床表現,多數學者認為本病屬本虛標實,本虛以心氣虛、心陽虛為主,血瘀水停、痰濕內阻為標[2]。近年來,不少醫(yī)家亦根據自己臨床經驗對慢性心衰病機進行補充,并根據病人的不同臨床表現對慢性心衰進行辨證分型。張鵬等[3]對冠心病慢性心力衰竭證候及證候要素分布特點的多中心橫斷面研究發(fā)現,冠心病慢性心力衰竭經驗辨證的分布特點:氣虛血瘀證、氣陰兩虛證、痰瘀互阻證、水飲內停證、痰濁證、心血瘀阻證、血瘀水停證、陽虛水泛證、心陽虛證等9型。肖群杰[4]認為中醫(yī)慢性心衰發(fā)病的機制在于心,其表現主要有三個方面:心虧氣虛、血脈瘀滯、水邪為患。鄧鐵濤[5]將慢性心衰病機概況為以心之陽氣(或兼心陰)虧虛為本,是心衰之內因。陳可冀教授[6]認為慢性心衰中醫(yī)病機可以用“虛”“瘀”“水”來總結。華新宇[7]在總結臨床經驗的基礎上,結合中醫(yī)三焦理論,提出慢性心衰的病機關鍵是心氣(陽)虧虛,導致三焦失利,氣水代謝失常。袁東超等[8]對112例心衰病例進行回顧性分析,得出慢性心衰為本虛標實之證,本虛尤以陽虛為主,標實尤以水阻為著。
綜上,慢性心衰的病機以本虛標實為主,本虛主要以心氣虛為主,標實以血瘀多見。但不同醫(yī)家對病機的認識亦存在差異:有醫(yī)家認為本虛只是單一證素,或單純氣虛,或單純陽虛;也有醫(yī)家認為慢性心衰本虛的病機是多種證素結合,包括氣虛、陽虛和血虛等;標實也不僅僅包括血瘀,亦存在水飲、痰濕。此種認識差異可能由于各醫(yī)家臨床經驗不同所致。
2 根據證素、證型分布規(guī)律對證候進行辨證分型
“證素”即“證候要素”,是辨證的基本要素,是根據中醫(yī)學理論而提煉出的具體診斷單元。“證素”是通過對 “證候”(癥狀、體征等病理信息)的辨識,而確定的病位和病性,是構成“證名”的基本要素[9]。目前,中醫(yī)對心力衰竭證候規(guī)律的認識多源于個人經驗判斷和簡單的病例總結,缺少大樣本的群體研究資料,尚缺乏全面的認識[2]。任建歌等[10]通過對186例慢性心衰的中醫(yī)四診信息與病理因素的相關性研究將CHF分為6個證素(氣虛、血瘀、陽虛、陰虛、水飲、痰濁),認為早期CHF多為氣虛、血瘀、痰濕水飲,后期多兼見血虛、陰虛、陽虛。在證型分布規(guī)律方面則認為心衰III、IV級的常見證候是氣虛血瘀水停,在疾病發(fā)展的不同時期還兼夾陽虛、陰虛、痰濁。林曉忠等[11]通過對404例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中醫(yī)證候分布規(guī)律研究,將CHF分為9個證素,并且認為本虛為氣虛、陰虛、陽虛,標實有血瘀、痰濁、水飲。其中最多的2個病性證候要素是氣虛和血瘀。王娟等[12]通過對630例慢性心衰患者中醫(yī)證候分布規(guī)律研究將CHF分為8個證素,認為氣虛最多,其次是血瘀、水停,再次為陰虛、痰濁、陽虛、熱證、氣滯證。并認為CHF以三證(氣虛血瘀水停)組合方式為最常見,其次是四證(氣虛血瘀陽虛水停)組合和兩證(氣虛血瘀)組合,再次為五證(氣虛血瘀水停兼夾痰濁證、陽虛證)組合, 而單證和六證組合的方式相對較少。劉娟等[13]通過對315篇文獻進行分析,將CHF分為32個證素,并且認為本虛首在心、腎,以陽虛為主,久而累及肺、其他臟,標實則見血瘀、水停。判定CHF證型以復合證為主,單一證型出現較少,體現了該病臨床證型的復雜性。張鵬等[3]通過對596例CHF患者證型的調查,氣虛血瘀證、氣陰兩虛證遠多于痰瘀互阻證、水飲內停證、痰濁證、心血瘀阻證、血瘀水停證、陽虛水泛證、心陽虛證等證候類型。鄒旭等[14]對512 例CHF 患者進行病例調查,結果顯示最多的是氣虛痰瘀證,其次為氣陰兩虛、痰瘀內阻證,心陽不振、痰瘀阻絡證,陽虛水泛證,其他各證型較為分散。在證候虛實組合中,本虛標實證占97.5%。
綜上,目前大部分臨床研究多參照2002年修訂——衛(wèi)生部頒布的《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慢性心力衰竭診斷標準將分為心肺氣虛證、氣陰兩虧證、心腎陽虛證、氣虛血瘀證、陽虛水泛證、痰飲阻肺證、陰竭陽脫證7種中醫(yī)證型。此7種證型的分類方法無法應對慢性心衰患者因個體差異、發(fā)病節(jié)氣、不同的原發(fā)病及合并病、地域等因素,而出現紛繁證型,存在局限。
3 按照心功能分級對證候進行辨證分型
NYHA心功能分級是評估慢性心衰患者心功能嚴重程度的指標,隨著NYHA級別的升高,心功能逐漸向惡化的方向發(fā)展[15]。尹學鳳等[15]認為氣虛血瘀證及痰飲阻肺證患者以心功能III級為主,陽虛水泛證患者心功能分級多集中在IV級。段文慧等[16]總結160例慢性心衰病例得出,心功能II級患者氣陰兩虛心血瘀阻證占優(yōu)勢,心功能III級的患者氣虛血瘀水停證占優(yōu)勢,而心功能IV級的患者心腎陽虛血瘀水停證占優(yōu)勢。徐重白等[17]認為心功能分級I級以心肺氣虛證為主,心功能分級II級以氣陰兩虛證為主,心功能分級III級以氣滯血瘀證為主,心功能分級IV級以痰飲阻肺證為主。通過臨床長期利用中醫(yī)藥辨證治療慢性心衰的相關研究和體會, 探討在中醫(yī)理論指導下中醫(yī)對慢性心衰的臨床分期分級。張燕等[18]根據不同的發(fā)病階段, 把慢性心衰分為早、中、晚3期, 慢性心衰早期以氣虛血瘀證多見,中期以氣陰兩虛兼血瘀證多見,慢性心衰晚期以陽虛水泛證多見。
慢性心衰臨床上具有病情遷延、反復發(fā)作等特點,故可將其分為急性期、緩解期。根據慢性心衰患者臨床癥狀的不同,亦可總結規(guī)律對證候進行辨證分型。梁蘊瑜等[19]對217例慢性心衰患者進行調查研究總結出,慢性心衰急性發(fā)作期中醫(yī)證候的病性要素以氣虛、陽虛、痰濁、血瘀為主,病位要素與心、脾、肺、腎、肝相關,不同時期表現為不同病性要素與病位的結合。趙志強等[20]認為慢性心衰急性加重期最基本的中醫(yī)證候特點為氣虛血瘀兼水飲或痰濁,病位以心腎為主,五臟皆可累及。蔣梅先教授[21]認為慢性心衰屬本虛標實之證,在臨床上有穩(wěn)定期和急性加重期之分。辨證首先要明確分期,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辨清本虛標實孰輕孰重。穩(wěn)定期以扶正固木為主,在辨證論治的基礎上參以活血通絡、寬胸利水之品;急性加重期宜及時祛除誘因,加強祛邪扶正,遵循“急則治標”的原則。
按照心功能分級進行辨證分型更加符合臨床實際,可能更加容易操作,但心功能分級主要依靠臨床醫(yī)生的主觀判斷,缺乏客觀指標的支持;按照發(fā)作的急緩進行辨證分型可指導短期內臨床治療,證候的演變相對迅速,需要密切觀察,此二者仍有利弊。
4 將證候與客觀指標相結合
中醫(yī)證候辨別標準即中醫(yī)辨證客觀化研究是現代中醫(yī)藥研究的重要內容。目前廣泛開展CHF的中醫(yī)辨證分型與現代實驗指標的相關性研究可以為CHF中醫(yī)辨證分型提高客觀實驗參考依據,有助于揭示CHF的證候本質,指導臨床治療,發(fā)揮中醫(yī)治療CHF獨特的優(yōu)勢。
LVEF是反映左心室收縮功能的主要指標,臨床上分為收縮性和舒張性。趙金龍等[22]對117例CHF患者LVEF進行測定,結果發(fā)現LVEF 與中醫(yī)證型間存在負相關性,LVEF按照心肺氣虛、心氣陰虛兼血瘀→氣虛血瘀→心脾陽虛兼血瘀水停→心脾腎陽虛水泛兼血瘀逐級遞減。李榮等[23]就134例CHF患者的LVEF進行分析得出:與痰飲阻肺證相比,氣陰兩虛、血瘀水停證與氣陽兩虛、血瘀水停證的心衰患者LVEF 均顯著降低,具有統(tǒng)計學意義,而且氣陽兩虛、血瘀水停證患者的LVEF最低。汪芳等[24]對44例慢性心衰急性發(fā)作患者進行研究得出,慢性心衰急性發(fā)作患者早期NT-ProBNP水平即明顯下降,就診時監(jiān)測NT-ProBNP水平對判定患者病情和危險分層有一定的價值。陳國通等[25]選取105例CHF患者,得出結論各中醫(yī)證型組的血漿BNP水平由高到低順序為痰飲阻肺證>陽虛水泛證>心腎陽虛證>氣陰兩虧證>氣虛血瘀證>心肺氣虛證,心腎陽虛證組、陽虛水泛證組、痰飲阻肺證組均顯著高于心肺氣虛證組、氣虛血瘀證組、氣陰兩虧證組(P<0.01),且同一心功能級別的血漿BNP水平存在一定差異,NYHA III級患者的血漿BNP水平在氣虛血瘀證組與痰飲阻肺證組中存在顯著性差異(P<0.05),提示BNP可以作為中醫(yī)辨證分型的參考,并有獨立于心功能分級外的證型診斷價值。左室射血分數和BNP、NT-proBNP可以作為CHF中醫(yī)辨證的一個量化指標。
龔乃鵑等[26]對60例CHF患者C-反應蛋白(CRP)進行研究,得出CRP是一種高敏非特異性急性期反應蛋白之一。結果顯示,不同中醫(yī)證型心衰患者的超聲指數及血清CRP水平由高到低的排列順序為陽虛證> 氣陰虛證> 氣虛證,陽虛證與氣虛證比較,差異具有統(tǒng)計學意義。吳樂文等[27]對136例CHF患者血尿酸水平與CHF中醫(yī)證型的關系,得出隨著心力衰竭程度的進展和中醫(yī)證候的加重,血清UA 水平亦隨之明顯增高,即心肺氣虛證<氣陰兩虛證<氣虛血瘀證。馬莉等[28]認為彌散功能減退是心衰患者最重要的肺功能改變,在輕度心衰(NYHA 分級Ⅰ級)時就可發(fā)現明顯降低,是發(fā)現早期心衰的潛在敏感指標,心衰病人進行肺功能檢查作為一種無創(chuàng)性循環(huán)功能受限評估的輔助手段,具有重要的臨床應用價值,應當予以重視。
雖然近年來慢性心力衰竭中醫(yī)辨證分型在客觀化研究方向逐漸受到重視,但仍存在問題,如客觀化指標種類繁多,缺乏標準化等。中醫(yī)辨證具有明顯的整體性,客觀指標因具有專一性、針對性,不能完全體現其整體性,二者存在矛盾。中醫(yī)辨證分型不統(tǒng)一也使得研究指標與CHF患者的中醫(yī)分型之間缺乏特異性和相關性,極大影響了臨床研究的質量。
5 問題與展望
綜上所述,不論中醫(yī)或西醫(yī)對慢性心衰的研究已取得很大進步;雖然公認CHF的病機為本虛標實,但由于不同學者對心力衰竭的辨證認識存在辨證方法不統(tǒng)一、證候分型不一致、對辨證要素間關系未予重視,都影響了心力衰竭辨證標準的臨床應用推廣和療效評價體系的相對完整性建立,也極大影響了CHF臨床研究的質量和對臨床的指導意義。
由于時代變遷,經濟發(fā)展、工作節(jié)奏、生活方式及習慣等等的顯著改變,使國人的體質、疾病譜和臨床表現都發(fā)生了顯著變化;以臨床表現為辨證依據的“證候”無疑也會隨之改變,證候的分布情況無疑也在發(fā)生著顯著變化。因此,單純局限于某一地區(qū)、甚至某個人的辨證方法進行的臨床研究往往得到業(yè)內的公認,由此引發(fā)的學術爭鳴更加不利于中醫(yī)藥發(fā)展[29]。任何指南、規(guī)范或標準的建立都離不開可靠的、科學的流行病學調查資料。而國人臨床常見疾病的中醫(yī)證候分布究竟如何,目前仍然是一個未知領域。那么,要產生高質量的中醫(yī)研究、中醫(yī)診療指南、規(guī)范或標準,都是困難的。故在全國范圍內開展臨床常見疾病國人中醫(yī)證候分布特點的調查研究,對確立符合臨床實際的常見疾病中醫(yī)證候分型標準、從而進一步確立診療規(guī)范和療效評估方法等行業(yè)標準,無疑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1] 王吉耀,內科學[M].2版.北京:人民衛(wèi)生出版社,2014:186.
[2] 張艷,禮海,王彩玲.淺談慢性心衰中醫(yī)病名病機研究[J].遼寧中醫(yī)雜志,2011,38(1):12-13.
[3] 張鵬,朱浩,陳嬋,等.冠心病慢性心力衰竭證候及證候要素分布特點的多中心橫斷面研究[J].中西醫(yī)結合心腦血管病雜志,2013,11(12):1412-1414.
[4] 肖群杰.慢性心衰中醫(yī)病機及臨床辨證治療[J].中國現代藥物應用,2013,7(8):131-132.
[5] 葛鴻慶,趙梁,郝李敏.鄧鐵濤教授從脾論治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之經驗[J].上海中醫(yī)藥雜志,2002,36(4):9-10.
[6] 李立志.陳可冀治療充血性心力衰竭經驗[J].中西醫(yī)結合心腦血管病雜志,2006,42(2):136-138.
[7] 華新宇.慢性心力衰竭中醫(yī)病機的三焦觀[J].光明中醫(yī),2010,25(11):1963-1964.
[8] 袁東超,楊關林.慢性心力衰竭中醫(yī)證型與病因關系探討[J].遼寧中醫(yī)藥大學學報,2010,12(12):93-94.
[9] 朱文鋒,張華敏.“證素”的基本特征[J].中國中醫(yī)基礎醫(yī)學雜志,2005,11(1):17-18.
[10] 任建歌,張艷,王辰,等.186例慢性心衰的中醫(yī)四診信息與病理因素的相關性研究[J].遼寧中醫(yī)雜志,2014,41(2):276-279.
[11] 林曉忠,潘光明,鄒旭,等.404例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中醫(yī)證候分布規(guī)律研究[J].新中醫(yī),2011,2(43):20-22.
[12] 王娟,陳嬋,張鵬,等.630例慢性心衰患者中醫(yī)證候分布規(guī)律研究[J].北京中醫(yī)藥大學學報,2013,36(8):567-571.
[13] 劉娟,謝傳榮.慢性心力衰竭中醫(yī)證候分布特點的現代文學研究[J].亞太傳統(tǒng)醫(yī)藥,2012,8(7):7-8.
[14] 鄒旭,潘光明,盛小剛,等.慢性心力衰竭中醫(yī)證候規(guī)律的臨床流行病學調查研究[J].中國中西醫(yī)結合雜志,2011,31(7):903-908.
[15] 尹學鳳,袁春霞.慢性心力衰竭中醫(yī)證型與BNP、NYHA心功能分級的相關性研究[J].光明中醫(yī),2012,27(2):255-256.
[16] 段文慧,鄭思道,苗陽,等.慢性心力衰竭中醫(yī)證型與心功能關系探討[J].中西醫(yī)結合心腦血管病雜志:2010,8(5):511-513.
[17] 徐重白,賈堅,吳中華.慢性心衰中醫(yī)辨證分型及規(guī)范化治療與預后的相關性[J].江西中醫(yī)藥,2011,42(9):9-11.
[18] 張艷,宮麗紅,錢新紅,等.慢性心衰中醫(yī)分期分級臨床辨證體會[J].遼寧中醫(yī)雜志:2010,37(5):801-802.
[19] 梁蘊瑜,鄒旭,潘光明.慢性心力衰竭急性發(fā)作期中醫(yī)證候要素及演變規(guī)律的初步研究[J].中西醫(yī)結合心腦血管病雜志,2011,9(8):897-899.
[20] 趙志強,毛靜遠,王賢良,等.慢性心力衰竭急性加重期中醫(yī)證候特征的多中心調查分析[J].中醫(yī)雜志,2013,54(12):1038-1042.
[21] 蔣梅先.談談慢性心力衰竭的中醫(yī)分期論治[A].第七次全國中西醫(yī)結合心血管病學術會議,2005.
[22] 趙金龍,李大鋒,管益國,等.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左室射血分數與中醫(yī)證型關系的研究[J].現代中西醫(yī)結合雜志,2011,20(31):3912-3913.
[23] 李榮,陳海生.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左室射血分數和B型利鈉肽與中醫(yī)證型的相關性研究[J].中國中醫(yī)藥信息雜志,2010,17(8):13-14.
[24] 汪芳,王莉,邊文彥,等.慢性心力衰竭急性發(fā)作患者N端前腦鈉素水平的變化[J].中國危重病急救醫(yī)學,2005,18(4):195-198.
[25] 陳國通,陳永忠,鄒襄谷.B型利鈉肽與慢性心力衰竭中醫(yī)證型的關系[J].中外醫(yī)療,2010,29(24):53-54.
[26] 龔乃娟,李青,陳婕,等.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中醫(yī)證型與超聲指數及CRP的相關性研究[J].浙江中西醫(yī)結合雜志,2010,20(6):336-337.
[27] 吳樂文,呂健,楊帆,等.心力衰竭中醫(yī)證型與血尿酸水平及心力衰竭分期相關性研究[J].實用中醫(yī)藥雜志,2013,29(12):988-989.
[28] 馬莉,孫興國,潘世偉,等.心臟瓣膜病患者肺功能改變及其臨床意義[J].中國循環(huán)雜志,2013(Z1):82-83.
[29] 姚成增,朱靈妍,王肖龍,等.也談慢性心衰中西醫(yī)結合治療的臨床策略[J].醫(yī)學與哲學,2014,35(2B):80-82.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No.81273959,81403352);上海市科委項目(No.12401901402);海派中醫(yī)流派傳承研究基地建設項目 (No.zy3-cccx-1-1001);上海市中西醫(yī)結合重點病種建設項目(No.zxbz2012-08);國家基礎科學人才培養(yǎng)基金項目(No.J1103607)
1.上海中醫(yī)藥大學基礎醫(yī)學院中醫(yī)學七年制2009級(上海 200021);2.上海中醫(yī)藥大學附屬曙光醫(yī)院心內科(上海 200021)
△通訊作者
10.3969/j.issn.1003-8914.2016.19.055
1003-8914(2016)-19-2894-04
?赟
2016-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