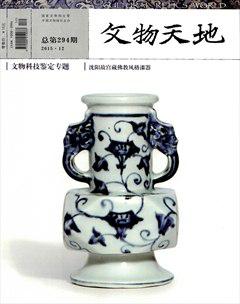“京津畫派”指稱新探
王曉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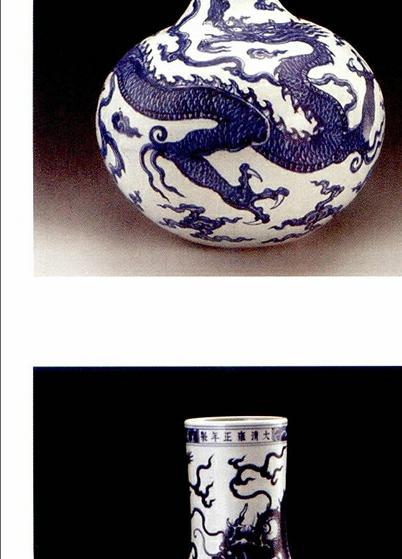

“京津畫派”是近現(xiàn)代中國美術史中的一個重要的藝術團體,與“海派”“嶺南畫派”并馳畫壇,影響極大。而“京津畫派”一詞卻是近些年美術史研究中出現(xiàn)的概念,學界在使用這一指稱時也有不少爭論,故其所指的內(nèi)涵和外延尚有待深入探討和發(fā)掘。
在中國近現(xiàn)代美術史研究領域中,關于地域畫風的構建和美術家群體性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內(nèi)容之一。特別是20世紀早期的中國畫壇,傳統(tǒng)繪畫在觀念、技巧、題材等諸多方面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隨之而來的是百家爭鳴和藝術實踐創(chuàng)新。在這一時期,圍繞著中國畫的革新和前途命運的討論蜂擁不斷,而“京津畫派”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京津畫派”是近十幾年學術界出現(xiàn)的一種提法,主要指民國時期活動于京津地區(qū)的畫家團體,是與上海、浙江、江蘇地區(qū)的“海派”和廣東地區(qū)的“嶺南畫派”并存的中國北方地區(qū)最大的畫家集群。這三個藝術群體在20世紀前期的中國畫壇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對后來中國繪畫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雖然“京津畫派”一詞日漸頻繁地用于美術史研究、博物館展覽和藝術拍賣等諸多領域,但是就學理而言,其究竟是不是一個完整的概念,它所指代的畫家集群是否構成一個具有統(tǒng)一藝術宗旨的派系,尚值得深入探討。而對于京津畫派與近現(xiàn)代美術現(xiàn)象的關聯(lián),它存在的時間、地域、畫家構成,以及形成過程、發(fā)展狀況、藝術主張、歷史影響等問題,還有很多研究和商榷的空間。因此,厘清這一指稱的內(nèi)涵和外延,使之在今后的學術研究或展覽、出版中規(guī)范地應用,而不至于讓人產(chǎn)生太多的分歧和誤解,將會產(chǎn)生積極意義。
關于“畫派”的問題
中國傳統(tǒng)書畫中的派別之論,歷史久遠。尤自明代以后,董其昌作“南北宗”論,更是把派別之分推到一個頂點,甚而給藝術批評以極大的影響。一般而論,畫派須具有如下幾個基本特征:
1.具有地域性。如新安畫派是以新安(今安徽徽州)地區(qū)為主,吳門畫派以吳門(今蘇州一帶)地區(qū)為主。
2.有畫派領袖。如浙派的領軍人物戴進,吳門畫派的沈周、文徵明等。
3.有明顯的藝術師承。如嶺南畫派二居、二高一陳、關黎趙等,代代師承關系明確,藝術特征明顯。
這種派系主導畫壇的現(xiàn)象在明清時期達到鼎盛,而至清末開始逐漸衰敗。隨著西方科技、文化對中國社會越來越強的震動,傳統(tǒng)畫壇也不可避免地卷入這場變革浪潮之中,而此時的“畫派”也在轉(zhuǎn)變著自己的角色。
學界一般認為,民國初期的畫壇呈現(xiàn)的是三足鼎立的局面。而這“三足”所指的是以滬寧蘇杭為中心的“海派”、以廣州為中心的“嶺南畫派”和以京津為中心的“京派”。很明顯,這延續(xù)了明清以來“以地別為派”([清]張庚:《浦山論畫》云:“劃分南北,始于唐世。然未有以地別為派者,至明季方有浙派之目”)劃分畫派的傳統(tǒng)。三者皆以大城市為中心而形成了地域性的繪畫群體,各自持有自己鮮明的繪畫理念和藝術主張。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三個畫派的活躍時間正逢中國社會巨變和文化思潮革新的年代,其于美術界的影響已經(jīng)超出傳統(tǒng)畫派在畫壇所發(fā)揮的影響力。換句話說,在中西方文化對沖激烈的時代,這些所謂的“派”是不可能延續(xù)著傳統(tǒng)畫派的發(fā)展模式前行而無視周遭的文化環(huán)境變革的。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三“派”都具有多元的構成和新的發(fā)展模式。正如薛永年先生所說,在西洋繪畫在中國畫壇發(fā)生越來越強烈的影響時,傳統(tǒng)的繪畫群體也開始產(chǎn)生了不同的回應態(tài)度,他們“因應著新的形勢在起衰振興中呈現(xiàn)了兩種走向。一種是引西潤中,即引進西方的藝術觀念和方法,以融合中西或謂折衷中西的方式改造舊有的中國畫。另一種是借古開今,即保持本土文化的立場,以借鑒晚近失落的傳統(tǒng)精華之途徑更新舊有的中國畫。前者被稱為革新派、融合派或折衷派,后者被稱為國粹派、傳統(tǒng)派或保守派,近年更有人稱前者為開拓派,后者為延續(xù)派。”(薛永年:《民國初期北京畫壇傳統(tǒng)派的再認識》,《美術觀察》,2002年第4期)按此種說法,則這里所謂的“派”是指有共同的藝術態(tài)度和主張的藝術群體,如果前文所謂的畫壇三足的“派”單純指地域劃分的話,則這兩個概念在內(nèi)容上則有交叉之處。例如,徐悲鴻的藝術主張向來被人們看作是中國畫革新派的代表,然而他的主要藝術活動則是在北京,也可以歸為“京派”。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京派”的所指應該有更深層次的含義,薛永年先生稱它做“北京畫壇的傳統(tǒng)派”。近幾年來“京津畫派”概念的傳播越來越廣,也似乎被人們所認可,但是僅限于概念熟識階段,關于此畫派存在的時間、地域、畫家構成,以及形成過程、發(fā)展狀況、藝術主張、歷史影響等等,還基本沒有進入實質(zhì)的研究,且現(xiàn)有的論述少有從京津畫派的內(nèi)在發(fā)展線索、主要階段、代表人物以及風格演進等方面進行詳細的探討和研究。 “京津畫派”與“海派”比較
民國二三十年代,一場關于地域文化的論爭異常熱鬧,這就是“京海之爭”。1933年10月18日,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刊載了沈從文《文學者的態(tài)度》一文,因文中有“在上海賦閑”,“賦閑則每禮拜必有三五次談話會之類”的話,引起海上文人的反感,此后有杜衡起、曹聚仁、徐懋庸等人發(fā)文反擊,《大公報·文藝副刊》和《申報·自由談》成為這場論戰(zhàn)的主要陣地,此期間發(fā)表的文章還有沈從文的《關于“海派”》、曹聚仁的《續(xù)談“海派”》、蘇汶的《文人在上海》、青農(nóng)的《誰是“海派”?》、毅君的《怎樣清除“海派”?》、師陀的《“京派”與“海派”》、胡風的《再論京派海派及其他》以及姚雪垠的《京派與魔道》等。(朱少偉:《海派文化的起源及“京海”之爭》,《探索與爭鳴》2002年第12期)有學者指出“海派”通常也被用來指稱上海人所特有的某種作風做派,行為方式。(金志浩:《三十年代“京海之爭”》,《上海檔案》2003年第5期)這似乎不無道理,但是又不盡全面。1934年1月7日,沈從文在《大公報·文藝副刊>發(fā)表的((論“海派”》-文中講:…名士才情與‘商業(yè)競賣相結合,便成立了我們今天對于海派這個名詞的概念。但這個概念在一般人卻模模糊糊的。且試為引伸之:‘投機取巧,‘見風轉(zhuǎn)舵,一看情形不對時,即刻自首投降,且指認栽害友人,邀功牟利,也就是所謂海派。因慕渴出名,在作品之外去利用種種方法招搖;或與小刊物互通聲氣,自作有利于己的消息;或每書一出,各處請人批評;或偷掠他人作品,作為自己文章;或借用小報,去制造旁人謠言,傳述攝取不實”很明顯,沈從文在這里所指的“海派”乃是一種出現(xiàn)在上海地區(qū)的風氣現(xiàn)象,更多指向其中的一些文人在做人做事上的劣行,批評文學上的一些虛假現(xiàn)象,但是并未拿“海派”概括此地區(qū)的文風或文人的主流作風。所以,從“京海之爭”的現(xiàn)象可以看出,京派和海派這兩個概念的生成是指代兩個文化區(qū)域中的“偽惡”的一面,而不是“真善”的一面,其“爭”的實質(zhì)是在互相抨擊地域文化中弊病,而非是評價對方的文化精粹。魯迅先生于1934年2月3日《申報·自由談》中發(fā)表的《“京派”與“海派”》一文中則更加精確扼要地道出了兩者的區(qū)別:“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全國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獲利,而自己也賴以糊口。要而言之,不過“京派”是官的幫閑,“海派”則是商的幫忙而已。但從官得食者其情顯,到處難以掩飾,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據(jù)以有清濁之分。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國舊習,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魯迅:《“京派”和“海派”》,《魯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1月)
京海之爭雖然發(fā)自文學領域,其內(nèi)在的動因是關于兩個文化區(qū)域的不同文化趣味和品質(zhì)的相互比較,其中主要是互相攻訐和批評,但是卻也揭露出各自文化傳統(tǒng)中的弊病。更為重要的是由京海之爭引起了后來人們對于南北文化風格和形態(tài)差異比較的關注。美術史上出現(xiàn)“南吳北金”(分別指吳昌碩和金城)、“南張北溥…‘南黃北齊”等說法正是基于北京和上海兩個繪畫區(qū)域所體現(xiàn)出的不同的繪畫傳統(tǒng)的比較。
從繪畫角度講,“海派”是指1840年鴉片戰(zhàn)爭以后至民國初近百年內(nèi)在上海興起的繪畫流派。值得注意的是,它的興起與它之前的傳統(tǒng)繪畫流派有著很大的不同。關于海派的定義,單國強先生說:“海上繪畫不是單純在傳統(tǒng)基礎上的延續(xù)、發(fā)展和變革,它是中西文化撞擊和影響下的產(chǎn)物。上海畫家也不是以某名家為首領、師資傳承、風格相近的畫家群體,而是師承各別、畫法迥異的一批畫家。因此以傳統(tǒng)含義的‘流派角度看,它并未形成一個派別,然而,它在同一時代背景、地域氛圍、文化因緣孕育下生成,也形成了若干鮮明的共性”。(單國強:《試析“海派”含義》,《故宮博物院院刊》,1998年第2期)清中期以后,上海已經(jīng)成為東南地區(qū)的經(jīng)濟重鎮(zhèn),文化藝術亦有相當?shù)陌l(fā)展,書畫會活動頻繁,最早出現(xiàn)的有較詳細記載的書畫會組織是“平遠山房書畫集會”,其后有“吾園書畫集會”(據(jù)許志浩《中國美術社團漫錄》記載,我國有資料記載的最早成立的書畫團體是“墨林詩畫社”,清代初期成立于上海華亭縣(今松江縣),由曹重、朱雪田等人發(fā)起,但是具體活動不詳。“平遠山房書畫集會”于1792年成立于上海舊城之西,由李廷敬創(chuàng)辦和主持,其記載見于楊東山著《海上墨林》序言)、“小蓬萊書畫集會”(1839年秋成立于上海城隍廟南之小蓬萊,由蔣寶齡發(fā)起組織并主持)等畫會出現(xiàn),它們已經(jīng)有別于傳統(tǒng)的文人雅集和畫派聚會,擁有固定的組織機構和活動會址,活動內(nèi)容帶有相互提攜、播揚名聲和謀求經(jīng)濟利益的性質(zhì),且畫家?guī)煶杏袆e、風格多樣,總體上這種書畫會具有固定性、持續(xù)性和功利性。及至海上題襟館金石書畫會(清光緒中期成立,會長汪洵,副會長吳昌碩,會員有陸恢、王一亭、陳巨來、趙子云、曾熙、黃賓虹、錢瘦鐵、賀天健、馬駘、張石園、熊庚昌等七八十人,對上海畫壇產(chǎn)生巨大的影響,1916年秋停止活動)、豫園書畫善會(1909年3月3日成立于上海,由錢慧安、楊佩父、馬瑞西、吳昌碩、黃旭初、金城、王一亭等人共同發(fā)起組織,錢慧安擔任首任會長,并立有《豫園書畫善會緣起及章程》)等更具社團性質(zhì)的繪畫相繼興起后,上海地區(qū)逐漸形成了具有鮮明特色的上海畫家集群,而其藝術成就的代表則是被譽為“海派三大家”的趙之謙、任伯年和吳昌碩。
民初的北京畫壇有與之相似的情形。1915年成立的“宣南畫社”,是當時北京較早出現(xiàn)的美術社團,地點在宣武門外,是各地會館林立、京官府邸眾多、文玩商鋪繁榮的文人薈萃之地,也是帶有濃郁京土風情的文化圈。畫會的成員有湯定之、梁啟超、姚華、陳師曾、賀良樸、林紓、蕭俊賢、陳半丁、沈尹默、蕭愻、郁曼陀、王夢白等人。他們從藝術創(chuàng)作到藝術理念都具有與“海派”相異的風范,而此種現(xiàn)象亦全然借助于京津地區(qū)特殊的人文環(huán)境而生發(fā)出來,因此具有極強的生命力。
從“京津畫派”與“海派”的對應關系可以看到“京海之爭”的一個片面。筆者認為,這種比較是源于長久以來兩個地域文化形成的比較,對于兩地的傳統(tǒng)畫家來說,雖然都是在繼承和發(fā)展傳統(tǒng)中國畫,但是從兩地畫家身份的構成到具體的美術活動則體現(xiàn)出各自不同的特點,兩地呈現(xiàn)的文化差異使得這兩個畫家群體各具特色。因此,“京津畫派”這一指稱具有雙重含義——既指代一個藝術群體,又代表一種地域文化。也可以說,京津畫派的形成是不期然而然之事,是地域文化凝聚力的必然結果。 “京津畫派”的構成和藝術特點
從以上的分析來看,無論是“海派”還是“京派”,其形成都是與有別于傳統(tǒng)書畫雅集意義的繪畫社團的興起和畫家集群的誕生分不開的。而京津畫派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正是因循著這樣一個內(nèi)在的邏輯,即起初由少數(shù)畫家組成一個團體,繼而擴大影響,吸引更多的畫家,從而組成一個具有固定藝術宗旨和章程以及一定規(guī)模活動的繪畫社團,而由繪畫社團又輻射出一個總體藝術特征相近的畫家集群。我們分析民初京津畫壇傳統(tǒng)派骨干人物的籍貫可以發(fā)現(xiàn),其中南北方人相雜,大量成員并非出自京津地區(qū)。
從此表不難看出,民國初期寓于京城的傳統(tǒng)派畫家大多數(shù)并不是本土本籍的地方性畫家,他們與南方的畫壇有著很大的聯(lián)系(比如金城就參加過上海的豫國書畫善會,見許志浩:《中國美術期刊過眼錄(1911年-1949年)》,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第13頁),正是這種南北溝通和信息資源的交換使民初的北京傳統(tǒng)派畫壇并非我們想象的那樣沉寂、保守,從這個意義上看萬青力先生所說的“南風北漸,南方旅京畫家主導的局面”確實是當時北京傳統(tǒng)畫壇的一個特征。筆者從當時南北傳統(tǒng)書畫家交往密切的史實推斷北京傳統(tǒng)繪畫社團的成立也許受到了南方畫會的一定影響,至少從組織形制上得到了一定的借鑒。當然,“繪畫社團與集群既是一種社會現(xiàn)象,又是一種文化現(xiàn)象,是按照一定文化發(fā)生互動關系的人類共同體。……以繪畫集群作為一個特定文化單位的話,那么,在其內(nèi)部,成員間因出身、經(jīng)歷、個性、氣質(zhì)不同,會有若干小的集團或流派,它們之間對立統(tǒng)一、分化組合會極大地影響整個集群的發(fā)展走向。在集群外部,又無疑會受到它所生存的地域文化影響,與其他集群產(chǎn)生沖突融合的矛盾,同樣所有的繪畫集群之生存發(fā)展,又都受制于民族文化甚至世界文化發(fā)展的影響。”(喬志強:《近代繪畫社團與集群之社會文化學研究論綱》,《美術研究》,2004年第4期)應該講中國畫學研究會和湖社這樣極具規(guī)模的繪畫社團的成立是和北京獨有的政治、文化背景分不開的,影響其發(fā)生和發(fā)展的因素可謂復雜紛繁。而之所以促成京津繪畫社團獨有面貌,其文化環(huán)境中的一個淵源即來自于“京派”和“海派”的比較,而且事實證明自“海派”繪畫成熟化后不久,京津地區(qū)也逐漸形成了弘揚和發(fā)展傳統(tǒng)繪畫的畫家群與之遙相呼應,且兩者之間的對話也從來沒有間斷過,以致很多美術現(xiàn)象的發(fā)生源于這種比較和爭論。
1920年5月30日“中國畫學研究會”成立,終成為當時京津地區(qū)規(guī)模最大,影響力最強的美術團體,圍繞著它形成的京津畫家集群也是“京津畫派”人員構成的基礎。也有人提出“津門畫派”(崔之進:《論津門畫派的藝術特征及其主要代表人物的藝術特質(zhì)》)的概念,但是筆者認為從當時的畫家藝術成就和社團影響力來看,北京畫壇無疑處于主導地位,而所謂“津門畫派”的奠基畫家和代表人物如劉子久、陳少梅、張其翼等人,他們也大多數(shù)與北京的畫家和畫會有很大的聯(lián)系,(崔之進:《論津門畫派的藝術特征及其主要代表人物的藝術特質(zhì)》,【碩士學位論文】,天津大學,2006年)無論是師承還是藝術主張都受到北京畫壇傳統(tǒng)派的影響(像天津本土畫家劉奎齡這樣的名家,雖然自稱一種風格,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天津傳統(tǒng)繪畫中的一種面貌,但是與本問所指稱的京津畫派的畫家之群體風格特征并不相符,故而不在此范圍內(nèi),需另當別論),目.京津兩地的繪畫交流活動頻繁,北京的名畫家多數(shù)都在天津辦過展覽。京派傳統(tǒng)畫家通過建立湖社天津分會等繪畫社團組織為天津地區(qū)輸送和培養(yǎng)了一批畫家,因而在堅持傳統(tǒng)繪畫繼承上,天津的這部分畫家是和京城畫家相呼應的。所以從這個意義上應該說“津門的傳統(tǒng)派實為京派的流脈”(薛永年:《民國初期北京畫壇傳統(tǒng)派的再認識》,《美術觀察》,2002年第4期),在論述上應該合到一起而作為一個整體現(xiàn)象去討論。故而,從民國初期的京津畫壇來看,許多學者把其中的傳統(tǒng)派畫家集群廣義地概括為“京派”雖不為過,但是基于京津兩地密切的聯(lián)系和傳統(tǒng)畫家在這兩地集中頻繁的活動,用“京津畫派”這個指稱似乎更為嚴密準確一些。
京津畫派在藝術上能夠兼收并蓄,畫家中既有政府官僚與文人雅士,也有職業(yè)畫家與繪畫學員,作品中既有北方的粗獷厚重,同時也不失江南的細美幽約。他們以傳統(tǒng)筆墨功力為基礎,以西洋光影和寫生技法為借鑒,以院校教育和家傳或師承親授為傳承方式,它所包容的傳統(tǒng)畫家集群無論其規(guī)模影響還是對傳統(tǒng)繪畫的繼承和發(fā)揚都足以讓它成為民國時期舉足輕重的藝術群體。朱京生先生認為“所謂京派不應該只是一個地域概念,不應該指所有京籍或居京的中國畫畫家(林風眠、徐悲鴻等不應歸在其中,因為它們的藝術與北京特有的“文脈”沒有太大關系),它大約應該是以清末民初北京‘宣南畫社、‘中國畫學研究會、‘湖社、‘松風畫會等有著國粹傾向的藝術團體為中心的,長期或一度生活在北京且受到北京文化生態(tài)、藝術生態(tài)的深刻影響,同時又有著大致相同或類似的藝術主張(精研古法,博采新知)和追求的一批中國畫畫家和他們的弟子。”(朱京生:《京派繪畫四題》,《美術》2005年第8期)那么作為更加精準的新概念“京津畫派”也同樣適用于這個解釋。
筆者認為“京津畫派”的發(fā)生是和京津地域的傳統(tǒng)美術團體的發(fā)展緊密聯(lián)系著的,它的成熟化和影響力也是伴隨著繪畫團體的發(fā)展和興盛而日漸增強。它的“內(nèi)核”是“京派”的傳統(tǒng),它的外延卻擴展到了全國各地,其影響力甚至遠播世界(這當然與中西文化的交流和日益現(xiàn)代化的媒介傳播密不可分)。而“京津畫派”的輝煌時期也集中在民國二三十年代,尤與“湖社畫會”的十年活動關系密切。它所倡導的“保存國粹”的主張及對傳統(tǒng)中國畫所作出的不懈努力無論在民國時期還是在新中國時期乃至在今天的中國畫界都產(chǎn)生了非常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