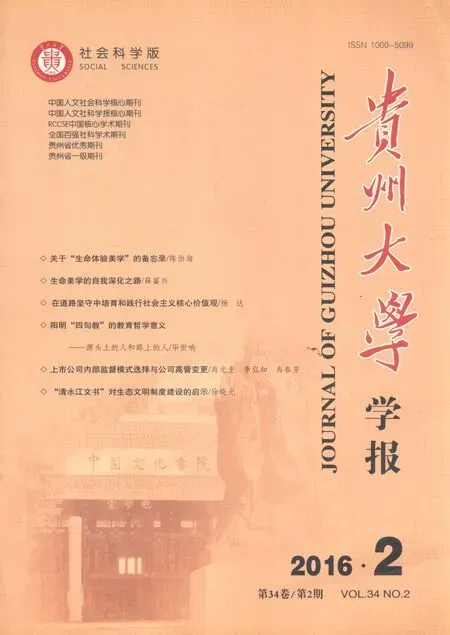清代黔東南亮寨龍氏土司家族的發(fā)展與演變
王勤美*
(中山大學(xué) 社會學(xué)與人類學(xué)學(xué)院, 廣東 廣州 510275)
?
清代黔東南亮寨龍氏土司家族的發(fā)展與演變
王勤美*
(中山大學(xué) 社會學(xué)與人類學(xué)學(xué)院, 廣東廣州510275)
摘要:以清代貴州東南部亮寨龍氏土司家族為例,討論西南邊陲的土著人群在特定的歷史情境下,通過借助修撰族譜、建造祠堂、參加科舉考試、建立地域性的宗族等文化策略與國家展開互動,借以掌握一套象征國家權(quán)力的話語,以確立其在國家秩序中的位置。
關(guān)鍵詞:龍氏土司;宗族建構(gòu);文化策略
注重血緣和地緣關(guān)系的宗族(或是家族)是地方社會結(jié)構(gòu)的重要組織形式,家譜作為宗族的象征和重要組成部分,其追述、紀(jì)錄了祖先的由來、遷移發(fā)展、以及宗族分支等內(nèi)容。歷史學(xué)和人類學(xué)的研究者將宗族的考察和族譜研究視作認(rèn)識和了解中國鄉(xiāng)村社會結(jié)構(gòu)的重要路徑之一①*①歷史學(xué)方面較具代表性的研究如:(日本)多賀秋五郎:《中國宗譜の硏究》,日本學(xué)術(shù)振興會,1981年;鄭振滿:《明清福建宗族組織與社會變遷》,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9年。。科大衛(wèi)、劉志偉有關(guān)珠三角宗族研究中指出,宗族既是一種獨特的社會意識形態(tài),又是一種社會經(jīng)濟(jì)關(guān)系,是“庶民用國家的禮教來把自己士紳化”[1],他們強(qiáng)調(diào)自己詩禮傳家,貼上“漢人”標(biāo)簽,炫耀門第,并將宗族視作為一種文化策略。[2]肖鳳霞等學(xué)者將帝國視為一個文化觀念,認(rèn)為帝國權(quán)威的隱喻向地方社會的滲透,并非只是自上而下地發(fā)布法令去實行,而是地方通過操控和運作宗族文化等國家權(quán)力象征,自下而上主動提升自己,以建立其在國家秩序中的位置。[3]此外,拉爾夫·利青格(Ralph Litzinger)指出瑤族知識分子如何以民族研究以及民族歷史的建構(gòu)作為行動工具,在當(dāng)代中國多族群的意象中,為瑤族的主體性尋找空間。[4]
正是在這樣的學(xué)術(shù)脈絡(luò)思考下,本文以清代貴州東南部的亮寨龍氏家族為個案,試圖討論西南邊陲的土著人群在與國家的互動中,如何借助編修族譜、建立祠堂、參加科舉考試、建立地域性的宗族等文化策略,進(jìn)以掌握一套象征國家權(quán)力的話語,與自我想象的“中心”確立聯(lián)系,以此回應(yīng)我族群體的政治文化訴求。
一、貴州苗疆開發(fā)與龍姓的定居入籍
1.關(guān)于亮司龍姓的定居與入籍
據(jù)家譜記載,始祖龍政忠,湖南會同巖壁人,洪武四年,其隨明朝大軍入黔平蠻,從征白巖塘銅關(guān)鐵寨等處有功,被授“承直郎并亮寨蠻夷長官司正長官”之職,由此定居于亮司。同治三年成書的龍氏家譜《迪光錄》載錄:
狀供遠(yuǎn)祖,于漢時有功,歷授本司正長官職事。自漢、唐、宋、元、明,仍授前職,遺至始祖龍政忠,于洪武二年歸附仍授前職,洪武四年,內(nèi)奉調(diào)帶兵征進(jìn)白崖塘銅關(guān)鐵寨等處有功,除授世襲不支奉承直郎亮寨蠻夷長官司正長官職事,頒給銅印一顆、誥命一道。二世祖龍友仁系政忠嫡長親男,于本年八月內(nèi)承襲,洪武十六年四月內(nèi)病故,無嗣。龍友義系政忠次男,友仁胞弟,于本年十月內(nèi)承襲,洪武十八年因草寇吳面兒作耗,前項印信誥命丟去,洪武二十四年七月內(nèi)病故。三世祖龍志誠系友義嫡長親男,于洪武二十五年二月內(nèi)承襲,洪武三十年因林小廝作耗,調(diào)取志誠征討,永樂元年二月內(nèi)復(fù)頒銅印一顆,正統(tǒng)十二年三月內(nèi)病故。*參見(清)龍紹訥:《龍氏迪光錄·長官司圖冊式》卷三,光緒四年刻本,錦屏檔案局藏。
明初朱元璋西征,軍隊進(jìn)入亮江流域,每到一處就“撥軍下屯、撥民下寨”,軍屯在內(nèi)的土地占用造成苗侗土著的土地急劇流失,從而導(dǎo)致“軍、民、苗”不同人群之間的對抗。洪武十一年(1378),黎平侗民吳勉揭竿而起,亮江地區(qū)的“十二長官司悉應(yīng)之”。洪武三十年(1397),錦屏婆洞的林寬再次起事,喊出“打回新化,奪回土地”的口號,明軍統(tǒng)兵五萬討古州蠻寇林寬等*參見《太祖洪武實錄》卷二五二,第六頁。。據(jù)龍姓家譜的敘述,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龍政忠、龍友仁、龍志成三位祖先順應(yīng)時世,接受朝廷調(diào)遣,參與平定“苗蠻”,建立功勛,世襲亮寨土司職權(quán),入住亮司。
始祖龍政忠先后生了友仁、友義二子,長子友仁無嗣,次子友義襲替父職,明代土司實行嫡長子繼承制,如若長房無后,可由堂弟或堂弟之子接任。到了四世祖龍永福,先后生了寬、正、海、清四子,龍姓始分四大房,而七世祖龍鳳生韜、璋、珠、夏、滾、現(xiàn)六子,至此長房再次分為六支。隨著世代的繁衍,家族規(guī)模也在不斷的擴(kuò)大,到了清乾隆壬寅(1782)年龍文和修譜時,“三房無嗣,二、四、五房人戶亦少,其最繁者長房,六房次之,七房又次之”,這樣龍姓形成了以長房(也就是世襲土司的一房)為中心的家族系統(tǒng)。
2.宗族何以成為一種文化策略
湘黔界鄰地區(qū)的亮江流域,明代漸次進(jìn)入王朝國家的直接控制,先后出現(xiàn)了黎平府、新化府、五開衛(wèi)、銅鼓衛(wèi)、新化所、隆里所以及亮寨、潭溪等十二長官司,形成了衛(wèi)所、土司、府州縣犬牙交錯的政治格局。清雍正年間,隨著鄂爾泰、張廣泗開辟“苗疆”、疏浚清水江的軍事行動,作為清水江下游支流的亮江得以通航,商貿(mào)日漸發(fā)達(dá),地處亮江中游的亮寨仰賴著天時地利,成為重要的商埠碼頭,在黎平府下轄的眾土司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據(jù)家譜《迪光錄》的記載,自明洪武四年(1371)第一任長官龍政忠始,至清道光七年(1827)最后一任長官龍家謨止,亮寨龍姓共有23人相繼世襲土司之職,歷經(jīng)明清兩朝,長達(dá)456年,前后共領(lǐng)銅印五顆。而各種史料的記載顯示,這一時期的龍氏土司活動頻繁,對朝廷表現(xiàn)出較為積極的姿態(tài),不時朝覲貢馬,與黎平府的關(guān)系也不一般,在同級的土司中頗為突出。整個明清時期,亮司地方社會都在龍姓的控制之下,其家族的發(fā)展壯大都與之密切相關(guān)。就文化策略視角頁言,可從如下兩個方位進(jìn)行分析。
(1)明清以來宗族禮制的改革
朱熹為代表的宋儒時代,只有帝王貴族有權(quán)為祖先立廟祭祀,庶民并沒有為祖先建廟的資格,頂多在墓地旁邊搭建一個小房子,或是家中掛上祖先畫像,履行酒禮焚香,稱為“影堂”。明嘉靖十五年,夏言題請“官自三品以上為五廟,以下皆為四廟。為五廟者,三間五架,中為二室,附高、曾,左右為二室,附祖、禰。”*參見夏言:《桂洲奏議》卷12《請定功臣配享及令臣民祭祀始祖立家廟疏》。夏言這一“詔天下臣工建立家廟”的奏疏,得到了當(dāng)時廣東士大夫霍濤、方獻(xiàn)夫等人的積極支持,這樣,到了萬歷年間,《大明會典》還專門立了“品官家廟”的條目,對不同品官階層能的祠堂規(guī)制做了描述和限制。
雍正二年,清世宗頒布《圣諭廣訓(xùn)》,對康熙九年的十六條圣諭進(jìn)行了更為詳盡的解說,其中的第一條就是強(qiáng)調(diào)對父母兄弟的孝悌之義。雍正帝提倡“以孝治天下”,尤為重視孝道,并將此視為維系國家秩序的道德標(biāo)準(zhǔn)。第二條“篤宗族以昭雍睦”,其實,兩條內(nèi)容是相輔相成的。雍正帝認(rèn)為“故人之待其宗族也,必如身之有四肢百體,務(wù)使血脈相通,而疴癢相關(guān)”,試圖在地方社會推廣尊親孝悌、敬宗睦族的思想倫理,通過對宗族的控制進(jìn)而達(dá)到間接治理地方社會的目的,誠如雍正帝所說:
凡屬一家一姓,當(dāng)念乃祖乃宗,寧厚毋薄,寧親毋疏,長幼必以序相治,尊卑必以分相聯(lián)。喜則相慶,以結(jié)其綢繆,戚則相憐,以通其緩急。立家廟,以薦蒸嘗;設(shè)家塾,以課子弟;置義田,以贍貧乏;修族譜,以聯(lián)疏遠(yuǎn)。即單姓寒門或有未逮,亦隨其力所能為,以自篤其親屬,誠使一姓之中秩序藹然。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兄與兄言友,弟與弟言恭。雍睦昭孝弟之行愈敦。有司表為仁里,君子稱為義門,天下推為望族,豈不美哉!若以小故而墮宗支,以微疑而傷親愛,以侮慢而違遜讓之風(fēng),以偷薄而虧敦睦之誼,古道之不存,即為國典所不恕。爾兵民其交相勸勵,共體祖宗慈愛之心,常切水木本源之念,將見親睦之俗成于一鄉(xiāng)一邑,雍和之氣達(dá)于薄海內(nèi)外。諸福咸臻,太平有象,胥在是矣。[5]
雍正皇帝提倡立家廟,修族譜,設(shè)私塾,其目的是要將臣民與其所在的宗族建立和諧的關(guān)系,只有家庭、宗族和睦,王朝的統(tǒng)治秩序才能得以維系。乾隆時期更是出臺了“凡子孫盜賣祖遺祀產(chǎn)至五十畝,照投獻(xiàn)捏賣祖墳山地例,發(fā)邊遠(yuǎn)充軍”保護(hù)條例,將祀產(chǎn)、祭田、墓田、宗祠視為宗族共有財產(chǎn)。實際上,清朝的官方態(tài)度不僅否定了宗法主義,而且將象征宗法實現(xiàn)的祠堂、義田、族譜、家塾等作為統(tǒng)合的物質(zhì)基礎(chǔ)排斥在正式的禮制框架之外,這是對現(xiàn)實妥協(xié)的一種策略。[6]可以說,清代國家對宗族的積極態(tài)度,直接影響到了地方社會宗族的發(fā)展。
(2)科舉教育的推展與士大夫階層的涌現(xiàn)
相比于“內(nèi)古州”的苗疆生界,地處外古州的亮江地區(qū),最晚已在明永樂年間開始了國家的文字化歷程。據(jù)史料記載,永樂年間,新化府*永樂十一年(1431),析思州、思南宣慰治地設(shè)思南、鎮(zhèn)遠(yuǎn)、銅仁、烏羅、新化、黎平、鎮(zhèn)遠(yuǎn)、石阡八府;永樂十二年(1415 年)三月,貴州布政司所轄的湖耳、亮寨、毆陽、新化、中林驗洞、龍里、赤溪湳洞長官司隸新化府;永樂二十二年(1434),因地狹人稀新化府并入黎平府,亮寨土司并入黎平府管轄。就設(shè)有儒學(xué)、醫(yī)學(xué)、陰陽學(xué)等,宣德年間,亮寨土司聯(lián)合新化府所轄六土司向朝廷請奏:“童蒙入學(xué),若比內(nèi)地府學(xué)每歲選貢,實無其人,請比縣學(xué)三年一貢,上以邊郡立學(xué),欲其從化耳,不可遽責(zé)成材,各所司隨宜選貢。”*參見《宣宗宣德實錄》卷三十二,第6頁。有明一代,國家對貴州苗疆的教育是有針對性的,土司子弟可以接受國學(xué)受業(yè),以通君臣父子之道,禮樂教化之事,使土俗同于中國。而這與其說是一種特權(quán)還不如說是一項必須的義務(wù),按照當(dāng)時土司的承襲規(guī)定,其中一條就是土司候選人必須識漢字、習(xí)漢禮,而水平的高低會作為考核的標(biāo)準(zhǔn)。盡管如此,身為世襲貴族的土司世子并不允許參加科舉考試,以免占據(jù)流官選拔的有限名額,而下到一般的苗民庶族就連讀書識字的機(jī)會都極為渺茫。直至康熙四十三年(1704),時任貴州封疆大吏的于準(zhǔn)呈《苗民久入版圖請開上進(jìn)之途》稱:
貴州遍地皆苗,種類頗繁,官士斯者,視苗如草芥;居斯土者,擯苗為異為類,既不鼓舞,又不教習(xí),遂使若輩沉淪黑海,罔見天日。應(yīng)將土司族屬人等,并選苗人之俊秀者,使之入學(xué)肄業(yè),一體科舉,一體廩貢,既久苗民變少為漢,苗俗漸少化而為淳,邊來遐荒之地,盡變中原文物之邦。[6]
次年朝廷準(zhǔn)議,貴州苗民可以依照湖廣例,以民籍應(yīng)試,進(jìn)額不必加增,卷面不必分別,土官土目之子弟仍準(zhǔn)一體考試。雍正八年(1730)貴州巡撫張廣泗題請《請設(shè)苗疆義學(xué)疏》、《考試分棚疏》,在這樣的形勢下,各府州縣始設(shè)義學(xué),“將土司承襲子弟,送學(xué)肄業(yè),以俟襲替其族屬人,并苗民子弟愿入學(xué)者,亦令送學(xué),并頒發(fā)御書,匾額奉縣各義學(xué)。”[7]可以說,向苗人子弟開放科舉,使得土司子弟和苗民群體踏上科舉仕途之路,這在貴州教育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這無疑是龍姓人期待已久的事情,乾隆年間,龍姓在宗祠、二樟堂(庵廟)、哪伽寺內(nèi)辦公學(xué),設(shè)書院,就連治下的九南寨亦積極響應(yīng),設(shè)立義學(xué),建崇圣宮。這一時期的教育主要以《三字經(jīng)》、《增廣賢文》、《幼學(xué)瓊林》、《百家姓》、《四書》、《五經(jīng)》等科目做啟蒙教材,教育的推廣和普及為苗民子弟提供了學(xué)漢語、識漢字、接受漢文化的機(jī)會。我們無從知曉地方實施的具體細(xì)節(jié),但從題為《凌云館碑》的興教辦學(xué)碑,可大概看出康乾之后,隨著文字下鄉(xiāng)和科舉取仕的推展,亮江地方社會積極應(yīng)因的情景:
世俗矜驕之習(xí),大家怙侈之風(fēng),先王以為非鄉(xiāng)學(xué)之所能稽也,故立國學(xué)以教之;四民頑梗之風(fēng),五方蠢愚之習(xí),先王以為非國學(xué)之所能遍也,故又立鄉(xiāng)學(xué)以教之。所以負(fù)表橫徑,野處亦不匿其秀;而砥行礪德,上國亦可觀其光。……吾鄉(xiāng)雖僻壤,久有文人學(xué)士之風(fēng),各姓先祖,負(fù)□來游,亦知鐘點鼓之靈,鸞旗之澤。先于乾隆間已立義學(xué),崇建圣宮,額“凌云”之號,無知如俸資歉乏成功。蓋難百余年來,人才依然告竭,而文章顯耀經(jīng)明,行修之士,仍難覯多人。茲有里中好義之熊君禮科者,因不吝囊金承蠲學(xué)。今日后,吾鄉(xiāng)子弟,咸論秀而樸,樸而造,崇儒重道,文教日昌。*此碑無明顯的年代記載,據(jù)內(nèi)容分析,大概刊刻于乾隆之后。1990年,九南小學(xué)新教學(xué)樓建成后,將碑文磨平刻上新學(xué)校建設(shè)的內(nèi)容,今立于操場邊。
碑刻文字生動地展現(xiàn)了國家教育對苗疆社會產(chǎn)生的深刻影響,苗民開始自覺引導(dǎo)子弟“崇儒重道”,讀書上進(jìn)。龍氏家族注重教育,并通過培養(yǎng)出功名之人,進(jìn)一步掌握地方話語權(quán),以此實現(xiàn)家族的發(fā)展壯大。據(jù)《迪光錄》所述,康熙至清末二百年間,亮寨教育延續(xù)不輟,人文蔚起,龍氏家族共涌現(xiàn)仕宦類20人,科第類5人,文學(xué)類5人,恩貢22人,例貢5人,監(jiān)生27人,廩生21人,增生14人,文庠147人,武庠26人。出仕做官的有長房人龍亨極,康熙辛卯年(1711)獲貴州鄉(xiāng)試第三十四名舉人,官至四川安岳縣知縣,龍文和乃乾隆癸酉年(1776)貴州鄉(xiāng)試副榜,后出任湖南安化縣教諭,《迪光錄》的集大成者龍紹訥,為道光舉人。
值得一提的是,雍正十三年(1735),亮寨司十七世長官龍紹儉向貴州學(xué)政晏斯盛請求參加鄉(xiāng)試,雍正皇帝本人親自下詔應(yīng)允其“一體應(yīng)試”,如若考中,可推選別的龍姓成員承襲土司職,*參見(清) 龍紹訥:《龍氏迪光錄·舊典》卷三,光緒四年刻本,錦屏縣檔案局藏。而據(jù)說這是中國西南歷史上,第一個土司參加科舉考試的先例,由此可見清代龍姓在亮江地區(qū)顯赫的地位。毫無疑問,家族成員在科舉道路上的成功,是龍姓成為地方望族極為重要的資源,一個依靠正統(tǒng)文化規(guī)范發(fā)展壯大的宗族,勢必會利用這些文化規(guī)范去建立更為制度化的宗族組織。
三、龍氏宗族實體的建構(gòu)過程
雖然姓氏家族是一個基于血緣繼嗣關(guān)系而形成的群體,但祖先的遷移也好,定居也罷,都不意味著宗族的建立,大凡對宗族研究有所涉獵的學(xué)者都知道,宗族的形成并非是一個簡單的生殖繁衍過程,更多的是一系列社會行為疊加的文化過程。宗族實體的最終形成需要借助家譜編修,建立祠堂祖墓,規(guī)范祭祖禮儀以及創(chuàng)立宗族共有財產(chǎn),并以此為依托不斷培養(yǎng)出獲得功名的家族成員等一系列儀式性和制度性的舉措才得以完成。
1.修建龍氏祠堂,樹立地方權(quán)威
修建祖先祠堂是整合宗族,加強(qiáng)成員凝聚力的重要手段,在亮司龍姓的發(fā)展歷史上,亦不例外。明末清初,龍姓家族財富也不斷積累,對于一個世襲土司之職的貴族之家而言,加之康熙開放科舉以來,龍姓已培養(yǎng)出大量有功名之人,修建祠堂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情。乾隆五十五年(1783),在龍文廣、龍文和的積極倡導(dǎo)下,龍姓始修宗祠,甲辰(1784年)破土立柱,乙巳(1785年)完工落成。據(jù)《迪光錄》收錄了一則《新祠堂碑記》,其內(nèi)容如下:
祠堂者,報本追遠(yuǎn),敬宗收族,以時習(xí)禮之地也。禮祀蒸嘗之,不舉恩誼倫理之,不明恭敬揖遜之,不篤非所以為人,是故祠堂重焉。朱子家禮一書所當(dāng)列乎,其間相與講諭,而率由之也。頭基非宏敞則湫隘,終嫌制不莊嚴(yán),則茍且何貴,有心者觀舊祠之卑小荒涼,未嘗不喟然長嘆也,今歲壬辰夏五月,宗孫禹夫挈室徙安慶,其所購遁園既莫之居,司人乃以數(shù)百金購之,禹夫曰予為此勞心血者數(shù)年,今雖南遷,千秋后魂魄獨思此,尋慰而解之,曰君尚介介,于是乎君為龍氏大宗,以大宗之室妥歷代之靈當(dāng)亦君之所安者,就合鵲巢鳩居亦盈虛消長之理所時有也,其又何憾焉君之悲,宗族之幸也。*參見(清) 龍紹訥:《龍氏迪光錄·遺文》卷四,光緒四年刻本,錦屏檔案局藏。
碑記的撰寫者是龍文和,乾隆六年(1741)貴州應(yīng)童子試拔第一,然而時運不佳,鄉(xiāng)闈輒蹶,乾隆癸酉(1753)科誤中副車,郁郁不得志,乃放浪形骸,大有“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感,惟孜孜以授徒養(yǎng)親為事,尤深于易象春秋和醫(yī)學(xué)地理,后出任湖南安化縣教諭。這段文字詳細(xì)敘述了修建祠堂的過程,強(qiáng)調(diào)了祠堂對于敬宗收族,以時習(xí)禮的重要性。引文中出現(xiàn)的宗孫禹夫,也就是上文提及的第一個獲準(zhǔn)科舉考試的土司龍紹儉,其字禹夫,號遁園居士,雍正七年(1729),以郡庠身份承襲亮寨土司長官。他一生熱心功名,兩度會考,因弟死己病均不得志,尤嗜購書,家有藏書數(shù)千卷,遍讀唐詩,悉心評點,著有《周易簡》2卷、《全黔人鑒》1卷、《廣義》4卷、《聲律易簡》2卷、《黎平府志》15卷、詩文8卷,后因無力付梓,藏諸箱底。乾隆三十六年(1771)二月,因揭發(fā)黎平知府王勛索賄土司林秉虔銀兩,反被人誣告,獲罪下獄,三十七年(1772)依照軍例,攜帶妻兒發(fā)配安徽安慶懷寧縣,這就是碑記中所說的“禹夫挈室徙安慶”事件。龍紹儉遠(yuǎn)走異鄉(xiāng)后,原居住地“遁園”日漸閑暇荒蕪,族人認(rèn)為“用以大宗之室妥歷代之靈當(dāng)亦君之所安者,就合鵲巢鳩居亦盈虛消長之理所時有也”,于是買來作為祠堂宅基,而這恰恰也是龍紹儉本人的意愿,此時的他飄搖異鄉(xiāng),前途未卜,每每念及客死他鄉(xiāng),魂魄無所皈依,不禁潸然淚下,于是再三叮囑族人一定要修建祠堂以祭奠祖先之靈,想來也甚是悲涼。
建成后的龍氏宗祠規(guī)模宏大,取名為“敦厚堂”,為三進(jìn)三出磚瓦樣式,包括內(nèi)外寢廳各五間,左右?guī)扛魅g,前廳建有“偉績丹心”坊一座,為前門,門前月池一口,池處甬墻一堵,左右立有轅門,墻四周三十六丈,合周天之?dāng)?shù)。祠內(nèi)種桂樹二株,一本十余干,左雄右雌,枝葉濃密,圓如帽頂,遠(yuǎn)近罕見,正寢雕鏤金漆神龕二座。道光二十九年(1819)龍周行、龍紹訥等增修,加祠左邊客廳三間。清代龍氏宗祠的修建,是家族整合的標(biāo)志,此后數(shù)百年間,敦厚堂一直作為亮司龍姓的象征,對成員形成了極強(qiáng)的凝聚力,同時也預(yù)示著龍姓家族的權(quán)威。
2.制定家規(guī)章程,實踐祭祖儀禮
祠堂既已建成,那么制定祠堂管理制度,規(guī)范祭祖禮儀就成了維系家族必須的舉措。譜牒中收錄了數(shù)十例家規(guī)條約,對祠堂的管理、春秋祭祀、族譜的使用和保存,以及宗族成員的責(zé)任和義務(wù)做了明晰的規(guī)定,在此僅選取與主題相關(guān)的幾條,摘引如下:
1.譜牒當(dāng)慎重收藏,非春秋祭宣讀,不許輕動,倘要開閱,必先焚香以告,如有無故擅自翻閱甚至賣祖討喫,將履歷開與同姓不宗之人,發(fā)覺者送官究治。
2.譜當(dāng)三十年一修,三十年不修必至遺忘散失,凡我族讀書人曉大義者,須留意焉。
3.祠內(nèi)必于族中擇一老成忠直之人任事,凡事必稟命任事而后行,新老任事二人,以備補(bǔ)缺。每年執(zhí)事二人自春秋祭日始至,太祖誕日終,在祠公議,上交下接,不得私交,不得推托,收股之日,執(zhí)事人照管如收,不足親身取討,入倉之時,出入清理,每與祭不著分金,先期在祠辦事,祠上僅供飯食,不許醉飽酒肉,如違罰銀一兩。
4.祠用費照依舊規(guī),不得過奢,亦不得過儉;祭器若干,該執(zhí)事人清查載簿交代,如有遺失,除賠償外,罰銀一兩;生辰及春秋祭祀,執(zhí)事人先期清掃省牲滌器,如有怠緩廢事者,罰銀一兩五錢;生辰及春秋祭祀,執(zhí)事人必先期十日出貼通知,遲延者議罰。
5.凡有功名者,除年六十歲以上,均當(dāng)與祭,如有要緊事故,必先期到祠報明,如不到者罰香資一兩,至年七十歲以上,力能入祠祭祀拜跪,準(zhǔn)飲福酒不取分金。
6.祠堂乃祖宗之靈爽所棲,凡族中事故無關(guān)倫常要件者,不許擅開,違者罰銀三兩。
7.差徭既系同族,自應(yīng)均派,但學(xué)宮碑刻所載凡生監(jiān)之家,一應(yīng)差役俱免,原屬優(yōu)恤士子之意,嗣后族中差役不派監(jiān)生,非異視也,勉子弟讀書以求上進(jìn)以榮祖宗耳。
8.先人藏書,大清律例一部二十四本,大學(xué)衍義五十本,文獻(xiàn)通考十二本,遠(yuǎn)淵監(jiān)類函二百本,子史精華四十八本,貴州通志三十二冊,黎平府志兩函。有志者來祠批覽,不準(zhǔn)他揣。*參見(清) 龍紹訥:《龍氏迪光錄·舊典》卷三,光緒四年刻本,錦屏檔案局藏。
上述家規(guī)的主要制定者,也是祠堂的倡建之人龍文廣,乾隆五十五年(1790)貢生,先后任江西直隸州州判,贛縣縣丞,凡歷仕途十六年,卓有政聲。事政而不廢學(xué),以文交友,賓朋嘆服,贊其文章“詞簡而明,筆勁以達(dá)”。嘉慶十二年(1807),因病告歸,復(fù)授徒于司內(nèi)純一堂,清代亮司進(jìn)士曾統(tǒng)一、舉人龍紹訥、朱達(dá)清等皆受業(yè)其門。家規(guī)條目中,讓人耳目一新的是最后兩條,龍姓家族內(nèi)凡有監(jiān)生以上功名的家庭,可以免除徭役,年七十者,春秋祭祀可免費享用福酒,龍姓用這樣獨特方式的鼓勵子弟讀書上進(jìn),這在苗疆腹地實屬難得。不僅如此,祠堂就是家族圖書館,藏書豐富,種類繁多,涵蓋國家律例,地方史志可供成員借閱。也難怪乎,亮司龍姓能在康熙開科取士之后短短兩百年的時間里,培養(yǎng)出各類功名仕宦人士多達(dá)270多名。
毫無疑問,王朝國家對西南邊疆實施文質(zhì)教化,允許苗人土著參加科舉應(yīng)試的政策,深刻影響到了龍姓人對自己歷史文化的思考,漢語語言及漢文字書寫系統(tǒng)進(jìn)入地方社會后所引發(fā)一連串的反應(yīng)躍然紙上。
3.家譜編修,追述祖先源流
對于一個宗族而言,家譜既是一種文化意義的關(guān)鍵象征,同時對宗族實體的擴(kuò)張和維系也有重要的作用,家譜的編修既是對某一部分宗族成員的整合,同時也帶有極強(qiáng)的排他性。在龍姓家族的歷史上,修過三次家譜,乾隆任寅年(1782),乘家祠落成之機(jī),龍文和動員族人修了家譜,并在序言中首次提出了修譜的步驟和方法:
雖兩次勒碑于祠,然未見分曉,愛約集宗族,自二十三世始至分七房,后按世次清查,房具一本,以便合修,時老練達(dá)者皆曰善。乃卒為之,邱墓、科第、仕宦、明經(jīng)、俊秀、輿夫、孝友、方正、節(jié)孝、耆德、祠廟、村寨、山川之類為一冊,而終之以藝文既峻厥事。*參見(清)龍紹訥:《龍氏迪光錄·修譜原序》卷首,光緒四年刻本,錦屏檔案局藏。
可以說,龍文和將家譜分類、分冊的意見對日后龍紹訥采用地方志與家乘結(jié)合編撰《迪光錄》產(chǎn)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龍紹訥,生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卒于同治十一年(1873),被今人尊為錦屏名儒和著名苗族詩人。據(jù)弟子吳師賢為其撰寫的《木齋先生墓志銘》所贊,其自幼天資穎異,“長為文,矯矯不群”,十七歲并“應(yīng)童子試 ,冠一軍”,入學(xué)為秀才,歲試均列優(yōu)等。然而一生仕途多舛,屢次科舉均名落孫山,四十四歲才中舉人,眼看年過五旬,遂絕意仕進(jìn),于鄉(xiāng)間開館授徒,致力于詩文創(chuàng)作。隨后傾注心血,同治三年(1864)“閱數(shù)十寒暑成龍氏族譜八卷”,命名為《迪光錄》。此八卷家乘涵蓋卷首序言、君恩祖德、地靈人杰、舊典遺文和譜系,近三十萬字,其中卷首由凡例、序、年表、圖五部分組成,收錄序言多達(dá)22首,有服圖、襲替圖、居宅圖、邱墓圖共39幅插圖。有別于一般的家譜文類,其采用“家譜、地方史志、蠻夷長官司志”三合一的編修體例,將地方大事件與家族源流相結(jié)合,縱向上敘述了明洪武至晚清時期亮寨龍氏土司家族的發(fā)展及長官司的更迭,橫向上展現(xiàn)了同時期清水江及亮江流域的山川古跡、形勝風(fēng)俗。不言自明的是,這樣的的架構(gòu)安排,不僅彰顯了明清時期龍氏土司在亮江地方社會中的突出地位,同時也從另一個側(cè)面也反映出王朝禮儀傳統(tǒng)和漢文字教育對貴州苗疆社會的深遠(yuǎn)影響。
縱觀明清時期的家譜,大都會追溯到某個時代的顯赫遠(yuǎn)祖,攀附名門,以此來標(biāo)榜族群簪纓世胄的高貴血統(tǒng)。家譜中最早的序言聲稱抄自“龍氏老譜”,其署名是東漢文人蔡文姬的父親“陳留蔡邕伯喈”。清代的這次修譜,再次強(qiáng)調(diào)了龍姓來源的正統(tǒng)性,精心制作的22首序言將龍姓族裔的來源追述到宋代,其時龍氏先祖自南京應(yīng)天府,后到江西做官,這位先祖“若河?xùn)|衛(wèi)輝及黔楚皆其所游歷平定地也”,當(dāng)了宋朝的黔楚招討使,被派往楚地,封了王,后代成了楚人,之后家族壯大分支,其中一支到了亮寨,因軍功授了土司職。我們很難考辨和揣度龍姓家譜這些敘述的真實性,或許可以說,關(guān)于早期祖先事功及受封土司的記載不詳,并非疏漏,而是出于當(dāng)時社會環(huán)境之下某種需要而有意為之,其動機(jī)就是要從源頭上與“苗蠻”劃分開來,從而說明其身份的正統(tǒng)性。
四、 結(jié)語
在傳統(tǒng)中國社會中,與宗族禮制相關(guān)的族譜編修、祠堂規(guī)制都經(jīng)了一個由王朝、貴族階層逐漸演變,被挪用、模仿,最后進(jìn)入庶民之家的歷程。具體到地方社會,宗族已演變?yōu)橐惶滓揽垦壓偷鼐壝}絡(luò)形成的有關(guān)祭祖、財富繼承、宗親聯(lián)結(jié)甚至政治權(quán)力的復(fù)合體,宗族建構(gòu)的過程也是一個可以詮釋、虛構(gòu)、再造歷史和文化的過程。縱觀龍姓宗族的歷史敘述,其以“原籍江西泰和縣”“漢時以受功”“有自明以來宗支圖冊可考”而載入地方志和家譜中,看似虛構(gòu)的祖先歷史傳說及身份塑造,是在特定的社會情境下土著族群一種有意識的表達(dá),有著相當(dāng)實際的效用。“在宗族歷史敘述中,無論是真實記錄也好,附會虛飾也好,都是后來被刻意記錄下來的,因而是人們一種有意識的集體記憶,而這種集體記憶,在地方社會發(fā)展的歷史過程,更有其特定的社會和文化意義。”[8]在地方與國家的互動中,試圖攀升的龍姓土司借助家譜撰寫、祠堂修建、踐行士大夫行為、宗族建構(gòu)等文化策略,掌握了一套象征國家權(quán)力的話語,以確定其在地方統(tǒng)治的合法性與權(quán)威性,進(jìn)以尋求其在國家歷史坐標(biāo)中的位置。
參考文獻(xiàn):
[1]科大衛(wèi),劉志偉.宗族與地方社會的國家認(rèn)同——明清時期華南宗族發(fā)展的意識形態(tài)基礎(chǔ)[J].歷史研究,2000(3).
[2]David Faure.The Lineage as a Cultural Invention: the case of Pearl River Delta[M].Modern China,1989,15(1).
[3]肖鳳霞,劉志偉.宗族、市場、盜寇與疍民——明以后珠江三角洲的族群與社會[J].中國社會經(jīng)濟(jì)史研究,2004(3).
[4]〔USA〕Ralph A Litzinger. Other Chinas:The Yao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Belonging[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5]〔清〕 昆岡等修,劉啟瑞等纂.欽定大清會典事例: 卷三九七〈禮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清光緒石印本影印.
[6]〔日〕井上徹.中國的宗族與國家禮制——從宗法主義角度所做的分析[M].錢杭,譯.上海: 上海圖書出版社,2008:202.
[7]黎平縣志編纂委員會.黎平縣志[M].點校本.北京:方志出版社,2014:512.
[8]劉志偉.附會、傳說與歷史真實[M]//王鶴鳴.中國譜牒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57.
(責(zé)任編輯楊軍昌)
國際DOI編碼:10.15958/j.cnki.gdxbshb.2016.02.016
中圖分類號:K281/288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1000-5099(2016)02-0114-07
作者簡介:王勤美(1986—),女,云南楚雄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族群歷史與區(qū)域文化、歷史人類學(xué)。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biāo)項目“清水江文書整理與研究”(11&ZD096);廣東高校優(yōu)秀青年創(chuàng)新人才培養(yǎng)計劃項目“反思西南民族地區(qū)的移民歷史與族群關(guān)系:以清水江流域為中心”(2012WYM_0039)
收稿日期:2015-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