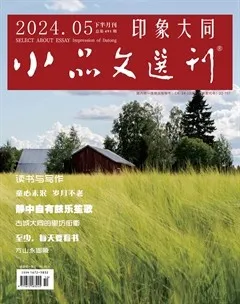《詩經(jīng)》里的枸杞
林衛(wèi)輝

《詩經(jīng)》在《小雅·杕杜》首次提到枸杞。《詩經(jīng)》中“雅”部分,分為大雅、小雅。雅樂,即正調(diào),朝廷之音,也指當時西周都城鎬京地區(qū)的詩歌樂調(diào)。這是一首妻子思念長年在外服役的丈夫的詩歌,也有說是夫思妻的。此詩主要采用賦和興的手法表現(xiàn)主人公真摯深切的感情,也反映出長期的戍役給下民帶來的痛苦,全詩分四章,每章七句,說到枸杞的是第三章:“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大意是,登上北山高山坡,采摘枸杞頗奔波。國家戰(zhàn)事無休止,擔心父母心傷悲。檀木役車已破敗,拉車四馬也疲憊,征人也應(yīng)快回歸。
枸杞還在《小雅》里又露了四次面。在《小雅·湛露》這首寫貴族們在舉行宴會,盡情飲樂互相贊揚的詩里:“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說的是早晨露珠灑在枸杞酸棗叢,這就如光明磊落的君子,個個都有好名聲。在《小雅·北山》里居然一字不漏照抄《小雅·杕杜》,也是“陟彼北山,言采其杞”。不過后面一章的幾句讓后人不停傳誦:“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一位下層官吏到北山采枸杞,抱怨勞逸不均,抱怨歸抱怨,小人物改變不了現(xiàn)狀,只有憂傷和憤慨。在《小雅·南山有臺》里有“南山有杞,北山有李”“南山有枸,北山有楰”等用枸杞樹等樹木歌領(lǐng)王公高山仰止,令人肅然起敬。在《小雅·四月》里則有“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一個被放逐至南方的臣子自喻為山上生長的蕨菜薇菜,濕地里生長的枸杞赤楝,至于這些植物是北方的還是南方的,都有可能。
枸杞是茄科,枸杞屬多年生木本植物,起源于我國,《詩經(jīng)》年代它還只叫杞,之所以后來叫枸杞,李時珍在《本草綱目》里說清楚了:“枸、杞,二樹名。此物棘如枸之刺,莖如杞之條,故兼名之。”原來是覺得它身上的刺像枸樹,枝條如杞樹,所以就叫它枸杞。
枸杞只出現(xiàn)在《小雅》里,這也說明當時的京城鎬京盛產(chǎn)枸杞。枸杞分布于溫帶和亞熱帶地區(qū),西周鎬京就是現(xiàn)在的西安市長安區(qū),正是最適合枸杞生長的地方。北宋科學(xué)家沈括在《夢溪筆談》中就說:“枸杞,陜西極邊生者,高丈余,甘美異于他處者。”枸杞可生于山坡,《小雅》兩次出現(xiàn)“陟彼北山,言采其杞”,那個時代枸杞就是野生于山上。“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這四句話以枸杞來贊譽尊貴君子的美德美名,說明周朝時期枸杞在人們的生活中已經(jīng)享有盛譽,其知名度及普及性不亞于今日之“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溫杯里泡枸杞”。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詩經(jīng)》時代,枸杞是野生的,想吃的時候到山坡上采摘就是。枸杞的嫩葉和果實皆可當蔬菜。東漢經(jīng)學(xué)家鄭玄《毛詩傳箋》說:“杞非常菜也,而升北山而采之,托有事以望君子。”說枸杞不是經(jīng)常吃的蔬菜,初唐經(jīng)學(xué)家孔穎達在《五經(jīng)正義》中說:“杞木本非食菜而升北山以采之者,是托有事以望汝也。”則干脆說枸杞不是蔬菜,這說明從漢至唐,枸杞已經(jīng)從蔬菜行列里由淡出到退出。漢朝和唐朝,人們已經(jīng)優(yōu)選出味道和口感更佳的蔬菜進行種植。枸杞葉微苦,枸杞子則被賦予藥用功能,在蔬菜界里地位不彰顯也很正常。
孔穎達說“杞木本非食菜”太絕對了,即便是唐之后,枸杞一直還是被拿來當蔬菜吃的,只是地位不那么重要而已。蘇軾就是枸杞的狂熱愛好者,他寫下的詠贊枸杞養(yǎng)生益壽的詩文不下四篇,在密州任上,因地方公使錢暴減,蘇軾又要勒緊褲腰帶,想辦法籌措糧食,用于收養(yǎng)數(shù)千棄孩,客人來了,但“齋廚索然”,啥都沒有,他和通判劉廷式二人沿城尋覓廢圃中野生的枸杞和菊花來招待客人,他在《后杞菊賦》中云:“吾方以杞為糧,以菊為糗。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實而冬食根,庶幾乎西河南陽之壽。”從枸杞苗吃到枸杞葉、枸杞子,連枸杞根都不放過。他寫《枸杞》:“神藥不自閉,羅生滿山澤。日有牛羊憂,歲有野火厄。越俗不好事,過眼等茨棘。青荑春自長,絳珠爛莫摘。短籬護新植,紫筍生臥節(jié)。根莖與花實,收拾無棄物。大將玄吾鬢,小則餉我客。似聞朱明洞,中有千年質(zhì)。靈龐或夜吠,可見不可索。仙人倘許我,借杖扶衰疾。”大意是,好的藥物不會自動隱藏起來,會長滿山野。白天有牛羊的煩惱,年年還要遭受野火的焚燒。越地的風(fēng)俗不重視枸杞,把它當作荊棘一般的雜草看待。青色的嫩芽在春天里自由生長,結(jié)出的紅果實也不去采摘。我把它移植過來護上籬笆,紫筍似的芽從節(jié)中生出。它的根莖與果實對人都有好處,沒有可拋棄的。大的功效可使我鬢發(fā)變黑,小的功效可以饋贈賓客。聽說羅浮山洞中有千年生的枸杞。但守洞的仙狗有時候夜里會叫,所以無法取得。倘若我長壽,那就借助枸杞之力,來治愈我的衰弱之疾。蘇軾一生顛沛流離,晚年窮困潦倒又身患疾病,但無論逆境還是順境,卻一直保持樂觀豁達的精神,從枸杞中咀嚼出美味綿長。
到了明朝,人們還是把枸杞當蔬菜吃的,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就說,枸杞“春生苗,葉如石榴葉而軟薄堪食,俗呼為甜菜”。現(xiàn)在廣東和廣西人們?nèi)匀淮蟪蕴爻澡坭饺~,春天吃是甜的,其他季節(jié)雖然微苦,但兩廣人不怕苦,照吃不誤。枸杞葉豬肝湯、枸杞葉瘦肉湯被賦予滋陰養(yǎng)血、清肝明目、預(yù)防動脈硬化等功效,枸杞葉含甜菜堿,所以有甜味,加上蘆丁和氨基酸,構(gòu)成特殊的風(fēng)味,很是特別,最起碼不難吃,喜歡的人還特別喜歡。
選自《書城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