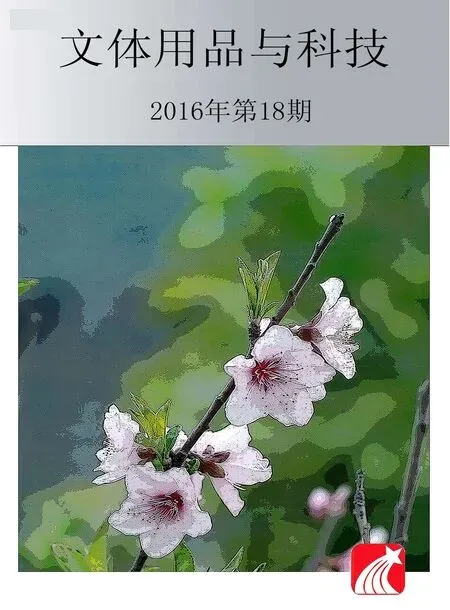文化學視域下貴州少數民族傳統體育的傳承與發展
□張栩倩(貴州大學人文學院貴州貴陽550025)
文化學視域下貴州少數民族傳統體育的傳承與發展
□張栩倩(貴州大學人文學院貴州貴陽550025)
從文化學視域下去研究,挖掘、整理貴州少數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可以有助于對貴州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進行文化定位,有利于促進其在現代化進程中有效地融入我國當前大力提倡的文化創新體系建設。深入剖析如何通過農耕文化、教育文化、傳媒文化、宗教文化、節慶文化等途徑使貴州少數民族傳統體育得到傳承和發展。
文化學視域貴州少數民族傳統體育傳承發展
1、前言
少數民族傳統體育在貴州人民的生活中根深蒂固,是人們文化生活重要的組成部分,在我國是產生現代競技項目的沃土,在世界更是優秀文化的瑰寶。其原汁原味的少數民族文化再現了各民族千百年流傳下來的生產生活技能和節慶習俗。從文化學的視角研究貴州少數民族傳統體育的傳承與發展,對弘揚少數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和建設我國的體育強國之路都具有重要的意義。本文主要是對貴州少數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傳承和發展進行探討,以貴州實際為出發點,分析貴州少數民族傳統體育的主要文化特征,力爭為貴州少數民族傳統體育的傳承和保護提出有效策略,為貴州少數民族地區體育事業的發展和繁榮提供借鑒。
2、貴州少數民族傳統體育發展現狀
貴州長期生活著的民族多達49個民族,其中世居少數民族就有17個。他們擁有豐富多彩的民族傳統體育項目,這些項目反映著各個民族獨特的生活習慣、文化特征和宗教觀念。
從1982起,四年一屆的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使貴州少數民族傳統體育活動由封閉型向開放型轉變。2011年更是在貴州舉行了第九屆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這次運動會不僅增加了貴州獨有的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項目“獨竹漂”,而且,向全國乃至世界展現了貴州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這朵奇葩。各地基層也逐漸建立起相關的部門,有些民族傳統體育項目得到了有組織、有計劃、有目的的管理。
貴州的少數民族傳統體育從內容被分為兩類,一類是經常出現在國家和地方各級少數民族運動會中以競技為主的比賽項目,例如:高腳、押加、陀螺、蹴球、搶花炮、賽龍舟、獨竹漂等。通過體育賽事使這些民族項目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傳承和發展。另一類則是被民族學、文化學等相關學者譽為“民族活化石”的以社會風俗、禮儀節慶為內容的表演性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項目。如舞龍、舞獅、上刀梯、飛石鎖等,因缺乏競技性和完善的比賽規則而無法進入到大型的體育賽事中去,這些項目絕大多數在平時基本得不到傳播,面臨著失傳乃至絕跡的風險。
契合人們向往自然、回歸自然的心理愿望,貴州旅游部門充分利用“體育—旅游”的雙重效應,結合民族地區的自然環境和人文地理條件,建立特色少數民族村寨,組織人員為游客不定期的進行少數民族傳統體育的展演,對增強旅游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起到良好的效果,頗有名氣的就有貴州西江苗寨使少數民族村寨體育獲得了進一步的持續發展。
3、從文化學的視角談貴州少數民族傳統體育的傳承與發展
3.1、原始的農耕文化與貴州少數民族傳統體育的傳承和發展
在貴州農業占有主導地位的經濟文化結構中,少數民族農耕信仰、農耕文化與民俗互融的民間體育,對早期貴州少數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建構和發展具有深遠意義。在史前時期,走、跑、跳、擲、攀登和游水等,是人們生活中的重要內容,也是原始體育產生的基礎。在史前農耕村與放牧休閑中,原始的音樂、舞蹈等活動,體現著健身、嬉戲、競技和人們愉悅的心理體驗。
在經濟飛速發展的今天,村寨體育、社區體育日夜強盛,廣場舞文化遍布了大中小城市,載歌載舞依然是一種娛樂和健身方式。將少數民族舞蹈融入健身操,帶入廣場成了可能。正因為少數民族傳統體育舞蹈具有的健身性、民族性、群眾性等特征,使居民的參與熱情更濃。圍繞全民健身綱要的開展,定期舉行地方體育比賽,把民族傳統體育項目與現在運動項目相融合,實現人人參與,人人傳承的目的。另外,把當地村寨體育運動的高水平者和老藝人作為紐帶,向當地居民傳授村寨體育活動的各項技術技能,以此來開發民族地區村寨體育發展的軟資源,帶動村寨體育的持續發展,進一步建立與西部民族地區的文明進程互動發展體系,使貴州少數民族傳統體育得到更好的傳承和發展。
3.2、宗教與貴州少數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互相滲透
早期的少數民族傳統體育受宗教觀念的影響,有些項目甚至直接淵源于宗教儀式。人們創造神靈并把希望和力量寄寓它,在信仰和祟拜需要物化的形式中有了巫術。巫師用身體活動來表現種種巫術。巫師被認為是最早的音樂家、戲劇家、舞蹈家,也是最早的體育家和運動員,漸漸的,一些巫術變為游戲、競技,變為傳統的體育活動。大眾在參加這些宗教體育活動的過程中,客觀上推動了民族傳統體育的發展。
信教群眾認為宗教信仰是融入他們的血肉里的,從生命開始到生命的結束都不會停止。正如劉鳳虎在《從文化學的視角談民族傳統體育的傳承與發展》中寫到的那樣“當一項體育運動像儀式一樣融入人們的生活的時候,也就得到了最好的保護和傳承”。因此,將民族傳統體育固有的宗教元素加以挖掘和深化與宗教文化互相滲透,是促進民族傳統體育更深的融入人們的生活,得到更好的傳承和發展的有利途徑。
3.3、貴州少數民族傳統體育在教育文化中的傳承與發展
人類早期的教育,主要是通過舞蹈和體育活動形式實現的,教育的主要手段是現場的口授和身教,開始時主要內容就是一些簡單的生產技能和自衛本領。
21世紀,許多國家把未來競爭的戰略目標投向人才的競爭和培養人才的高等教育改革上,探索技術,文化并重的教學模式已經成為傳承和發展貴州少數民族傳統體育必然的選擇。隨著經濟飛速發展,人們過分強調競技化,進行標準化改造,這遮蔽和抹殺了植根于傳統文化中的“非競技性和多元文化整體性”。然而,教學本身就是一個傳承文化的過程,須將貴州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項目融入到教學中去,這樣才能達到傳承民族文化、為民族文化的傳承培育大批專業人才和保持民族傳統體育項目不斷創新與發揚。
貴州少數民族傳統體育可以與當地教學環境相結合通過在小學、中學體育課中進行教學,在進入大學之后,可通加強不同文化學生之間的交流,把本民族特色的體育項目教給其他同學,實現民族文化的擴展。通過在貴州省內的大學校園開設民族體育項目課程,培養校園民族體育文化氛圍,據調查,貴州大學體育學院近年來就給本科生開設了舞龍、蹴球、板鞋等民族傳統體育項目,還帶有專業的押加、珍珠球等專業運動隊,貴州民族大學近年更是加強了多項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項目的專業人才培養。大多數貴州的高校都有自己的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隊,他們除了在貴州省內舉行的少數民族運動會取得了理想的成績,還在全國民運會上大放異彩。在當下的大數據時代,對繁雜的少數民族傳統體育資源按一定的分類標準,進行梳理和歸類,建立一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資源庫,在開展少數民族傳統體育的過程中根據各學校實際情況和教育培養目標,有選擇的加以利用,將會更好的實現貴州少數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傳承。
3.4、通過傳媒文化促進民族傳統體育的傳承與發展
傳媒在當今自媒體時代中有著巨大的威力,互聯網上的精武網站融合了廣播電視傳媒和平面傳媒的優勢,克服了傳統書籍文化的單一性,將比賽相關信息快速、直觀地滲入人們的生活。《少林寺》使中國武術聞名世界。同樣,通過各大媒體的報道,北京奧運會是向全世界展現了一個今非昔比的強大中國,第九屆少數民族運動會也驚艷了全國乃至世界。通過傳媒文化的宣傳報道,體育能更好的發展壯大,體育也可以增加大眾傳媒宣傳報道內容的豐富性和吸引力。另外,對一些表演性的民族傳統體育項目,如舞龍、舞獅從體育的視角做好宣傳工作,突出民族體育的主旋律,也可以很好的利于民族傳統體育的傳承和發展的。
3.5、通過節慶文化促進民族傳統體育的傳承與發展
隨著物質精神生活質量的不斷提高,對節日中的體育活動提出了多功能和大眾化的要求。傳統節日中的體育活動內容更要顯示出民族的文化特色。如在彝族民間的“火把節”中,精彩激烈的摔跤、跳火繩比賽、民間歌舞等引來了四方賓客。節日中的各種經濟貿易活動更是熱鬧非凡,這不僅促進了各民族地區之間的內外經濟貿易交往,而且使民族傳統節日和民族傳統體育由一種文化形式變為一種有效資源,直接推動民族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和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兩個文明建設,為民族傳統體育的多功能和大眾化發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動作用,滿足了傳統節日中對傳統體育的內在需要。
政策的支持力力度對少數民族傳統節日與民族傳統體育的互動發展效果起決定性的作用。政府職能部門應在政策上給予大力支持,加大對民族地區文化、體育經費的投入,實行國家、企業、集體、個人等多種渠道集資,減免民族傳統節日中某些活動的相應稅收,大力扶持民族體育事業等措施;李志清在描述搶花炮時寫到在政府舉辦節慶活動時,大部分的人都會要求得到經濟補償,他們認為這是政府要求我們這樣做的就應該給予一定的經費,但是當政府把舉辦節慶活動的權利下放到民間,他們會認為這是自己的節日,很多人就會主動義務參與,主動出錢出力。
4、結語
縱觀近年,論述關于民族傳統體育項目傳承和發展的文章,其主要路徑主要是通過制度文化、宗教文化、節慶文化、傳媒文化、申遺、與社區健身相結合、與教育環境相結合等途徑得到傳承和發展。正如前文提到的“當一項體育運動像儀式一樣融入人們的生活時,也就得到了最好的保護和傳承”因此筆者更傾向于在民俗文化中發展民族傳統體育項目,在民俗活動中開展民族傳統體育正是將其融入人們的生活中。另外,抓住貴州旅游大省的優勢,加大貴州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項目融入旅游的力度,促進貴州少數民族傳統體育的傳承和發展。針對貴州的許多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項目其內涵大多來自其生產勞動,一般要在豐收或者播種的時候展演才更顯其民族性,這與很多旅游旺季對不上,使外來游客很少能夠觀看和感受到各個地方民族體育深刻的民族內涵,如果一味的將民族項目表演時節隨意更改,將對民族項目保持其特有的民族性帶來極大地威脅,為此,筆者認為,應增加民族傳統體育項目的展演次數和加強專業人才的培養,即在以往固定的節日中表演該傳統項目是必須的(維護民族傳統體育項目的原型),在旅游旺季,由專業人員指導教授,同樣開展一些可以表演該項目的活動,從而達到該項目的傳承和發展。
[1]何景明.邊遠貧困地區民族村寨旅游發展的省思——以貴州西江千戶苗寨為中心的考察[J].旅游學刊,2010,(2).
[2]李志清.儀式性少數民族體育在鄉土社會的存在與意義(六)——現代背景下的搶花炮[J].體育科研,2007,(5).
[3]孫杰遠.文化共生視域下民族教育發展走向[J].教育研究,2011,(12).
G85
A
1006-8902-(2016)-09-SY
張栩倩(1989-),女,漢族,貴州畢節人,貴州大學少數民族傳統體育專業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少數民族傳統體育教學與訓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