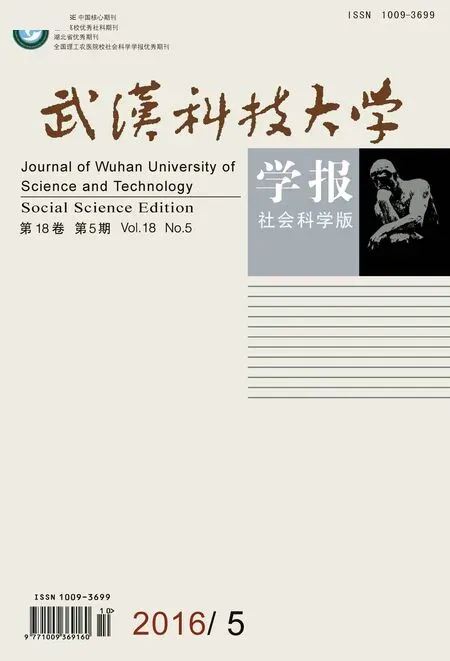“君從敘拉古來?”——評深陷“洞穴”中的哲人
孫冠臣
(1.蘭州大學哲學社會學院,甘肅蘭州730000;2.蘭州大學絲綢之路經濟帶研究中心,甘肅蘭州730000)
“君從敘拉古來?”——評深陷“洞穴”中的哲人
孫冠臣1,2
(1.蘭州大學哲學社會學院,甘肅蘭州730000;2.蘭州大學絲綢之路經濟帶研究中心,甘肅蘭州730000)
通過分析海德格爾對柏拉圖“洞穴隱喻”的解讀,可以幫助人們理解海德格爾三十年代所謂的政治錯誤,這里涉及到哲人與政治家的區分,同時意味著走出洞穴與再次回到洞穴中的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過程。柏拉圖與海德格爾在討論“洞穴隱喻”的時候都沒有區分上升過程(哲學家)與下降過程(政治家),在筆者看來,這正是哲人遭城邦厭棄、容易陷入政治困境中的現實原因。海德格爾作為一個返回到希臘性層次上的哲人,他的返回步伐在筆者看來一直屬于駐留于走出洞穴的上升階段,如果他是在上升階段上運思的,那么,當人們熱衷于談論深陷洞穴中的哲人時,恰恰表明我們將哲人泛政治化、泛道德化了,由此而來,我們才是深陷洞穴中的人。
柏拉圖;海德格爾;洞穴隱喻;哲人
一、深陷“洞穴”中的海德格爾
1934年當海德格爾辭掉弗萊堡大學校長職務重返教席時,他的同事曾這樣譏諷他:“從敘拉古回來了?”這一譏諷既是海德格爾下半生必須面對的政治責難,也是哲學與政治領域的又一樁公案,聚訟紛紜。我們從柏拉圖的“洞穴隱喻”出發嘗試著揭示哲學家與政治的關系。
盡管柏拉圖認為,正義城邦的實現,在于哲學家能夠成為國王,但無論是柏拉圖還是海德格爾都沒有以王者自居,對他們自身的現實處境而言,能夠成為王者之師,努力成為一個時代精神的引領者、教師就已經是最高追求了。當他們各自在自己的思想道路上準備下降到城邦中去的時候,哲人作為遭城邦厭棄的人的詛咒就已經降臨到他們的頭上了。
柏拉圖三次敘拉古之行,皆以失敗告終的結局已經用事實告訴我們“哲人王”政治理念的空想性。理論上,柏拉圖在沒有真正解決哲人與政治家悖論時,就只身再次回到洞穴中,其遭遇必然不僅是要面對現實的困境,更要直面“哲人王”理論的尷尬。如果國家社會主義就是海德格爾所心儀的要回去的城邦,那么,海德格爾意圖將他私人的存在論思想直接擺渡為城邦公眾的存在論精神,在其存在論思想與城邦之間建立起一種引領與協同關系,而海德格爾本人則是存在論思想的代言人和城邦的牧師,因此,哲學作為時代的精神,當一種宣揚新命運的哲學碰到要把一個民族帶向世界中心的集權政治的蠱惑時,他們之間想不發生曖昧關系都難。于是,海德格爾轉身成為所謂納粹的“幫兇”。
到底是哲學可以成就城邦,還是城邦應該認可哲學?這是一個問題。
1931~1932年,海德格爾在關于柏拉圖“洞穴隱喻”的講座中說:“哲人必然保持孤獨,因為他按其本質而存在,……孤獨并非其所愿。正是因為這樣,他必然一次又一次在關鍵時刻存在于此并毫不退讓,切不可如此膚淺,把他的孤獨誤解為對事物的一種退讓或任其自然。”[1]接下來當海德格爾通過擔任校長的政治參與而重溫這個話題的時候,必定切身體會到這種孤獨:“孤獨屬于哲學家的本質,這種孤獨根植于他所是的方式以及他在世間中的位置,他陷入完全的孤獨中,因為在洞穴中他不能退縮。在孤獨狀態中呼喊,[哲人]在關鍵時刻說話,他說話時甘冒的風險便在于,他說出來的東西可能立刻就會走向對立面。”[2]183在1933年,哲人是否看到了返回洞穴的機會?是否意識到只有參與到這種決定德國命運的危機時刻,才能履行其獻身真理的使命?對此,海德格爾保持沉默。
盡管海德格爾在面對西方傳統哲學時皆采取一種對峙態度,不斷抗爭的海德格爾的經驗教訓告誡我們,哲學事業本性上是要打破習俗的、是爭辯的、甚至是顛覆性的,哲學家是遭城邦厭棄的人,即使是最偉大的哲學,如果喪失這種抗爭,對城邦政治表示哪怕一絲順從,都是對蘇格拉底的背叛,必將深陷洞穴之中,喪失其哲學性。但如果徹底貫徹蘇格拉底的精神,只做城邦政治的牛虻,柏拉圖又怎么提出哲學家應該為王呢?而且哲學家為王還是正義城邦得以實現的前提條件?在蘇格拉底言談里的正義城邦中,哲學家應該成為國王這一“應當”命題是從哲學家的本質規定性這一“是”命題中推論出來的,這一推論本身就面臨近代以來哲學家們從“是”能否可以推出“應當”的理性質疑。
蘇格拉底對哲學家的本質規定具體有三:①哲學家是看見過美、正義和善的真實的人;②哲學家是人世間最富有的人;③哲學家是最不貪戀權利的人。
哲學家“在某種必然的命運”的安排下率先走出“洞穴”,他們是看見了善的形式的人,他們的心靈永遠渴望逗留在高處的真實之境,并把對真的追求看作是人生的目標,從而并不把“洞穴”中的名譽、權利以及財富看作是重要的事情。一個真正的哲學家只會“參與自身心靈的快樂,不去注意肉體的快樂”[3]231。
“這種人肯定是有節制的,是無論如何也不會貪財的;因為,別的人熱心追求財富和巨大花費所要達到的那種目的,是不會被他們當作一件重要事情對待的”[3]231,在他們看來,真正的富有是心靈的富足,是對“真實”的擁有。而且,哲學家天生就不是愛權利的人,而是愛智慧的人,在蘇格拉底看來,沒有什么生活比真正的哲學生活能夠有資格輕視政治權利的了。因此,蘇格拉底才說:“只有當你能為你們未來的統治者找到一種比統治國家更善的生活時,你才可能有一個管理得好的國家。因為,只有在這種國家里才能有真正富有的人來統治。當然他們不是富有黃金,而是富有幸福所必需的那種善的和智慧的生活。如果未來的統治者是一些個人福利匱乏的窮人,那么,當他們投身公務時,他們想到的就是要從中獲取自己的好處,如果國家由這種人統治,就不會有好的管理。因為,當統治權成了爭奪的對象時,這種自相殘殺的爭奪往往同時既毀了國家也毀了統治者自己。”[3]281
哲學家是只求真、不貪戀任何世俗名利尤其是政治權利的人。從這一本質定義出發,我們得出柏拉圖哲人王的第一個悖論:真正的哲學家是不愿意做統治者的,所以,哲人為王本身就是一個悖論。然而,哲人的宿命并不在于走出洞穴,還要求再次下降回到洞穴,由此產生了哲人王的第二個悖論:一方面,哲學家必須要回到洞穴中去承擔起解放者的角色;另一方面,作為啟蒙者和解放者,其結局是死亡。柏拉圖首先從哲學家為王的必要性上作出規定,他們必須要回到洞穴里與其他人同住,因為他們是已經看見過美、正義和善的真實的人,所以一旦他們再一次習慣了看模糊影像,他們就會比其他人看得更加清楚,不但能夠分辨出各種不同的影像,而且還知道影子所反映的真實,因此,讓哲學家來承擔城邦的護衛者,不但能夠更好地保護城邦公民的利益與主張,而且也是最符合正義的。“事實是:在凡是被定為統治者的人最不熱心權利的城邦里,必定有最善最穩定的管理,凡是與此相反的統治者的城邦里,其管理必定是最惡的”[3]280,可見,柏拉圖不是沒有意識到這兩個悖論,而是巧妙地利用了這兩個悖論。正是因為真正的哲學家從不貪戀權利,才被要求為王;哲學家作為走出洞穴、看到過真實的人,返回洞穴,成為啟蒙者和解放者則是他們應盡的義務,再次下降到洞穴中是哲學家必須背負的歷史使命。“哲學家應當為王”或許可與中國儒家“內圣外王”的人生理想相對照:在儒家道統中,君子(哲學家)的最高境界是“內圣外王”。如果說,哲學家觀照到善的形式是內圣的要求,那么哲學家下降到洞穴中解放其他人,則是外王的應有之義,內圣因此并不是哲學家追求的最高目標,而僅僅是實現外王的必要準備。在柏拉圖哲人為王的設想中,雖然在學理上存在著悖論,但是,正是這種規定使得在哲學家統治的國家里,再也不會出現為了權利而爭斗的現象;再也不會為了防止因權力滋生的腐敗而需要對權利進行監督和制衡。柏拉圖對哲學家應該為王的設想除了哲學家是見過真實的人這一基本規定之外,還看到了哲學家擁有權力卻不被權力所詛咒的能力,徹底擺脫了“至尊魔戒”的誘惑。孔孟之道在解決“至尊魔戒”的難題(擁有權力的同時又受到權力的詛咒)時,則是訴諸于政治家個人的“道德修行”,這是他們的差別。無論如何,這種設想足以使蘇格拉底充滿憧憬地說:“我們關于國家和政治制度的那些意見并非全屬空想;它的實現雖然困難,但還是可能的,只要路子走得對,像我們前面說過的那樣做。只要讓真正的哲學家,或多人或一人,掌握這個國家的政權。他們把今人認為的一切光榮的事情都看作是下賤的無價值的,他們最重視正義和由正義而得到的光榮,把正義看作最重要的和最必要的事情,通過促進和推崇正義使自己的城邦走上軌道。”[3]310這樣的城邦和所采取的政制將是最善和最正義的。
柏拉圖聽從哲人歷史使命的召喚三次進入敘拉古,期望通過對僭主狄奧尼修斯一世、二世的教化和影響,實現其建立正義城邦的理想,雖然都以失敗告終,但這并不能構成柏拉圖的人生污點。相較而言,海德格爾的政治錯誤實在是算不了什么,1933年做了弗萊堡大學校長10個月,順帶加入納粹黨,現在整理出來的黑色筆記本內容中仿佛也有足夠的證據顯示其在“二戰”期間有反猶言論,這些似乎都頑強地構成了海德格爾的人生污點,并直接影響了人們對其人品的評價,但這種由政治正確裁決一切的做法普遍忽略了一點:作為啟蒙者、牧師、教師與政治家、統治者是有巨大差別的。
二、海德格爾對柏拉圖“洞穴隱喻”的解讀
海德格爾對柏拉圖“洞穴隱喻”的興趣主要集中于1930~1940年代,這期間連續開設了《論真理的本質:柏拉圖的洞喻和〈泰阿泰德〉講疏》(1931/32冬季學期)、《存在與真理》(1933/34冬季學期)等課程,并著有《柏拉圖的真理學說》(1931/32)(收錄于《路標》)的重要論文。海德格爾在解讀柏拉圖的“洞穴”時,雖然突出了“真理”概念與“存在”概念的本質聯系,但1930年代的海德格爾帶有明顯的政治“情懷”,除了熱烈歡呼一個“偉大的破曉”之外,即使在闡釋柏拉圖的“真理”概念時,也沒有忘記其政治使命,因此他在闡釋柏拉圖的“洞穴隱喻”時,不僅突出強調了走出洞穴的過程就是獲得真理的過程,而且還故意將柏拉圖的“洞穴隱喻”劃分為四個階段,并突出強調了第四個階段,即下降到洞穴中的階段,帶有明顯的政治意圖。海德格爾對“洞穴”四個階段的重新構建與解讀,帶有濃郁的政治立場導向。但是,海德格爾沒有清晰地認識到回到洞穴的過程不是哲學活動而是政治活動,因此,他與柏拉圖一樣最終都深陷“洞穴”之中。
海德格爾在闡釋柏拉圖“洞穴隱喻”時主張,走出洞穴的過程也是發現真理與獲得自由的過程,發現真理與獲得自由在這里是一回事,而且獲得自由與自我解放也是一回事。海德格爾將人類走出洞穴亦即真理的發生細化為四個階段[2]127-185:
(1)人在地下洞穴中的處境(514a-515c)。
在第一階段,柏拉圖描述了人在地下洞穴中的處境:有一些人從小就住在這個洞穴里,頭頸和腿腳都被鎖鏈綁著,不能走動也不能轉頭,只能向前看洞穴的后壁,在他們的身后洞穴外高地上,有一堆火,火光恰好投射到后壁上,在這些人與火光之間的洞口處,有一條通道,沿著路邊已筑有一道矮墻,這種設置和處境使得在這條通道上發生的事或出現的物,它們的影子都將被火光投射到洞穴中的后壁上。因此,洞穴中的人只能看到這些影子,而洞穴外所發出的聲音,他們也認為就是這些影子發出來的。他們并不知道他們所看到的東西就是影子,也不認為那就是影子,他們認為通過后壁所看到的就是真實的,所認識的知識就是真理。
由于洞穴中的人并不能認識到或建立起影子、火光與洞穴外移動著的物之間的關系,這種處境導致他們只能看到顯象和外觀,而不能把握事物本身和整體。事實上,這種處境也是人們日常生活中的普遍處境。
(2)洞穴中人的解放(515c-e)。
在第二階段,某種事情發生了,歷史發生了。其中有一個人被解除了鎖鏈,被迫站立起來,轉頭環視,走動,抬頭看望火光。由于他的眼睛并不適應明亮的火光,他并不適應新的處境,這會給他帶來痛苦,他本能的反應是回到他原先熟悉的處境中,因此,僅僅解除鎖鏈是不夠的,他會抵制這樣的自由。由于鎖鏈是突然被解除的,他并不能認識到他早先的所有認識僅僅是影子,相反,解除了鎖鏈的他會極端反感現在的認識,因為現在的認識給他帶來了混亂。所以,解除鎖鏈并不是真正的解放,它只是一種外在的解放;解除鎖鏈并沒有改變他內在的條件,沒有改變他的意志,他的意志要求他退回到熟悉的狀況下。
這第二個階段,雖然看起來是一種解放,但結果是失敗的。由于解除鎖鏈的人并沒有成功地在火光與他們的認識之間建立起聯系,更沒有認識到真理的本質與人的本質、自由的本質之間的關系。
(3)真正把人解放在光明之下(515e-516c)。
在第三個階段,洞穴中的人被強行拽出洞穴,置身于洞穴外的陽光之下,在這種狀況中,被帶出洞穴的人在經歷痛苦之后,就有可能經驗許多不同的顯象、影子、水中的倒影等等,最后則是陽光和太陽。一旦逐漸習慣和適應了洞穴外的環境,他就會明白事情的真相,就會得出結論:“造成四季交替和年歲周期,主宰可見世界一切事物的正是這個太陽,它也就是他們過去通過某種曲折看見的所有那些事物的原因。”[3]274-275
現在,我們還不能匆忙地就得出結論說,把握了事情真相和原因的人就是自由的人和完全解放的人,海德格爾提醒我們,在這里有四個條件需要注意[2]144-145:
第一,洞穴中的人必須被強制帶出,解放就是暴力,這種暴力會遭遇到抵制,因為洞穴里的人并不想走出洞穴,改變他已經習慣了的處境,而且被帶出來的道路是曲折的,過程也是艱難的。因此,解放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不是在公園里散步,不是請客吃飯,是艱苦的斗爭過程,需要努力。
第二,對解放成功達到預期目標而言,僅僅解除鎖鏈走出洞穴是不夠的。真正的解放,是被帶出洞穴的人慢慢地、穩定地對洞穴外環境的習慣和適應。逐漸熟悉外面的世界,意味著對陽光的熟悉,并不是對個別事物的熟悉,這就需要再教育,從與洞穴中相似的影像開始,從夜晚開始,逐漸過渡到真實的事物和陽光下的世界。
第三,只有當他的眼睛完全適應了陽光,看清了陽光下的事物,而且最終領會了光的源泉——太陽,太陽不僅僅是光的源泉(包括洞穴外的火堆),而且還是時間的原因,那么,人就會領悟,時間是通過太陽來測量,太陽規定了時間是什么,這時,所有的一切第一次根據太陽而成為可以理解的,太陽本身就是一切存在的根據。
第四,真正的解放不僅需要暴力,而且需要意志力,長期的勇氣是完成以上所有過程的保障,而且勇氣可以承受挫折和失敗,只有對解放所必須的每一個過程有充分的了解,才能保障解放最終的勝利。
在走出洞穴的第三階段,對光的再適應就是解放的本真過程,通過這個過程,外面的事物成為可見的。在這里,光與自由的關系,真理、敞開與存在的關系也確立起來了,一個新的世界出現了。如果“洞穴隱喻”的洞內情景所揭示的就是生活在蒼穹之下地球上人類的真實處境,那么,洞外這個新的世界就是一個理念/形式的世界。如果說,在“洞穴隱喻”中,真理就是對理念的一種看、一種創造性的看見,那么,真理就不是一個偶然的事件,而是一種發生,是對事物本質的一種創造性的籌劃,海德格爾認為,這種“看見”本質上是一種自我捆綁,既是與存在者的捆綁,更是與理念/形式的捆綁,這種捆綁就是解放的本質,解放就是走向真理。這樣,人就生活在真理中。不過,走出洞穴的第三個階段并不是解放的完成,我們還需要找到那個解放者,對他進行第二次捆綁。
(4)被解放的人返回到洞穴中(516e3-517a6)。
開始于洞穴中的解放是一種上升過程,上升的過程把洞穴中的人帶上來,帶到陽光下,一個個體的解放完成了,但人類的解放并沒有完成,才剛剛開始,從這個意義上說,柏拉圖的“洞穴隱喻”這個故事所講的就是人類的歷史。因此,解放還有一個下降的過程,被解放的人返回到洞穴中。
已經適應和習慣了洞穴外的世界的那個被解放的人又返回到洞穴里,坐在了他原先的位置上,他將要面對的不是鮮花與掌聲,而是嘲笑與死亡。當他從明亮的陽光下回到陰暗的洞穴里時,由于眼睛還沒有適應陰暗,他連石壁上的影像都看不清了,必然會遭到嘲笑,而當他一旦適應了陰暗,向大家宣講他所認識的真理與自由,并打算把大家帶到陽光下時,迎接他的將是死亡。“洞穴隱喻”以對死亡的預期而結束,被殺的命運揭示了什么?首先值得我們深思的是誰的死亡,誰的被殺?被殺的人就是那個要把解放洞穴中的人作為自己使命的人,就是我們要尋找的那個解放者,這個解放者,也就是蘇格拉底口中的哲學家。
因此,一個真正的哲學家就是那個已經爬出洞穴、并習慣了外面的陽光然后又爬回洞穴承擔起解放洞穴中囚徒的啟蒙者。作為解放者的哲學家將把自己置身于死亡的境地中,他的死就掌握在那些在洞穴中制定真理標準擁有權力的居民手中。盡管如此,哲學家還是返回到洞穴里,回去不是為了與洞穴中人進行一場真理大辯論,而是為了解放他們。這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結局與人類解放的歷史聯系起來。
盡管柏拉圖的蘇格拉底在這里還沒有來得及告訴我們,哲學家返回到洞穴里如何解放他們,但這個故事結束的時候,我們已經搞清楚的事實是:哲學家作為看到事情真相的人,他所看到的東西與洞穴中人所看到的東西是不一樣的,他知道什么是光照,什么是影像,什么是真正的實在,什么是模仿,他知道洞穴中人所看到的存在是什么樣的實在,他知道他們并不能把影像看作影像。總之,雖然他又回到了洞穴中,但他與洞穴中的居民已經完全不一樣了。因此,哲人王并不是一個統治者,而是一個啟蒙者或解放者。如果把哲人王看作是純粹的統治者,必然導致波普爾所指責的智慧統治——種族論,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系就是牧羊人與羊群的關系。而如果把哲學王看作是一個解放者,他就是一個引路人、教師……
三、哲學家與政治家的區分
如果說深陷洞穴中的柏拉圖有“三部曲”(《泰阿泰德》《智者》《政治家》)以及《第七封信》留給我們;那么同樣深陷洞穴中的海德格爾留給我們什么呢?針對他1930年代的政治作為,他說有《尼采》為證,然后就是永遠的沉默。也許這種沉默并不像一些人認為的那樣是死不認罪的頑固,而是已無話可說,該說的早已在《德國大學的自我主張》中說了。
海德格爾顯然并沒有吸取柏拉圖深陷洞穴的教訓。哲人必須下降到洞穴中,不僅是為了拯救城邦,更是為了在可理解的理念光明中花費了些時間之后,理解政治領域的特殊性,或者說,返回洞穴不僅是為了布道、教化、啟蒙,更是為了理解經驗世界的真實。
當哲人剛下到洞穴中時,由于他無法適應在幽暗中觀看,所以他在洞穴外所獲得的真實并不能幫助他領會城邦里的政治。他需要花些時間來理解哲學(洞外)和政治(洞內)兩個領域的差異,還要學些城邦內的經驗技巧,通過反復地上升和下降,才有可能勝任城邦中的政治生活。海德格爾在解讀柏拉圖的“洞喻”時,完全忽略了這一點,只是簡單地將哲人歸為啟蒙者,可能被民眾殺死,而流露出對民眾的不信任。在此立場上,我們說,海德格爾的政治幼稚并不是反映在與國家社會主義短暫的媾和,倒不如說是他一貫的精英主義立場和對普泛大眾的輕視。
因此,筆者主張將柏拉圖的“洞穴隱喻”劃分為兩個階段,一是上升階段(哲學階段),一是下降階段(政治啟蒙階段),并由此嘗試著向前推進柏拉圖與海德格爾對“洞喻”的經驗。與柏拉圖的“洞喻”相對照,他們二人所陷入的“政治困境”,就在于沒有區分上升與下降是兩個性質與方向完全不同的過程,上升與下降方向是反的,上升屬于哲學求真范疇,下降屬于政治解放運動范疇,而不是他們眼中的水到渠成的同一過程的不同階段。上行而求其貫通為“道”,下行而求其落實為“術”。上則達于“道”,下則落于“術”。上升為求“是”求“真”,下降則是為了落實“用”,為了“應當”。從“是”推不出“應當”,雖然治大國如烹小鮮,但誰也不會認為一個高級廚師就一定能把國家治理好,哲學家亦是如此,雖然哲學家窺探到了一些真實,進而發現真理,但并不意味著他就能將其很好地踐行和落實,落實/實施“真”更不意味著就必定給人民帶來“善”。
柏拉圖在為其老師蘇格拉底辯護的過程中,已經闡明真正的哲學家是遭城邦厭棄的人,而且真正的哲學家是不過問政治的,就像他的老師蘇格拉底,其一生的使命是教育人民向善、求真,過正義的生活。柏拉圖給哲學家的定義實在苛刻,僅僅從這一定義出發,世間僅有一個蘇格拉底。但同時,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又給我們提供了何為哲學家的榜樣,哲學家總是要過政治生活,與政治糾纏不清。蘇格拉底的死、柏拉圖的敘拉古之行、海德格爾的自信等都告訴我們,真正的哲學家一方面用第三只眼睛看世界(第三只眼睛:看過真實者都擁有這只眼睛),總是以第三者的立場對現世政治制度持批評態度。蘇格拉底曾把自己比喻為城邦的牛虻,不時地對其叮咬,目的是為了讓城邦處于不斷的思考和反省中,因此,哲學家是遭城邦厭棄的人。由此可見,柏拉圖提出哲學家為王,其深意并不是主張哲學家必然成為城邦的統治者,而是要告訴我們,正如一個正義的人的靈魂必定是由靈魂的最高部分——理性所統治一樣,一個正義的城邦,也必定由最高智慧所統治才是可能的。從這一立場出發,“哲人王”嚴格說來只是一個隱喻,就像“洞穴隱喻”一樣。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中,柏拉圖的蘇格拉底為我們提供了一系列的隱喻:“洞穴隱喻”“太陽隱喻”“線喻”,接下來我們建議,將哲人王也稱為“哲人王隱喻”,如此可化解后人單純從各自的政治立場出發對柏拉圖“哲人王喻”的各種批判和攻擊。
柏拉圖不但是一個熱衷于政治生活的哲學家,而且是第一個系統論述如何在理想城邦中安排生活的人,他不可能不為他的哲人王喻嘗試著提供一個解決方案。首先,在柏拉圖看來,城邦就像一個人的身體,在理想狀態下,每一個部分都完美地合作,協調一致。就像由理性部分統攝靈魂的人是一個正義的人一樣,作為一個完美城邦的統治者,必須擁有真正的知識,即擁有關于“善的形式”(the Form of Good)的知識,除此之外,他們還需要掌握統治的藝術(the art of ruling)。統治的藝術就像航海技術一樣,是可以學習的,這又回到了《理想國》的一個主題——教育,哲人蘇格拉底的唯一身份就是教導青年人向善,只有經過審慎考察的生活才是值得過的。其次,走出洞穴和再次下降回到洞穴區分為兩個過程,亦即將哲學家和政治家區分開來是重要的,柏拉圖在“洞喻”中提供了這種區分,而且,如果我們按照隱喻模式閱讀柏拉圖的話,正如雅可比·克萊恩所主張的柏拉圖的“三部曲”一樣,《泰阿泰德》《智者》《政治家》作為三部曲的結構告訴我們,柏拉圖也嘗試著解決了哲人王的悖論問題,隱晦地暗示了哲學家如何轉變為政治家,為再次下降到洞穴中做好準備。
柏拉圖的三部曲《泰阿泰德》《智者》《政治家》講述了發生在兩天中的三個對話、三個場景、三個故事,但主角只有兩個人:一個智者、一個哲人。在這里,柏拉圖暗示我們,在從哲學家向政治家轉變的過程中,作為一個中介、一個過渡,智者正是我們要找的人。從哲學家的定義出發,哲學家是不可能成為政治家的,但理想城邦的道義要求哲學家必須轉變為政治家,即哲人為王,那么,哲學家蛻變為智者,然后再蛻變為政治家,就不僅僅是一種權宜之計,而是一條必須要走的道路。而且,在柏拉圖的《第七封信》中,老年柏拉圖反思了自己的三次敘拉古之行。對哲人而言,他們都在各自的領域內研究世界的“無限”和萬物的始基“一”,而政治生活則是“有限”的“雜多”,由各種各樣的形態、樣式混合而成。當哲人從理念、形式的“天國”下降到世間生活的洞穴中,用見過真實的眼光透視千姿百態的差異性和多樣性時,其言辭是否能說中政治生活的真諦,其話語民眾是否可以聽得懂、聽得進去,那的確是值得商榷的。智者們早就用他們的行為和書寫表明,哲人始終囿于自己的認知與洞穴來塑形和開拓城邦的政治生活,民眾的困惑和反抗理所當然。
在《政治家》中,柏拉圖向我們展示了眾人尋求政治家的過程,也就是探討政治家之所是、之定義。在斯特勞斯學派看來,從政治家經智者到哲學家是一個上升的過程,那么我們是否可以說,從哲學家經智者再到政治家是一個下降的過程呢。從柏拉圖的視角審視城邦,一個正義的城邦就像一件藝術品,從對編織技藝的探討入手,一個健康的城邦自然是由掌握了“統治藝術”的人建設的,只不過真正懂得這門技藝的人是智者還是哲學家,則有很大的分別。為了擺脫智者對王權的窺視,避免將城邦交給那些自稱擁有王者技藝的人,柏拉圖將政治家的基本統治技藝規定為“立法”,“立法屬于王者之技藝”,不過這只是柏拉圖向現實的暫時妥協,他并不認為法治是最好的,只有將城邦交給最有智慧的哲人手中,才是最好的。因為法律不能準確理解什么對所有人才是最好的、最正義的,也沒有能力給與他們最好的東西,而哲人作為擁有智慧、懂得整體知識的人,則有能力分辨什么對國有利或者不利,能夠照顧到不同人的需求和活動,就像織布一樣,把不同的人、不同的活動協調、編織在一起,于是,“德性和諧現于其中”。可見,柏拉圖的《政治家》與提出哲人王的《理想國》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強調和分析了統治的技藝。《理想國》止步于走出洞穴,《政治家》則開始重視和強調哲人走出洞穴以后重新下降到洞穴中的過程。
因此,從《理想國》到《政治家》,我們清晰地看到了柏拉圖政治理念(尋求正義城邦)的發展軌跡,主線則是蘇格拉底設定的一個類比:“城邦是放大的個人,個人是縮小的城邦”,個人的正義在于靈魂三部分的和諧統一:理智(智慧)、激情(勇敢)、欲望(節制);城邦的正義在于組成城邦的三個等級之間的和諧統一:統治者(智慧)、護衛者(勇敢)、被統治者(節制)各安其位、各司其職,實現城邦最大的善。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初步回答了何為正義的城邦,提出了哲人王的理念,在《政治家》中開始尋求真正的、好的政治家以及對次好的現實的政治家以及法律的認可。如果說哲人王屬于柏拉圖的“理念世界”,那么向現實世界的回歸,就是柏拉圖必須要走出的一步,而這一步恰恰在《政治家》中完成了。
如果我們忽略柏拉圖在《政治家》中對統治技藝的補充和強調,就很容易陷入波普爾對歷史主義批判所構建的一系列困境。波普爾將哲學家柏拉圖混同于政治家了,而且他在構建其開放社會的政治主張時,根本就沒有思考人類如何“走出洞穴”的哲學問題。海德格爾則總是在強調他的存在發問一直在途中,并告誡人們,只有走上這條追問存在的道路,才能贏得其可能性。因此,如果我們說海德格爾追問存在的道路是走出洞穴的上升之路,那么他的《德國大學的自我主張》的演講顯然是下降到洞穴中對洞內人說的。
德國大學的自我主張就是追求其本質的原初的、共同的意志。我們將德國大學視為這樣的高校,她從科學出發,并通過科學,來教育和培養德意志民族命運的領導者和守護者。追求德國大學的本質的意志,就是追求科學的意志,也就是追求德意志民族的歷史精神使命的意志,這個民族是一個在自己的國家中認識自己的民族。科學和德國的命運必須同時在追求這一本質的意志中獲得權力。然而,只有,也只有在下面這種情形下,它們才能實現這一點,那就是,我們——教師和學生,一方面讓科學直面其最內在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在德國命運極度艱難的時刻擔負起它的命運。[4]
海德格爾口中的科學也可以翻譯成知識。他主張從科學出發,并通過科學來教育和培養德意志民族的領導者和守護者,這里的科學或知識顯然是在柏拉圖“理想國”的語境中講的,也是在傳統形而上學意義上講的,所有的科學都生根于希臘哲學的那個開端,科學就是立于不斷自我遮蔽的存在者整體中間,堅持追問。這與他在《形而上學導論》中強調德意志民族是形而上學的民族遙相呼應。海德格爾在這里有意識地將他對存在的發問與德意志民族的歷史使命聯系起來,“因此,對存在者之為存在者整體的發問,對存在問題的發問,就是喚醒精神的本質性的基本條件之一,它從而也是歷史性此在的原初世界得以成立,防止世界陷入晦暗的危險,承擔我們這個身處西方中心的民族之歷史使命的本質性的基本條件之一”[5]。拋開他有意識地賦予德意志民族西方中心的地位去承擔拯救世界的歷史使命這一意識形態,我們將《形而上學導論》中關于傳統形而上學對存在的雙重遺忘的分析與《德國大學的自我主張》對德意志民族精神的期許聯系起來,就會清晰地看到海德格爾顯然沒有意識到哲學家與政治家的嚴格區分,或許他是有意將二者身份混同的。無論如何,站在海德格爾的立場上,精神將從存在之思的源頭中再次贏得輝煌和宏大,整個西方的歷史與本質都凝結在其中。精神也正是由于其源始性而具有力量,因此,“一個民族的精神世界決非一種文化的上層建筑,同樣也不是各種有用知識和價值的武庫;相反,它是一種權力,這種權力最深層地保有著這個民族那扎根在大地和流淌在血脈中的力量,這種權力最內在地激起和最深遠地震撼著這個民族的此在。惟有一個精神世界向這個民族保證了偉大。因為它迫使我們在追求偉大的意志和聽任墮落之間不斷做出決斷,并讓這種決斷成為我們征程中的步伐的法則,我們的民族已經踏上了這一征程去開啟它的未來”[4]。將民族精神的內在規定性推向存在之思,將精神面向存在之本質的、原初的被規定的認知的決斷,看作是在最深處保護民族的鮮血與土地的強力,是激起和震撼這個民族的實存的強力。于是乎,傳統形而上學對存在的遺忘與世界的沉淪、精神的沒落同步,同樣,對存在的追問也將與民族精神的救贖統一起來,這就是深陷洞穴中的海德格爾的哲學、政治主張。
當我們把哲人與柏拉圖的“洞穴隱喻”放在一起討論時,筆者主張,一定要區分“上升”與“下降”兩個過程,一定要區分政治上的海德格爾與思想上的海德格爾,“畢竟不是海德格爾支配了第三帝國,畢竟不是海德格爾制定了種族主義的綱領,不是海德格爾實行了種族主義清洗。”[6]我們的立場是,海德格爾作為一個返回到希臘性層次上的哲人,他的返回步伐在筆者看來一直屬于駐留于走出洞穴的上升階段,如果他是在上升階段上運思的,那么,當人們熱衷于談論深陷洞穴中的哲人時,喋喋不休于海德格爾與納粹的關系時,這種無聊的閑談、獵奇,即使以當代嚴謹的學術論文的形式出現,也只是表明我們沒有理解和把握住海德格爾“思的事情”,當我們故意或不經意熱衷于將哲人泛政治化、泛道德化的時候,也只是再次證明了我們才是深陷洞穴中的人。
[1] 海德格爾.論真理的本質——柏拉圖的洞喻和《泰阿泰德》講疏[M].趙衛國,譯.北京:華夏出版社, 2008:83.
[2] Martin Heidegger.Sein und Warheit[M].Victtorio Klostermann.Frankfurt am Main,2001.
[3] 柏拉圖.理想國[M].郭斌和,張竹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4] 海德格爾.德國大學的自我主張[EB/OL][2016-05-04].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 3526093/.
[5] 海德格爾.形而上學導論[M].王慶節,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55.
[6] 陳春文.關于海德格爾與納粹[C]//《國學論衡》第三輯——甘肅中國傳統文化研究會學術論文集, 2004.
[責任編輯 彭國慶]
B516.54
A
1009-3699(2016)05-0465-07
2016-06-29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15LZUJBWZX019).
孫冠臣,蘭州大學哲學社會學院教授,哲學博士,主要從事現代西方哲學、德國哲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