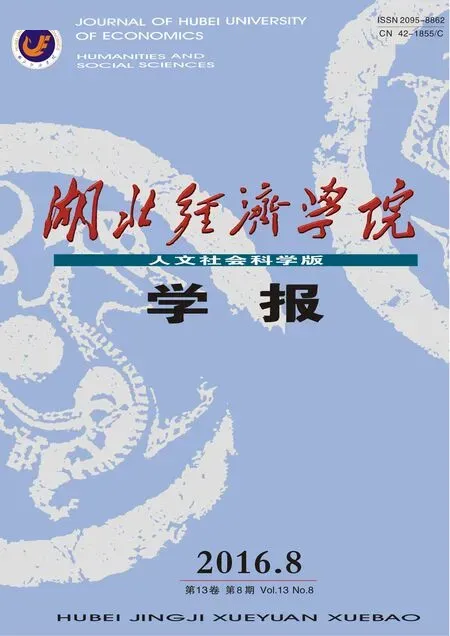《桃花扇》:書寫歷史興亡的客觀規律
王一博
(河南大學,河南 開封 475000)
《桃花扇》:書寫歷史興亡的客觀規律
王一博
(河南大學,河南 開封 475000)
本文從孔尚任孔族后裔的特殊身份、個人為官的經歷,以及康熙時期滿漢地主階級合流的時代背景入手,論證孔尚任在創作《桃花扇》過程中飽含著復雜的情感,以客觀的角度、清醒的態度去探究明亡清興的原因,書寫歷史興亡的發展規律。
孔尚任;《桃花扇》;民族意識;歷史規律
《桃花扇》問世以來,針對其中所蘊含的民族情感到底是“頌清”還是“悼明”,爭議聲持續不斷。但是孔尚任作《桃花扇》,其思想情感是極為復雜的。首先,孔尚任作為孔子的嫡系子孫,要恪守孔子提出的“夷夏之大防”的民族觀。其次,他曾受到康熙的知遇之恩,但之后他的仕途走得坎坷不順,也曾直面官場浮沉與世情冷暖。再次,康熙積極提拔任用漢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這一時期滿漢地主階級已經合流,孔尚任作為孔族后裔,是這階級中的一員。總之,《桃花扇》中蘊含的民族情感,是無法用悼明或頌清而簡單評判的。
一、“華夷之辨”與孔子第六十四代孫
東漢末年,四夷交侵。作為華夏文化的堅守者,孔子著春秋大義,強調管仲“尊王攘夷”的功績。他堅守華夏文化的正統性,反對夷狄文化對華夏文化的浸染。《論語·八佾》記載:“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這表明孔子認為文化落后的國家還有個君主,倒不如華夏沒有君主,即有君無禮,不如有禮無君。
盡管孔子的思想流露出“重夏輕夷”的情感,但是,孔子的民族觀絕不是狹隘的愛國主義。他雖視華夏為正統,但是他的夷夏之分,是以文化作為區分的標準,而非血統種族。此外孔子對少數民族持有包容開放的態度,只要尊崇禮儀,發揚華夏文化,便可被視為華夏之人:“先進于禮樂,野人也;后進于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唐代詩人韓愈就在《原道》中,對孔子“重視文化而輕視種族”的民族觀念給予評價:“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1]
孔子的民族觀念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尤其是經過宋亡元興、明亡清興這兩次改朝換代,夷夏之大防徹底成為一個具體的現實問題。明末清初的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等知名學者,其學術論著都彰顯了鮮明的民族意識,他們甚至都在一定程度上參與了抗清斗爭。
孔尚任出生于滿清入主中原后第五年。盡管他長大成人時,清廷已經基本上平定了各地反清的武裝斗爭,但這依舊是一個充滿著追憶離世思潮的時期。更為重要的是,孔尚任有著極為特殊的身份——孔子第六十四代孫。作為孔子嫡系的子孫,孔尚任必然要尊崇至圣先師的教誨,在這個特殊時期更要深刻體味孔子的民族觀念。于是,孔尚任就面臨著人生的重大選擇:作為孔族后裔,是不仕二朝,嚴格恪守夷夏之大防?還是退而求其次,歸隱田園?再或是“識時務”做清朝順民?最終,孔尚任沒有脫離“學而優則仕”的傳統文人的人生軌道。
雖然孔尚任不安心于隱居世外,但他也絕不是完全歸順新朝。他的內心始終滿懷著對歷史的敬畏和“興亡之感”。《桃花扇·本末》中寫道:“族兄方訓公,崇禎末為南部曹,予舅翁秦光儀先生,其姻婭也。避亂依之,羈棲三載,得弘光遺事甚悉,旋里后數數為予言之。”[2]“族兄方訓公”所講得前朝遺事足以打動孔尚任的內心,激起他的創作欲望。
因此,孔族后裔的特殊身份,對孔尚任創作《桃花扇》產生了特殊的影響。他要秉承孔子的民族觀,銘記漢人身份,抒寫“興亡之感”。但如何抒發這種興亡之感,如何避免因感懷歷史而遭致文字之禍?是孔尚任面臨的更為艱難的選擇。
二、學而優則仕的道路
雖然選擇了入仕為官的道路,但是孔尚任的仕途走得并不平坦。
康熙十七年(1678)秋,31歲的孔尚任游濟南,參加鄉試未中。后游石門山,隱居其中。34歲那年,入仕之心強烈的孔尚任典田捐納,獲得了監生的科名。康熙二十三年(1684),可謂是孔尚任的人生轉折年。這年九月,康熙南巡,返京時路過曲阜祭祀孔子。孔尚任受衍圣公孔毓圻推舉在御前講經,得到康熙的稱許,當即被破格任用。此時的孔尚任對統治者充滿了感恩戴德之情,“犬馬圖報,期諸沒齒”。
康熙二十四年(1685),孔尚任被召入京。次年,他隨工部侍郎南下淮揚治水。滿懷壯志的孔尚任看到的卻是官員的無作為:“九重圖畫籌難定,七邑耕桑戶未收。為向瓊筵諸水部,金尊倒盡可消愁?”(《淮上有感》)。[3]空有一腔壯志的孔尚任面對官場的腐敗與人事爭斗,頗為失望。這一時期,他游歷了南明故地。他游秦淮河、過明故宮,訪問并結交明代遺老,接受他們的感懷之情,加深了對南明弘光王朝興衰的認識,為繼續創作《桃花扇》做了充分的準備。
康熙二十九年(1690),孔尚任結束湖海生涯回京,官國子監博士。此時,重回天子腳下并未給他的官途帶來轉機。始終遭受冷遇的孔尚任相繼創作了《岸堂稿》、《長留集》等詩文作品,抒發自己壯志難酬、窮困潦倒之情。
康熙三十八年(1699),三易其稿的《桃花扇》定稿,一時間洛陽紙貴,王宮官員爭相借抄,康熙也索去閱覽。次年春,《桃花扇》上演,引起朝野轟動。孔尚任隨即被罷官。
從孔尚任的為官經歷可以看出,他對統治者和官場的認識是由感性到理性,由一腔熱血到心灰意冷。孔尚任剛做官時,對康熙報以感激之情,他也渴望在官場做出一番成就。但隨著仕途升遷的坎坷,隨著他在宦海沉浮中嘗盡世間冷暖,他對康熙所謂的知遇之恩有了更清醒的認識,對官場的殘酷現狀也有了更深刻的體悟。而孔尚任在南下治水期間,游歷南明故地,撫今追昔。與前朝遺老的深入接觸,讓他對歷史興亡的規律有了深刻的認識。種種的經歷決定了他在《桃花扇》的創作中,有意識地把南明的興亡歷史與現實困境相聯系,客觀地書寫歷史浮沉的規律。可以說,《桃花扇》是孔尚任成熟、理智的創作。
三、滿漢地主階級的合流
由此可見,孔尚任在創作《桃花扇》時的思想情感是極為復雜的:首先,他作為漢人,又是孔子第六十四代孫,需要站在漢民族的立場之上,記錄明亡清興的歷史。其次,他曾受恩于康熙,也曾期盼在官場中能有一番作為。但他的仕途生涯幾起幾落,使他對官場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加之他生活的年代,清朝的統治已經進入平穩的時期,民族意識相較于早期抗清時淡弱了很多,這決定了他不可能冒著被“文字獄”的風險,過分地以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角度“悼明”。
此外,還需要注意孔府與清廷的關系。盡管清朝實行剃發易服,對漢文化造成破壞,但是滿清貴族對漢族傳統文化仍是持以接受、尊重、保護的態度。孔府作為歷朝一品公爵府第,世享尊榮。而儒家學說在封建社會中的統治地位是難以動搖的。這一時期,康熙不遺余力地推崇尊孔崇儒的政策,全面吸收儒家學說。依照孔子的凡奉行周禮者皆為華夏的思想,非漢統治者只要是在堅守漢文化的基礎上,便可以為漢人所接受。更為重要的是,康熙積極提拔任用漢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他采取祭孔、開科舉等文化措施,力圖安撫漢族知識分子,以求在政治角逐中,獲得受到認可的“正統”地位。
可以說,這一時期漢、滿地主階級已經合流,“所以孔尚任——孔府——清王朝結成了不可分割的階級一體關系,而正是封建社會傳統的君臣關系,它對清王朝的責任感,對康熙的至誠,是一以貫之的”[4]所以,孔尚任作為這個時代的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中的一員,他要維護宗族利益,維護階級利益,要以大局為重,要站在客觀的角度,希冀清王朝吸取南明滅亡的歷史教訓。
四、以客觀視角,書寫歷史興亡的規律
于是,孔尚任在創作中所面臨的問題便是:作為“圣裔”,如何對待明亡清興的歷史?曾受康熙恩寵的清廷官員如何書寫前朝歷史?作為滿漢合流的地主階級中的一員,如何客觀深入感慨歷史變遷?孔尚任采取地辦法便是:“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盡管無法露骨地記錄清軍屠城的悲慘場景,也無法直接地的描繪歷史變遷、國破家亡之痛,孔尚任只好采取以小見大的方式,從侯方域與李香君的“兒女之情”入手,以小情見大情,以小家的破裂見大國的沉淪。把候李二人的結合、離別、雙雙入道,與政治斗爭的發展緊密聯系在一起,把對舊朝的悲憫和歷史感懷融入進人物的悲喜離合之中。
孔尚任所站得角度絕對不是“反清”的狹隘民族主義,也不是一味的“頌清”。他的立場是中立、客觀的。盡管作為歷史劇,《桃花扇》自然有虛構的地方,但孔尚任采用征信求實的原則,做到了藝術真實與歷史真實的統一。
孔尚任站在歷史長河之外,記述明亡清興的史實,總結歷史發展的規律,希望清王朝以南明滅亡的痛史為借鑒,避免由盛世變為末世。正如井維增的評價:“不能以是否反清作為標準。道理很簡單,中華民族是個大家庭,歷史上各民族之間的斗爭雖然有是非之分,但決不能以漢族為準則。……總之,《桃花扇》的思想內容是較為復雜的,對其政治傾向應從歷史和階級的觀點作全面的分析。”[5]盡管孔尚任對滿清入主中原、漢民族被統治的歷史表現出感傷之情,但他始終是清醒的,‘桃花扇底送南朝',一個‘送'正是他態度的體現。
即使劇中有對歷史興亡的感懷,但孔尚任“也不是回歸到以君臣之義為首要的封建倫理中,而是把國家放在了人倫之最上,以國家為君、臣、民賴以立身的根本”。[6]劇中,孔尚任借張瑤星之口說出:“兩個癡蟲,你看國在哪里?家在哪里?君在哪里?父在哪里?偏是這點花月情恨,割它不斷么!”[7]孔尚任對君臣民關系的思考不再是狹隘的民族之見,“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道理,其意義也就超越了明亡清興的易代之悲,更多的是對歷史興亡客觀規律的感懷與思考。
[1]吳楚才著.吳調侯編選.古文觀止[M].太原:三晉出版社,2008.299.
[2]孔尚任.云亭山人評點[M].云亭山人評點桃花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9):121.
[3]袁世碩.孔尚任年譜[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62.26.
[4]劉世德.桃花扇的出現適應了清初封建統治者的政治需要[J].光明日報,1956.
[5]井維增.《桃花扇》的政治傾向及其評價問題[J].齊魯學報,1981,(6).
[6]袁行霈.中國文學史 (第四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245.
[7]蔣星煜.《桃花扇》研究與欣賞[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