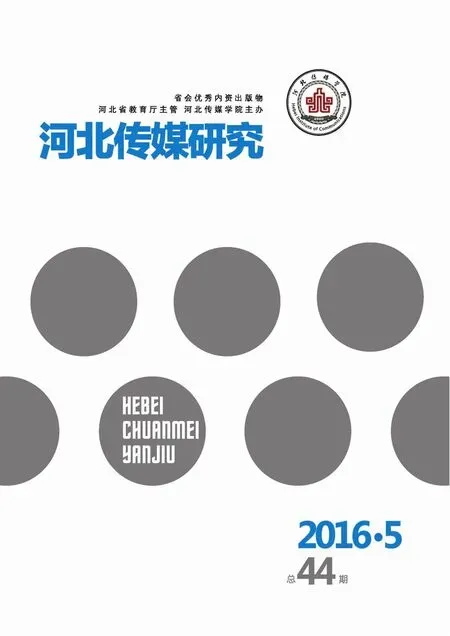論濟慈詩歌的唯美主義傾向
孫慧聰 王志慧 陳 娟
(河北傳媒學院,河北石家莊 050071)
論濟慈詩歌的唯美主義傾向
孫慧聰 王志慧 陳 娟
(河北傳媒學院,河北石家莊 050071)
作為19世紀初英國浪漫主義詩人,濟慈熱愛美并在作品中宣揚美,被看作是唯美主義的先驅之一。濟慈詩歌的唯美主義傾向表現在:脫離真實之美,表現為神話入詩、夢幻之美、悲情之美;美與真實結合,表現為理性之美、心靈之美、藝術形式之美。
濟慈;詩歌;唯美主義
濟慈是19世紀初英國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之一,同時也是一位純美詩人,他對美有著無限的眷戀,“美”成為他筆下使用最頻繁的名詞。正因為濟慈對美的熱愛和崇拜,唯美主義者將他看作先驅,許多文學家也認為唯美主義的一些原則早在濟慈的詩歌創作中就得到部分確立。品讀濟慈的詩歌,可以發現濟慈詩歌中的唯美主義傾向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脫離真實之美
濟慈一生都懷有一種脫離真實的審美恐懼:美麗的花朵即將枯萎,美麗的容顏即將褪色,美麗的心情即將被破壞,美麗的女人即將變成丑陋的妖怪。究其原因,一方面,19世紀初英國社會受工業革命影響,人們大多崇尚名利,庸俗虛偽,人情味不足。另一方面,濟慈遭受了殘酷的命運安排:父親意外死亡、母親突然改嫁使孩提時的濟慈孤苦無助;緊接著傳來濟慈祖父的死訊;之后濟慈母親離家出走,等到再回來時已經是病入膏肓直至死亡。從此,濟慈兄妹只剩下外祖母這個唯一的依靠。然而好景不長,外祖母也離他們而去。后來濟慈的弟弟也得了在當時無法醫治的肺結核……濟慈的親人接二連三地從生活中消失,使濟慈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疾病和死亡的折磨。殘酷的現實使他變得痛苦而敏感,這使他超脫了平庸的生活,轉向藝術想象。加上他卓越的才識,成就了一位唯美詩人。
(一)神話入詩
古代神話是濟慈在學校時的必修課程。那時的濟慈還處于天真年少時期,他在最初接受教育之際便走進了希臘神話藝術的殿堂,接觸并認識了希臘神話中的人物和故事并對此產生了極大興趣。于是,神話入詩便成了濟慈抒情長詩創作的結構源泉和思想動力。
濟慈的《安狄米恩》是一部取材于希臘神話故事的長詩。濟慈沒有沿用原始神話的故事情節,而是將其適度改編,使其更具創造力。在詩中,主人公安狄米恩先是在夢幻中看到了純潔美麗的月亮女神,從此,便開始堅持不懈地尋找她。于是,詩歌情節的發展和變換都圍繞這位人間王子對女神的思戀與追求而展開。濟慈通過對自然美景的描述與眾神歡樂的建構,勾勒出神境之美、自然之美、山谷之美、姐弟情感之美、圣夜戀情之美,使得詩歌充滿神奇而美麗的內容,表達了濟慈對古代文明中美的世界的追求,反映了他對現實環境的憎厭。詩歌在整體上呈現出唯美主義傾向。
(二)夢幻之美——夢醒美去
作為一名浪漫主義詩人,濟慈總是喜歡脫離苦難的現實創造一個想象中的美好世界。從意境看,濟慈許多詩歌中所創作的美都是一種夢幻式的美,而夢幻過后,夢醒美去。
濟慈在《睡與詩》中描述了詩歌中兩種不同境界的美。第一種是他“首先要去游逛的”“花神和老獵鷹的國度”,這是一個由幻想創造出來的純美國度。在這個國度里,綠衣仙女在翩翩起舞,玉腕女神和詩人在嬉戲;渴了可以“品嘗那里清純的甘泉”,餓了可以“以鮮活的蘋果和楊梅充饑”。這種境界中的夢幻美是愉悅感官的,它不涉及任何社會功利,只給詩人個人帶來滿足。然而,詩人知道這只是夢幻,夢醒后還是要進入第二個境界。
現實的美是短暫的,只有幻想之美才永恒真實。濟慈在其詩歌《幻想》中說:
甜蜜的幻想啊,讓它脫韁;
夏天的愉悅被享足就消亡,
春天的種種賞心樂事,
等花開花謝一切都流逝……[1]193
現實是丑陋的,而幻想是如此的美妙,因此詩人就會沉浸到幻想中去,他的詩歌形態也表現出自然幻覺之美。然而他在詩中用“消亡”“流逝”表達了對美之易逝的憂傷。
《冷酷的妖女》創作于1819年4月,創作背景源于一件事。那年4月中旬,濟慈收拾他和弟弟托姆留在威爾道的信件,發現了一堆署名為阿米娜寫給托姆的情書,然而他發現這些情書都是托姆的朋友查爾斯·威爾斯偽造的,阿米娜這個女性人物根本就不存在。這件事讓濟慈憤怒,同時也再一次喚起濟慈心中“美原來是夢”的感傷。在這種情緒的驅動下,濟慈創作了《冷酷的妖女》。這首詩描寫一個騎士遇到一位姑娘,這位姑娘“美麗妖冶像天仙”,騎士與妖女在一起嬉戲并享受著這份歡樂,因此這首詩主要篇幅描寫兩情相悅的場景:
我為她做了一頂花冠……
她對我凝視,像真的愛我……
她側著身子依著我,
唱出一支仙靈的歌謠……
她用奇異的語言說話,
想必是“我真愛你! ”[1]203
然而,這一切的美好原來只是一場夢。騎士一覺醒來,發現美貌的妖女不在身邊,她的甜言蜜語與溫柔撫愛只是在夢中出現。于是,回到現實,夢醒的騎士在湖邊沮喪地徜徉,孤獨惆悵。
(三)悲情之美
《亮星!但愿我像你一樣堅持!》是一首杰出的愛情詩。這首詩中所描繪的愛情讓詩人陶醉,令讀者沉迷:
以頭枕在愛人酥軟的胸脯上,
以便感到它柔軟的起伏,永遠……[1]133
這兩行詩文把愛情刻畫得纏綿刻骨,但它卻被死亡的陰影所籠罩:
而醒來,心里充滿甜蜜的激蕩,
永遠傾聽它溫柔地呼吸不止,
就這樣永生......或昏醉地死去。[1]133
詩人一方面希望能留住時光和甜美的愛情,盡情地享受這一切,另一方面又希望即使是死亡,也要在體驗愛情的巔峰中昏迷而死。這兩種愿望概括了全詩生與死、愛情與理想的主題,并將二者達到了永恒的境界。即便是死去了,愛情將會永遠停留而永生。濟慈把這種悲情也表現得如此之美,讀者又一次看到了他對美的執著追求。
在《我恐懼,我可能就要停止呼吸》中,濟慈又一次提到了死亡,并表達了對美即將消逝的恐懼:
——于是,我一人獨自
站立在廣大世界的涯岸上,思考……
等愛情和名譽沉降為虛無縹緲。[1]99
濟慈的詩歌充滿著在萬事萬物中尋求美的渴望,甚至是死亡,也被他寫得如此美麗。也許悲情的東西最能打動人們內心深處,或許正是這種悲情才會使得詩歌愈加美麗。這正是唯美主義的體現。
二、美與真實的結合
濟慈在寫完《安迪米恩》第二章之際結識了朋友貝萊。比濟慈年長4歲的貝萊博學多識,不僅對詩歌,還對其他各領域知識有較為深刻的理解。濟慈后來在信中稱貝萊為渴求真理的人,或者說是“有想象力但同時又關注想象結果的那類人——他們的生存部分依賴于感覺,部分依賴于思想——對他們來說歲月必定帶來哲理情懷——我認為你就是這類人。”[2]133濟慈通過貝萊看到自己是憑借感覺追求美,而對方更為重視的是通過思想與推理追求美。在這種感覺與思想的對撞中,濟慈產生了把美與真實結合起來的想法,即心中的美雖然是由想象創造出來的,但完全可能以一種真實的方式存在。
(一)理性之美
濟慈在少年時代就被安狄米恩與月神的戀愛故事所打動,為抵觸“美不等于真”的審美恐懼,濟慈需要在一些作品中宣揚“美等于真”,以求心理上獲得平衡。于是,《安狄米恩》的開篇就表達了濟慈對于美的敏銳之愛:一件美的事物永遠是一種快樂;它的可愛與美好隨著歲月的流逝逐漸增加;它永遠不會變成虛無;而是永遠讓我們享有一個靜謐的居處,一次睡眠,充滿著美夢健康和均勻的呼吸。濟慈不知自己為何如此著迷于這個故事,只知道在細細敘述這個未被別人展開過的故事時,自己心中有一種觸及先驗之物般的體驗與歡樂。濟慈相信美的事物是一種永恒的愉悅,相信讀者也能從他的敘述中感受到同樣的愉悅。濟慈的《安狄米恩》雖然是再現希臘神話故事,然而故事的結尾創造性地將月神與印度女郎合二為一變成一人:
黑眼睛姑娘興高采烈地站起來,
使安狄米恩吃驚,
她用甜蜜似愛情的新聲說道:
“憑愛神的鴿子,
憑我胸中百合花一般的忠貞起誓,
你可以這樣做!親愛的年輕人!……”
啊,他見到了福柏,他的情之所鐘啊![1]144
這樣的結局使得安狄米恩與月神之間的現實之愛成為可能,于是這對相愛的戀人消失在圣林中。在這首詩中,濟慈讓自己一系列的美的幻想以一種真的方式存在,美不只是停留在幻想層面,而是賦予理性。美只有與真實相結合,才能更加深刻。這首詩既體現了濟慈的審美價值追求,又顯示了濟慈的藝術創作心志和創造性想象力。
(二)心靈之美
濟慈在《睡與詩》中闡述了自己的詩歌理念。他祈求命運給他10年時間,讓他從事他的心靈所擬定的業績,即在詩歌中尋求美。他在這首詩中描述詩歌美的不同境界。上文提到第一種境界是想象的純美世界,而第二種境界則是“更崇高的生活”,里面有“人心的痛苦和沖突”。這種境界的美不再是愉悅感官,而是賦予了深層的理性內容。濟慈明確表示,要舍棄第一種境界而進入第二種境界:“是的,我必須舍棄他們去尋找更崇高的生活。”他提到要反映“人心的痛苦和沖突”,就要去表現社會生活,反映大眾疾苦,賦予詩歌深刻的思想內容,其作用不再是為了只滿足詩人個人。此外,濟慈在詩中還明確表達了詩不是為了詩本身或詩人自己,而應是為了“人”,為了人世上的痛苦,為了提高人的思想境界。這“偉大的目標”和美的第二種境界完全一致,也符合濟慈一貫主張的“為世界做些好事”。由此可見,濟慈胸懷崇高目標,并且執著、奮不顧身地追求。這體現了更高層次的美,即美在心靈。這又是唯美主義的一種體現。
(三)藝術形式之美
形式這一概念在唯美主義者中逐漸有語言結構、繪畫、雕刻、音樂和美學統一起來的趨勢。無論是語言結構、繪畫還是音樂之美,都在濟慈的詩歌中有所體現。濟慈雖然以詩歌作為最高追求,但與海登的頻繁交往使他懂得不能小覷其他藝術門類,例如音樂、繪畫、雕刻等,這些藝術在某些方面能夠產生比詩歌更為強烈的藝術效果。因此,濟慈的詩歌謳歌了繪畫之美、音樂之美。
1.繪畫之美
濟慈的《希臘古甕頌》創作于1819年。濟慈在一件普通的藝術品中發現美的典型。面對雕刻著圖案的古甕,濟慈情不自禁,陷入想象之中。
從全詩看,濟慈在心中塑造了一個代表藝術之美的古甕形象。在第一部分的詩句中,古甕上的石雕是令人悠然神往的古代生活圖景:
你——“寧靜”的保持著童貞的新娘,
“沉默”和漫長的“實踐”領養的少女……
怎樣瘋狂的追求?竭力的逃脫?
什么笛,鈴鼓?怎樣忘情的狂喜?[1]23
這是一個喧鬧的歡慶場面,有使用風笛和鈴鼓的樂隊,欣喜的少年正按某種儀式瘋狂追逐,多情少女則在鼓樂聲中俏皮閃躲。這些圖景描寫生動,令人想到古希臘人為祭祀酒神而舉行的狂歡歌舞。
在接下來的詩行中,濟慈贊美了攝取人生美妙一瞬間的畫面:
樹下的美少年,你永遠不停止歌唱,
那些樹木也永遠不可能凋枯;
大膽的情郎,你永遠得不到一吻……
她永遠不衰老,盡管摘不到幸福,
你永遠在愛著,她永遠美麗動人![1]23
畫面上,石雕上的美少年想吻他心愛的姑娘,雖然他總也吻不上心上人的嘴唇,但他可以一直享受接吻前的甜蜜等待;而年輕的少女雖然不能與近在咫尺的情郎攜手,卻能夠永葆青春與美麗。這樣的場景使濟慈擺脫了之前的審美恐懼,引發了對藝術的看法:時間在畫面上停止了流逝,藝術形式給現實以某種永恒。濟慈認為,風笛、樹木和少男少女一旦被畫在古甕上,就變成了永恒的美。聽不見的樂聲比聽見的更美,捕捉不到的感受比捕捉到的更美,沒有經歷的比經歷過的更美,因此,詩人寫道:
啊,幸福的樹枝!你永遠不掉下
你的綠葉,永不向春光告別;
幸福的樂手,你永遠不知道疲乏,
永遠吹奏出新鮮的音樂;
幸福的愛情!……
永遠等待著享受……[1]25
在這些詩句中,畫在古甕上的風笛、樹木和戀人代表了一種永恒美的存在狀態。這是藝術為人類作出的令人快樂的貢獻之一。在詩的最后,濟慈從畫面的世界中掙脫了出來,感慨地對古甕說:
啊,雅典的形狀!美的儀態!
你呵,緘口的形體!你冷嘲如“永恒”……
等老年摧毀了我們這一代,那時,
你將仍然是人類的朋友……
“美即是真,真即是美”——這就是
你們在世上所知道、該知道的一切。[1]27
濟慈在這里其實是表達了自己的信念:除了真和想象力與美相連外,藝術也與美同在。因此,“美即真,真即美”中所說的“真”屬于藝術范疇。濟慈在普通的古甕上發現的這種藝術美,超越了時間和空間的概念,獲得了永恒,即藝術之美在于永恒。
2.音樂之美
如果說《希臘古甕頌》贊美的是訴諸視覺的造型藝術的話,《夜鶯頌》則更多地詠頌了訴諸聽覺的自然音樂,即夜鶯的歌聲。《夜鶯頌》的靈感來自梅園里的夜鶯,其開篇便描寫夜鶯的歌聲給自己帶來的聽覺享受。這種享受是一種類似于吸毒后陷入麻木境地的陶醉之情,是一種以痛感為先導的歡欣:
我的心疼痛,困倦和麻木使神經痛楚,
仿佛我啜飲了毒汁滿杯……
是你的歡樂使我過分的欣喜……
你讓悠揚的樂音
充盈在山毛櫸的一片蔥蘢和濃郁里,
你放開嗓門,盡情地歌唱著夏天。[1]21
在接下來的詩篇中,夜鶯的歌聲激發了詩人一連串的想象,一幅幅色彩瑰麗的圖畫和情景相繼展現。然而無論詩人的想象有多么不著邊際,夜鶯的歌聲卻一直與其相隨,就像是畫面之外的音樂伴奏,達到了音畫合一的效果。因此,全詩被賦予一種想象和音樂相結合的藝術結構,讀者完全可以感受到作為藝術之一的音樂的魅力與美麗,這種美深入人心、震撼人心。另外,在這首詩的后部,夜鶯被稱為“永生的鳥”:
你永遠不會死去,不朽的精禽!……
我今天夜里一度聽到的歌音
在往古時代打動過皇帝和村夫……[1]22
這些詩句說明夜鶯已經被點化成藝術精靈,它的歌聲永遠不停,瞬間因此也被延續成永恒。藝術神話之鳥能從古代唱到今天,詩人借此又一次通過音樂藝術形式表達了他的唯美主義傾向,即藝術之美在于永恒。
結語
濟慈熱愛美、歌唱美,他的詩歌追求“美”和“純粹的藝術”,體現了唯美主義傾向。在西方文學史尤其是英國文學史之尚美傳統中,像濟慈這樣典型的為追求純美而大聲疾呼的詩人極為少見。雖然濟慈生命短暫如曇花一現,但他的作品為西方文學史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的詩歌正如他所追求的美一樣,獲得了永恒。
[1]約翰·濟慈.濟慈詩選(英漢對照)[M].屠岸,譯.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1.
[2]傅修延.濟慈評傳[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133.
(責任編輯:邢香菊)
2016-06-05
孫慧聰,河北傳媒學院國際傳播學院副教授,碩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學;王志慧,河北傳媒學院國際傳播學院副教授,本科,研究方向:英語教育;陳娟,河北傳媒學院國際傳播學院副教授,碩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