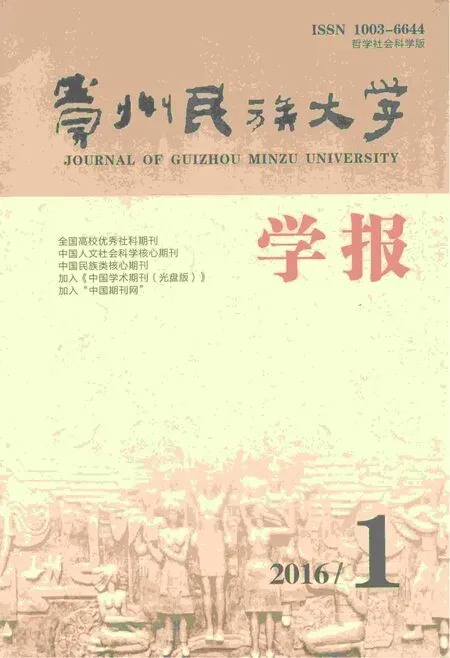達馬斯卡證據法理論中三個程序支柱的相互關系*
陸 而 啟
達馬斯卡證據法理論中三個程序支柱的相互關系*
陸 而 啟
達馬斯卡在《漂移的證據法》一書中提出“支撐英美證據法大廈的三根支柱”為原型審判法庭、集中式程序和對抗制。這種觀點的合理性在細致檢討其程序支柱與證據規則的相互衍生和支撐關系之前,甚至首先是檢討這三個支柱之間的相互關系。通過與不同觀點的相互比較以及對英美法系訴訟文化背景的考察,這三個支柱之間的確存在著獨立性、充分性、關聯性和層次性的關系,這三個支柱不獨可以解釋證據法的過去,還可以因應程序的變化而預測證據法的未來。
達馬斯卡;程序支柱;普通法證據;相互關系
作者陸而啟,男,漢族,安徽長豐人,博士,廈門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福建 廈門 361005)。
一、引言
經驗描述往往比理論論證更富有貼近真相,但是任何經驗往往又是在一定理論視角下的主觀描述。對在人類證據法發展史上獨具一格的英美證據法產生原因的深層背景的追問,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把歷史考證置身于理性思辨之中,因而每個人的結論都帶有一定的主觀性。一個證據制度歷史起源上的因果關系可能證明規則的正當性,但也有支持某個證據規則和慣例的有說服力的理由并沒有歷史起源上蛛絲馬跡。而達馬斯卡在其《漂移的證據法》一書中認為有二元的法官-陪審團制度、程序的時間集中制和當事人主導的對抗制這三個因素對英美法系證據法的產生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從而稱之為“支撐英美證據法大廈的三根支柱”。[1]達馬斯卡的分析一石激起千層浪,雖然其以文化作為其制度基石,但是分析的內容主要還是集中于一些制度特征層面,還是受到了來自Friedman對證據制度進行價值解釋方面的批評。[2]P1921-1967其實,制度本身就是文化的組成的部分,承載著價值觀念,但是不是制度圍繞著價值轉。制度除了有縱向的歷史流變之外,還存在橫向的比較差異。從我國學者湯維建對達馬斯卡該書內容的梳理之中,[3]可以看出三個支柱的相互關系。
二、三個支柱的獨立性
有學者認為達馬斯卡對英美證據法的三大特征分別開來加以探討,在分析上存在著問題或缺陷。[4]P1493歐洲大陸以一個專業法官的糾問制度來填補英諾森三世禁止神裁留下的空白,而在英格蘭則出現了以12個外行的地主鄰居組成的陪審團來行使審判權。有關陪審團的神話,雅典、羅馬、英國《大憲章》(1215年約翰王與貴族叛軍間簽訂的停火協議)都曾被視為該制度的創始者。事實上,陪審團審判與它們之間并無聯系。其有跡可循的是,幾個世紀以來,英國統治者總會召集一群宣誓者,然后再提供資訊給他們,而早在西元879年,在阿爾弗雷德大帝和丹麥國王古斯魯簽署和平協議的時候,就可以看出這十二個宣誓者與審判的關系。該協議里規定,在任一統治者的領土上的殺人犯,如果想要洗刷罪名的話,可以要求由十二名宣誓者進行審判(如果他敢的話)。只要一個簡單的想象步驟,就可以把共誓滌罪的儀式轉型為陪審團審判。[5]P91-有學者指出,羅馬帝國的消亡使得古希臘和古羅馬的陪審制度“嫩芽”沒能生長起來。普通法的故鄉英國成為由“征服者威廉”從歐洲大陸帶到不列顛群島的陪審制度的“苗圃”*參見何家弘:《陪審制度縱橫論》,《法學家》1999年第3期。關于現代的陪審制度由法入英的觀點,參見Origin of the jury : The Frankish inquest, at Pollock & Maitland,The History of English Law , Vol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rchive, 1968, pp.140-143;還有更多的學者認為,陪審制度實際上起源于英國。轉引自王利明:《我國陪審制度研究》,《浙江社會科學》2000年第1期。范·卡內岡教授總結了前人的研究成果,逐次批駁了陪審制英格蘭本土起源和北歐起源的學說,肯定了布倫納的觀點,即陪審制起源于加洛林王室,后傳入諾曼底并由諾曼人引入英格蘭。參見[英]卡內岡編著:《英國普通法的誕生》(第二版),李紅海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譯者序第11頁。因此,達馬斯卡指出,從歷史經驗上看,非專業人員的裁決或者陪審團審判與技術性的證據法并沒有必然聯系。古羅馬的平民法官、古代英國非專業治安法官以及專業法官和非專業法官組成的混合式法庭,可以循日常生活和個人事務中采用的習慣方法和策略進行事實認定,而不需要技術性的證據法。這更突出了作者所要論證的,之所以需要證據制度,突出的不是外行人員的素質缺陷而是法官與陪審團的二元分權。
達馬斯卡認為,“普通法歷史上一些偶然因素導致這種時間集中式法律程序依賴于使用非專業事實裁判者”[6]P6,因為“業余裁判者都有其他事務,倘若審判分為一個個獨立的階段,則很難在開庭時將他們召集起來”[7]P83。傾向于“一審終結”的集中式審判產生后,并不是如影隨形于陪審團審判,而可以對證據制度和證據規則的形成和建構起著獨立的影響作用。例如,受舉證時限制度的限定而排除遲延提交的證據,是集中制審判所產生的直接結果,與實行陪審制不具有內在的關聯性。不過,一種二分地看,一些證據法則和慣例可能只適用于準備粗略(無專業偵查機構)而且時間節制(無常規上訴機制)的訴訟程序,因此,一方面,在當前可能“曠日持久”的典型或者假定訴訟模式之中就不具有意義,甚至當下的陪審團審判更為復雜;另一方面,即使一些保存下為“當庭訴辯式” (day-in-court) 審判所需要的證據法則和慣例在當下也需要重新檢討。
在到底對抗制還是陪審制對英美證據制度的形成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達馬斯卡似乎更青睞對抗制的作用。對抗制是指一種程序活動由當事人控制的裁判制度,而裁判者則基本上保持被動。達馬斯卡指出:“以這種方式來界定,對抗制顯然與法院組織結構的各種形式以及訴訟程序的時間安排無關。當事人之間的爭斗既可由專職法官來裁決,也可由業余法官來定奪;當事人可以在當庭訴辯式審判的單一輪回中對抗,也可以在分段審理的若干回合中較量”。[8]P103從歷史發展來看,英國陪審制逐步式微,但是其對抗制勢頭不減,甚至從庭審延展到庭前程序;而大陸法國家的民事訴訟采用對抗制程序模式,而其審判組織是參審制的。可見,對抗制也可以離開陪審制而存在,并且在不同的訴訟階段上延展或者滑動,正是對抗制而不是陪審制是普通法的核心觀念。
三、三個支柱的充分性
在達馬斯卡所提出的英美證據法的三個支柱之外,還有人認為,陪審團、宣誓(oath)和普通法的程序對抗制很大程度上是構成證據法的排除特征的三個因素,尤其是與開示規則相聯系,成本現在也可以加上去。[9]P2這里提出了宣誓的要素,宣誓昭示了一種證明制度的歷史文化背景或者宣誓審判的當代轉化。宣誓是證人作證的一個前提,未經宣誓的證據形式——屬于要排除的傳聞不得進入法庭調查領域。在英美國家出庭證人的宣誓是一種在尊崇宗教信仰基礎上的內心規訓,具有一定的預防作用,甚至是追究證人偽證責任后果的機制前提,湯維建認為,宣誓僅是從作證人的視角而非從訴訟程序中的主要角色(“訴訟主體”)來看待問題,因此有點邊緣和偏離重心。其實,在古羅馬和中世紀日耳曼國家盛行的誓審恰恰是原告或被告單方或雙方的宣誓為主,盡管在中世紀的日耳曼法中,宣誓神判除了“誓證法”(compurgation)還有有人到庭助誓的“輔助宣誓”(oath-help)制度,當代英美的刑事訴訟制度同樣賦予了被告人的選擇宣誓作證的權利。另外,蘭博約將對律師的司法控制等因素歸入其支柱性因素。對律師的司法控制也對證據法的形成起了作用。[10]對律師的司法控制則體現了對抗式訴訟制度的過度律師化及其矯正。還有人將之歸因于試圖獲得公正對判決的可接受性而不論判決正確與否。[11]
筆者以為,首先,不論是宣誓還是對律師的控制,都將法律看作是一種限制權利的手段,更準確地說是出于對為或者代表當事人而偽造證據的一種擔心,而不是約束權力的命令。證據法產生的這種歸因不管是出于防止證人作偽證還是控制律師這些都使得證據法帶上了“治民”的色彩。或許在現代證據法應該轉換為“限權”視角通過對事實審理者進行約束來確立其規則的合法性;甚至現代證據法也突破了傳統的強調對客觀事實進行準確認識的視角而轉向了訴訟主體的溝通共識,因而作為訴訟主體的控辯雙方可能不僅僅局限于準確的證據提供而突出其暢通的意見表達渠道。其次,基于其他因素所產生的證據規則還是可以被解釋為達馬斯卡的三種要素之內。傳聞證據規則所產生的原因可以歸結為陪審團審判和對抗制模式,前者防止不可靠的傳聞混淆陪審團的視聽,后者要求證人出庭以保障當事人有效地對證人實施交叉詢問,宣誓作為一種宗教文化因素并非證據法的主要原因,因為宗教強調的信仰而不是真實。此外,意見證據規則、品格證據規則等其他一些規則也難覓對“宣誓”的依賴成分。對律師進行控制的因素其實也屬于對對抗式審判的矯正;作為開示規則所考慮的“成本”因素,也是對集中審理制度的矯正;所謂裁判可接受度的后果或者價值評判往往也通過對抗式的意見宣泄或者表達制度渠道來實現。
可以說,舊證據規則更多的考慮是證據的資格問題,因此側重于一種外來的規范限制,而現代證據制度則更突出對證明程度的判斷和推理問題,側重于對法官自由裁量的內在限制。當然,對證據法的程序支柱的分析并不是意味著規則就一成不變,恰恰是為了在程序變動之中把握其可能的相應規則轉型。
四、三個支柱的關聯性
(一)正關聯
概而言之,集中審理包含了舉證質證集中和認證裁決集中。一方面,在英美法系庭審舉證質證活動都落在了雙方當事人身上,由此庭審體現了強烈的對抗式特征;另一方面,事實認定活動由陪審團來承擔,由于陪審團審判有人多、分布分散、陪審員兼職參審的非職業性和非營利性等特殊性,要求其能持續性并且能最好一次性地進行,因而,陪審團審判延伸出集中審判的要求。陪審團審判與集中制審判幾乎是一對孿生兄弟。集中式的訴訟程序的運作樣式比較適合陪審團審判,換句話來說,陪審團審判就是通過“集會”一樣的方式來決定案件,而開一次會要一次聚齊12個人都不容易,所以,庭審連續不間斷的集中審判制度是陪審團審判的一個內在要求。“英美法傾向于集中解決與提交給事實認定者的證據有關的問題”,達馬斯卡“則將晦澀的陪審團裁決與英美法的這種傾向聯系在一起了。”[12]P61所以,集中制對證據規則的影響,一定意義上可以看作是陪審制對證據規則的影響。在英美司法制度發展歷史上陪審制和集中制同步實行。湯維建指出,我國集中審判制度推行,也同樣帶動了證據制度的變化,如證據失權制度、證據交換制度、當庭質證制度以及證人出庭作證制度等等,一定意義上都與集中制的推行有內在關聯。[13]
當然,從歷史上看,陪審制的實行也有助于對抗制訴訟機制的形成。最早的陪審員“就是”證人,而他們“說出的真話”,是唯一需要的證詞。隨著知情陪審團審判向非知情陪審團制度轉變演化,作為發現案件真相的模式,也相應地發生了由“告知真理”向“發現真理”的轉變。[14]P12其審判的過程是:“在法庭上,每方當事人自己或者通過其律師首先向陪審團講述案件爭議問題和他們將要提出的證據,以便使法庭得知爭議問題的事實真相;然后他們就讓其證人出庭作證;每個證人都要先宣誓,然后就其知曉的案件爭議問題提供證據”。*William Andrew Noye: Evidence: Its History and Policies. (1991) p20.轉引自湯維建《英美證據法學的理性主義傳統》,載[美]約翰·W.斯特龍(Hohn W.Strong)主編,[美]肯尼斯·S.布榮(Kenneth S.Broun)等編著:《麥考密克論證據》第5版,湯維建等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該文又收錄到湯維建著:《民事證據立法的理論立場》,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雙方當事人在橫向上的信息交換和觀點交鋒要以法官作為法律的看門人做出指示在縱向上傳遞給12名負責裁決的陪審員,陪審團審判最后的參與者。然而,英國學者薩達卡特·卡德里(Sadakat Kadri)依然斷言,陪審團裁決的最重要特征絕不是理據,而是裁決的存在。[15]P336-337因此,離開陪審制而依然可能成立的對抗制,在具體的運作方式上,尤其在證據規則和證據制度的內容上,會發生一定程度上的變化。
(二)負關聯
在陪審團逐漸淡出訴訟舞臺以后,法官從法律的守門員轉變為獨攬認定案件事實和適用法律大權的單一主體,而正是為了準確適用法律刺激了法官探求事實真相的沖動。法官積極參與和介入事實認定過程,遏制了當事人雙方試圖激發陪審團審判感情用事的積極性,導致了對抗制一定程度上的弱化。可見,陪審制的弱化引發了對抗制弱化的連帶反應。[16]
傳聞規則甚至都可以集中體現陪審制(防止誤導陪審員)、集中制(防止訴訟拖延)和對抗制(對質詢問)三根支柱的支撐作用。如果不實行陪審團審判,也只能得出結論說該特定的證據規則在有效性上被弱化了,而不能在邏輯上得出結論認為該證據規則就要消失了。如果其他兩根支柱依然存在,那么,該證據規則仍然會發揮其作用。[17]P23
因為庭前準備程序對法庭訴訟行為留下的長長的影子,對非專業事實認定者的信賴與以審判為中心不再形影不離,歷史上牢不可破的普通法中證據法之基礎理論的基體已經解體。不過,因為當事人雙方律師材料豐富、漫無目的的審前準備,這種證據資料的增加,在拖垮對方當事人的時候,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和無序性既模糊了事實真相,又激化了庭審的對抗性。自從這種準備模式成為當代對抗制程序的一個方面后,作為普通法證據理論基礎的集中制就已獨立于其對抗制了。“雖然陪審團審判和時間被緊縮的訴訟已經衰落,但是各種訴訟的當事人仍然求助律師以幫助其解除所涉責任”。[18]P188
五、三個支柱的層次性
追問證據制度產生的理論基礎和本質原因,這種追根溯源可以使我們深入了解一些復雜的證據制度的來龍去脈,也可以對表面現象穿針引線。達馬斯卡一開始就把這個問題擺在我們面前,一種較老觀點認為,英美的證據法是“陪審團之子”,以此防止陪審團的認知弱點。其代表人物有賽耶(James Bradley Thayer),[19]P266威格莫爾(John Henry Wigmore)等。另一種更近觀點認為,英美的證據法是“對抗制之子”,以保證提供公平機會獲得公正或者克服對抗式對真相的扭曲,其代表人物有摩根,[20]/[21]P156南西。[22]/[23]耶魯大學著名教授約翰·蘭博約(John H. Langbein)雖然不認同米特蘭和威格莫爾等人的觀點,即中世紀的知情陪審團(self-informing juries)作為積極的鄰里調查者轉換到被動聽審者需求證人出庭和形成法庭指示模式而產生證據法,他自己從御座法院首席法官達德利·賴德爵士的審判筆記之中總結認為其中蘊含的前現代證據法關注書證真實性和證人資格,而至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才產生以口頭證據為核心的現代證據法為避免陪審團成員無力評估證據而采傳聞規則等,也認為現代證據法恰恰是克服陪審團的內在弱點而存在和發展的[24]P1168-1202。湯維建認為,集中制審判相對于陪審制以及對抗制來說,其對證據制度的形成和發展并不具有主流意義和決定性作用。那么,在陪審制和對抗制兩個主要因素(即兩個主要理論)中,究竟是哪一個因素處在更高的層次從而具有根本性?必須要作一個選擇性的回答。克勞斯認為兩者理論并不排斥,有時被交叉在一起。
在這三大支柱中,對抗制最為根深蒂固。但是,陪審制與對抗制在美國證據制度形成中的作用如何?通說認為是陪審制的推行產生了證據制度。因此,證據制度是陪審制之子。達馬斯卡提出一個疑問,12世紀形成了陪審制,到17、18世紀才正式地、大規模地形成的證據制度,而這之間存在12-17世紀之間只有陪審團而無證據規則的“斷檔”現象。因此,達馬斯卡認為,證據規則的產生與實行陪審團審判沒有必然聯系,而與將審判法庭作出內在職能的劃分有必然的聯系。證據規則是用來規范二元化法庭關系的調節器。甚至認為,只要審判組織分化為兩個部分,哪怕二者都是專業的審判者,也同樣需要證據法的調整。[25]P35克服陪審團的認知缺陷僅僅是證據法產生的不太重要的因素,而陪審團集體決策和秘密評議以及審判法庭分為非專業和專業兩部分的二元化審判組織制度,才是形成證據法的根本原因。然而,陪審團審判對證據制度的需求,一方面不是以法定證據制度為彌補事實認定者的認知缺陷或者限制事實認定者的過分自由來尋求事實認定正確,而是以事先的程序監督實現陪審團裁判結果的正當化;另一個方面是體現了職業法官以證據規則來控制外行法官實現二者的衡平。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陪審團制度的出現,本來就是對職業法官不予信任的產物;證據規則的出現,則成為對陪審團不予信任的產物。
針對于陪審團對英美法系證據規則支撐作用的程度如何,隨著陪審團審判的衰落,傳統的、現在仍有法律效力的證據規則是否依舊在發揮作用呢?進而言之,歷史上,哪些證據規則因陪審團制度產生,而由陪審團制度起著支撐作用?這些證據規則中哪些因為陪審團制度的抽離而完全失效,哪些可能僅僅是擺設,哪些還可以繼續發揮作用?達馬斯卡認為陪審團審判與證據規則并無必然關聯。對此,達馬斯卡給出了幾點理由:第一,證據規則的產生與陪審團的產生不同步,并且遠遠落后于陪審團的產生,恰恰是專業人士發展出了技術性的證據規則。第二,陪審團制度歷史早期向美國的傳播以及18世紀末在法國的移植,更突出的是將陪審員設想為人民主權的代表以制約專業法官的濫權擅斷,可見,陪審團審判并沒有成為技術性證據法的發源地,反倒便利了抵制羅馬教會證據法的滲透,同時產生了自由心證制度。[26]P34-36由此存在第三個問題,既然陪審團事實裁決方式本身是不需要復雜的證據規則,那么,不正好可以用證據法來矯正陪審團可能具有的認知缺陷嗎?然而,達馬斯卡將陪審團與證據法的關聯推翻之后再踏上一只腳,認為,以技術性證據法來規范陪審團是與陪審團具有認知缺陷的假定相互矛盾的,這就接近了中國成語“對牛彈琴”的意味。然而,筆者以為,達馬斯卡還是看到了證據法所具有的約束和控制非專業人士的認知傾向的目的,甚至他也看到了證據排除規則更多的是由職業法官掌握,但是他對這種程序目的和實行機制提供了另一套解說,也就是“二元分化的法庭”,然而,我必須認識到之所以存在二元分化,恰恰是人為理性和自然理性兩種認識論互補的結果,并且將這兩種思維模式分別極化為法官和陪審團兩種組織元素,由此可見,英美證據法的形成還是與陪審制脫不了干系。
對于對抗制和陪審制對英美證據制度的形塑作用那個更甚?美國學者蘭博約提出了刑事訴訟的律師化而導致對抗式訴訟模式形成和發展的命題,同樣,就證據制度的發展而言,他認為:“自18世紀中期證據法的形成多少與刑事審判中的律師化機制登場存在聯系,因此,我的觀點是,證據法真正的歷史上的活動由陪審團控制并不多于由律師控制”。[27]P306正是因為律師控制的口頭審判方式與證人分類、排除傳聞、舉證責任、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沉默權、不被迫自證其罪等證據法或者程序法原則密切相關。這個觀點也得到了達馬斯卡的贊同。因此,對抗制與英美的證據法具有最為緊密的聯系,對抗制一旦崩潰,英美的證據法也就完全失去了存在的空間。
六、結論
綜上可見,對證據法程序支柱的考察既意圖追根溯源地解釋過去,又意圖有根有據地預測未來。通過對英美法系證據法的程序支柱相互關系的考察,大體可見,英美法系證據法主要是在陪審團審判和對抗式審判之中有其用武之地,這兩種程序上的特別之處決定了證據法的特別之處,由此,可能會影響到所謂的英美證據法排除規則的普適性,將之移植到訴訟制度文化與之不同的國家可能會造成水土不服。對證據法的支柱的不同歸因,如所謂的陪審團、宣誓、對抗式、集中式、成本、裁決可接受性等整體而言可能對證據法產生這樣的影響,一部分是關注證人資格、證據真假的注重證據客觀性防止法庭受到偽證和捏造證據影響的傳統證據法,另一部分關注訴訟主體在庭審之中以口頭證據為基礎的證據提出、交叉詢問以及意見表達的現代證據法。證據法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型主要有這樣一些體現:從限制權利注重后果責任轉向保障權利注重程序參與,從信任知情的事實裁決者和事實的主動調查的情境裁量轉向懷疑法官以及懷疑陪審團而設置一系列預防法官受偏見信息干擾的程序機制、從自然理性和人為理性的事實認知方式相互獨立分離轉向以職業法官依排除規則審查證據資格和非職業法官自由裁量證據證明力等權力分工合作。當下,隨著訴訟模式的多元化以及訴訟程序的科學化,證據法的程序支柱自身也不斷變化,當然,受程序規則影響的證據法也隨之變革。但是,總體而言,不論何種證據法,不論何種事實認定模式,都必然逐步體現出限制公權力濫用以及保障人權的制度設置,盡管真相不是可有可無的。結合當下的中國實際而言,有必要注意以下兩點:
第一,當下我國刑事訴訟法以審判為中心的改革取向必然對證據法的發展起到一定的沖擊作用,突出的變化是意圖讓卷宗筆錄確認程序逐步轉變為以交叉詢問為主體的口頭審理程序,而這種“從分段式審理到集中式審理”的提倡已經與傳統的集中式審理在案件事實認定思維模式上有著巨大的差別,更加突出法律職業精英對程序技術的操控,因此,一方面要法律職業群體自身的素質能夠適應庭審中心的要求,另一方面為防止專業壟斷所引發的技術支配和權力濫用反而要通過重構法庭組織而引入普通民眾的自然化認識。
第二,與之相同步的是刑事速裁程序的試點和推廣,這以被告人認罪為前提的程序多元化探索完全抽離了訴訟的對抗精神,由此證據法也從傳統的注重對證據資格的審查轉為法院對被告人認諾的明知性和明智性的審查,訴訟主體多方合意下裁判的可接受性在追求效率的過程之中大有超越“對抗求證”的傳統意味。當然,速裁案件更大的特點是真相先于裁決而不是通過裁決來決定真相,因此,“集中審理”更突出體現為一種當庭裁判,并且控訴方和審判方也有一種集約化組織方式行使職權,在所謂的“簡程序而不減權利”的口號下,律師不是以辯護人而是以提供法律咨詢意見的值班律師來參與程序,并且律師的參與在庭審程序之外而不是參與到庭審程序之中。
[1][6][7][8][12][18][25][26][美]達馬斯卡.漂移的證據法[M].李學軍,劉曉丹,姚永吉,劉為軍譯. 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
[2]Richard D. Friedman,. Anchors and Flotsam: Is Evidence Law "Adrift"? Evidence Law Adrift by Mirjan R. Dama?ka[J]. The Yale Law Journal, Vol. 107, 1998, (6).
[3]湯維建.達馬斯卡證據法思想初探——讀達馬斯卡《漂移的證據法》[J].甘肅政法學院學報,2005,(3).
[4]Park.An outsiders's view of Common Law Evidence[J].Vol.96 Mich. L. Rev.1998,(6).
[5][15][英]薩達卡特·卡德里.審判的歷史:從蘇格拉底到辛普森[M].臺北:商周出版,2007.
[9]Colin Tapper. Cross & Tapper on Evidence (12 edition)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10][27]Langbein. The Criminal Trial before the Lawyers[J]. Vol.45, U.Chi.L.Rev. 1978, (2).
[11]Charles Nesson. The Evidence or the Event? On Judicial Proof and the Acceptability of Verdicts[J]. Vol.98, HARV. L. REV,1985,(7).
[13][16][17]湯維建.達馬斯卡證據法思想初探——讀達馬斯卡《漂移的證據法》[J].甘肅政法學院學報,2005,(3).
[14]何家弘.西方證據法的歷史沿革 (代序),載何家弘,張衛平主編.外國證據法選譯[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
[19]James Bradley Thayer. A Preliminary Treatise on Evidence at the Common Law[M].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Elibron Classics edition, 1898.
[20]Edmund M. Morgan. The Jury and the Exclusionary Rules of Evidence[J]. Vol. 4 U. CHI. L. REV,1937,(2).
[21]張衛平主編.外國民事證據制度研究[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
[22]Dale A. Nance. The Best Evidence Principle[J]. Vol. 73 IOWA L. REV,1988.
[23]吳洪淇.英美證據法的程序性解構—以陪審團和對抗制為主線[J].證據科學,2012,(5).
[24]John H. Langbein, Historical Foundations of the Law of Evidence:A view from the Ryder sources[J].Vol. 96, Columbia Law Review, 1996,(5).
責任編輯:楊正萬
Dama?ka’sEvidenceLawAdrift:MutualRelationshipbetweenThreeProceduralPillars
LU Erqi
In the book “Evidence Law Adrift”, Dama?ka proposes “three pillars for British and American evidence law mansion”, namely trial court, concentrated procedures and opposition system. It is argued that we should examine their mutual impact and suppor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ir independence, fullness, relevance and layers, and to further know the change of responding procedures and the future of evidence law.
Dama?ka; procedural pillar; common law evidence; mutual relationship
D915.3
A
1003-6644(2016)01-0176-09
* 2014年度福建省社會科學規劃一般項目“刑事訴訟的律師化研究”[項目編號:2014B235];福建省法學會2015年度法學研究重點課題“特洛伊木馬:品格證據的價值檢視與制度構建”[編號:FLS(2015)A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