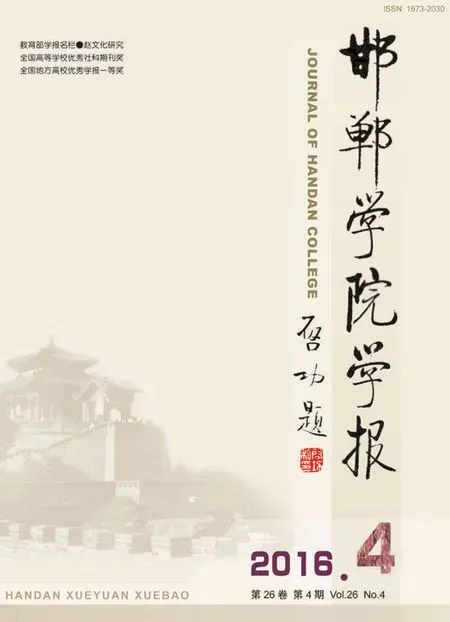在禮與法之間:荀子的制度之思
林桂榛
(曲阜師范大學 哲學系,山東 日照 276826)
在禮與法之間:荀子的制度之思
林桂榛
(曲阜師范大學 哲學系,山東 日照 276826)
荀子“不求知天”而求“治道”,求“治”必須本乎人性人情。探人性可玄,言人情總實,荀子主張“天情”論下“擾情——養情”。荀子思想有一個“由禮到法的發展”,學說上是“由禮到法的橋梁”。于禮法關系,荀子謂禮法相通而禮高于法,或謂禮法并用而法強于禮,或謂禮法分用而各有側重。“灋”(法)從“”(獬豸)即與判斷是非曲直之事相關,從“氵”則表標準義(如準從氵),故“灋” 本義即是非標準義。《說文》“灋,刑也”及《論語》“君子懷刑”等刑本作?,從井之“?”是秩序與條理義,與“法”的標準義相關。荀子重視治道,重視治理效率,故主張沿禮而張法。但荀子也重視法治正義與法治藝術。荀子是先秦最精通治道或法治的一位儒家,是一位真正最具有現代意義的曠世大儒。
荀子; 治道; 禮; 灋(法); ?(刑); 標準; 正義
孟荀論“天道——人性”有很大的差異,但其各自的“天道——人性”論是貫通一體的。荀子人性論與天道論一體,并且是相提并論的,但這種貫通或一體并不是思孟或后來宋代道學、明代心學的貫通,而是天文學與實證人性論的貫通,是洞察天人生態一體及如何具體一體生息運行機制的貫通。而為了擺脫形而上學性的本源或本原論思維的人性論尤其是性善論等,荀子不僅嚴謹地探討了“性”范疇及人性的血氣心知真相,而且努力將人性論導向不具有任何形而上學并且是具體可知、人人可證可驗的人情論。荀子由“人性”論推進到“人情”論(人性可抽象,但人情抽象不了),荀子將人性人情貫通又將人性人情貫通于“天”,并在人性人情論下論治世之道,如此開啟了德性及制度并思的思想方向。
一、“天情——擾情——養情”
《荀子·正名》曰:“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又曰:“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情然而心為之擇謂之慮,心慮而能為之動謂之偽,慮積焉能習焉而后成謂之偽。”①“慮積焉能習焉而后成謂之偽”之“偽”本作“僞”,人為、行為義;而“心慮而能為之動謂之偽”之“偽”則當如楚簡本作“”,可隸作“//”等形,乃心為、思動之義。、僞二字有語義差異,或也可通用。包山楚簡、郭店楚簡、上博楚簡等皆有從“心”之“”字,明梅膺祚《字匯》有“”字。——詳見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932頁。這就明確界定了“性——情——欲”三大概念,此正如荀子后裔荀悅所謂“凡情意心志者,皆性動之別名也”(《申鑒·雜言下》)。
《天論》篇由天到人,由天文學天道論講到“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臧焉,夫是之謂天情”,而“情”是意識的,心理的,是“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或“好惡喜怒哀樂臧焉夫是之謂天情”。荀子的人性論與孟子同樣講心理的內容,但孟子是將屬于后天德性范疇的仁義禮智等(當然孟子不認為是后天的)予以配“天”而言,并謂之“五行”;荀子卻是將“好惡喜怒哀樂”作為情的內容,并將情配“天”而言曰“天情”。
“性”字從“忄”從“生”,就人而言,“生”在血氣肉身,“心”在情感意識,而情感又尤其以好惡為多,故荀子提出“擾情—養情”問題——不合理的情予以擾之,合理的情予以養之,故言“情”無限無節趨勢下的性樸之人性教化與管制的問題:
(1)人之性不善,其善者偽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于爭奪,合于犯分亂理,而歸于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后出于辭讓,合于文理,而歸于治。……故枸木必將待檃栝、烝矯然后直;鈍金必將待礱厲然后利;今人之性不善,必將待師法然后正,得禮義然后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古者圣王以人性不善,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為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始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荀子·性惡》)
(2)禮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于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芻豢稻梁,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苾,所以養鼻也;雕琢刻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鐘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養耳也;疏房檖貌,越席床笫幾筵,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孰知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知夫出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荀子·禮論》)
《荀子》全書“性”字凡119見,而“情”凡118見,而且“情實”、“情感”兩義并存且多“情感”之“情”的用法,此其大異孔子、孟子理論之處。到了荀子弟子韓非子所作的《韓非子》一書中,“性”凡是18見,“情”則凡75見;《管子》“性”凡18見,“情”76見。在《荀子》及有類似思想的先秦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大量談人情人欲的文字,但不就“養情”而論,而單獨就“矯情”、“擾情”或“情性”之矯擾而言,一般法家強調人君或國主因循人情而用賞罰操控人民以實現國家功利,而儒家代表之荀子則強調尊重人情事實或禮俗等而約束人,與一般法家表面有相同處,實又大有不同。
用什么來操控人民?法家如此說法及法治:
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君執柄以處勢,故令行禁止。柄者,殺生之制也;勢者,勝眾之資也。廢置無度則權瀆,賞罰下共則威分。是以明主不懷愛而聽,不留說而計。故聽言不參則權分乎奸,智力不用則君窮乎臣。故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故賞賢罰暴,舉善之至者也;賞暴罰賢,舉惡之至者也;是謂賞同罰異。賞莫如厚,使民利之;譽莫如美,使民榮之;誅莫如重,使民畏之;毀莫如惡,使民恥之。然后一行其法,禁誅于私。家不害功罪,賞罰必知之,知之道盡矣。(《韓非子·八經》)
法家法論或法治論的人性論基礎是民之好惡之情的事實(歸納性的規律或人之道),也即其人性論基礎是趨利避害的自然人情論。在這一點上,法家和荀子是有共識的,這也意味著他們在社會治理的效率上有共識,強調因順人情而務實管制。章太炎《檢論》曰:“禮者法度之通名,大別則官制、刑法、儀式是也。”[1]526正因古時之禮多數具有法一樣的規范約束性,故言“我愛其禮”的孔子從未否定禮的約束性功用,也未否定禮蘊藏法及法治的事實性內涵(西方謂習俗禮屬自然法)。《左傳·文公六年》曰:“……為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眾隸賴之,而后即命,圣王同之。”孔子說:“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禮記·仲尼燕居》)“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就約束功能而言,禮樂刑政皆類法,故曰“法者,禮樂刑政是也”(《瓊琚佩語·政術》)、“法制禮樂者,治之具也”(《文子·上義》)。孔子關注禮治或重視禮法性管制(管治)的必要性及適當方式,這一點由戰國大儒荀子發揚光大了。
二、“由禮到法的發展—由禮到法的橋梁”
《荀子》全書出現“法”字約183次,出現“禮”約343次,出現“禮法”4次,出現“師法”10次,其中名詞“禮法”內涵比較豐富,而名詞“師法”即“教化(引導)”與“管治(強制)”之旨。荀子如此重視“禮”以及大談“法”甚至深談“禮法”,跟荀子注重世俗社會的治理有密切關聯,故《荀子》出現“治”字253次(出現“理”字 106次),比“法”字還多。孟子重視德性與天道,故以“善”言天與性;荀子重視人性與人道,故以“治”言性與人世。
《性惡》曰:“凡古今天下之所謂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謂惡者,偏險悖亂也:是善惡之分也矣。”《性惡》曰:“……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于爭奪、合于犯分亂理而歸于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后出于辭讓、合于文理而歸于治。”管分、治道之樞要、樞機在君、在義、在禮法,故《性惡》曰:“為之立君上之勢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是圣王之治而禮義之化也。”《性惡》又曰:“古者圣王以人性不善(“不善”原作“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為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始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所以,孟子的哲學思想精粹是求“天”或“天道”(倫理天道而已),是“盡心盡性”;而荀子則是“不求知天”,求“治”或“治道”,故求“為之起禮義、制法度”。
何謂“禮”?荀子認為禮是民俗,禮是制度,禮是標準,禮是儀式,禮是道理,總而言之禮是規矩及治具,故《荀子》曰:“繩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規矩者,方圓之至;禮者,人道之極也。”(《禮論》)“禮者,治辨之極也,強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議兵》)“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勸學》)“禮者,眾人法而不知,圣人法而知之。”(《法行》)“禮者,政之挽也;為政不以禮,政不行矣。”(《大略》)“禮者,人主之所以為群臣寸尺尋丈檢式也。”(《儒效》)“若夫斷之繼之,博之淺之,益之損之,類之盡之,盛之美之,使本末終始,莫不順比,足以為萬世則,則是禮也。”(《禮論》)“程者,物之準也;禮者,節之準也;程以立數,禮以定倫。”(《致士》)“禮者,人之所履也,失所履必顛蹶陷溺;所失微而其為亂大者,禮也。”(《大略》)“水行者表深,使人無陷;治民者表亂,使人無失,禮者,其表也。”(《大略》)“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則陷。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則亂。禮者,表也。”(《天論》)“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論》)“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修身》)“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富國》)“故禮者,養也。”(《禮論》)“恭敬,禮也;調和,樂也。”(《臣道》)“禮者,謹于治生死者也。”(《禮論》)“禮者,謹于吉兇不相厭者也。”(《禮論》)“禮者,以財物為用,以貴賤為文,以多少為異,以隆殺為要。”(《禮論》)“禮者,斷長續短,損有余,益不足,達愛敬之文,而滋成行義之美者也。”(《禮論》)
《荀子·禮論》曰:“禮之理誠深矣。”禮字本寫作禮,小篆寫作“”,《說文》曰:“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從示,從豊,豊亦聲。”禮來自豊加“示(礻)”而得,豊()乃豆器上盛物祭祀之狀,一般認為所盛是玉串,玉是當時最珍貴及最有代表性的禮物,故孔子、荀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故《禮記·禮運》曰:“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荀子·禮論》曰:“禮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是禮之所起也。”《王制》曰:“勢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則必爭;爭則必亂,亂則窮矣。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王制》又曰:“人生不能無群,群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故宮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頃舍禮義之謂也。能以事親謂之孝,能以事兄謂之弟,能以事上謂之順,能以使下謂之君。”《君道》曰:“請問為人君?曰:以禮分施,均遍[徧]而不偏……古者先王審禮以方皇周浹于天下,動無不當也……夫是之謂圣人,審之禮也。”《富國》曰:“離居不相待則窮,群居而無分則爭;窮者患也,爭者禍也,救患除禍,則莫若明分使群矣。”《富國》又曰:“人之生不能無群,群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故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也。”《王霸》曰:“故君人者,立隆政本朝而當,所使要百事者誠仁人也……立隆正本朝而不當,所使要百事者非仁人也……是人君者之樞機也。”
《荀子》不僅繼續講禮,而且由禮脫胎而出倡導法,這就是荀子的“隆禮至法”論。荀子屢云“隆禮至法則國有常,尚賢使能則民知方”(《君道》)“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議兵》)“法后王而一制度,隆禮義而殺詩書”(《儒效》)“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強國》)等。而由禮進法、以法治世,這其實是孔子“謹權量、審法度”(《論語·堯曰》)及“禮有因革損益”(《論語·為政》)的禮法觀,是荀子“與時遷徙、與世偃仰”(《非相》)的明智立場,也是韓非“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韓非子·五蠹》)及商君“變法以治、更禮以教”(《商君書·更法》)的政治智慧。《大戴禮記·禮察》曰:“禮者禁于將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正是基于極端講究治理效率或效應的單一立場,先秦法家對當時虛浮之儒偏崇禮樂及一味期望德性持一種否定立場;也正是基于治理效應考慮,先秦法家力倡以法治世、以法治國。
培養了李斯、韓非且其實很重視教養、很重視禮樂(《荀子》前四篇即《勸學》《修身》《不茍》《榮辱》,滿書講禮樂、禮義、仁義)的荀子很清楚:禮樂教養是有益人格臻良及社會臻治,但禮樂教養畢竟不是剛性的、標準的、強制的、政府組織的,于一個日益龐大而復雜的社會,于一個巫神日益褪去恐敬之權威而人民日益多識及自主的時代,宗教拜祀與世俗禮俗混雜(本同源)的“禮”其直接的治世效率是日益下降或局部的,這實是無可阻擋的人類歷史大趨勢①古希臘哲人也重視法,亞里士多德說:“如果一個青年人不是在正確的法律下成長的話,很難把他培養成一個道德高尚的人。因為,節制和艱苦的生活是不為多數人所喜歡的,特別是青年人。所以要在法律的約束下哺育,在變成習慣之后,就不再痛苦了。……多數人寧愿服從強制,也不服從道理,接受懲罰而不接受贊揚……對于那些天性卑劣的人,要用懲罰使他們服從。而對于那些不可救藥的惡棍,就要完全趕了出去。……法律,作為一個出于思考和理智的原理,具有強制性的力量。……顯然,對德性的共同關心要通過法律才能出現。有了好的立法才能有好的法律。法律不論是成文的還是不成文的并沒有什么區別。”(《亞里士多德全集》第八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33-234頁),故法家代表作《管子》曰:“人故相憎也,人之心悍,故為之法。法出于禮,禮出于治。治禮,道也,萬物待治禮而后定。”(《管子·樞言》)
陳柱說:“簡括言之:法家蓋起于禮,正猶學校之內,先有種種應守之規則,而后乃有賞罰之規則也。禮不足治,而后有法,禮流而為法,故禮家流而為法家,故荀卿之門人李斯、韓非皆流而為法家也。”[2]95熊偉《從先秦學術思想變遷大勢觀測老子的年代》一文援引錢穆講演見解而說:“法家乃是從儒家出來的。儒家在初時只講禮。只講政治活動,到后來曾子等人卻退化來將儀文小節。但傳到魏國去的一派,卻依然從事政治活動,遂把儒家原來的宗旨發揚廣大。通常總認曾子孟子一派為后來儒家的正宗;其實就儒家的本旨論,法家毋寧算是儒家的正宗,曾子孟子等在魯國的一支反而是別派。古代貴族的禮一變成了儒家的士禮,再變成了墨家的墨禮,三變便成了法家的法。”②錢穆:《老子辨》附錄,大華書局1935年版,第110頁;又見《古史辨》第六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86頁。
杜國庠(即杜守素)說:“荀卿和他的學生韓非,都是戰國末葉綜合以前學術的大學者。雖然荀子是儒者,韓非是法家,他們學派不同;但他們生在同一時代,又有師生的關系,自然思想上可能有共通的地方。可是,還不僅此。他們的思想的遞嬗,實有內在的必然的聯系。我們在荀子的思想中,就可看出由禮到法的發展的痕跡。這是歷史發展的反映。所以韓非雖事荀卿傳其學(一方面),卻一轉而為法家的集大成者,不是偶然的。”③杜守素:《先秦諸子批判》,作家書局1948年版,第138頁;杜國庠:《先秦諸子的若干研究》,三聯書店(北京)1955年版,第126頁。侯外廬等雖不懂荀子與孔子自然天道觀的一脈相承性,但也說到禮到法的發展問題:“一般說來,荀子的禮的思想,源于儒家的孔子,然而他的天道觀和所處的時代不同于孔子,因而他的禮論,也就變成了由禮到法的橋梁。”[3]575
毛子水說:“《論語》記孔子曰:‘君子懷刑。’(榛按:此“刑”實本作“?”,從井刂不從開刂)孔安國解釋道:‘安于法也。’所謂‘安于法’,就是‘守法’的意思……儒者雖然主張以禮義治天下,但是亦很尊重法律的。實在說,儒家所謂禮,便已包括了法;所謂義,便是守法。(后世法成一家,禮和法乃別。)我們知道禮義在儒家教育中的地位,我們便可推測我國古圣賢怎樣看重法這件事情了。”④毛子水:《子水文存》,文星書店1963年版,第162頁。——毛子水又說:“一個國家里守法的精神,好像應自政府中人先作榜樣……守法當然是國民全體——男女老幼——的義務;但我以為守法的習慣,須從青年時代養成……我們國家將來的命運,全寄在青年人身上。我們國家若不能漸漸走上法治的軌道,則我們國家恐怕便沒有一個光明的將來;我們青年人若不從現在便養成守法的習慣,則我們國家恐怕走不上法治的軌道。”(《子水文存》,第162-164頁)
林語堂《孔子的智慧》也說:“若只將禮字做禮儀或典禮講,就大為錯誤了。”[4]31“‘禮’這個字,也可以說是一種社會秩序原理,以及社會上一般的習俗……禮是包括民俗、宗教風俗規矩、節慶、法律、服飾、飲食居住,也可以說是‘人類學’一詞的內涵。在這些原始存在的習俗上,再加以理性化的社會秩序之中的含義,對‘禮’字全部的意義就把握住了。”[4]145-146“顯而易見‘禮’之含義包括了社會秩序、社會規范、典禮儀式的社會傳統……儒家‘禮’字的中心觀念的含義可作以下解釋:作宗教解;作社會秩序原則解(其中包括宗教);作理性化的封建秩序解;作社會、道德、宗教習俗的整體解(一如孔子以之教人,一如孔子之予以理性化)。”[4]131-132
《莊子·徐無鬼》曰:“法律之士廣治。”《論衡·非韓》曰:“夫韓子所尚者,法度也。”《論衡·謝端》曰:“法律之家,亦為儒生。”可謂至論。《荀子·勸學》曰:“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戰國時的荀子重視法、禮法、禮義并經常將“禮”切換到“法”上,這是有確切而深刻的社會原由的,也是有儒家深刻思想淵源的,荀子的法論并非空穴來風,更非橫空出世。《荀子》全書內里“禮——法”連說或并稱、對說者甚多,大體有三種情況:
(1)說禮法相通且禮高于法,如“禮者,法之大分,(群)類之綱紀也”(《勸學》)、“故非禮,是無法也;非師,是無師也……故學也者,禮法也”(《修身》)、“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禮,禮莫大于圣王……文久而滅,節族久而絕,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褫”(《非相》)、“隆禮至法則國有常,尚賢使能則民知方”(《君道》)、“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人君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強國》,又見《天論》《大略》,文字略異)、“……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禮法之大分也……是百王之所同,而禮法之大分也”(《王霸》)、“是百王之所以同也,而禮法之樞要也”(《王霸》)。
(2)說禮法并用且法強于禮,如“故為之立君上之勢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性惡》)、“圣人積思慮,習偽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性惡》)、“故圣人化性而起偽,偽起而生禮義,禮義生而制法度”(《性惡》)、“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后出于辭讓,合于文理,而歸于治”(《性惡》)、“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而應之,無所儗作;張法而度之,則晻然若合符節——是大儒者也”(《儒效》)。
(3)說禮法分用而各有側重,如“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眾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富國》)、“其耕者樂田,其戰士安難,其百吏好法,其朝廷隆禮,其卿相調議,是治國已”(《富國》)、“志意定乎內,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儒效》)、“必將修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民”(《富國》)等。
荀子強調本乎禮而起法及圣賢來制法,以保障法的正義性、合理性。《荀子·解蔽》曾批評先秦法家慎子是“蔽于法而不知賢”,此是就慎子知“法”而不知“賢人”或“賢德”而言,也是就慎子不重“禮”、“師”而言。因為荀子或儒家認為禮義甚至好的法律,都是出自眾民中先覺的圣賢、圣王代民而立、為民而立。《荀子·非相》曰:“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禮,禮莫大于圣王。”《荀子·法行》曰:“公輸不能加于繩墨,圣人不能加于禮。禮者,眾人法而不知,圣人法而知之。”《荀子·性惡》曰:“凡禮義者,是生于圣人之偽……圣人積思慮,習偽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禮義生而制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
《荀子·王霸》曰“政令制度,所以接天下之人百姓”,又曰“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圣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曰以禮以分“是百王之所以同也,而禮法之樞要也”、“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均平,莫不治辨[徧],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禮法之大分也”。《荀子·解蔽》曰:“圣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兩盡者,足以為天下極矣。故學者以圣王為師,案以圣王之制為法,法其法以求其統類、以務象效其人。”《荀子·大略》《荀子·天論》曰:“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荀子·強國》曰:“人君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此正如《管子·侈靡》所謂“禮義者,人君之神也”、“法制度量,王者典器也”。
《荀子·禮論》曰“禮之理誠深矣……禮者人道之極也”,《荀子·勸學》曰“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禮”本來就是自然法、習慣法,“法”是“禮”的延伸,正義之“法”當合符“禮”;“禮”則反映道理的“理”,反映道義的“義”,《荀子·樂論》《禮記·樂記》曰“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禮記·禮運》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法若協諸義,則也是“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這就是禮與法的因革損益問題。
荀子強調法及法義的重要性,也強調立法、執法者素質、能力尤其政府人員素質、能力的重要性,主張知“法”且知“賢”,故《荀子·王制》說完“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聽之盡也”后就接著說:“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這無疑是強調正義而高效地運用法律、行使管理對于有效維護良好社會秩序的重要性,而運用法律或行使管理在“君”或政府,故《荀子·君道》又說:“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遍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后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荀子·富國》曰:“人之生不能無群,群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故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也。”《荀子·大略》曰:“言治者予三王,三王既以定法度、制禮樂而傳之……無三王之法,天下不待亡,國不待死。”此即賢者制法且以法行治。《荀子·富國》曰“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眾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
荀子強調法或司法的是有原則有標準的靈活運用。《荀子·君道》“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之“類”即《荀子·勸學》“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之“類”,“法—類”對說必近義,故《勸學》該句唐楊倞注曰:“禮所以為典法之大分、統類之綱紀,類謂禮法所無、觸類而長者,猶律條之比附。《方言》云齊謂法為類也。”《說文》曰“類,種類相似,唯犬為甚。”楊雄《方言·第十三》曰:“類,法也。”《方言·第七》曰:“肖、類,法也。齊曰類,西楚梁益之間曰肖。秦晉之西鄙自冀隴而西使犬曰哨,西南梁益之間凡言相類者亦謂之肖。”《荀子·君道》“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即《孟子·離婁上》“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之義①關于“徒法不能以自行”,詳見林桂榛:《“徒法不能以自行”究竟何意——兼與張岱年、郭道暉等先生商榷》,《華中科技大學學報》2002年第 6期;《“徒法不能以自行”真的究竟何意——就孟子原意駁王心竹博士〈“徒法不能以自行”到底何意〉一文》,《華中科技大學學報》2004年第2期。該兩文收入林桂榛《“親親相隱”問題研究及其他》一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即法需人尤賢人來推行,故《史記·太史公自序》曰“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
古羅馬法學家說:“法學是關于神與人的事務的知識,是關于正義與非正義的學問(scientia)。”又說:“法是善良與公正的藝術。”[5]《荀子·大略》曰:“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以其本知其末,以其左知其右,凡百事異理而相守也。慶賞刑罰,通類而后應;政教習俗,相順而后行。”《荀子·王制》又曰:“故公平者,聽之衡也;中和者,聽之繩也。其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聽之盡也。偏黨而不經,聽之辟也。”荀子說的是聽訟斷獄之合理、公正、靈活、周到的問題,這當然既是司法,也是藝術——正義或實現正義的藝術。
三、作為是非標準的“法(灋)—刑(?)”
如《周禮·冬官考工記》曰:“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懸],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又曰:“匠人建國,水地以縣[懸]。置槷以縣,視以景[影]。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懸是懸物取垂直于大地,水是水衡取平準于水面,測日影或建房屋以“懸—水”取直角來校正垂直或平衡是自古以來的方法。“衡”就是“平”的狀態及意思,故詞曰“平衡”;平則是效法水之平,故詞曰“水平”。故《荀子·禮論》曰“衡者,平之至”,《史記·禮書》曰“衡者,平之至也”,《論衡》曰“論衡者,論之平也”、“故論衡者,所以銓輕重之言、立真偽之平”。“公平”概念本是“公”之平,“水平”概念本是“水”之平,“公平”、“水平”都是公允、高低與否上的“平”即“準”、“標準”。
《漢書·律歷志》曰:“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準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繩者,上下端直,經緯四通也。”《說文》段注曰:“天下莫平于水,水平謂之準,因之制平物之器亦謂之準。”清桂馥《札樸》曰“木工一目衺(邪)視謂之準”,《釋名》曰“水,準也,準平物也”,《經典釋文》引《周易》鄭注曰“準,中也,平也”,古代還有校音性質的樂器稱“準”。“標準”之“準”從“凖”省,“凖”又本作“準”,如“法”[灋]一樣從“氵”;古有“平準”概念,亦有平準令、平準官,《史記》有《平準書》,“平—準(準)”二字其義一也。故《淮南子·時則訓》曰:“繩者,所以繩萬物也;準者,所以準萬物也;規者,所以員萬物也;衡者,所以平萬物也;矩者,所以方萬物也;權者,所以權萬物也。……準之以為度也,平而不險,均而不阿,廣大以容,寬裕以和,柔而不剛,銳而不挫,流而不滯,易而不穢,發通而有紀,周密而不泄,準平而不失,萬物皆平,民無險謀,怨惡不生,是故上帝以為物平。”
“夫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規矩繩墨也。夫矩不正,不可以求方。繩不信,不可以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管子·七臣七主》)“灋”字從“”又從“氵”表示是非曲直的標準之義,此與“法”的別字“佱”的含義很是相近或相關①有關法的范疇,《說文》曰:“笵,法也。”“式,法也。”“模,法也。”“規,有法度也。”“型,鑄器之法也。”“劾,法有辠也。”“镕,冶器法也。”“辠,犯法也。”“辟,法也。從卩,從辛,節制其辠也;從口,用法者也。”《爾雅》曰:“憲憲泄泄,制法則也。”《釋名》:“五典,典,鎮也,制法所以鎮定上下,其等有五也。”《方言》:“肖、類,法也。齊曰類,西楚梁益之間曰肖。”。《玉篇》曰:“佱,古文法。”《說文·亼部》曰:“亼,三合也。從入一,象三合之形。凡亼之屬皆從亼。讀若集。”望文生義地去理解,“佱”字或即表示“正”的匯集即“正義”的匯集,或表示匯集正或正義,此如同“灋”跟是非曲直及是非曲直的標準有關。“佱”字又寫作“峜”,如《管子·輕重戊》曰“虙戲作造六峜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逸周書·糴匡解》曰“企不滿壑,刑罰不修”之“企”字一般認為是“峜”字即“佱”字,清朱右曾《逸周書集訓校釋》注曰:“佱,古文法字。”郭沫若等《管子集校》引清洪頤煊曰:“佱,古文法字。”清王念孫《讀書雜志·漢書第十三》亦曰“佱,古文法字”,并曰小篆“佱”訛形為“定”并引《周書·大誥》“爾時罔敢易法”證之。
《論語》“君子懷刑”、“齊之以刑”、“刑罰不中”及《樂記》“禮樂刑政”之刑本作?,?者法也,?即法則之義,與“法(灋)同義。《說文》“灋,刑也”之“刑”,也本當從井作“”[?]。《說文》曰:“?,罰辠也。從井,從刀。《易》曰:井,法也。井亦聲。”古人曾謂“”造字來源于武士執刀護井,如《初學記》卷二十曰:“《春秋·元命苞》曰者侀也,《說文》曰刀守井也。飲之人入井陷于川,刀守之,割其情也。罔言為詈,刀守詈為罰……井飲人,則人樂之不已,則自陷于川,故加刀謂之,欲人畏懼以全命也。詈以刀守之,則不動矣,今作罰,用寸。”馬端臨《文獻通考》卷十二曰:“昔黃帝始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是以情性可得而親,生產可得而均,均則欺凌之路塞,親則斗訟之心弭。”
今有詞語曰“井井有條”,此“井井”即源于“井”字的條理、法則義。《荀子·儒效》曰“井井兮其有理也”,《越絕書·外傳記地傳》曰“禹井,井者法也”,《周易·井卦》曰“往來井井”,此等皆可印證“”字讀井韻及表法則與秩序。《說文》曰“刑,剄也”、“剄,刑也”,刑≠,刑是刑殺、刑戮義,是法則義;然“刑—”音同形近,故又多通用或假借。《爾雅》曰:“典,彝,法,則,(刑),范,矩,庸,恒,律,戛,職,秩,常也;柯,憲,(刑),范,辟,律,矩,則,法也。”此即以“常”、“法”釋“”,《爾雅》“,法也”亦多被引用。=法=灋,灋字如前所述乃從直(辨是非)從準(有標準)之義;作為圣賢之制或理想的社會構造,與法即正義的標準或標準的正義。
《荀子·禮論》曰:“禮之理誠深矣……故繩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規矩者,方圓之至;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禮之中焉能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者焉,斯圣人矣。”這是將“禮”作為社會規則、秩序的標準,此類法家強調以“法”作為社會規則、秩序的標準。故《荀子》曰:“君子治治,非治亂也。曷謂邪?曰:禮義之謂治,非禮義之謂亂也。故君子者,治禮義者也,非治非禮義者也。”(《不茍》)
《慎子》有逸文曰:“有權衡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長短;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詐偽。”《韓非子·難三》則曰:“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韓非子·定法》曰:“法者,憲令著于官府,刑罰必于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韓非子·定法》曰:“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絀羨齊非,一民之軌,莫如法。”——這正是“法”的標準意義或標準角色。《荀子·大略》“禮者,其表也”、《荀子·天論》“禮者,表也”、《荀子·致士》“禮者,節之準也”,此“表”即圭表、標尺,此“準”即標準,故荀子的禮類法、法本禮,故《荀子·儒效》曰“禮者,人主之所以為群臣寸尺尋丈檢式也”,《荀子·修身》則曰“故非禮,是無法也”、“故學也者,禮法也”。
四、荀子重視治道及法治效率、法治正義
荀子曰:“土之與人也,道之與法也者,國家之本作也。君子也者,道法之摠要也,不可少頃曠也。得之則治,失之則亂;得之則安,失之則危;得之則存,失之則亡。”(《致士》)基本于人情論或人情事實,基于“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禮論》)的事實,基于“人之生不能無群,群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富國》)的事實,故荀子主張教化與管制,主張禮樂與刑政。嚴復1896年《原強修訂稿》曰:“故學問之事,以群學為要歸,唯群學明而后知治亂盛衰之故而能有修齊治平之功。嗚呼,此真大人之學矣!”[6]18《譯群學肄言序》又曰:“群學者,將以明治亂盛衰之由,而于(正德、利用、厚生)三者之事操其本耳。”[6]123欲修齊治平則當明荀子說“師法之化、禮義之道”及“為之起禮義、制法度”等(《性惡》),而明乎“禮樂性?政四達而不悖”就是明乎荀子發明的“群治”論,斯乃通往王道之路。
荀子主張“禮法”,而韓非子則只主張“法”,這可見荀子理論是向法過渡。但說法家來自荀子則荒謬不已,因法家的源頭是刑制,商周就有用刑的傳統及用刑的思想,故《漢書·藝文志》說:“法家者流,蓋出于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另外,韓非等法家與荀子是完全不同的,要義不在重法還是重禮的問題,而是法的目的何在或法是否正義及合理的問題。韓非子的“法”是君主之術,是牧民統治,為了管理效率,他主張實行純粹的君國法治,而將荀子的“法義”、“義法”遠遠拋棄,將儒家“禮”作為法所具有的自然法即民俗民德之正義遠遠拋棄。法家之所以能成為獨裁者的“智謀者”或法家的法之所以成為獨裁者的“機器”,無非法家主張常常(非所有法家)背離法及法治的民意正義性,從而將法與政治推向單向鉗制人民的工具,由此法及法家往往成為“暴政”的輔弼。
但在先秦時代,儒家并非集體走向了道德幻想主義或玄思心性之救世幼稚病,或走向了法家式為君主專權獨治而鼓噪“勢——術——法”的犬儒法學,因為先秦儒學集大成者荀子已經在“性者本始材樸也”的人性命題下開朗而光明地標舉了禮法并舉、教化與管制(管治)并舉的思想大格局(力倡勸學修身等又頻言師法、君師、禮法、禮義),也標舉了將“君主”倫理切換到“民主”倫理以及推崇“法義”或“義法”的思想大格局。《荀子·大略》曰:“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故古者裂地建國非以貴諸侯而已,列官職差爵祿非以尊大夫而已。”這是“君主”轉換到“民主”的支點,也是法治轉換的支點。荀子的法或法治并非是商韓“君主本位”的工具性法治論,而是“民主本位”的正義性法治論,故《荀子》明確說“法義”與“義法”,反復強調“禮義法度”及“仁義法正”,強調“之所以為布陳于國家刑法者則舉義法”(《王霸》)、“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雖博臨事必亂”(《君道》),這是荀子講“君”與“法”的最可貴之處。
《荀子·非相》有曰:“夫妄人曰:‘古今異情,其所以治亂者異道。’而眾人惑焉……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類度類,以說度功,以道觀盡,古今一也。類不悖,雖久同理。”《荀子·君道》曰:“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遍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后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荀子·大略》又曰:“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以其本知其末,以其左知其右,凡百事異理而相守也。慶賞刑罰,通類而后應;政教習俗,相順而后行。”《荀子·成相》曰:“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修百姓寧。明德慎罰,國家既治四海平。”《荀子·富國》曰:“故明君不道也。必將修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民。”荀子無疑是先秦最精通治道或法治的一位儒家,一位真正最具有現代意義的曠世大儒!
[1]章炳麟. 章氏叢書[M] 臺北:世界書局,1982.
[2]陳柱. 諸子概論[M]. 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
[3]侯外廬. 中國思想通史: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4]林語堂. 林語堂名著全集:第22卷[M]. 長春: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
[5]林桂榛. 論古人的社會治理思想——以先秦儒家為中心[J]. 孔子研究,2015(3).
[6]嚴復. 嚴復集:第1冊[M]. 北京:中華書局,1986.
(責任編輯:蘇紅霞 校對:賈建鋼)
B222.6
A
1673-2030(2016)04-0070-08
2016-08-15
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荀子疑難問題辨正與荀子思想體系研究”(14BZX041)、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人性論通史”(15ZDB004)的階段性成果
林桂榛(1974—),男,江西贛州人,曲阜師范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哲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