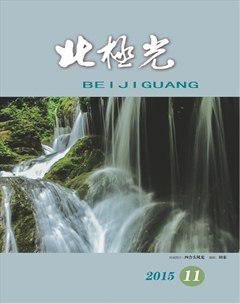從空間敘事看布寧《陳年舊事》的“變化”主題
周薇薇 楊麗新
摘要:俄羅斯著名文學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布寧在他創作于僑居時期的短篇小說《陳年舊事》中采取了多層次的空間敘事策略,敘事地志空間、人物心理空間與文本認知空間多位一體地托舉出作品重要主題——由“少數”到“多數”、由邊緣向主流的變化。這一主題正是布寧流亡時期隱秘思想轉變的外化與流露。
關鍵詞:布寧;《陳年舊事》;空間敘事;“變化”主題
《陳年舊事》是俄羅斯著名僑民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伊·阿·布寧創作于1922年的短篇,小說以第一人稱敘述人“我”的觀察與回憶,復現了“某一個春天”里莫斯科阿爾巴特大街北極飯店房客伊萬·伊萬內奇的生活片段——他寄居旅館,原本過著一成不變、孤僻單調的生活,隨著“公爵”到此下榻,他的生存狀態發生了某種意外的、煥發新生般的變化。
小說情節洗練,刻意淡化時間標記(故事發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某一個春日”),幾近靜止、共時的創作體現出“繪畫性”特征,但在敘事空間上卻能劃分出多元立體的層次——顯在的“地志空間”,即“北極飯店”,這是故事賴以發生的物理空間;潛在的人物心理空間,寄寓著主人公伊萬·伊萬內奇以及敘述者“我”的心理流變,以及體現作品意義歸旨的文本認知空間。這三重敘事空間對應并行而又聯系緊密:地志空間是心理空間和認知空間的標志物和具象外化,心理空間和認知空間層層深入地體現著內涵,指作品在整體意義上的主題和價值。
小說的地志空間被聚焦式地框定為阿爾巴特大街“北極飯店”,這是主人公伊萬·伊萬內奇居住的地方。那里看似人來客往,可在敘述人“我”眼里,這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封閉空間:它最突出的部分不是開闊熱鬧的大廳或者燈火通明的活動場所,而是走廊和客房共同組成的晦暗壓抑的空間——“曲軸形的走廊”:暗示陀螺般年復一年、一成不變的莫斯科;“客房的窗戶都朝內院開,房門上端的玻璃又不大透光”:陰暗的光線與局促的視野指向封閉壓抑的旅館生活;“轉一個彎以后是更長更暗的甬道”,象征過渡的通道也剝奪了洞見光明的可能,仍舊導向沉重的黑暗,只有“閃著紅光”的壁燈和“令人不好受”的反光鏡制造出光亮和開敞的假象。此外,伊萬·伊萬內奇的房門在他每天下午四點返回后即被鎖閉,直到第二天早晨九點才會被再次打開——主人公的生活也仿佛那道上鎖的門:“他在屋里干些什么在?怎樣消磨時間?只有上帝知道……”只有當飯店的女仆和茶房在“送茶炊、收拾床鋪和糟糕的洗臉池時”才會偶爾打破他的自我封閉。甚至見到其他房客,無論是生機勃勃的大學生、魅力獨特的女速記員,還是有著一頭漂亮頭發的小老太太,伊萬·伊萬內奇也只是出于禮貌鞠躬問好,卻既不期望、也不需要對方回應——伊萬·伊萬內奇的心理空間與其說是憂郁的,不如說是淡漠隔閡的。他那緊鎖的心靈久已忘卻一切開放、成長、熱烈、有所期待的生命力元素,反而對這種“極為罕見的單調的存在方式”抱以麻木的習慣(“對北極飯店不習慣的人來到這走廊上會覺得難受,可是伊萬·伊萬內奇一點這種感覺都沒有,他毫不在意地沿著這條走廊款步走去……”),無論在生活方式上還是心理體認上如陀螺般不停重復自己、停滯不前,封鎖了通往外界、通向光亮的“走廊”。此時,文本認知空間指向“令人疲憊的”、灰色的“冬季”圖景。
冬去春來,隨著某公爵到北極飯店租了間客房,成了伊萬·伊萬內奇的近鄰,三重敘事空間都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變化——在地志空間上,原本陰暗窒悶的旅館空間被置換為“日復一日陽光普照,使人興奮”的明媚場景,封閉的房門變成了打開的房門:伊萬·伊萬內奇總是忐忑而興奮地等待晚歸的公爵,有時還把頭伸到“房門外去”,看公爵是不是過來了,好跟他搭句話。模仿著公爵,伊萬·伊萬內奇也開始把自己那雙皺巴巴的皮靴“放在門外”,以前他可只在十二教堂大節才讓人刷鞋。他還學著公爵出門去看馬戲,甚至在早晨打開房門朝走廊大喊:“要茶!要茶!”不僅如此,伊萬·伊萬內奇還“買了一頂淺灰色的帽子,以及上路用的東西,想著夏天一點要去圣三一修道院或者新耶路撒冷……”對應地志空間的開敞,主人公緊閉的心靈之門也豁然打開,他原本淡漠孤寂的心理空間變得興快熱烈:當公爵禮貌而冷淡地對他答話,伊萬·伊萬內奇“已經覺得滿足了”;一天,當他終于看了馬戲,他在夜里欣喜萬分地對公爵說,“自己真開心極了……”伊萬·伊萬內奇想要開始過一種新的、有些體面和樂事的生活,即使那種生活終究會是一場虛無的想往,“渴望被迷住”本身已足以令他享受萌動的充實與生存的歡樂。此時,文本認知空間由“冬季”圖景轉而指向“節日般的”、絢爛的“春天”景象。
小說地志的、心理的及認知的敘事空間從不同層面由具象到抽象、由現象到內涵、由局部到整體地有機構建出文本“并置一轉換”的敘事邏輯:冬天變為春天,滯重變為萌動,單調變為豐盈,冷漠變為熱烈,封閉變為開敞,晦暗變為光明……它們共同托舉出“變化”的主題,這正是開啟小說核心價值的鑰匙。從表面看,伊萬·伊萬內奇變化的緣起不過是他想讓“生活中多一些春天的放任,添一點氣派”,也即跳脫他多年來的常軌以及“那些陰暗的走廊和他那房門上的玻璃不透光的斗室”,過一種“騷動的”、但是更具生命力和希望的生活。但不應忽略,伊萬·伊萬內奇的所有變化是經由第一人稱敘述者“我”的視角展現詮釋的,“我”對于“那個遠遠逝去的莫斯科的春天”以及屬于那個春天的伊萬·伊萬內奇的回憶構成了小說敘述層,“我”對人物帶有評價干預的色彩。當“我”憶起那個充滿節日般躁動氣息的莫斯科之春時評價道:“他(伊萬·伊萬內奇)也出門,也到什么地方去了,干些自己的事,小事,極小的事,因此有了在我們中間生存下去的權利……”敘述話語多次將伊萬·伊萬內奇與“我們”對立,采用內向型言說立場,凸顯類別與邊界——“我們”是作為主流的多數,是熱烈包容的麇集生活的代表;伊萬·伊萬內奇是作為邊緣者的“絕少為人注意”的少數,是“罕見的”封閉生活的典型。從這個意義上說,伊萬·伊萬內奇從內到外的變化不僅是他個體生命的嬗變,更是他由“他者”變為“我們”、由邊緣走向中心的過程。在此基礎上,沉潛于“變化”主題之下的小說核心歸旨浮出水面——邊緣“少數”向中心“多數”的轉變。
四、結語
《陳年舊事》創作于1922年,正值布寧流亡法國之初。在遠離本土的僑居國,物質處境與文化身份的雙重邊緣性使俄羅斯流亡作家一方面渴望精神超越與獨立,保存自身文化純粹性與優秀根基,一方面卻肉身困厄,亟需俗世溫暖與襄助——“1921年,剛開始流亡生涯的布寧,必須用文學作品來養家糊口,也必須用文學作品來證明自己的存在……在巴黎,盡管出版俄文作品仍然是那樣多,但是,卻老是在固定的讀者圈子里閱讀、談論。大家似乎眾日一詞地說著同樣禮貌的話語,卻難以掩飾同樣的文化失落。這個時期,布寧的心情是極為灰暗的。”僑居生活之初物質與精神依托的雙重失落使布寧在《陳年舊事》中借助分層推進的空間敘事埋設了由“少數”向“多數”、由邊緣向主流轉變的渴望——不再安于蟄居精神的塔尖而愿自我下放,呈現出精英知識分子在特殊境遇下的“準民間性”轉向。
(作者單位:西南石油大學)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