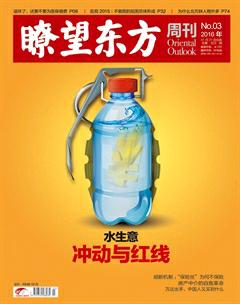掘金大數據征信
陳振華
從盡職調查到企業征信,再到個人征信和大數據征信,包括傳統金融機構、互聯網金融公司、大數據技術公司等一大批公司,紛紛涉足征信領域
信用是商業社會存在的基礎,和每一個人都息息相關。然而在中國,許多人都并不了解什么是征信。
“通俗一點說就是幫你了解合作方的信用狀況,幫你打聽消息的。借貸雙方、買賣雙方、交易雙方,彼此不了解,委托一個第三方機構,給你做一個信用調查報告或一個信用評分,幫助你作決策,就是征信。”考拉征信服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考拉征信”)總裁李廣雨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考拉征信是2015年1月央行試點首批開展個人征信業務的8家社會機構之一。
2015年7月,央行結束對八家企業的驗收,2015年10月結束第二次驗收工作。只是直到2016年1月,正式發牌結果仍未公布。
然而,這只未落地的靴子,卻讓征信從2015年“火”到2016年。

2014 年8 月30 日,北京中國國際金融展上,拉卡拉社區通展臺
而不少業內人士將2015年稱為“大數據征信發展元年”。在《2015展望:網絡征信發展元年》一文中,中國人民大學信用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吳晶妹曾寫道:“網上的一切數據皆信用,網絡征信是一個完全的‘大數據概念。網絡征信是傳統征信的業態升級,是對傳統征信的徹底改革。”
從盡職調查到企業征信,再到個人征信和大數據征信,包括傳統金融機構、互聯網金融公司、大數據技術公司等一大批公司,紛紛涉足征信領域。
這批掘金者,或許看重千億級市場,或許沉醉于技術帶來的革新,或許是出于搭建信用體系的公共責任,又或許,僅僅是為了一塊個人征信牌照。
千億市場
在2015年1月央行試點個人征信業務市場化之前,只有央行征信中心可以做個人征信,擁有個人信用信息。
而對與錢打交道的行業來說,這些信用信息可用于風險控制。能否申請信用卡或貸款,額度多少,這些評估均依賴于征信報告。
事實上,央行從2005年開始,就推動工商、環保、質檢、稅務、法院等公共信息納入征信系統,共采集了16個部門的17類非銀行信息,包括行政處罰與獎勵信息、公積金繳存信息、社保繳存和發放信息、法院判決和執行信息、繳稅和欠稅信息、環保處罰信息、企業資質信息等。
央行征信中心研究發展部總經理李連三曾透露,央行征信中心的個人信用信息大約每天被查詢164萬次。僅在2015年前三個季度,個人信用信息累計已被查詢4億次。
截至2015年9月,央行征信系統已收錄8.7億自然人。然而,這其中有信貸記錄的僅為3.7億人,而可形成個人征信報告、得出個人信用評分的僅有2.75億人。
這相當于有10億中國人是沒有信用記錄的。

2015 中國國際金融展現場的中國人民銀行征信中心展臺
“我們想關注這個人群,通過我們的數據分析、畫像,幫助這些人獲得他們的信用狀況,為他們的信貸、就業等方面提供信用支持。”李廣雨告訴本刊記者。
這當然也是一片巨大的藍海。據平安證券《計算機行業征信市場系列研究》數據預測,中國征信行業未來市場規模將達千億元,其中企業征信市場規模有百億元,個人征信市場規模有千億元。
而宏源證券發布的研報數據更為細致:通過中美對比測算中國個人征信市場空間為1030億元,而中國目前個人征信和企業征信的總規模為20億元。
即便是發展已久的企業征信領域,也給掘金者留下了機會。
傳統企業征信的做法,主要基于工商數據等公開數據,依靠人工完成信審。一般標準企業征信報告得花大約一周的時間。
這種模式在北京宜信致誠信用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致誠信用”)董事總經理趙卉看來,是低效的。
“現在許多單位有短平快的需求。我們的大數據征信平臺‘致誠企福可以更迅速地生成報告,以便用戶兼顧貸前的風險評估及貸后的動態監控、風險預警。”趙卉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從價格上來說,大數據征信也有優勢。
“你是愿意花5000元買30個字段的征信報告,還是愿意花5元買1000個字段的征信報告?”天創信用服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天創信用”)常務副總經理王衛東告訴《瞭望東方周刊》,“互聯網行業有句話,離錢近賺錢快,離錢遠賺錢難。”

解放人力
當然,更重要的是,大數據征信能帶來更多的價值。
在2015年中國大數據技術大會(BDTC 2015)上,阿里巴巴集團首席技術官王堅就曾談到:“互聯網是一種基礎設施,而數據是一種新的生產資料。”
對掌握大量電商數據、交易數據的阿里巴巴來說,作為一種新的生產資料的數據,如何產生更多價值?
“我們基于本身的大數據,建立模型,進行分析,觀測看模型效果,保持可解釋性,再迭代更新模型。”螞蟻金服副總裁、首席數據科學家漆遠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這是普遍的大數據征信模式。
通過運用大數據、云計算、深度機器學習等技術,芝麻信用也成為央行首批試點個人征信的8家公司之一。
在支付寶里,個人可查看芝麻信用評分,有身份特質、履約能力、信用歷史、人脈、行為偏好等維度綜合評估。這些數據指標,主要基于阿里云上的數據及其他第三方數據。
“我們現在云平臺上有800PB的數據,一天進來1PB的數據,量是非常大的。”阿里云事業群副總裁章文嵩告訴《瞭望東方周刊》,這些數據中,包括訪問日志數據、交易情況、出行的數據,等等。
漆遠透露,通過芝麻信用信息驗證等反欺詐服務,已有銀行將虛假辦卡的識別能力提高近3倍,通過行業關注名單識別不良用戶占比達到平均的4倍以上。
更重要的是,大數據技術能做到人做不到的事情。
“大數據首先可以解決的問題是人工信審的自動化和產能提升。”宜信大數據創新中心首席數據科學家項亮在2015年中國大數據技術大會(BDTC 2015)上,這樣對本刊記者表示。
余下的工作,便可以讓人“做人最擅長的事情”。
項亮解釋稱,人最不擅長的就是作決策,而最擅長的東西,是可以搜集很多機器搜集不到的東西。“比如可以通過打電話跟人產生交流,可以感覺到這個人靠不靠譜。我們希望人和機器配合中發揮雙方的優勢。”
免費邏輯
即便大數據技術能在征信領域開拓一片新天地,其應用前景卻仍陷于迷霧中。大數據征信真的能賺錢嗎?
“征信行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行業,跟賺錢相比,社會責任要放在首要地位。更何況這個行業并不容易賺大錢。”李廣雨坦陳。
至少在目前,更多依賴于大數據技術的征信公司提供的是免費服務,包括考拉征信。
“信用評分依賴于評分模型,需要經過多次的打磨訓練和調整的。怎么做呢?只有經過大量的數據測試和樣板分析來去看,這個模型成熟至少需要做好幾年,每家都一樣。”李廣雨介紹說。
因此,與考拉征信合作的機構要給反饋,進行數據回流,教化模型。“我們的邏輯是向用戶免費,成熟后有可能向機構收費。”李廣雨說。
致誠信用的做法則是,免費開放宜信9年業務積累的個人借貸數據的“阿福平臺”,供從業者查詢。
“個人借貸數據,特別是貸后數據,是做信貸業務的強參數。整個P2P行業其實沒有誰愿意主動開放。我們開放這些數據,主要是為了降低整個行業的欺詐和一人多貸的風險。”趙卉說。
她告訴本刊記者,免費開放給從業者,是指做個人信貸業務的機構,并不包括征信公司。
而查詢數據依然會沉淀下來,為風險控制提供可靠的參數。
“數據庫中的某個人被查詢次數過多,很有可能就是他向多家平臺申請借款了,對此我們會給客戶提供風險預警功能,對于一個有經驗的風控人員而言,他會判斷是否存在一人多貸的風險,或許會考慮調整啟動追款程序,等等。”趙卉說。
無論如何,一個共識是被廣泛接受的:單純靠賣征信報告,贏利太微薄。
王衛東向本刊記者坦言,有企業征信資質的天創信用,企業征信報告分為三類:“簡單版本的是免費的,復雜一些的賣幾十元,有定制需求的價格則在上百元。”
也正是由于不賺錢,天創信用業務中占大頭的是“征信+金融”,既做征信,也對接投資方和資產方,從而促成交易,收取服務費用。
爭奪牌照
即便贏利微薄,甚至不賺錢要免費,掘金者也趨之若鶩。
2015年7月央行結束對首批8家個人征信機構驗收后,有報道稱,包括百度、京東金融、快錢、北京安融征信、拍拍貸等30余家機構,均有意申請第二批個人征信牌照。
然而,截至目前,第一批個人征信牌照仍未落地。
《征信機構監管指引》(以下簡稱“《指引》”)卻先于牌照在2015年12月低調下發。《指引》從機構設立的審慎性條件、征信機構保證金、非現場監管和現場檢查四個方面設置了持牌條件。
“據我們的了解和猜測,央行確實對這個牌照的發放還是非常慎重的,所以發牌之前先發了《指引》,目的是為了監管先行。我認為這有助于這個市場回歸理性”李廣雨說。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業內人士告訴本刊記者,實際上個人征信是個燒錢的行業,真正值錢的是牌照。
“征信牌照是有價值的,有公司通過獲得牌照立馬就獲得投資,征信概念股也在資本市場炙手可熱。得到牌照后,也有公司倒手賣錢,溢價轉讓。”上述人士說。
實際上,《指引》中規定了股權變更超過5%以上需要央行重新審批,有分析人士稱,這一規定,目的也是防止牌照發放以后倒買倒賣。
只是,對于市場來說,遵循的邏輯是“物以稀為貴”。
“關鍵是這牌照也不知道發幾塊,如果是通過一家就發一塊,這牌照就不值錢;如果只發十塊,那么就很值錢。”前述不愿具名的人士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