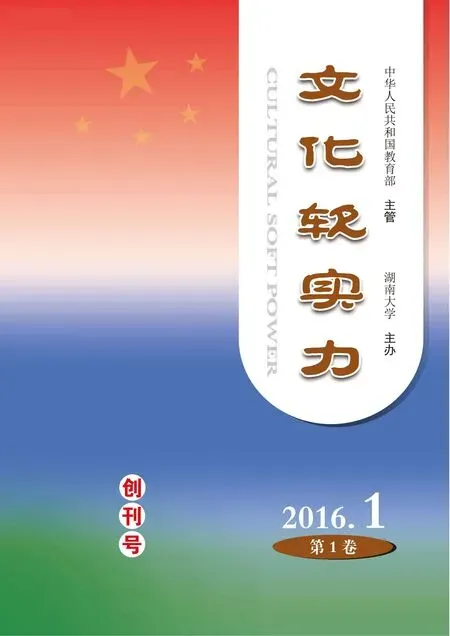“柏林墻倒塌”與“蘇東劇變”的歷史對話
張國祚, 埃貢·克倫茨
“柏林墻倒塌”與“蘇東劇變”的歷史對話
張國祚, 埃貢·克倫茨
中宣部黨建網編者按:2015年11月3日,國家文化軟實力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在湖南大學主辦了中德國際學術論壇,主題是“柏林墻倒塌與蘇東劇變的歷史對話”。原德國統一社會黨總書記、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國務委員會主席埃貢·克倫茨應邀出席論壇。國家文化軟實力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主任張國祚教授主持了論壇,并與克倫茨先生進行了一場深刻而富有啟迪的對話。
聽歷史發生地的決策者講歷史,或更有參考價值
張國祚:德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德意志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歷史上出現過很多杰出的名人,例如,偉大的思想家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和資本主義生產的剩余價值、創立了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其思想高峰和世界影響迄今無人超越;偉大的科學家愛因斯坦,他不僅因成功解釋光電效應而推動量子力學的發展、創立了狹義相對論和廣義相對論,而且還是維護世界和平的著名社會活動家;偉大的數學家高斯,他是世界數學史上最有影響的數學家之一,數學領域有110個數學研究成果以“高斯”命名;德國還有一個值得尊敬的政治家勃蘭特,1970年,他訪問了波蘭,在全世界注視下跪在猶太人遇難紀念碑前。雖然他是無辜者,但是作為西德總理,他為前納粹德國法西斯的罪行表示羞愧,對猶太受害者表示深切的道歉。這一跪,與今天依然美化侵略歷史、拒不深刻反省、堅持參拜靖國神社的安倍晉三等日本右翼勢力,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談到戰后的德國政治家,還應提到昂納克,柏林墻就是他主政東德時修建的,而昂納克的繼任者就是我們今天的嘉賓埃貢·克倫茨先生。他是德國統一社會黨最后一任總書記、國務委員會主席、國防委員會主席。雖然他的任期僅僅三個月,但他也很知名,因為他不僅是“柏林墻倒塌”的親歷者和見證者,而且是主要決策者。今天,我們有幸把他請到現場,請他談談對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看法。克倫茨先生,下面我想請教的問題是,1961年修建了柏林墻,到1990年柏林墻被拆除了,其間經歷了29年,在這期間,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克倫茨:張教授提的這個問題,對我來說意味著整個一部歷史教科書。凡是聽到“柏林墻”這個概念,人們就感覺是一段妖魔化的歷史,這好像是發生在很久以前的一段痛苦的歷史。西方人談到柏林墻的時候,總是把世界上最骯臟最污穢的語言都加在它身上。在1961年,柏林墻建立之前,整個民主德國有過12年根本就沒有大墻包圍的歷史。而在這段歷史當中,美國及其北約成員國,想盡一切辦法要把我們民主德國消滅在萌芽中。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1961年8月13日,華沙條約國在莫斯科做出一個歷史性決議——在東西兩個柏林之間建立起一個邊界設施,以阻攔西方的干預和破壞,這就是“柏林墻”。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柏林墻實際上也是一條經濟邊界,當時整個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之間都有著一種經濟互援互助,柏林墻也是為了阻攔西方人越境到民主德國來享受經援好處。1961年,當時的蘇聯共產黨總書記赫魯曉夫和美國總統肯尼迪在奧地利的維也納談到邊界問題。有人曾經問起肯尼迪總統對于建墻的評價。肯尼迪說,這不是一個好的解決方法,卻是一個可以接受的比較理智的權宜之計。事實上也證明,在柏林墻存在的29年中,整個歐洲沒有發生過戰爭。然而在冷戰進行到最后時期,戈爾巴喬夫等蘇聯領導人認為柏林墻似乎沒有必要再存在了。但我至今仍然堅信,如果蘇聯沒有解體,如果民主德國沒有淪亡,那么,當今的世界上就不會有這么多戰爭,比如說在敘利亞,在利比亞,在伊拉克,在很多阿拉伯國家和非洲國家。
柏林墻的修與拆要歷史地看、辯證地看
張國祚:我想,對于柏林墻修建和倒塌這樣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可能要從這樣幾個角度去看。
第一,必須把柏林墻的修建和拆除都放在美蘇冷戰大背景下來看。原因主要來自華約和北約、蘇聯和美國兩個方面,當時民主德國(東德)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受蘇聯制約。二次世界大戰后,蘇聯占領了德國東部,美英法占領德國西部;首都柏林也被割裂,東柏林由蘇軍控制,西柏林由美英法軍隊控制,而整個柏林又在東德版圖之內。開始階段蘇聯處于攻勢,1948年、1958年、1961年,先后發生的三次“柏林危機”都是由于蘇聯試圖強迫美英法軍隊撤出西柏林而引起的,但美英法拒不退讓,蘇聯才支持東德修建柏林墻,試圖阻斷西柏林同外界的交通,逼迫北約把西柏林交出來。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彼此力量的消長和蘇聯內部的演變,柏林墻漸漸成了蘇聯和華約國家的一個包袱。1989年12月3日,戈爾巴喬夫和老布什在馬耳他舉行了一次峰會,戈爾巴喬夫面對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先后改旗易幟,一廂情愿地宣布冷戰結束了。1990年7月,西德總理科爾為了謀求兩德統一,誘使蘇聯以同意兩德統一來換取西德對蘇聯的經濟援助,于是戈爾巴喬夫又同意東德拆除柏林墻。到了1991年7月1日,戈爾巴喬夫又宣布正式解散華沙條約,同年12月25日,戈爾巴喬夫被迫辭職,蘇聯徹底解體。這就是柏林墻倒塌前后的歷史過程。所以我們談到柏林墻,無論是修建還是拆除,一定要把它放在美蘇冷戰的大環境下去看。
第二,柏林墻倒塌既是東西方政治經濟較量的結果,也是東西方意識形態較量的結果。柏林墻是一道政治經濟墻,它區分開東歐社會主義和西方資本主義;柏林墻是一道軍事墻,它區分開華約集團和北約集團;柏林墻是一道意識形態墻,它區分開蘇聯僵化的馬克思主義和西方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對于柏林墻倒塌和蘇聯解體,戈爾巴喬夫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為他犯了兩個致命的錯誤:一個是他重用了一個人,這個人就是雅科夫列夫,他上臺之后,推著戈爾巴喬夫一步一步地遠離馬克思主義、遠離社會主義,搞起了所謂以“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為旗號的“新思維”,主張政治多黨制、思想多元化、軍隊非黨化、經濟私有化、解除“報禁黨禁”。在這種大氣候影響下,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這些國家都先后改旗易幟。民主德國的演變已在所難免,被柏林墻隔開的東西方兩種勢力的斗爭,最后以美國的勝利和蘇聯的失敗而告終。在這個過程當中,作為德國統一社會黨,雖然在政治上信仰馬克思主義,但在很多情況下,都是身不由己。
第三,對柏林墻倒塌的原因要“一分為二”地看。我不贊成把柏林墻倒塌完全歸因于西方的思想文化滲透,也不認為柏林墻倒塌就證明資本主義制度比社會主義制度好。但我們必須實事求是地對歷史進行反思。經過29年的歷史演變,柏林墻不但沒有限制住西德的發展,反而拉大了東德經濟落后的差距,更沒有抵御住西方的思想文化滲透。柏林墻突出的負面作用是阻斷了東德西德人民之間的來往、親屬之間的聯絡,漸漸成了東德民眾反對的焦點。根據有關資料的記載,在柏林墻存在的29年中,從東德經過匈牙利等國跑到西德去的東德人,有大約二百萬;有61個東德人因為要翻越柏林墻而被東德軍隊槍殺了;有5000多東德人,試圖翻越柏林墻,或成功,或被抓回判刑。我認為這是值得反思的一個問題。剛才克倫茨先生談到了當時美國總統肯尼迪對修柏林墻的近于認同的看法。但是,肯尼迪針對柏林墻還說過另外一段話,他說:“世界上的圍墻都是防止外面的人闖進來的,只有一種圍墻是防止里面的人出去的,那是什么?那就是監獄的圍墻!”顯然,肯尼迪是在嘲諷東德修柏林墻。我們當然不能認同肯尼迪的諷刺,但對柏林墻的倒塌確實應該“一分為二”地看,也要從蘇聯和東德自身政策失誤查找原因。我認為,蘇東劇變是僵化的馬克思主義的失敗、是前蘇聯帶有霸權主義色彩的社會主義的失敗,而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和符合國情的社會主義是不會失敗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前無古人的偉大創舉,已經取得令全世界驚羨的巨大成就。我的上述看法,不知克倫茨先生是否同意。
克倫茨:張教授現在提出的這個問題,是一段非常復雜的歷史。有一個歷史事實,在邊境地區,所有的死亡或者受傷的人,每一個人都不應該死,每一個死亡案例都是一個悲劇。在當時民主德國統一社會黨的政治局里面,對發生在我們兩德邊境上的每一宗死亡案例都感到至深的悲哀。世界上任何一個人的生命都是可貴的,任何人的生命都是不可替代的,都是不可挽回的。但是,當時的政治環境、當時的國際環境造成了這樣的歷史事件,不能夠單方面地追究一個國家或者邊境一方的責任。而我要強調的是,當時都是由復雜的雙方所引起的歷史事件造成的,對此,雙方須共同承擔這些歷史責任。剛才張教授也提到戈爾巴喬夫宣布冷戰已經結束。我認為冷戰到今天仍然在繼續,冷戰非但沒有終結,冷戰甚至在某些地區演變成熱戰。所有這一切,歷史的現實都是有根源的,我認為戈爾巴喬夫應該承擔很大的歷史責任。1989年11月1日,我們在蘇聯克里姆林宮,與戈爾巴喬夫進行了一場為時4個小時的談話,談到了關于民主德國未來的命運。我們這個國家事實上把蘇聯看成是自己的父親,因為民主德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產物,也是冷戰的產物。民主德國實際上是蘇聯的兒子。戈爾巴喬夫看了看我說,從國際法上來講,民主德國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我不能夠設想兩個德國走上統一。然而到了1989年11月底的時候,他與當時的美國總統在馬耳他又舉行了一場會談,認為現在冷戰已經結束了,他沒有征求我們民主德國領導層的同意,就認為兩德統一時機已經成熟了。在兩德統一的談判中,提到了統一后的德國究竟留在北約還是留在華約,戈爾巴喬夫居然說,同意德國加入北約,而且事后很快又宣布解散華約。當時,美國口頭承諾北約只停留在北約現有的地盤上,不會向東擴展。現在的歷史現實是,幾乎所有歐洲國家都已經加入了北約,北約的邊境已經擴展到了俄羅斯的邊境,可以看得出來,冷戰并沒有結束,歐洲緊張的氣氛并沒有得到緩解。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思想演化要防微杜
張國祚:克倫茨先生關于兩德統一的歷史脈絡,講的很清楚。對“冷戰”的看法也有一定的道理。我們說“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題”,很大程度上是指絕大多數國家在主觀上都希望和平與發展,這并非意味著世界已經完全實現了普遍和平與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40年代末50年代初形成了一個社會主義陣營,在歐亞大陸連成了一大片。除蘇聯和東歐9個社會主義國家之外,亞洲的中國、蒙古、朝鮮和越南也都建立起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高歌猛進,影響越來越大,正如毛澤東所說“東風壓倒西風”,就連柬埔寨國王西哈努克都公開講,他很希望自己也成為一個社會主義者。但是,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東劇變”后,除了中國、朝鮮、越南之外,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紛紛改旗易幟。習近平指出,“一個政權的瓦解往往是從思想領域開始的,政治動蕩、政權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間發生,但思想演化是個長期過程。”。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不能把“蘇東劇變”僅僅歸罪于戈爾巴喬夫一個人,追根溯源,是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大反斯大林埋下了禍根。抹黑蘇聯歷史、扭曲了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蘇聯社會帝國主義霸權思想的滋生、社會主義陣營的分裂,無不始于赫魯曉夫大反斯大林。請問克倫茨先生,您怎樣看待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大反斯大林?
克倫茨:首先,我完全同意張教授對這件事的看法。我只有一點補充意見,如果說歐洲的社會主義國家全部走向衰亡,這里面也有它自身的很多歷史教訓可以汲取。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認為對歷史事件的評論應該從主觀和客觀兩方面進行綜合分析,但是遺憾的是,實際上世界到現在為止沒有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角度對這段歷史進行客觀的評價和定論。剛才有一點我不敢肯定,您認為東歐已經“和平演變”了?實際上我們還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而不是走蘇聯后來的道路。
張國祚:“和平演變”是上世紀50年代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提出的旨在改變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顏色的戰略。不管東歐原來的共產黨人是否還信仰馬克思主義,但事實上東歐國家都已改旗易幟。“東歐劇變”從某種意義上看也是美國實施“和平演變”戰略的一個結果。美國的“西化分化”戰略,煽動“顏色革命”的戰略,都屬于“和平演變”戰略的延伸。“革命”一詞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當中是進步的、是推動歷史前進的一種進步的力量,一種正能量的運動。而“顏色革命”雖然也叫“革命”,但同馬克思主義所說的革命是有本質區別的。一是兩者目的不同。馬克思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無產階級和被壓迫人民的解放而斗爭,建立起真正為人民服務的政權;“顏色革命”的組織領導者只是為了拉攏選民、推翻執政當局、奪取執政權。二是組織領導者的地位不同。領導被壓迫階級起來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往往都被統治階級視為非法的鎮壓對象;而“顏色革命”的組織領導者都是有合法地位的反對派。三是斗爭方式不同。面對統治階級的殘酷鎮壓,馬克思主義政黨不得不領導人民進行武裝斗爭,往往把“暴力革命”看成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普遍規律”;而“顏色革命”組織者由于擁有合法政治地位,他們可以冠冕堂皇地打著“自由、民主、人權、反腐敗”的旗號,以“合法”的方式搞所謂“街頭和平抗爭”,制造輿論,抹黑當局,煽動民眾對當局執政合法性持懷疑和否定的態度,造成族群分裂和社會動亂。四是結果影響不同。馬克思主義革命讓人民翻身解放做主人,帶來社會進步、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而“顏色革命”的結果往往建立起親西方的政府,不但不能給人民帶來真正的利益,而且還給“顏色革命”發生國和周邊地區帶來政治動蕩、經濟衰退、民生凋敝、社會災難,甚至帶來生靈涂炭,最近涌向歐洲的難民潮就是個證明。
究竟怎樣評價斯大林,也是個大是大非的問題
克倫茨:在這點上,我們有同感。另有一點我跟你意見完全一致,就是當年的社會主義從中國的黃河,延伸到德國的易北河。我還認為,1949年之后,如果民主德國局勢能夠繼續下去的話,我們今天還是社會主義;如果當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蘇聯,當然也包括其他的社會主義國家,都團結一致走共同道路的話,今天的世界就會是另外一種景象,今天的世界就會更加和平,更加美好。剛才您提到了蘇共第二十大,這次會議遺憾地導致了蘇聯共產黨與其他的歐洲共產黨與中國共產黨之間漸行漸遠,我認為蘇共第二十大是一個不團結的大會。當時蘇共中央并沒有經過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共同分析討論,就片面獨斷地提出了一個理論,就認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面臨很多問題。批評斯大林的有些做法我認為尚可理解,但是這種批評方式有些過激過度。我對中國共產黨后來的發展方向是非常看好的,也非常羨慕。盡管對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功績有功與過的兩分法的評論,但是毛主席像至今仍然屹立,這個做法就跟蘇共二十大的做法截然不同。歷史應當就是歷史,不能夠因為一個人的過,而否定他的功,不應該這樣武斷地對待共產黨的領導人。就連當時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家,包括英國的首相撒切爾曾經就蘇共二十大對斯大林批評的方式都提出了異議。大致意思是說,斯大林曾經離開了木材的革命,然后呢進入了核武器的時代……
張國祚:這是不是翻譯出了問題(指克倫茨的翻譯)?講這句話的不是撒切爾,而是另一位英國前首相邱吉爾,他說:“斯大林接手的俄羅斯是一個使用木犁耕種的國家,而當斯大林撒手人寰的時候,他留下的是一個能夠制造原子彈的強國。”中蘇論戰時我們黨發表了“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其中“二評”就是“關于斯大林問題”,文中引用過一段西方格言:“鷹有時比雞飛得還低,但雞永遠飛不了像鷹那么高。” 斯大林雖然有錯誤,但他“就是一只高高盤旋的雄鷹”。毛澤東更是一只值得敬仰的雄鷹。
克倫茨:也許我們的消息來源不盡一樣,但意思大致差不多。
中國人對自己的發展道路,要更有信心
張國祚:很高興我能與克倫茨先生有這么多共識。我想再請教一個問題。您做過民主德國青年團中央書記,曾對中國青年提出這樣的寄語,“我希望中國的青年能承擔起歷史的責任,中國青年要提高警惕,我們這個世界十分復雜,我相信中國的紅旗是不會倒的。”您能否展開說一下,您希望中國青年警惕什么?為什么那么肯定中國的紅旗不會倒?
克倫茨:法蘭克福衛報是德國一份資本主義的大報,最近刊登一篇文章,主調說中國改革陷于停滯,認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作用應該淡出。在談到“改革”的時候,我必須非常謹慎,資本主義國家、媒體和他們的政治家就是希望把社會主義的因素改革掉。這就應該警惕!我堅決地贊成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應該置于中國共產黨強有力的領導下,而不是像西方所希望的那樣,走資本主義道路。西方有些人確實把中國現在說成是資本主義社會,我個人堅決反對他們的說法。我認為中國在幾十年的改革開放進程中,使幾億人口從貧困當中擺脫出來,這就是社會主義,這絕對不是資本主義。我認為,中國在世界政治舞臺上正在做出越來越大的貢獻,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當中,中國在同俄羅斯的戰略合作伙伴關系當中,正在為世界做出越來越大的貢獻,正在抵御、牽制美國的戰爭政策。中國在社會科學領域也做出了巨大貢獻,尤其是關于二戰的分析和研究。現在歐洲第一次清晰地知道,中國曾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當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僅僅中國一個國家,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當中犧牲了3500萬人。歐洲的視角總是局限于歐洲的實踐,他們一直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日或勝利日是1945年的5月8號,現在歐洲人才突然發現,噢,實際上是到9月份才結束。我非常羨慕中國人能夠走在社會主義道路上。請允許我最后再說幾句:不要為所謂西方大國的閃光迷了眼睛,不要去羨慕美國人的一切,要腳踏實地地為中國建設出力。
張國祚:非常感謝克倫茨先生對中國飽含深情,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高度認同。我贊同克倫茨先生的觀點:中國青年要提高警惕,因為以美國為首的國際敵對勢力西化、分化中國的圖謀從來沒有停止過。我也很贊同克倫茨先生的另一個觀點,那就是怎么看待改革。改革應當是體制機制的完善,而不是改旗易幟。雖然我們在實踐中也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但解決這些問題不是照搬西方的發展模式,而是靠我們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有一句老話:“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我們國內一些人常常對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實有些抱怨,有不少意見,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沒有任何現成的模式可參照,在前進中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在所難免。但是,我們畢竟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不斷解決問題中高歌猛進,已經取得了舉世公認的輝煌成就。今天克倫茨先生熱情洋溢的演講實際上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世界看好中國的新佐證。所以我們一定要堅持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