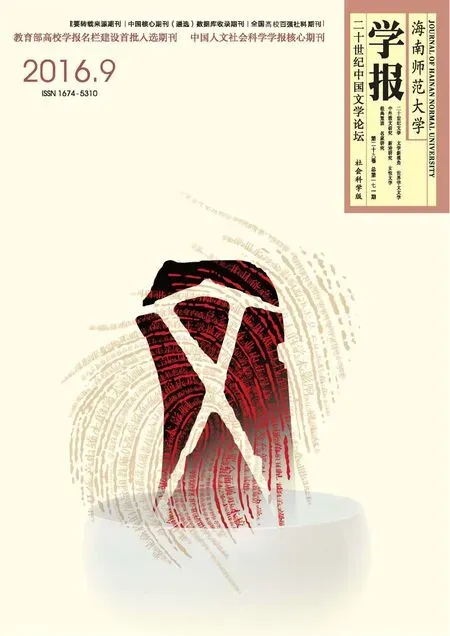場域轉換與《朝花夕拾》的情感裂隙
李彥姝
(教育部 高等學校社會科學發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080)
?
場域轉換與《朝花夕拾》的情感裂隙
李彥姝
(教育部 高等學校社會科學發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080)
《朝花夕拾》創作于1926至1927年間,發軔于北京、續寫于廈門、修訂于廣州,誕生于魯迅輾轉漂泊的人生旅途中。其間魯迅經歷了被北洋政府通緝、與許廣平相知相戀、南下任教“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等歷史事件或個人遭遇。地域環境的轉換、個人經歷的更迭、社會時局的變遷等,使散文中暗藏著相當程度的情感裂隙:在北京的創作反映出對于社會境況的不滿和譏諷,在廈門的創作流露出溫情與落寞相雜糅的回憶之美,在廣州的創作體現出虎落平陽、壯志未酬的理想幻滅。視角在回憶與現實的兩端游移,反映了特定歷史時期魯迅思想的多面性和復雜性。
魯迅;《朝花夕拾》;場域轉換;情感裂隙
魯迅的創作一向與悲涼、幽暗、戰斗這類詞扭結在一起,把筆觸伸向個人“回憶”是少有的事情。如此說來,散文集《朝花夕拾》①本論文所引《朝花夕拾》文字均出自《魯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可算作一次偏離軌道的創作旅程,其流露的審美風格、折射的生命意識與魯迅其他文章迥然不同。讀《朝花夕拾》不難發現,魯迅不僅擅于以筆為劍,憑借悲憤犀利的語詞刺穿社會的黑暗,也擅于以溫潤的心靈去感受沐浴生命之光,以平和的姿態緬念往昔歲月的靜好,以質樸的情感眷戀既杳渺又真切的故土與親人,以細膩的心思捕捉日常生活的靈光等等。
《朝花夕拾》所射出的不是刺眼的烈日強光,而是含情脈脈的一抹夕陽。為何《朝花夕拾》會在1926至1927這短短一年多顛沛流離的經歷中破土而出呢? 厘清《朝花夕拾》創作的時代背景與地域環境,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它卓爾不群的價值和內涵。《朝花夕拾》的創作起始于北京、延續至廈門、封筆于廣州,誕生于魯迅輾轉漂泊的人生旅途中,其間經歷了被北洋政府通緝、與許廣平相知相戀、南下任教、“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等重大歷史事件或個人遭遇。《狗貓鼠》、《阿長和山海經》、《二十四孝圖》、《五猖會》、《無常》五篇作于北京;《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父親的病》、《瑣記》、《藤野先生》、《范愛農 》五篇作于廈門;最后于廣州修訂成冊,并寫小引與后記。因為創作場域的轉換,所以這部散文集看似渾然一體,實則文本內部存在著相當程度的情感裂隙。魯迅對這一點有著清醒的認識:“文體大概很雜亂,因為是或作或輟,經了九個月之久。環境也不一樣。”
一
分析作于北京的數篇散文,絕對繞不開當時的政治語境。卷入北京女師大風潮(1924年至1925年)、“三一八”慘案(1926年)以后,魯迅在北京失去了公職,并與周作人、許壽裳等文教界人士一起被北洋政府通緝,這期間他為了避難,先后輾轉于山本醫院、德國醫院、法國醫院等地。《朝花夕拾》里在北京期間所寫就的作品,呈現出一種復雜的文體風格——有細膩的記敘,有犀利的議論,也有引經據典的考證。寫作視角時而流連于過去,時而又回到現在,將對現實的諷刺批判夾雜在復雜的回憶之情中。此時,魯迅在現實與回憶的天平上周旋游移,“在回憶往事中不忘社會啟蒙的追求,仍舊進行著文化批判,并且視野異常開闊”*莊漢新:《中國二十世紀散文思潮史》,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年,第75頁。。
《狗·貓·鼠》作于魯迅寓居北京的后期,正是他因“女師大風波”與“現代評論派”筆戰之時。這篇散文可以被看做魯迅“閑話風”散文的代表作。“‘閑話’也稱‘漫筆’,不僅是題材上漫無邊際,而且是行文結構上的興之所至的任意性。”*錢理群等:《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40頁。這種“任意性”深切表達了魯迅深陷政治風波時心境的雜蕪和凌亂,欲遠離世俗塵囂而不得的矛盾心理。談到仇貓的理由,魯迅主要列出兩條:幸災樂禍的陰暗心理和討好茍且的一幅媚態。貓缺乏虎獅一般的剛烈和強硬,貓軟弱、世俗、叫囂……而這些均指涉了魯迅眼中“現代評論派”浮滑、不徹底的偽君子文風。最初,現代評論派傾向于北洋政府,拒斥國民革命,后來看到革命形勢如火如荼,又轉身投奔革命。魯迅從這類人的騎墻心態中看到了革命的危機,現代評論派的投機舉動恰恰與魯迅所倡導人生的嚴肅性、純粹性、徹底性背道而馳。《狗·貓·鼠》的前半段都是在以畜喻人,夾敘夾議,具有濃厚的隱喻性和諷刺性,繼承了魯迅一貫的“嬉笑怒罵”的雜文風格。但是魯迅沒有將這種文風延續到底,而是突然筆鋒一轉,從現實轉入到回憶:“這都是近時的話。再一回憶,我的仇貓卻遠在能夠說出這些理由之前,也許是還在十歲上下的時候了。”把現實的不快拋到一邊,充分沉浸在回憶的情境中,這之后,便盡是些幽默、詼諧、充滿童趣的文字了。原來,兒時仇貓的原因是極其簡單的:“只因為它吃老鼠,——吃了我飼養著的可愛的小小的隱鼠。”作者花了不少篇幅,講述童年時對于寵物隱鼠的喜愛。描寫了對于“老鼠成親”這一傳說的神往,記錄了蛇與鼠這對天敵間的周旋與博弈,講述了了長媽媽誤傷隱鼠而嫁禍于貓的經過……童年的幸福正隱藏于此類看似無甚意義卻摩挲心靈的奇聞軼事中。作者饒有興味地追憶幼時聽祖母講故事的情景:“那是一個我幼時的夏夜,我躺在一株大桂樹下的小板桌上乘涼,祖母搖著芭蕉扇,坐在桌邊,給我猜謎、講故事。忽然,桂樹上沙沙地有趾爪的爬搔聲,一對閃閃的眼睛在暗中隨聲而下。”人與動物、植物、自然渾然一體,構成一幅溫馨和諧、令人沉醉的夏夜圖景。作者在文章的最后,又從時光機器中跳脫出來,從現實中來,又回到現實中去,首尾呼應,再一次表達了對于所謂現代評論派的譏諷和不滿:“我大概也總可望成為所謂‘指導青年’的‘前輩’的罷,但現下也還未決心實踐,正在研究而且推敲。”人屆不惑之年,現實與回憶展開交鋒是自然之事。同一個命題之下,魯迅對于世態炎涼的認識日漸深刻,既以現實的姿態與論敵針鋒相對;又以溫暖的筆致與兒時的趣味欣然重逢,使得已悄然遠去的童年記憶重新發酵。
在《二十四孝圖》中,作者批判了“老萊娛親”、“郭巨埋兒”等故事中所折射出的偽善的傳統“忠孝觀”。這套忠孝觀念隨著時代推移,已經很少有人真心去實行,卻被當作經典來教育一代又一代國人。作者談到“郭巨埋兒”給幼小心靈留下的陰影:“我從此總怕聽到我的父母愁窮,怕看見我的白發的祖母,總覺得她是和我不兩立。”一個原本用來教育后輩行孝的故事,反倒造成了親人間的隔閡,這是對中國封建傳統文化的巨大諷刺。《無常》一文,作者明則寫鬼,暗則喻人;明則寫古,暗則喻今。魯迅評價無常:“爽直,愛發議論,有人情。”無常雖在陰間,屬攝魂之鬼,但它對人間、對將死之人竟懷著那樣的憐憫和恩賜。魯迅憑借“無常”之名,一方面回憶了幼時參加迎神賽會的生動景象,另一方面也表達了對于現實生活中“人生無常”的慨嘆,由“生的苦趣”,聯想到人世間的“公理”不存,于是生發了對于陰間的向往。魯迅本人的經歷似乎也印證了“公理之不存”的說法:“我這幾年來,常想給別人出一點力,所以在北京時,拼命地做,忘記吃飯,減少睡眠,吃了藥來編輯,校對,作文。誰料結出來的,都是苦果子。”*莊鐘慶、莊明萱:《兩地書·集注(廈門-廣州)》,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88頁。動蕩的時局以及澆薄的人心,使魯迅不便于直抒胸臆,然而又不甘于放棄戰斗。作者的思緒游離于回憶和現實之間,現實的幽暗、世事的纏繞,讓他不能徹底地沉浸于妙趣橫生的兒時記憶。雖將一系列文章歸入“舊事重提”的行列,但是陳釀中摻雜了新酒,回憶之門時開時合、有所遮蔽。回憶帶有幾分偽飾的色彩,更像是一個幌子,為的是襯托出借古喻今之義。北京生活希望之不存,使魯迅必須另辟蹊徑,繼續生活。
1926年8月22日,魯迅于離京前夕在女師大演講時說:“我們所可以自慰的,想來想去,也還是所謂對于未來的希望。希望是附麗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魯迅:《記談話》,閻晶明選編:《魯迅演講集》,桂林:漓江出版社,2001年,第45頁。“存在”可以理解為還原并皈依樸素的生命和生活本身,魯迅正是帶著所謂“存在之希望”遠赴廈門的,南下之行既暗含著收斂鋒芒、韜光養晦的企圖,也可視為返璞歸真、回歸日常生活的選擇。
二
1926年9月,魯迅從上海登船,次日來到廈門,就職于廈門大學。許廣平也啟程奔赴廣州工作。此時,魯迅已經遠離了北京的是非,雖然在廈大也為人事而煩心,但是魯迅畢竟算是逃離了政治風波的漩渦,開始了一段較為安逸閑適的學者生活。另一種慰藉源自愛情,在廈門的135天時間內,84封“兩地書”成為了他和許廣平友誼、戀情的見證。這種書信交往的方式,也使魯迅適時宣泄了內心的苦悶,使他的內心變得柔軟平和,沖淡了他對于外部現實的敏感和關注。
魯迅在廈門度過的是一段寧靜欣喜與落寞無聊相互交雜的時光。文風較為平和,思緒遼遠,對于日常生活、自然世界、親人朋友的回憶星星點點,落筆成文。“以眷戀、珍惜、傷感、感傷、了悟來替代那空洞而不可解決的‘畏’和‘煩’。”*李澤厚、劉緒源:《“情本體”是一種世界性視角》,《決策與信息》2011年第3期。即使偶爾向著現實投去一瞥,也代替不了對于往昔回憶的深情和專注。魯迅在廈門,一直未間斷地與許廣平通信,這些信件從側面折射出他的創作背景和創作心態。廈門是一個潛心作文的好地方,魯迅談到生活與創作的關系時說:“窮苦的時候必定沒有文學作品的……忙的時候也必定沒有文學作品,挑擔的人必要把擔子放下時,才坐下來做文章。”*魯迅:《革命時代的文學》,《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439頁。
與北京相比,魯迅的廈門生活大致是舒心的,既遠離了窮苦,“薪水不可謂不多”*莊鐘慶、莊明萱:《兩地書·集注(廈門-廣州)》,第21頁。,又遠離了繁忙:“我的能睡,是出于自然的,此地雖然不乏瑣事,但究竟沒有北京的忙,即如校對等事,在這里就沒有。……和在北京的天天提心吊膽,要防危險的時候一比,平安得多,只要自己的心靜一靜,也未嘗不可以,暫時安住。”*莊鐘慶、莊明萱:《兩北書·集注(廈門-廣州)》,第60-61頁。
愛情的力量,使魯迅的童心被喚醒,讓魯迅重新發現了自己身上那種溫柔細膩的情感,使得魯迅重新對樸素的日常生活投入熱情,并將筆觸重新伸向已逝的童年時光。與許廣平的通信中,魯迅常提及衣食住行等生活瑣事,展現出其親近于世俗生活的一面:“飯量照舊,這幾天而且更能睡,每晚總可以睡九至十小時;但還有點懶,未曾理發,只在前晚用安全剃刀刮了一回髭須而已。……此地的點心很好;鮮龍眼已吃過了,并不見佳,還是香蕉好。”*莊鐘慶、莊明萱:《兩地書·集注(廈門-廣州)》,第22頁。
但是,這種生活狀態對于一位精神斗士而言不免太過寂寥,魯迅多次在與許廣平的通信中提及其心無定所的游子心態:“此地四無人煙,圖書館中書籍不多,常在一處的人,又都是‘面笑心不笑’,無話可談,真是無聊至極。”*莊鐘慶、莊明萱:《兩地書·集注(廈門-廣州)》,第17頁。“其實此地對于我的身體,仿佛到好,能吃能睡,便是證據,也許肥胖一點罷了。不過總有些無聊,有些不高興,好像不能安居樂業似的。”*莊鐘慶、莊明萱:《兩地書·集注(廈門-廣州)》,第17頁
與此同時,由安閑而滋生的寂寞正是通向文學創作(尤其是回憶體文章)的一條正當路徑。回憶所需要的溫情由紛至沓來的信箋滋養,回憶所需要的寧靜與寂寞由廈門的地理環境孕育,由此,魯迅借助溫情和寧靜,打開塵封的記憶之門。如果一個人沒有深刻的溫情、深邃的寧靜和深切的寂寞,單為現實囂擾所累,很難說他能夠那樣徹底地進入到回憶的隧道中去。《朝花夕拾》中作于廈門的五篇散文,可以看作是魯迅遠離中心,寄身孤島的“閉關”之作。
人沉浸在具體而細微的生命體驗和日常生活之中,通過品味、珍惜和回首的方式,找尋情感之依、生命之根。它是“散步的時候偶爾在路旁折到的一枝鮮花,是路邊拾起的別人棄之不顧而自己感到興趣的燕石”*宗白華:《美學與意境》,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9頁。。日常生活是現實的存在,童年回憶是沉淀的存在。兩者相結合,便體現出魯迅欲從童真中搜尋意趣、從“存在”中尋找希望的真義。在《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中,有對孩童日常玩耍情景的細致描寫:“不必說碧綠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欄,高大的皂莢樹,紫紅的桑椹;也不必說鳴蟬在樹葉里長吟,肥胖的黃蜂伏在菜花上,輕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從草間直竄向云霄里去了。……”在我們十分熟悉的這段文字中,充斥著飽滿豐富的意象和蓬勃的生命氣息,作者以童年的視角,用簡潔明快的文字,對于百草園中的花鳥樹蟲等大大小小的生命,從視覺、聽覺、味覺上加以描摹,正所謂“萬物靜觀皆自得”。這些卑微、少為人們所關注的意象在魯迅筆下復活,與童年快樂時光相得益彰。
“人”是回憶中最生動也最深刻的因素,魯迅此時的散文中出現了人物群像:父親、長媽媽、衍太太、藤野先生、范愛農……父親早逝,在魯迅心中父親形象是模糊的,而《父親的病》中病痛纏身的父親形象復活,魯迅回首父親臨終前的一幕,流露出深摯的思戀之情和悔疚之意。少年無知般的喊叫打破了父親臨終時的平靜安詳,這成了魯迅永遠的隱痛。《父親的病》和《瑣記》中都出現了衍太太這個人物。作者以極簡的筆墨勾勒出鄰家中年婦女衍太太身上的戲劇性。她圓滑世故、口是心非,對自家孩子嚴加管教,卻慫恿鄰家的孩子們去“吃冰”、“打旋子”、“偷東西”……但是她的所作所為在小孩子眼里看來卻是莫大的善良和寬容。作者雖然被衍太太的流言所傷害,但是時過境遷,回憶衍太太的時候,怨恨已經漸漸消散,作者可以超然地一笑而過。剩下的只是對這個戲劇性人物善意的嘲笑,丑行蛻化為笑談,正如薩義德在談到自己回憶錄時所說:“寫這本回憶錄的主要理由,當然還是我今日生活的時空與我昔日生活的時空相距太遠,需要連結的橋梁,這距離的結果之一,是在我重建一個遙遠時空與經驗時,態度和語調帶著某種超脫和反諷。”*[美]薩義德:《格格不入:薩義德回憶錄》,彭淮棟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第5頁。
回歸童年記憶,回歸日常生活,魯迅的記憶之門和細膩情感完全敞開,在廈門的日子里,魯迅固然流露出被寂寞包裹的游子心態,但這種心態亦可成為溫情回憶的催化劑。走異路,逃異地,于他鄉,念故土,魯迅在南國寫就了一段柔軟而鮮活的童年詩篇。
三
1927年3月,魯迅南下廣州去中山大學執教,與許廣平及好友許壽裳同住廣州白云樓,將“舊事重提”這十篇散文集結成《朝花夕拾》,并在此完成了小引和后記。
魯迅來到廣州有與許廣平相聚的用意,但就魯迅的本心而言,廈門的生活太過消磨意志,適合于短暫休憩,不適于人生長久之計:“這里的惰氣,是積四五年之久而彌漫的,現在有些學生們想借我的四個月的魔力來打破它,我看不過是一個幻想。”*莊鐘慶、莊明萱:《兩地書·集注(廈門-廣州)》,第208頁。安逸生活太容易磨損人的銳氣:“我來廈門,雖是為了暫避軍閥官僚‘正人君子’們的迫害。然而小半也在休息幾時,及有些準備,不料有些人遽以為我被奪掉了筆墨了。……我先前對于青年的唯唯聽命,乃是退讓,何嘗是無力戰斗。”*莊鐘慶、莊明萱:《兩地書·集注(廈門-廣州)》,第194頁。去廣州,是為了愛情,是為了擺脫渙散的惰氣,更是為了在短暫停頓之后繼續在精神之路上前行。魯迅用了“野心”一詞形容他赴廣州的目的:“我還有一點野心,也想到廣州后,對于‘紳士’們仍然加以打擊,至多無非不能回北京去,并不在意。第二是與創造社聯合起來,造一條戰線。”但是,現實難遂人愿,魯迅來到中山大學不久,國民黨就策動了“四·一二”政變,畢磊等30多名中山大學學生被捕,魯迅多方營救無果。年過不惑的魯迅對于生命無常、世態炎涼早已深有感觸。“五四”時期發出“吶喊”聲的魯迅,此時無助地落入到無所歸依的“彷徨”情緒之中。
《朝花夕拾》小引中的文字寫于1927年5月,分別對于創作背景、命名原由、回憶的真實性等問題作了簡要的說明。此時,離“四·一二”事件距離很近,魯迅頗有虎落平陽、壯志未酬的“百無聊賴”之感:“看看綠葉,編編舊稿,總算也在做一點事。做著這等事,真是雖生之日,猶死之年,很可以驅除炎熱的。”“一個人做到只剩了回憶的時候,生涯大概總要算是無聊了罷。”
帶著積極的入世心態來到廣州,結果卻還是要返回到記憶洞穴:“帶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夠。”現實距離太近,是難于被歸納描述的,記憶須經過時間的發酵沉淀,經過空間的輾轉漂泊,才能彰顯出它的珍貴和魅力。記憶是一處避風港,以對逝去韶光的懷念,來對抗現實的死寂與灰暗,徘徊猶疑的生命腳步可以暫歇于此,以勵再行。
那么,記憶與昔日的現實又構成了怎樣的關系呢?魯迅舉了一個很形象的例子:“曾經屢次憶起兒時在故鄉所吃的蔬果,都是極其鮮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鄉的蠱惑。后來,我在久別之后嘗到了,也不過如此;惟獨在記憶上,還有舊來的意味存留。他們也許要哄騙我一生,使我時時反顧。”幻想的美妙總是悄然屹立于現實的庸常之上,當幻想唾手可得之際,人們才恍然大悟,覺得不過如此、意興闌珊。記憶也是想象的一種,是人對于過往生活有所選擇的想象。回憶的內容與實際情況有出入在所難免,“這十篇就是從記憶中抄出來的,與實際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現在只記得是這樣”。回憶被過濾、被沉淀進而成為了一種被美化了的、“理想性”的想象。
至于后記,作者寫后記的目的本來“只想尋幾張舊畫像來做插圖”,卻不料又寫成了一篇頗有點“掉書袋”意味的長文,“或作或輟地幾乎作了兩個月”。對正文中《二十四孝圖》的引用錯誤進行勘誤,對于《百孝圖》不同繪制者、編纂者的態度進行比較,贊賞胡文炳刪除“郭巨埋兒”一章的“勇決”,隱約批評了“紀常鄭績”先生“模棱兩可”態度——這自然與魯迅所一貫反感的“不徹底性、不純粹性”相呼應。后記還羅列了曹娥投江、老萊娛親、活無常等不同版本的插圖,對其來歷和典故娓娓道來,對不同作者的畫風一一點評,批評了世道的澆漓輕浮、以“肉麻”為“有趣”的低俗趣味,以及以“史料”冒充“學問”的不良風氣。
這篇后記“漫談式”的寫作風格,更像是一篇精心考據、精彩論證的雜文——是文體上的天馬星空,亦是情感上的疏離雜蕪。恐怕其原因仍是作者的寂寞:在史料上用力,是“很新穎的,也極占便宜”。這讓人聯想到當初辛亥革命落潮之后,魯迅對于佛經、碑拓的收藏和研究興趣。正是對于當下失去了興趣,才會對古跡萌發出興趣,主觀情感被客觀史料所淹沒。此一點,乃正是魯迅作此后記時的心境——如果說寫于北京的文章中還帶著點對現實的恨意,寫于廈門的文章中滿懷著天真雍容之愛,那么作于廣州的小引和后記,則流露出作者看盡滄桑、寵辱不驚的平靜和落寞。廣州見證了魯迅雄心之重燃至希望之幻滅的起落過程。希望之幻滅并不是終點,在情緒的低位上固然有令人沮喪的現實,也有痛定思痛后選擇新路的權利。
《朝花夕拾》,是魯迅創作歷程中的一個異數,但又是魯迅整體思想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正當他對當下的現實感到消沉無助、對未來的選擇感到迷茫恐慌時,他將思緒從社會轉入到自身,從現實轉入到回憶,卻又從未真正地遠離社會現實。《朝花夕拾》更像是魯迅思想進程中的一條“縫隙”,緩解了彼時魯迅的思想困境,它既是彷徨失落中的回望,也是重振雄風前的砥礪,沒有情感的波動和沉潛,也就沒有日后勇士的復出。
(責任編輯:王學振)
Field Transformation and Emotional Fissure inLifeisaMoment
LI Yan-shu
(CenterforSocialSciencesDevelopmentandResearchinInstitutionsofHigherLearning,MinistryofEducation,Beijing100080,China)
Written between 1926 and 1927,LifeisaMoment, initiated in Beijing, continued in Xiamen and revised in Guangzhou, was produced in the course of Lu Xun’s vagrant life journey, during which he had undergone historical events or personal encounters such as his being wanted by the Beiyang government, his acquaintance and love with Xu Guangping, his teaching experience in the south, and the counterrevolutionary coup on April 12, etc. The changes in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social events have replenished his prose with some emotional fissure, namely his dissatisfaction with and satire of the social situation embodied in his prose written in Beijing, the beauty of reminiscence mixing warmth with loneliness demonstrated in his writings in Xiamen, and his disillusionment of ambitions mirrored in his works written in Guangzhou. The switch of the perspective between reminiscence and reality is indicative of the diversity and complexity of Lu Xun’s thought during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period.
Lu Xun;LifeisaMoment; field transformation; emotional fissure
2016-09-03
李彥姝(1983-),女,遼寧大連人,教育部高等學校社會科學發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文學博士,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文藝美學和電影批評等研究。
I206.6
A
1674-5310(2016)-09-0018-05